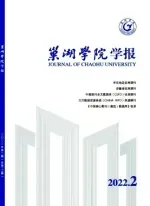论江有诰《诗经韵读》之成就与不足
荆兵沙 曹 强
(渭南师范学院,陕西 渭南 714000)
论江有诰《诗经韵读》之成就与不足
荆兵沙 曹 强
(渭南师范学院,陕西 渭南 714000)
通过深入研究江有诰的《诗经韵读》发现,其中得中有失,失中有得,失误中还包含着某些合理的因素。其成就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1.首次以韵读形式系统地展示出《诗经》的用韵情况;2.对《诗经》用韵研究多有发明;3.在处理《诗经》“合韵”上成就颇多;4.订正了段玉裁、王念孙等研究《诗经》用韵的诸多纰缪;5.能以音变理论审视《诗经》的韵脚字;6.分古韵为二十一部,对上古韵部体系的建构贡献良多。其不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对某些篇章用韵体例的理解错误;2.在《诗经》“合韵”处理上有缺失;3.韵字注音理论认识上有缺失;4.早期对上古声调的认识错误。
江有诰;《诗经韵读》;成就;不足;影响
江有诰,字晋三,号古愚,清徽州歙县(今安徽歙县)人。他认为顾炎武、江永、段玉裁等人所定的古韵部类的多寡与平入相承的关系都不尽与《诗经》音、《楚辞》音相合,于是继承段氏研究《诗经》韵的方法,将《诗经》305篇一首一首地分析其中的韵脚,审查其韵部,写成《诗经韵读》。《诗经韵读》是江氏研究古音学的核心材料,也是研究古韵必读之作。其中包含江有诰诸多古音学的理论,同时也是其古音学理论的具体实践。考察、分析和研究《诗经韵读》,不仅有助于全面了解江有诰古音学的理论,重新认识江有诰的古音学成就,而且对清代古音学的研究大有裨益。我们以江有诰的《诗经韵读》为基础,旁及其《群经韵读》、《楚辞韵读》、《廿一部谐声表》、《唐韵四声正》和《入声表》等著作,深入挖掘原材料,并与段玉裁的《诗经韵分十七部表》、王念孙的《古韵谱》和王力先生的《诗经韵读》等进行穷尽式地比较,总结归纳江氏的《诗经韵读》的得失。
1 江有诰《诗经韵读》之成就
《诗经韵读》创获颇多,总结起来,其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1 首次以韵读形式系统地展示出《诗经》的用韵情况
《诗经》是唱出来的“天籁”,是押韵的。系联归纳《诗经》的韵脚字,就可以大致弄清上古韵部的状况。自朱熹以来,学者不断系联归纳《诗经》的韵脚字,如顾炎武的《诗本音》,江永的《古韵标准》,段玉裁的《六书音韵表》,孔广森的《诗声类》,王念孙的《古韵谱》等。顾氏的《诗本音》考订《诗经》韵脚字的本音,但顾氏定古韵为十部,终不免有疏失。江永、段氏、孔氏、王氏则以韵谱形式展示《诗经》的用韵情况。而江有诰的《诗经韵读》将《诗经》三百篇一首一首地分析其中的韵脚,“于正韵者,○之,隔韵者,□之,其可韵而不必以为韵者,║之。”[1]第一次以韵读形式系统地展示出《诗经》的用韵情况。韵读比起以前诸家的韵谱更为优越。韵谱只把入韵字汇集在一起,而韵读则把用韵的背景材料一并呈出,诚如王力先生所说:“这不但更利读者,而且使读者能更清楚地看见古人的韵例,更确切地知道二十一部的分立是证据确凿的。”[2]《诗经韵读》对先秦古韵的研究以及对《诗经》的学习和研究都有巨大贡献。
1.2 对《诗经》用韵研究多有发明
江有诰虽未专文阐释《诗经》用韵的体例,但《诗经韵读》中对《诗经》用韵分析及《古韵总论》中的有关阐述已发凡体例。我们整理了《诗经韵读》中圈定的韵脚及《古韵总论》中的相关阐释,结果发现,江氏共列《诗经》韵式有常格不换韵式、变格换韵式、特殊韵式和无韵四大类,韵式共计51例。江氏总结归纳的《诗经》韵例格式已相当完备,对各种韵式的分析是可取的,对后人研究《诗经》韵式颇多启示。我们统计,王力先生的《诗经韵读》中共列韵式48例。通过二者比较发现,江氏所析《诗经》的韵式包括王先生总结出的全部《诗经》韵式,较王先生多“一句二韵”和“半句谐”等三种韵式。
江有诰不仅总结归纳《诗经》的用韵体例,而且还能以宏观的角度,系统地来研究 《诗经》押韵,并采用内证法,辨别韵和非韵,校勘《诗经》的用句。如《小雅·正月》第六章,顾炎武以“局”、“厚”韵,孔广森以“高”、“局”韵。 江氏认为“蹐”、“脊”、“蜴”押韵,并在“局”字下注“无韵”。 江氏指出“下六句,韵皆在次句之末,不应首二句异例,故不从”。[1]以《诗经》韵式整齐性的特点,否定了顾氏和孔氏对此章的理解。又如,《大雅·桑柔》第四章,江有诰认为“自西徂东”应为“自东徂西”,并以“西”字与“慇”、“辰”、“痻”押韵。 江氏的理由是《诗经》中八句交互押韵的都是第七句不入韵,并举 《沔水》、《十月之交》、《桑柔》、《板》、《出车》等诗篇为证据。江氏认为《桑柔》第四章同样是八句交互押韵,然而第五句“自西徂东”的“东”字与“慇”、“辰”、“痻”三字不能押韵,这是传写误倒的原因。[1]江氏言之凿凿,其观点为王力先生采纳。
1.3 在处理《诗经》“合韵”上成就颇多
江氏在处理《诗经》“合韵”上取得成就颇多,对音韵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统计,江氏的《诗经韵读》中,实际言《诗经》“合韵”的共99次,其中通韵67次,17种类型;合韵22次,11种类型;借韵10次,5种类型。[3]顾炎武从《诗经》本音出发,讲变音不讲“合韵”,段玉裁讲“合韵”不讲变音。[4]而江氏在借鉴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既讲“合韵”又能以音变理念审视某些“合韵”现象。江氏指出或考证了“合韵”字的异文及其校勘问题,并参照“合韵”,修正了段氏十七部的排列次序。江氏的“合韵”说是对段氏“合韵”说的继承和发展,他剔除了段说不合理的内涵,而给予更科学、更简洁的解释,使“合韵”说更具说服力。
1.4 订正了段玉裁、王念孙等研究《诗经》用韵的诸多纰缪
我们将江氏的《诗经韵读》与段玉裁的《诗经韵分十七部表》和王念孙的《古韵谱》进行了穷尽式地比较,结果发现,江氏的《诗经韵读》于段氏、王氏有匡补之功,其中订正了段氏、王氏的诸多纰缪。江氏对韵和非韵的辨别,较段氏、王氏高明;比段氏、王氏更注重同篇各章在韵式上的整齐性;对某些句子或篇章是否入韵,较段氏、王氏谨慎;分析句中字是否入韵时,较王氏谨慎;能择善而从,兼采段氏的某些观点;所析的韵式较段氏、王氏全面。此外,江氏在《诗经韵读》中多次提及顾氏和孔氏的看法,并以充足的理由,确凿的证据,否定了顾氏、孔氏的观点,纠正了两人的多处错误。
1.5 能以音变理论审视《诗经》的韵脚字
《诗经韵读》中有大量音注材料,是其古韵理论的实践。我们统计,《诗经韵读》中直音共计268字例,直音283个,652次;反切共计195字例,切语206条,520切次。江氏已认识到今音与古音不同,并能以音变理论审视《诗经》的入韵字。《诗经韵读》中于六处加注“如字”,有些韵脚本来相谐,江氏仍然加注读音,这说明江氏并非在今音读来不谐的地方才加注读音。我们将江氏所注的直音与陈第《毛诗古音考》所考的古音比较,二者有193字相同或相近,占江氏直音总数的72.01%,这说明江氏所加的注音是他心目中的古音。据初步观察,江氏注音目的是为便于初学者学习,注音时常常折中今古。江氏的注音除标明读音外,大部分注音具有以音表义的作用。
通盘考察《诗经韵读》中作为术语出现的58处“叶”字,都可以理解为“与……押韵”或“押韵的话应当读……”。据我们观察,江氏的叶音标准是他心目中的古音,他不注叶的韵字,就是他认为古今相同的音,他注叶的韵字,就是他认为古今不同的音。他的叶音本意是多音中选择一读,即说明押韵时涉及到多音字时,为韵字选择一个合于诗韵的读音。[5]
从中古等呼的角度,将《诗经韵读》中的被注字和注音字进行了全面比较,结果发现,江氏韵字下的注音有两呼四等,其中三等多于一二四等。通常学者们说,江有诰等古韵学家只求音类,不讲音值,这不是说在他们心目中就无假定的古读。据我们初步观察,江氏不是依据中古的开合系统来研究上古语音,他几乎每一部都有假定的古读,只是他不能用音标系统地拟定。他这种探求的精神值得肯定。
1.6 分古韵为二十一部,对上古韵部体系的建构贡献良多
江有诰精研顾炎武的《音学五书》和江永的《古韵标准》,在江永分部的基础上,析古韵为二十部,后接受孔广森的东、冬(中)分部说,析古韵为二十一部。江氏的二十一部之分,创获颇多。我们统计,《诗经韵读》中东部独用40韵段,中部独用14韵段;东、中部合用的共计4韵段,合用数仅占总数的7.41%。中部、侵部独用总数为51韵段,合用7韵段,合用数占总数的13.73%。如果略去可韵可不韵的2韵段,合用数仅占总数的9.80%。祭部独用55韵段,祭部与脂部、元部、支部合用总数为17韵段。祭部与脂部合用韵段占总数的17.91%,祭部独用韵段占总数的82.09%。缉部独用13韵段,合用3韵段,独用韵段占总数的76.92%;葉部共5韵段,独用4韵段,独用韵段占总数的80%。此外,《诗经韵读》中祭部独用55韵读,其中去声独用20韵段,入声独用21韵读,去声和入声通押的有14韵段。去声独用者和入声独用者共占全部的74.54%。这说明东、中、祭、缉、葉各部当分立。江氏著书时不知道王念孙的二十一部,也未见到段玉裁的《六书音韵表》,但他的支、脂、之三分,幽、侯二分,真、文二分与段、王二家不谋而合;脂、祭之分与戴震相合;祭、月相配,与戴、王二家之说相合。尤其是祭部的独立,其价值重要在于祭部独立而引起的古韵系统内部相邻韵部的局部性质变。另外,“缉”、“葉”二部的建立,江氏功不可没。江氏以考据为主,辅以审音,定古韵为二十一部,参照《诗经》“合韵”,修正了段氏十七部的次序,江氏的二十一部次序为:之、幽、宵、侯、鱼、歌、支、脂、祭、元、文、真、耕、阳、东、中、蒸、侵、谈、葉、缉。他的二十一部以音近为邻,始之终缉,环环相扣,反映了韵部远近的亲疏关系,其排列次序为王力先生等采纳,成为后世拟测古音的基础。
2 江有诰《诗经韵读》之不足
《诗经韵读》的不足,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2.1 对某些篇章用韵体例的理解错误
江有诰所析“半句互谐”式是错误的,我们观察,那类只是语音的偶合,而非诗人有意用韵。通过与段玉裁的 《诗经韵分十七部表》、王念孙的《古韵谱》和王力先生的《诗经韵读》穷尽式地对比,[6]结果发现,江氏对某些篇章用韵体例的理解是错误的。如《唐风·蟋蟀》第一章,江氏只认为“莫”、“居”、“瞿”韵,段氏、王念孙、王力先生都以“堂”、“康”、“荒”韵,“莫”、“居”、“瞿”韵,认为属于交韵。“堂”、“康”、“荒”三字,上古同属阳部,可以押韵。江氏以其不入韵是错误的。
2.2 在《诗经》“合韵”处理上有缺失
江氏将《诗经》个别本韵的篇章误认为“合韵”,个别本为“合韵”的篇章,却理解为本韵,个别地方舍《诗经》韵而取谐声归部,致使韵字归部错误等。 如《大雅·绵》第八章,江氏以“拔”、“兑”、“駾”、“喙”韵,他认为“喙”字,从彖声,古属元部,因此认为此章属祭元“合韵”。 验之以《诗经》等上古韵文及异文材料等,“喙”字上古当归祭部(王力先生归月部)。江氏依据谐声归部,误将此章理解为“合韵”。又如,《邶风·新台》第二章,江氏以“洒”、“浼”、“殄”韵,认为“洒”、“浼”二字古属元部,“殄”字从声,古属文部,此章属元文“合韵”。 按:“洒”字,《诗经》中仅此一见,《楚辞》等上古有韵之文亦不见入韵。“洒”,《广韵》两读:所卖切,汛也,卦韵;先礼切,灑扫,荠韵。《集韵》又增六切:苏很韵,惊貌,很韵;所寄切,汛也,寘韵;思晋切,灑也,稕韵;先见切,灑也,霰韵;取猥切,高峻貌,《诗·新台》有“洒”,贿韵;肃恭貌,苏典切,铣韵。从谐声偏旁看,“西”,《诗经》中入韵一次,江氏归元部,江氏的《谐声表》中,“西”声亦归元部。王力先生的《诗经韵读》中归“西”字为文部,《汉语史稿》中归“西”声为文部。《上古韵母系统研究》文中,王先生说:“‘西’字,依《说文》是与‘栖’同为一字,古文字学家释甲骨文仍用其说;按《诗经》‘妻’声的字入脂部,‘西’声的字入谆(文)部。”[7]但在《古韵脂微质物月五部的分野》一文中,王先生又说:“段玉裁、朱骏声以西声入文部(十三部屯部),江有诰入元部。我认为江氏是对的。高本汉把西声划归脂部,不可靠。”[7]而王先生的 《古代汉语·上古韵部及常用字归部表》中“西”字又兼入脂部和文部。[8]陈复华、何九盈二先生根据韵文材料及异文等,归“西”声为文部,并指出从“西”得声的“洒”字,也应该归文部。[9]据以上分析可见,“洒”字上古当归文部。江氏以“洒”字归元部是错误的。
2.3 韵字注音理论认识上有缺失
江氏在《诗经韵读·古韵凡例》中说:“字母之学虽出于后世,然实天地自然之理。今音虽与古音异,而母不异。 ‘索’,《中庸》作‘素’,而‘索’、‘素’同心母;‘曷’,《孟子》作‘害’,而‘曷’、‘害’同匣母;‘州’,《谷梁》作‘祝’,而‘州’、‘祝’同照母;‘毫’,《公羊》作‘蒲’,而‘毫’、‘蒲’同滂母;‘姬’,鲁人作‘居’,而‘姬’、‘居’同见母;‘登’,齐人作‘得’,而‘登’、“‘得’同端母;‘昧’,《左传》作‘没’, 而 ‘昧’、‘没’ 同明母;‘戲’,《大学》音“‘呼’,而‘戲’、‘呼’同晓母。 故注古音者,必从字母转纽乃确不可易。”[1]认为“今音虽与古音异,而母不异”,所以,江氏注古音时以三十六字母为纲。他的《入声表》以韵图形式呈现古音系统,声母也采三十六字母,说明三十六字母是他心目中的上古声母系统。江氏笃信“今音虽与古音异,而母不异”,理论认识上有失,在注音实践中就不能不犯错误,这是其古音学说的一大缺失。但据我们整理,《诗经韵读》中,江氏也非严格地以三十六字母为被注字注音,遇到舌上、轻唇和正齿音,无字可音时,江氏只好采用古类隔切;于个别字,江氏只注意到被注字和注音字的古韵部相同,对其声母是否相同,却无暇顾及;由于江氏自身方言的影响,被注字和注音字中有清音和浊音互作切上字,以及疑母、影母和云母互作切上字现象等,这些是江氏韵字的缺点,但从另一方面看,却为研究清代歙县方音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
受时代学术水平限制和历史观点的局限,江氏相信“古音多敛,今音多侈”的说法,他在《古韵凡例》中说:“佳与支、皆灰与脂、咍与之、寒删与元仙、谈与盐、去声泰夬与祭废、入声没屑与质、曷与薛、德与职,虽相去不远而敛侈迥异。戴氏谓“古音多敛,今音多侈”。兹悉取侈音而敛之,所以复古音也,亦以便人诵读也。”[1]江氏相信了戴震的“古音多敛,今音多侈”的说法,于“皆”、“咍”、“寒”、“删”、“谈”、“泰”、“屑”、“曷”、“德”等韵字,以 “脂”、“之”、“元”、“仙”、“盐”、“祭”、“废”、“质”、“薛”、“职”等韵字注音,志在于复古,而且便于诵读。例如(括号内为《广韵》的等、韵、呼。举平声以赅上去):
偕(皆开二),音几(脂开三) 哉(咍开一),音兹(之开三)枚(灰合一),音眉(脂开三)
岸(寒开一),音彦(仙开三) 慢(删开二),音面(仙开三)蓝(谈开一),音廉(盐开三)
哕(泰合一),音喙(废合三) 没(没合一),音密(质开三)噎(屑开四),音壹(质开三)
渴(曷开一),音朅(薛开三) 北(德开一),音逼(职开三)
王力先生据此批判江氏道:“他 (江有诰)以为之韵是古本音,于是硬说‘采’读此止反,‘来’音厘;由此推知职韵是古本音,于是硬说‘得’读丁力反。他以为祭韵是古本音,于是硬说‘带’读丁例反;以为歌韵是古本音,于是硬说‘皮’音婆;以为元韵是古本音,于是硬说‘叹’读他连反,等等。”[10]王先生的批评可谓一语中的。江氏相信戴氏“古音多敛,今音多侈”的说法,这是他理论认识上的缺失,所以,在注音实践中难免会出现将侈音注为敛音的现象。这与他所处的时代及当时的学术水平有很大的关系,江氏以前的学者注古韵文音多将侈音注为敛音,如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引沈重《毛诗音》:“南,协句,宜乃林反。 ”[11]其中,“南”字是侈音而“林”字是敛音。朱熹《诗集传》注《周南·桃夭》“家”字“古胡反”,[12]其中,“家”字是侈音而“胡”字是敛音。吴棫《韵补》:“展,张连切”,其中,“展”字是侈音而“连”字是敛音。陈第、顾炎武、戴震、段玉裁等人把许多侈音注成敛音。由于当时知识水平和历史观点的局限,缺乏比较语言学知识的古代学者看来,两个敛侈互押同部的韵中,选择其中一个作为正音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所以,江氏受时代学术水平限制和历史观点的局限,致使他的古音理论有失,这不能不说是江氏古音学的一大缺点。
2.4 早期对上古声调的认识错误
江氏早期坚持“古无四声”的说法,未能认识到声调的发展变化,为追求“声韵谐适”,[3]修改了小部分韵字的声调,这是江氏在理论认识上的缺失,也是其古音学理论的一大缺陷。同时我们也发现,江氏并非随意修改韵字的声调,据我们整理,江氏韵字下标注声调者,共计277字例,江氏改易声调的,共31字例,占总数的11.19%。也就是说,江氏为韵字标注的声调大多数是正确的。
3 江有诰《诗经韵读》的影响
《诗经韵读》的研究是很全面精到的,前代古音学家做过的工作,江氏几乎都重新做过,然而江氏并不是简单地重复别人的工作,而是更高、更深的钻研,取得的成就自然超过以前各家。段玉裁称赞江氏的 《诗经韵读》“精深邃密”,“集音学之大成,于前五家(指顾、江、戴、孔、段)皆有匡补之功”,[1]这些评价与事实相符,一点也不过誉。《诗经韵读》对治古音学者影响甚大。
以研究《诗经》的用韵为例,陆志韦先生称赞江氏说:“江有诰的《诗经韵读》最为适用,音理上也比较容易教人明了。”[13]陆先生于1948年作《诗韵谱》,文中陆先生多处兼采江氏对《诗经》用韵的理解,不同江氏之处,大多列江氏的观点以备参考。王力先生也认为“江有诰于《诗经》用韵,所定是基本可从的”。[14]王先生于八十年代又作《诗经韵读》,通过两部《诗经韵读》的全面对比可知,王先生的《诗经韵读》继承并发展了江氏的《诗经韵读》,王先生的《诗经韵读》中多处借鉴或采纳了江氏的观点。[6]李葆瑞、王显、李毅夫、史存直和邵荣芬等先生讨论《诗经》韵例时,也多次引用或参照江氏《诗经韵读》的观点。周祖谟先生曾说:“江有诰的《音学十书》是研究古韵必读之作”,[1]此言甚是,而江有诰的《诗经韵读》可谓必读中之必读。
江有诰参照《诗经》通韵、合韵和借韵,修订段氏六类十七部的古韵次第,以音的远近排列成,始之终缉,环环相扣的二十一部次序,反映出上古各韵部间音的远近关系,剔除了段玉裁“合韵”说不合理的内涵,使“合韵”说更具有说服力,为后来学者研究“合韵”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江氏以考古为据,辅以审音,以《诗经韵读》等材料证明东部、中部、祭部、缉部、葉部、真部、文部等独立的合理性。江氏的古韵分部及排列次序,理清了古韵部间的关系,成为后世学者拟测古音的基础。
江有诰早期坚持“古无四声”的说法,未能认识到声调的发展变化,为追求“声韵谐适”,修改了小部分韵字的声调。江氏经过反复深入研究后,敢于修正自己以前的错误,认为诗文中间有四声通用、合用的情况,明确指出“古无四声”说是拾人牙慧,指出古人实有四声,只是所读之声和后人不同而已,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的。[1]近年来,唐作藩先生通过对《诗经》全部297首、1134章有韵诗篇共1755个韵段的同调与异调相押材料进行分析、统计与研究,指出:“从《诗经》中去声独用、与平上声相押以及入声通押的情况看,上古去声的独立性还是很强的,至少在王力先生的古韵体系里属于阴声韵部的去声字在 《诗经》时代是已经存在的。”“从《诗经》用韵或用词来看,由于词义的发展、分化或词性的变化,在《诗经》时代已出现一字(词)异读的现象(有的是通过假借而产生的异读),其去声一读可能是新产生的。”[15]上古有平、上、去、入四声说,为后来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江有诰处于他的时代,“自奋于穷乡孤学”,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实属不易。总体而论,《诗经韵读》的成就远远大于其缺失。通过深入挖掘《诗经韵读》中的原材料,结果发现,《诗经韵读》得中有失,失中有得,其失误中还包含着某些合理的因素。这给我们很大的启示:研究江氏的古音学不仅要总结其得失,还应该更深入地研究其得中之失和失中之得,这样才能客观、公允地评价江氏的古音学成就。
[1]江有诰.诗经韵读//江有诰.音学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3.
[2]王力.中国语言学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3]曹强.论江有诰对诗经合韵处理之得失[J].汉语史学报(待刊).
[4]张民权.清代前期古音学研究[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5]曹强.江有诰诗经韵读叶音本意考[J].语言科学,2009,(5).
[6]曹强.江有诰诗经韵读与王力诗经韵读用韵之比较[J].宁夏大学学报,2009,(2).
[7]王力.王力语言学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8]王力.上古韵部及常用字归部表[C]//王力.古代汉语(第二册),1999.
[9]陈复华,何九盈.古韵通晓[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10]王力.诗经韵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1]陆德明撰,黄焯汇校.经典释文汇校[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2]朱熹.诗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3]陆志韦.诗韵谱序[A]//陆志韦.陆志韦语言学著作集(二)[C].北京:中华书局,1999.
[14]王力.清代古音学[M]//王力.王力文集(第十二卷)[C].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
[15]唐作藩.上古汉语有五声说——从诗经用韵看上古的声调[J].语言学论丛,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THE GAINS AND LOSSES OF JIANG YOUGAO’S RHYME ANALYSIS OF THE THE BOOK OF SONGS
JING Bing-sha CAO Qiang
(Weinan Teachers University,Weinan Shanxi 714000)
Through in-depth study of Jiang Yougao’s Rhyme Analysis of the the Book of Songs discovery,which shall in any errors,lost in something to make mistakes but also contains a some reasonable factors.Its was mainly in six areas:1.The first time,rhyme-time basis to systematically demonstrate the Rhyme Analysis of the the Book of Songs with the rhyme situation;2.On the"Book of Songs" with the study of more inventive rhyme;3.In dealing with"Poetry The"" Hop Dance"on the achievements of many;4.revised Duan Yu-cai,Wang Nian Sun and other research" Book of Songs"with the rhyme of the many defects;5.be able to tone change theories,"Book of Songs"to rhyme characters;6.Sub-rhyme for 21,right on the rhyme contribution to the Ministry of Construction of the system.The loss mainly reflected in four aspects:1.Rhyme style with some chapter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error;2.In the"Book of Songs,""Hop Dance"handling flaws;3.Rhyme the word phonetic theory,there is lack of understanding;4.Early on the ancient knowledge of the error tone.
Jiang Yougao; Rhyme Analysis of the the Book of Songs(《诗经韵读》); achievements; inadequate; impact
H113
A
1672-2868(2010)02-0073-06
2009-11-29
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项目编号:09JK073)。
荆兵沙(1977-),女,陕西蒲城人。渭南师范学院教师。
责任编辑:陈 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