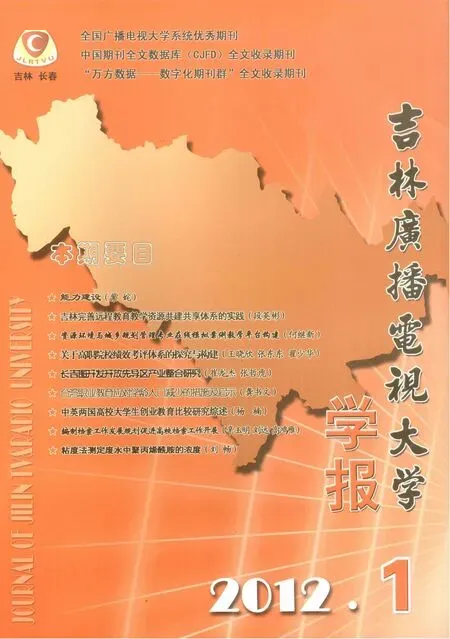有效辩护的实现机制
——以优化刑事诉讼中控辩审的权力 (利)配置为视角
魏琳涵
(郑州大学法学院,河南郑州 450001)
有效辩护的实现机制
——以优化刑事诉讼中控辩审的权力 (利)配置为视角
魏琳涵
(郑州大学法学院,河南郑州 450001)
在法官强制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影响下,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诉讼各方权力 (利)配置欠缺应有的科学性、合理性和民主性,审判权过于强大,控诉权运行扭曲,辩护权应受重视不够,所受限制较多,最终导致了行使辩护职能未能很好地实现。这些因素决定了我国更应当合理协调控辩审三方之间的职能关系,保障辩护权的有效行使。
辩护权;审判权;控诉权;有效辩护;优化配置
一、刑事诉讼中辩护权运行机制的理性思考
1、辩护权行使的自由度
辩护权的自由度是指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辩护时是否受到某种限制以及所受限制的具体程度。显然,任何国家的刑事辩护权都不可能完全自由,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受制于法官或者法庭。然而,在受限制的程度上,即辩护权的自由度上两大法系却大不相同。在英美法系,法官对辩护权的限制较少,其自由度较大,相反,大陆法系国家法官则对辩护权的行使有着诸多限制,辩护权的自由度相对较窄。
2、辩护权对审判权行使的引导力
辩护权对审判权行使的引导力指的是辩护活动是否推动审判进程以及推进效果。在英美法系国家,由于实行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辩护活动对审判具有的引导力很大。首先,审判的具体内容和进程由控辩双方决定。其次,辩护权的行使会对审判权的行使产生直接影响,辩护权行使与否,如何行使都会直接影响到案件的最终审判结果。在大陆法系国家,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是否辩护,如何辩护并不会直接严重影响审判进程和审判结果。其主要原因在于大陆法系国家都或多或少地掺有法官职权主义的色彩,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审判内容由法官决定,而非控辩双方决定。其次,是由于大陆法系国家审判进程的推进是由法官一手控制,在整个审判活动中,控辩双方都是配角,辩护仅仅是审判的辅助性活动。
3、两大法系的比较分析
基于对两大法系国家辩护权行使的自由度与其对审判权行使的引导力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辩护权运行的一般性结论:其一,英美式的辩护权运行机制有利于保护被告人的权益。作为刑事被告的公民个人及其辩护人能够享有较为有充分、自由的辩护权进行辩护,相应地司法机关也能够尊重和保障辩护权的行使。其二,两者查明真相的作用各有千秋。英美法系的特别强调法官 (包括陪审团)通过辩护方和控方的对抗性辩护 (即质询),并藉此加以比较、分析和研究,弄清案情,明辨是非,最终发现和认定客观事实真相,做出正确合理的结论,从而防止法官主观的片面臆断。反之,大陆法系的法官直接介入真相发现过程,控辩双方的法庭活动受到了严重的干预和限制,因而辩护活动难以充分展开,辩护对审判结果缺乏实质性的影响。总之,笔者认为,充分辩护更符合民主政治的要求,更有利于发现客观真相。
二、我国刑事诉讼中控辩审三方权力(利)配置对刑事辩护的的影响
从立法上看,我国庭审模式属于“强制权主义”或者称作“超职权主义”。主要是我们在查明犯罪、惩罚犯罪的整个过程中,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的各个环节职权色彩非常浓厚。这种超职权主义表现在我们的案卷全案移交制度上,就是当检察机关将起诉书和案件材料“全案移送”到法院后,法官就开始对案件书面材料进行审查,并进行积极主动地进行庭前活动。大陆法系是职权主义的,主要反映的是审判程序中法官的职权,而我们国家整个审查起诉和侦查程序都存在这个问题,所以称之为“超职权主义”或“强制权主义”。
实际上,我国刑事审判权的运行有违科学性和民主性也与人们的思想观念有关。在中国,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公安司法机关“进行”刑事诉讼,而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是“参与”刑事诉讼,这个就是本质区别。
1、审判权:在诉讼中过于积极主动,庭前介入有违诉讼民主
在我国,刑事诉讼以犯罪控制观为哲学基础,实行的是超职权主义模式,法官职权过于扩张,其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居于主导的支配地位,是诉讼的指挥者和控制者,他主动收集证据,讯问被告人和证人,被告在诉讼中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辩护活动难以有效展开,这显然不利如充分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此外,法官为有效开展法庭审判活动,单独在庭前开展一系列活动,通常在庭前就确立了内心确信,先入为主,明显有悖于无罪推定原则,违反诉讼民主性要求。
2、控诉权:庭前过于积极,庭中过于消极
第一,控诉活动庭前化。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控方在开庭前与法院通气,就起诉书认定的案件事实、法律的适用和法官审查案件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交换意见,以便达成一致意见。二是控方庭前可以向法官了解相关的审查意见,然后再根据要求补充相关证据或者材料或者将自己新发现的证据材料直接送交法官,而且通常并不采取公开正当的补送方式,而是私下送达,其结果往往导致法官有意或无意地倾向控方的主张,严重损害被告的合法利益。
第二,庭中控诉形式化。这既表现在法庭调查时完全消极,不举证、少举证,也表现在法庭辩论是极为消极,不积极论证公诉主张。显然,这种状况极为不妥,它违背了诉讼规律及诉讼程序设计要求,亟待改革。
3、辩护权:重视不够,限制较多
由于历史渊源、法律结构、思维方式和法官地位、作用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及其相应的辩护权运行机制主要存在以下缺陷:
第一,辩护权的行使在法庭调查阶段比较消极。在法庭调查中,调查证据实际上主要为法官所展开,辩护方很少通过提出、调查证据的方式论证自己的辩护主张,更未依靠对抗性的辩护权批驳控方的主张和证据。
第二,辩护权的行使受到相当限制。这既体现在法庭调查阶段,也表现在法庭辩论阶段。在法庭调查阶段,法官对辩护方的证据调查行为拥有批准权,法官决定是否同意辩护方提出的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重新鉴定或勘验的申请。在法庭辩论阶段,辩护的内容、时间都要受到法官的干预和限制,实践中辩护人针对控方指控进行的反驳,常以与本案事实无关或无证据证明等为由予以制止,致使控辩双方的对抗性活动难以真正、全面地展开,辩护权的作用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限制。
第三,律师介入诉讼过程过迟。虽然在96年《刑事诉讼法》中提前了律师及其他辩护人参加诉讼的时间,为充分行使辩护职能提供了时间保障。但是律师能以辩护人的身份介入在诉讼中却仍然是在提起公诉后,这样被告方很难进行有效的准备工作来收集有利于己的证据,也很难进行有效的辩护,与公诉方很难形成有效的对抗,从而导致辩护流于形式。
三、优化控辩审三方权力 (利)配置,实现有效辩护
笔者认为,对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中控辩审三方权力 (利)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应当通过立法者的程序设计来得以改革,这中改革的主导应是以避免诉讼职能的集中或混淆,突出当事人主义为主,职权主义为辅,建构一种新型的犯罪追究模式,科学合理地配置控辩审三方的权力 (利)。申言之,就是要弱化法官的职权作用,增强控辩双方的对抗,并完善相应的配套制衡制度与措施。
1、法官活动的限制。要建立起专门负责审查起诉的案件的审查机制,避免法官对案件的主管预断。通过各种途径阻断法官过早接触到案件,可以更好的使法官在庭审过程中兼听则明,对抗式的模式能更充分得以实现。
2、法庭调查应突出以控辩双方为主导,法官保持消极中立。在调查顺序要先控方后辩方,通过交叉询问的方式,使得法官查明事实的真相。法官不得实施过多的司法调查活动,避免法官的行为拥有太大的任意性和随机性。更多是赋予辩护方充分的辩护权,和拥有强大力量的控方形成事实上的平等对抗。当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弱化法官的职权作用是有限度的,绝不是完全照搬当事人主义,不能走极端。
3、减少对辩护权行使的限制。诉讼民主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和体现,其主要内容就在于保障人权,尤其是被告人权利。据此,应当赋予被告方充分的辩护权利。
4、完善相关制度的构建。如真正的建立“无罪推定原则”而不是一方面规定未经审判不得认定为有罪,另一方面又规定对侦查人员的讯问应如实回答的义务;建立起“起诉状一本主义制度”以此来实现司法权力运作之平衡目标,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双重目的。
最后,也是我们所要注意的,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法律文化,不是一件可以随意脱掉的外衣,它的历史惯性足以吧异质的诉讼模式打上折扣并将其改造得更接近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因此,我们在重建犯罪追究模式,合理配置控辩审三方的权力(利)的过程中不能忽视的就是要先转变公检法三方的诉讼观念,必须确立符合改革目标的新观念,正确认识控辩审三方权力 (利)的位置,防止“换汤不换药”的做法,只有做到让所有法律人在文化意识层面重视刑事辩护,有效辩护才真正能够落到实处。
[1]左卫民.价值与结构——刑事程序的双重分析[M].法律出版社,2003,(1).
[2]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 [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
[3]宋英辉.刑事诉讼原理 [M].法律出版社, 2007,(2).
D915.3
A
1008-7508(2012)01-0112-03
2011-12-19
魏琳涵 (1985~),女,河南巩义人,郑州大学法学院2010级法律硕士 (法学)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