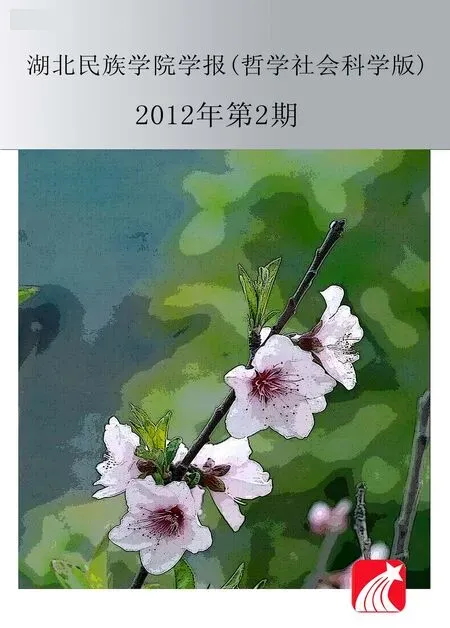国家话语的言语证据策略研究
——以《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为例
孙自挥,黄 婷,黄亚宁
(四川教育学院 外语系, 四川 成都 610041)
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所呈现出的能引起人的思想或感情活动的具体形状或姿态[1]。国家话语既是一个国家自我认定的国家形象的展现,又是一个赢得国际认知的传播活动。白皮书是一种国家对外话语,为了使其提供的信息为受众所接受,白皮书必然要对所提供信息的证据来源及其可靠程度加以说明。因为信息的认可离不开证据的支持,它们是确保白皮书客观公正、令人信服的资源保障。本文将通过对《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2009年中国国务院发布)中证据手段的聚焦研究,解读语篇中的证据手段的多种功能,探索它们在语篇中的认知编码规律,以期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个可行的分析模式。
一、理论框架
本文拟采用“言据性”(evidentiality)理论为研究框架。言据性是一个语言学范畴,取之“言之有据”之义,主要指语言运用者对信息的来源及其可靠程度在语言中的表达方式,反映说话人对所述命题信息的来源及其可靠程度与语言编码之间的对应关系[2]。言据性在语言中的表达形式称为言据性成分。Mushin从认知立场的角度来审视言据性,认为言据性的基本功能就是标示认知立场。当语言运用者在传达信息时,有必要为如何获取该信息采取一个立场,它是信息建构的一个必要部分,反映了说话人对信息来源的建构以及对获取信息的评价[3]。正是这个认知立场同其他因素的结合,导致了说话人在言说中采取特定的言据性表达形式。基于此,Mushin提出了言据性的五类认知立场:事实、报告、推论(包括归纳和演绎)、个人经验、想象。
本文将主要依据Mushin基于认知立场的言据观,并考虑到国家对外话语的语言特点,确定了以下言据性分析指标:事实、引证、归纳、演绎和信念。事实是指过去和现在所发生的事,在陈述事实时,说话人常常不使用特殊的话语标记,即所谓零标记。引证是指说话人通过语言从其他人那里获取信息的一种方式,如引用或转述原作或原作者的观点,常见的话语标记如“据某某说”、“某人认为”等。推理是说话人依据某些数据、前提等为出发点进行理性推导的过程,常有两种形式:归纳和演绎。归纳是基于已有的材料进行理性概括的过程,汉语中常用“显然”、“由此可见”等。演绎则是建立在某种已有的假设而进一步推理的过程,汉语的表达方式有“如果…那么”、“假设…一定会”等。信念是说话人自己的观念和判断,汉语中常用“我认为”、“我们相信”等来表达。依据上述有关言据性的分类,我们对《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中主体部分出现的言据性成分的使用频数进行了统计。为适应本研究的特定目的,我们的统计是基于命题而不是句子,以便避免重复。统计结果如表1。
二、分析与讨论
(一)事实
由上表可以清楚看到,该白皮书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言据性成分是事实,达76次,占统计总体的52.4 %,说明事实是作为白皮书证据来源的最主要方式。

表1 言据性成分统计表
注:频数是指出现次数;%是指各分项频数占全部项目总体频数的百分比。
例1:1959年至1960年两年内,西藏建立起几十个现代化小型工厂,培养了2万多名藏族工人。
白皮书注重事实证据,是由于事实的客观性使然。所谓事实,是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情或事件,“是不论我们对之持有什么样的看法而该是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东西,而不是由我们的思想或信念创造出来的”。罗素进一步认为事实“指的是使一个命题成真或者成假的那种情况”。[4]
命题,即句子所表达的内容或意义,是语言和现实最直接的接触面。刘易斯指出,命题最重要的属性就是它的真假,当一个命题是真的时,它的外延属性就是现实世界。因此,“一个命题的重要的外延属性就是它的真值(真或假)”[5]。一个命题只有在可以被证实为真或为假的场合下才具有意义。而证实的证据就是经验或现象,凭借这种经验我们可以判断命题为真或为假[6]。感知觉经验是我们亲临事物、真理、价值为我们而构成的那一时刻;它可以把客观性本身的真实条件告诉我们[7]。所以,如果一个命题可以依据由感知经验所获得的经验判据或与经验判据相关联而得到真值判定,那么它就是基于事实的真,是一个“事实真理”,即金岳霖所说的经验事实[8]。
中国政府白皮书中大量的历史和现状的事实描述,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在相当的程度上具有陈述事实的命题的特征,它们观察并记录了“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在西藏大地上的历史和现实事实或事件,这些事实或事件的发生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些语句所表述的命题直接与存在的事实相符,是身处这一情境的言语共同体对客观对象的实际直接感知的结果,是可以依据由此而得到的经验证据进行真值判定的。因为证据虽然不是事实本身,却可以视为形成事实的符号化方式,逼进事实的过程,具有“客观性”[9]。
正是事实证据的“客观性”,使其成为中国政府白皮书中被广泛使用的手段。以事实为依据,正是中国政府有关西藏问题的基本原则,因为,“要了解这个地区的真实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事实摆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西藏问题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白皮书·前言》.北京,1992年9月。当一副客观、真实、美丽的西藏画卷展示给世界时,整个世界都会为之动容。
(二)引证
引证也是白皮书中使用程度较高的言据性成分,主要表现为对有关西藏的其他文献或研究的引用,达52次, 占总体的35.9 %。Goldman等社会认识论者认为,知识未必完全是对外部实在的表达,而且还可以是一种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建立起来的主体间的信念,这种信念的获得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主体间相互交流的产物[10]。依据这种观点,知识是一种社会构建物,知识的产生主要来自群体而非个人。因此,知识的证据并非完全来自认知者的直接经验,还可以来自他人的可以信赖的陈述,如专家、权威的见解,学校的教育等。在当今的科学研究专业化、团体化时代,不仅普通人的知识依赖于权威的知识,就是专家、权威们的知识也是建立在对别的专家、权威的专门知识的依赖之上。Strawson指出,人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普遍共识:我们的知识的大部分、也许是绝大部分,都是来自倾听或阅读别人所说、所写的东西。事实上人们是把这些东西(虽然不是全部)当做真实的知识加以接受[11]。
我们注意到,在白皮书的众多引证中,有大量来自官方的统计资料、历史文档等。
例2:据17世纪清朝初年统计,当时西藏约有耕地300万克,其中30.9%为封建地方政府占有,29.6%为贵族占有,39.5%为寺院和上层僧侣占有。
在此处,引证是一个语篇中话语身份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得以建构的资源。在Kristeva看来,文本不仅是一个语言学现象,还是一个意义生产过程,是一个受到社会历史语境限制和关联的话语过程。现有文本与社会/历史的文本具有内在的关联,“将历史/社会插入到文本之中”,就是把过去的东西——已有的文本——改造成现在的东西,从而将社会/历史因素纳入文本视野之中[12]。一个文本的意义不完全是文本本身所赋予的,还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换。通过引用旧文本,新的文本可以获得知识方面的合法性,从而建立起自身话语身份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毫无疑问,通过大量引用官方统计资料、历史文档等,中国政府的西藏话语的合法性更有依据,更具权威性。
Mushin指出,普通人更加倾向于接受那些来源于权威的、值得信赖的、可靠的信息,比如专家学者、专业人士、可靠的媒体等。这些信息的发布者一般属于社会精英层。对社会精英地位信赖的心理作用,容易使信息显得更为可靠。对这些信息的引用、尤其是直接引用,等于是提供了“支持某人事实陈述的证据”[3]。来自这种渠道的信息越多,就越少受到质疑。
例3:英国随军记者埃德蒙·坎德勒在《拉萨真面目》中有详细的记载。他说,当时的西藏,“人民还停留在中世纪的年代,不仅仅是在他们的政体、宗教方面,在他们的严厉惩罚、巫术、灵童转世以及要经受烈火与沸油的折磨方面是如此,而且在他们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也都不例外”。
专业人士讲话的直接引用,无疑会大大加强话语的可信度。
(三)归纳
在科学论证中,对事实或现象的解释构成了一种重要科学认识方法——归纳。人们在依据感知觉的基础上借助理性思维, 从个别深入到一般而形成知识。从辩证唯物的角度来看,归纳作为人类推理的一种形式,并非纯粹是主观的产物,相反是具有客观基础的:即个别与一般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并通过个别表现出来,无个别即无一般。另一方面,一般与个别又紧密相联,一般只能存在于个别之中。因此,通过对个别的分析、概括,就可能从中归纳出潜藏于这些个别之中的某种共性, 形成关于该类个别事实的某种一般性原理, 这是符合认识的规律的,因为同类事物必然具有共同的一般性。
虽然有人质疑,认为由归纳证实得到的理论仅仅具有概率性或或然性真理,理由是任何理论都应包含普遍的命题,而在归纳中证实它们的证据却是有限的[13]。然而,不可否认,理论的普遍性来源于这个理论所反映的客观规律的普遍性,来源于人类实践的普遍性。也就是说,只要在相同的条件下,在相同的实践中,必定会产生相同的结果。例如,要证实“原子弹有巨大杀伤力”,人们无需要投掷所有的原子弹,只需投掷一、两枚,通过观察其造成的可怕后果就足以得出结论。由此观之,证据与结论之间的关系之所以是一种必然,是因为这个必然,并非单纯表示确凿程度的概念,而且还是一个与推论相联系的概念;不仅是一种事实上的、还可以是一种概念上的联系,不仅是一种物理-本体上的、还可以具有一种认识论上的联系[6]。
例4:现存的20世纪50年代初西藏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致热布典头目的一封信件称:“为达赖喇嘛念经祝寿,下密院全体人员需要念忿怒十五施食回遮法。为切实完成此次佛事,需于当日抛食,急需湿肠一副、头颅两个、多种血、人皮一整张,望立即送来。”达赖念经做法事要用人血、人头骨和人皮,旧西藏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的残忍和血腥由此可见一斑。
白皮书从达赖做法事要用人血、人皮和人头骨这些现象,完全可以归纳出农奴制的残忍和血腥。
(四)演绎
在科学论证中,一个论题的客观性不仅体现在论题的内容是对客观世界存在的陈述,还可以表达一种人们应该去做什么或怎样做的规范。基于某种理论(预设)进行推理而获得结论,这种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方式就是演绎。演绎是对预设的加工和推理, 也就是说演绎得到的知识是建立在预设的基础之上的,一般要求在预设中要提及相关的证据[14]。在演绎推理中,预设起着关键的作用。作为假说或背景知识的组成部分,预设是问题中确定的和已知的部分,是问题和答案的桥梁。根据莫里斯对预设的研究,预设可以分为两类:语义预设和语用预设。语义预设指从语义的意义或命题真值角度来考察和定义预设,此时预设的意义在于“为了使一个语句为真或为假,它必须是真的”[14]。因此,语义预设是一种意义上的联系,并且是狭义意义上的联系,用逻辑的术语来说就是:一个命题和它的预设必定相关联,当、且仅当该预设是真的。如下例:
例5:正是由于全民族信教和宗教首领执掌政教大权这一因素,导致西藏丧失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形势的能力。
政教合一的统治已被历史证明是落后的,它只会阻碍社会的文明和进步,这已是当今人类发展所形成的共识。由此可见,由一个语义为真的预设而演绎出来的结论,问题可以直接获得答案,自然就容易被接受。
如果说语义预设是使一个语句具有真值的条件,语用预设就是在语言交际过程中使一个语句具有恰当性的条件。所谓“恰当性”,指的是语句在当时的交际环境中是恰当的、合适的。语用预设更多的涉及了语言使用者双方的关系,涉及他们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因素,以及彼此协调的问题。在此时的交际中,人们主要不是以陈述与事件的相符作为判据,而更多的是看话语双方对事件背后的理据是否有共同的理解。哈贝马斯指出,一个成功的言辞行为,不仅要注重对客观事件作出陈述的真实性,看命题内容是否符合事实,更要关注命题形式是否符合交往世界的规范与准则,即是否“得体”和“恰当”,最为重要的是能够使交流双方都进入彼此认同的人际关系之中[15]。
例6:西藏许多上中层的开明人士也认识到,如不改革旧制度,西藏民族断无繁荣昌盛的可能。
尽管对该命题的真值性双方的认识可能会有差异,然而,由于命题的预设来自双方均可以接受的群体,因而这个命题在当时的交际环境中就是恰当的,也是有效的。可见,语用预设的价值就在于强调交流各方对事件的预设的社会性和普遍有效性,它与语义预设往往互补互辅,相得益彰,共同提高话语的交流性。
(五)信念
根据Chafe等的解释,信念是一种“知晓”的方式,不强调对证据的依赖[2]。这就意味着信念与信息之间不具有那么直接的联系。从信息与可靠性的关系来看,“信息越间接,可靠性就越低”[16]。
Nuyts首先注意到证据的主体间性问题,指出,如果证据是为包括说话者在内的一群人所共知,由此得到的认知判断就较为客观。相反,如果证据只是说话人一人所知,其得到的认知判断就更为主观[17]。由一群人所共有的认知判断通常比一个人的认知判断更为可靠,因为共有的认知判断可被视为一致意见,具有主体间性,而个人具有的认知判断知识仅仅局限于个人自己。证据的主体间性越高,其认知判断就越可靠。如果缺乏这种可靠性,就难以成为主体间认同的依据,难以让别人相信作出的解释和判断,从而容易导致交际失败。正因为信念证据的主体间性较低,在白皮书这种官方文件中较少使用。我们的分析文本中仅有两例,而且主要还是以反证的方式出现的。
结语
通过对《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中证据手段如事实、引证、归纳、演绎和信念等的统计和解读,本文分析了证据手段在国家话语中的多种建构功能,初步探讨了这些语言现象背后的社会、文化、认知等运作机制,展示了语言与人、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表明,全面正确地认识证据手段所蕴含的语言和社会意义,科学地把握其对语篇的动态建构作用,将有助于加强我国对外话语的研究,有助于重塑具有中国主体性的世界话语,使中国话语在国际舞台上更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陈佳璇,崔蓬克,胡范铸. 言者身份与修辞力量:国家形象修辞分析的问题[J].当代修辞学,2011(2):70-76.
[2] Chafe, W. & J. Nichols (eds.). Evidentiality: The Linguistic Coding of Epistemology[C]. Norwood, NJ: Ablex, 1986: 89-112.
[3] Mushin, I. Evidentiality and Epistemological Stance[M].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1.
[4] 罗素.逻辑与知识[M].苑莉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5] 涂纪亮.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涂纪亮哲学论著选 第一卷)[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6] 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7] Merleau Ponty, Maurice. Le Visible et Invisible[M].Paris: Editions Garlimard,1964.
[8] 彭漪涟.略论金岳霖关于事实与理论关系的基本观点[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6):20-24.
[9] 孟华.“言据性”与证据的符号性质[M]//第二届证据理论与科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上卷,2009.
[10] Goldman,A.Knowledge in a Social World[M].Oxford: OUP, 1990.
[11] Strawson,P.Knowing from Words[M].Dordrecht: Kluwer, 1994.
[12] 费尔克劳夫.话语与社会变迁[M].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4.
[13] 苑成存.对归纳职能评价的历史综述[J].学术交流,1994 (4):102-103.
[14] 周燕,闫坤如.科学认知的哲学探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5] 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16] Plungian, V. A. The place of evidentiality within the universal grammatical space[J].Journal of Pragmatics,2001(33):349-357.
[17] Nuyts, J. Subjectivity as an Evidential Dimension in Epistemic Modal Expressions[J].Journal of Pragmatics,2001(33):383-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