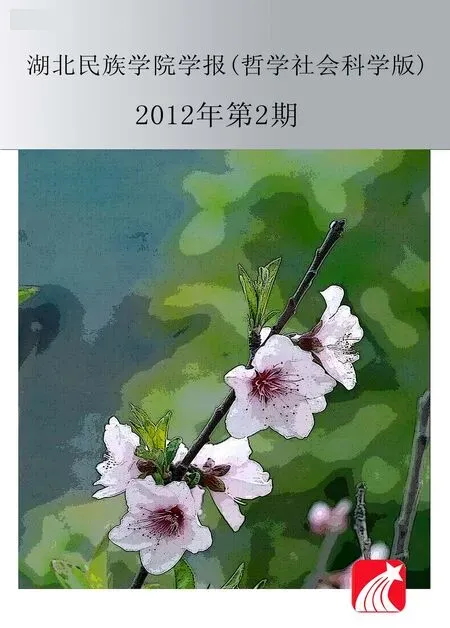目的论视角下的商务话语共同体建构
刘 辉
(黑龙江大学 应用外语学院, 哈尔滨 150080)
语言是人与动物分道扬镳的最后标志。两千多年来,为了揭开语言的神秘面纱,研究者分别从很多角度探索了语言的不同侧面。但是,“语言是什么,与语言密切相关的人和人的世界如何在如何是呢?迄今为止,语言学的回答让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分析哲学的努力失败了;日常语言哲学的研究让人看不到希望;欧洲大陆哲学的回答尽管不乏精彩、深刻,但是同样存在须要商榷之处”[1]。由此可见,语言的存在方式究竟如何?却是学者们仍无法回答的一个难题。
有学者认为,人类社会是由无数的话语共同体(discourse community)依照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s)而逐级构成的终极话语共同体[2]。那么,从逻辑分析主义的角度,我们可以认为话语共同体是构成人类世界的原子,商务话语共同体(Business Discourse Community)就是其中之一。斯威尔斯(J. M. Swales, 1990)认为,“体裁(genre)是有共同交际目的的特定话语共同体开展的结构明确的交流事件”[3],是话语共同体成员之间交流的基本模式,是划分话语共同体的基础。然而,体裁的确定又是以交际目的为主要参数的。因此,本文尝试以哲学目的论为基础,另辟蹊径,构建以目的(purpose)为基础的商务话语共同体,以期为商务英语话语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一、目的研究反思
学界普遍认为,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本体论、认识论和语言论。在近三千年的哲学史中,几乎每位大哲都或多或少有过对目的的论述。希腊先哲苏格拉底(Socrates)是最早用目的论来解释世界的学者,他和柏拉图(Plato)都认为,事间万物是神的目的的体现。“既然世界是这样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必然是照着理性所认识的,永恒不变的模型创造出来的”[4]。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第一个用哲学分析的方法对目的进行了分析。他以人的有目的的活动为依据,提出著名的四因说: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最重要的是,亚里士多德提出,达到目的必须凭借手段,而手段又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
到了认识论时期,康德(E. Kant)提出,人是目的。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目的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之一,是人的行为的根本属性”[5],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表现。他指出,“有理性者与世界的其余物类的分别就在于有理性者能够替自己立一个目的,人乃是世上惟一无二的存在者能够形成目的的概念,对有机的自然生物,必须进行目的论的考察,即用不同于机械力学因果观念的目的的观点来解释”[6]。康德强调了人作为有思想的有机体与其他生物的不同,在他看来这种不同就是人是有目的的,而在近代语言哲学家们看来,这种不同就体现为人的语言。
人与动物的区别就是人类拥有语言,目的的表达与实现都要依靠语言。因此,海德格尔(M. Heidegger)说“语言是人类的家园”,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说,“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然而,目的是存在于主体头脑中的一种观念形态,“是主体在认识客体的过程中,按照自己的需求和对象本身的固有属性预先设计的。它体现了对自身的需求与客观对象之间的内在联系”[7]。随着语言哲学(philosophy of language)的兴盛,哲学家们对目的的追问与探讨逐渐的外化为对语言的研究与认识,然而语言的复杂性与多面性使得学者们被迫进一步地细化研究范围。因此,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福柯(Foucault)提出,人与世界之间是一种话语关系,话语是唯一的在者(being)。这样,对目的的研究就转化为对话语的探讨,学者们尝试使用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的方法展现目的的表达方式与实现途径,反之以目的为基础来研究话语、行为与社会结构。廖美珍(2003)根据对法律互动话语的研究提出目的原则(principle of goal),将目的性视为人类的根本属性,认为交际是人类的存在方式,而交际都是受目的的驱动而产生的。没有目的,交际就没有意义,也就不存在交际。在这个意义上,交际的意义就是目的的表达与追求,而交际的形式就是话语。换句话说,话语就是人的存在方式。人通过话语出场,在话语的选择与使用过程中追求着自己的目的,同时与对方互动。因此,为了更好地研究人脑内部看不见的目的,我们就可以从外在世界可见的话语入手,通过这种外化的表现形式来推断内在目的的具体状态。
二、话语共同体解读
现代意义上的话语共同体思想来自于哲学、人类学和语言学领域的相关研究。有学者认为,话语共同体的形式理念主要来源于相对论者和社会建构主义者。也有学者认为话语共同体的形成吸收了福柯、罗蒂(Rorty)和后期维特根斯坦等的思想。目前,国外学术界对话语共同体的理论建构并不多见。赫茨伯格(Herzberg, B.)等学者对话语共同体的理论渊源仅仅是简单提及并没有详细论述(Hertzberg 1986,Fennell et al. 1987,Porter 1988)[8]。
目前,学界公认度最高的话语共同体定义是斯威尔斯于1990年在《体裁分析》(Genre Analysis)一书中提出的:话语共同体“是一个由具有共同目的、相互交流机制、特殊文体和专用词汇作为成员而组成的团体”[9]。在话语共同体中,语言使用是一种社会行为。话语是维持和扩展共同体成员共有知识以及吸纳新成员的手段。同时,话语也是成员共有知识的组成部分与认知方式,是共同体存在的基础。此外,斯威尔斯还提出话语共同体的6个区别性特征[10]:(1)话语共同体具有被广泛认同的常见的公开目的;(2)话语共同体的各成员之间具有相互交流的机制;(3)话语共同体运用这种交流机制作为成员之间交流信息的基本方式;(4)在交流目的的促进下,话语共同体使用并占有一种或多种体裁;(5)除了拥有体裁外,话语共同体还使用一些特有的词汇;(6)话语共同体的入门级成员要了解一定的相关内容和专业话语知识。由此可见,在斯威尔斯对话语共同体的建构中,各个特点之间是并列的关系。他认为,话语共同体是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而存在的社会修辞(socio-rhetorical)网络。
但是,斯威尔斯的观点也受到很多学者的挑战。我们认为,斯威尔斯(1990)只是归纳出它的6个特征,没有系统地论证这些特征的内在机制。伯格(Borg)认为,有关话语共同体的规模以及稳定程度等方面都还有待探讨。同时,口语的使用情况是否也该被视为话语共同体的特征之一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温格(Wenger,1991)为了强调共同体的社会性,提出了实践共同体(community of practice)的概念,旨在进一步强调成员之间的平等参与与共同合作。我们认为,话语本身也是一个社会性的概念,它就是语言在社会情景中的具体使用形式。人类的社会实践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是不能脱离话语而存在的,简言之,实践是通过话语实现的。只有少数的即时性实践可以通过肢体语言来交流,但是这种情况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占的比例微乎其微。
遗憾的是,话语共同体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应用语言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但是,对这个概念本身的建构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探讨。很多学者都在尝试不断地发展与完善这个理念,提出了交际共同体、实践共同体与地域话语共同体等各种概念。我们认为,话语共同体本身就是一个抽象的理念。他与具体现象之间的关系就尤如维特根斯坦探讨的红色与红色的东西之间的关系一样。他说,“红色的东西可以被消除,但是红色无法被消除”[11]。在现实的世界中,你可以拿出红色的笔、红色的本和红色的衣服,但是永远不能拿出一个红色展示给人们。话语共同体和现实的社会现象之间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鉴于此,话语共同体的规模与范围就无从谈起了。
廖美珍(2009)认为,“没有目的,交际就没有意义。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目的,没有对目的的追求,便不存在交际”。那么,我们认为,追求目的是话语产生的根本动力。很多人对同一个共同目的的追求就使得他们在一定的时空维度内构成话语共同体。因此,目的性是话语共同体的根本特点。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人是有目的的动物,在社会活动中,人为了追求目的就会将这种目的外化为话语。这个外化的过程就需要发话人根据受话人的情况选择专业知识,包括百科知识和文本知识(knowledge of texts)来构建话语,即构成话语的意义。众所周知,语言具有形式和意义二重性。话语作为语言的物质性的现实存在,必须拥有一定的表现形式。这种话语的具体表现形式在宏观上体现为体裁,在微观上就体现为词语。体裁是语篇的结构框架,词语是构建语篇的最小单位。人们会根据自己的交际目的,将语词在体裁的架构下组合起来,通过一定的交流媒介,如书信、电子邮件、电话和面谈等方式传播给受话人。受话人再通过逆向操作将话语回归大脑内部,再循环上面的过程,将话语再次传递给对方。多人之间的无数次的如此循环往复形成了互动。这些参与互动的人也因为他们所使用的话语而构成了话语共同体。整个过程如下图所示:

话语共同体构成结构示意图
我们认为,以上就是话语共同体的运作机制和构成方式。简言之,目的才是构成话语共同体的根本要因。在目的的驱动下,人们通过形式和意义两个层面对语言的选择与彼此交流而构成话语共同体。
三、商务话语共同体建构
“在我国,商务语言一般视为经商的手段,因此叫做特殊目的英语。其实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商务语言已经成为人类的基本存在方式,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地区、集体和个人发达程度的标尺”[12]。商务英语作为国际商务活动的通用语言已经逐渐进入国内外话语分析学者的视野。国外学者将商务英语视作一种机构话语,置于话语分析,甚至在多模态话语分析的框架内进行了详细的探索。很多国外的知名学者都与跨国公司合作,对商务话语共同体进行田野调查。他们获得了很多真实语料,说服力很强,科研与教学价值都很高。遗憾的是,在我国,商务英语更多地被视为一种语言技能而作为语言教学研究的对象。作为话语的商务英语研究可谓凤毛麟角,有关商务话语共同体的理论建构更是匮乏。国内的研究现状与当今跨国商务活动如此频繁的事实形成鲜明的对比,使得中国的商务话语共同体研究成为了一个相对空白的领域。
商务活动是典型的以目的为导向的活动,是人类日常生活中的基本活动。商务英语(Business English)是指应用于商务交际活动中的英语,是商务英语话语共同体成员在实际交往过程中,结合自身的主观因素和个体特征,遵循共同体的相关规约与准则进行有效沟通时所使用的符号系统。该符号系统参与构建商务英语话语共同体,并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其运行机制。在我国,主要在国际商务环境下,进行跨国商务活动时才会使用到商务英语。商务话语共同体就是由以商务合作为目的,通过各种媒介进行沟通的人群构成。在这个共同体中,成员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但是却很少在话语中直接体现出自己的目的。有时,“为了达到某种特殊的交际目的,发话人把原本可以清楚表达的意思故意使用不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13],因此,发话人通常采用间接言语行为(indirect speech act),而受话人多数情况下需要经过较为复杂的会话含义推导才能明确对方的目的。
既然目的是话语共同体构建的基点,我们认为以目的为基础的商务话语共同体建构与分析应以对目的的区分为基本出发点。在商务话语共同体中,人们对目的的追求较其他的共同体更为强烈。在这种目的的强烈驱使下,商务成员会调用大脑中的百科知识来构建话语内容,同时也会根据自己的文本知识对将要使用的体裁与词语进行选择。这些都是发生在发话人大脑内部的活动。通过这些语用选择,发话人的目的被外化为现实的话语,通过音响形式或文字符号表达出来。正是这些外化的话语体现着商务话语共同体成员目的的复杂性。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他们会采用复杂的手段,例如主动示好、打折让利、拉关系或是佯装生气等。这些都是他们基于自己的目的对已有共同体知识的选择。由此可见,商务活动自身的目的性为商务话语共同体的建构与划分提供良好的切入点。我们应当尝试发掘商务话语共同体的目的性基础,以此为标准对共同体进行划分,同时借助真实语料为佐证,剖析话语在共同体建构中的具体运作方式,展现商务话语共同体的具体存在方式。鉴于篇幅所限,我们将另辟专文论述,此处不再赘余。
结束语
著名生物学家乌克威尔(J. von Uexkull)曾经说过,在苍蝇的世界里,就只有苍蝇的事情;在海胆的世界中,就只有海胆的事情。这也就说明,世界是依据不同的主体来划定的,是以主体的意志(目的)为中心。语言哲学研究者认为,“在世界—语言—人组成的系统中,语言发挥着中介作用。正是凭借语言的帮助,人才同世界建立起联系”[14]。本文认为,由商务话语共同体—话语—目的(人)同样构成类似的框架,话语是连接二者的桥梁。同样,商务话语共同体也是以人的目的为主宰的。因此,我们认为,商务英语话语的研究应当是以目的为基础,以成员话语的分析为突破口,大胆借鉴哲学、社会学、民族志学和语言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而实现语言哲学、语言学与真实语料相融合的研究脉络。商务话语共同体的构建有助于提升我国的商务话语研究水平,指导国际商务实践,进而增强我国国际竞争的软实力,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同时为其他相关研究的发展提供新的参考与借鉴。
参考文献:
[1] 李洪儒.西方语言哲学批判[J].外语学刊,2008,(6):17.
[2] 严明.话语共同体理论建构初探[J].外语学刊,2010,(6):88.
[3] Swales,J.M.Genre Analysis: English in Academic and Research Settings[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45-47.
[4]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 古希腊罗马哲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67.
[5] 廖美珍.目的原则与交际模式研究[J]. 外语学刊,2009,(4):62.
[6] 廖美珍.法庭问答及其互动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364.
[7] 夏甄陶.关于目的的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3.
[8] Herzberg, B.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Communities[M].Paper presented at the CCC Convention, 1986; Fennell, B. Carl, H. & Carolyn, M. Mapping Discourse Communities[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CC Convention, 1987; Porter, J. The Problem of Defining Discourse Communities[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CC Convention, 1988.
[9] Cutting, J. Analysing the Language of Discourse Communities[M]. Oxford: Elsevier Science Ltd, 2000:1.
[10] Swales, J. M. Genre Analysis: English in Academic and Research Settings[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24-27.
[11] Wittgenstein, L.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 1958:28e.
[12] 严明.话语共同体理论建构初探[J].外语学刊,2010,(6):85.
[13] 李元胜.语用模糊策略的语境顺应性[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118.
[14] 刘辉.索绪尔与后期维特根斯坦:继承与超越[J].外语学刊,2009,(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