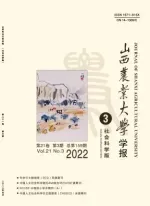浅谈大卫·希顿的 《道德经》译本的失与误
何晓花
(闽江学院外语系,福建福州,350108)
《道德经》流传两千多年以来,一直颇受中外学者的青睐。它仅五千余言,但文约义丰,博大精深,涵盖天地,被认为是中国文学殿堂的奇珍异葩。随着十六、十七世纪 “东学西渐”风潮的掀起,《道德经》开始不断地被翻译成各种西方文字。到2010年2月份为止,其西译本已达到643种之多,其中英译有206种。[1]这些译本不仅在风格上迥然相异,而且在质量上也良莠不齐。既有像理雅各的译本那样不仅能准确传达原文意思,又颇具音美和形美的神韵佳作,也有一些译文不仅在音和形上全无美感,而且在遣词造句方面也存在诸多失误。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本文主要从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方面讨论大卫·希顿的 《道德经》译本存在的失与误。
一、语言障碍
汉语是分析性语言,遣词造句深受中国传统哲学整体观、中国传统思维及半封闭大陆型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而英语是综合性语言,受西方传统哲学分析观、西方传统思维及其海洋型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因此两种语言的表现形式截然不同。这势必给翻译造成巨大的障碍,尤其是在英译 《道德经》这部集中国古代政治、军事、哲学、经济、文学和艺术于一体的 “天书”时,译者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词汇的通假现象和词汇深层意义的传递问题。
(一)词汇通假现象与误译
通假又叫通借,是古人用字写词时本有其字而不用,却用一个音同音近的字来代替的现象,即借甲字之音表示音同或音近的乙字之义,是古汉语书面形式的特殊现象,其特点是纯属表音,“凡同音的字都可以作为某音的音符,凡读此音的,随便写这些同音字中的哪一个都可以。”譬如 《尚书》中的 “曰若”、 “越若”用字均有不同;而 《孔子家语》中的 “望羊”, 《论衡》作“望阳”,《汉书》“欧阳”,汉碑作 “欧羊”。[2]
这种通假现象也普遍存在于 《道德经》的语言中,比如第5章的最后一个句子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其中,“数”通 “速”,是加快的意思,而 “中”通 “冲”,指内心的虚静。全句的意思是 “炫耀博闻会更快陷入困穷,不如守护内心虚静中和。”[3]但希顿的 《道德经》译本中这个句子的译文是"words go on failing and failing,nothing like abiding in its midst."[4]显然,“数”被误译为 “越”,而 “中”被误译为 “中间”。笔者以为应改译为"Much speech soon fails,and it is better to keep inner heart free"。第6章有“绵绵若存,用之不勤”之句。根据 《老子新诠》, “勤”通 “尽”,指用完。[5]全句的意思是“绵延不断,用之不尽”。但是希顿把这个句子译成"gossamer so unceasing it seems real.Use it:it's effortless"。[5]显然,“勤”被误译为“努力”。应改译为:"…Use it as you will,it will never run out."第49章的“德善”与“德信”中的 “德”也是通假字,通 “得”,是得到的意思。但是希顿却把这两个短语译为"such is the nobility of Integrity"和"such is the sincerity of Integrity",显然是不对的。应该改译为"get goodness"和"get truthfulness"。显然,通假字夹杂在汉字以表意为基本体系的古代典籍中,势必给译者带来相当大的障碍。要想克服这种障碍,译者应该对汉语有相当多的了解,参阅有关通假字的书籍,并反复推敲通假字和正字的对应关系,了解语音字义的变迁等。
(二)词汇的深层含义与表层翻译
《道德经》原文有意不在言中的情况,尤其是数词 (比如:“万物”、“万乘”、“百姓”、“五音”、“五色”、“五味”、“六亲”等)和形象比喻词 (比如 “刍狗”、“谷”、“朴”、“雌”、“雄”、“燕处”等)。这些词汇的表层结构之下负载着特定的内涵蕴义。译者在翻译这些词时应该透过表层结构去挖掘其深层意义,这样才能使读者真正领略 《道德经》深刻的思想内涵。但是希顿在这些词的翻译上过于拘泥于字面结构或只停留在表层含义上而导致表层翻译、欠额翻译甚至完全误译。
1.数词
《道德经》中的很多数词并非是用来实指数量的多少,而是表示模糊的概念,用在文中有其所指代的深层含义,但是希顿的译文对这些词的处理过于拘泥于字面结构。例如 《道德经》原文中频繁出现的数词“万物”被希顿译成"the ten thousand things"以及26章的“万乘之君”被翻译成"a lord having ten thousand chariots"显然不太妥当。因为这里的 “万物”是指天下所有的事物,而非实指一万种事物,而 “万乘”在文中意指兵车之多,而非实指一万辆马车。尽管英语中也有类似的表达法,用来表示夸张,比如"I've seen this film for a thousand times",但鉴于 《道德经》这部哲学经典集深刻的蕴义于简洁的诗化语言中,所以在这些数词上过于直译有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西方读者对原作思想的理解和把握。倘若说以上两个数词的翻译勉强可以采用直译,但是希顿的 《道德经》译本把原文出现频率也很高的另外一个数词 “百姓”译成" the hundred-fold people"未免太过于牵强,实不可取。正确的译法应为"(all)people"。再如《道德经》第12章的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中的 “五色”、“五音”和“五味”被希顿译成"the five colors"、"the five tones"和"the five tastes"也颇为不妥。尽管“五色”、“五音”和 “五味”在汉语中的确有所指对象,“五色”指 “青、赤、白、黑、黄”五种颜色, “五音”指 “宫、商、角、徵、羽”,“五味”指 “酸、甜、苦、辣、咸”五种味道,然而它们在文中分别是用来喻指华美的衣服、靡靡之音以及珍馐百味。[6]加上东西方文化对于色彩、音乐和味道的分类存在差异性,因此希顿的译文会让西方读者感到费解。笔者以为对于此类有指代含义的数词可采用意译法直指其抽象的深层内涵,或者是直译加注释法。这样可以消除因文化差异带来的理解障碍,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作的思想内涵。
2.形象比喻词
中国传统思维是一种注重观物取象、立象尽意、设象喻理、取象比类的形象思维。受到这种形象思维模式的影响,汉语在用词方面倾向于具体,常常以实的形式表达虚的概念,以具体的形象表达抽象的内容。[7]《道德经》就频繁使用形象的比喻词来表达抽象的哲学内涵,比如 “刍狗”、“谷”、“朴”等。这使得原本抽象晦涩的哲学思想变得形象生动。希顿对于这些形象词的翻译基本上都采用了直译法。例如,《道德经》第5章中有这样一个句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里的 “刍狗”就是一个形象比喻词,原指祭祀时用草扎的狗,往往用完就扔掉。在文中 “刍狗”喻指 “万物的生长完全是自然的,并非天地有什么人仁爱之心予以养护”。[3]这体现了 《道德经》“无为而治”的思想内涵。希顿把这句话译成"Heaven and earth are Inhumane:they use the ten thousand things like straw dogs.And the sage too is Inhumane:he uses the hundred-fold people like straw dogs."显然,把原文中的“刍狗”直译成"straw dogs",不仅无法再现原作的审美效果,而且使这个形象比喻词的深层含义在很大程度上遭受损失,因此无法向读者,尤其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西方读者,传达原文 “无为而治”的哲学思想。笔者以为这个词的翻译可以用直译加注释的方法:"Heaven and earth are ruthless,treating all things like straw dogs.The sage too is ruthless,treating people like straw dogs",并在页尾加上注释:"Straw dogs are dogs made of straw,which were usually used in ancient China when people offered sacrifice to gods or ancesters and thrown away after the sacrifice.Here,straw dogs are figuratively used to mean all things grow spontaneously,instead of being humanely tended by someone,which embodies Laozi's ideology of governing by doing nothing that goes against nature."这样既保留了原文的语言特色,又可以让译入语读者更好地领悟这个形象比喻词的深层含义以及原文所要传达的思想内涵。
二、文化差异
每种语言中都存在一些承载着特定文化内涵的词汇或短语,即文化词。这类词在其他语言中往往没有完全的对等词,这势必给翻译带来极大的困难。因此,在译语中,这类词的原语信息往往会被译者忽视或打了不应有的折扣,而导致信息度过小,读者得不到理解原文意思的必要信息,即欠额翻译。[8]希顿的 《道德经》译本中就有很多这样欠额翻译的现象,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 “道”的译文。“道”是老子思想的核心概念,在 《道德经》里共出现74次。“道”的本意是道路,但是 《道德经》全文中可作 “道路”解的地方只有两处:第41章的 “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类”和第53章的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大道其夷,而民好径”。尽管这两处的 “道”已有转义,但是转义跟本义几不可分。剩余72处的 “道”包含三层基本含义:万物的起源、自然法则、人类社会和行为的准则。显然这样一个意蕴异常丰富的概念,是不可能在英语中找到完全对等的词,因此企图用任意一个意思相近的英语单词来翻译 “道”的做法显然都是不明智也不可行的。但是希顿把 《道德经》里所有的 “道”都翻译成具有浓厚的西方宗教色彩的"Way",不仅无法使译入语读者正确地理解原文的思想内涵,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带来误导读者的负面影响,因此不妥,应英译为"Tao"。
再如 《老子》31章 “是以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此处的 “左”和 “右”也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在古代中国,以左为阳,右为阴;而尚左和尚右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种特有的仪式,因此这里的“左”和“右”与英语的"left"和"right"是有差异的,不能完全对等。因此,希顿译文把这两个承载着特定文化内涵的词译成"left"和" right",只是一种假象对等,无法向译入语读者准确地传递古代中国的文化原味。因此,更好的译法是在直译的基础上加上注释。
三、结语
由于 《道德经》是用玄幻的语言表达深邃的哲理,因此全文很多地方都存在意不在言中的现象,译者在翻译上如果过于拘泥于字面结构或只停留在表层含义上就会导致表层翻译或者欠额翻译甚至完全误译。为了避免表层翻译、欠额翻译以及误译,译者应该充分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参照并比较众多的注释本,在翻译策略上力求忠于原文。翻译不应仅仅是语言之间的转化,还承载着文化传递的使命。因此对于那些承载着特定文化内涵的文化词,译者在翻译的时候要更加谨慎,不能过于执着于字面对应的译法,否则不仅不能向译入语读者传达原文的思想内涵,而且容易产生误导读者的负面影响。
[1]KNUT WALF.Westliche Taoismus-Bibliographie(WTB)[M].Veriag DIE BLAUE EULE,Essen:Germany,2010:53.
[2]马天样.《古汉语通假字字典》前言[J].西北大学学报,1986(4):54-55.
[3]孙以楷.老子解读[M].合肥:黄山书社,2003:14.
[4]David Hinton.TAO TE CHING/Lao Tzu[M].Washington,D.C:Counterpoint,Washington,D.C,USA,2000:7.
[5]邓立光.老子新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55.
[6]邓立光.老子新诠——无为之治及其形上理则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69-70.
[7]narcissus2222.汉英语言对比第七讲抽象与具体[EB/OL].(2011-03-11)[2011-07-21].http://wenku.baidu.com/view/ca735163caaedd3383c4d3f2.html.
[8]方梦之.译学辞典 [Z].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