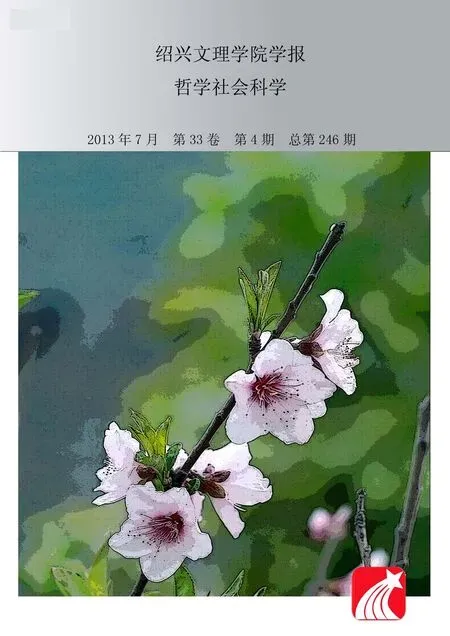古代书院环境理念探析
计丹峰
(安徽工业大学 思政部,安徽 马鞍山243000)
在中国古代,从扮演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功能来讲,与当代大学比较相近的是古代书院。早在1924年2月,胡适在南京发表《书院制史略》,指出古代书院为“国内最高学府和思想渊源”,并感叹“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1]。书院文化兴起于唐末,经五代、宋元、明清,历千年沉浮,至近代而断层。其思想丰硕,尤在人文环境的营造方面独具一格。本文从环境理念的视角来回眸千年书院,对其自然环境和人文理念进行重新探讨、阐发。
一、书院的选址之道与布局理念
(一)“避官、修身、塑心、筑学”的选址之道
从唐末起的数百年里,许多书院的建址就集中于名山秀水之中,如宋代四大书院岳麓、白鹿、嵩阳、石鼓等书院都建于名山脚下,风景怡然。如此一斑的选址,归因于几个方面。第一,书院的选址有意避开官府。在中国古代,教育机构主要分为两类:官学与私学,而书院正是隶属于私学一类。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由受国家主权机构主办,前者强调的是“学在官府、学术官府”,以实现“政教合一”,实为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而设;而后者强调的是“官师分离”“政教分离”,以实现“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其为社会或个人需要而设。这两者服务对象的本质差别让后者常有被统治阶级“排挤”“矫正”之闲,因而躲避官府是其一个重要原因。第二,静以修身,塑心养德。书院“深山老林式”的选址,其空气清新,风景宜人,有利于修学者修身养性,“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智仁们”见山光而净人性,阅湖水以静心境,把自己的人生情怀与大自然的壮丽风景交汇融合,寄情于山水之间,御天人而合一。第三,与其教育目的性紧密相关。古语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孟子·滕文公章句下》),“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荀子·劝学》)。环境之于人的影响具有强烈的自发性和隐蔽性。在封建社会里,如若要成就一番伟业,求学者必先要排除杂念,经历一番潜心的学习。因此,远离闹市,规避浮躁也是其选址重要考量范畴。第四,在一些学问高深的学者看来,求学之路一旦沦为科举的工具,就严重丧失了教书育人的本质。他们不浮于功名,而把做学问当做一种生活,所以求得一个安静避世之寓,筑学修书之所即可。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教学时曾勉励自己的学生:“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好去山头且坚坐,等闲莫要下山来。”[2]
(二)“崇德、重志、细腻、清雅”的布局理念
按功能性来分,不论是颇具规模的知名书院,还是寂寂无名的小书院,其建筑格局大体相近。第一,体现教育为主,德育并重的教育原则。依其建造格局而言,以其主体建筑为基准向内依次推进,书院宗祠等祭祀类建筑一般都安置在大堂和讲堂之后[3]。这彰显出书院的教学目的性,又不失尊师重道的文化精神,以及对师承理法、道德品质的重视。第二,体现醒人励志,注重实体功能的教育要求。从具体的形式来讲,书院的布局样式多样,以三合院、四合院居多,但基本都包括几个部分:讲堂、藏书阁、书斋、祠堂、庭院等,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其中讲堂是教学相长之地,其称谓常常极富个性,如广学斋、明志斋、清风斋等,这些名称皆为醒人励志而设,足见书院创建者对于“学生”志向引导的重视;藏书阁相当于现在的馆藏室,伏藏各式典籍要术,而书斋则是以备学生查阅和借读的阅览室;祠堂是供奉祭祀先圣之地,如孔子、孟子、孔明以及书院的一些先仕鸿儒。第三,体现细腻清雅,天人合一的释道追求。书院内庭是书院内的实体建筑之间的缓冲区域,如南阳卧龙书院的庭院,前后分别连接大殿和后堂,左右是明志斋、广才斋,既显得清雅自然又结构严谨[4]。书院创建者非常用心于细节的营造,彰显细腻精致。其常在庭院之中植树种花,精修假山奇石,清泉流水,尽显诗情画意;院落之间,青砖铺地,绿草茵茵,苍松翠柏,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融为一体,舒适怡然,清新悦目。唐代诗人曹唐在《题子侄书院双松》一诗中这样描写的书院的美景:“自种双松费几钱,顿令院落似秋天。能藏此地新晴雨,却惹空山旧烧烟。”
二、古代书院的“软环境”
(一)“诗浮于外,神孕其中”的楹联、书刻文化
在古代书院之中,为了营造优雅怡人的学习环境和氛围,近乎所有的书院内部都有形式多样、颇具人文气息的文字题刻。门厅院落、亭台楼阁之间有楹联、匾刻,尽显诗情画意,意蕴盎然;假山奇石、小桥流水之侧有碑刻、名篆,铁画银钩,笔力遒劲。如明代顾宪成创办无锡东林书院时撰下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意味悠长、传承至今;嵩阳书院大门的藏头联“嵩岳名山,阳城古邑;书藏万卷,院集群英”,更抒发了一方学府,英才齐聚的豪情。又如宋朝年间朱熹在白鹿洞书院的溪边的题刻、碑篆“漱石”“钓台”“意不在鱼”“清如许”等,仍富有浓郁的文墨之气,可谓“诗浮于外,神孕其中”。因此,它在整个书院中起到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装饰了书院的内环境,给院舍注入了“灵魂”,显得典雅庄重。
其次,这种文化往往代表了一段时期内书院的文化取旨、道德追求和学术方向。它在书院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文化的传递效应,让生活在周围的人感受先圣留下的文化脉搏,见贤而思齐。譬如长沙云山书院奎光阁联“彩笔自凌云,有万丈光芒上腾霄汉;高楼真得地,看千秋人物并壮江山”,鼓励书院学子要打好基础,须有真才实学,方能成就大器;又如安徽雷阳书院联“名教中乐地无涯,对山色湖光,足以荡涤胸襟,放开眼界;善学者会心不远,看鸢飞鱼跃,便是精微道理,活泼文章”[5],揭示了学术与生活的联系,道出了“深奥的哲理常常蕴藏在平实的生活之中”的真谛。因此,它常常以一种含蓄的方式,宣扬了书院的办学思想,或启人心智,或咏物言志,或激励学术。
第三,楹联碑撰文化在书院之中,是一种隐性的文化存在,它在润物无声的不知不觉的过程中,影响人的品性和思想,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其核心内涵应该在于它对成仁的追求,对道德的诉求,如白鹿洞书院的楹联:“日月两轮天地眼;诗书万卷对贤心”,劝人只有善读诗书,心无旁骛,才能领悟圣贤之心,净化人心,以达圣贤之境[6]。师生们逐渐地在长期的教学和实践的过程中慢慢形成一种富有共识的心理倾向和行为价值观。因此,它对学生树立自己的人生目标、激发前进的斗志、自省规范自己的行为都有重要的意义。
(二)“平等论辩,话语有榷”的讲会文化
讲会是古代学术产生、生存、发展、繁荣的一支重要的根脉,也是影响绵延至近代的重要学术交流的基石。宋代以来,学术的发展经历了数次高潮:从宋朝的程朱理学,到明朝的王阳明、湛若水心学,再到清朝的乾嘉汉学、实学。这些学术流派的形成与发展都与书院密切相关,都是通过书院的研讨研究、讨论交流得到传播和发展。因此,它是书院文化建设的一种重要独特的手段和组织形式,也是书院区别于一般学校的重要标志[7]。
书院讲会起始于南宋中后期,它以探讨学问为目的,展开学术辩论、研讨。各个书院常常独树一帜,积极组织并参与其他书院的讲会;各学派互相切磋,即使同一学派内部也经常出现不同的主张。讲会发展到明朝中期,其数量、规模都达到一个历史的高点,逐渐地演变为一种习惯化的制度,影响深远。讲会文化备受推崇,其核心在于它思想的自由性、形式的开放性、话语的平等性。无门户高低之见,无尊卑轻重之嫌,倚重学问之前提,崇尚学术之思辨,大有百家争鸣之风,取长补短之意。讲会之中,学生可以对“名师”提出疑问和不同观点,进行辩论,它鼓励学习者独立思考,敢于质疑批判,敢于突破权威。朱熹在讲学时注重“随问而答,略无倦色,多训以切己务实,毋厌卑近而慕高远,恳恻至到,闻者感动”[8]。它给予学术中“不同声音”一起讨论、思辩的机会,这样的环境下共同促进彼此学术水平的提高。从这一点上来讲,讲会中所涵盖的“讲会精神”是先进思想产生、交汇、迸发的不竭动力,它推动了整个社会上层建筑的新陈代谢,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世界性。
(三)“信仰塑造,道德践履”的书祭文化
书院祭祀活动最早见于宋代,其主要祭祀的对象除了孔子和儒家先圣之外,还包括各自书院相关联的“学术大家”和“先贤”以及在书院发展过程中劳有功绩的民宦、乡贤[9]。书院祭祀出自民间,却卓有不同。书院祭祀的成因更多的成分是秉承先人的师承教导,表达崇敬之情、学术认同及道德认同,而非民间祭祀纯粹宗教意义上的非理性的信仰。
书院的祭祀文化是一种多用于教育生徒的独特的教育形式,其核心在于“信仰的塑造,道德的践行”。对于生徒而言,“师傅领进门,修行在自身”,那么书院要“引领”的是:第一,对于尊师重道精神的认道,其包括先圣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宽仁的处世精神的认可与共勉;第二,对于信仰的塑造,包括对师承理法表达崇敬,对于学习目标的建立、榜样模型的形成;第三,对于道德的根植,对先贤表达道德认同,共勉于先贤们的宽厚仁德,形成自身的道德行为基准。
书院的祭祀文化是对学术精神的“符号传承”。至南宋起,许多书院的都将祭祀仪式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做,尤其把书院发展中曾独树一帜的“学术先贤”放到重要位置,作为标榜学院学术追求,达到“正道脉而定所宗”的目的。通常学派之间的区分就是通过祭祀的对象、过程得到体现。正所谓“非其师弗学,非其学弗祭也。”因此,书院祭祀被“仪式化”“符号化”,通过这样祭祀活动,让学生在仪式活动中受到熏陶,以先贤为榜样,涵养品性,陶冶情操,以规范学生的行为,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行。
(四)“灵活自主,自成一家”的治学文化
和公办学堂相比,书院在办学制度、管理体系上独立于政府规制之外,不受纳入政府的“官学体系”[10]。因此获得更大的自由度和自主性,也隐去了封建中央集权下学术环境不良的后顾之忧。
第一,教学带有明确的学术倾向性。书院的教学组织相较于官学,其形式较为活络,少有固化的“官派气”[11]。尤其在宋代年间,其学术教研方向具有突出的自主性和方向性。书院会把他们认道的那一支或几支学术流派作为学院教学的重点,有明显的学术倾向性,而非传统意义上为“科举出仕”为纯粹目的,很大程度上淡化了功利色彩。如宋代程颢一派就要求学生从十四五岁起,花三、五年来潜心学习,修学储能,掌握真才实学,而不求功利。
第二,开放式的交流学习环境。书院对于各类求学者都是开放的,不计年龄不论出身,不拘一格降人才,可谓“草野之芥民”“总角之童子”都可以“环以听教”,来满足学子们“寻道问学”的需要[8]。在各个书院之间,不仅仅学术大师可以通过讲学来达到交流的目的,许多书院的生徒更是可以灵活地游走于各书院之间,进行交流学习。这样,相对便利和频繁的学术交流在此基础上产生,不同派别的思想在此交错汇聚,擦出新的火花,给学术的发展和求学者个人道德修养境界的提高提供了较低的门槛。
第三,以人为本的管理制度。在学校的日常行政管理中,书院完全独立制定书院规章,管理分工明确。例如在山长以下,有副山长、堂长、讲书等职,他们各司其职,协助山长维持书院正常的教学秩序。在对学生学习管理上,其更注重调动学生的兴趣和自觉性,较少使用惩治学生的方式,而多以鼓励式的方式为主。例如,南宋时期的延平书院,有成文的考核标准,即每个月有三次小考试,对考试中取得好成绩的学生给予物质奖励。
三、书院软环境的当代启示
书院文化,陈酿千年,必有香醇之余酿可为当世所用。透过古代书院的“余香”,并结合当下教育的一些特点,笔者着重谈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书院软环境之自主研究的“研修精神”的重建。在宋朝以来,书院形成了一套具有“自动研究精神”的学术发展体系。胡适把书院的这种学术交流形式提到了一定高度:在胡适看来,所谓“书院的精神”,大致有三:一是代表时代精神;二是讲学与议政;三是自修与研究。而最后一点尤为重要。他说:“书院之真正精神唯自修与研究,书院里的学生,无一不有自由研究的态度[1]。如今,学术研究变成了某些人评选职称的加油站,程式化地制造所谓的学术成果。更有甚者,为了结果去反求符合其成果的证据体系,偏离了“学术”的正轨,也失去了学术的纯粹性和价值无涉性。
书院的学术精神是自发的:自修与研究;也是大众的,每一位书院的学生都有研究的态度,具有大众性和普及性。在当下社会,学术常常被视为是大学教授、学者的“阵地”,普通人民大众难有机会参与其中,然而“书院式的精神”却给予一种平等性的诠释:如若有研究精神,那么与之身份、地位无关。因此,笔者认为,应要让学术平民化,民间人士有机会进入学术圈,了解学术,参与学术,还“学术”于民。为此,书院的自主研究的“学术精神”的重拾对当下学术界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书院教育环境之“道德至上”教育宗旨的重提。当前,国内高校教育从教育的深度和广度上来讲,都到了历史的一个高点;但是,高校的道德水平却步入至历史的一个低谷。“复旦研究生投毒门”“南航金城学院宿舍门”等恶性事件频发却让人心寒。道德水平与教育水平的极不对称反应出两个问题:一是道德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放轻”;二是道德教育面临的瓶颈:包括教育内容、方法和评价体系与现实生活的严重脱离。书院环境下倡导的道德教化氛围(包括书院的祭祀、教师的表率)是以道德为核心,以成仁为诉求,在学生进入书院学习的过程中,第一重视的就是道德品质,其次才是文化知识。相较于当下高校教育的“唯成绩”“偏成绩”评价体系来讲,书院更重于人格、品德的培养。
因此,作为高校,首先在选拔人才的环节要重视“德育指标”,在评价人才的时候更要重视“德育分”。其次,面临道德教育瓶颈,高校所要学习的是书院的“道德践履”,一是教师的以身作则是最好的教科书,教师要避免工作、生活两张皮的纯职业状态,表里不一,使学生上行下效。再者,把书院的道德课程化的思考。高校要适当开设道德必修课、道德实践课等,把公益服务如敬老(服务老人)、助学(义务家教)、行孝(给父母行孝)等纳入课程体系,给予一定的学分,作为其社会实践和道德自修的必修课,要让学生亲身体会道德并不是“教师口中之词”而是“切身的践行”。
第三,“去粗取精,古为今用”下的书院文化精粹的传承与创新。古代书院在营造环境的方法、理念中,仍有许多优秀的观念,可以经过创新在当下教育中“古为今用”。譬如,透过书院关于学校选址、微环境的营造、楹联书刻文化、学术研究文化、生徒信仰教育、个性化教学制度等方面,我们还可以挖掘许多,如建立新的高校教育文化机制、高校隐性课程(文化)的开发与应用、高校人文环境的塑造与建设、大学生传统礼仪课程的设置、普通高校学生学术精神的培养等。
参考文献:
[1]胡适.书院制史略[J].东方杂志,1924(3).
[2]白雁.古代的书院[J].文化的印记,2011(11):14-15.
[3]田建荣.现代大学实行书院制的思考[J].江苏高教,2013(1).
[4]刘灏.从南阳卧龙书院的建筑特点看古代书院之职能[J].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11(3):86-89.
[5]冯刚,田昀.泉清堪洗砚,山秀可藏书——从楹联谈中国古代书院建筑的审美取向[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24-28.
[6]黄梅珍.从书院楹联看古代书院的价值追求[J].学理论,2011(3):158-159.
[7]陈元晖,尹德新,王炳照.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M].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141.
[8]毛礼锐.中国教育史简编[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
[9]赵新.古代书院祭祀及其功能[J].煤炭高等教育,教育史论,2007(1):94-96.
[10]朱汉民.中国古代书院自治权的问题[J].大学教育科学,2010(3):73-78.
[11]毛心娟,刘焕丽.宋代书院教学特点及其对我国大学教育的启示[J].文史研究,2012(0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