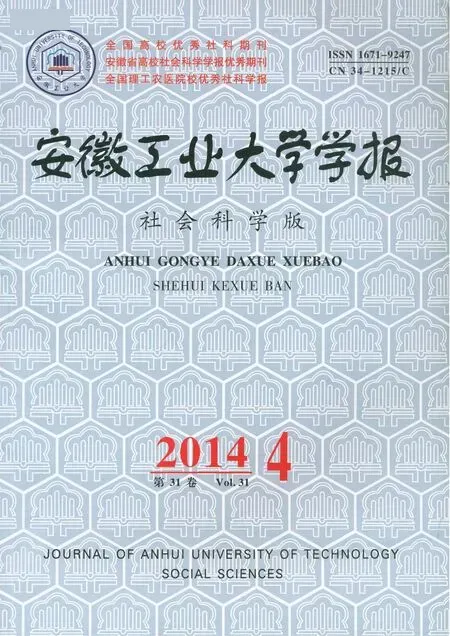论《福》对《鲁滨逊漂流记》的反话语重写
吴大志,雷 娟
(安徽工业大学工商学院,安徽 马鞍山243002)
后殖民文化理论中的反话语一直是后殖民文化视角研究的焦点之一。早期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就将其阐释为“审查欧洲话语对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殖民统治中所强加和维持的文化符码”。[1]对殖民话语的颠覆和对殖民文化的反抗,即是反话语实践的主要表征。如果说《鲁滨逊漂流记》是对殖民文化的英雄主义美化和歌颂,那么J.M.库切的《福》则是对殖民罪恶真实的重现和对帝国权威的颠覆。“要达到真正的理解殖民,必须去除掉欧洲话语所强加给东方的文化符码,解构这些文化符码的背后作为支撑的殖民话语体系”。[2]因此,反话语的叙事写作即成为阐发边缘群体渴求的必要手段,也是解构后殖民文化理论和后殖民文学作品的重要策略。
《福》是J.M.库切的第五部小说,也是库切成名之后的一部扛鼎之作。它是“一次回溯的行动,一次用新鲜的眼睛回溯的行动,一次从一个新的批评的方向进入旧文本的行动”。[3]所以,《福》的创作并非简单的回归经典,而是将殖民主义的典型文本置于南非的后殖民语境中进行审视和发掘。这样,库切的反话语重写看似具有破坏性,偏离了笛福笔下的早期殖民探险故事的主题,而实质上则对殖民霸权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并在建构殖民地“他者”形象的同时,力图挑战殖民权威。反话语的策略旨在颠覆殖民权威,在此策略下,故事的叙述者和故事人物的关系既对立又同谋;因此,星期五的沉默和苏珊·巴顿的抗争不仅折射殖民时代南非的社会冲突,而且打破了殖民扩张的英雄形象。事实上,库切假《福》之名,以言抨击殖民霸权之实。
一、同名主人公的比照
从情节和人物的布置上来看,《福》是对《鲁滨逊漂流记》的戏仿(mimicry),这种戏仿是反讽性的颠覆。虽然笛福笔下的鲁滨逊被视为欧洲文明人精神的象征,也为殖民征服提供合理的精神基础,但是库切却让鲁滨逊·克鲁索(下文简称克鲁索)丧失了英雄的气概和求生的渴望。比较主人公所处的环境及其精神状态和行为的差异,有助于进一步深入探析库切对经典文本的反话语重写的主题和意义。
首先,同名主人公的境遇的对比可以看出两位作家的出发点和终结点的差异。笛福所塑造的鲁滨逊,作为18世纪英国经典冒险小说人物,是殖民时代新世界的拓荒者。新土地上充满生机,物产丰富,在奇遇和探险中鲁滨逊凭借海难中剩下的零星工具、枪、种子和《圣经》开始了在富饶新大陆的殖民征服活动。工具和枪象征了西方先进的科技文明,种子代表了西方殖民霸权的欲望和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而《圣经》将殖民者的形象推向文化超越的合理优势。“鲁滨逊代表了一种征服者的形象,代表着欧洲的自我,是未来、文明、理性、语言和权力的代名词”。[4]显然,笛福的立场体现了西方早期殖民者之维,代表殖民霸权言说。《福》中海岛和土地贫瘠不堪,没有魅力无穷的美丽沙滩,没有能让沉船遇难者解渴避暑的小河,没有甘甜的水果,而主人公面对的则是“一座平顶的巨大的岩石山,突兀地从海中升起,只有一边点缀着从来不会开花和遮蔽它们的叶子的灌木丛,毫无生气,海岛外面生长着棕色的海草,被海浪冲到海岛上来,散发着有毒的恶臭”。[5]7库切出发点是剥夺“海岛”的殖民合法性,打破殖民“自我”的霸权形象,旨在通过后殖民反话语重塑颠覆殖民言说。正是基于不同的写作初衷,两部作品趋于不同的创作终结点: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为西方殖民掠夺提供了充分理由,该作成为英语文学传统的开启者和西方以理性文明对野蛮种族展示其优越性的文本宣言;库切的《福》以怀疑的态度对待西方殖民霸权,通过人物重塑和环境重置,达到了对文本化帝国话语的提前消解,这样重构了《鲁滨逊漂流记》所建立起来的探险英雄的形象。
其次,主人公在岛屿上精神世界的对比和被救赎之后内心的对比分析有助于观照库切在《福》中的反话语策略。一方面,笛福的鲁滨逊充满工作热情,他28年来永不放弃和为获救奔走的不断进取精神,让他具有一身英雄气概;他的探险精神和对星期五的仁慈教化又给他以正义和文明的光环,这样他对荒岛的占有就诠释了必然的伦理性。鲁滨逊的精神是欧洲殖民者文明身份的象征,也为殖民活动和以后的资产阶级的工作伦理提供了精神基石。库切的克鲁索却因多年的与世隔绝放弃了获救的欲望,他沉浸在孤岛狭小的王国里不能自拔,进行着荒谬又徒劳的工作,消极的工作并不在于给土地撒上种子,而是“清理土地和堆石头,虽然这远远不够,但总比无所事事地空坐着要好得多”。[5]33这种怠慢的劳动缺少价值目标,是对欧洲殖民征服和资产阶级工作伦理的颠覆与削弱。另一方面,获救之后笛福的鲁滨逊回到英国,如入佳境,不仅重获一切还得到一个海岛作为奖赏,这又一次成为欧洲殖民权威能战胜任何困难和异己的有力证据,刺激了殖民欲望。库切的克鲁索已经习惯于海岛生活,从内心里拒绝获救,当离开岛屿时不断地进行着内心的挣扎,因为“被救出的克鲁索对世界来说,会是一种深深的失望”。[5]35库切也戏剧性地改掉了故事的结局,克鲁索在被迫离开海岛的路上死去。《福》完成了对殖民帝国主义和殖民者形象的重新刻画,其在后殖民语境下的反话语的典范改写实现了对殖民霸权的颠覆。
二、反话语视角下颠覆的价值
笛福的名字原本叫“福”(Foe),在1695年他自己在名字前加了“De”(贵族的标志),自此就叫笛福(Defoe)。Foe在英语里意为“敌人、仇敌”,库切以《福》(Foe)为名寓意深刻,隐含着受苏珊委托书写的作家福(即笛福)与无声的他者星期五的对立,以及男性作家福与女性叙述者苏珊的对立。正是这两种对立关系揭示了《福》对《鲁滨逊漂流记》的权威性和可靠性的颠覆。星期五和苏珊与叙述主体中心的对峙,映射出《福》反话语颠覆的价值意义。
星期五的沉默是《福》中压倒一切的叙述力量。《鲁滨逊漂流记》中的星期五接受着鲁滨逊的语言和驯化,一切都从被鲁滨逊救起开始任人摆布,既没有言语的欲望也没有言说的必要,因为故事都是从其主人鲁滨逊口中倾倒而出,鲁滨逊与星期五的主仆关系是理所当然的事。而《福》的故事是由苏珊口述作家福书写而成,星期五(在《鲁滨逊漂流记》中的星期五是加勒比有色人种)是被割掉舌头的黑人。在白人殖民者看来,星期五显然是不入主流的“他者”。后殖民批评家艾勒克·博埃默则这样定义主体之外的“他者”概念,“‘他者’指主导性主体以外的一个不熟悉的对立面或否定因素,因为它的存在,主体的权威才得以界定”。[6]库切通过建构他者星期五的形象,不仅巧妙地把经典故事背景迁移到非洲,把矛头直指欧洲的非洲殖民史,而且还让星期五作为沉默者的形象出现。星期五的沉默弥漫着整个故事,深刻表征了被剥夺了言说权力的南非黑人的集体沉默;同时,“星期五的哑巴可以被读作在种族环境下被黑人所内化的无法表达的精神伤害”。[7]虽然星期五失去了舌头,并不表明他失去了语言。事实上,沉默更是一种反抗的方式,它是对异族文化侵入的抵制和消解。它表现出一种巨大的反抗力量,因为“遭受痛苦的身体本身就拥有一种权威:这就是它的力量”。[8]语言在构建主体性特征方面具有核心功能,库切的高明之处并不是让他的人物发出自己的呼声,而是让他们沉默以待,可谓“此处无声胜有声”,因此“星期五的无声是无助的无声,是对殖民者无声的谴责。”[9]这种无声构建了反话语的强大力量,颠覆了殖民文化中的西方话语霸权,为“他者”言说打开了空间。
女性主义叙述者苏珊的“他者化”抗争也是阐释库切反话语策略的另一视角。《鲁滨逊漂流记》是鲁滨逊的自我叙事,这也印证了殖民文学中男性是权力的中心,女性处于边缘地位,失去言语权,所以整个故事没有女性角色的出现。库切深谙这一点,在对经典文本的改写中,他有意以边缘弱者的白人女性苏珊的口吻讲述另一版本的克鲁索的故事,让作家福记录书写。苏珊越是要求话语叙述的“真实性”,越是不能实现女性真实性自我,她只有借助父权社会体系下权力的主体代表作家福去实现,所以苏珊的故事只能通过重新的“解释”才能迎合社会的认可;这种声音虽然来自女性,却不能完全像主体言说者那样自由言说。话语事实上是权力的一种运作方式,福对苏珊的“真实性”的否定,实际上是对女性谋求独立建构自我的否决,苏珊也沦为弱势的“他者”境地中不能陈述自我的女性代表。200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中这样描述:游戏式的寓言小说《福》把文学与生活的不兼容性和不可分离的特质编织在一起——那女人渴望成为小说的主人公,而在生活中却只是籍籍无名的小人物。[10]这样,非洲黑人星期五与苏珊的文本内容形成了鲜明的类比。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交相呼应下,女性他者的抗争和被压迫种族的言语潜能的释放欲望让《福》透射出库切反话语重写经典的真实用意和剑芒所指。
三、结语
《福》对《鲁滨逊漂流记》的反话语重写作为“经典的反话语”样本,具有重大的颠覆价值。它从后殖民视角解读欧洲经典文本,揭示了欧洲殖民叙事之下的权力话语,解构了殖民宗主国视角,释放了殖民地土著人的“他者”言说潜能。正如库切本人所言,“《福》不是从殖民主义或权力问题的撤离,‘谁写作’的问题,谁占据了权力的位置”。[11]在颠覆经典的反话语过程中,颠覆是库切对殖民主义权力体系的挑战。诚然,克鲁索的命运和抉择是库切的蓄意安排,星期五的沉默和苏珊的抗争也是他反话语写作的技巧布局,旨在为弱势“他者”释放言说潜能。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交织中,《福》给人留下多重意义符码的印象,阐释性空间无限延伸。
[1] 罗钢,刘象愚.后殖民文化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313.
[2] 高文惠.后殖民文化语境中的库切[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217.
[3] Susan Vanzanten Gallagher.A Story of South African:J.M.Coetzee’s Fiction in Context[M].Cambridge 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173.
[4] 张勇.殖民文学经典与经典改写[J].国外文学,2011(1):154-155.
[5] J.M.Coetzee.Foe[M].New York:Penguin Books,1987.
[6] 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M].盛宁,韩敏中,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22.
[7] Dick Penner.Countries of the Mind:The Fiction of J.M.Coetzee[M].Connecticut:Greenwood,Westport,1989:124.
[8] J.M.Coetzee.Doubling the Point:Essays and Interviews,ed[M].David Attwell,Cambridge 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248.
[9] 王敬慧.永远的流散者—库切评传[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44.
[10] J.M.Coetzee.等待野蛮人[M].文敏,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215.
[11] Tony Morphet.Two Interviews with J.M.Coetzee 1983and 1987[J].Triquarterly,1987(62):454-464.
——评《后殖民女性主义视阈中的马琳·诺比斯·菲利普诗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