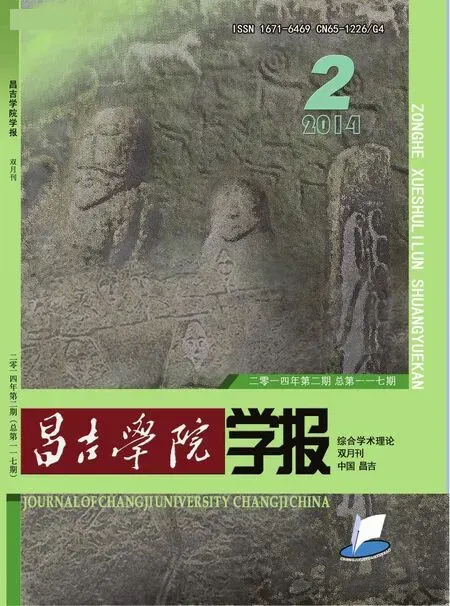污染力与女性:人类学视角下的月经禁忌
——基于闽南山河村的考察
张小红
(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污染力与女性:人类学视角下的月经禁忌
——基于闽南山河村的考察
张小红
(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人类学有关女人与污秽的研究已有不少,且多将聚焦点集中在月经的污染问题上。但污染绝不是孤立存在的,只有将其置于所存在的文化与社会语境中,才能分析出“污染”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与社会作用。文章通过收集山河村老年妇女有关月经禁忌及相关习俗的口述材料,分析了其中所映射的女性身份具有污染力的文化意象,并以女性在亲属制度秩序中的模糊性身份为着力点探讨了导致该文化意象的社会根源。
月经禁忌;女性身份;污染力;文化意象;社会根源
在中国的文化象征体系中,女性的形象较之男性总是带有更多的巫术—宗教性意味,她们的象征形象往往表现为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又是有危险性和污染性的,一些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了女性身份的这种文化意象。[1][2]女性身份具有污染力的文化意象反映在一系列围绕女性的禁忌方面,尤其是在与妇女的生理特征相关的情况下,这种污染性力量就更加明显。[3]P223-224因此了解和记述与女性月经相关的禁忌,有助于理解“女性身份是一种象征性的污染系统”的文化意涵。
一、有关月经禁忌的人类学研究
二战以前,部落社会的月经文化一直是人类学关注的焦点,弗雷泽、韦斯特马克、涂尔干和费洛伊德等人类学家都有关于女性月经禁忌现象的研究。[4][5][6][7]二战后,受非殖民化浪潮影响,离开异邦“田野”的欧美人类学家的注意力由“发现”取向逐渐转为“解释”不同的文化现象,月经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Menstruation)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随着人类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不同的人类学流派在研究月经文化现象方面实现了高度整合,其代表人物是英国女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她的《洁净与危险》一书开创了月经人类学理论建设的先河。在其影响下,人类学对月经研究的成果不断出现,彻底颠覆了医学唯物主义和精神分析学派对月经禁忌的理论假说。[8]随着人类学对身体研究的关注,妇女医疗中的月经问题逐渐成为月经人类学的重点,[9][10]对月经禁忌的跨文化研究也逐渐将文明社会纳入分析的视野。[11]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妇女月经问题的论著以美国汉学人类学者马丁(Emily Martin Ahern)的《“不洁”的中国妇女——经血与产后排泄物的威力与禁忌》为代表。[12]而国内有关月经禁忌的论述始于20世纪上半期,多见于民俗学者的研究。[13][14][15]改革开放后,当代中国性人类学对此问题关注较
多,从2004年起,学者李金莲与朱和双连续在国内各类刊物上发表有关月经禁忌的研究论文,其中尤其关注中国少数民族妇女。[16][17][18][19][20][21]此外,以翁玲玲为代表的有关台湾妇女月经禁忌问题的研究也不断出现。[22][23][24]
国外对月经禁忌问题的研究的坚实基础扎根于对异邦原始民族月经文化现象的收集与整理;国内人类学领域的相关研究起步则较晚,且较多关注少数民族。此外,无论是传统民族志报告还是现当代有关月经文化的人类学专项研究,都指出人类不同族群在对待经期妇女和经血时存在某种程度的禁忌。月经及行经妇女被普遍视为具有污染力和危险性的观念延伸至妇女本身,导致女性身份成为一种象征“污秽”的系统。女人与污秽的关系在人类学界已积累了相当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都是将聚焦点集中在月经的污染问题上。如我国著名人类学家林惠祥认为,“原始人由于迷信的心理对于妇女的月经是很觉恐怖的,……妇女对于凡有圣洁性质的举动不得参加,对于神圣的物件不得接触。……实在是由于妇女的生理上所引起的一种迷信的恐怖。”[25]P192但自玛丽·道格拉斯奠定了人类学对月经研究的理论基础后,象征结构分析最常被引用于讨论女性经血与产生污秽的理论架构,即将女人的污染物质模拟为社会秩序之异常,污染物质亦象征代表着对社会秩序的威胁。[26]妇女的正常生理排泄物缘何被定义为具有危险性的“污染物质”?具体到传统中国,学者李霞认为应从在父权、夫权亲属制占支配地位的宗族文化中女性的身份归属这一角度去探询其真正的社会根源,而月经禁忌也许只是女性身份具有污染力文化意象的一种突出表现。[27]
二、山河妇女的月经禁忌 具有污染力的女性文化意象
2013年暑期,笔者于闽南地区一个传统的汉民族村落——山河村进行了为期45天的田野调查,调查主题为农村妇女的日常生活。山河村(解放前称山宝雷村)坐落于福建诏安县县城西北10公里处,行政隶属于福建省漳州市诏安县西潭乡。自清朝康熙丁已年(公元1677年)建村至今,该村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是诏安县唯一的省级历史文化名村。山河村现有家户730户,人口3200人,土地面积325亩,全村单姓沈。在田野调查过程中,笔者交替运用了深入访谈、记录个人生命史、参与观察、查阅文献等方法。通过收集整理村中65岁以上老年妇女的口述史材料,了解了20世纪上半叶当地农村妇女的经期护理方式、月经禁忌以及相关的女性习俗。本文尝试以山河村妇女的月经禁忌为例,探讨并分析传统中国女性身份所具有的文化意象及其社会根源。
“禁忌是人类迄今所发现的唯一的社会约束和义务的体系,它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石,社会体系中没有哪个方面不是靠特殊的禁忌来调节和管理的。”[28]P34禁忌的仪式属性表明与被禁止的人或物的任何接触都可能隐藏着神秘的危险,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月经禁忌就是由于人们担心受到经血污染而招致灾害所遵循的行为规范。一切有关月经的内容因之成为忌讳,不仅男性对其讳莫如深,在妇女圈内相关内容的交流也是隐秘的。山河老年妇女在谈及“月经”时常用相对含蓄、婉转的词汇,通常“骑马”暗喻行经,“我今天骑马”即指“我今天来月经了”。调查中还发现已为人妻、人母的中年妇女对于母亲一辈的老年妇女如何处理月经等相关知识了解甚少,可见即使是母女之间也很少交流作为女人都要经历的生理问题;而访谈老年妇女时也要尽量避开旁人进行单独交流,虽然历经世事的老妇人对月经这一话题已不再害羞避讳,但若在人前公开讨论,还是会陷她于尴尬境地。因为即使到今天,与月经、性(月经禁忌涉及相关话题)相关的话题也是不可随意公开谈论的。月经是女人很私密的问题,羞与他人谈论,只有上了年纪的老妇人之间才可以在近旁无闲人时以此话题谈笑。此外,对于彼时的年轻女孩来说,虽然常在
十七八岁才经历月经初潮,但由于在此之前几乎没有机会了解相关的生理常识,所以她们当中不少人都曾经历过“初潮恐惧”。访谈中一位老人讲述了这样一个女孩:无父无母,跟随兄、嫂生活。第一次月经来潮时她被吓得躲在墙角哭,待嫂子询问原由时她才又害羞又恐惧地哭诉了“下身流血事件”。她的经历也许是许多同样因无知而恐惧的女孩的共同记忆。由于长辈妇女对月经的遮掩和回避,使得女孩在提及月经时会不自觉地有一种羞耻感。在这样的心理预设下,她们在行经前或过程中出现乳房涨痛或下身坠痛时通常都选择忍而不言,即使是母亲或祖母般亲近的人也三缄其口。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回忆年轻时的每次痛经都令她头晕目眩,脸色发青。她曾一度怀疑从身体里流出的块状物不是血而是肝,因此曾令其深陷死亡的恐惧,为了验证事实她鼓起勇气尝试用手掐碎流出的经血块。已为人妻人母的妇女虽已不再因羞于言表而忍痛惶恐,但当痛经或经期不正常时,碍于传统和有限的经济条件也不便求医问药。她们只能亲自动手,使用一些民间偏方缓解身体的不适。年代越是向前追溯,女人的月经越是隐蔽,女孩们对于月经的知识也越欠缺。这种文明和愚昧的分野,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人类对月经的认识进程,其中隐藏的性别内涵——女人是低贱而卑微的,与女人的身体紧密相关而与男人的身体无关的事物也是低贱而卑微的,它们不能享有公共空间(因为公共空间是男性化的),只能默默地发生,偷偷地被处理,悄悄地结束。[29]
即使妇女自身也认为月经是污秽的,需要被遮蔽,并且来月经既麻烦又不舒适,但她们也知道月经和生育之间是相互关联的,所以她们必须学会处理月经以及遵守与其相关的禁忌。解放前山河女人来月经时都使用布,俗称马布①。女人行经时长多为三至七天不等,不出门时只垫马布即可,如要出门劳动就需在布里包裹灶灰增强吸收能力,因为田地里不便更换马布;但当经血较多时,即使不出门也要包裹灶灰以防侧漏。遇见这种情况,女人通常都不能也不敢坐,怕弄脏裤子或板凳,举止行为也要十分注意,否则马布很有可能从宽松的裤子里掉出来。如果一旦出现上述情况女人会陷入十分耻辱、尴尬的境地,不但长辈的斥责怒骂免不了,同辈也会嘲笑戏弄。解放后出现的橡胶材质卫生带结实耐用,大大增加了使用的安全性,让经期女人少了不少尴尬与不安。②但卫生带需要从商店购买,当时很多年轻女人不好意思亲自去买,尤其是遇见男性店员时,因此常央求年长的妇人代为购买。
山河村人不仅认为经血是污秽不洁之物,对其采取掩盖、回避、视而不见的态度,还由此延伸至与之相关的人与物,认为经期妇女及其相关物品也是具有污染性和危险性的,从而都被列为禁忌对象。所以经期妇女总要“偷偷摸摸”,如马布里包的灶灰或后来固定在卫生带上的粗纸都不能随意丢弃,必须避开人偷偷扔进厕坑。有的女人羞于出去处理,就在房前屋后近便处挖坑掩埋;又如马布或固定在卫生带上的布都可重复使用,所以每次使用后要清洗干净,但这个过程也不宜让男人看见。因此女人一般选择晚上去河边洗,洗净的马布亦不能晾在屋外晒太阳,只能挂在床尾下方的横木上任其阴干。③此外,妇女行经时必须每晚清洗下身,尤其是夏天,否则身体会散发出难闻的味道。此时家中人要外出回避,并将大门紧闭,洗前要先用布将经血擦拭干净,以免污染脚桶④中的水。但即便如此,洗过的水也要趁门外无人时倾倒。而女人用于清洗下身的脚桶是她们的亲密伙伴,无论沐浴,给孩子洗澡、洗衣等都使用它,但男人一般不使用。
围绕经期妇女自身也有诸多禁忌规范和习俗。在山河,每逢节日、神诞或特殊日子都要供奉、祭拜神明,这种活动俗称拜拜,且通常由妇女完成。但由于人们对经血的误解,认为经血的肮脏会亵渎神灵,所以如果女人来月经了就不能去庙里拜拜;经期女人也不能跨坐在门槛上,据说
这样会触犯“财门”,使家中诸事不顺。在大多数社会中,人们在妇女月经期间都对性行为存在着某种节制,认为同经期妇女性交是十分危险的事。芬兰人类学家爱德华·韦斯特马克在讨论月经期间的性交禁忌时提到“每月之中,做丈夫的都必须同妻子分居一段时间”,[30]P996-997如果男人违背这一禁忌,不仅亵渎了风俗,还可能因此感染各种奇怪的病症。汉族民间也将月经视为“血污”,在山河村人眼中女人行经是在流毒,如果同房时恰巧妻子来月经,男人就“撞到了老马头”,即中了经毒,他们的眼睛会因此变模糊。由于女人的经血很毒,如不及时医治会染麻风病,具体症状为手指不能伸直,走路时一条腿不能抬起。丈夫服药期间不能与妻子同房,否则妻子不仅会出现相同症状,月经还会中断。虽然现在看来,基于“经血有毒”这一认知而形成的经期性交禁忌,其原初目的在于保护男性远离“危险”而不是出于女性身体健康的考虑,但不容否认的是它在客观上降低了妇女在身体条件脆弱的情况下受细菌感染的几率。
在人类认识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对正常的月经流血现象无法给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只能基于经验性的认识——流血常意味着死亡,误将经血视为一种不吉利、污秽的象征,对其充满恐惧。[31]由此形成的月经禁忌将经血、经期妇女及与月经相关的物品都列为禁忌对象,正如上文所述。原始先民借助具体的物象来暗示在特征上相似或相联系的观念,因此从对经血的禁忌延伸到了一切与此相关的事物,[32]导致与妇女相关的禁忌并不只见于月经周期内,在非例假时期的日常生活中也存在将女性物品化,甚至女性身份本身污名化的现象。据山河老年妇女口述,过去女人的衣裳不能置于男人或小孩的衣服之上,洗衣时要先洗女人的以保证将其衣物置于最下方;洗好的衣服晾晒在门前屋檐下悬挂着的三根高低不一的竹竿上,从高至低分别晾男人、孩子和女人的衣服,不得乱序,且女人的衣服要晾在竹竿两侧,不能挂在正中间,以免男人从其下穿过;而存放在衣柜中的衣服同样要恪守女下男上的秩序。女人的裤子由于与经血贴近而需遵守更严格的禁忌规范,如绝对不能用女性穿过的裤子缝补家人的衣物,尤其是男人的;还不能用女人的裤子裁剪成抹布擦桌椅,或用于拼接包婴孩的小毯子等。此外,昔时山河妇女的如厕习俗同样可以映射“女性身份具有污染力”这一文化意象。以前村中男性使用公厕,而妇女要在家中置于床头巷(床尾与墙之间的狭窄夹缝)的木制马桶内便溺,直到后来几乎每个家户都已建有坑厕时此风依旧。老人说有女人的家就有马桶,因为无论昼夜女人都要用其便溺。马桶分便桶和尿桶,其中便桶尤其不能示人,所以女人一般要在早晨天亮前倒马桶,以免撞见男人。因为惧怕才要加以回避和限制,而在山河传统观念中男性更是认为女性具有强大的破坏力,能够危害身体、家庭甚至社会秩序。如解放前山河人用甘蔗自行熬制食用糖,但整个过程主要由男人完成,且在制糖的关键环节禁止女人进入专用于烧糖的糖寮,否则会导致制糖失败。
上述女性习俗都与认为妇女不洁有关,它们无一例外地为女性身份贴上了晦气与危险的标签,使其在不自觉中被赋予了具有污染力的文化意象。“不洁”、“污秽”、“危险”的观念俨然超越了月经禁忌的原始作用范围,这一扩大化现象是人们由对经血的误解、贱视而引发的女性象征污秽系统的观念的外延,还是月经禁忌本身即同其它女性习俗一样,只是女性身份这一文化意象的表现之一?要探究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探讨月经禁忌缘何产生。
三、女性身份具有污染力的社会根源
月经禁忌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虽然不同民族对经血及经期妇女的看法在细节处会因文化的不同而有差异,但在经血是污秽的和经期女性是危险的这一认识上却是相同的。弗雷泽将经期妇女喻为恶魔附身,直
言“没有任何人像来月经期间的妇女那样为人们所畏惧。”[33]P312对于妇女月经这一自然的生理现象,为什么会有如此相似的恐惧甚至厌恶感呢?关于月经禁忌产生的原因,学界有着不同的认识。较主流的观点认为月经禁忌的产生与早期人类对血的看法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原始民族从可见的生活经验认识出发将血视为生命的源泉,因而十分畏惧流血现象的发生,月经禁忌就是受这种流血禁忌(blood-taboo)观念的支配。但妇女流失经血的现象与先民们在日常生活中获得的有关流血的经验并不相符,如年轻女孩和中年妇女每月都会没有任何可见缘由地流出经血,并且每次持续数天却不像一般流血事件那样带来死亡,甚至多数时候没有痛感,也没有因此变得虚弱;更重要的是除了女人,男人和孩子都没有经血。上述诸多无法得到合理解释的现象让先民们大惑不解,从而加深了他们对经血的恐惧。这也印证了早期人类思想中对不符合预设分类的、未知的、不确定的事物的恐惧,因为没有明确分类的东西就像不明身份的陌生人敲门一样,有着不可预知的危险。为隔离和控制不能被划分为“流血事件”的妇女行经现象会带来的恐惧和危险,发展出了多样且成系统的行为规范习俗,即月经禁忌。另有观点认为对月经的禁忌也可能起源于人类把涉及流血的行为视为圣礼的倾向。妇女身体具有定期向外流血的能力,因而是令人敬畏的,神圣不能接触的。“禁忌”一词同时具有神圣和不洁两层含义,而其原初释义即为“神圣的”。在人类和平的母系文化没落之前,女人身体和月经周期都曾被尊为神圣。考古学发现6000年前女人用刻有记号的骨头记录月经生理周期,而这个刻有女性生理周期的骨头在当时也被人们当做日历使用。这一考古发现的迄今为止最原始的日历,从侧面印证了女性曾经作为神圣存在的事实。[34]此外,在人们尚不能科学认识很多问题的时代,常常将寻求解释和答案的目光专注于充满神灵鬼怪的宗教迷信世界。不能掌握月经实质的早期人类就认为妇女每月定期流经血的现象是被某种精灵鬼怪撕咬所致,或是与某种精灵交合的结果。一些民族志资料曾提到,人们认为此精灵是女孩的某个祖先,人们由此进一步推论经期女孩身上附着着祖先的灵魂,所以她们是令人敬畏的,应被作为禁忌对待。[35][P241]也有学者指出月经禁忌之所以蔓延整个人类历史,其缘由不仅是神秘或宗教上的顾忌,由于经常性的沐浴净身对大多数族群而言,是后来才逐渐发展出的一种活动,所以月经使妇女身体变得“不洁”这一客观因素不应忽视。[36]P12-13
今天随着科学知识的发展和人们理性思维能力的提高,对月经的误解已经慢慢减少,妇女们也早已从环绕原始先民的月经禁忌和恐惧中解脱出来,但是女性身份具有污染力的文化意象并没有随着月经禁忌的弱化而解除,尤其在与山河妇女生产相关的习俗中体现更明显。如孕妇不能进新娘子的新房;产妇不能在娘家或别人家生产;坐月子的女人不能去别人家串门,不能准备年节拜拜所需的食品,更不能去庙里拜拜,否则会亵渎神明;而“产妇不洁”观念的外延导致伺候产妇做月子的人也成了禁忌对象,围绕着他们也有诸多禁忌事项,如不能随便碰触办喜事人家的桌椅、杯盘等器物。可见污染因素与妇女特有的生理特征紧密相关,但为什么是与妇女相关的,而不是与男性相关的生理特征被认为是污染性的?在探讨男性与女性的区别时,不应只停留在生理结构层面,性别的区分也有不同文化风貌的烙印。因生理特点(如月经、生育)而将妇女视为“不洁”“秽亵”“危险”的象征加以避讳禁忌,只是可见的浅层表象,更深层的原因存在于社会文化当中。正如一些研究者已经指出的,女性具有污染力的文化意象与女性在社会秩序尤其是在亲属制度秩序中的模糊身份相关。[37]李霞在《娘家与婆家》一书中即指出:在中国父系制的象征秩序中,女性的一生都处于从“娘家人”向“婆家人”过度的“阈限”状态。她认为从这个角度探讨
中国社会中女性的身份,可以为我们理解相关的女性意象提供不少启发。[38]
“作为经由联姻方式进入丈夫家族的外来人,妇女在其夫家家族中的成员资格并不像她的丈夫那样由自己的出身先赋决定,而是由她作为此家族中某男子的配偶和某(或某些)男子的母亲而得以确定的。因此,她在婆家的身份确认是附属性的。”[39]P218女性的身份归属已完全属于其夫家是以其真正作为婆家家族的祖先被发丧和被祭祀为仪式性标志的。也就是说,直至其生命历程的终点处,她们才最终完成从娘家到婆家的身份转换。特纳在“阈限”或曰“中介”的扩展概念中指出阈限或中介不仅是过渡仪式的一个阶段,还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有时是持久的状态,包括那些处于社会结构之外的无身份的人或事物。[40]P116“女性的模糊身份或曰不确定身份正是源于她终其一生都处于一种延续性的‘阈限’阶段,这种过渡状态,使她在亲属关系秩序中处于不确定身份的状态,她既不完全属于娘家,也不完全属于婆家。”[41]P224范内热普认为一个社会类似于一幢分成若干房间和走廊的房子,从一间房转换到另一间房是有危险的,这种危险表现在处于过渡状态中的人自己处于危险之中同时也向别人散发危险。危险处于转换状态之中,因为中介阶段意味着不确定性。[42]P22
而处于过渡状态中(因为不能明确分类)的人和事物不仅具有某种危险的能量并且是不洁的,具有污染力的。道格拉斯指出,“污染”的观念其实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表达,是由于有些事物在社会秩序内的类别不清而形成的对秩序的扰乱造成了污染的观念。“污染”作为秩序的对立面,从反面反映了社会观念中的秩序。[43]P3-4由此可见,肮脏是相对的,洁净与肮脏的区分取决于分类体系以及事物在该体系中的位置。在人们的观念中有一个总体的分类系统,不符合这一有序分类系统的事物即被认为违反了秩序,是“脏”的。[44]涂尔干认为个体的知识习得是一个不断接受外界分类的过程。这种分类不是个体发明的,只可能起源于社会。将超出了分类的、反常的或者意向不明的东西宣布为危险的东西,是社会处理分类困境的一种方式。[45]道格拉斯认为社会定义的“肮脏”并不意味着卫生学或者病理学意义上的不卫生,而是意味着失序。即不洁不是因为事物本身不洁净,而是因为他们错位了(out ofplace)。错位则暗示着对于秩序的挑战,而挑战中总蕴藏着危险。肮脏虽与秩序相抗衡,但秩序与肮脏总是相伴而生。因为“污染从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只有在有秩序的观念体系中才可能出现。因此,任何对其他文化的污染规则做片面的解释都不会成功,污染的观念只有与总体的思维结构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有意义。在总体的思维结构中,界限、边缘、内部差异等都是通过分隔仪式来维持的。”[46]P51因此对于“污染”的分析要将其置于所存在的文化与社会语境中,分析污染之所以具有污染力和危险性的象征意义与社会作用。此外,从身体政治的角度来看,不洁其实意味着未知的权力力量给现行体制带来的危险,意味着超越分界所带来的危险。妇女身份的“阈限”性质,即作为从娘家向婆家过渡的身份,以及作为父系家族的“外来者”同时又是“自家人”的矛盾角色,威胁着父系制度中父系家族界限,并成为女性污染性文化意象的社会根源。[47]P225而“红颜祸水”、“外姓外心”等民间俗语则突出表达了从外面嫁入的女性会威胁和破坏父系群体的团结的观念。在有关月经禁忌的话语表述中也有男性是社会建构的主体,而女性是破坏性力量的来源的内容。[48]由此或可将“月经禁忌”这一认知阐释为是男性畏惧社会结构中具有模糊性的女性力量的表现。
四、结语
女人与污秽的关系在人类学界已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绝大多数都是将聚焦点集中在月经的污染问题上,缺少结合具体的文化背景,深入探讨月经这一女性正常的生理现象缘何成为具
有污染力和危险性的禁忌对象的社会根源的研究。本文基于在中国闽南地区一个汉族村落的田野调查,通过搜集和整理村中老年妇女有关月经禁忌及其相关女性习俗的口述材料,详细记述和分析了月经禁忌等诸多体现女性身份具有污染力文化意象的民间禁忌习俗,并尝试在此基础上探讨和分析传统中国女性身份具有污染力的文化意象及其社会根源。
属于禁忌范围的物体都是带有两义性因而无法明确归类的东西,在中国父系宗族文化中,女性身份长期处于从娘家到婆家的过渡状态,女性身份所具有的这一阈限性质(因为不能明确分类)使其成为禁忌对象,因为具有两义性,即模糊性身份的人或物是危险的、有污染力的。也就是说,女性具有污染力的文化意象与女性在社会秩序尤其是在亲属制度秩序中的模糊身份密切相关。但“污染”并不是指卫生学意义上的不卫生,而是意味着对已有秩序的扰乱和挑战,即处于一种失序的状态。为了避免和防止社会结构中具有污染力,即破坏性的女性力量威胁和扰乱已有的父系宗族秩序及其团结,形成了许多限制女性行为的禁忌习俗,尤其体现在以月经禁忌为代表的围绕着女性所独有的生理特征(如月经、生育)而形成的习俗规范。道格拉斯强调了女性身体作为承载社会意义的象征系统,并且把经血具有的潜在威力视为年轻已婚妇女实际社会权利的一种象征性表现。[49]P35月经象征着女性具有破坏性的负面力量,而通过月经禁忌对其身体进行控制,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女性身份所具有的污染力会带来的危险。
注 释:
①其布料较厚,呈梯形、长方形或正方形,末端有两根长短不一的绳子,前端经折叠缝合后可穿绳。使用时将马布折叠成宽窄合适的长条置于胯下,再将长绳环腰穿过前面的道绕至另一侧腰际与短绳相系便可将其固定在身。未婚女人所使用的马布多由破衣旧布做成,结婚生子后便可用专门的大黑布裁剪。村人称此黑布为“花子布”,长约五尺,可裁三块马布,是陪嫁必有之物。据说女人生产后经血量大,唯用专置的大黑布裁剪马布才妥当。此外“花子布”还寓意使用此布的女人可以男、女孩交替生育。
②其实卫生带的形貌和固定方法与传统马布基本相仿,只是卫生带的前端不再可以穿绳,而是改设扣眼,纽扣即缝于其下方。使用时将有扣眼的一端下折裹住环腰系好的线圈再与纽扣相扣即可,如此不仅方便如厕时解开卫生带,仍系在腰间的线绳还可防止其不慎掉落。卫生带较之于马布最大的变化在于其面上设有两个橡胶圈,用于固定垫布。改进的好处在于可以灵活拆换垫布,重复使用。并且在不更换卫生带的情况下,家庭条件好一些的女人也可以用粗纸替代布固定其上使用。
③昔时山河人睡的床类似于古人常用的架子床,床尾下方有一根横木,月经布清洗后即晾在上面。
④多为杉木材质,呈圆形,上宽下窄,高约及小腿,可容一人坐浴。
[1]Arthur Wolf.Gods,Ghosts,and Ancestors[A].Arthur Wolf(ed.).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C].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
[2][37]Emily M.Ahern.The Power and Pollution of Chinese Women[A].M.Wolf and R.Witke(eds.).Women in Chinese Society[C].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
[3][27][38][39][41][47]李霞.娘家与婆家——华北农村妇女的生活空间和后台权力[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4][33](英)詹姆斯·乔治·弗雷泽.徐育新等译.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
[5][30](芬兰)E.A.韦斯特马克.李彬译.人类婚姻史(第三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6](法)爱弥尔·涂尔干.汲喆等译.乱伦禁忌及其起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7][35](奥)弗洛伊德著,滕守尧译.性爱与文明[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
[8]李金莲,朱和双.洁净与危险:人类学对月经研究的理论与实践[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
[9](美)费侠莉著,甄橙主译.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10]Charlotte Furth,Chen Shu-Yuen.Chinese Medicine and the Anthropology of Menstruation in Contemporary Taiwan[J].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1992,6(1).
[11][48]李金莲,朱和双.月经人类学:聚焦女性被遮蔽的生活方式[J].世界民族,2012,(3).
[12]马丁.“不洁”的中国妇女——经血与产后排泄物的威力与禁忌[J].思与言,1982,19(5).
[13]江绍原.血与天癸:关于它们的迷信言行[A].王文宝,江晓蕙,编.江绍原民俗学论集[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14]黄石.关于性的迷信与风俗[A].高洪兴,编.黄石民俗学论集[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15]曹聚仁.月经的禁忌[A].彭国梁,编.性之趣[C].珠海:珠海出版社,2003.
[16]朱和双,李金莲.生殖与象征:云南少数民族宗教节祭中的交媾仪式[J].宗教学研究,2004,(1).
[17]李金莲,朱和双.云南少数民族对月经的认知与妇女经期护理[J].民族研究,2004,(3).
[18]李金莲,朱和双.论中国少数民族的月经禁忌与女性民俗[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5,(5).
[19]李金莲.中国传统婚俗中的月经禁忌与民间信仰[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6,(7).
[20]朱和双.当代中国的性人类学研究及其发展趋势[J].广西民族研究,2008,(2).
[21][31]李金莲.阿昌族民间的月经禁忌与信仰习俗[J].宗教学研究,2008,(4).
[22]翁玲玲.产妇、不洁与神明:坐月子仪式中不洁观的象征意涵[J].两性平等教育季刊,2002,(18).
[23]翁玲玲.汉人社会女性血余论述初探:从不洁与禁忌谈起[J].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1999,(7).
[24]翁玲玲.坐月子的人类学探讨:医疗功能与文化诠释的关系[J].妇女与两性学刊,1993,(4).
[25]林惠祥.文化人类学(第2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26][29][32]李金莲.女性、污秽与象征:宗教人类学视野中的月经禁忌[J].宗教学研究,2006,(3).
[34](奥)费洛伊德.杨庸一译.图腾与禁忌[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28]陈建宪.《白水素女》:性禁忌与偷窥心理[J].民间文化,1999,(1).
[36]蕾伊·唐娜希尔.李意马译.人类情爱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
[40]Victor Turner.The Ritual Process: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M].Chicago: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1969.
[42](法)范热内普.张举文译.过渡礼仪[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43][46][49]MaryDouglas.PurityandDanger[M].London:BostonandHenley,1966.
[44]朱文斌.分类体系的社会秩序建构——对《洁净与危险》的述评[J].社会学研究,2008,(2).
[45]梁永佳.玛丽·道格拉斯所著《洁净与危险》和《自然象征》的天主教背景[J].西北民族研究,2007,(4).
C912.4
A
1671-6469(2014)02-0001-08
2014-03-26
张小红(1989-),女,新疆伊犁人,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女性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