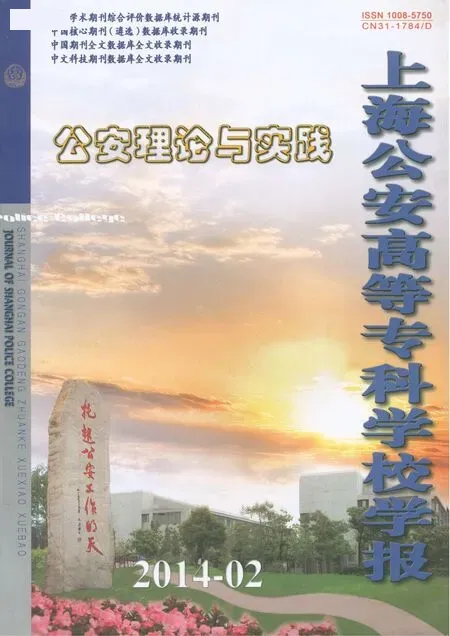中美刑辩律师保密特权制度的比较与启示
熊理思,高 飞
(华东政法大学, 上海 200042;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 上海 201199)
中美刑辩律师保密特权制度的比较与启示
熊理思,高 飞
(华东政法大学, 上海 200042;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 上海 201199)
新刑事诉讼法第46条相关规定标志着辩护律师保密特权在我国的正式确立。虽然辩护律师保密特权在英美法系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但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法律上对律师保密特权的具体内容及行使程序均缺乏具体规定。作为一件“舶来品”,律师保密特权在我国的发展必将经历一个从简单到完善的过程,其中的许多问题值得我们从法律比较与法律完善的角度进行探讨。
刑辩律师;保密特权;中国;美国;比较
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第46条新增了辩护律师的保密特权——“辩护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有权予以保密。但是,辩护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应当及时告知司法机关。”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60条又补充规定:“辩护律师向人民法院告知其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实施、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记录在案,立即转告主管机关依法处理,并为反映有关情况的辩护律师保密。”这两项条文标志着律师保密特权在我国刑事诉讼领域的正式确立。但目前法律对律师保密特权的具体内容及行使程序均缺乏具体规定。虽然辩护律师保密特权在英美法系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但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法律上由模糊到相对完备需要一个过程。下面笔者就从我国律师保密特权的发展历程、存在的问题、国外法借鉴、我国法律完善等方面对刑事诉讼中的辩护律师保密特权展开讨论。
一、律师保密特权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新《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标志着“律师保密”在我国实现了由“义务”到“权利”的转变。关于律师保密的规定,过去只有《律师法》、《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予以涉及。例如,1997年、2001年的《律师法》第33条均规定:“律师应当保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和当事人的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2007年《律师法》将之调整为第38条,并增加了第2款“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但是,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其他严重危害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事实和信息除外。” 以上法律条文使用的均是“应当保守”、“不得泄漏”等义务性规定,直到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46条才转变为“有权予以保密”这一赋权性规定。法律用语的微小变化折射出立法价值的巨大转变,表明立法者开始承认与重视律师保密特权。由此带来了“律师保密”在刑事诉讼领域出现了两个可喜变化:一是律师保密性质由义务型转向权利型,增强了辩护律师在对抗制中的主动性;二是保密内容从过去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当事人隐私转向委托人与律师之间交流的信息,更加突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护。为什么这一变化会于2012年率先出现在《刑事诉讼法》中,而不是其他时间、其他法律中呢?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价值观的改变。随着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的社会经济发展,权利本位已获得社会主流价值的认可,而且随着一些冤假错案的曝光,人们也逐渐认识到了刑辩律师在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中的重要性。二是我国加入的国际人权公约中有关于律师保密特权的规定,作为成员国我们有义务在国内法上予以体现。①例如,1988年12月联合国大会第43/173号决议通过的《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第18条规定:“被拘留人或被监禁人应有权与其法律顾问……,在充分保密的情况下与其法律顾问联系的权利。”此外,1955年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1988年联合国《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等文件也有类似规定。
二、我国刑诉法中律师保密特权的不完备之处
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46条相关规定对我国律师保密特权的确立具有划时代意义。在条文设置上,它既从正面对辩护律师对“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的保密权予以肯定,又从反面对该特权作出限制性规定,将“辩护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信息排除在保密特权之外。但作为一项新生事物,《刑事诉讼法》第46条中的律师保密特权显得过于单薄。
第一,权利主体过于狭窄。《刑事诉讼法》第46条实际上只规定了律师保密特权的一个方面——律师拒证权,即律师虽具有证人的适格性,但可就其在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所知悉的当事人秘密事项拒绝提供证言的一种诉讼权利,但这只是律师保密特权的一个方面。[1]而在律师保密特权发源地的英美法中,律师保密特权被称作“律师—客户特权”,其权利主体是委托人,律师拒证权也是源自委托人的此种权利。在我国其权利主体却是律师,换句话说,如果律师放弃这一权利,委托人不愿意也无可奈何,这显然违背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诉讼权利的立法初衷。
第二,对辩护律师与委托人的身份界定不明。《刑事诉讼法》第46条中的“执业活动”从什么时候起算,是从正式达成委托协议之时起算,还是从为委托而进行谈判之时起算?在此过程中,辩护律师聘请的律师助理、专业人士知悉相关情况的是否也享有保密特权?委托人除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还包括可以代表他们的亲属?委托人为单位的,律师与单位中哪些人的交流属于保密范围?
第三,受保护信息的范围不明确。《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辩护律师“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属于有权不予披露的信息。那么,委托人向辩护律师秘密提交的犯罪工具等物证是否也在此之列呢?再如,委托人向辩护律师作有罪陈述后又将该信息无意中说给第三人听的,是否还受保护呢?对此,有必要通过司法解释等方法增加第46条第2款的例外规定,以统一司法尺度。
第四,特权的行使程序不明确。虽然《解释》第60条对《刑事诉讼法》第46条第2款进行了补充,“辩护律师向人民法院告知其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实施、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记录在案,立即转告主管机关依法处理,并为反映有关情况的辩护律师保密”,但对第46条第1款的权利如何行使并无规定。缺乏程序规定将使权利形同虚设,因此必须对律师保密特权的行使程序予以明确。
第五,特权的存在期限不明确。双方委托关系终止后,委托人与辩护律师过去的秘密交流是否仍受保护?委托人为自然人的,委托人去世后其相关信息是否仍受保护?委托人为机构、组织的,该机构、组织解散后,他们之前的秘密交流是否仍受保护?
第六,保密特权与其他条文冲突时的解决机制不明确。为保障律师保密特权不受侵犯,《刑事诉讼法》第37条增加了“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的内容,同时废除了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96条“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的规定。这些配套措施保障了律师保密特权的实施,也使诉讼法条文整体上保持和谐,但条文之间仍存在冲突的地方。例如,《刑事诉讼法》第46条只规定律师对委托人或其他人准备或正在实施的某些严重犯罪有报告义务,而第108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报”,这里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当然包括律师。因此108条的举报范围已超越第46条规定的告知范围,二者存在一定冲突。法律上对如何解决辩护律师可能面临的两难境地尚待明确。
三、美国证据规则中的“律师—客户特权”
英美法系是律师保密特权的发源地。针对以上问题,下面笔者以美国法为蓝本介绍英美法系中的“律师—客户特权”,相信其完备的法律规定可以给我们带来不少启示。
第一,立法背景及价值基础。为鼓励某些特殊社会关系的存在,美国证据法逐渐发展出多种证人免予作证的特权,分别是:律师—客户特权、医生—患者特权、精神治疗师—患者特权、配偶特权、不得自证其罪特权、神职人员—忏悔者特权、会计师—客户特权、职业新闻记者特权、政府特权等。所谓免予作证的特权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当事人有权拒绝透露某些种类的秘密信息,二是当事人有权禁止其他人透露某些种类的秘密信息。[2]美国法认为,即使有时会使一些具有高度证据价值的信息无法作为证据使用,但出于公共政策的考虑,法律认可这种特权的存在。
律师—客户特权是美国最早建立的一项免予作证特权,起初它是普通法上的一项特权,但目前许多司法区已将之法典化,对它的限制也比其他特权要少得多。规定律师—客户特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鼓励客户在与律师进行交流的过程中充分披露与案件有关的事实,以使律师能够更有效地维护客户的权利。根据这一特权,客户有权拒绝披露或拒绝他人披露其与律师之间的某些秘密交流的信息。由于美国的证据规则并不区分民事与刑事,而是一部统一适用的规则,因此下文所指的律师—客户特权不限于刑事诉讼程序。
第二,律师—客户关系的界定。首先,律师—客户关系的所涉人员具有广泛性。律师—客户特权所指的客户既包括个人,也包括公司、政府机构等组织,以及该个人或组织的代表。律师不仅包括被授权从事法律业务的人,也包括客户有合理理由相信被授权从事法律业务的人;不仅包括律师本人,还包括律师雇佣的秘书等律师代表,以及律师雇佣的其他领域的专家。以上广义客户与广义律师之间的交流,均受律师—客户特权的保护。若客户同时雇佣多个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之间所作的有关案件的信息交流也是该特权的保护对象。其次,律师—客户关系的形成时间也采用广义说。律师—客户关系从何时起算呢?常识性的理解是从委托关系的建立之日起计算,但对保密特权而言却从客户以寻求法律服务为目的就是否雇佣某一律师进行谈判时起算,即使最后客户没有雇佣该律师,他们也构成特权中的律师—客户关系。[3]例如,A突然跑到律师B的办公室说自己杀了人,想请B为其辩护;即使A与B最后没有达成委托关系,B也不能就A对他所做的犯罪陈述作证。
第三,保密信息的范围。客户在向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过程中与律师之间所作的秘密陈述或其他信息交流均属于不予披露的范围。受保护的信息既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但以下情况不属于受保护的信息:(1)律师观察到的不具传达信息性质的事实,例如律师可以就客户的外表特征作证。(2)传达的信息中体现的事实,例如虽然客户向律师陈述时说到事故发生时是红灯,但若庭审中客户被问及事故发生时是否红灯,客户仍需如实回答。(3)律师—客户关系形成前就已存在的文件,例如律师—客户关系形成前客户的支票、信件等。(4)物证,例如作案工具等。(5)有其他人在场时所作的陈述。例如,客户明知有其他不相干的人在场仍向律师作出陈述,则该信息不受该特权保护。(6)自愿披露的信息。例如,一个客户自愿告诉朋友其与律师谈话的信息,则该信息不受保护。(7)被放弃特权的信息。例如,在他人寻求披露某信息时,客户未及时主张自己的特权,或当事人事先通过合同约定将来在诉讼中放弃该特权。[4]
第四,特权的行使。客户是这一特权的行使者。在他人要求披露某一信息时,客户必须及时引用该特权,否则就丧失了该特权的保护。如果客户及时引用了该特权,一般由法官来决定相关信息是否属于该特权的保护范围。法官一般会在寻求披露方不在场的情况下,以“关门”(In Camera)的方式对有关信息进行审查,以确定该信息是否属于受保护的范围。如果法官确认这些信息不受保护,客户仍然拒绝披露这些信息的,法庭可以裁定客户藐视法庭。
第五,特权的期限。特权所提供的保护一般应延续到委托人死亡之后,这一观点已被广泛接受。若客户是个人,则该特权期限为永远,即使客户已死亡,该信息也不得被披露。若客户是组织,这种特权可以持续到组织解散。解散后,组织的继承人、受托人等可以继续主张该特权。
第六,特权的例外。虽然律师—客户特权适用范围广泛,但以下情况下不得适用:(1)律师提供法律服务以帮助当事人在将来实施犯罪或欺诈的;(2)遗产继承诉讼中,死者作为立遗嘱人,其生前就遗产争议事实对律师作出有关陈述的;(3)律师与客户之间发生争议的,包括客户不满律师服务而公开发表对律师有伤害的指责或起诉律师,以及律师因客户拒付律师费而起诉客户等情形。无论哪种情形,客户与律师之间所作的和当前案件的诉请或抗辩有关的信息交流均不适用该特权。
四、对完善我国刑辩律师保密特权的启示与借鉴
通过比较,不难发现律师保密特权在美国立法上已有较完备的规定,并经受住了长期司法实践的检验;而刑辩律师保密特权在我国是一项新的制度,条文较原则,缺乏一定的可操作性。因此,笔者建议可在吸收与借鉴美国法的基础上对我国的刑辩律师保密特权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完善。
第一,应明确律师保密特权的功能定位。价值基础是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源泉。因此构建一项法律制度时首先要明确其背负的功能定位。根据国际刑事司法精神,律师保密特权的功能主要有以下两点:(1)保护当事人信赖利益。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委托关系,而这种委托关系的基础就是相互信赖。这种信赖,是律师得以开展业务活动的基础和前提。[5](2)阻止控诉方从辩护律师口中得到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言词证据,这与我国《刑事诉讼法》“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精神是一致的,律师保密特权彻底杜绝变相获得源自被告人的言词证据。虽然以上价值观与我国注重实体真实、打击犯罪的诉讼传统存在差异,但任何理由都不能阻挡现代刑事诉讼程序向对抗制和保护人权方向发展的步伐。
第二,应明确律师保密特权的具体内容。在律师保密特权的具体内容设置上,笔者认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有选择地借鉴美国法的成熟经验。首先,应将委托人纳入权利主体。既然律师保密特权的主要功能是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那么他们更加有权拒绝披露或禁止他人披露与律师秘密交流的信息,而不应将这一权利止步于辩护律师。其次,保密信息的内容应包括委托关系成立前的法律服务谈判。这是因为,委托人向拟聘请的辩护律师诉说案情后最终却没有达成委托协议的情形常有发生,若将这部分交流信息排除在保密信息之外则会使寻求法律服务的谈判缺乏公平交易的基础。再次,该特权的期限应为永久。这不仅与国际惯例相符,也已在我国《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第39条中有所体现。①《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第39条规定:“律师对与委托事项有关的保密信息,委托代理关系结束后仍有保密义务。”最后,还要丰富律师保密特权的例外性规定,以进一步明确该受保护信息的范围。例如可将物证、律师—客户关系形成前就已存在的书证、委托人明知不相干的第三人在场仍向律师所作的陈述、委托人自愿向第三人泄露的信息等排除在外。
第三,应明确律师保密特权的适用程序。首先我们应当明确委托人、律师是这一特权的主体,然后当他人要求披露某一信息时,权利主体必须及时引用该特权,否则视为放弃。该特权可在刑事诉讼的任何阶段予以引用。若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引用的,侦查机关、公诉机关不得强制权利主体就保密内容作证,应待进入审理阶段后由法官作出是否属于保密范围的判断。
第四,应明确法条冲突时的解决办法。鉴于《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的含辩护律师在内的人的举报义务范围已超越第46条辩护律师特权的例外规定,因此,笔者建议将《刑事诉讼法》第108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报”调整为“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报,但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主要是考虑到现代法治精神对辩护关系、亲属关系等特殊信赖关系的保护。对第108条增加但书规定,可以为律师保密特权及刑事诉讼法日后的其他修改留有了余地,有利于增强法条之间的兼容性,促进法律的不断完善。
[1]葛同山.辩护律师保密特权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2][美]史蒂文·L·伊曼纽尔.证据法(第四版)[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
[3][美]约翰·W·斯特龙.麦考密克论证据[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4.
[4]高忠智.美国证据法新解[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5]时显群,章进.律师与公证学[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
Legal Comparison and Inspiration on Chinese and American Attorney-Client Privilege
Xiong Lisi, Gao Fei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0042, China; Shanghai People's Procuratorate of Minhang District, Shanghai 201199, China)
Article 46 of the newly amended criminal procedure law has officially established attorney-client privilege in China for the f rst time. Although attorney-client privilege has a long history in common law system, it is a brand-new system in China where its specif c contents and implementing process are still not clear. As a borrowing concept, attorney-client privilege is deemed to experience a tough development from simple to integrated process. So a lot of issues are discussed on the basis of legal comparison and legal perfection.
Criminal Law Attorney; Attorney-Client Privilege; China; America; Legal Comparison
DF71
A
1008-5750(2014)02-0071-(05)
10.13643/j.cnki.issn1008-5750.2014.02.012
2014-02-25 责任编辑:孙树峰
熊理思(1982- ),女,华东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高飞(1978- ),女,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助理检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