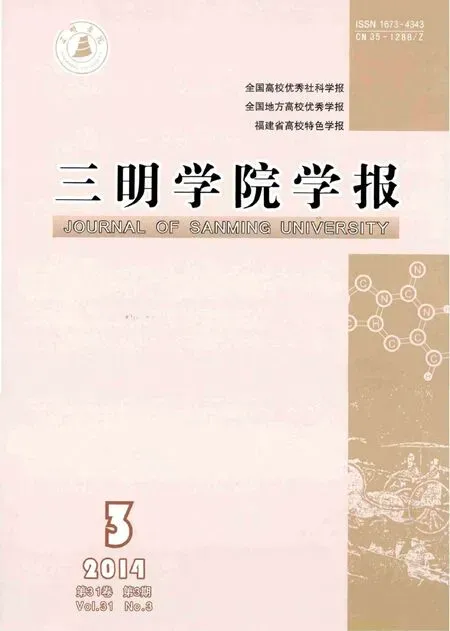唐五代小说中的掘墓现象
杨亚男
(淮北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唐五代小说中的掘墓现象
杨亚男
(淮北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唐五代小说中各种情形的掘墓现象非常多见,而其所涉及的一系列由盗墓取财、改葬和合葬、获罪斲棺、误葬活人以及其他一些产生诸如此类掘墓现象的原因都与其当时存在的社会风俗、历史现实息息相关。唐五代小说中所记述的掘墓现象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丧葬习俗,如改葬、合葬等风俗已经在社会上普遍存在以及人们对墓地选择的重视和对棺墓敬重的社会心理;小说中也记载了一些为世人所认可的掘墓现象,如在官司中若需要开棺验尸等。唐五代小说中所保存下来的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对于研究社会生活史具有很高的价值。
唐五代;小说;掘墓现象
由于受到中国传统 “入土为安”观念的影响,古代人们对丧葬和坟墓尤为重视,盗掘坟墓则是被人们所唾弃的行为,这种行为也是见不得阳光的。而在唐五代的小说中却有诸多有关盗墓现象的记述,其中有些盗掘甚至是明目张胆的。目前学术界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多是以对皇陵和世家大冢的盗掘为主,而对其他的盗掘现象鲜有提及,如已出版的《盗墓史》和《中国盗墓史》①均过于重视对盗墓这一现象本身的研究,却相对忽略了与之相关的社会风俗、文化内涵的联系。本文拟通过对唐五代小说中关于掘盗现象记载的分析来探讨其所反映出来的社会文化和心理。
一、唐五代小说中掘墓现象的原因
(一)盗墓取财
厚葬之风在我国一直极为盛行,墓中的各种随葬品尤其是奇珍异宝便成为盗掘的最主要诱因。历代各种史书中多是记载帝王将相陵墓被盗,而对于民间盗掘,只称有其事,却不见其实。而在唐五代小说中,则有大量有关盗掘的材料,其中所见盗墓者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职业盗墓贼,此类人专以盗墓取财为主,在当时不但成为家族世代相袭的一种职业,贼人甚至纠合多人组成团伙来加强盗掘的力量。如《玉堂闲话》“发冢盗”篇云:“光启、大顺之际,褒中有盗发冢墓者,经时搜索不获。长吏督之甚严。忽一日擒获,置于所司。淹延经岁,不得其情。拷掠楚毒,无所不至。”[1](P73)第二类是临时掘盗,这种多为村里乡民一时贪财而盗掘邻家大冢。《穷神秘苑》“李俄”篇云:“汉末,武陵妇人李俄,年六十岁,病卒,埋于城外。已半月,俄邻舍有蔡仲,闻俄富,乃发冢求金。”[2](P625)第三类为骄兵悍将以及农民军,此类群体多趁乱世而手握兵权之机私自掘墓,小说对此也有详细记载。《稽神录》“陈金”篇云:“陈金者,少为军士,隶江西节度使刘信。围虔州,金私与其徒五人,发一大冢。”[3](P83)而杜光庭 《仙传拾遗》载张良死后,“葬于龙首原。赤眉之乱,人发其墓”[4](P45)。只知张良之墓是赤眉之乱时被掘,至于何人所盗却不得而知,因而并不排除当时有人趁乱盗墓之嫌疑。
(二)改葬、合葬
为改葬而掘墓者又有几种原因,其中最为普遍的就是按风俗对先人进行改葬,这在唐五代小说中就有诸多的记载。《朝野佥载》“舒绰”篇云:“舒绰,东阳人,稽古博文,尤以阴阳留意,善相冢。吏部侍郎杨恭仁,欲改葬其亲。(‘其亲’原为‘观王’,明朝本所改)求善图墓者五六人,并称海内名手,停于宅,共论艺,互相是非。”[5](P748-P749)又如《通幽记》中“萧遇”篇记载:“信州刺史萧遇少孤,不知母墓。数十年,将改葬。”[6](P323)另外,唐五代小说中也有改葬以安魂的记载。最典型的就是《大唐新语》“唐王皇后”篇载唐玄宗惠妃武氏诬陷太子瑛及同生鄂王瑶、光王琚致死,海内号之为三庶,“太子既冤,武氏及左右屡见为崇,宫中终夜相恐,或闻鬼声叫笑,召觋巫视之,皆曰三庶为厉。先是收鄂王、光王,行刑者射而瘗之,乃命改葬,祝而酹之。武妃死,其厉乃息”[7](P172-P173)。最无奈的当属墓地被占,不得不迁。《稽神录》“海陵夏氏”篇载:“戊戌岁,城海陵县为郡,侵人冢墓。有市侩夏氏,其先尝为盐商,墓在城西,夏改葬其祖。百一十年矣,开棺。”[8](P130)
合葬之事见于小说者皆为夫妻合葬。《法苑珠林》“史阿誓”篇云:“(史阿誓)终后十年,其妻死,乃发冢合葬。”[9](P94)《纪闻》“明崇俨”曰:“俨尝行,见名流合祔二亲者,輀已出郊。 ”[10](P243)由此可见当时夫妇合葬已是社会常见现象。
(三)获罪斲棺
对于获罪斲棺的事例,《朝野佥载》中就有多处记载,如“郝处俊”篇:“唐郝处俊,为侍中,死。葬讫,有一书生过其墓,叹曰:‘葬压龙角,其棺必斲。’后其孙象贤,坐不道,斲俊棺,焚其尸。”[11](P749)《新唐书》中也记载了这一史事:“(处俊)孙象贤,垂拱中为太子通事舍人,后素嫌处俊,故因事诛之。临刑,极骂乃死。后怒,令离斲其尸,斲夷其祖、父棺冢。 ”[12](P4218)
(四)误葬活人
对于误葬活人的事例,正史及其他相关的史料记载甚少,但唐五代小说中却对此有不少的记载。如《酉阳杂俎》“王氏”篇云:“(王氏)贞元中,忽暴疾卒。埋已三日,其家复墓,闻冢中呻吟,遂发视之,果有气。”[13](P231)又有《五行记》“陈朗婢”篇载:“义熙四年,琅玡人陈朗婢死,已葬。府史夏假归,行冢前,闻土中有人声,怪视之。婢曰:‘我今更活,为我报家。’其日已暮,旦方开土取之,强健如常。 ”[14](P627)
(五)其他
吊唁死者,开棺一见。这种风俗,查诸史料,均未见有提及,然而小说中却有记载。“后魏尚书令古弼族子元之,少养于弼,因饮酒而卒。弼怜之特甚,三日殓毕。追思,欲与再别,因命启棺,开已却生矣。”[15](P79)另《法苑珠林》“河间男子”也载河间有男女相悦,男从军,女家以女适他人,忧死。“男还悲痛,乃至冢所,始欲哭之,不胜其情。遂发冢开棺,即时苏活,因负还家。”[16](P479)
死者复现。《续仙传》“马自然”篇就记载,马自然死,“乃棺敛。其夕棺訇然有声,一家惊异,乃穸于园中。时大中十年也。明年,东川奏剑州梓桐县道士马自然,白日上升。湘于东川谓人曰:‘我盐官人也。’敕浙西道杭州覆视之,发冢视棺,乃一竹枝而已。 ”[17](P217-P218)《高僧传》“佛图澄”篇中也载类似事件:“初虎殓澄,以生时锡杖及钵内棺中,后冉闵篡位,开棺唯得钵杖,不得见尸。或言澄死之日,有人见澄于流沙。虎疑其不死,因发墓开棺视之,唯见一石。 ”[18](P582-P583)
畜兽居冢。《酉阳杂俎》“狼冢”篇就曾记载:“临济郡西有狼冢。近世有人曾独行于野,遇狼数十头。其人窘急,遂登草积上。有两狼乃入穴中,负出一老狼。老狼至,以口拔数径草,群狼遂径拔之。积将崩,遇猎者救之而免。其人仍相率掘此冢,得狼百余头杀之,疑老狼即狈也。”[19](P134)
二、掘墓现象所反映的社会风俗和心理
通过对唐五代小说中所涉及掘墓现象的分析,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可以在正史中找到相关记载,同时这部分内容也可以对以往的记载起到补充和佐证的作用;另外,小说中还有一部分内容是正史记载中没有涉及的,对于研究社会生活有很大的作用。因此,从中可以得出许多关于当时社会风俗文化的现实状况。
首先,唐五代小说中的掘墓现象折射出当时流行的一些丧葬习俗。如前所述,有关改葬、合葬的记载在唐五代小说中是十分常见的。而“改葬其亲”等字眼在小说中已是屡见不鲜,由此可以得出:改葬、合葬作为丧葬习俗在唐五代时期已经较为流行了。而《大唐开元礼》也曾对改葬程序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卜葬、启请、开坟、举柩等,共有十几个步骤,礼之繁复,可见一斑。[20](P673-P674)小说中的描述与国家所定礼制相吻合,这也正是当时社会风俗习惯的一种反映。对于夫妇合葬在小说中也多有可查,而唐朝这一风俗着实可查是在关于争论武则天是否能够祔葬乾陵一事上,“按杜佑《通典》,神龙元年十二月,将合葬则天皇后于乾陵,给事中严善思上表曰:‘臣谨按《天元房录》葬法云,尊者先葬,卑者不合于后开入……于乾陵之旁更择吉地,取生墓之法别起一陵。’”[21](P59)严善思既未能阻止武则天祔于乾陵,而唐人并将合葬之仪加于礼仪典制之中。上行下效,夫妻合葬上自王公大臣,下到平民百姓各个阶层,合葬成为社会最真实的写照。此外,唐五代小说对葬地风水也尤为重视,因为葬地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后世子孙的前途命运。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念,才会发生斲棺焚尸的悲剧,也才有“不祥之地”的说法,因而人们争相寻找合适的墓地,以求得祖先庇佑,享受荣华富贵已成为当时社会的普遍风气。
其次,小说中的描写充分体现了社会心理对棺墓的重视。灵魂观念在人类社会初期普遍存在,这也是丧葬文化赖以存在的基础。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尤其崇拜祖先,殷商时期人们信奉祖先一元神的宗教,这种法天敬祖的思想发展出了“孝”观念,而“孝”在早期也更侧重于对父母后世的处理,夏商时称为“追孝”或“孝祀”,即是一种祭祀习俗。《周礼·檀公》云:“葬也者,藏也,欲使人弗得见也。”[22](P47)因而曝尸于外乃是人所不欲,也被看作是一种失礼。《释名·释丧制》曰:“墓者,慕也。孝子思慕之处也。”[23](P136)所以说,在特别重视祖先讲求孝道的中国古代宗法社会,“墓”决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的存在,它同时具有在心灵世界中的崇高位置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而唐五代小说对这一社会现象进行了细致的刻画,鲜明地呈现出当时人们对棺墓的敬重程度。
最后,小说的记载说明很多掘墓行为是有其合理原因的,并为世俗所允可。如在官司争执中需要开冢验尸取证,在小说的记载中并没有发现有反对的声音。因此,虽然掘墓行为受到整个社会意识的否定,但与生者的清白甚至性命比起来,死者的安寝却不再那么重要了,当然人们会认为这种迫不得已的行为会得到亡灵的谅解。至于误葬活人,则应该是当时人们对死亡的一种误断,由于传统医学和民间公众均认为心跳消失、呼吸停止即为死亡,如今的医学对此可以作出解释。然而当时人们不免认为这是奇迹,由此而讹传、推衍出许多神奇的故事,这在唐五代小说中有诸多记载。对于这种不能理解的现象,古人便托于冥司福报,神鬼庇佑而记录于小说中,也出现了唐五代小说中浓郁的宗教色彩。唐五代小说中就有多处记载通过托死而成仙成佛的事例,仅在《太平广记》中引录成仙成佛者就达七八条之多,民间口耳相传,足见当时宣传之盛。在这类宣传中最著名的当属张果,《明皇杂录》《宣室志》和《续神仙传》中都有他的记载,相传此人年逾数百,唐太宗、唐高宗屡次征之不应,至则天时佯死。玄宗曾召之入宫,以为异人,“天宝初,玄宗又遣征召。果闻之,忽卒。弟子葬之。后发棺,空棺而已”。[24](P32)甚至两《唐书》均为张果列传,《新唐书·张果传》载“张果者,晦乡里世系以自神”[25](P5810),张果通过这种炒作的方式使自己成为众人羡慕的“神仙”,并家喻户晓,而这种成功当然借助了世风的力量,人们信仙慕仙,渴望成仙才为他打开了方便之门。
通过对唐五代小说中掘墓现象的的粗略整理与分析,可以发现其中保存了大量的社会生活史料,其中一部分可以作为正史记载的佐证和补充,如小说中涉及的盗墓现象即反映了盗墓在整个社会的风行;对改葬、合葬、相墓、拜扫等社会风俗的描述不但说明正史记载的正确性,更是从普通民众的视角直接体现了相应的社会实践状况;对于正史所未涉及的内容,如因官司约请开棺、对于入葬之人复活的种种讹传以及畜兽居于古冢等的记载,而小说却恰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目前学术界对这一珍贵史料的研究还不多,掘墓现象所反映的一系列社会风俗,若将其作为社会生活史研究的一个方面,相信以后还会有更大的突破。
注释:
① 殷啸虎,姚子明.《盗墓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王子今.《中国盗墓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
[1]蒲向明.玉堂闲话评注:第2辑[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
[2][宋]李昉.太平广记·李俄:卷三七五[M].北京:中华书局,1961.
[3]徐铉.稽神录·陈金条:卷五[M].北京:中华书,1996.
[4][宋]李昉.太平广记·张子房:卷六[M].北京:中华书局,1961.
[5][宋]李昉.太平广记·舒绰:卷三八九[M].北京:中华书局,1961.
[6][宋]李昉.太平广记·萧遇:卷三三八[M].北京:中华书局,1961.
[7]刘肃著,许德楠,李鼎霞点校.大唐新语·惩戒第二十五:卷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4.
[8]徐铉.稽神录·海陵夏氏条(补遗)[M].北京:中华书,1996.
[9][宋]李昉.太平广记·史阿誓:卷一〇九[M].北京:中华书局,1961.
[10][宋]李昉.太平广记·明崇俨:卷三二八[M].北京:中华书局,1961.
[11][宋]李昉.太平广记·郝处俊:卷三八九[M].北京:中华书局,1961.
[1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郝处俊传:卷一一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3]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金刚经鸠异:卷七[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4][宋]李昉.太平广记·陈朗婢:卷三七五[M].北京:中华书局,1961.
[15]牛僧儒,程毅中点校.玄怪录·古元之条: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6][宋]李昉.太平广记·河间男子:卷一六一[M].北京:中华书局,1961.
[17][宋]李昉.太平广记·马自然:卷三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61.
[18][宋]李昉.太平广记·佛土澄:卷八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61.
[19]段成式.酉阳杂俎·广动植之一·毛篇:卷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0]萧嵩.大唐开元礼:卷一四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1][清]陈梦雷,蒋廷辑锡.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礼仪典·丧葬部:52[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版,1987.
[22]礼记·檀弓上:卷三[M].崔高维,点校.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23]王先谦.释名疏证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4]郑处诲.明皇杂录·道士张果:卷下[M].田廷柱,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
[25]新唐书·方技·张果:卷二四〇[M].北京:中华书局,1975.
(责任编辑:刘建朝)
On Digging Grave Phenomenon in the Novels of Tang Dynasty and Five Dynasties
YANG Ya-nan
(School of History and Society,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Huaibei 235000,China)
A variety of digging grave phenomenon was very common in the novels of Tang Dynasty and Five Dynasties. These events involved various types of digging grave such as grave robbers,re-interment,chop coffin,coffin,and judgments etc.,which were closely related with social customs and historical reality at that time.The novels of Tang Dynasty and Five Dynasties reflected popular funeral customs,such as Gaizang,Hezang and other customs which had existed generally in the heart of community,people's attention on selecting tombs and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respecting coffin and graveyard.Novels also recorded some grave digging phenomena that people could understand,such as the lawsuit,etc.The rich and valuable historical information which preserved in these novels had a high historical value for studying the social life.
Tang Dynasty and Five Dynasties;novels;digging grave phenomenon
I207.41
A
1673-4343(2014)03-0076-04
2014-01-19
杨亚男,女,安徽宿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