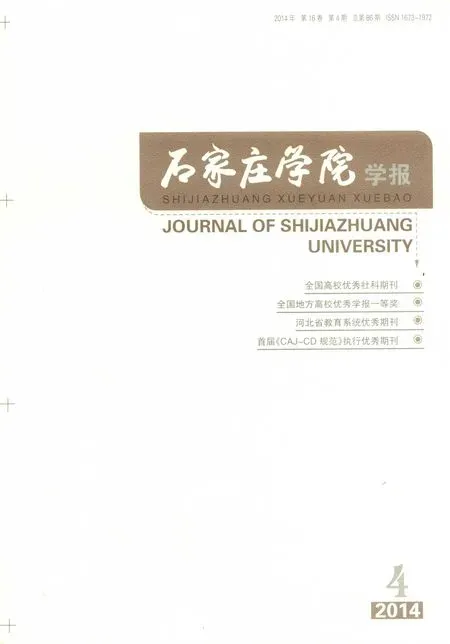以自己的话语言说人生
——论《乡里旧闻》
张占杰
(石家庄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35)
以自己的话语言说人生
——论《乡里旧闻》
张占杰
(石家庄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35)
晚年的孙犁历尽沧桑,洗尽铅华,他所失去的并不是进取之心和呼唤之力,而只是更多地关注内心真实的感受,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价值观念,以难得的“赤子之心”面对世界。无论是在逝去的世界中咀嚼人生,还是接续小说家散文的余脉,《乡里旧闻》的写作宗旨在于寻找自己的话语方式,以表现云淡风轻之后孙犁对于这个世界的独特认识。
孙犁;话语方式;小说家散文;文体
晚年的孙犁有两部系列作品,一部是《芸斋小说》,另一部就是《乡里旧闻》①从1980年开始,孙犁以《乡里旧闻》为总标题,另以不同的小标题,系列描述了少年时代在故乡见闻的行行色色的人物和离奇曲折的平常故事。文中未标注之文献均出自孙犁《乡里旧闻》,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芸斋小说”已经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一时成为热点,出现了大量的专题论文,细致梳理了它的内容,初步探讨了它的文体,视点不一,意见纷呈。相比而言,《乡里旧闻》的研究略显不足。到目前为止,专题研究论文有三篇,一是傅瑛的专著 《我读孙犁》中的 《清风朗月识人生——读孙犁系列散文〈乡里旧闻〉》,二是郭志刚专著《荷塘纪胜——论孙犁的散文》中的《“但愿人间有欢笑”》,三是滕云的《孙犁十四章》中的第六章《散文孙犁》的第二节《志人之什》之三《乡里笔记》。除此之外,更多的是在论及孙犁散文的内容、风格时将它作为例子提及。整体来看,我们对《乡里旧闻》独特价值的挖掘并没有像“芸斋小说”那样深入、全面。本文试图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对《乡里旧闻》的内容、文体特点、所蕴含的美学追求及意义作一次较为全面的阐释,以就教于方家。
一、在逝去的世界中咀嚼人生
《乡里旧闻》所写大都是自己的远亲近邻,有些有接触,有些只是听说,孙犁从他们的经历中找到与自己晚年思想、情绪的契合之处,无关“进取”,不需“呼喊”,抛却各种意识形态有形与无形的束缚,对人生的滋味重新咀嚼。《乡里旧闻》是晚年孙犁的人生启示录,表现的是“这一代人的心情”[1]230。
《乡里旧闻》将关注的目光集中于小人物身上,从他们多舛命运中感受人生的无常。孙犁选择的人物大多是农村中的边缘人物,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就甘于这种边缘化,边缘化是挣扎之后的结果。每个人都有自己辉煌的时刻,充满一股人生豪气,但又因各种机缘走上穷途末路,感觉命运不是自己可以把握的,没有了以一己之力闯出一片天地的乐观情绪,剩下的时光更多地用来品味人生的苦涩,孙犁与此心有戚戚。《第一个借给我红楼梦的人》中的刘四,家中有四兄弟,老大在家,其余三人早年都下了关东,去寻找自己的未来。在农村中,出外闯生活,衣锦还乡当然有面子,叫人艳羡;空手而归之人,则会遭受村中人更大的歧视。兄弟三人闯关东没什么收获,结果是:“老二一直没有回过家,生死存亡不知。老三回过一次家,还是不能生活,只在家过了一个年,就又走了。听说他在关东,从事的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勾当。”“老四在将近中年时,从关东回来了,但什么也没有带回来”,还曾染上吸毒的毛病①孙犁在一篇《书衣文录·戚序石头记》中说他“以吸毒落魄死”,滕云先生据此推断:“刘四下关东期间染上吸毒,落魄返乡后,不为兄嫂所容,生活无着的他,却仍穿着先前阔过时候穿的长衫,在村街上‘蛇摇担晃’地行走,让村人告诫子弟莫学此人形状。后来就有了刘四到集上帮工,醉归遭祸情事。”参见滕云《孙犁十四章》第33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这就注定了老四被看瘪的地位。孙犁并没有描写刘四年轻时是什么样子,但中年落魄,在集市上帮人家卖肉时的动作和精神使我们依稀看到他早年的风采:“他高大的身材,在一层层顾客的包围下,顾盼神飞,谈笑自若。”“他站在肉车子旁边,那把刀,在他手中熟练而敏捷地摇动着,那煮熟的牛肉、马肉或是驴肉,切出来是那样薄,就像木匠手下的刨花一样,飞起来并且有规律地落在那圆形的厚而又大的肉案边缘,这样,他在给顾客装进烧饼的时候,既出色又非常方便。他是远近知名的‘飞刀刘四’。”然而,他命运不济,自我失控,最后落得醉酒抢劫,随后被冤杀的结局。《玉华婶》中的玉华婶,父亲因偷盗被正法,母亲好吃懒做,将赌注压在女儿身上,而玉华婶本人却是“窑变”,“十三四岁的时候,在街头一站,已经使那些名门闺秀黯然失色。到十六七岁的时候,出脱得更是出众,说绝世佳人,有些夸张,人人见了喜欢,却是事实”。“论人才、口才、心计,在历史上,如果遇到机会,她可以成为赵飞燕,也可以成为武则天。”但她生在穷乡僻壤中,父母又有劣迹,只好嫁了一个比自己大许多的老光棍春瑞叔,还因家庭纠纷跳井自杀未遂,最后在家里支起了牌局,陪男人们喝酒、吸烟、打麻将,以此为生计,晚年更是泼得出奇,同儿媳们打架、对骂,谁还能看得出她就是当年那个拥有罗敷式的美貌、清纯之人?孙犁娓娓的叙述,重点不再是《白洋淀纪事》中对女人从外到内的优美展示,在女人身上寄托自己的理想,而是展现了一个女人挣扎、蜕变的历史,在残酷的人生中,咀嚼命运的每一次变化。孙犁晚年总结自己时说:“我们的一生,这样短暂,却充满了风雨、冰雹、雷电,经历了哀伤、凄楚、挣扎,看到了那么多的卑鄙、无耻和丑恶,这是一场无可奈何的人生大梦,它的觉醒,常常在瞑目临终之时。 ”[2]52-53此刻的孙犁,不再有什么幻想,他直面人生,无所顾忌,在这些边缘人物身上他看到了人生的无奈和命运的无常。他用平视的眼光看待他们,从而彰显人生更深一层的真实,作品虽然没有了早年纯美的理想色彩,但这种残酷的真实带给读者的是另一种审美享受。
孙犁以小说家的敏感,进一步揭示了这些乡村小人物的精神世界。他不再以革命伦理看待这些人,无论他们曾经有过怎样的不堪,曾经被多少人痛骂、蔑视、轻视、同情,他都很少作道德上的评判,而以悲悯的眼光注视着他们精神深处的翻江倒海。凤池叔身材高大,仪表非凡,是远近闻名的长工,“不只力气大,农活精,赶车尤其拿手”,很得地主们的赏识。但他的问题在于“太傲慢,从不低声下气”,因此常常失业,家徒四壁,死之前,将三间屋子卖掉才为自己出了一个体面的殡。即使这样,他仍一身傲骨,即使没有吃的,也从“不向别人乞求一口饭,并绝对不露出挨饥受饿的样子,也从不偷盗,穿着也从不减退”。孙犁以小说的笔触刻画了这样一个极度自尊的穷人形象。瞎周娶了媳妇,因为婆媳不和,和父亲分了家,一气之下下了关东,这在农村有点大逆不道。但在关东他也没有混上吃一个肉丸饺子的日子,被打瞎了眼,灰眉土脸地回来了,被村里人当做笑话,认为“这是他在家不行孝的报应,是生分畜类孩子们的样子”。孙犁并不只是写瞎周的命运,还以细致的笔墨写了他内心的波澜。父亲去世,按当地风俗,作为独子,他要打幡摔瓦,这块瓦在灵前摔,越碎越好。但他眼瞎了,主事人担心他摔不好,想让他儿子代替。“但瞎周断然拒绝了,他说有他在,这不是孩子办的事。这是他的职责,他的孝心,一定会感动上天,他一定能把瓦摔得粉碎。”于是,他默默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和练习,出殡那天果然一摔中的,瓦片摔得粉碎。从民俗理解,摔瓦是儿子对长辈最后的孝心,瞎周这样做,表明他的忏悔,也想在乡亲们面前找回自尊。这是一个有些鲁莽,但不失淳朴的农民。
艰难时世当中,农民们内心深处的善良会表现出难得的温情。这种温情有时是贫贱夫妻的一点和谐之音。菜虎以卖菜为生,他的小推车会发出连续的、有节奏的、悠扬悦耳的声音。“这是田野里的音乐,是道路上的歌,是充满希望的歌。有时这种声音,从几里地以外就能听到。他的老伴,坐在家里,这种声音从离村很远的路上传来。有人说,菜虎一过河,离家还有八里地,他的老伴就能听见他推车的声音,下炕给他做饭,等他到家,饭也就熟了。在黄昏炊烟四起的时候,人们一听到这声音,就说:‘菜虎回来了。’”这种温情有时是对弱小者和不幸者的同情。干巴生活艰难,老婆生孩子后没吃的被饿死,虽然孩子瘦弱、胆小、敏感,受到村中同龄人的欺辱,却是干巴生活的希望,但这点希望也随着孩子的意外死亡破灭了。乡亲们同情他,冬天他靠捡地里的黄豆、黑豆,磨成豆腐生活,“即使他在地头地脑偷一些,人们都知道他寒苦,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忍去说他”。他帮助村里人埋死孩子,母亲们在事情完毕,会给“干巴送些粮食或破烂衣服去,酬谢他的帮忙”。“这种工作,一直到干巴离开人间,成了他的专利。”这种温情有时是自己从晚辈羡慕的眼光中寻求的一点慰藉。愣起叔帮人做饭虽挣不了什么钱,除去吃喝,就是看戏方便,满足了他的个人爱好,因此,他懂得各种戏文,也爱唱,闲来无事便和孩子们一起搞个三弦弹唱,虽然热心的听众只有三祖父一个人,但也不亦乐乎,穷苦无着的阴暗生活因此增加了一抹亮色。刘四回到家乡,受到歧视,以说笑话寻求解脱,“有时,他坐在他家那旷荡的院子里,拉着板胡,唱一段清扬悦耳的梆子”哄小孩们乐,还和少年孙犁交朋友,借给他一部《金玉缘》。童真的孩子们不懂大人们的势利,这些失意者在与孩子的交往中找到了暂时的安慰。
《乡里旧闻》中还有另一组文章,包括《度春荒》,《吊挂》《锣鼓》《小戏》《大戏》《听说书》等,描写童年的经历或记忆中的风俗。孙犁清醒地意识到,“不管怎样说和如何想,回老家去住,是不可能的了”,“梦中每迷还乡路,愈知晚途念桑梓”[3]。他将一切都行诸文中,寄托自己的乡愁。人年老了,思乡;在外遭遇挫折了,也思乡。故乡,对于游子来说,是精神家园。孙犁对家乡的书写,对童年的回忆,也是一次次的精神返乡之旅,是在外遍体鳞伤之后,找个僻静之处一个人默默地舔舐伤口的过程。一旦关涉乡土、童年,书写者的语调便会变得温润、平和,充满了向往。正是带着这样的心态,孙犁所写的故乡风俗、人情,便有了一种诗意在其中。《度春荒》写的是故乡春天的饥饿以及孩子们觅食的经历。春天的冀中,即使没有兵荒,秋天的粮食也十之八九接济不上,孩子们的主要工作是到野地里剜可以吃的野菜。孙犁描写的正是冀中春天最为常见的“风景”,但在他的描写中,已经没有了饥饿带来的愁苦情绪:“在春天,田野里跑着无数的孩子们,是为饥饿驱使,也为新的生机驱使,他们漫天漫野地跑着,寻视着,欢笑并打闹,追赶和竞争。”“春风吹来,大地苏醒,河水解冻,万物孳生,土地是松软的,把孩子们的脚埋进去,他们仍然欢乐地跑着,并不感到跋涉。”“清晨,还有露水,还有霜雪,小手冻得通红,但不久,太阳出来,就感到很暖和,男孩子们都脱去了上衣。”“为衣食奔波,而不大感到愁苦,只有童年。”孙犁还深情地回忆了故乡春节时的吊挂和锣鼓,在这些白描中,透露出故乡人民节日的情趣。“每逢新年,从初一到十五,大街之上,悬吊挂。”“吊挂是一种连环画。每幅一尺多宽,二尺多长,下面作牙旗状。”“吊挂的画法,是用白布涂一层粉,再用色彩绘制人物山水车马等等。故事多取材于封神演义,三国演义,五代残唐或杨家将。其画法与庙宇中的壁画相似,形式与年画中的连环画一样。”节日里另一活动就是敲打锣鼓。这些锣鼓平日放在家庙中,春节拿出,放在大街上供人娱乐。“其鼓甚大,有架。鼓手执大棒二,或击其中心,或敲其边缘,缓急轻重,以成节奏。每村总有几个出名的鼓手。遇有求雨或出村赛会,鼓载于车,鼓手立于旁,鼓槌飞舞,有各种花点,是最动人的。”故乡迷人的风俗除了节日的欢乐外,还有平日里的各种仪式活动。如“大戏”和“小戏”,孙犁都进行了生动的描写。农村中的丧事分两种,一种是横死、早亡,死者早早地被掩埋,除了一家人的悲声,没有任何鼓乐伴随。另一种则是家中老人寿终正寝,这样的丧事称为喜丧。家中亲人尽可悲痛万分,村中其他人则如过节一般。大家对其家人及亲戚朋友的悲伤程度评头论足,也会围观吹奏音乐的人、念经的道士,“出殡时,他们在灵前吹奏着,走不远农民们就放一条板凳,并设茶水,拦路请他们演奏一番,以致灵车不能前进,延误埋葬。经管事人多方劝说,才得作罢”。这只是一种冀中农村的丧葬风俗,“灵前有戚戚之容,戏前有欢乐之意”。孙犁充分理解这种风俗所蕴含的乡村伦理,认为“中国的风俗,最通人情,达世故,有辩证法”。百姓之所以如此,除了对生死理解的豁达之外,更多的是“平日文化娱乐太贫乏的缘故”。丧事吹奏是“小戏”,除此之外还有“大戏”,“农村唱大戏,多为谢雨”。唱戏一般是三天三夜,小伙子为表现力气,扒台板看戏,“唱大戏是村中的大典,家家要招待亲朋;也是孩子们最欢乐的节日”,他们有四大高兴,“新年到,搭戏台,先生走,媳妇来”。足见大戏在村中人心目中的地位。这是农民们的集体狂欢,也是农民们娱乐精神的生动体现,使他们在穷苦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一次喘息的机会。
二、小说家散文
文体的选择,必须充分体现“艺术家个人的感知现实生活的方式和对生活认识的深度和广度”[4]292。晚年的孙犁,有一种强烈的“过来人”心态,不再迷信,不再轻狂,洞察人生几微,看穿堂皇语言下不可告人的企图,强调以个人的视角省察曾经的生活,对历史、社会、人生做出自己的解读。创作不仅需要激情,还需要理智,孙犁也极力寻找适合这种内容的文体形式。滕云先生曾对《乡里旧闻》的文体做过精彩的描述,他说:“孙犁的‘乡里旧闻’一类作品,是纪实的散记体、随笔体写作,不是常规的人物速写、人物素描,写法是点彩法或点染法,不是单线平涂。这些乡里笔记不是即时写作,它们拉开了与当年的时间距离,但又不同于历史记事,不同于小说,而介乎小说与方志之间,介乎文学特写与历史记载之间。朴朴素素的讲述中,有诗情,有哲思。悠淡深浓的怀旧意绪里,有弃旧望新的情怀。作者以个性鲜明的叙事风格,写出关于乡土乡民的一篇篇文学笔记,绘出了旧时代中国北方农村的一幅幅艺术册页,唱出了关于乡土农民的一曲曲田野之歌、道路之歌、希望之歌。”[5]335-336一言以蔽之,这是一种小说家的散文。小说家散文是“五四”后文学散文的一种形式,1930年代发展成型,以鲁迅、巴金、沈从文、茅盾、靳以、芦焚等人的作品为代表,在书写真情实感和真人真事的基础上,注重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场景和片断,客观、切实地描绘社会生活,比较细致地刻画人物形象,注意结构完整严密,融化了短篇小说的某些观照方式和表现方法,使散文带有某些小说化倾向。
《乡里旧闻》在文体方面,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乡里旧闻》以小说家观照社会人生的方式写散文,在民间伦理与人物现实处境的冲突中表现人物的命运,于不同寻常的行为中展现复杂的内心体验,在司空见惯的人生中透露出深刻的悲剧性。《木匠的女儿》中的进善,木匠出徒以后结婚、过日子,“附近村庄有些零星木活,比如修整梁木,打做门窗,成全棺材,就请他去做,除去工钱,饭食都是好的,每顿有两盘菜,中午一顿还有酒喝。闲时还种几亩田地,不误农活”。但这种悠闲随着儿女出生,老婆去世而结束。女儿小杏被人勾引,堕落,二十几岁上便得病死去。儿子“经过一些坏人引诱怂恿,带着县长的两支枪,投降了附近的炮楼,当了一名伪军”。因其无恶不作,名声很坏,被八路军枪毙示众。抗战胜利后,进善因为手艺好,被要求去修抗日纪念塔。但他是汉奸家属,一双儿女又以那样一种名声死去,“工作之暇,他也去看了看石匠们,他们正在叮叮当当,在大石碑上,镌刻那些抗日烈士的不朽芳名”,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与个人的悲剧中,他难以自拔,“回到家来,他孤独一人,不久就得了病”,“过去相好的那些人,都被划成地主或富农,他也不好再去找他们。又过了两年,才死去了”。孙犁的叙述徐缓而有节制,进善前后生活的对比,共同的节日和个人的悲凉的反差,自有一种凝重、拨动心灵的力量。
第二,《乡里旧闻》将对普通农民悲剧命运的小说化书写和作者的感发紧密结合,共同完成作品的主题,使被忽略的另一种历史和人生焕发了光彩,也为孙犁的“郁结”找到了独特而完美的表现形式。孙犁认为,“所谓感发,即作者心中有所郁结,无可告语,遇有景物,能而发之,形成文字,韩柳欧苏之散文名作,无不如此。然人之遭遇不同,性格各异,对事物的看法不同,因之虽都是感发,其方面,其深浅,其情调,自不能相同,因之才有各式各样的风格”[6]182。“感发”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在《乡里旧闻》中的表现,或见解透辟,情感丰盈,闪耀着作者人生智慧的光芒;或由人物的境遇引发联想,洞悉人生和历史的幽微;或对人物的行为及其背后的心理动机进行深入的理解,拨开层层包裹,直抵事物核心。这些无处不在的联想、感慨和引申扩大了这组散文的艺术容量。孙犁以个人的阅历,对小杏逐渐堕落的过程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贫苦无依的生活,在旧社会,只能给女孩子带来不幸。越长得好,其不幸的可能就越多。”“绝望之余,她从一面小破镜中,看到了自己的容色,她现在能够仰仗的只有自己的青春。”“女人一旦得到依靠男人的体验,胆子就越来越大,羞耻就越来越少;就越想去依靠那钱多的,势力大的。这叫做一步步往上依靠,灵魂一步步往下堕落。”正是基于对人物心理和行为逻辑的理解,他的描写才显得含蓄而隽永,处处透露着自己的惋惜与感伤。孙犁因为是 “过来人”,能够理解像老焕叔这样的农民的行为,他才能为老焕叔画一幅出神入化的肖像。老焕叔 “身材魁梧,仪表堂堂”,幼年随父亲到山西做过买卖,还当过巡警和衙役,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在村里虽然难言正派,却也有其所长。因为在穷乡僻壤中,“乡野之民,不只怕贼,也怕官。听说官要来了,也会逃跑”。这样,“每逢兵荒马乱之时,总需要一个见过世面,能说会道的人,出来应付,老焕叔就是这样的人”。孙犁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乡村保护者的形象,尽管老焕叔身上有种种毛病,他还是受到乡亲们的包容、尊敬。在文章的附记中,孙犁以历史研究者的身份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老焕叔:“如写村史,老焕叔自当有传。其主要事迹,为从城市引进麻将牌一事。”孙犁借此又写了农村混混曹老万的恶行。以一句“古人云:不耕之民,易于为非,难于为善。这句话,还是可以考虑的”结束全文,其联想、总结给人以无穷的想象空间,使读者参与到文本的建构中,韵味悠长,这就是孙犁感发的妙处。
《乡里旧闻》有着一般散文所没有的小说化书写,但它仍然是典型的散文文体,关键就在于其中的“感发”,这组散文由“感发”而来,又以“感发”的方式表达,引人联想、慨叹、会心一笑,豁然开朗于作者的点睛之笔。“感发”是这组散文的灵魂所在,也是孙犁的艺术精湛之处。
第三,白描中透出的语象功力,突出了这组散文抒情的蕴藉风格。白描是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中经常使用的写作手法,它不饰雕琢,专注于形象本身特点的勾勒,作者的思想、情感不着痕迹地传达出来。孙犁有意识地将白描手法运用于散文中,构成了他散文独特的风格。《乡里旧闻》中的白描手法,突出在于作者对语象的运用。所谓语象,是“作品中随着文学语言的使用,在微观层次(句子、句群、段落)上所出现的小的画面、片断的情境”[7]376。《乡里旧闻》中,孙犁寥寥几笔,或使人物的声口、神态栩栩如生,跃然纸上;或使生活场景或生活画面活灵活现;或勾勒出优美的意象,传达出动人的情致。如《瞎周》中和尚爷的描写:“虽叫和尚,他的头上却留着一个‘毛刷’,这是表示,虽说剪去了发辫,但对前清,还是不能忘怀的。他每天拿一个小板凳,坐在门口,默默地抽着烟,显得很寂寞。”“毛刷”“发辫”“抽烟”,几个关于人物形态和精神的关键词,就将和尚爷的神情和精神呈现于读者面前。再如《根雨叔》中对根雨叔的描写:“根雨叔从早到晚在磨坊里工作,非常勤奋和欢快。它是对劳动充满热情的人,他在这充满秽气,挂满蛛网,几乎经不起风吹雨打,摇摇欲坠的破棚子里,一会儿给拉磨的小毛驴扫屎填尿,一会儿拨磨扫磨,然后身靠南墙,站在罗床踏板上:踢踢跶,踢踢跶,踢跶踢跶踢踢跶……筛起面来。他的大辫子摇动着,他的整个身子摇动着,他的浑身上下都落满了面粉。他踏出的这种节奏,有时变化着,有时重复着,伴着飞扬洒落的面粉,伴着拉磨小毛驴的打嚏喷、撒尿声,伴着根雨叔自得其乐的歌唱,飘到街上来,飘到野外去。”这一描写,有声音,有形象,根雨叔内心的满足和作者欣赏的态度紧密结合,语象纷呈,作者的抒情蕴含于白描之中,感情饱满而含蓄。深厚的语象功力是孙犁长期浸淫中国古典文学的结果,也是他人到老年,世事洞明,崇尚自然、含蓄的结果。阎庆生教授认为:“正是靠着包括‘语象’功力在内的综合素质的跃升,才使得他晚年的散文与早年的散文的散文艺术品位和美学境界相比,出现了很大幅度的提高,并藉以获得了‘散文大师’的声誉。 ”[7]378-379诚哉斯言!
三、寻找自己的话语方式
晚年的孙犁,历尽沧桑,洗尽铅华,文学上更关注内心真实的感受,以“赤子之心”面对生活。无论是在逝去的世界中咀嚼人生,还是接续小说家散文的余脉,《乡里旧闻》的写作宗旨在于寻找自己的话语方式,以表现云淡风轻之后对于这个世界的独特认识。
对自己的话语方式的寻找,使他回归了五四时期所倡导的人道主义精神。1940年代以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解放区文学发展的规范作用日益凸显,进一步影响了新文学发展的走势。随着新中国成立,新文学在整体上最终完成了由“人的文学”向“人民文学”的转型,开启了新文学的“人民文学”时代,作为标志,并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国家抒情体制,从制度上排斥文学观念的多元状态,文学创作无条件服从于政治路线和政治需要,以阶级论为基础观照人和历史,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在作品中有着十分突出的表现,人物在作品中的主次地位、评价,都有着严格的标准。革命意识形态对创作的深层介入,使作品越来越模式化,文革中的“三突出”,是这种模式发展的必然结果和登峰造极。《乡里旧闻》是一种回顾,固然有眷恋、缅怀,但孙犁更多的是咀嚼,在现代人道主义视野中发现了一群用主流的观念无法定位的边缘人物,他们日常生活的道德、行为或许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他们同样是值得尊重的个体,有着自己的人生轨迹和命运,正因为社会地位低下,即使在农村也多被看不起,他们的人生、命运显得更为曲折,有着较一般人更真实、更深刻的人生体验,精神世界更丰富,这才是孙犁所关心的。这种对小人物的关注、理解和悲悯,以人道主义的视角观察人物、体察人生的方式,与五四文学精神一脉相承,又与新时期人道主义思潮相呼应。《乡里旧闻》的特别之处在于,孙犁采取内化诗情的方式,在对往事的随想回忆中,把自己的爱与恨、痛苦与欢乐、希冀与失落化为一种凝重的感情,淡淡流出,渗透了自己对现实人生的审美判断。这里的每一个句子,都不是轻易写下的,浸透了血泪和忧思,刻在作家生命的年轮里。“文革”的痛苦经历促使他更殷切地寻觅流逝的理想、道德、人性、人情。现代人道主义观念引导了他对生活的认识,帮助他找到表达的切入点。人道主义在他的作品中并不是抽象的、概念的,是和他对生活的认识、理解融为一体的。
对自己话语方式的寻找,使他突破了“文革”前十七年散文创作的僵化模式,以自己的实绩启示新时期的散文创作:散文是一种实录,容不得任何情感意态和事实的虚假,这是对五四和古代散文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是一种拨乱反正。古代散文就文体而言,多是应用文体,其基本要求是说真相,抒真情,否则就失去了这种文体的立身之本。五四散文在现代人道主义语境中,更是把真实作为它的第一要务,这才出现了风格各异、精彩纷呈的五四散文的繁荣,才有朱自清等人所认为的其成就在小说、诗歌之上的论断。[8]406建国后,随着国家抒情机制的建立,以杨朔、刘白羽、秦牧为代表的作家,以“大我”的身份、颂歌的方式抒发阶级的、集体的感情,散文话语中只有现成的政治信念和伦理道德,无视现实,千篇一律。这一创作倾向,一直延续到新时期文学中,正如孙犁所指出的,“不少散文,缺乏现实主义精神。本来散文不同于小说,现实意义,理所当然地应当大些、多些,其实不然。有些作品虽然是记事写景,但因为作者的立意不妥,就使所记之事,所写之景,失去了本色本性。这里说的立意不妥,包括浮夸不实,自我卖弄,要求功利,哗众取宠等等”[6]230。
《乡里旧闻》最突出的美学品格在于它的实录性——说真相、抒真情。《乡里旧闻》书写的是一种赤裸裸的现实,使后世的我们有幸看到历史的另一面。在《老刁》中,我们看到革命者在抗日的同时,也会时刻惶惶恐恐地经受着来自组织的扩大化审查,也会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消失。1946年,孙犁将这一故事的主要内容改头换面创作了《琴和箫》,和其他同时期昂扬的作品不同,它自始至终弥漫着忧伤,显示着孙犁对眼前的一切的迷茫、不解。[9]作品发表了,又想叫人忘记,多少年不将这篇杰作收入文集中,直到晚年才释然。在孙犁的抗战小说中,从来没有像《木匠的女儿》中所写的那样一个家庭复杂:女儿出卖抗日县长,儿子当伪军,父亲抗战后以汉奸家属的身份去修抗日烈士纪念塔。孙犁小说中的人物,都是一些单纯、热情的小儿女,即使是《风云初记》中的俗儿,也透着几分可爱,完全没有原型小杏的那种忧伤以及作者深深的悲哀。农民以民间伦理对待抗战中的敌我,它构成了《乡里旧闻》中所写抗日战争的日常生活,这和主流意识形态下大多数文学作品中的抗战生活是完全不同的图景,是我们以前很少领略的抗战历史描写。孙犁的抗战小说表现的是一种文学真实,《乡里旧闻》则是一种历史真实,是作者的实录。《乡里旧闻》还将笔触触及到一些新的领域和新的人物,如上所述,其中的人物都是农村中的边缘人物,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孙犁依回忆讲述,勾勒人物生活、命运的轮廓,实录生活原生态,不求其全面、完整,但它带来的是一种历史形态的乡村生活。每篇一二千字、二三千字,把乡间各色各别的人与事,逸事逸闻也罢,异事异闻也罢,喜也罢悲也罢,正也罢邪也罢,若断若连,组成了时代的旧事载记,乡村的旧闻实录。“虽然这是一个不到一百户的小村庄,但它也是一个社会。它有贫穷富贵,有尊严耻辱,由士农工商,有兴亡成败。”[10]184我们不禁联想到1990年代出现的新历史小说,对历史的书写摒弃了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单一视角观察、诠释历史模式,注重被革命意识形态的“正史”回避、忽略、遗漏的那一部分历史生活,创作主体深深介入作品,重新解说历史或消解原有的历史观念。创作于1980年代的《乡里旧闻》虽然是散文,但所展示的观察历史的视角和历史观念,正是随后新历史小说所努力追求的。《乡里旧闻》和新历史小说相比,除了文体的差异外,孙犁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写作不是出于对某种理论的实验,而是出自人生经历和经验,对农村和农民的另一种审视,建构了农村的另一种生活史、风俗史,使我们看到了农民的精神世界,于不可捉摸的命运中,他们以怎样的方式与命运抗争、妥协。总之,孙犁对他们的勾勒,已经摆脱了“人民文学”语境中对农民、农村变迁史中观察、理解原有的主流意识形态视角,其评价也超出了革命语境的价值规范。无意间,《乡里旧闻》启示了新历史小说,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晚年孙犁的一大贡献也不为过。
无论是过去还是当前,以实录精神表现历史,对作者来说都是不容易的,他不仅需要历史精神,也需要表现的勇气,孙犁在晚年的一篇读书记《读〈史记〉记(上)》中这样说到实录者的甘苦:“事理本不可分。有什么理,就会叙出什么事;叙什么事,就是为的说明什么理。作家与文章,主观与客观,本是统一体,既无所谓主体、客体。过于强调主体,必使客体失色;同样,过于强调客体,亦必使主体失色。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也是很难做到的,要有多方面的(包括观察、理解、文辞)的深厚的修养。因为既辩,就容易流于诡;质,就容易流于俗。辩,是一种感情的冲动,易失去理智;文章只求通‘俗’哗众,就必然流于俚了。至于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就更非一般文人所能做到。因为这常常涉及到许多现实问题,作家的荣辱、贫富、显晦,甚至生死大事。所以这样的文章著述,在历史上就一定成为凤毛麟角,百年或千年不遇的东西了。”“希望当代的文士们,以这三十个字为尺度,衡量一下自己写的文字,有多少是直的,是可以核实的,是没有虚美的,是没有隐恶的。”[2]240-24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犁在这组散文中,清除了散文的“杨朔模式”,强调“小我”的存在,以五四时期开创的现代人道主义精神统摄人物和历史,显示出独特的识见,呈现出散文久违的个性特点,在继承传统、重建散文的风骨精神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孙犁.致李蒙英[M]//孙犁.芸斋书简.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
[2]孙犁.如云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
[3]孙犁.老家[M]//孙犁.无为集.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
[4]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5]滕云.孙犁十四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6]孙犁.陋巷集.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
[7]阎庆生.晚年孙犁研究——美学心理学的阐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8]朱自清.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M]//俞元桂.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
[9]叶君.感伤及其他:一个故事的三种写法——关于孙犁《琴与箫》的症候式阅读[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14-17.
[10]孙犁.木匠的女儿[M]//孙犁.澹定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 周亚红)
A Review of Sun Li’s Anecdotes of My Hometown
ZHANG Zhan-jie
(School of Arts&Communication,Shijiazhuang University,Shijiazhuang,Hebei 050035,China)
Sun Li had gone through a great many changes in his later years and returned to nature.However,he never lost an enterprising heart and voice to call.H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his true feelings,trying to find the values of his own,in the face of the world with a rare “utter innocence”.Chewing life in the passed world,or following the flows of a novelist’s prose,his writing purpose of Anecdotes of My Hometown is to find their own way to show his unique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Sun Li;discourse;novelist’s prose;style
I207.42
A
:1673-1972(2014)04-0076-07
2014-04-24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新文学传统建构中的孙犁”(HB12WX013)
张占杰(1964-),男,河北衡水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