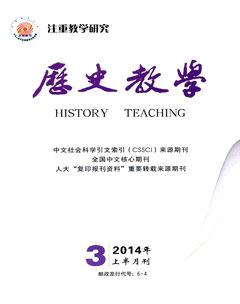《宋明理学》教学研究
关键词:明理学,中学,教学
《历史教学》2013年6月上半月刊刊载了李凯老师的《高中必修课程“宋明理学”教学分析》一文。作者从思想史发展的脉络出发,提出“挑战——应战”的线索,使人深受启发。思想史既是“思想”,也是“历史”,除了从思想史的内在逻辑去理解思想本身外,也要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探讨。如教材所言,儒学危机从魏晋以来便已存在,那为什么要等到宋朝提出理学才得以成功应对呢?笔者试图在此基础上补充宋明两朝的一些社会历史背景,并以此来贯通理学的内容和影响,最后对两个重要概念做一些辨析。
我们知道宋代理学家们的使命就是要重振儒学,原因除了应对佛、道的冲击和挑战外,还与宋朝特殊的社会背景相关:一方面,唐末五代以来政权的频繁更迭使国家权威失坠,如何确立北宋新政权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便成为统治者和士大夫阶层共同关心的问题。通过必修一的学习,我们已经知道,宋初统治者通过“杯酒释兵权”、改革中央和地方官制,从权、钱、兵全面加强中央集权,巩固了新政权。这是政治家从政治层面来树立国家权威的做法,而从思想层面看,“士人相信,中唐以来国家权威的失坠,是由于社会的道德沦丧、伦理崩坏,人们对国家合法性与秩序合理性的漠视,正是这种观念的松懈和自觉意识的消失,使历史出现了这样的危机,长达两个世纪的变动,曾经给士人留下相当痛苦的回忆和相当深刻的印象,也刺激了重建国家与思想秩序的想法”。①正所谓“欲治其末,必端其本”,士大夫阶层认为国家权威的基础不仅要建立在政治权力上,更要建立在社会伦理道德和文化心理上。
另一方面,“古代中国人总是有这样的习惯,他们认为中国不仅在空间位置上是‘天下的中心,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在文明意义上是‘天下的中心”。②宋朝虽然结束了中原地区的分裂和混乱,但统治疆域与和唐朝已不可同日而语,不得不与强大的异族政权辽、西夏等并立,这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宋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既然现实不能让宋人在地理空间上确立俾睨四方、君临万国的豪迈和自信,那么就更需要在思想文化上“尊王攘夷”,确立其在文明上的“正统”地位。而当时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夷”主要是佛教,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孙复在《儒辱》中,极力申斥“(佛老)绝灭仁义,摒弃礼乐,以涂窒天下之耳目”,呼吁捍卫儒家学说。另一宋儒石介在《中国论》和《怪说》中也极力抵御瓦解“中国之常道”的佛教,因为它“灭君臣之道,绝父子之情,弃道德,悖礼乐。裂五常,迁四民之常居,毁中国之衣冠,去祖宗而祀夷狄”。③也就是说,在当时思想价值观普遍混乱之下,清理思想和信仰的边界,抵御佛老等思想的入侵,重新确立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也是宋朝建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需要。
总之,无论是要树立国家权威还是建立民族自尊心,宋朝都需要重整伦理纲常,凸显儒学的重要性。但是在当时佛、道盛行而儒学又有着明显缺陷的背景下,这谈何容易?简单重复过去的经典显然是走不通的,正如岳麓版课本里开篇提到的:“随着时代发展,社会进步,汉代儒学粗糙的天命思想以及唐代儒学大师韩愈《原道》‘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上则诛之类赤裸裸的恐吓已经无法控制人心,所谓‘儒门淡薄,收拾不住。”所以,必须为传统儒学找到一个永恒性的精神基础。在历经了魏晋以来几百年的三教论争、融合之后,到了宋朝,被动应战也好,主动学习也好,总之宋儒吸收了佛道理论性和思辨性的精华,经过重新整合,为传统儒学找到了一个形而上的根本依据——“理”。由于对“理”的认识和理解不同,理学内部分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个派别。
程朱理学认为“理在事先”,即“未有这事,先有这理”。如,一棵树生长出来,它的基本特性,在此树前早已存在。所以,一事物必须是合乎某种理才能出现,比如马生牛,断无此理。“由此,又可得一结论,即一切事物的法则,包括人类社会的各种原则都是永恒存在,而且不会改变的”。①既然“理”是永恒存在的,而“理”体现在社会上是儒家伦理道德,所以儒家的伦理道德是永恒存在的,再推之,我们必须去遵守它们。这样儒家伦理道德的合理性得到了哲学层面的高度认证。但这只是理论的前提,要真正践行儒家的伦理道德还需要解决一个现实的问题。那就是“理”虽然是“天理”,是永恒的,但也是客观的,独立于人身之外的;而人内心不可否认有“人欲”,人心在欲的支配下随时都有沉沦的危险。当两者产生冲突的时候,就要“存天理,灭人欲”。因此“存天理,灭人欲”的实质就是“把世俗的情欲与纯然的天理分开,在对世俗欲望和感情的克制中,使人渐渐提升到天理的高度”。②这个提升的过程是一个相当艰辛的学习和修炼过程,“格物致知”正是这一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步骤。这就是程朱理学的要义:用外在高尚的道德律令来约束内在的沉沦的人心,从而建立合理的思想和社会秩序。我们可以把程朱理学的这个特点概括为“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所谓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通常对人的道德伦理境界提出相当高的要求,即要求人们对自己的心理与行为有自觉的认识与反思……在普遍认同的基础上,不通过国家法制的强制性约束,便确立一种符合理想的社会秩序”。③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也同样如此。一方面,“宋明理学细密地分析、实践地讲术‘立志‘修身,以求最终达到‘内圣外王‘治国平天下,把道德自律、意志结构,把人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人优于自然等方面,提扬到本体论的高度,空前地树立了人的伦理学主体性的庄严伟大”,④这塑造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道德的优良品质。但另一方面,把道德理想拔得太高,在“以理统情”中,“理”的成分远大于“情”的成分,就容易走向反面,变成压抑人性了。尤其是当这种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从最初的由士人自发地去实践,变为后来被统治者所利用,将其转化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规范,大力宣扬,甚至以礼入法,这就产生了消极影响。正如戴震所抨击的那样,“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理学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都由这种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而来,而又与宋朝特殊的时代背景相关。endprint
心学是对程朱理学的反动,虽然在南宋已初步兴起,但其发扬光大是在明朝中后期。这与王阳明的个人经历及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王阳明青年时代深受朱熹影响,严格按照其格物之学进行修炼,不但没有得到所谓的理,反而更困惑了。在王阳明生活的明中期,宦官当权、皇帝荒淫无道、吏治腐败,社会世风日下,农民起义不断。王阳明认为正是学术流弊导致道德沦丧,从而引起社会动荡。那么程朱理学的弊端在哪里?一方面,程朱理学严辨“天理”和“人欲”,用外在高尚的道德律令来约束内在沉沦的人心,从而建立合理的思想和社会秩序。尽管其出发点是好的,让人对自己的“私欲”时刻保持警惕,“但理被提高为强大的客体权威,而限制了主体在建立道德自觉的能动性”。①另一方面,作为官方哲学的程朱理学已逐渐被异化,成为高高在上的训诫律令和考取功名的敲门砖。在这内外双重作用下,程朱理学到这时已变成束缚人心的教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王阳明提出“心外无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思想主张。而“致良知”又是王阳明思想的核心。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理解:
第一,良知虽然人人现成具有,但常常受到私欲的遮蔽,所以就要致良知。“‘致首先是扩充,就是使良知扩充至极。另一方面,‘致又表示实实在在地力行、践行,把人的良知努力地实现出来,变为具体的行动”。②所以,“致良知”本身也体现了“知行合一”。王阳明特别强调“行”,这是他比陆九渊进一步的地方,更是对朱熹“先知后行”的反动。他认为朱熹“先知后行”的观点恰好给那些只说不做的伪君子提供了借口,从而导致道德沦丧。他强调不能行的知就不是真知,要是真知必能自觉去行。王阳明自己一生的盖世事功是其“致良知”思想的最佳注脚。
第二,既然良知人人现成具有,只要自己不断反省内心,克服私欲,就能成为圣贤,在此基础上,王阳明进一步提出“人皆可为圣贤”。但反过来说,若不能成为圣贤,不在于客观条件不足,而是主观上不够努力,这就强调了自我的主动作用。“心学强调不应该把道德价值异化为纯粹外在的命令,必须把理变成主体的自觉意愿,道德应当以自律为基础”。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心学”冲破了教条化的程朱理学的束缚,在晚明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也只有从这个角度讲解,才能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理学重视主观意志力量”这个结论。
第三,我们过去一般会从哲学的角度来讲述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的差异,强调程朱理学是客观唯心主义,陆王心学是主观唯心主义。笔者认为没有必要在中学历史课堂里作如此深奥的哲学辨析,这节课的概念本来已经很多,再增加这两个哲学概念只会加重学生负担。而且受政治课讲授马克思唯物主义影响,学生很容易形成“唯心主义(尤其是阳明心学)是反动的”的结论。对于两者之间的差异,最好还是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去讲解。与程朱理学主要针对上层统治者和士大夫不同,王阳明“致良知”之教主要是面对下层民众。为什么会有这个区别,这得先从儒家的“得君行道”的传统说起。儒家学派一直有治国平天下的高远理想,怎么实现呢?就是君主在儒家士大夫的指导和辅助下施行仁政。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君主”,只有得到君主的支持才能施展抱负,这可概括为“得君行道”。宋朝以“重文轻武”政策立国,对士大夫特别优容,“更重要的,宋代皇权在积极方面还充分显示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雅量”,④宋神宗对王安石变法的支持便是活生生的榜样。这让理学家们看到了“得君行道”的希望。所以,宋朝时期的理学初衷一直主要以君主和上层统治者为立教的对象。但到了明朝,这种可能性变得很低。从明太祖开始就经常对读书人杀戮与凌辱,如著名的廷杖制度,就是明朝的创制。王阳明自身的经历(上封事、下诏狱、受廷杖到最后被贬龙场)也让其对统治者十分失望。正是在儒家传统的“得君行道”这条道路行不通之后,王阳明另辟蹊径,将目光转向下层,希望唤起民众的觉醒来挽救社会,这条道路可概括为“觉民行道”。可见,明朝政治生态的恶化是促使王阳明思想转向的主要原因。此外,明中叶以来,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层崛起,民间社会展现了空前的跃动。王阳明敏锐地察觉到社会的变化,“1525年他为一位商人写《墓表》便说了‘四民异业而同道这样惊人的话。他的语录中也常常出现‘须作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满街都是圣人等说法。可见他已将‘道的重任从士身上推拓出去,由所有社会成员(‘四民)共同承担了。这是他的良知说的社会背景”。①相对程朱理学“格物致知”的繁琐艰辛,王阳明的“致良知”简约易行,这与其针对下层民众的这个特点相辅相成。
心学是理学内部的分支,本质上也是一种理想化的道德主义。但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有着较大的差异,影响也有所不同。因此建议教师在教学中将其分开,而不是讲完两个派别的差异后一起笼统地讲宋明理学的影响。
最后,笔者还想补充分析“存天理,灭人欲”这个常被误解的概念。李凯老师认为“‘存天理灭人欲和佛教中的灭欲如出一辙”,这是不恰当的。二程认为:“耳闻目见,饮食男女之欲,喜怒哀乐之变,皆性之自然,今其(佛)言曰:‘必灭绝是,然后得天真。吾多见其丧天真矣。”(《二程粹言》卷一)朱熹说得很清楚:“若是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则此欲亦岂能无?问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朱子语类》卷十三)饮食是人的正常需求,是天理,但要过分追求美味,便是人欲。同理,夫妇之间的性关系是人伦的正当表现,而为满足自己的私欲引诱已婚的异性并破坏他人家庭便是人欲。这样看来,天理和人欲的界限就是一个度的问题。所以,“人欲”是指那些超出社会道德规范的过度欲望,并不是佛教的禁欲主义。而且“存天理,灭人欲”这一观点所诉求的对象主要是上层统治者。“‘存天理,去人欲说,从普通意义上讲,是修身立德之通则,可以适用于任何人。但从施行程序及社会效果方面讲,则是专对于政治上的统率者而指出的。因为中国的政治,向来是和伦理道德联系在一起,政治社会的好坏,与统治者的品德有重要的关系,所以宋儒提倡此说,总是先从帝王国君之正心诚意说起,然后才谈到治国行政的具体措施”。②其次,这句话也是对学者士人说的。朱熹说:“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朱子语类》卷十三)这是士大夫修身立德的准则。endprint
与“存天理,灭人欲”相比,程颐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更为一般人所误解。首先这句话原意并不只是针对女性才提出的要求,他认为如果男人娶寡妇为妻,也是一种失节行为。而且更重要的是所谓“节”本来指气节、节义,即广泛意义上的道德操守,而不特指贞节。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在其名篇《鱼我所欲也》中也阐述了“舍生取义”的原则,所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儒家一脉相承的道德原则,只不过它的表达更鲜明而已。“从道德观念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程颐或理学其他思想家并没有发明守节这一规范,程颐本人也只是在其门人将‘守与‘饿的选择提出来的时候,从舍生取义的普遍原理出发对既有的贞节规范作了伦理学上的强势的肯定。事实上,许多理学家(如朱熹)就并不绝对反对孀妇再嫁。”③
既然“存天理,灭人欲”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在理学家的本意中有着积极的意义,但为什么却在现实中产生了消极影响呢?除了思想家本人对其思想在不同场合阐述不完全一致,有时候使用定义不规范,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外,主要原因有以下四方面:
1.这些道德原则有着复杂的理论含义,尤其是“存天理,灭人欲”,一般只有知识分子才有研究的兴趣,普通民众很容易就望文生义。而且思想在通俗化过程中,往往会丢失一部分复杂的原意,以取得传播上的便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思想所产生的土壤已不复存在,其含义也容易被歪曲,特别是明中期以后,程朱理学已成为人们考取科举功名的敲门砖,逐渐失去以之寻求圣贤学问的精神。
2.“存天理,灭人欲”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一种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虽然主要针对的是上层统治者和知识分子,但上层的风气会引领下层。这里试举一例:“从现存各种文献来推测,北宋时代对于妇女身体的禁忌似乎没有那么严厉,十一世纪的宋仁宗能够在大庭广众之下,与众人一道观看‘妇人裸戏于前,大约当时并没有对裸露女性身体有异常感觉,可是司马光觉得,这是违背礼法的事情,要求‘今后妇人不得于街市以此聚众为戏,而一些高雅的士人也同样对这种事进行抵制,渐渐地,妇女裸体相扑的游戏再也不见于文献记载,想来是渐渐被禁止了,至少这种禁忌已经成为了‘共识,妇女身体在这种观念中,一方面成了不洁的象征,另一方面成了隐秘的东西。”①“所以,尽管在法律层面上或对普通民众上,它并不是通行的规则,但是作为一种理想主义的道德观念,由于它从拥有文化权力的士绅中被广泛接受与宗奉,于是,渐渐会通过来自士绅象征性表彰和来自政府的有意惩罚,成为民众中的普通道德与伦理规范。”②或者说:“儒家伦理必须褒扬那些不食嗟来之食的义士或自愿守节的烈女,但这种崇褒中隐含着一种危险,那就是有可能导致在不断的褒扬中把道德的最高标准当成了道德的最低标准,给一般人造成较大的道德心理负担。”③
3.“存天理,灭人欲”本来是针对统治者,体现了儒家努力约束专制统治的传统,但在元代以后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这些道德准则反过来被统治者利用,成为约束人们的思想工具。“统治者冒充为‘理的化身,片面强调被统治者的义务而抹杀其权利,其后果就会表现为普遍的道德压抑”。④
4.朱熹把“天理”和“人欲”绝对地对立起来,要求人们舍弃内在的“人欲”,服从外在的“天理”,“于是在两段之间就蕴涵了巨大的紧张,即肯定超越与承认现实之间的紧张,这种紧张虽然使人始终对自己的精神心灵有所警惕,但也使人永远处在肯定外在万物和内心情感与否定外在万物与内心情感的矛盾之中”。⑤这就容易引发人们对这个理论的反感。这是“存天理,灭人欲”带来消极影响的内在因素。
通过以上的辨析,我们搞清楚了“存天理,灭人欲”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本来面目,便会发现这些理论在去除其阶级和时代局限性后,对当下社会也是有一定价值和意义的。课堂上,教师可以联系现实社会中一些道德方面的例子来讲解,可让学生更有亲切感。
《宋明理学》一课概念比较多,又有一定难度,需要教师们仔细辨析。思想史的讲解除了注重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之外,更要结合具体的社会历史现实来理解。本文在这方面做了一点探索,希望能起抛砖引玉之效。
【作者简介】黄杏婵,女,中学历史一级教师,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石门中学教师,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学研究。
【责任编辑:吴丹】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