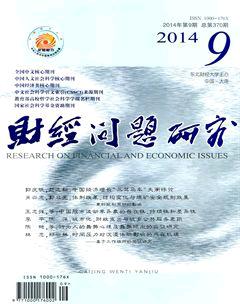中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失衡悖论
郭庆旺+赵志耘
摘要:在中国经济保持长达三十余年高速增长为世人瞩目的同时,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净出口的“比例失衡”也遭到垢病。本文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基于112个国家近四十年数据进行国际比较分析发现,中国的消费需求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疲软,经济增长也并非是出口导向型的,而近二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的确主要依赖投资拉动,但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投资过度。笔者认为,支撑中国长期高速增长的“三驾马车”“失衡”,实质上是一种宏观动态结构性均衡,或者说没有这种“三驾马车”的比例关系,也就没有这一时期的长期高速增长。展望未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经济增长战略在适度降低增长速度的同时转向创新驱动增长,“三驾马车”“失衡”自然会明显改观。
关键词:中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失衡悖论
中图分类号:F1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4)09000316
一、引言
近年来,社会各界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净出口的“失衡”垢病不断。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就把当时出现的投资膨胀现象比喻为“投资饥渴症”[1],表现出社会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投资过热的担忧。近十年来,由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中,投资贡献率明显高于消费贡献率,经济学界乃至社会各界形成了“投资依赖(驱动)型经济增长”的共识,甚至将此现象看成是粗放型经济增长的一个标志。与此同时,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出口大增,贸易顺差连年,于是经济学界又根据东南亚国家或地区曾走过的历程,将中国归类于“出口导向型经济”或“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国家”;又因21世纪初的头6年,中国进出口规模日益增大,经济学界又出现了“外贸依存度过高”的说法。基于这样的认识,社会各界普遍认为,中国依靠“粗放型”的投资和不可控的外需推动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于是,人们不约而同地专注于如何解决国内消费需求“不足”或“疲软”问题,纷纷开据药方,提出政策建议,政府为此也先后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刺激消费。
面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严重失衡或比例失调,有些学者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分析了其中的客观必然性。罗云毅[2]通过详细分析消费与投资比例的长期态势与短期波动、消费率与投资率的关系、居民部门消费储蓄比例的内在决定机制及政府调控政策的有效性等若干重要问题,认为“在我国目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低消费、高投资是我国经济运行的常态。”樊纲[3]指出,“保持总需求各部分的稳定增长,不能只强调消费增长,出口、投资都要平衡稳定地增长。这样一个比较平衡的政策符合现阶段中国的需要。”张军[4]认为:“一个可以理解的现象应该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总消费支出占GDP 的比重依然是低的,这是因为我们仍处在高增长、高积累阶段,每年要拿出很大部分去投资,提高人均资本存量和劳动生产率。”
笔者赞同上述学者的基本观点,同时更进一步地认为,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消费需求并非疲软,也很难说中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在中国过去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各种发展战略下,高速经济增长的“投资依赖”是一个客观的必然且相对合理的结果。
二、两个基本事实
1.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长期高速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甚至可以追溯到新中国诞生以来,平均来看,中国经济的高速增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中国在经历了1953—1977年25年平均经济增长率7.3%的较高增长基础上,到2011年又保持了34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率平均高达10%。即使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初,1953—2011年近六十年的时间来看,经济增长率平均也高达8.8%, 1953—1977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表3—3国内生产总值指数”计算而得;1978—2011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表2—4国内生产总值指数”计算而得。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根据世界银行按人均GNI对世界各国的分类,我们把目前人口在500万以上的112个国家分为四类,即低收入国家、下中等收入国家、上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 这里需要做两点说明:第一,各国的人口是2011年数据。第二,有些国家人口虽然超过500万,但因国情特殊(如长期内战或特殊体制等)而未列入(如阿富汗和朝鲜等);有些国家人口不足500万但接近500万,如哥斯达黎加(460万)、新西兰(440万)和挪威(490万),也纳入本文的研究范围。不过,在过去四十年里,许多国家在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不同收入水平组的变化,为了准确反映不同时期各国所处收入水平组情况,我们按5年一期划分各国所属类型。 鉴于世界银行的收入组标准最早始于1987年,故本文假定1987年以前的国家分组与各经济体1987年所属分组相同。
第一,中国为何能保持如此之久的高速经济增长?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探究了各种原因。在笔者看来,这完全可以一言以蔽之——用已提出的“中国模式”发展道路来解释。但何为“中国模式”?从Ramo[5]最初所说的“北京共识”,到最近张宇等[6]所总结的五点内容,张宇[8]等将中国经济模式的主要特征总结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新型市场经济体制, 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新型工业化和体制创新为动力的科学发展道路;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战略;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渐进式转型。众说纷纭,不一而足。在笔者看来,“中国模式”可概括为: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市场机制,政府调控;增长引擎,科学发展。“一党领导,多党合作”是政治保障,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保证政治稳定、社会安定,这是增长与发展最根本的前提条件。“市场机制,政府调控”是制度保障,只有不断完善市场经济制度,才能充分调动各经济行为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同时,只有及时、适度的政府调控,才能不断地对市场机制纠偏。“增长引擎,科学发展”是基本目标,只有在优化经济结构、保护生态环境和缩小收入差距的同时,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才能使我们这样一个“只争朝夕”的追赶型国家早日实现“中国梦”。
第二,中国今后还能不能保持如此之高的增长率?比较困难。究其原因,暂且不说受到现有资源环境承受能力、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体制改革产生的激励释放趋弱等重要因素的约束,就是两个常识性问题,也会使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降下来:一个是基数问题。在经历了过去三十余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高达10%之后,增长基数越来越大,国际经济环境也越来越复杂,不大可能再有30年甚至20年平均10%的高速增长。一个是战略问题。中国正在致力于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特别是有迹象表明逐渐要从增长导向发展战略转向公平导向发展战略,这显然也会放缓经济增长。
第三,中国今后还需不需要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需要!其理由有很多。本文仅选择人均GDP为标准进行国际比较发现,尽管中国近四十年来经济增长强劲,人均GDP水平显著上升,但其他国家的人均GDP水平也在提高。就中国刚刚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2010年来说,人均GDP的世界平均值、上中等收入国平均值、高收入国平均值,分别是中国的2.8倍、2.6倍和11.7倍。可见,中国人均GDP要赶上世界和上述国家的平均水平还需要做出持久的不懈努力。 我们依然强调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也许会遭到一些质疑。比如,还强调高增长会不会使环境更加恶化?在笔者看来,高增长与环境破坏不一定具有直接因果关系,要看以什么方式实现高增长。又如,还强调高增长会不会导致能源供给捉襟见肘?我们认为这一问题在某一时段的确会存在,但也要动态地看能源的开发与利用,比如中国正在开发的页岩气,其储量在世界数一数二。
2.一个似是而非的事实:“三驾马车”失衡
所谓“三驾马车”失衡,一般指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以及外贸依存度偏大。的确,表1显示的信息不得不让我们得到“三驾马车”失衡的结论。首先,就近十年平均的家庭消费率来看,中国仅为39.1%,只相当于低收入国家(77.3%)的一半、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59.3%)的66%。资本形成率则出现了截然相反的情形:资本形成率几乎是所有各类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倍。同时我们发现,伴随经济的全球化, 对外贸易在各国经济中的比重都在上升,中国外贸依存度也迅速提高,从20世纪70年代的11.6%一路上升到21世纪头10年的63.8%,几乎平均每年上升1.5个百分点。
经济学原理和人类历史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当一国达到某一经济发展阶段之前,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一国的消费率会逐渐下降;但达到一定发展阶段后,消费率会上升而投资率会下降。可是,中国现阶段的消费率下降到如此程度,资本形成率长期居高不下,确实异常。
不过,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虽然“事实胜于雄辩”,但我们有时会忽视这种事实形成的背后真相。特别是,我们时常会站在某一角度去强调或夸大事实。因此,“三驾马车”这种“失衡”现象背后的真相需要我们去认真探索。
三、消费疲软悖论
根据国民经济核算的支出法,“三驾马车”中的“消费”是指最终消费支出,即包括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因政府消费支出所占比例通常不大且是可控的,故人们所关注的主要是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主要统计指标解释”,居民消费支出指常住住户在一定时期内对于货物和服务的全部最终消费支出,包括居民直接以货币形式购买的货物和服务的消费支出,以及单位以实物报酬及实物转移的形式提供给劳动者的货物和服务、住户生产并由本住户消费了的货物和服务、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媒介服务。
如前所述,如果从国民经济核算的结果来看,中国的家庭消费率的确很低(如表1所示)。不过,我们不能据此就断言中国的家庭消费疲软,因为家庭消费率衡量的是家庭消费水平,而判断家庭消费是否疲软还应当用其他一些指标来度量,比如居民消费支出实际增长率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率等。同时,无论是家庭消费率还是居民消费支出实际增长率的高低,也要考虑体现当今中国国情的其他社会经济因素。
1.居民消费支出实际增长率
从消费增长情况来看,近四十年来,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实际增长率平均达到8.3%,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平均高达10.9%。近二十年来,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实际增长率同20世纪80年代相比平均下降8.6%,最近10年的平均值降低到8%。
2.社会批发零售总额实际增长率
在评价居民消费是否“疲软”时,除了上述的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状况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状况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一国的消费水平。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年)“主要统计指标解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企业(单位、个体户)通过交易直接售给个人、社会集团非生产、非经营用的实物商品金额,以及提供餐饮服务所取得的收入金额。但在进行国际比较时,因联合国国民账户统计没有该指标,本文则选取与之相近的“批发零售总额”作为替代指标。联合国“国民账户主要总量数据库”中的“批发零售总额”包括批发、零售额以及住宿餐饮服务和机动车辆维修等的收入金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批发零售总额实际增长率都远高于其他国家: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中国的社会批发零售总额实际增长率分别是其他各类国家中该指标平均水平最高国家的3.6倍、2.6倍和1.9倍,是各期世界平均水平的3.7倍、2.6倍和4.9倍。需要指出的是,近二十年来,家庭消费支出实际增长率在下降,批发零售总额实际增长率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有所下降,但最近十年又有明显上升。
图7批发零售总额实际增长率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国民账户主要总量数据库”(2012年)的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中国的居民消费实际增长率和批发零售总额实际增长率都已大大超出其他各类国家的情况下人们还认为“消费疲软”,到底多高算不疲软?
3.有待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1) 低消费率与高经济增长率间的关系问题
也许有人反问道:既然居民消费实际增长率不低,可消费率为何如此之低?对此,我们尚未做深入研究,但我们推测其中的一个重要缘由可能是经济增长速度过快所致。近二十年来,中国GDP“蛋糕”膨胀很快,而人们的消费理念、消费习惯和消费结构等短期不会迅速变化,高边际增长率也就只有靠投资拉动了。
我们不妨以一个数字例子来说明。假定经济增长率为7%时,“三驾马车”中的投资贡献率为35%、消费贡献率为65%(暂且不考虑净出口的贡献)。倘若经济增长率达到10%,因居民消费水平在短期不会有明显变化,则多出来的3个百分点(从7%到10%)的经济增长率,就必然要靠投资拉动,而且投资贡献率还会逐渐增大:多出1个百分点可能需要60%的投资贡献率,再多出1个百分点,投资贡献率可能要达到70%,而最后多出的1个百分点,投资贡献率也许要高达85%甚至90%。因此,中国在持续了几十年高速经济增长后,最近十余年在经历两次世界性经济危机之后仍保持近10%的高速增长,必定要靠投资拉动,消费率必然会相应降低。
(2) 消费数据的全面性问题
过去在中国的企业、事业单位甚至国家机关中,向职工发放购物卡现象屡见不鲜。这些购物卡的发票开成了办公用品和低值易耗品等,其价值摊入生产经营成本或作为办公经费、业务经费列支,而职工用这些购物卡购买日常生活用品。这必然会出现两个问题:一是居民用卡购买的消费品的价值未记入计算消费率的“消费额”中,降低了消费率;二是居民不用现有收入购买消费品,减少了居民消费支出。
(3) 消费结构问题
本文所说的消费结构是指消费品结构和消费者结构。
就消费品结构而言,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吃、穿、用(各种用品,如家用电器之类)、住、行(包括交通工具)、玩(包括休闲度假旅游)方面的开支几乎成为居民消费支出的全部。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在前三方面的消费支出占比会越来越低,而后三方面的开支占比会越来越大。可是,虽然中国居民收入水平明显提高,但因中国国情,人们都一心想购买住房,而买房属于投资,租房才属于消费;虽然自有住房采用估算租金方法计为消费支出,但存在低估现象。休闲度假旅游也是越来越重要的居民消费项目,但中国盛行单位出资组织“集体活动”。
就消费者结构而言,消费者可大致分为三类:即低收入阶层消费者、中等收入阶层消费者和高收入阶层消费者。尽管低收入阶层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很大,但因其收入水平较低,对居民消费总额的边际贡献率不会很大,而后两者虽然边际消费倾向比不上前者,但因其收入水平较高,无疑对居民消费总额的边际贡献率较大[8]。我们来看一则报道:世界奢侈品协会公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奢侈品市场年消费总额达126亿美元(不包括私人飞机、游艇与豪华车),占据全球份额的28%,已成为全球占有率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世界上奢侈品消费的平均水平是用自己财富的4%左右去购买,而在中国,用40%甚至更多的比例去实现“梦想”的情况屡见不鲜,甚至这些群体构成支撑奢侈品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新闻网(2012年1月16日)《中国奢侈品消费全球第一的隐忧》。不难看出,中国人的消费欲望和消费需求不可谓不旺盛,而具有很高消费能力的中高等收入阶层的“炫耀性消费”主要放在了国外市场。 中国奢侈品市场研究机构财富品质研究院于2013年14日在上海发布的《中国奢侈品报告》表明,2013年中国人奢侈品消费总额将达1 020亿美元,占全球奢侈品市场总量的47.0%,其中,本土消费占27.5%,境外消费占72.5%。
综上所述,尽管以居民消费率度量的居民消费水平比较低,但以家庭实际消费支出增长率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率度量的消费趋势并不疲软。据此我们可以预期:在长期,随着中国城镇化率的提高和二元经济结构的调整,“橄榄型”社会结构将形成;在短期,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特别是财经纪律的执法力度和违法成本的加大以及公民道德水平的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必然会明显提高。因此,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现阶段的经济发展阶段对国内消费需求产生重大影响,不能简单地说“消费疲软”。
四、出口导向悖论
所谓“出口导向”,简单来说就是一国主要以出口增长带动经济增长的战略模式。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迅速发展,外贸依存度一路上扬(如表1所示);同时,1978—1995年的18年间,贸易顺差为10年,而自1996年以来连续保持贸易顺差。于是,国内外经济学界都认为中国也是出口导向型国家。
然而,尽管中国外贸依存度提升很快、贸易顺差连年不断,也不一定说明中国是出口导向型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中国外贸依存度提高较快是改革开放这一国家战略转变的落实结果,根本不是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大力鼓励出口,也主要是为换取外汇,以购买本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国外新机器设备和技术。即使后来出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拉动因素,但通过详细分析一些指标,我们也很难得到中国是出口导向型国家的结论。
1.外贸依存度
4.出口贡献率
出口贡献率指净出口增量与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增量之比,衡量的是净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如上分析,尽管中国的贸易顺差额占GDP的比率较高,但平均来看,净出口贡献率并非很大。在1971—2010年的40年间,长期存在贸易顺差的低收入国家、下中等收入国家、上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出口贡献率平均水平分别为-2.8%、32.9%、10.6%和10.4%,中国为3.3%。特别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20年间,上述各类国家的平均出口贡献率分别高达33.8%、110.4%、 这类国家在这一时期的出口贡献率之所以如此之高,是因为支撑经济增长的另外“两驾马车”——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在很多年份都是负增长。38.3%和17.8%,而中国仅为4.4%。
5.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从上述指标分析中,我们很难说中国是出口导向型国家。而且,世界各国可能无一例外都会鼓励出口。即便中国的贸易顺差额占GDP的比率比较高,但若由此断定中国是出口导向型国家,就会导致政府改变发展策略,这有可能又会与其他一些战略产生冲突。
(1)出口与外国直接投资的关系问题
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项主要内容。1980年中国内流FDI仅为0.57亿美元,1990年增加至34.87亿美元,2000年升至407.15亿美元,到2010年跃至1 057.35亿美元。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在中国内流FDI迅速增加(已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引资国)并以来(进)料加工贸易这种“两头在外”的利用外资方式的同时,外商投资企业货物出口额占全国货物出口额的比重不断上升,从有据可查的1992年的20.4%,一路上升到2005年的58.3%,以后虽略有下降,但最低的2010年也为54.6%。如果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导致一国出口增加这一观点成立, 有关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与出口增加的关系,谁是前因后果,学术界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出口增加导致外国直接投资增长[9],而有更多的学者认为二者间的关系是相反的[10-11]。如果承认中国是出口导向型国家,那么,要改变“出口导向”格局,就必须做出下列抉择:要么减少内流FDI总量,要么改变利用外资的方式;前者等于说不再积极吸引外资,后者又不是轻易能改变的。
(2)出口与中小企业发展的关系问题
据统计,中国中小企业上缴税收占50%,创造GDP超过60%,发明专利占65%,进出口贸易额占70%,企业技术创新的75%、新增就业岗位的80%也都是中小企业贡献的。可见,中小企业的成长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然而,由于中小企业的进出口贸易额占比高达70%,若要限制或不鼓励出口,首先受到冲击的是中小企业。如果中小企业的产品因此而滞销,也就谈不上企业成长。也许有人会说,这正是一个契机,促使中小企业放弃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迫使其加速产业(产品)结构升级,生产并出口高附加值产品。可是,倘若如此,问题就会接踵而至,先不要说中小企业的资金实力、技术力量和市场开拓能力等问题,如若中小企业不从事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生产,放弃这种比较优势,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文化水平不高、技术技能较低的大量劳动力的出路何在?
(3)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
前文主要是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分析了“出口导向”的一些重要指标,其结果都难以表明中国是出口导向型国家。不过, “出口导向”的另一核心问题是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结论莫衷一是。有学者认为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有学者则认为经济增长是出口增长的引擎;还有学者认为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而也有学者认为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很微弱。 因篇幅有限,上述观点的相关文献就不在此一一列举,有关文献综述可参阅许和连和赖明勇[12]以及Giles和Williams[13]。甚至有学者认为二者没有任何因果关系,这两个时间序列变量的增长路径都是由其他无关变量(比如投资)决定的[14-15]。不过,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得到的结论是上述情况因国而异,无一定之规[16-17],甚至有学者对出口导向增长假说提出了质疑[18]。
关于中国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起始于20 世纪90 年代,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其中,大多数文献的结论是存在双向因果关系[19-20]。He和Zhang[21]虽然也承认中国的经济增长依赖出口,但认为出口依赖程度远没有出口占GDP比率所预示的那么高, Herrerias和Orts[22]也认为,出口导向型增长假说只能解释中国过去长期高增长的一小部分。而且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源于它对供给面全要素生产率的有益影响而非需求面的乘数效应。特别是,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完全是国内需求导向(Domestic Demand-Led)的经济增长[23]。
可见,中国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问题远未澄清。我们即使不用经济计量方法,只是将实际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近四十年的变化路径做简单国际比较就能看出端倪。我们把比较对象分为两类:一类以美国为例,该国被认为是典型的内需导向经济增长;另一类是亚洲部分国家或地区,包括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它们被认为是典型的出口导向经济增长。
看来,中国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问题尚需深入系统地探讨。比如,中国的出口增长真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吗?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真的很高吗?又如,假使中国是出口导向型国家,为什么中国比其他国家(地区)更成功[24-25]?再如,即使中国是出口导向增长战略,但因与其他新工业化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不同——地域广大、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出口目的地并非局限于一二个地域和对外部冲击能做出充分调整等,且如果能再更多地出口高技术、高附加值、高质量的产品,将出口导向增长战略作为赶超发达国家的手段就真的不可取吗?
五、投资过度悖论
无论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来看,还是从投资率来看,中国近二十年的高速增长无疑主要依赖投资。我们不能否认投资依赖型增长这一事实,但问题是:第一,过去依赖投资的增长是高速增长,如果经济增长速度没有过去那么快,投资率和投资贡献率自然就不会那么高。第二,如果投资依赖型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那么,如表1所示,家庭消费率高达65%和75%的下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消费依赖型经济增长也不一定是可持续的。第三,高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不一定就代表着投资过度。本部分通过对一些重要指标的考察,对投资过度论点提出质疑。
1.投资规模
投资规模一般指一个经济体在一年内实际完成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根据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方法并为了便于国际比较,我们考察人均固定资本形成额。 资本形成总额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存货增加之和,其中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获得的固定资产减处置的固定资产的价值总额。从国际比较来看,近三十年来,中国无论是资本形成率还是人均实际固定资本形成增长率(如图5所示),都明显偏高,据此似乎可以认为中国“投资过度”。然而,倘若从人均实际固定资本形成额看, 样本国家的人均实际固定资本形成额是以200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的各年固定资本形成额除以当年人口。如图6所示,就是在被认为投资过度最明显的近十年,中国人均实际固定资本形成额分别仅相当于上中等收入国和高收入国人均实际固定资本形成额平均水平的2/3和1/10。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国民账户主要总量数据库” (2012年)的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通过观察图6,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点推论:第一,较高增长要由较高人均实际固定资本形成额来支撑;这一点早已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所主张。不要说强调只有不断投资和资本存量增加才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以及旗帜鲜明地指出“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加快资本积累”的刘易斯二元经济增长模型,就是强调技术进步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也没有忽视资本积累的重要作用。当经济成熟度达到一定水平后,一个富裕的社会也必须由较高人均实际固定资本形成额来支撑;没有相应的固定资本形成额,不可能有较快的经济增长,富裕社会也不可能持续。第二,较高消费率必须在一定程度的人均实际固定资本形成额基础上才能实现,如果没有较高的人均实际固定资本形成额支撑高消费率,经济将停滞不前,甚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们通过观察图6似乎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各时期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实际固定资本形成额在过去近四十年里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可能是其中许多国家一直不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一个重要原因。
2.投资效率
从总体经济运行来说,如果一国的投资过度,投资效率肯定低下。近年来,已有许多学者论证了中国投资效率不佳是投资过度的结果。然而,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的投资效率并不低。宋国青[26]研究了中国的投资回报率和同时期的利率水平,认为中国的投资回报率大大高于利率水平。白重恩等[27]曾详细考察过中国的总体投资回报率,得到的结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总体投资回报率一直维持在20%以上,这一数据比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要高,表明中国目前的投资还不存在过度问题。孙文凯等[28]则从另一侧面论证了中国投资效率比较高:中国居高不下的投资率是由于中国具有非常可观的投资回报。他们进一步指出,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在过去三十年内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平均高达21.9%,高出日本及美国十多个百分点;在未来数年内,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将会继续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并将高于日本及美国。
CCER“中国经济观察”研究组[29]通过估测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工业企业资本回报率9个系列指标,系统观察了中国资本回报率长期走势特点: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近二十年在波动中呈现下降趋势,这一下降趋势在1998年开始发生逆转, 从1998年开始稳步上升;虽然美国和日本的资本回报率也经历了不同幅度升降, 但相比之下,中国资本回报率在1978—1997年间下降幅度以及1998年以来回升强劲程度都来得更大。梁红[30]也针对工业企业资本回报率进行了研究,发现近年工业企业资本回报率上升超过市场预期, 并通过分析企业投资与利润存留关系、比较中外企业资本回报率水平,认为中国投资高速增长具有可持续性。
赵志耘等[31]则从物质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角度讨论过投资效率问题。技术进步可分为“非体现式技术进步”(Disembodied Technical Change)和“体现式技术进步”(Embodied Technical Change)。简单地说,体现式技术进步是指技术进步包含在新生产出来的资本品之中。作者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中过去和目前都存在着明显的体现在设备资本中的技术进步,1990—2005年间这种技术进步率至少在5.1%—6.0%以上,并且一些中西部地区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也较高。即便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是高投入型增长,但因在这种高投入中的设备资本投资包含着技术进步,因此,中国经济高投入式增长未必就完全属于“粗放型”增长,更不一定就是低效增长。
有学者即使认为中国投资效率较低,但也区分了不同情况,比如张军[32]就深入讨论了中国投资体制和投资效率的关系。他指出,“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的投资效率和投资行为的分析结果显示:非国有部门的投资效率一直处于改善之中,只有国有经济的投资效率是恶化的而且幅度较大。”我们借此能否做如下引申:即使投资效率在下滑,也不一定是因投资规模过度所致,也许是因投资主体特征所致;即使国有经济投资效率在恶化,除了国有经济主体的经营管理“软约束”等因素之外,有无可能因为国有经济投资承担了大量的社会责任乃至特定的政治任务?况且,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在逐年下降,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平均65%,下降到90年代的58%和2000—2005年的41%,2006—2010年进一步下降到29%。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表6—2按经济类型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中国统计年鉴(2006)》“表6—3各地区按经济类型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相关数据计算而得。因此,即使国有经济投资效率在下滑,也不一定意味着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效率不佳。
其实,用一种很简单的方法就可以从一个侧面来判断投资效率的高低——投资率(资本形成率)除以经济增长率,或者说“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之比”。其经济含义是每1%的经济增长率所需要的投资率,或者说用多少投资率才能换取1%的经济增长率,该数值越低说明投资效率越高。
3.政府投资
尽管很多人认为政府在“铁公机”上投资过多,但无论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当前需要还是长期需要来看,铁路、公路、机场的建设还远远不够,况且现在的建设成本要比以后建设成本小得多。也许还有人会说,现在的“铁公机”建设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并将其归咎于投资过多地集中于这些领域。然而,在我们看来,腐败行为的存在,不在于投资于哪一领域;如果缺乏有效的管理监督机制与制度,这笔钱用在别的领域同样会出现类似现象。需要我们反思的是,中国当前是否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从某种程度上说,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有余,而微观治理能力不足。
4.有待进一步解释的问题
(1)投资率与储蓄率的关系问题
宏观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投资和储蓄要大体上相等。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个人净收入要用于储蓄和消费,而储蓄又会最终转化为投资,储蓄量和投资量总会相等。虽然按照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储蓄增加与投资增加在数量上不一定一致,但如果储蓄长期低于投资,则会令投资减少,削弱未来的经济增长。可见,不管哪一经济学派,都不否认投资与储蓄存在密切关系,这也是被很多经济学家的实证分析所证实的事实[33-34]。
为此,我们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中国的储蓄规模大不大?第二,中国的储蓄规模与投资规模有无密切关系?第三,据此如何评价中国投资规模?
其次看中国储蓄规模与投资规模之间的关系。我们从图7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储蓄率与投资率存在密切关系。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投资需求(资本形成)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从20世纪80年的28.6%、90年代的36.1%,到21世纪头10年的53.5%,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和2011年)“表2—20三大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的相关数据计算而得。越来越高。可是,即便如此,储蓄率不仅仍然高于投资率,而且高出的差额却更大;而这个不断扩大的差额还是在外国直接投资比重不断下降、投资主要由国内储蓄融资的情况下形成的。 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构成来看,中国利用外资所占比重从1981年3.8%逐渐上升至1996年的11.8%,而从1997年开始一路下滑,从10.6%降至2010年仅为1.6%。
于是,需要深入探究的问题是:既然理论上说如果储蓄长期低于投资会削弱未来的经济增长,那么是否可以说储蓄图7中国的储蓄率与投资率
资料来源:储蓄率数据同图21,投资率数据同表1。长期高于投资就等于放弃了更高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在短期无法通过迅速扩大消费来消化储蓄的情况下,这些巨额储蓄不用于投资而闲置起来,岂不是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可见,如果从与高储蓄率相匹配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投资率并非过高。 李扬和殷建峰[35]从劳动力转移的角度深入分析了中国转轨经济独特增长模式的典型特征——持续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认为剩余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 工业化) 、由农村向城市( 城市化) 、由国有向非国有( 市场化) 的持续转移是我国经济能够长期、高速增长的关键, 而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既是这种增长模式的必然结果, 也是劳动力得以持续转移乃至这种增长模式得以维持的关键原因。
也许人们会问:中国如此之高的储蓄率难道就是合理的吗?我们对此并未做过专题研究,无法判断其是否合理,但必须承认它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出现的必然结果。不过,我们倒是认为这样高的储蓄率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因为其有些成因(如人口红利)会变弱或消失。 形成高储蓄率的原因很多,主要有高经济增长、有利的人口结构(劳动力人口比例高)、稳定的低通胀宏观经济环境和较高的储蓄意愿等。针对中国家庭高储蓄率成因的分析参阅Modigliani和Cao[36]、Horioka和Wan[37]以及Ma和Yi[38]。同时,我们更不认为多出来的储蓄一定要进行投资,也可以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海外获取外币资产等。可是,就目前经济学界为减少储蓄而提出的政策建议来看,无论是通过刺激消费直接减少储蓄,还是通过建立健全各种保障制度减少预防性储蓄,都无法立竿见影地解决当前的问题。
(2)投资规模与各种发展战略的关系问题
为了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自1998年前后开始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后又掀起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紧随其后的就是中部崛起战略;为了缩小城乡差别,开始了解决三农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及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为了推动创新和产业升级,各级政府纷纷建立各类开发区; 目前国家级开发区就有经济技术开发区(132个)、边境经济合作区(14个)、高技术产业开发区(106个)、出口加工区(57个)、保税区(18个)以及台商投资区等共计多达近400个,省级各类开发区更多达1 500多个。为了以点带面,发展地域经济,形成了“珠三角”、“长三角”、“黄三角”、“滨海新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们必须承认,上述发展战略无疑是支撑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但同时我们必须看到,这些发展战略的实施与实现,无疑需要一定规模的投资。即使是推动技术进步,也必须要有投资,因为技术进步分为两类:一是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二是非体现式技术进步。前者是说资本投入(积累)蕴涵着技术进步。因此,生产设备投资有利于技术进步。问题是,一方面说我国的投资规模过度,另一方面迫切要做的事情又需要大量投资,这显然有些矛盾。
(3)投资规模与产能过剩的关系问题
早在2009年,国务院就批转了发改委等部门《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将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和风电设备六大行业列入产能过剩行业,成为调控和引导的重点。社会上的确普遍存在着这样的认识,即过度投资是导致中国一些行业出现产能过剩的原因。可是,在我们看来,企业的投资行为是市场机制作用的自然结果,本无可厚非,但在现阶段,中国投资规模与产能过剩的关系至少有三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第一,如何界定产能过剩?用什么指标来度量产能过剩?是数量型过剩还是结构型过剩?第二,产能过剩往往与重复建设相关联,是谁推动了重复建设?如果没有超额利润,如果没有地方政府在背后的支撑,企业为什么会热衷于此?第三,如何化解产能过剩问题?国家发改委原主任张平在2013年3月6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新闻会上,就“经济社会发展与宏观调控”的相关问题做出回答时,针对当前存在的产能过剩,提出了“四个一批”的解决方案,即解决一批产能、消化一批产能、淘汰一批产能和转移一批产能。而无论是通过兼并重组、技术改造,还是通过优胜劣汰、到海外直接投资,产能过剩的化解将不可避免地需要新的投资。
(4)投资率、消费率与居民收入增长率的关系问题
六、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
我们在讨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时,忽略了增长核算理论与产出核算理论的区别。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经济增长,二是经济周期,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长期的生产能力和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周期是指总体经济活动的短期上下波动,或繁荣或衰退。而研究的逻辑起点是产出(GDP)核算。产出核算有三种方法,即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我们目前谈论的“三驾马车”,源于产出核算中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四个变量——消费支出(C)、投资支出(I)、政府支出(G) 政府支出指的是政府购买性支出,最终形成政府消费和公共资本,分别纳入“三驾马车”中的最终消费支出和资本形成总额。和净出口(NX)。如果用Y表示经济体的GDP总额,则有:
七、结束语
中国三十余年的持续高速经济增长为世人瞩目,与此同时,投资、消费和净出口这“三驾马车”的“失衡”也成为众矢之的。然而,如果从结果来看,中国三十余年来特别是被认为“三驾马车”不断走向“失衡”的近二十年来,不但GDP“蛋糕”迅速做大,而且居民收入水平大大提高,尤其是仅仅用了十几年时间,就从低收入国家一跃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由此看来,倘若支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真的是脱离国情的严重“失衡”,也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了。 这样的结果不能不说是极其成功的。就中国与印度比较来说,两国都是人口大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人均GDP水平不相上下,而之后中印两国的人均GDP水平开始拉开差距,到1999年中国进入下中等收入国家,印度到2007年才勉强进入下中等收入国家。特别是中国于2010年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而印度仍看不到挤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前景。更要提请注意的是,印度不仅经济制度更接近市场化,就是语言、政治制度也更接近西方国家。
暂且先不追问如果“三驾马车”不“失衡”的话,认为“失衡”的人们心目中的平衡的度或平衡的比例关系到底是多少,本文只是从不同角度,选择各种指标,系统考察中国的居民消费是否疲软、出口是否过大、投资是否过度。总的来说,笔者并不认为中国的消费需求是疲软的、经济增长是出口导向型的,而投资依赖是事实,但它正是支撑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必然结果。
首先,度量消费需求是否疲软的指标不只是消费率,至少还有居民消费支出实际增长率、社会批发零售总额实际增长率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因素。就居民消费支出实际增长率来说,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居民消费支出实际增长率分别是其他各类国家中该指标平均水平最高国家的2.8倍、3.2倍和1.2倍,是各期世界平均水平的3.5倍、3.2倍和3.2倍,且与中国各时期的经济增长率和居民收入增长率相适应。就社会批发零售总额实际增长率而言,无论是从近四十年的平均水平来看还是分各时期来看,中国的社会批发零售总额实际增长率都远高于其他国家: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中国的社会批发零售总额实际增长率分别是其他各类国家中该指标平均水平最高国家的3.6倍、2.6倍和1.9倍,是各期世界平均水平的3.7倍、2.6倍和4.9倍;而且这还没有考虑中国消费数据的全面性问题、消费结构等问题导致的消费核算不充分和消费制约因素。
其次,尽管中国外贸依存度提升很快、贸易顺差连年不断,也不一定说明中国是出口导向型国家。就外贸依存度而言,即使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外贸依存度一路上升的情况下,仍是各类国家中外贸依存度最低的国家。就出口依存度而言,就是中国出口依存度比较高的近十年平均值,也只高于低收入国的平均水平,仅相当于同类的下中等收入国平均水平的83%。就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而言,在1981—2010年间长期存在贸易顺差的国家中,下中等收入国家、上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出口贡献率平均水平分别为50.9%、13.9%和12.2%,中国仅为4.1%。
最后,中国近二十年的高速增长的确主要依赖投资,但高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不一定就代表投资过度。虽然中国的资本形成率和人均实际固定资本形成增长率都明显偏高,但从人均实际固定资本形成额看,就是在被认为投资过度最明显的近十年,人均实际固定资本形成额分别仅相当于上中等收入国和高收入国人均实际固定资本形成额平均水平的2/3和1/10。就投资效率而言,有的学者研究表明,无论是从中国的总体投资回报率、工业企业资本回报率,或是从物质资本积累导致的技术进步率来看,结果都表明中国的投资效率较高;特别是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的投资率—经济增长率之比一直大大低于其他各类样本国家的平均水平。就政府投资规模而言,虽然政府投资规模较大,但大多都属于基础设施投资。况且,今后中国无论是以技术进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还是以新农村建设推动城乡一体化,抑或以开发战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都离不开一定规模的投资。
当然,我们对“三驾马车”失衡论提出质疑,并非说目前的“三驾马车”比例关系没有问题。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地看,特别是不能全然不顾时代背景而予以否定。 正当我们为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而苦恼,千方百计要走向消费导向型经济之际,一些发达国家却在想方设法要从消费导向型经济(Consumption Led Economy)转向投资导向型经济(Investment Led Economy)。参阅Skilling[40]。在我们看来,正是过去这种“三驾马车”的“失衡”,支撑了长达三十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换言之,在过去创新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支撑这种长期高速增长的“三驾马车”“失衡”,实质上是一种宏观动态结构性均衡,或者说这种“三驾马车”的比例关系恰与那种长期高速增长相匹配。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经济增长战略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方式从依靠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的投入驱动转变到依靠知识、管理和创新驱动经济增长[41]以及社会物质财富已积累到一定程度前提下,伴随着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收入日益增加以及居民消费理念和消费行为的转变,“三驾马车”的“失衡”明显改观将是一个自然的结果。
参考文献:
[1]曹尔阶.我国投资饥渴症的起因及其防治[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1986,(1).
[2]苏挺.关于投资饥饿症理论的探讨[J].财政研究,1986,(9).
[9]胡红伟.学者建议收入增长要超GDP实际增长率提高个税起征点[N].新京报,2010-12-05.
[13]Lucas, R. On the Determinants of Direct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East and South Asia[J].World Development , 1993,21(3).
[14]冼国明,严兵,张岸元.中国出口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1983—2000年数据的计量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03,(1).
[16]Zhang, K.H.,Song,S. Promoting Exports: The Role of Inward FDI in China[J].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0,11(4).
[18]王志伟,侯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的促进作用:2000—2008——基于贸易引力模型的分析[J].社会科学研究,2011,(6).
[21]Pack, H.Industrialisation and Trade[A].Chenery,H., Srinivasan,T.N.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C].Amsterdam:Elsevier,1988.
[26]Bahmani-Oskooee, M.,Economidou,C. Export Led Growth vs. Growth Led Exports: LDCs Experience[J].Journal of Developing Areas,2009, 42(2).
[30]Shan, J.,Sun,F.On the Export-Led Growth Hypothesis: The Econometric Evidence from China[J].Applied Economics,1998,30(8).
[31]沈程翔.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1977—1998[J].世界经济,1999,(12).
[46]Claus, I.,Haugh,D.,Scobie,G. ,Tornquist,J. Saving and Growth in an Open Economy[R].New Zealand Treasury Working Paper,No.01/32,2001.
[48]Kuijs, L.How Will Chinas Saving-Investment Balance Evolve?[R].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No.3958,2006.
[52]Chamon, M.D.,Prasad,E.S.Why Are Saving Rates of Urban Households in China Rising?[J].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2010,2(1).
张中华.投资饥渴症理论剖析[J].财政研究,1991,(7).
[2]罗云毅.低消费、高投资是现阶段我国经济运行的常态[J].宏观经济研究,2004,(5).
[3]樊纲.让“三驾马车”均衡前行[N].人民日报,2006-09-11.
[4]张军.中国经济还能再增长多久[J].传承,2012,(9).
[5]Ramo,J. C. The Beijing Consensus[R].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2004.
[6]张宇,张晨,蔡万焕.中国经济模式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1,(3).
[7]孙乾,张伟摄.专家称北京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率已超过经济增长[N].京华时报,2012-11-12.
[8]郭庆旺.消费函数的收入阶层假说[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3,(1).
[9]Hein,S. Trade Strategy and the Dependency Hypothesis: A Comparison of Policy,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Latin America and East Asia[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92,40(3).
[10]Bayoumi,T.,Lipworthl,G. Japa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Regional Trade[J].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1998,9(4).
[11]杨迤.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进出口影响的相关分析[J].世界经济,2000,(2).
[12]许和连,赖明勇.出口导向经济增长(ELG)的经验研究:综述与评论[J].世界经济,2002,(2).
[13]Giles, J.A.,Williams,C.L. Export-Led Growth: A Survey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and Some Non-Causality Results: Part 1[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2000, 9(3).
[14]Reizman, R.G.,Summers,P.M. ,Whiteman,C.H. The Engine of Growth or Its Handmaiden? A Time Series Assessment of the Exportled Growth[J].Empirical Economics, 1996,21(1).
[15]Cuadros,A.,Orts,V.,Alguacil,M.T.Re-Examining the Exportled Growth Hypothesis in Latin America: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Trade and Output Linkag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R].European Trade Study Group Working Paper Series,2000.
[16]Kónya, L.Export-Led Growth, Growth-Driven Export, Both or None? Granger Causality Analysis on OECD Countries[J].Applied Econometrics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04, 4(1).
[17]Shirazi,N.S. ,Manap,T.A.A.Export-Led Growth Hypothesis:Further Econometric Evidence from South Asia[J].The Developing Economics ,2005,43(4).
[18]Dreger,C.,Herzer,D.A Further Examination of the Export-Led Growth Hypothesis[J].Empirical Economics, 2013,45(1).
[19]Kwan, A. C. C.,Cotsomitis,J. A.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xpanding Export Sector:China 1952—1985[J].International Economic Journal,1991,5(1).
[20]Liu, X. ,Song,H.,Romilly,P.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Opennes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Applied Economics,1997,29(12).
[21]He, D.,Zhang,W.How Dependent Is the Chinese Economy on Exports and in what Sense Has Its Growth Been Export-Led?[J].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10,21(1).
[22]Herrerias, M.J.,Orts,V.Is the Export-Led Growth Hypothesis Enough to Account for Chinas Growth?[J]. China & World Economy, 2010,18(4) .
[23]Anderson,J. Is China Export-Led? [R].UBS Investment Research, Asian Focus,2007.
[24]Xue,J.J.The Export-Led Growth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in China[J].Hitotsubashi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36(2).
[25]Tingvall,P.G.,Ljungwall,C.Is China Different? A Meta-Analysis of Export-Led Growth[J].Economics Letters ,2012,115(2).
[26]宋国青.全社会投资效率在上升[J].财经,2004,(10).
[27]白重恩,谢长泰,钱颖一.中国的资本回报率[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
[28]孙文凯,肖耿,杨秀科.资本回报率对投资率的影响:中美日对比研究[J].世界经济,2010,(6).
[29]CCER“中国经济观察”研究组.我国资本回报率估测:1978—2006[J].经济学(季刊),2007,(3).
[30]梁红.中国投资的高速增长是可持续的[R].高盛全球经济研究报告系列,2006.
[31]赵志耘,吕冰洋,郭庆旺,贾俊雪.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动态融合: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典型事实[J].经济研究,2007,(11).
[32]张军.资本形成、投资效率与中国的经济增长——实证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33]Feldstein, M.,Horioka,C.Domestic Savings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J].Economic Journal ,1980,90(358).
[34]Obstfeld, M.,Rogoff,K. The Six Major Puzzles In 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s: Is there A Common Cause?[R].NBER Working Paper ,No.7777,2000.
[35]李扬,殷剑峰.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和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5,(2).
[36]Modigliani, F. ,Cao,S.L.The Chinese Saving Puzzle and the Life-Cycle Hypothesis[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4,42(1).
[37]Horioka,C.Y.,Wan,J.The Determinants of Household Saving in China: A Dynamic Panel Analysis of Provincial Data[J].Journal of Money, Credit & Banking,2007,39(8).
[38]Ma, G. ,Yi,W. Chinas High Saving Rate: Myth and Reality[R].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Working Paper,No.312,2010.
[39]Solow, R. M.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57,39(3).
[40]Skilling, D. Home Is where the Money Is: The Economic Importance of Savings[R].The New Zealand Institute Discussion Paper, No.1,2005.
[41]赖德胜.使改革红利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
(责任编辑:刘艳)
[16]Kónya, L.Export-Led Growth, Growth-Driven Export, Both or None? Granger Causality Analysis on OECD Countries[J].Applied Econometrics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04, 4(1).
[17]Shirazi,N.S. ,Manap,T.A.A.Export-Led Growth Hypothesis:Further Econometric Evidence from South Asia[J].The Developing Economics ,2005,43(4).
[18]Dreger,C.,Herzer,D.A Further Examination of the Export-Led Growth Hypothesis[J].Empirical Economics, 2013,45(1).
[19]Kwan, A. C. C.,Cotsomitis,J. A.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xpanding Export Sector:China 1952—1985[J].International Economic Journal,1991,5(1).
[20]Liu, X. ,Song,H.,Romilly,P.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Opennes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Applied Economics,1997,29(12).
[21]He, D.,Zhang,W.How Dependent Is the Chinese Economy on Exports and in what Sense Has Its Growth Been Export-Led?[J].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10,21(1).
[22]Herrerias, M.J.,Orts,V.Is the Export-Led Growth Hypothesis Enough to Account for Chinas Growth?[J]. China & World Economy, 2010,18(4) .
[23]Anderson,J. Is China Export-Led? [R].UBS Investment Research, Asian Focus,2007.
[24]Xue,J.J.The Export-Led Growth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in China[J].Hitotsubashi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36(2).
[25]Tingvall,P.G.,Ljungwall,C.Is China Different? A Meta-Analysis of Export-Led Growth[J].Economics Letters ,2012,115(2).
[26]宋国青.全社会投资效率在上升[J].财经,2004,(10).
[27]白重恩,谢长泰,钱颖一.中国的资本回报率[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
[28]孙文凯,肖耿,杨秀科.资本回报率对投资率的影响:中美日对比研究[J].世界经济,2010,(6).
[29]CCER“中国经济观察”研究组.我国资本回报率估测:1978—2006[J].经济学(季刊),2007,(3).
[30]梁红.中国投资的高速增长是可持续的[R].高盛全球经济研究报告系列,2006.
[31]赵志耘,吕冰洋,郭庆旺,贾俊雪.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动态融合: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典型事实[J].经济研究,2007,(11).
[32]张军.资本形成、投资效率与中国的经济增长——实证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33]Feldstein, M.,Horioka,C.Domestic Savings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J].Economic Journal ,1980,90(358).
[34]Obstfeld, M.,Rogoff,K. The Six Major Puzzles In 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s: Is there A Common Cause?[R].NBER Working Paper ,No.7777,2000.
[35]李扬,殷剑峰.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和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5,(2).
[36]Modigliani, F. ,Cao,S.L.The Chinese Saving Puzzle and the Life-Cycle Hypothesis[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4,42(1).
[37]Horioka,C.Y.,Wan,J.The Determinants of Household Saving in China: A Dynamic Panel Analysis of Provincial Data[J].Journal of Money, Credit & Banking,2007,39(8).
[38]Ma, G. ,Yi,W. Chinas High Saving Rate: Myth and Reality[R].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Working Paper,No.312,2010.
[39]Solow, R. M.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57,39(3).
[40]Skilling, D. Home Is where the Money Is: The Economic Importance of Savings[R].The New Zealand Institute Discussion Paper, No.1,2005.
[41]赖德胜.使改革红利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
(责任编辑:刘艳)
[16]Kónya, L.Export-Led Growth, Growth-Driven Export, Both or None? Granger Causality Analysis on OECD Countries[J].Applied Econometrics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04, 4(1).
[17]Shirazi,N.S. ,Manap,T.A.A.Export-Led Growth Hypothesis:Further Econometric Evidence from South Asia[J].The Developing Economics ,2005,43(4).
[18]Dreger,C.,Herzer,D.A Further Examination of the Export-Led Growth Hypothesis[J].Empirical Economics, 2013,45(1).
[19]Kwan, A. C. C.,Cotsomitis,J. A.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xpanding Export Sector:China 1952—1985[J].International Economic Journal,1991,5(1).
[20]Liu, X. ,Song,H.,Romilly,P.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Opennes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Applied Economics,1997,29(12).
[21]He, D.,Zhang,W.How Dependent Is the Chinese Economy on Exports and in what Sense Has Its Growth Been Export-Led?[J].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10,21(1).
[22]Herrerias, M.J.,Orts,V.Is the Export-Led Growth Hypothesis Enough to Account for Chinas Growth?[J]. China & World Economy, 2010,18(4) .
[23]Anderson,J. Is China Export-Led? [R].UBS Investment Research, Asian Focus,2007.
[24]Xue,J.J.The Export-Led Growth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in China[J].Hitotsubashi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36(2).
[25]Tingvall,P.G.,Ljungwall,C.Is China Different? A Meta-Analysis of Export-Led Growth[J].Economics Letters ,2012,115(2).
[26]宋国青.全社会投资效率在上升[J].财经,2004,(10).
[27]白重恩,谢长泰,钱颖一.中国的资本回报率[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
[28]孙文凯,肖耿,杨秀科.资本回报率对投资率的影响:中美日对比研究[J].世界经济,2010,(6).
[29]CCER“中国经济观察”研究组.我国资本回报率估测:1978—2006[J].经济学(季刊),2007,(3).
[30]梁红.中国投资的高速增长是可持续的[R].高盛全球经济研究报告系列,2006.
[31]赵志耘,吕冰洋,郭庆旺,贾俊雪.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动态融合: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典型事实[J].经济研究,2007,(11).
[32]张军.资本形成、投资效率与中国的经济增长——实证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33]Feldstein, M.,Horioka,C.Domestic Savings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J].Economic Journal ,1980,90(358).
[34]Obstfeld, M.,Rogoff,K. The Six Major Puzzles In 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s: Is there A Common Cause?[R].NBER Working Paper ,No.7777,2000.
[35]李扬,殷剑峰.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和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5,(2).
[36]Modigliani, F. ,Cao,S.L.The Chinese Saving Puzzle and the Life-Cycle Hypothesis[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4,42(1).
[37]Horioka,C.Y.,Wan,J.The Determinants of Household Saving in China: A Dynamic Panel Analysis of Provincial Data[J].Journal of Money, Credit & Banking,2007,39(8).
[38]Ma, G. ,Yi,W. Chinas High Saving Rate: Myth and Reality[R].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Working Paper,No.312,2010.
[39]Solow, R. M.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57,39(3).
[40]Skilling, D. Home Is where the Money Is: The Economic Importance of Savings[R].The New Zealand Institute Discussion Paper, No.1,2005.
[41]赖德胜.使改革红利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
(责任编辑:刘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