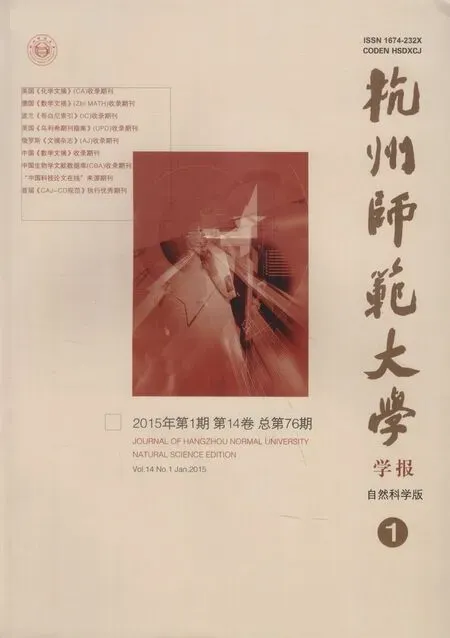从“他者”到“自我”:中国武术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主体意识
罗立平,方国清
(1.杭州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浙江 杭州 310036; 2.浙江工业大学体军部,浙江 杭州 310014)
从“他者”到“自我”:中国武术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主体意识
罗立平1,方国清2
(1.杭州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浙江 杭州 310036; 2.浙江工业大学体军部,浙江 杭州 310014)
摘要:针对中国武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为了能与“国际接轨”,越来越西化,越来越丢失“民族性”的标志而趋向“他者化”的问题,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的基础上,运用后殖民理论中关于“他者”与“自我”的思想对此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完全站在迎合西方人对民族体育欣赏口味的立场上来展示武术,分明就是一种文化上的“他者化”,这是应该加以警惕的;武术的发展其主体意识不可丢失,当下及未来的武术国际化传播与国内的发展改革还须重新围绕“民族特色”这个关键点来展开,即从“他者”走向“自我”的回归.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之间应该是一种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自我与他者不是一个征服与对抗的关系,而是一个主体与主体、相互借鉴塑造的关系.
关键词:武术;他者;文化认同;主体意识
中华武术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一直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牵系着中国人的情感,寄托着中国人侠义、自强与不屈的情怀,构筑着黄河畔农业文明多姿多彩的生活场景.但是,自从在体育全球化的“征程”中与西方体育这个“他者”相遇后,却遭遇了“两千年未有之变局”. 直到目前,中国武术圈内的人士更是对传统武术技击性遭受质疑以及现代竞技武术越来越无法体现中国武术传统文化特色等,表达了高度的关切,不同的声音与理论甄别也纷至沓来见诸于各类报刊之上.尤其是当2008年武术“申奥”冲刺未果后,武术的发展又一次近乎陷入了“婆家不喜,娘家不爱”的尴尬境地,这再次激起了人们穷追不舍的追问与更多向的反思.有人说,今天的武术似乎成了“基督信仰中迷失道路的歧路之羊,既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该向哪里去.”[1]因此,当我们发现昔日的国粹已经开始逐渐丧失“民族性”而越来越“他者化”时,亟需一种新的理论或思想来帮助我们去拨开在“后奥运”时代武术发展的迷雾.后殖民理论中关于“他者”的论述在回答这个问题上无疑有着非常贴切的意义与帮助.也许,只有从“他者”这样一个哲学的视界审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身份”与内涵的“精神禀赋”,从“他者”的论域来看中国武术的发展问题,才能更好地为武术今后的复兴指明方向与道路.
1关于“他者”的后殖民理论简述
“当代哲学与文化中关于他性的问题已经成了一个几乎所有问题都与之相关的新焦点,这一点现在正变得越来越明显,无论是全球化、地方性、身份认同、普遍主义、共同体、西方与东方、多元论和相对主义、文明冲突、暴力、大众文化、交往和对话、博弈与合作等等表现着这个时代特征的问题都从各自的方向联系到他者这样一个核心问题.”[2]现代以来的“主体性”(subjectivity)原则已经远远处理不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思想新形势.
提及“他者”(the other),其概念可以追朔到18世纪末的西方世界.当时,西方人为了开拓自己的疆土以及满足自己对外部世界的猎奇、征服之心,在其殖民扩张的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对于与自己不同的“他者”世界的记述和认识.西方人凭借着他们先进的航海技术,打着“上帝旨意”的旗号进行了浩浩荡荡的地理大发现.所到之处,狂热的基督教徒只要遇见有异教徒或不信教的人,为了能使他们皈依基督教而不惜使用武力.由于新大陆的瓜分,导致了无数印第安人被大肆屠杀,非洲黑人被大批贩卖,黄金、白银、香料等不断运回欧洲.在这个征服与掠夺的过程中,欧洲人很快确立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地位.自然,他们把新大陆与非洲世界视为野蛮、未开化的“他者”世界,相对应的欧洲则是文明、高雅、聪明的“自我”的世界.至此,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也得以形成了.事实上,在遥远的东方,中国自古也有着类似的表述,如“南蛮西夷”、 “万邦来朝”、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这种居高临下的文化心态,甚至于歧视其他民族的心理表明,不仅仅是西方,任何一个民族只要足够强大或自认为足够强大,都很容易产生自我中心的思想,并借助其权力话语构建自我与他者的二元体系,以此来增强整个国家的凝聚力与认同感.
本文之所以运用后殖民理论,更为看重的是,西方后殖民理论中的他者还涵盖着与自我彼此依存的意义,以及如何处理与对待自我与他者两个文化间关系的问题.在后殖民理论看来,自我的理解与认识总是通过他者的镜像来反映的.这恰恰与中国古代“中和”的价值观念如出一辙[3],都强调:假使自我与他者想要达到合一的状态,其前提是“中”,是不偏不倚的态度与平等的价值观念,是主体性、个体性的确认,多元主义的倡导.其次在“和”,通过他者的对比映照,重塑新的自我,并继续形成与他者“美美与共”的关系.
2武术发展中的文化“他者化”倾向
今天,“自我”和“他者”的划分早已超越了狭隘意义上的殖民主义,渗透到了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他者”和“自我”(self)是一组相对的概念,对第一世界来说,第三世界国家是他者;对西方体育来说,中国武术是他者;对于中国现代(竞技)武术来说,传统武术已经变为了他者……如此种种,不胜枚举.当我们把这种后殖民理论中关于他者的论述联系到武术的发展史上时,我们会发现,这并不仅仅是一种理论的联想,极有可能给我们提供如何处理中国民族体育与西方体育两个文化间关系的新思路.
提到中国武术的“他者”化即近现代的发展,就不能不提到“土洋体育之争”.作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在体育领域里的反映,这场运动着实对中国体育后续的发展带来不小震动.如果说国人一开始还对西方体育的漂洋过海表示出了某些抵触情绪,那么后来似乎这种对他者的抗争就越来越微弱,武术的发展事实上自“土洋体育之争”起,就开始了传统向现代的悄然转型,即“他者”化的历程.随着西方体育在一些传教士的推广下,中国民族体育相对的文化自主性和原生的单纯性遭遇到了威胁,取而代之是西方体育文化在本土语境中的“旅行”.
众所周知,近代西方体育在中国的传播与其他诸如好莱坞大片、各类译作、网络游戏、外国广告等等形形色色的异质文化因素一样,隐含在这后面的同样是更为深层和复杂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当然,这里不能简单地以非此即彼的两极来定论,西方体育的流入对武术的推广普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与影响,同时,对立的价值观念也让今后的武术发展走上了一条艰辛坎坷的道路.在“他者”化的过程中,以拳种门派、师徒教授为主要传承形式的武术被肢解成现代武术散打和现代竞技武术套路两大类别,以至于在技术评判上,武术竞赛套路难以完全符合现代体育的要求;在文化上,武术散打又失去了武术所能体现出的传统文化精神与风格.
更为广泛的是,整个国家的体育都在进行着一场“科学化”、“西方化”的大运动,如:为了武术更全面、更快速地普及,体育部门按照西方体育简单化、规范化的特点组织专家编写了一系列面向不同层次人群习练的武术套路;各级各类的学校武术教育内容开始统一化、教学开始程式化;各级各类的武术竞赛活动即赛事的举办应具有“西方宗教情节的宏大仪式;要具有达尔文主义和民主理念倡导下的公平竞争中优胜劣汰的比赛形式;要有体现民主的法权思想的竞赛规则;要有表现个人英雄主义和团队协作精神的项目设置;要有体现现代科学精神和大工业精神的竞赛目标明确的项目设置、动作规范的技术体系等等.”[4]武术的国际化传播推广同样要努力与国际奥林匹克接轨,等等.这一切操作都表明了,武术的改革发展彻底地走上了他者化的道路.
3武术文化“他者化”的负面效应
所有当年这些举措,今天审视起来,正是武术体操化、舞蹈化、杂耍化等一系列“他者”化的一个重要诱因,是它们一步一步将武术固有的本质特点消弱、删减乃至完全放弃.当代武术的发展由于缺失了应有的主体意识,使得武术文化无论是其活动形式、体育目标及价值观念,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迷失和更迭.也正是这些变化催生了我们对武术过去的认识和怀旧,对传统武术流失的忧患和反思.
历史上,武术的形成与发展可以说从未离开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和滋养,反过来,武术也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深刻传递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等元素.中国的古典哲学、医学、艺术和历史等都是构成武术文化的基础,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认可武术并不只是体育,而更应该是一个活态的文化宝库.这一文化库存集聚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的智慧,是西方体育理论无法完全阐释清楚的.在整个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武术发展所形成的历史偏向,其实质是对“自我”的不够自信,是对“他者”的过份献媚.针对武术发展“他者”化的情况,著名武术学者周伟良在文章中这样写到:“近30年的时间内,竞技武术套路样式成为了中国武术的样板.在‘高、难、美、新’的竞赛规则杠杆撬动下,套路运动的操舞化、造型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以‘创新动作’为难度的动作组合如同一块任意拼装的七巧板,充满‘摇滚’特色,与所谓‘遵循技击规律’、‘体现攻防含义’云云相剥离,不过是张徒有虚名的文化标签.”[5]知名武术学者王岗教授也在文章中这样描述到:“对他者的文化模仿实质上是对自己文化无知和缺乏自尊的一种表现,也是创造力匮乏的一种无奈之举.对西方体育几乎极致的偏执模仿也造成了我们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瓶颈,找不到突出重围的办法.因此,对西方体育文化的简单模仿绝非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正途,只有自己掌握文化创造的主动权,才能使得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走向一条康庄大道.”[6]
在当前体育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民族体育文化正在努力地以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参与到全球体育文化的共建与交流中去,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在这种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我们有些民族文化的输出者已不知不觉地落入到了如萨义德所说的将东方文化‘他者化’的陷阱中,站在迎合西方人对民族体育欣赏口味的立场上来展示民族体育,这是我们应该加以警惕的.”[7]如果一味地“他者化”以求得别人的认可,到头来,武术的发展只可能会由西方人“看不懂”改变成“看懂”再变成“不以为然”,这一过程则是以丧失文化为代价的.
4从“他者”回归“自我”:武术的发展其主体意识不可丢
当体育全球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又一个不可回避浪潮的时候,中华民族体育——武术如何从传统的“怀旧”与“他者”化的历史偏向中回头,找回自己迷失的、曾经独立的主体身份便显得尤为必要.萨义德在其东方学研究中所指出的后殖民理论,同样适合对于武术发展中所遇问题的解析.中国武术在试图脱去“自我”老旧的外衣融入“他者”潮流的过程中,却落入了国际奥委会那些“东方主义”者们对东方体育设下的陷阱中,对这段武术滑出正轨的发展历史进行反思需要有力的理论支撑,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作用正在于此.
“后殖民理论出现的意义在于它有力地消解了西方中心主义”.今天,“自我”和“他者”的划分早已超越了狭隘意义上的殖民主义,渗透到了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体到中华武术与西方体育这对“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上时,我们又将如何看待呢?对于中国武术的国际化问题历来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强调接轨奥林匹克,就是西方化亦即“他者”化,另一种观点则强调中国武术自成体系并与西方体育相抗衡,亦即民族体育“自我”认同.其实,自我与他者不是一个征服与对抗的关系,而是一个主体与主体、相互塑造的关系.
4.1 中国武术的发展其主体意识不可或缺
《易传》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苞者,本也.凡物系于苞本,则固.”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精神家园和文化主体意识,武术的世纪之行当然不能没有自己的主体意识.主体意识乃是中国武术与他者文化交流的原则.“武术如果失去民族文化自我的特性,失去中国武术之为中国武术的传统内涵,武术将不会再称之为武术.”[8]今天,强势的西方体育和奥林匹克运动仍在伴随着西方文化进行着世界性的扩张,在这里,中国武术的“民族性”无疑被西方体育的“世界性”视为一个“他者”.此种情形下,中国武术的改革应清醒地意识到:模仿、依附都不是正途,坚持独立的主体意识才是最重要的.对于武术的发展应持有一种“和而不同”的态度,这就是武术可以走向世界和世界接轨,但传达与表现的一定是纯粹的中国制造,至少也是有着中国印记与标识的武术.
后殖民主义关于自我和他者的理论认为,自我与他者两者相辅相成,存在显著差异又存在着冲突与融合的可能,它不是以往那种“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我与你”式的对话的关系.这就告诉我们,中国武术走向世界是必须的,应该有勇气和西方体育进行对话,应该有勇气与西方体育不同,后殖民理论与中国古老的“中和”观同样是一致的.自我与他者“合一”的意义首先在“中”,即是以不偏不倚的态度,以平等与共存的价值观念,确立作为个体的各个元素的独立性与主体性;其次在“和”,“和”的前提是“中”,是主体性、个体性的确认.因此,我们认为当下及未来的武术国际化传播与国内的发展改革还须重新围绕“民族特色”这个关键点来展开,即从“他者”走向“自我”的回归.
4.2 武术作为民族文化的凝聚形式,对他者文化的吸收同样也是有必要的
因为,“任何一种文化要建构自我的主体,都必须树立一个文化他者,依赖他者的视角.离开他者,存在便是虚无.”[9]正如萨义德的《东方学》所指出的,西方文化的自我认同实际上也是通过对“东方”的想象来界定的.在体育文化认同的方式上,那种文化原教义主义所提倡的“自我与他者”对立的二元模式,始终将是当今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重重障碍.武术文化传播对于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提高国家空间凝聚力、促进国家产业创造力、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传承民族生命力等方面具有积极影响[10].
但中国武术必须是以保持自我的文化主体意识为前提,不能把武术自我独特的民族性和价值体系轻易地消融到他者的文化语境中去,一个民族的身体文化同样是构成整体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样讲求内在精神与文化个性.武术的时代性,要求我们必须走出古代所构建的体系,但也要防止把武术建成西方模式.因此,中华武术既要成为世界体育大家庭中的一员,同时又不能以丢弃自己的精神根基与主体意识为代价,这应是当代武术发展中的一个值得深思的战略问题.
总之,正如我们不能因为跟西方人一样做“人”就不做“中国人”,中国武术也不能因为要入选奥运会,就全面地迎合从而彻底更改我们民族的文化标识.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因为跟西方人一样遵守奥林匹克的“铁律”就不保持中国民族体育的“特色”,反之亦然.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应该是一种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应该是一种“互相依赖又互不依附、互不征服的平等关系;互相独立又互不排斥、互相独立又互不对抗的伙伴关系;互相呼唤、互相应答的对话关系;互相映照、互相吸纳、互相补充的互动关系.”[8]
5结语
身体语言是一个民族和文化的载体、象征,他们本身并无高低贵贱之别.中华武术,应当可以按照自我的文化逻辑,在全球化的汹涌浪潮中坚持“和而不同”的中华精神,通过其智慧与实践,继往开来,与西方体育这个“他者”一起搭建起一座平等交流的文化立交桥, 在以文化进行自我认同的同时,为体育的全球化做出建设性贡献,同时与中华民族的灿烂历史和理想相称.
参考文献:
[1] 文善恬.竞技武术,歧路之羊?武术发展要警惕一种“去竞技化”倾向的回潮[J].体育科学,2008,28(11):87-91.
[2] 乐黛云,钱林森.迎接新的文化转型时期[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481.
[3] 何胜保,高红斌,杨春,等.融摄与对话:《周易》哲学对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影响发微[J].体育科学,2013,33(10):93-96.
[4] 李印东,李军.从土洋体育之争的历史文化背景谈西方体育对武术的影响[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0,33(4):7-9.
[5] 周伟良.文化安全视野下中华武术的继承与发展[J].学术界,2007,122(1):59-78.
[6] 王岗.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中的问题:文化模仿[J].体育科学,2006,26(7):71-74.
[7] 方国清.自我与他者: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武术文化认同的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08.
[8] 骆红斌,方国清.关于中国武术发展中文化断裂现象的思考[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8,32(3):68-70.
[9] 罗贻荣.走向对话:文学自我传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6.
[10] 郭玉成,范铜钢.武术文化传播构建国家形象的战略对策[J].中国体育科技,2013,49(5):80-85.
From the “Other” to “Self”:
The Essential Subject Consciousnes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Wushu
LUO Liping1, FANG Guoqing2
(1.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36,China; 2.Institute of P.E
and Martial Training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14, China)
Abstract:During the past century, in order to be geared t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Chinese Wushu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westernized, it loses the symbol of “nationality”, but tends to “othering”.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is problem by the thought of “other” and “self” in the postcolonial theory. The paper considers that it should vigilant that displaying Wushu completely standing on the position of westerners’ appreciates to the national sports, which clearly is a culture of “oth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Wushu cannot lose its subject consciousness, the current and future Wushu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domestic reform should focus on th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that is, the returning from “other” to “self”. Chinese Wushu and the west PE should be a relationship of self and other, other and self is not a conquest or confrontation relation, but the relationship of subject and subject, learning from each other.
Key words:Wushu; other; cultural identity; subject consciousness

文章编号:1674-232X(2015)01-0102-05
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674-232X.2015.01.019
通信作者:罗立平(1970—),男,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武术文化与学校体育研究. E-mail:luoliping66@163.com
收稿日期:2014-0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