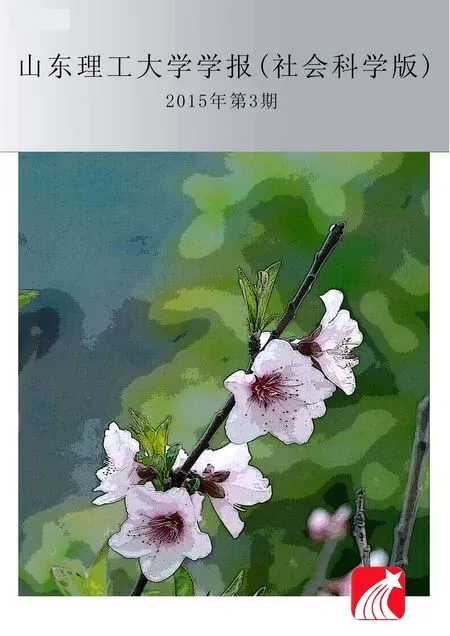《焦氏笔乘》音韵思想探幽
陆 露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350007)
《焦氏笔乘》音韵思想探幽
陆 露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350007)
《焦氏笔乘》是明代著名学者焦竑的读书札记,内容博杂,考据精审。除提出“古诗无叶音”的主张外,焦竑还明确意识到古韵今韵之不同,这一点要早于陈第的音移观。《焦氏笔乘》中亦已体现出较为科学的古音研究方法,对陈第的影响直接而深远。
《焦氏笔乘》;音韵学;“古诗无叶音”
焦竑(1540~1620),字弱侯,号澹园,又号漪园,人称澹园先生或漪园先生、焦太史,谥文端、文宪,江宁(今江苏南京)人,是晚明最负盛名的学者之一。其传世著作有三十余种:《国朝献征录》120卷、《熙朝名臣实录》27卷、《逊国忠节录》4卷、《国史经籍志》6卷、《玉堂丛语》8卷、《皇明人物考》6卷、《京学志》8卷、《词林历官表》3卷;此外尚有汇录大量考理笔记的《焦氏笔乘》(下称《笔乘》)6卷和《续笔乘》8卷等。
十四卷《笔乘》内容涉及经学、史学、哲学、宗教、博物、典章制度、金石文字、目录版本等方面,而且多是作者亲自考据、思考所得,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正是在《笔乘》中,焦竑最先明确反对“叶音说”,提出“古诗无叶音”的观点。这无疑是汉语古音研究的转捩点,自此之后,陈第、顾炎武、江永等学儒们开始明确地意识到语音的时空演变问题,由此拉开了科学研究上古音的帷幕。
目前学术界对《笔乘》的研究重在史学及文献考据学方面:如王炜民(1984)、亢学军(2004)、陈瑞芳(2010)、史振卿(2013);亦有龚仕明(1999)关于其中所载医方之研究。王炜民(1984)、刘青松(1998)、李剑雄(1998)、亢学军(2004)、史振卿(2013)曾对《笔乘》的音韵学价值做过概略介绍。但考察以上各家之言,多是针对“古诗无叶音”这一条目进行重点评析,主要集中在提出的意义上,对本条目所包含其他信息内容关注度不足,同时亦缺少对全书涉及音韵学内容的系统整理和研究。
《笔乘》共收逾千条札记,有明确标示条目者计491条。其中涉及音韵者计有:卷一:19朋当在东押、21咎繇锺繇二繇同音、56师古注误、61缠读如战、78浊古音独、83随误改隋、84角里;卷二:118鄂不;卷三:144古诗无叶音、159追蠡、173李夫人歌、209杜诗用投字、211诗误出韵、245当歌之当非去声;261三十六字母、268霓可两音、269廿卅卌三音、270甄有三音、274繇有六义、275率有五音、276敦有九音、278苴有十四音;续集卷三:312提耳;卷五:427琵番蒲司帆作仄声、466星宿。[1]凡25条。这些条目,清晰地记录了焦竑对于古音的认识及他考证古音所选择的材料、所用的方法,并兼有他对诗韵与字音的考据与辨析。同时,另有卷六“264杨用修字书目、265英公用修有闻见字书目其未备者辄疏于此”,这两则条目记录了明代著名学者杨慎的存书目录和闻见书目,涉及许多史传未及的音韵学书籍,是一份音韵学文献的珍贵资料。
本文主要依据这27条札记的相关阐述,探求焦竑透过它们所表达出的音韵学思想。
一、《焦氏笔乘》的音韵学观点
(一)《诗经》乃“韵之祖”
焦竑之所以能提出“古诗无叶音”这一观点,首先源于他对诗韵根源的正确认识:《诗经》中所依押的韵是古代的韵,即当时的本音,而不是今时的韵,应以古韵为宗。而“叶音”说的认识根源在于以今泥古,用当时的“今音”去求古音的协和,即以今韵为宗。
卷一第19条“朋当在东押”在用《左传》、东汉刘桢《鲁都赋》中的相关材料考证《诗经》“每有良朋,烝也无戎”一句中“朋”当与“戎”“相叶*结合上下文,焦竑这里所指的“相叶”,应是读音协和之意,而不是叶音说中的妄改读音。”之后,指出沈约将“朋”置于“烝韵”,而“肱”、“鞃”、“堋”、“薨”、“宏”列之后,是编次的错误,并且明确提出:且《毛诗》,诗词之祖,则其韵亦韵之祖也。舍圣经不宗,而泥沈约偏方之音,其固甚矣。此所当首辨也。
焦竑认识到,既然《诗经》是诗词之祖,那么《诗经》所依押的韵,也就是韵的始祖,是要“宗”的“圣经”,这是首先应当辨明的问题。之所以将《诗经》提到“圣经”的地位,是因为焦竑认为:“韵之于经,所关若浅鲜,然古韵不明,至《诗》不可读;《诗》不可读,而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之教或几于废,此不可谓之细事也。”[2]128虽然焦竑出于封建教化礼教作用如此强调《诗经》的地位,但也清楚地指出了正确的韵读对于《诗经》的重要作用:古韵不明晰,《诗经》就无法正读。这一点,看上去好像无关紧要,其实却关系着对《诗经》时代语音的确定:用古音读古韵才可取。
有了正确认识,才能引领学术研究走上科学道路。焦竑这种客观、正确的认识无疑为古音学发展带来了转折与进步。认识到这一点,也就为“古韵今韵”的辨别打下基础。
(二)韵有古今
焦竑在卷三第144条“古诗无叶音”中明确提出:诗有古韵今韵。这话虽不似陈第“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般铿锵震耳,但却意识到语音的历史演变,认识到诗歌之韵有古韵和今韵不同,不能像“叶音说”那样随意地用今天的韵去改求古韵的和谐。这已然是一种较为明晰的语音发展观。这一点其实可以看作是“古诗无叶音”观点的理论依据:正是因为古韵与今韵有不同,才不必用今音去苛求古音的协和。而陈第正是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意识到空间方位不同,语音也会有所不同,乃“势所必至”。他的这种语音发展观还表现在:认识到《离骚》时代(即战国时期)、汉、魏距离《诗经》时代不远,所以它们用韵相同。《离骚》、汉、魏去诗人不远,故其用韵皆同。世儒徒以耳目所不逮,而凿空附会,良可叹矣。这种划分(即将《诗经》《离骚》时代与汉魏归并),是基本符合实际情况的:上古汉语时期大致为周、秦、汉三代*目前学术界的汉语史分期一般以唐作藩先生的分期为基础,针对语音、语法发展的不平衡性做出适当调整。远古汉语时期:商以前(前11世纪以前);上古汉语时期:周、秦、汉(前11世纪~2世纪);中古汉语时期:六朝、隋、唐、五代(3世纪~10世纪);语法史的中古期从东汉末年开始,以王充的《论衡》为标志。近代汉语时期:宋、元、明、清、民国前期(11世纪~1919年);语音史的近代期从元代开始,因为宋代口语标准音仍以河洛(河南、陕西)方音为基础,并且官韵韵书与唐代一致;元代以后,口语中心转移至北京。语法史的近代期从五代开始。现代汉语时期:五四运动以后(1919年至今)。。
在考证古音时,焦竑注意用同一时期的诗文韵文材料来加以佐验。如第78条“浊古音独”。《孟子》:“沧浪之水浊兮”,“浊”音“独”,舆“足”叶。《史·律书》:“浊者,触也。”《白虎通》:“渎者,浊也。”《汉书》:“颖水浊,灌氏族。”《古乐府》:“独漉独漉,水深泥浊。”张君祖诗:“风来咏愈清,鳞萃渊不浊。斯乃玄中子,所以矫逸足。”又俗谓不明曰“毂浊”,以酒为喻;或作“骰突”(李剑雄校注:骰突,疑是“鹘突”之误。)或作“糊涂”,并非。
焦竑在证明战国时期成文的《孟子》中的“浊”古音当为“独”时,就列举了西汉时期《史记》、东汉时期《白虎通》和《汉书》、记录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的《古乐府》、东晋张翼(字君祖)的诗作来加以验证。
综合考察其他涉及古音考证的条目:21咎繇锺繇二繇同音、56师古注误、61缠读如战、159追蠡、84角里、118鄂不,可以总结出焦竑研究古音、考证古音所选取的材料:《孟子》《史记》《白虎通》《汉书》《古乐府》《离骚》《大戴记》《礼记》《古尚书》《周礼》《世说新语》《淮南子》苏伯玉妻《盘中诗》、刘桢《鲁都赋》、张翼(字君祖)的诗作。可以看出,他所选择材料的范围是明确的,就是秦、汉、魏晋等距《诗经》时代不远、语音面貌大致相同的诗歌韵文。
这一点,焦竑比吴棫进步了许多。吴棫虽然对古音有所发见,而且对古韵进行了系统研究,将之归纳为九部。但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材料的选择年代跨度太大,上起《周易》、《尚书》、《诗经》、《楚辞》,下取欧阳修、苏轼、苏辙等人的诗证。如此,其实还是混淆了古音的概念与时间界限。而焦竑不光意识到古韵今韵的区别,还对古韵的时间界限做了很好界定,其对语音发展的认识不可谓不精准。
受焦竑影响,陈第在《毛诗古音考自序》中,也强调说考证《诗经》本音的材料的本证是出自《诗经》,而旁证就是出自《左传》、《国语》、《易经》、《离骚》、《楚辞》、秦碑、汉赋,以至上古歌谣、箴、铭、赞、诵*陈第.《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康瑞琮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版,第7页:“又《左》《国》《易》《象》《离骚》《楚辞》、秦碑、汉赋,以至上古歌谣、箴、铭、赞、诵,往往韵与《诗》合,是古音之证也。或谓三百篇,诗辞之祖,后有作者,规而韵之耳。不知魏晋之世,古音颇存,至隋唐澌尽矣。”。[3]7
(三)“古诗无叶音”
作为对“叶音说”的批判,“古诗无叶音”并不是一句凭空口号。它不仅有自己的理论基础(诗有古韵今韵)和研究实践(对具体语音的考证),而且对“叶音说”错误的根源以及这样做会产生的严重后果也有客观认识。
焦竑首先指出“叶音说”错误的根源:用今韵去读古代的韵文材料,有不合辙押韵之处,就强改读音,即是今而非古、以今律古。古韵久不传,学者于《毛诗》《离骚》,皆以今韵读之。其有不合,则强为之音,曰:“此叶也。”并点出自己对这种现象的否定态度:“予意不然。”前有学识淹贯者如杨慎,虽然也有对“叶音说”的怀疑,却没能彻底对之进行否定。只有焦竑,言之确凿地进行了批判与否定。同时他也指出“叶音说”会带来严重后果:字无正音,诗无正字。如“驺虞*朱熹.《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5页:“彼茁(音拙)者葭(音加)。壹发五豝(音巴)。于(音吁)嗟乎驺虞(叶音牙)。”“彼茁者蓬。壹发五豵(音宗)。于嗟乎驺虞(叶五红反)”。”,[4]5一“虞”也,既音“牙”而叶“葭”与“豝”,又音五红反而叶“蓬”与“豵”;“好仇*朱熹:《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4页:“肃肃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叶渠之反)。(兴也。逵、九达之道。仇、与逑同。匡衡引关雎、亦作仇字。公侯善匹、犹曰圣人之耦。则非特干城而已、叹美之无已矣。下章放此)”。。”[4]14一“仇”也,既音“求”而叶“鸠”与“洲”,又音渠之反而叶“逵”。如此则“东”亦可音“西”,“南”亦可音“北”,“上”亦可音“下”,“前”亦可音“后”,凡字皆无正呼,凡诗皆无正字矣,岂理也哉?
需要说明的是,“驺虞”这一条,杨慎也做过考证*“虞字,一也,此诗一音牙,一叶五红。诗有二章而叶音二变,使诗五、六章尾句同者,亦五、六变乎?不知古诗有屡章而尾句同者多不叶,如《蜀离》《桑中》《椒聊》《文王烝哉》之类也,此犹为远”(杨慎)。。二者不同之处在于:杨慎虽然也说此种叶音“纰缪之极”,却只是想要纠正“叶音说”中不那么合理的地方,并未要否定它;而焦竑却透过同样的例子,看到了叶音说的严重后果:如此则音可乱叶,最终会造成字无正呼、诗无正字!所以,他第一个用极具概括性与力量性的语言明确地否定了叶音说:“古诗无叶音”。
可以说,“古诗无叶音”是焦竑科学的语音发展观念的具体体现。正是因为意识到《诗经》时代有《诗经》时代的韵读,今韵有今天的韵读,所以,“古诗”才根本不必去“叶”今天的“音”。
(四)义别音殊
焦竑认识到一字有不同之音,亦有不同之义。在不同的意义中,字的读音也不相同。第83条“随误改隋”中举杨坚改国号为“隋”之例而证明音呼之异与意义之别,并明确提出义别音殊的观点:《天官书》:“廷藩西有隋星五。”“隋”音“妥”。宋均曰:“南北为隋。”“隋”谓垂下也。杨坚国号改“随”为“隋”,意义既别,音呼亦殊。王应麟曰:“随,安步也,吉莫大焉。隋,裂肉也,不祥莫大焉。而妄改之,不学之过也。”
这一认识也指导其在进行语音考证的时候,很好地运用了汉字形、音、义结合的特点,来确定字的音读,尤其是多音字的音读。如第275条“率有五音”:将率之率音帅;《孟子》“彀率”、《左氏》“藻率”、唐“率更令”,皆音律;量名音刷;督率之率音朔;算法约数之率,音类。
二、《焦氏笔乘》的音韵学文献记录
焦竑学识渊博,作为文献考据名家,其《笔乘》中还有几条涉关音韵学的文献记录。
(一)关于《切韵指掌图》及三十六字母
第261条“三十六字母(二条)”记录了《切韵指掌图》的面貌以及相关门法。另有吴幼清、陈晋翁对三十六字母的增删意见。
(二)关于音韵学相关著作
第264条“杨用修闻见字书目”记录了杨慎的闻见字书目录;第265条“英公用修有闻见字书目其未备者辄疏于此”补足上条之未记录者。
其所记录的书籍名录,恰好可以和其他史记材料相互映证;而有些书籍,则是在其他文献中都没有记录的,颇具考记价值。
三、《焦氏笔乘》的音韵学研究方法
观点的提出要依赖具体研究的支撑,否则,那观点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不可为信的。焦竑的音韵学观念是通过具体研究而提出的,虽然还没有系统地进行古音系联,但基本理论思想及研究的基本原则都比较明晰地提出来了,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科学的。
(一)本证、旁证方法的初萌:材料互证方法
陈第《毛诗古音考》受到推崇的另一原因,是其所采用的诗例详实、可信。其在《毛诗古音考自序》中明确提出:“又惧子侄之学《诗》而不知古音也,于是稍为考据,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本证、旁证两相互证的方法,可以说是科学证明的一个有力证据。不仅在《诗经》内部找到其他例证,而且在同一语音时代找到其他的例证,两相参验,证明力自然大大提升。焦竑在《毛诗古音考序》中也直言:可以“令读者不待其毕,将哑然失笑之不暇,而古音可明也”。这一点,《钦定四库全书提要》也犹为强调:“本证者,《诗》自相证,以探古音之源;旁证者,他经所载,以及秦、汉以下去《风》《雅》未远者,以竟古音之委。钩稽参验,本末秩然,其用力可谓笃至。”[4]5这一科学的证明方法,焦竑在《笔乘》中就已有体现,在《古诗无叶音》中就已明确地使用了:
予儿朗生五岁,时方诵《国风》,问曰:然则“驺虞”、“好仇”,当作何音?余曰:“葭”与“豝”为一韵,“蓬”与“豵”为一韵,“吁嗟乎驺虞”一句,自为余音,不必叶也。如“麟之趾”,“趾”与“子”为韵,“麟之定”,“定”与“姓”为韵。“于嗟麟兮”一句,亦不必叶也。《殷其雷》《黍离》《北门》章末语不入韵,皆此例也。
《兔罝》,“仇”与“逵”同韵,盖“逵”,古一音“求”。王粲《从军诗》:“鸡呜达四境,黍稷盈原畴。馆宅充鄽里,士女满庄馗。“馗”即“逵”,九交之道也。不知“逵”亦音“求”,而改“仇”为渠之反以叶之,迁就之曲说也。
如“下”,今在祃押,而古皆作“虎”音:《击鼓》云:“于林之下”,上韵为“爰居爰处”;《凯风》云“在浚之下”,下韵为“母氏劳苦”;《大雅·绵》“至于岐下”,上韵为“率西水浒”之类也。“服”,今在屋押,而古皆作“迫”音:《关雎》云“寤寐思服”,下韵“辗转反侧”;《有狐》云“之子无服”,上韵为“在彼淇侧”;《骚经》“非时俗之所服”,下韵为“依彭咸之遗则”;《大戴记》:《孝昭冠词》“始加昭明之元服”,下韵”崇积文武之宠德”之类也。“降”,在绛押,而古皆作“攻”音:《草虫》云“我心则降”,下韵为“忧心忡仲”;《骚经》“惟庚寅吾以降”,上韵为“朕皇考曰伯庸”之类也。“泽”,今在陌押,而古皆作“铎”音:《无衣》云“与子同泽”,下韵为“与子偕作”;《郊特牲》“草木归其泽”,上韵为“水归其壑,昆虫无作”之类也。此等不可殚举。使非古韵而自以意叶之,则“下”何皆音“虎”,“服”何皆音“迫”,“降”何皆音“攻”,“泽”何皆音“铎”,而无一字作他音者耶?
在证明“驺虞”之“虞”自为“余”音,并不与“葭”“豝”及“蓬”“豵”相押,不必迁就而叶“牙”“五红反”时,焦竑就列举了《诗经》中《殷其雷》《黍离》《北门》三则章尾不入韵的例子,以资佐证。
在证明《兔罝》中“逵”,有一古音“求”时,同列东汉诗人王粲诗句为例。
在证明“下”之古音为“虎”时,列《诗经》中《击鼓》《凯风》《大雅·绵》之例。
在证明“服”古音为“迫”时,列《诗经》中《关雎》《有狐》之例,又列战国时《离骚》与汉代《大戴记》做佐证。
在证明“降”古音为“攻”时,列《诗经》中《草虫》之例;另列《离骚》例。
在证明“泽”古音“铎”时,列《诗经》中《无衣》之例,又列汉代《礼记》中《郊特牲》例。
这样的证明,也正如焦竑评价陈第的那样“不待其毕”而“古音可明”。需要另加说明的是,焦竑所做的这几则考证,陈第在《毛诗古音考》中也多有参验,如:
降音洪。本证中采用《草虫》之例: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旁证中亦采用《离骚》之例: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下音虎。本证中也采有《大雅绵》之例: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
(二)形音义结合的考证方法——结合字形、意义考证音读
焦竑的音韵学研究还体现在其对语音、诗韵所进行的考证上,而且他很好地利用汉字形、音、义结合的特点,从字形和意义入手去选择、确定字的音读,尤其是多音字的音读。如第312条“提耳”:
《诗》“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提音抵,言附耳以教之也。《礼·少仪》“牛羊之肺,离而不提心”,《史记》“薄后以冒絮提文帝”,《汉书》“景帝以博局提杀吴太子”,扬雄《酒箴》“身提黄泉”,皆作抵音。若作平声,当作揪扯之义,不如前说为近雅也。
这里焦竑结合了《礼记》《史记》《汉书》《酒箴》(扬雄)之例,证明《诗经》中的“匪面命之,言提其耳”中的“提”应读为“抵”(上声),是“附耳以教之”的意思,如果读为平声,则是揪扯的意思,于句意不和。
第245“当歌之当非去声”也是如此,通过字的意义去确定其在诗句中应读的音。
《卮言》云:“古乐府‘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二语妙绝。老杜‘玉珮仍当歌’本此。用修引孟德‘对酒当歌’云:‘得子美一阐明之,不然,读者以为“该当”之当矣。’大膭膭可笑。孟德正谓遇酒即当歌也。若以对酒当歌作去声,有何趣味?”元美此言,误会用修之意矣。用修正读当为平声,如当时之当,言人生对酒与当歌之时无几耳。何尝作去声如“当泣”、“当归”之当哉?子美诗“当”亦作平声,若如元美读,不成诗矣。
除此之外,条目56师古注误、84角里、118鄂不、159追蠡、269廿卅卌三音、270甄有三音、274繇有六义、275率有五音、276敦有九音、278苴有十四音、427琵番蒲司帆作仄声都是着眼于音义的辨别。同时,他也认识到韵书中也有读音不同而意义相同的现象,如第268条“霓可两音”中言:
霓,《说文》:“屈虹,青赤或白,阴气也。”雄曰虹,雌曰霓。研奚切;又五结切。《南史》:沈约作《郊居赋》,以艹示王筠,读至“雌霓连蜷”,沈抚掌曰:“仆尝恐人呼为平声。”范蜀公召试学士院,用彩霓作平声。考试者判《郊居赋》霓,五结切,范为失韵。当时学者为之愤郁。司马文正公曰:“约赋但取声律便美,非霓不可读为平声也。”按韵书此类甚多,有两音、三音而义同者,皆可通用。
他还能辨别同音假借,从而确定本字。如第209条“杜诗用投字”:
“远投锦江波”,“投”音豆,假借为“逗合”之“逗”也。又借为“句读”之“读”,马融《长笛赋》:“察度于句投。”又借为“酘酒”之“酘”,梁元帝《乐府》:”宜城投酒今行熟,停鞍驻马暂栖宿。”盖重酝谓之酘酒。
(三)依据诗意辨明韵读的方法
焦竑不光根据字形考证单个字的读音,还依据诗意而辨别诗歌中的韵读。如第173条“李夫人歌”:
武帝《李夫人歌》:“是邪非邪,立而望之,翩何珊珊其来迟?”“之”与“迟”一韵。“翩何珊珊”,言其来翩然,而佩珊珊然耳。许顗《诗话》云:“立而望之偏”,是退之“走马来看立不正”之所祖也。以“翩”字属上,不惟于韵不叶,且“立而望之偏”是何语邪?
四、《焦氏笔乘》的古音学贡献
《钦定四库全书提要》对陈第《毛诗古音考》推崇之至,认为其有开导先路之功:“国朝顾炎武作《诗本音》,江永作《古韵标准》,以经证经,始廓清妄论。而开除先路,则此书实为首功。”[4]5要探究陈第的思想根源,无法绕过焦竑。《钦定四库全书提要》还有这样一句话,深耐寻味:“初第(陈第)作此书,自焦竑以外,无人能通其说,故刊版旋佚。”这里所言指“说”,就是始自焦竑倡言的“古诗无叶音”之论。其意思即是说除了焦竑外,没有人能通解这一学说。而实际上,陈第正是受焦竑的影响,才作出这部《毛诗古音考》。而且焦竑在陈第著作此书时,也给予了大量帮助。
焦竑在《毛诗古音考序》中亦提到:
甲辰岁,季立过余,曰:“子言古诗无叶音,千载笃论,如人之难信何?”遂做《古音考》一书,取《诗》之同韵者胪列之为本证,已取《老》、《易》、《太玄》、《骚赋》、《参同》、《急救》、古诗谣之类,胪列为旁证,令读者不待其毕,将哑然失笑之不暇,而古音可明也。噫,季立之用心可谓勤矣!
陈第在《毛诗古音考跋》中也提到:
往年读焦太史《笔乘》曰“古诗无叶音”,此前人未道语也。知言哉!……秋末造访太史,谈及古音,欣然相契。假以诸韵书,故本所忆记,复加编辑。太史又为补其未备,正其音切。
从这两段话中可以明确:陈第的确是在焦竑的启发下明确了语音时地观,而且为阐发“古诗无叶音”之观点而做《毛诗古音考》;而在著作过程中焦竑也给予了大量帮助,不仅借给他相关韵书,甚而还进行了补备、正音工作。思想的启蒙、图书资料的证供、内容的补备与音切的确正,这些都是焦竑在《毛诗古音考》这一具有独特历史意义之书中所担起的工作,不可谓轻微。
正确的认识是学术研究的前提条件,科学的方法与可信的材料是进行研究的必要条件,而这些焦竑均已具备。
[1]焦竑.焦氏笔乘 [M].李剑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8.
[2]焦竑.澹园集 [M].李剑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9.
[3]陈第.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M].康瑞琮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
[4]朱熹.诗集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8.
(责任编辑 鲁守博)
Approaching the Phonology Theory Revealed inJiaoShiBiCheng
Lu Lu
(College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FujianNormalUniversity,Fuzhou350007)
JiaoShiBiChengis the study notes by Jiao Hong, a famous scholar in Ming Dynasty. The content of his book is miscellaneous, while the textual research in this book is irreproachable. In addition to the proposition that “There was no homophone in ancient poetry”, Jiao Hong also explicitly noticed that ancient rhyme wa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oday, which was stated much earlier than the sound shift notion by Chen Di. Besides,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s on ancient rhyme have also been embodied inJiaoShiBiCheng, which have exercised direct and profound influence on Chen Di.
JiaoShiBiCheng; phonology;“no homophone in ancient poetry”
2015-03-08
陆露,女,安徽淮南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H11
A
1672-0040(2015)03-007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