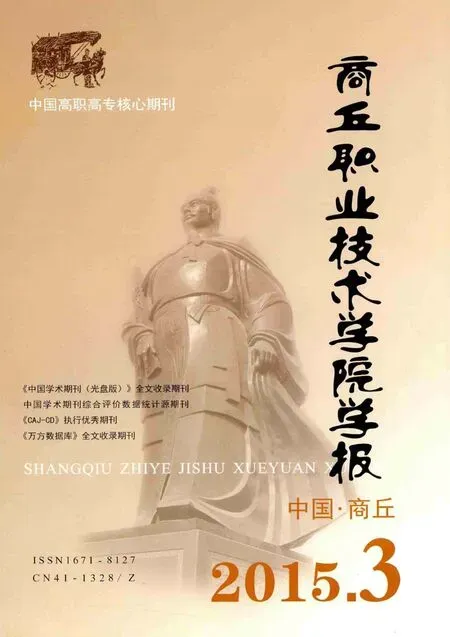探析男性身体书写中的文化规训
——以老舍、沈从文、郁达夫和白先勇的男性身体书写为例
姚 婷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作家以自我经验为书写对象“以摆脱男权中心文化对女性的限制和操控”[1]1,对身体书写的主流界定是女作家书写女性身体,但也有部分学者将对象扩展到男性,认为只要是“围绕着对人的肉体描写所展开的灵与肉、情与欲、意与性的升腾和搏战”[2]1即是身体书写。“身体”是富有生命活力和感情、敏锐而有目的取向的,而不仅仅是那个单纯由骨肉聚集而成的物质性“肉体”[3]5。以性别为横向坐标,以主流与边缘为纵向坐标,身体写作的范畴应当包含主流、边缘的男性、女性身体书写。本文以沈从文、老舍、郁达夫和白先勇的文本为例对应现代文学男性身体书写的四个维度,通过男性对自我身体的想象,进一步了解其精神世界的生态环境。
一、湘西大自然之子与城市底层劳动者
沈从文湘西世界中的小伙子都“结实如牛犊”[4]64,傩送二老“黑脸宽肩膀,样子虎虎有生气的”[4]117,《丈夫》里的男人“诚实耐劳,年轻而强健”[4]164,即使是渡船的老人都“硬朗得同棵楠木树一样”[4]88。这些男人不论年纪和职业都有共同的特点,肤色呈现自然的黑,肌肉结实,骨架宽大,极具男性的阳刚与雄健气质。成长于乡村世界,他们如大自然的其他生物一样生长,像小牛犊一样结实,像老虎有生气,像楠木树一样硬朗。体格健康的乡村男性心灵世界也是质朴而纯净的,大佬和二佬以类似鸟类求偶的方式唱歌来获取姑娘的芳心,老婆做妓女补贴家用被认为是正常的,水手和妓女之间存在着动人的真情。沈从文湘西男人的身体之所以能够以健康状态存在正是因为美好的自然环境与纯善的社会环境。
不同于湘西男人如小牛犊般的健壮,祥子作为城市的底层车夫,身体是如铁打一般的强壮。老舍认为人物的塑造是小说成败的关键,“不可泛泛地由帽子一直形容到鞋底;没有用的东西往往是人物的累赘”[5]443。老舍抓住了胸、背、肩、脚这几个部分刻画祥子的出场形象,可以依靠的“铁扇面似的胸与直硬的背”,能够承担重任的“多么宽,多么威严”的肩,“出号”[6]5的大脚则是脚踏实地的象征,简单几笔勾勒出了车夫行业的佼佼者应当具备的骨骼框架。紧接着描摹祥子并不出众的五官,永远红扑扑的脸上有圆眼、肉鼻子、很短很粗的眉毛,“腮上没有多余的肉,脖子跟头一样粗”,颧骨和右耳之间那一个小时候被驴啃过留下的疤说明祥子来自农村,对于靠体力吃饭的劳动者来说,头发这种修饰性的身体部件是不需要的,所以头顶“永远剃得发亮”。祥子对身体所有器官的看法是“只要硬棒就好”[6]6。祥子用自己年轻健壮的身体跑出了车夫行当中名贵的姿态,“活动,利落,准确;看不出急促而跑得很快,快而没有危险”[6]7,来自农村的健壮男性初入城市即以身体作为资本换来了金钱与荣耀,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他将自己辛苦买车的日子也作为自己的生日,在与车磨合的过程中,祥子把车变成了身体的一部分,“仿佛有了知觉与感情,祥子的一扭腰,一蹲腿,或一直脊背,它都就马上应合着,给祥子以最顺心的帮助,他与它之间没有一点隔膜别扭的地方”[6]12,跑车的时候生怕碰伤了车便对不起自己,因为车是他的命,车是铁做的,他觉得自己的身体也是铁做的。
祥子对身体的自信在婚后发生了改变,同行那里学来的性知识使他将虎妞看作吸人血的妖精,他开始“晓得一个卖力气的汉子应当怎样保护身体,身体是一切”[6]163。阳刚雄健是社会训规对正常男体的要求,当阳痿这种生理疾病与男性尊严挂钩的时候,随之而来的心理压力远远大于生理上的痛苦。在这种令自己觉得可耻的病好了以后,祥子就几乎变了一个人,“那股正气没有了,肩头故意的往前松着些,耷拉着嘴,唇间叼着支烟卷”[6]223。从最开始对身体有着强壮的期待,婚后对身体的怀疑,病后对身体的否定,直到最后对身体的放弃,祥子渐渐明白拉车是怎么回事。王德威评论“小说的喜剧设计经历了一个完整的过程——最后将人物变成了机器”[7]171。车曾被祥子看作身体的一部分,因为如同自己的四肢一样硬棒的车,可以帮助他换取想要的美好生活,一旦自己的身体先垮了,他对车便“不再那么爱惜了”[6]226。祥子的精神世界也随着身体的状况一步步跌入深渊,祥子对车的放弃象征的是对自我的抛弃。
健康的男性身体与健康的自然生存环境结合才能产生健康的灵魂,沈从文湘西世界里的男人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是不受传统规训的大自然之子,身体与心灵都处于自然健康状态。“健壮的身体与健康的自然生存环境分离的结果是,威严的肉体往往与邪恶的人格结合在一起”[8]329。一旦健康的男性身体脱离健康的自然生存环境,受到社会规训对男性身体想象的制约,男性身体便走向异化了。如祥子一般强健的男性身体书写中散发出来的身体焦虑感恰恰证明了男性群体在男权社会中受到的戕害和压抑并不少于女性,男性为了达到社会规训定义的刚强健壮付出了不容小视的代价。
二、男性边缘化的身体形态
正常的男性身体描述为阳刚健康雄壮的,与之相反,那些非正常的男性身体被人们冠以“病态”“变态”的形容词游走于话语体系的边缘。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塑造了一系列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他们的面孔都清瘦苍白,或许因为生病的缘故染上一层红色,纤长瘦弱的体型,情感丰富,泪腺发达。这群体弱多病、即使无病也爱呻吟的男性知识分子,跟祥子这种真正脚踏土地与生活角力的劳动者所处的社会阶级不同,让他们苦闷的原因也不尽相同。“大抵作家的人物,总系具有一阶级或一社会的特性者居多”[9]439。“作家对于人物的性格心理的知识,仍系由他自家的性格心理中产生出来的”[9]438。所以结合郁达夫个人小说观及其文中对男性身体的书写,大致可以了解那个时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自我身体的想象。
郁达夫自叙传小说中有许多因为性苦闷、偷窥癖、恋物癖、思乡病和青春忧郁病而备受精神折磨的男性,他们矫情的表达和廉价的眼泪总是让人无法相信那些赤裸裸的对自我灵魂的拷问是发自内心的。与其说他们因为自身的“病态”受到煎熬,不如说他们享受这样一种正常话语体系中的“病态”状态。《沉沦》中那个患了忧郁病的男主人公想起自己的苦处眼泪就如瀑布流下,在哭的同时大脑中出现幻象的声音“你别再哭了,怕伤害了你的身体!”,紧接着“他觉得悲苦的中间,也有无穷的甘味在那里”[10]41。《茫茫夜》中的质夫用妇人的手帕擦被自己刺出血的脸颊,想象手帕主人的态度,“他觉得一种快感,把他的全身都浸透了”[10]117。《迟桂花》里的翁则生病到痰里有血丝,脸上苍白,身体瘦削,家人都担心得不得了,也依然觉得“没什么惊奇骇异的地方”。郁达夫小说中的这些知识分子相当契合“文弱书生”的特质,病弱的身体或强作愁的心理状态更能刺激他们对于颓废美的追求,病态的身体让他们更能艺术地生活在幻象中。拥有健壮身体的祥子至死不能正视自我的欲望,这些身体病态的知识分子清楚知道社会训规对手淫、纵欲、偷窥的道德谴责,但依然选择正视人性最自然最真实的欲念。
另一种处在边缘的男性是被主流排斥为异端的男同。《孽子》中的男同性恋者是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犹自彷徨街头,无所依归的孩子们”。这个群体见不得日光,被人遗忘遭人唾弃,在黑夜的保护下他们才敢出来。记者在潜入安乐乡后写道,“这儿没有三头六臂的吃人妖怪,有的倒是一群玉面朱唇巧笑倩兮的‘人妖’”[11]300。这一发表于报纸的言论可见社会大众舆论对于这些男性群体的不理解、不屑和鄙视。作者白先勇先生本身是一个男同性恋者,他的描写足以反映一个男同性恋者对这个群体男性身体的想象。吴敏“两腮全削下去,一双乌黑露光的大眼睛,坑得深深的”[11]15;小精怪长得浓眉大眼[11]17;龙子“颧骨高耸,两腮深削下去,鼻梁却挺得笔直的,一双修长的眉毛猛地往上飞扬,一头厚黑的浓发,蓬松松的张起。……只有他那双深深下陷,异常奇特的眼睛,却像原始森林中两团熊熊焚烧的野火,在黑暗中碧荧荧的跳跃着”[11]21;阿凤“一双长眉,飞扬跋扈,浓浓的眉心却连接成一片。鼻梁削挺……一双露光的大眼睛,猛地深坑了下去,躲在那双飞扬的眉毛下……脸是一个倒三角,下巴兀的削下去,尖尖翘起。”[11]71白先勇对这些男性外貌的描写特别关注眉眼、鼻梁和头发,与老舍对祥子外貌的描写相对比差异巨大,祥子外貌以实用为主,而这些男性面貌却讲究俊俏立体,讲究审美的特点。除了面貌,这群男性的身材与穿着也是异于正常男性的。杨教头“穿着一身绛红的套头紧身衫……一条黑得发亮的奥龙裤子,却把个屁股包得扎扎实实隆在身后”[11]8;原始人阿雄仔是个门神一般的庞然大物,好像马戏团里的大狗熊,崭新的尼龙运动衫把他胸膛上的肌肉,绷得块块凸起[11]11;龙子身材高瘦,一身嶙峋的瘦骨,一根根往外撑起。深蓝的衬衫好像绷在一袭宽大的骨架上似的[11]21;华国宝“身材很帅,长腿细腰,一个倒三角的胴体,宽厚的胸膛上,两块胸肌嚣张的隆起”[11]97;铁牛“一条黑帆布的腊肠裤,箍得腿上的肌肉波浪起伏。皮带也不系,裤头滑得低低的,全身都在暴放着野蛮的男性”[11]98。这群男性高大而强壮,但却并非湘西男子或城市底层劳动者的模样,因为他们的身体包裹在色彩艳丽的紧身衫下,以一种最能暴露身体曲线的方式吸引他人的注目,这样性感的男体适合观赏,却不适合劳动。
他们并不是没有正经工作的机会,不论是阿青、小玉还是龙子,都有男人愿意给他们一份正经的工作,但那样体面的日子他们都过不惯,“仍旧会乖乖的飞回到咱们自己这个老窝里来。”[11]7这群野孩子追求的是一种精神和肉体上的自由,莲花池这个老窝象征着精神自由的绝对领域。他们宁愿在莲花池畔用自己身体短暂交易换取灵魂自由,也不愿被人用物质长久地束缚,就算是以爱的名义都不行,最典型的是黑暗王国的野凤凰阿凤,他深爱且深爱他的龙子将他们共同的家布置得衣食无忧,但阿凤宁可出卖身体给不爱的男人换取金钱。面对一个愿意把心掏出来给自己的疯狂爱人,这个不愿陷入爱情牢笼的野孩子说“我就是耐不住,一股劲想往公园里跑。”即使是爱也无法束缚骨子里向往自由的他。龙子越是深爱越是束缚,阿凤便越想逃离。阿凤必然是在爱与自由之间苦苦挣扎过的,他清楚自己活着一天身体就属于自由一天,同时他爱龙子但无法给爱人想要的安定,他爱他,更爱自由,所以选择了了结自己,所以倒在龙子怀里的阿凤垂死的眼神一点怨毒都没有,还露着令龙子心碎的歉然和无奈。
这些被正常话语称之为变态的男性身体因为逐心随性而显得放荡不羁,他们的灵魂却不曾被肉体羁绊,他们骨子里流淌的野性血液是具有反传统意义的,同性恋的身份使之成为异端,尽管正统话语对他们施以道德与舆论的封杀,这群不停飞翔的青春鸟依然追逐自己心灵的选择,演绎一曲生之悲歌。
三、结语
“文化史一再证明,每一次人的解放……都是人的肉体与‘上帝’和‘撒旦’战斗”[8]329。身体的想象是人们对形而下的“身体”的形而上“常识”,男性身体想象是长期社会训规的产物。在阳刚健壮的“正常”男性身体想象的普遍性下,经济状况、社会阶层和自我认知状态等因素决定个体男性身体想象的特殊性。个人所处的话语圈影响男性对自我身体想象的期待:天然的湘西世界里,纯朴如大自然之子的男性对于健康的身体有着深深的崇拜;黄包车夫这一行崇尚像铁一般的硬棒身体,所以祥子评判自己身体各个独立器官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硬棒实用;在男同性恋话语圈中,年轻漂亮的男性身体才有骄傲的资本,所以再有钱的盛公因为衰老也不能换来年轻一辈的真心陪伴,过气的电影小生阳峰只能跟着华国宝性感骚包的身体哀叹逝去的年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在常人避之不及的病态身体中找到了过剩欲望的释放窗口。
社会训规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社会各个阶层男性对自我身体想象的期待,当期待与现实发生冲突时,男性心理易走向崩溃。一味地将男性身体想象的可能形态单一化、强势化和精英化使处在男权社会中的男性所受到的压力和压抑也并不小于女性。所谓正常的男性身体可能在心灵上受到的禁锢更加严重,祥子无法正视身体并非无所不能这一事实,生理的疾病与道德、尊严相捆绑,阳痿的男性背上的更多是心理上的沉重枷锁。而低吼欲望的于质夫们、徘徊于莲花池畔的野孩子们,这些男性边缘身体形态的书写与反抗男权统治的女性欲望书写类似,都是以真正的人性抵抗社会的规训。
[1]李廷茹.误区中的女性话语——当代中国女性“身体写作”的文化分析[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7.
[2]张志忠.众声喧哗中的三重遮蔽——从郁达夫、王小波笔下的孽恋和虐恋谈起[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01).
[3]理查德·舒斯特曼.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M].程相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4]沈从文.沈从文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
[5]吴福辉.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M].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6]老 舍.骆驼祥子[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8.
[7]王德威.想像中国的方法[M].北京:三联书店,1998.
[8]张 柠.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9]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M].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0]郁达夫.郁达夫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11]白先勇.孽子[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