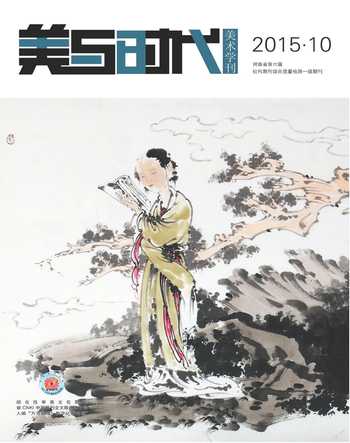“左图右史”在晚清:“世界图像的时代”与晚清的图绘复兴
摘 要:十九世纪,依托机械技术的发展,绘画与机械技术相结合,使人类逐渐步入了海德格尔所描绘的那个“世界图像的时代”。同时代下的晚清帝国也在战争中被迫开关,融入了“世界图像”的大潮。以明清之际“经世致用”的思潮为支撑、辅以“海西法”等绘画技法于明清之际的沉淀以及摄影、石印等西洋机械技术的引进与运用,中国古有“左图右史”的绘图、读图传统在历经长期暗淡后得以在晚清逐步复兴。
关键词:图绘;图像;晚清;“左图右史”;经世致用
一、“世界图像的时代”
十九世纪,随着欧美公众教育的普及,阅读群体得到了极大地增长。同时,摄影术、印刷术、煤气灯、电灯、蒸汽车船等科技产物的陆续问世,也给人们带来了更多阅读的机会与条件。阅读方式、阅读材料及阅读习惯的改变,使得观者对于与文字相对应的图像的需求愈发强烈。伴随着印刷技术的日益成熟,从1837年摄影术的诞生至1895年电影、放映机的出现,世界正逐渐步入一个全新的图像时代。正如海德格尔在《世界图像的时代》中所言,“科学乃是现代的根本现象之一。按地位而论,同样重要的现象是机械技术。”机械技术的崛起,给观者带来了更为直观生动的观赏、阅读材料,也为图像在公众之间的传播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论及机械技术,造纸业与印刷业的繁荣与成熟,是人类步入世界图像时代的一个重要因素。印刷术对于十九世纪的人们而言已经算不上什么新鲜事物,自文艺复兴以来,同一件艺术品通过雕版印刷已经能为身处异地的艺术家所共享。从约翰·谷滕堡(Johannes Gensfleisch zur Laden zum Gutensilberg)发明铅字印刷术之后,1798年,奥国人施纳菲尔特(Alois Senefelder)偶然发明了石版印刷技术,使得照相石版印刷成为可能。这一技术与传统的木板、铜版印刷相比较,具有成本低、印刷便捷等优点,更值得注意的是,石版印刷避免了图像的二次翻刻,节省了雕刻师艰苦而昂贵的工作,画师直接绘画于石版,使得印刷生成之图像非常忠实于原作。可以说,石版印刷技术的发明与发展,揭开了印刷工业化序幕。同时,十九世纪的印刷机已经可以对铜版与木版进行机械的处理,使之生产效率得以提升,这也拓宽了图像向公众的传播渠道。
虽然法国人达盖尔(Louis Jacques Mande Daguerre)早在1837年发明了“达盖尔摄影法”,甚至在此之前,一种“日照摄影法”也已问世,但由于技术操作与设备普及以及在摄影诞生之初,人们心理上的不适应所带来的对摄影的排斥感等问题,这一时期的图像制造并没有因新技术的出现而使绘画、雕塑等传统图像生成方式迅速走向没落。同时,介于艺术家自身对于工业化大潮到来所表现出的力不从心以及对于泛机械化风格的反感,致使包括摄影术在内的机械制作与逃避现实、回归传统的手工艺制作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常处于一种共融与抗衡的状态。十九世纪末出现在英国的“工艺美术运动”以及延续在法国的“新艺术运动”就是这种抗衡状态的极端显现。相比较这种参杂着艺术家的叛逆思想与逃避现实情绪带来的极端后果,机械与手工的合作与共融却是更应值得关注的。
新颖的主题、革新的观念、全新的受众以及新兴的市场,逐渐引起了一批艺术家们的关注,于是,艺术家们在不知不觉中被赋予了诸多新的属性。在那个崇尚机械科技而又反感机械化风格的时代,他们自觉地兼顾起了设计、绘制图像的任务,承担起图像与观众中间人的角色,掌控着图像生成的重要环节。某种程度上讲,绘画艺术家正于此努力重做图像的主人。
“现代的基本进程乃是对作为图像的世界的征服的过程。”(海德格尔《世界图像的时代》)反观机械技术兴起之初,在其催动下的图像的复制与传播于十九世纪的欧美诸国得到了空前的繁荣,继而伴随着战争、通商、传教等一系列人类活动,这场由机械复制所引起的图像风暴最终席卷了亚洲诸国。在此期间,不可避免的,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其“膜拜价值”(Kultwert)的没落继而转向其另一极端的“展示价值”(Ausstellungswert),使之失去了本雅明所言的“灵韵”(Aura),遂逐步沦为一种向大众传播的图像媒介。这也正应了海德格尔所提到的第三种现代想象:“艺术成了体验(Erleben)的对象”。作为一种直观的且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结果,正如鲁道夫·G.瓦格纳所描绘的那样,“我们看到画报和石版画这两种印刷品在十九世纪繁荣起来,进入了以前与印刷品市场根本无缘的那些阶级的家庭。”当然,十九世纪之图像绝不仅仅是画报与版画印刷品所能概括的,但是,其在生成与传播过程中,艺术家与观众的充分互动、机械技术的大规模运用,却是这个图像时代中一类很好的代表。自十九世纪初以来,绘画和机械印刷技术的结盟使得艺术创作与同样跟机械印刷关系密切的新闻业产生了交集,基于此,无数图画期刊、报刊的问世,构筑了瓦格纳所说的“全球想象图景(global imaginaire)的滥觞”,以微知著,一个世界的图像时代已经来临。
二、“左图右史”传统在中国的断代
中国图说形式由来已久,在文字中插入图像的做法也不是新鲜的事情。据现有史料,中国图说渊源可上溯至先秦的《伊尹·九主》。楚国帛书、秦国竹简、西汉马王堆出土的帛书,皆可寻图文共同绘制于竹帛之上者。至雕版印刷术问世,见中国最早的成品,为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所印《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佛经图文并茂,图像雕刻复杂精美,被公认为中国雕版印刷术之始祖。时至宋代,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与格致之学的兴起,使得书中附图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如《尔雅图》《博古图》《三礼图》《尚书图》《列女传》等皆是内附图像加之文字说明的书籍。对于画中插入作者姓名的做法也于北宋时期出现。宋人郑樵在其《通志》中撰《图谱略》一卷,阐述了图像治学的重要性,他已经意识到图像具有文字所不具备的价值:“图,经也。书,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图,植物也。书,动物也。一动一植,相须而成变化。见书不见图,闻其声而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图至约也,书至博也,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图像简约,文字博杂,虽说前人为学既有“左图右史”之传统,图文相得益彰,(“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故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举而措之,如执左契”)奈何这一传统并未很好地传承,后人放弃了图像而只是着眼于文字(“后之学者离图即书”),以至出现了一种藏书文字俱在而图像匮乏的境遇(“隋家藏书,富于古今,然图谱无所繁。自此以来,荡然无纪。至今虞、夏、商、周、秦、汉上代之书具在,而图无传焉。图既无传,书復日多,兹学者之难成也”)。
上下概览,虽然中国古来已有绘图、读图的传统,但事实上,这一传统并未撼动文字叙述的正统地位。正如钱穆先生所言:“书里不兼图,恐怕是我们中国学问很大一个缺点。西方一路下来,图书都连在一块。中国人不知何时起偏轻了图,这实是一个大缺点。”就中国美术史而言,“图”与“画”的关系是不易捕捉的。上古所载星象、玄学、地志、风物……各种图像资料,亦常见子后世画论之中,视“图”为“画”的现象,使得二者关系长期处于一种微妙的状态。颜延之曾述,古人“图载”形式有三,即图理(卦象)、图识(文字)、图形(绘画)。文字所成,或从图起,图形演变,遂成字体。可见,绘画与文字一样,皆是古人获取、传递信息,进行交流的载体,而“图”与“画”关系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得以体现。从文人画的角度看,画重在笔墨气韵,更多指向的是一种审美上的交互;图则重在存知,更为偏向信息的辨识与交流。“图”“画”之间相辅相成,实难有明确的界限加以划分,但二者之间仍然存在着张力。“图”、“画”多交汇,二者亦有别,中国传统视觉艺术大都摆动于二者之间。
三、图绘在晚清的复兴
依据柯律格(Clunas,C.)在《明代图像与视觉性》一书中对图绘(pictures)这一范畴的基本描述,它连接着绘画作品、印刷作品以及诸如陶瓷或漆器这类物品上的图像(images),此范围仍在扩大。
图像是在明清之际才开始造成广泛的视觉冲击的,特别是在晚清,图像的绘制与传播对整个社会造成的冲击与影响尤为明显。关于这一点,可以分为两个方面进行阐释:一是以“西风东渐”为大背景,在“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下,国人对于图像价值的重新重视;二是西洋传教士所传“海西法”的刺激以及摄影、石版印刷等技术的引进所引发的制图、印图、观图方式的改变。简述之,一为思潮使然,二为技艺准备。
与18世纪风靡于欧洲的“中国风格”相同,明清之际所述“泰西法”与“海西法”词义甚宽,具体于绘画所涉及的内容主要为单眼定点直线透视法和明暗对照法,其不仅是当时艺术实践的重要手段,也是晚清兴起“图学”与“视学”之基础。对于“海西法”在明清之际的沉淀一说,我们需要将其置于明清时期受到西方绘画技法的影响,在创作中不同程度地将中西绘画之方法融合到一起的“西洋风美术”中去审视。
以传教士来华和亚欧商业贸易为背景的明清之际“西洋风美术”,显现于三个较有代表性的艺术现象:宫廷洋画之兴起、姑苏版画之兴旺与广州十三行外销画之繁荣。
“我国自明末海禁驰后,东西洋文化,逐渐接触。至于绘画方面,自利玛窦(Matteo Ricci)献天主像后,画法上颇蒙其影响。迨至清代,郎世宁等西籍教士,又入画院供职,一般画人,多喜参用西法,相效成风。”(山隐:《世界交通后东西画派互相之影响》)是时中国统治者对于传教士的特殊政策,使得以西洋绘画为代表的异域图像与以“泰西法”“海西法”为代表的西方制图技法传入中原成为可能。随之而来的是这种异域图像的视觉经验经与新颖的制图手段统治阶层以及为其服务的宫廷画师,同时伴随着传教士的传教活动,逐步流入民间(此处“民间”相对于宫廷而言,尤以江南地区为代表)。
如果说三代帝王对于郎世宁的重用与欣赏折射了统治者对“西洋风美术”的认同与热忱,那么姑苏版画的兴起则反应了西洋图像在民间被接受的大好景象。所谓“姑苏版画”一般指明末至清乾隆年间,苏州桃花坞产以年画为主的版画类印刷品。“旺盛之时,桃花坞年产画数万张,远销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数省,甚至还出口日本和东南亚。”(莫小也《17—18世纪传教士与西画东渐》)这些产于民间,题跋有“仿泰西笔法”的版画作品,所体现出的是“西洋透视画法”“明暗投影”“铜版画细腻效果”等迹象,西洋图像的特点于此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姑苏版画也因此成为中国民间对西洋图像掌握、效仿、传播的经典案例。
将广州外销画置于“西洋风美术”的范畴虽说有失准确,但将其置于“西画东渐”的范畴下,从十九世纪初中国民间所产“西化图像”的对外输出这一角度去看,却是未尝不可。十九世纪上半叶,随着耶稣会的解散,其宗教势力步入低谷,传教士在华活动与影响范围已日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以频繁的亚欧商业贸易为背景,中国南方通商口岸之繁荣所带来的巨大商业潜力和国际吸引力。以英国乔治·钱纳利(George Chinnery)为代表的外籍画家陆续抵华以及以林呱为代表的众多默默无闻的中国画家效仿参与,二者相互作用促成了在中国画家眼中包括水粉、油画等在内的新的创作材料与在西洋画家眼中新的异国图景的结盟。用稚嫩的西洋绘画技术描绘东方古国风情,这样一来,一方面解决了中国本地画家图像创作的停滞不前之情景,另一方面满足了西洋对中国图像的渴求,也正是基于这种供求关系,广州外销画逐渐兴盛起来。笼统地讲,广州外销画的出现与兴盛,标志着中国对西洋图像完成了一个进口、消化融合进再出口的过程,从单方面的图像吸收转向到与西洋的互动。
以上述三种艺术现象为典型,明清之际,以“海西法”为代表的各种西洋绘画、制图技法在宫廷内外、民间上下得到了一定的渗透与沉淀,其为日后图学、图绘在中国的复兴提供了绘制技艺上的准备。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方势力以战争为手段的对华入侵,开晚清国门,使得昔日中国在欧洲人心目中的地位不复存在,中国统治者的那种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也已荡然无存。由此,十八世纪所呈现的“中国图像进欧洲”的情景已经逐渐被“西洋图像入中国”的状况所取代。对于这一现象的理解,M·苏立文在《东西方美术交流》中,从美术史的角度给予了一个简单的概括:“十八世纪的中国文人画家对于西方比较注意,对于西方美术多少抱着一种好奇的态度,但他们对于西方文明本身并没有多大兴趣。到了十九世纪,由于中国在西方列强的武力面前一次又一次地遭受侮辱,为了自卫,中国人痛感非得学习西方的技术不可。”所谓“西洋图像在中国(晚清)”,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中国进入到“世界的图像时代”,也正是在这个“学习西方技术”的过程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显现。
“经世致用”是儒学内部的一种思潮,它在遵守儒学根本信条的前提下,致力于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有清一代,经世致用思潮曾两度兴盛。一是清初以顾炎武等人为代表,总结前朝覆灭之教训,反对明末空疏学风。二是在进入十九世纪的晚清,以魏源为代表,主张师夷长技,向西方学习工业技术,提升国防实力。鸦片战争后,内忧外患交织,经世致用便成了统治阶层应对这个困境的基本思路。就一思潮在近代史和思想史上的诸多思辨,此处无需深究。而在此思潮影响下所产生的最为直接、直观的结果,便是国人对西洋机械技术的主动引入与运用。对于这一点,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实用之学的影响下,国人对于图像的重新重视以及机械技术的参与,促使晚清社会逐步迈入了“世界的图像时代”。康有为在日后的《万木草堂藏画目》中所言:“今工商百器皆籍于画,画不改进,工商无可言,此则鄙人藏画、论画之意。”严格说来,康文中所言“画”者,对应工商百器或为牵强,若以“图”称之,兴许更为贴切。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图学、工艺学等研究领域得到了重视与发展,由此,图像在晚清社会变革中所发挥的作用与其带来的影响愈发凸显。
晚清的图绘复兴,离不开机械技术与艺术的结合。正如郑工所描绘的那个从属于晚清洋务运动的“新工艺运动”那样,它是中国社会第一次工业化浪潮的产物,这场“新工艺运动”,工大于艺,工兼于艺,注重科学技术却也不排除手工艺。从系统化的行军地图、军工器械图纸测绘,到兴办学堂图画教育、运用插图教材;从官方举办、参加国内外博览会、美术展览,到民间各类画报、画刊、画谱的传播,虽然各类活动工、艺各有偏重,但其却共同绘制了一幅“世界图像时代”下图像在晚清复兴的图景,共同促成了中国古有“左图右史”传统的回归。
参考文献:
[1][德]马丁·海德格尔著.海德格尔选集(下)[M].孙周兴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12).
[2][德]鲁道夫·G.瓦格纳.进入全球想象图景:上海的<点石斋画报>[J],徐百柯译.中国学术,2001,(04).
[3]郑樵.通志十二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5.
[4]钱穆.中国史学名著[M].上海:三联书店,2000,(09).
[5][英]M·苏立文著.东西方美术交流[M].陈瑞林译.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
[6]郑工.演进与运动:中国美术的现代化(1875-1976)[M],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2,(05).
作者简介:
刘杨,海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美术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