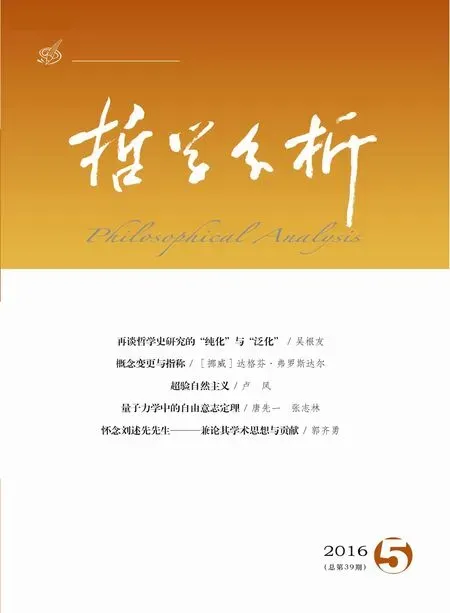重估“柏拉图未成文学说”的范式意义——评点先刚博士的《柏拉图的本原学说》
李 伟
重估“柏拉图未成文学说”的范式意义——评点先刚博士的《柏拉图的本原学说》
李 伟
在写出以下的评论和拙见之前,得先提及先刚君关于学术创新和批评的一个重要“表态”:
真正的“创新”毋宁在于潜心领会哲学家的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把哲学家的认识消化为自己的认识……当“柏拉图的”认识成为“我的”认识,它就已经是一个“新的”东西……如果有人随意批评柏拉图这里不对那里有错,进而指责我“盲从”柏拉图等等,我想借用西塞罗的一句话答复道:“你们别管我,我宁愿和苏格拉底及柏拉图一起犯错误!”①先刚:《柏拉图的本原学说——基于未成文学说和对话录的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前言”第5—6页。以下凡引此著皆以夹注方式标出页码。这里,且不说先刚君对“创新”的理解精当与否,只就所谓“随意批评柏拉图”言明以下几点。其一,真正严肃的学术讨论,都不是“随意的”,但都是“有意的”;其二,批评的对象可以有两种——柏拉图及柏拉图研究,任何人也没有资格把自己的研究等同于被研究对象,否则就有“随意”和“独断”之嫌。也即是说,先刚君断不能以其“柏拉图研究”来自居“柏拉图”,不能把自己的柏拉图研究等同于柏拉图本身,以为对前者的批评就是对后者的不逊。就此,我也明确一下本文的言说对象:不是柏拉图,而是先刚君的柏拉图研究,具体说就是这本《柏拉图的本原学说——基于未成文学说和对话录的研究》。毫无疑问,这是一本卓越的学术著作,雅需严肃待之。以下拟从学术立场、诠释策略、核心议题和哲学术语诸方面谈些不同的理解。
先说学术立场和诠释策略。先著始终站在“护卫”柏拉图的立场上,尽量让柏拉图自圆其说,如果现存的对话录不敷用,就会以此著重点发挥和深化的“未成文学说”来接济。对柏拉图著作中涉及的一切问题,都尽量予以“同情式”和“圆场式”的读解。这种策略和思路,对研究思想史领域中的经典作家和原典来说,是最最要得之举。那种动不动就以某种官家哲学来对经典作家和作品横加指责和批评的做法,着实令人反感,此乃政治对学术的不法僭越。①这里可能会有人反驳说:你以经典作家和作品为权威,我以某家为准的,不是一样吗?不一样,你的标准只有一家,我这儿是一种姿态和态度,可以是任何一个经典作家或作品。一家独大,是学术进展的大忌。
然而,学术“护卫”也是有限度的。比如在中国古代典籍的诠释中,就存在这样的倾向,叫“增字解经”。即是说,把某段令人费解的材料解释清楚是通过增加额外的材料才获得的,那这种释读就可能是不谛的。现代诠释学意识已明确,一切人文解释,都是视域之融合的结果,今人当下之所有,断不能在解经过程中被排除殆尽,实际上也无法做到想象中的那种净化,诠释总是循环的。只是需要辨明一点,伽达默尔他们并未对“前理解”做出进一步的类型上的区分。其实,所谓“前理解”需要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基础性的、前提性的、常识性的,比如要能认字,要对相应文化有相当之了解,有最起码的思维能力等等;一类是导向性的,先入为主,也就是那种“主题先行”甚至“上纲上线”和“遵命奉迎”的把戏。前者可称作“前见”即“前提性理解”,后者则可名为偏于一角的“偏见”即“强制性理解”。或许可以这样说,伽达默尔他们所强调的“前理解”主要是就“前见”而非“偏见”来立论的,对后者,他们觉得实在不值一驳。然而,即使就第一类“前理解”而言,它是否就一定没有“导向性”,不是我们的“一偏之见”?那又不能一概而论,因为这类基础性的“具有”,其间多少都是有价值判断渗透其中的,绝非纯粹的事实因素,可以把这类理解因素从中分离出来而名之为“融汇性理解”,以与纯粹事实性的“前提性理解”相区别;当然,它和那种铁了心地“拉郎配式”的“强制性理解”还是有根本不同的。对于“前提性理解”我们需要自觉,对于“融汇性理解”必须作“前提性批判”,掘出其中的价值判断,以自觉持论的潜在因素,对于“强制性理解”则必须坚决予以抵制。而且最终,一切经典诠释都必须经得起文本自身和历代接受者的重验。
一如著者自言,此著之最终学术意图是为柏拉图哲学提供一个“整体论述”。但细读来,其重点发挥者,还是图宾根学派的“基本立场”和“基本精神”,即强调“柏拉图口传的未成文学说”和“对话录与未成文学说的结合”(参见“前言”第1页)。更明确地说,此著是以“柏拉图未成文学说”为最终解释依据的,作为标题的“本原学说”即是来自这一“未成文学说”。再进一步说,它所提供的“整体论述”实质上是以“未成文学说”为统率和取舍标准的。一如作者所言:“未成文学说是整个柏拉图哲学的指导纲领和基本架构……它是对话录的根基和前提。”(第127页)取舍标准和整体立场的改变,必然使得整个解释格局发生大震动,使之不可能如著者所言的那样——“重点不在于讨论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的内容”(“前言”第1页)。因此,“未成文学说”无疑是理解此著的钥匙和关键。这一解释柏拉图哲学的致思策略,经图宾根学派几代学人的卓越开拓,已被伽达默尔断定为柏拉图解释中的“显要问题和中心问题”(“附录”第415页)。图宾根学派“未成文学说”即“以存在的最高本原及结构为对象的学说”(第416页)的逻辑前提,则主要建立在柏拉图《斐德若》中对“书写著述”的严厉批判上。这派认为,正是柏拉图严厉的“书写批判”最终导致他不愿或不能在“成文”的对话录中,畅快直接且毫无顾忌地表达和论证自己的全部学说,尤其是柏拉图自认最有心得和独创的那部分理论。故而,对柏拉图哲学整体而言,现有的“对话录”不仅不完整,甚至不是最重要的,也因之并不具有传统赋予的那种绝对权威性。
逻辑地看,柏拉图之不愿“直说”(因而例之成为“对话录”)而只诉诸“口传”之“未成文学说”,若恰能代表其哲学之真谛,根由无非有四:作为“媒介”的书写之先天缺陷,作为“内容”的学说本身之深奥难解,作为“受者”的听众之层次不够——此三者为“客观上不能”——和作为“授者”的柏拉图之对自家学说的珍视护爱——此为“主观上不愿”。图宾根学派释读策略的基本逻辑前提,则主要建立在《斐德若》中对“书写著述”的严厉批判上。也就是说,只有承认这个前提的“无可置疑性”,才能由此推定“柏拉图未成文学说”的优先地位和主导意义。这无疑是一个悖论:图宾根学派立论之基,恰恰是其决意要消除其“权威性”的“成文著述”即“对话录”——这里主要指《斐德若》中对“书写著述”的严厉批判。也就是说,图宾根“未成文学说”之“有效性”的根基即是“成文学说”的“权威性”,否则就得面对这样一个诘问:凭什么单单相信“对话录”中关于“书写批判”这一部分的“根本性”和“权威性”(第42页),而不是像以施莱尔马赫代表的“以对话为权威的柏拉图诠释模式”(第74页)那样照单全收?这就需要对柏拉图现有对话录做出内容上的分判,指出哪些可信,哪些是戏言。因此,“成文学说”恰恰是“未成文学说”得以成立的逻辑前提,推开来就是,图宾根学派不构成对“施莱尔马赫派”的“范式转换”或“革命爆破”(第74页),毋宁说是对后者的延伸和补充。
我这样理解所可能遭受到的最大质疑,无非就是图宾根学派特别看重并被视为重要学术创见的“善即是一,才是存在的最终本原”(第122页),并自豪可凭此颠覆以“理念”为柏拉图哲学核心范畴的传统认识。其实,这一点,也不像图宾根学派们所认为的那样具有“范式转换”的“革命性”。
关于最终本原的问题,如果从希腊哲学的一般特征及柏拉图现有对话录看,世界的最终本原是“一”,根本不是什么听众无以理解且解释起来如何困难的问题。《巴门尼德斯篇》整个对话就是从少年苏格拉底向芝诺请教“一”与“多”的关系引发的,最终是巴门尼德与少年亚里士多德关于“一”与“多”这两个概念的辩证法演练。再一个,就“善一”作为柏拉图哲学最高本原而言,它其实就是“理念”,目前没有任何足够且可信的理由不把“善一”理解成“理念”。这也是柏拉图自己招认的:在《理想国》中,他把“善的理念”亦称作“理念之理念”。这种称法,也完全符合柏拉图的致思模式,就易于接受的角度说,可以这样表达:最具体的现实对象来自其对应的概念(最低层次的理念,基本是“个名”),这些有现实意指对象的理念又来自更高一级的理念(比如共名)……以此类推,这过程结束于作为最高的也是最终的那个理念,其基本特征是“唯一”(“统一性”的最高体现,即后世所谓“绝对者”或“无条件者”),其基本功能是“可生”(同于老子所谓“可为天下母”),至于给这个“唯一”命名为“善”还是其他什么说法,那都无关紧要。它与世界万物之间的根本关系,无非就是古希腊思想家殚精竭虑的“多样性”与“统一性”即“多”与“一”的关系问题罢了。先著就柏拉图把“善一”仍诉说为“理念之理念”(肯定是从极力彰显“图根宾学派”创新性的考虑)曲为辩解道:
尽管就其名称而言还挂着“理念”一词,但严格说来已经不能再被理解为一个理念。因为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理念本身作为统一性原则却还处于多样性的规定之下,这说明在它们之上还存在着更高的乃至最高的统一性原则。(第270页)
只是先著所谓的“严格说来”,一点也不严格:柏拉图何时把理念可能具有的“最高统一性”剥夺了?先著对柏拉图理念的多层次性倒是有明确认知,既然理念是多层次的,那么,这个层次要不要结束于一个最高的范畴?把所有理念最终统一起来的居然不再是理念?我看,柏拉图真正的意思,恰恰是要把作为流变现实背后根据的一切,都名之曰理念,只是层次、地位和功能不同罢了。这样也更能显示柏拉图思考的一致性,也更能标明诸理念不仅具有相应的层次性,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上面这段引文,倒应该这样说:
尽管就其名称而言还挂着“善”一词,但严格说来还是那个“理念”,只不过是最高层次的理念罢了。
这大概就是先著在随后的论述中(比如第361页),也总是说“善的理念”如何如何的潜在根由。
再就作为“内容”的学说之深奥难解来说。先著所概“柏拉图未成文学说的基本内容”包括五个方面:最终本原是善其本质是一(可简称为“善一”)、存在阶次、走向本原和从本原出发的解释路向等(第113—125页)。而就“柏拉图未成文学说”这些具体内涵而言,实在说来,并不比柏拉图在《蒂迈欧篇》等对话录中解释“一”与“不定的二”如何通过“混合”而产生出诸多个别理念和具体事物的部分更神秘、更难以为一般听众所理解,这让我们不得不这样想:柏拉图用这种云里雾里的解释,夹带着缠绕的例证,到底是为了说明自己的哲学呢还是根本就没找到最佳的表达方式呢?如果他柏拉图认为,自己这样的解说都是可以被人们理解的,那么,把世界的本原追溯至“一”和“不定的二”,这有什么难以被理解的呢?除非他根本就不想把这一部分透露予外人,这就是“主观上不愿”。那么,柏拉图为何在主观上不愿传授自家学说的精义呢?看来根由只能是作为“受者”的听众之层次不够——这一点倒是实实在在的。
对柏拉图对话录的解读,最最紧要但又无法确知的问题是,这些对话究竟是“实录”还是“代拟”。如果是前者,上述的推论,尤其是图宾根学派立论之根基,就是坚固的,如若是后者,也就是说,这些对话完全是或者基本是“个人创作”,柏拉图不过是那不出场的“导演”罢了——那就非常糟糕了。因为,显然地,既然是自己导演,就根本不存在什么“听众之层次不够”的问题,如果不够,那也是“导演”的“故意为之”,那他自然就可以设置“高层次的听众”,否则,他或者故弄玄虚,或者无法表达自己,或者不想以之示人进而流布后世,这些都不太可能。更糟糕的是,从目前对话录的实情看,其间诸多人物决不能与历史上真正存在过的那些对应者等同。连图宾根学派的主要代表斯勒扎克(Thomas A.Szlezák)也极力主张其“戏剧性”①斯勒扎克:《读柏拉图》,程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110页。。在这一点上,先著亦承认这些参与对话的角色及其所传达的思想“究竟是否符合客观事实,还是仅仅是柏拉图的杜撰,这是不易断定的”(第147页)②先著在对柏拉图“对话录”究竟是“实录”还是“杜撰”这一点上是非常游移的,他之认同于哪一方,则要看对其先天看法是否有利而定。比如第192—193页对希腊智者的评论,就主要依据“对话录”中以他们的名义出现的那些人的言行来评定,就极不合适。既然作者无法断定“对话录”是“事实”还是“杜撰”,那怎么能不加证明地以“如实”作前提来推证呢?;并认为,“对于那些至关重要的学说,柏拉图并不是客观上‘不能’,而只是主观上‘不愿’将其托付给文字。”(第88页)这同样必须进一步追问,柏拉图为何“主观上不愿”?如果真的“不愿”,那又为何要在学院中讲给自己的学生听?
有一个证据可以明确回答这个疑问,这个证据给出的结论则是:柏拉图决没有“主观上不愿”的意思。请看先著从其立论之主要文献依据即盖瑟尔所编《柏拉图学说记述》中选录的出自阿里斯托色诺斯的一段文字:
亚里士多德曾经一再说道,那些来听柏拉图的讲课《论善》的人,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情形:在此之前,每个人都以为会听到通常关于人的福祉(比如财富、健康、体能或其他值得惊叹的幸福)的指导,但是,他们听到的却是关于数学,关于数、几何、天文学的讨论,最终竟然是这样一个命题:“善是一。”我觉得,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些完全意想不到的,很奇怪的东西,所以他们中的有些人对这些内容不屑一顾,有些则分开地拒绝它们。(第97页)
请您仔细琢磨其中“那些来听柏拉图的讲课《论善》的人,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情形”这个句子,不是明摆着柏拉图的“讲课”是不择听众,而且似乎还有课前预告之类的情况嘛。“这些来听课的人”,断然不会全是柏拉图的学生,否则,不可能会出现“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这种情形。“完全意想不到”不也说明这些人不可能就是学院的学生嘛。既然有那么多的外来客,那为何还要讲述自己那被图宾根学派指认为与“成文学说”相比更形紧要曾的“未成文学说”呢?因此,这足以说明,柏拉图并非“主观上‘不愿’”。
进一步的问题是,在有关柏拉图“未成文学说”的诸多论争中,最核心且最紧要的一个问题是,这些从别人,不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其他人的著述中,勾稽出来的所谓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与“对话录”的关系若何?逻辑地看,无非四种:两者相合,前有后无,前无后有,相互矛盾。第一种情形相对简单,但又是最基础的,可以作为讨论和裁定分歧的基本依据;第二、三种情形,亦不复杂,以之互补即可,只要它们与第一种情形不相矛盾即可。关键是第四种情形,遇之则以谁为准?还有就是,柏拉图对“书写”的批判,是一贯还是一时的?他是对著述“形式”的不信任,还是对构成著述之“文字”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是绝对的还是有所保留的?
再柏拉图所用术语的角度看。柏拉图对话录中,赋予“本原”以截然不同的诸种术语,先著本应对此类术语作一个系统集中的梳理和总结,尤其是“造物主”与“必然性”、“始终存在着”与“始终流变着”、“一”与“不定的二”、“存在”与“非存在”等范畴。
比如在论证“存在”与“非存在”的关系时,就应当明确,这种关系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是存在本身就包含着非存在,还是存在只有相对于非存在才能被称为存在?就像《斐多篇》(97a-b)里所说“二”是如何形成的一样(是“分的”还是“合的”)。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论证理路。此著对此,未加措意。
柏拉图二元本原之一的“物质”即“不定的二”,这个“无规定性的物质”,这个又被称为“必然性”,同时又被称为“偶然”,到底是一种可以实指的存在呢,还是仅仅是一种纯粹观念上的推定?如果是后者,我们就能理解谢林所谓的“‘不得不存在’这一必然乃是最大的偶然性”的要义,即是说,“不得不存在”是逻辑上推定的,推理到了这个地步所不得不设定为存在的东西,而“偶然性”则是说它的来源是无法再追究的和我们对之所无解的。
因此,就实质意义来看,“图宾根学派”的价值并不是像先著所说的那样巨大,而倒是在于一种“眼光”和“提醒”,让我们注意到柏拉图对话录中已然涉及的某些重要理论命题和思想罢了。
最后,就先著中出现的一些细节问题列举如下:(1)第11章“柏拉图政治哲学中的本原学说:哲学王与民众”在逻辑与全书不洽,或可移到第10章前,或并入前面“本原论”各章节中;而且,此部分的思考,与前相比,亦不够成熟,对柏拉图“哲学王”的理解本人以为不够通透,根源在于,论者缺乏相应的“事实与价值分野”的视野①笔者对此有较为细致的分析,参见《诗中有史不是史,史蕴诗心终非诗——事实与价值视域下文史关系的哲学辨证》,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3年第5期,又载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2014年第1期。。(2)“先著”未对国内柏拉图研究的前辈学者如严群先生相关重要著述作出必要的吸收和借鉴。(3)文中有不少特别“噱头”的语句和表达,读来倍觉多余,且不够尊重对手。(4)康德引文,只字不提今已较为成熟的汉译本,对本民族之哲学研究不够尊重;引第一批评时只注明A版页码,亦不合于国际惯例。(5)先著中多次提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概念外延关系的“种、属、类”等概念(如第121、267页),这里必须解释,尤其是亚氏所言种、属,与今日之含义正相反对。(6)文字上的问题:先著中多次(如第91页)用到“盖言之”,联系其上下文,此“盖”当是“概括”之“概”,而非“大概”之“概”(通“盖”);第120页,段二第二行小括号内的“影响”显系“影像”之误,第304页段二第一行亦是;第150页倒数第一段倒数第三行的“则是全都是”,第一个“是”是衍文;第224页页下第一、二个注所引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不是“V”卷,而是“Δ”。(7)著中诸如“每一个认真读过柏拉图的著作并且尊重柏拉图的人都必定会承认这一点”此类的话,须删去。这根本不是学术用语,也不是有效的论证,而是“诡辩”:如果你说你读了柏拉图,但不承认这一点,那是你不尊重柏拉图;如果你尊重柏拉图,也读过,但也不承认这一点,那是因为你读得不“认真”。一句话,我“总是在理”。
(责任编辑:肖志珂)
李伟,安徽师范大学副教授,台湾东吴大学客座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