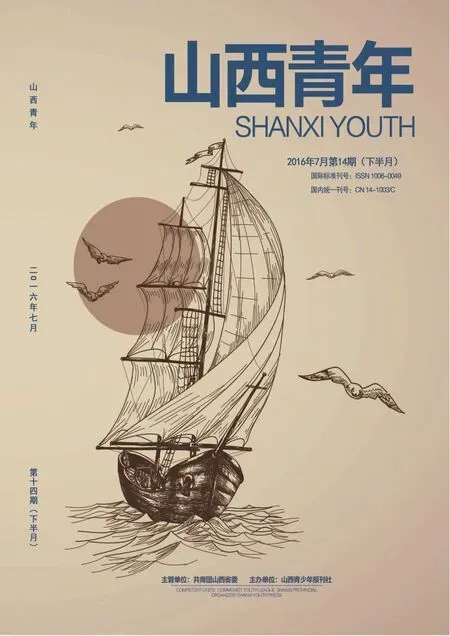没有非遗的非遗传承人
——浅析通海石板沟“高脚狮子”传承、生存现状
和 谞
云南艺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云南 昆明 650011
没有非遗的非遗传承人
——浅析通海石板沟“高脚狮子”传承、生存现状
和谞*
云南艺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云南昆明650011
摘要:高跷历史久远,源于古代百戏中的一种技术表演,北魏时即有踩高跷的石刻画像。全国各地都有高跷盛行,在盛行的地方大多是用于节庆表演。高跷是一种著名的民俗活动,具有传统戏曲的成分与杂技类的竞技项目元素,并且早在2006年被定为国家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高跷的兴起与界定大多属于中国北方地区,在中国的南方地区少有听过“高跷”这一技艺。但在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的石板沟“高脚狮子”却在当地小有名气,这一技艺主要以“高、险、奇”著名,成为了一项民间极具丰富观赏性的表演。但在受到当地人追捧的同时,其生存现状颇感危机。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去发掘“高脚狮子”在当地的生存现状、传承现状。
关键词:高跷;高脚狮子;高跷舞龙;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生存现状
一、绪论
高跷这一民族民间技艺距今已有600年的历史,根据历史记载,高跷源于古代百戏中的一种技术表演,在北魏时即有踩高跷的石刻画像。令人疑惑的是,高跷这一门技艺发源和发展不是从云南开始的,但是,在云南的通海地区它得以完整的保存并且传承至今是值得探索和不可忽视的。据当地地方志《大营村志》记载:“四街镇石板沟,其名有记载始于明代,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因屯军营地而得名。清康熙年间,原驻军已经民化。”但是一些风俗、文化、技艺随祖辈一起迁移至此并且一直流传,其中就包含高跷。既然高跷文化并不是始于通海,但是在这个多方文化并存的地域得到较好的保存,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那么,用文化人类学的说法可以理解为:驻军的到达和在民化的过程中,是从一个不完整的社会向一个完整社会的转变。这个完整的社会就是“当地人”延续之前一些熟悉的传统与文化,并且加之不断的发展和改造,最后形成当地特有的文化现象,那么高跷的延续也许就是这个原因。现目前,我们所熟知的高跷发展,分为:高跷走兽,海城高跷,辽西高跷,苦水高高跷四个。而这一盘踞在云南的独特高跷技艺——“高脚狮子”,以其“高、险、奇”的技术和观赏特点孤独的存在着,保护也成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二、“高脚狮子”的独特性
在通海县石板沟的“高脚狮子”,或许也是传统高跷技艺的一个分支。高跷表演在各地都大同小异,一般以舞队的形式出现,舞队人数十多人至数十人不等,大部分舞者都是扮演某个古代神话或历史故事中的角色形象,服饰多模仿戏曲行头。表演形式分为“踩街”和“撂场”两种。“高脚狮子”不外乎也有着以上的形式,只是在技术难度上又更上了一个台阶。这一技艺背后到底蕴藏着多少秘密,我们一起探究。
(一)“高脚狮子”的“高、险、奇”
高跷作为国内一项传统表演技艺,正是因为高而闻名的,国内普通高跷基本上都是从30厘米开始,而石板沟的高跷基本上从2.4米开始,比起其他地方的高跷,更具危险性与观赏性。石板沟的高跷也分为“文跷”和“武跷”。文跷重扭踩和情节表演;武跷重炫技功夫。它不只注重某一方面,而是做到了两者兼顾。
石板沟高跷的表演节目有《送京娘》、《桑园会》、《八仙过海》、《山伯访友》、《抛球招亲》等历史典故。在这些传统表演节目中,当地表演队又自己加入了独具特色的表演——高跷狮子舞。该表演分为“地狮子”和“高跷狮子”两种方式,“地狮子”由四人在地上表演舞狮,一人踩着高跷拿着“文刷”进行表演;“高跷狮子”顾名思义就是所有的表演都在高跷基础上加以完成。平均每副高跷高度在两米左右,并且需要在高跷上面完成高难度的动作,为了不让过高的高度影响表演者,所以在整个表演的过程中表演者都需要不停的移动高跷,靠小幅度的左右移动高跷达到保持平衡的目的,危险程度可见一斑,但同时也增加了该表演的可观赏性,这也体现出了“高”这一特点。
“险”,体现在表演者方面,除了传承人沈大爷外,表演者大多都是六岁到十岁的孩子们,这里面也包括了沈大爷的孙子。这项民间技艺在艺术与观赏性并存的前提下,也伴随着较高的危险性,孩子们的演出在很大程度上和当地的文化受众有关系。换句话说,石板沟的高跷技艺和其他地方的相比除了技艺上的不同,在受众和普及上也有偏差。所谓“受众”,即当地村民。同样是在村里的节庆上演出,不同在于其相对封闭,不会与外界产生交集,有点自产自销的意思,自我娱乐也没什么不好。所谓“普及”,也就是此次田野的重点,发现高跷技艺从孩子抓起,开设学堂进行教授,并且老师会给学生一点象征性的经济补贴,作为招生渠道与维持高跷技艺得以传承的方式。沈大爷告诉我:“虽然有些孩子打心底里喜欢这项技艺,但由于家长担心孩子的安全情况,直接造成了生源的流动性很大。”所以我认为,那点经济的补贴也许也是一种心理安慰和坚持下去的一点动力。
最后一点“奇”,这个特点便是集上述二者为一体,演变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地方独特技艺。孩子们踩着高跷,表演着一系列演出节目,据老人说,每个节目的时长都在6至8分钟左右,可以想见孩子们在其中投入的汗水和付出。
表演使用的高跷从2.4米到4.2米高度不等;而踩高跷最小的小孩只有三岁;在如此高的高跷上面还要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动作,真是令人难以想象,不由得会为表演者捏一把汗,所以通海的高跷舞狮因此闻名!
(二)“高跷狮子”的地域性
这个民间技艺属于通海县四街镇石板沟村,沈大爷他虽然从小就开始研习这门技艺,但是从21岁才开始正式踩高跷,一直坚持至今;并且沈大爷的儿子也从小跟随沈大爷学习踩高跷;现在到了沈大爷的孙子辈,小孙子从会走路开始就练习踩高跷,如今六岁的他已经可以踩着两米的高跷自如行走,也可以算得上是最小的非遗传承人。
石板沟高跷,有说法是只传本族人不传外村人,在当地有许多慕名而来的人找到沈大爷想学习高跷,都被拒绝了。沈大爷严格遵守祖上传下来的规矩,至多会教授自己本村的青年或孩子进行高跷技艺研习。虽然说这样不利于这一民间技艺的普及和传承,但是沈大爷这样做也是因为这一项百年技艺的传承从古至今均遵守这样的规则。作为一项口传心授的民间技艺,有这样的地域性也是理所应当的,或许在百年之前,祖先正是通过这样的一技之长维持自己家族至今,在古人看来这样的“独门绝活”是绝对不能被别人“偷”去的,所以制定这样的规矩也是情有可原,那么这样封闭的地域性也不能说是民间技艺的弊端。封闭,这一漏洞可能会造成传承的阻碍,并且现代文明发展迅速,对于相对“落后”的当地社会文化来说,势必会造成不小的冲击,那么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当地年轻人,对于这样的民间文化也会有一些抵触的情绪。所以,现代社会已经趋于完全信息化、科技化时代,在变革发展的道路上,总是会有某些历史和所谓“落后”的事物惨遭遗弃。在进化的过程中也不能忘记初级发展阶段,那么唤起世人的重视迫在眉睫。高产值地区经济高速发展,相应配套设施较为完善,在相对质朴的地区,他们的发展和生活可能就不这么引人注意。
这样地域性,作为传承技艺方面,保护了当地文化的完整性不被侵蚀;作为有效的传承发展当地民间传统技艺却造成不必要的沟壑。如何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成了一个值得思考并解决的问题。
三、“高跷狮子”传承现状分析
(一)“高跷狮子”生存现状
沈大爷早在2007年6月9日被任命为云南省非遗传承人,虽然在此之前他就已经对传承发展做过很多努力,但是在被任命之后并没有再更多的改善,反而增加了更多的责任。沈大爷带我看了一些村里空旷的场地,说平常孩子们就是在这些地方训练,没有特定的场地,并且也没有固定的时间。沈大爷还得变着法的吸引孩子们来学习。在这近20年的传承时间里,沈大爷和他的学生们渐渐形成演出队的形式,在当地也小有了名气。有时会有其他村的人来邀请他们去演出,也会给予一些劳务补贴,沈大爷更是分文不取的。基于这是一项口传的民族民间技艺,没有书本式的教学又无形的增加了传承难度。在最近两年的时间里,这一民间技艺慢慢得到了认可和重视,纵使学员坚持学习的情况仍不理想、学员人数也不稳定,但是这一门传统技艺也在磕磕绊绊中达到了不错的水平,逐渐被人们所认知。也正是因为这样,越来越多的邻村会邀请沈大爷和他的“高跷队”过去表演。
我也通过沈大爷老伴口中得知,在这几十年坚持的过程中,全部费用都是由沈大爷一人垫付。在所有的道具中,除了祖上传下来有着百年历史的“狮头”和“文刷”以外,在投入使用的四十多副高跷,都是沈大爷自己一个人制作,平均一副高跷的制作时间少则三五天、多则一个月。从选材到打磨、到上漆工序繁复,高跷分为立板和踏板两部分,其中踏板部分由于坚韧度的需要,选材必须是梨木,榫口的配对、承重量的计算也是沈大爷一人亲力亲为。
由于地域性的原因,如何吸引孩子们的加入也成了一个难题。沈大爷还肯定的告诉我,这项技艺从祖辈就开始一代代往下流传,所定下的规矩第一就是不外传的,学习的都是本村的年轻人或者小孩,同时作为他自己,也希望在不破坏祖辈规矩同时又能发扬高跷技艺。但是两者本就是相悖的,作为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他依然在寻找着一条两全其美的出路。
(二)与滇剧作对比,分析传承难的原因
滇剧的发展,已经历了清代、辛亥革命时期、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几个阶段。清代,是滇剧孕育、形成发展到逐步兴盛的时期,继前边提到的3个滇剧班子之后,又出现了泰洪、庆寿、福升等戏班,曲靖地区也出现了玉林班。到了光绪年间,滇剧已经比较兴盛。滇剧具有很高的艺术形态,讲究“四功五法、唱念坐打”,具有“雅俗共赏、古今同趣”的乐趣。
艺术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有人来“传宗接代”,作为这一个媒介自然而然的产生了艺术家这一个行当。在学习艺术的道路上有无数的辅助,影像资料也好书本理论也好,都能提供给无数艺术家们从模仿到创作这个过程的最大化帮助。当被问到什么是艺术的时候,艺术家们都会骄傲的说的头头是道,那么什么又是艺术家呢?说的直白些,就是艺术传承的载体。同样的,在民族民间艺术上,同样的需要传承发展延续,那么传承人也作为民族民间艺术传承的载体进行着自己的小范围活动。
那么就传承人这点来说,滇剧与石板沟高跷都有这个载体。作为传承人,他们也都确实做到了“传承”这一重点。民族文化民族艺术这一艺术形式,从发展开始就保持着一种原生态的延续方式,一辈一辈的口述、教授、模仿,一点点的继承下来保持着原有的姿态。每一个传承人不会是生下来就有这样的技能,或许有天赋但是也需要后天的培养。大多民族民间传承人,他们都已年过古稀但却保持着特有的生活习惯,除了从小养成的习俗习惯,不同领域的精湛技艺就是他们为之捍卫与自豪的东西。
作为地方戏来说,不同剧种都有着不同的风格,剧种同样也存在着地域差异。云南民族民间戏剧是多元化结合的地方戏剧,每种不同的剧种或许只适用于当地的人民,辅助当地人民劳动,让当地人民娱乐,提供给当地人民某种意义上的一种精神寄托。可以把这一切一切戏曲也好戏剧也好,比作艺术品,从其传承或是引进再到之后的发展演变,都是一种艺术品在彼此交通、互渗、共融的关系里彼此相互纠缠,处于不断被再生产再创造的过程。滇剧在打破规则从而融入大群体的路上,成为了一个成功的例子;一览无余展现在众人面前,传承人的教导不再局限于本家,跟随现代文化进行创新。
所以这样看来,高跷也是一样,需要一种途径进行共融,过于封闭的本体、难打破的规则、现代文化的冲击,这些种种都是阻碍石板沟高跷能够有效传承的路障。如何在熊掌和鱼之间尽量做到兼得,需要再加以讨论。
四、传承道路上的创新
(一)高跷舞龙
石板沟高跷在传承上,做出重要的决定——创新。沈大爷在原有的“高跷舞狮”的基础上进行改变创新,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新技艺“高跷舞龙”。这一想法是在沈大爷被评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之后萌发的,当他被评为省级非遗传承人之后,就想着如何为高跷技艺的保护传承做出更好的贡献。虽然每年省里会给非遗传承人3000块的奖励,但是这点钱对于做道具所需要的支出却远远不够。老艺人又自掏腰包,补上那一块资金的空缺,舞龙表演的道具才一点一点慢慢积累起来。
“龙身”长度十八米,同时需要九个人一起舞动才能完成,再加上一个手持“龙宝”戏龙的人,一共十人组成高跷舞龙队。由于舞龙道具过重,需要青年人来完成,所以沈大爷找了九个青年悉心教导。正当舞龙有一些起色时,其中一名队员发生了意外事件:在舞龙过程中用力过猛,导致颈椎半脱位。这样的意外,让本就不被大家看好的创新又蒙上了一层阴影,迫于其危险性队员们纷纷退出,使得“高跷舞龙”一度难以进行。直至最后,沈大爷做出一个大胆的改变,让孩子们来学习高跷舞龙。
舞龙的重量加上高跷的难度,孩子们不得不从“地上”开始学习。沈大爷用稻草扎一个十八米长的“草龙”,让孩子们先从简单的学起,再上到高跷上练习舞“草龙”,最后换成真的十八米长的龙进行表演。由于“龙头”重量过重,已经年到古稀的沈大爷自己担起这个重任,踩在四米的高跷上带领孩子们一起表演。通过两年的时间,沈大爷创新的“高跷舞龙”这一技艺也被人们渐渐认可,但其中的艰苦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二)传习馆建立在望
通过第三次的田野,也从沈大爷口中得知,2017年将会在通海县四街镇石板沟村为“高跷狮子”建立传习馆。在这个地方设立传习馆,能更好的保护和传承高跷这一文化技艺,这就类似于中国人类学之父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同时也更像是一个硬性的文化自觉。
在以前写过的论述中也提到了“文化自觉”这一概念,我觉得这一点是不得不提的,打个最简单的比方:沈大爷通过对儿子的教导,再到对孙子的培养,整个过程就可以说是文化自觉,并且是一个自发的由内而外的行动。暂且抛开古板与封闭不谈,这样的传承和对本村当地的培养,就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换言之,就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文化自觉的过程很漫长,需要坚持,在认识自己文化的基础上,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种文化都能各抒所长、共同发展的共处原则。石板沟当地的文化自觉,可以理解为现代文化与传统高跷技艺传承文化的相融合,在认识自己本土高跷文化的基础上,接受现代文化的冲击并且将二者融合,在这个融合的过程中,其载体和纽带就是高跷文化技艺传习馆。
通过传习馆教育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让文化传习者更好的传承自己的历史,同时也要让他们对自己民族文化未来发展得到理性的继承和合理的创新。在这个文化教育传承的具体实施过程中,让他们耳濡目染、感同身受。通过高跷文化技艺传习馆,让进入传习馆学习的当地人们,能够积极树立起应有的文化自信心是很有必要的。所以,通过传习馆进行教育,其目的是实施对文化的保护,追求的是对文化多样性的诉求。如果能够成立高跷文化技艺传习馆,我们就可以积极投身到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工作中去。同时传习馆也为年轻一代搭建言传身教的教育场所,更为文化保护者和传承人提供真实的、能够切身体会的、并且近在眼前的民族民俗文化和传统技艺的平台。
成立高跷的传习馆,也可以说是从侧面进行了文化技艺传承的创新,进行了一种辅助作用的创新。
五、从文化多样性保护的角度看“石板沟高跷”的当代价值
社会的进步和保护的必然性都在齐头并进,就石板沟高跷来说,尚未走到失传这一步,但是没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或说是受众群也渐渐老去,被外来文化所入侵失去了不可撼动的地位,走到那一步也只是时间问题。所以现在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如何与时间赛跑,争取时间在毁灭之前做好抢救措施。
有报道说,云南新平县一个数百年历史的花腰傣村寨,在现代文化和浪潮的冲击下当地文化已经濒危。古老的住宅渐渐被现代化房屋取代,服饰也渐渐被遗忘,更多的年轻人觉得这样的服饰“土气”,这样的服饰不符合他们的气质穿着会“丢脸”,开始听流行音乐唱外国歌曲,不是说崇洋媚外也不是不能这样做,只是年轻人们却因为这样渐渐放弃了本民族的语言。研究者们说过,一个民族的灭亡就是从语言的消失开始。从一个小乡村开始,可以深发到整个中国,对于我们自己国家的文化,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积极的去思考如何改变这一窘状。
上述例子只在于说明保护的重要性与保护不得盲目这一想法,同样的,石板沟的“高跷狮子”是当地文化的瑰宝,沈大爷一家把这一技艺视作文化的传承。这一技艺的传承从开始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保护这一技艺不说是造福于沈大爷一家,可以说是把这一段600多年的历史保护下来,云南本是一个流放官员民族聚居的地方,这段历史或许能从“高跷”中得到诠释。
保护是势在必行并且时间紧迫,但是在保护的过程中我们不能盲目,不能以保护的名号泛滥我们的民族民间艺术,虽然针对中国这样的媒体格局不可避免的会遭受到这样那样的宣传导向,但是作为有心保护的一份子的我们,不怕从头来也不怕一步步来,我们可以从传播开始,从分享开始,让更多的人了解民族民间艺术,但是不让其泛滥,画好这个圈。抢救也好,保护传承也罢,不是盲目的说出来就去做的事情,我们一步步做,把保护也作为一种传承,只要有人在就能不停的保护着我们的艺术成果,就能不停的传承下去。
六、总结
在整个田野的过程中,我还发现了一项有趣的事情。沈大爷作为非遗传承人,已经当了8个年头,却不曾知道“高跷狮子”是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在田野过程中没有看到任何挂牌形式的证明。查阅资料,只在报纸上的一篇报道中看到,说“高跷舞狮”入选了市级的非遗保护名录。那么老艺人在这样的市级保护项目里如何当上了省级的非遗传承人?还是说市级与省级的区分只是三星和五星的区别,并没有管辖的关系?这是我这次田野中最为困扰的问题,也是在查阅相关资料尚未得到证实的事情。
针对这样的问题,我也不敢妄自揣测,只能寄希望于上天,能给这位古稀老人以慰藉,也能真正在2017年正式成立传习馆,为这一民间技艺锦上添花。无论是我,还是沈大爷,都不希望让这一技艺砸在自己手中,更不希望成为一个没有非遗的非遗传承人。
[参考文献]
[1]石板沟村委会.大营村志[Z].玉溪,2006.
[2]百度百科.高跷[DB/OL].http://baike.baidu.com/link?url=aXZH-VuvcV2r9l7S0104HFo7bU6wvPpaH7AXQWtxg8btnwOU1ojc2oatInYU9iaQ9FsTUChoy3HnHNSQDoVlfq.
[3]百度百科.滇剧[DB/OL].http://baike.baidu.com/view/379973.htm.
[4]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和谞(1992-),男,纳西族,云南丽江人,云南艺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2014级研究生,研究方向:少数民族艺术。
中图分类号:K8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049-(2016)14-00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