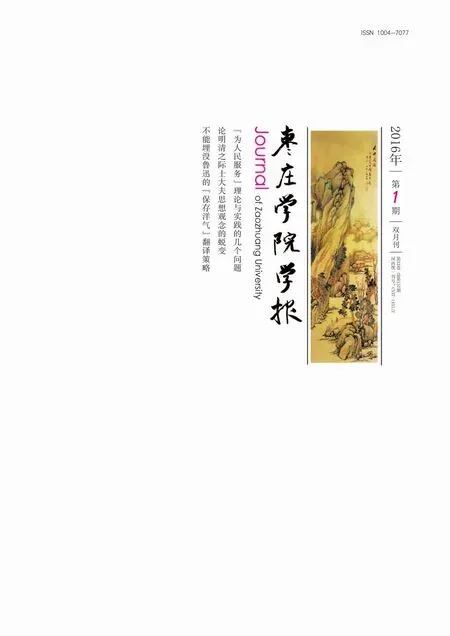论明清之际士大夫思想观念的蜕变
王记录
(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新乡 453007)
论明清之际士大夫思想观念的蜕变
王记录
(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新乡453007)
[摘要]明清易代的外部刺激和学术发展的内在因由,使传统士大夫的思想观念在明清之际发生了一系列蜕变,出现了新的思想因素。就“明道救世”思想而言,明清之际的学者更重视把学术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关注社会风习,并突破传统政治哲学的樊篱,提出了许多具有近代意义的政治观念。就气节观而言,人们对传统的节义思想进行了重新反思和辨析,把气节与忠义看作是“天地之元气”,民族之精神,不再执着于以死殉道的理念,而是把遗民精神当作传承文化的手段。明清之际对专制独裁的批判引人瞩目,君主被斥为“民贼”,尊君观念受到挑战,社会平等意识增强。在义利观上,人们从自然人性论出发,否定了义利对立的传统观念,提出了义利统一的思想,肯定个人私利的合理性,并把“利”提高到富民、救民的高度来认识。
[关键词]明清之际;士大夫;明道救世;气节观;启蒙意识;义利观
在中国思想史上,“明清之际”一直是特别引人关注的历史时段,易代改姓之王朝更迭所带来的思想的变化也一直是后世学者考察的重点,论著迭出,精义纷呈。然而,由于每个人解读历史的视角不同,人们对明清之际思想变化的认识也就有极大不同,再加上明清之际历史的曲折及思想的复杂,愈加使得这一课题具有了反复诠释的价值。本文即从四个方面对明清之际士大夫思想的变化提出看法,探讨这种变化的新特点。
一、学术与社会:“明道救世”思想的新变化
明清更迭,学术研究的气象发生极大变化,经世实学思潮涌动,人们猛烈抨击“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的恶劣学风[1](P627~628),主张治学要能“匡扶社稷”[2](P115~124),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呼号[3](P470~472)。易代改姓的痛楚使清初经世实学陡增一层国破家亡之恨,一大批士人,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费密、陈确、唐甄、傅山、李颙、颜元、李塨等,在无奈与痛楚中反思政治得失,推原学术精神,批判了理学空谈性命,脱离实际的空疏学风,重新阐释儒学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和学风,形成了以“明道救世”为核心的思想趋向,其范围涉及现实社会的方方面面,富有时代内涵。
首先,在学理上,强调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密切结合,注重学术研究的社会效用。明清之际,“明道救世”作为学者治学的最高追求,蕴含着一系列新的观念。如顾炎武认为治学就是求治道,他始终不渝地提倡要为自身发展和天下兴亡而读书,“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4](P41)。他批判理学末流“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的浮华学风,指出学界弊端就在于从不探究经史之学的深意,更不关心国计民生,只会空谈误国。在顾炎武眼里,做学问就是要“探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号召学者把学术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联系起来,极力扭转明末“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的腐朽学风[4](P40),他认为做学问就是“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4](P139)。他关注“民生之利害”,撰写《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等,“旁推互证,务质之今日所可行,而不为泥古之空言”[5](P227)。除顾炎武外,傅山、朱之瑜、颜元、李颙等都提倡学术研究要有社会效用,赞赏宋代陈亮、叶适等人的功利主义。如朱之瑜主张治学的重心应放在“经邦弘化,康济艰难”上[6](P194),认为“为学当见其大,实实有裨于君民,恐不当如经生寻章摘句也”[6](P193)。李颙也有同样的看法,认为“道不虚谈,学贵实效,学而不足以开物成务,康济时艰,真拥衾之妇女耳,亦可羞已”[7](P54)。
考察中国古代学术史,并不存在纯粹为学术而学术的现象,差别只在于是内省还是外修而已。但明清之际的学者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现实问题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改变学风走向,这在中国历史上还属首次。
其次,在政治观念上,传统的政治哲学被突破,“明道救世”被赋予新的内容。明清之际的社会变革使当时的人们不断思考政治问题,并突破传统政治哲学的樊篱,提出了诸多蕴含近代意义的政治观念。在君权和民众问题上,王夫之、黄宗羲等人强调民众利益高于君权、高于一家一姓之利益。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提出“一姓之兴亡,私也;生民之生死,公也”。认为国家治理的最高原则是维护民众之“生死”,而不是维护皇权。黄宗羲在论述历史变革时指出,“所有的变革都必须围绕万民的利益进行,都必须有利于民生,一切均要从民众之需要出发”[8]。黄宗羲在自己的著作里无数次地表达了这样的言论,诸如“志仁者从民生起见”[9](P146),“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等[9](P5)。从民众利益出发,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严厉批判专制君主乃“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的独夫。
明清之际,人们的个人权利意识明显增强,有人甚至将个人权益看作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在一些思想家眼里,作为个人权利的自私和自利被看作是人的天性,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云:“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人各自利。”既然利己是人类的天性,那么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私有财产权利亦理应得到尊重。与此相关,人们开始提出经济自由权利和言论自由权利。
明清之际的人们还对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依靠道德纽带来维系社会统治的人治现象进行反思,转而从体制上探讨制度建设的路径。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就提出自己的政治蓝图:在体制上,君臣要平等,共同来理事,以学校作为议论机关,监督君主的行为。在法律上,主张法治重于人治,要求“立天下大法”,“废一家之法”。在经济上,提出恢复井田制,抑制土地兼并。在文化上,兴办教育,提倡绝学等。
第三,在社会风气上,提倡正人心、厚风俗。明清之际,“明道救世”思想的一大特色是关注社会风俗,顾炎武的言论最具代表性。顾氏认为:“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4](P93)也就是说,人心风俗的好坏,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的治乱兴衰。欲“明道救世”,必须移风易俗。
在专制社会中,君王的一切行为都会影响到社会风气的变化。由此,顾炎武认为朝廷要带头行教化,由朝廷影响士人,由士人影响社会,所谓:“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3](P482)“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3](P482)。他甚至认为可以从社会风气的好坏来评价君主的功过,“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3](P468)。顾炎武还把“有廉耻”看作是存风俗的重要标准。他引《管子》云,“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赞同欧阳修的评论:“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3](P481~482)顾炎武生当明清易代之际,面对王朝更替,很多明人选择了降清,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现实使顾炎武益发觉得“廉耻”的重要,所以他一直高举孔子的“行已有耻”,作为匡世救俗的一面旗帜。
顾炎武不仅从政治角度论述了整顿“人心风俗”的重要性,而且还从经济角度分析了造成“人心风俗”优劣的根本原因。他继承《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思想,认为要使风俗变好,必须让百姓有安居乐业的物质条件,“今将静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制民之产,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后教化可行,风俗可善乎!”[3](P446)“非任土以成赋,重穑以帅民,而欲望教化之行,风俗之美,无是理矣。”[3](P398)顾炎武把“正人心厚风俗”的政治道德观与“甘其食美其服”的经济观联系在一起,颇具时代特征。
二、“忠义”与“天地之元气”:传统气节观的新内容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尚气节和信念的民族,越是沧海横流、世道变迁、王朝更替、异族入侵,人们越是砥砺名节,养天地之正气,成人生之高节。同时,在注重春秋大义、君臣名分的古代社会,气节又与忠孝联系在一起,气节往往表现为对国家、民族甚至是君主的忠诚。明清之际,世事巨变,传统士大夫中的气节观与忠义观再度彰显,并出现了一些新的思想因素。
第一,把气节与忠义看作是“天地之元气”,民族之精神。黄宗羲曾极力在自己的著述中表彰明末清初的气节与忠烈,并赋予了新的内涵。他指出,气节与忠烈是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的一种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而不是臣子对君主的“忠”。他对“臣道”有自己的看法,认为“杀其身以事其君”,并非“臣道”,“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在他看来,“臣道”乃是为天下、为万民之道,而非为一家一姓之君主之道,“为臣者轻视斯民之水火,即能辅君而兴,从君而亡,其于臣道固未尝不背也”[9](P4)。这可说是中国两千年封建政治观念的一大奇变。由此,黄宗羲所讲的“忠烈”、“忠义”,也就超越了封建伦理道德的范围。
明清易代,万民涂炭,忠义之士奋力抗清,这种抗争实际上已超脱于一家一姓易姓改号之上,而变成为民族利益、万众利益而斗争的一种凛然正气了。黄宗羲说:“盖忠义者,天地之元气,当无事之日,则韬为道术,发为事功,漠然不可见。及事变之来,则郁勃迫隘,流动而四出。贤士大夫敥起收之,甚之为碧血穷燐,次之为土室牛车,皆此气之所凭依也。”[1](P505~506)“忠义”乃“天地之元气”,和平年代,“韬为道术,发为事功”,历史巨变时期,或表现为忠烈,或表现为气节。这种“元气”实际上就是民族精神之正气。他在《苍水张公墓志铭》中还说:“语曰:‘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所谓慷慨、从容者,非以一身较迟速也。扶危定倾之心,吾身一日可以未死,吾力一丝有所未尽,不容但已。古今成败利钝有尽,而此不容已者,长留于天地之间。”事业有成败,抗争有胜负,这些都会成为过去,但延绵不断、长留天地之间的却是通过这种抗争所体现的“元气”——民族精神。正是这种民族精神,才使得中华民族敢于同任何邪恶势力做斗争,从而铸就了中华民族的脊梁和灵魂。
第二,对传统的气节观进行了重新反思和辨析,提出了新的认识。明清易代之际,士大夫面临生与死的抉择,其抉择的结果无非是苟活与殉道两种。生死是考验人们气节的重要手段,在异族入侵面前,是以身殉道,还是苟且偷生,就成了当时人们的一项艰难选择。传统的气节观,提倡杀身成仁,赞赏“见危临难,大节所在,惟有一死”[10](P1494)。但是,明清之际,除了舍生取义而死的“忠烈”外,还有很多苟活的“遗民”,这些存活下来的遗民,对气节问题进行了讨论,出现了较为理性的看法。他们不再执着以死殉道的理念,而是把遗民精神当作传承文化的手段,他们虽没有“死道”,但决不和清廷合作,而能保持气节,以便使自己有充足的时间从事学术研究,保持华夏文化不因异族的入侵而湮没。张煌言在《贻赵廷臣书》中云:“义所当死,死贤于生;义所当生,生贤于死。”死与不死,关键要看是不是符合“大义”。明代学者吴廷翰在论及方孝孺之死时,就提出一种中庸的看法,认为士人在面临死节之时,尽管应该成仁,但也不必过分激烈,最好要符合“圣贤中道”。清初学者陈确曾指出,对士大夫的结局,不能只以生死做出判断,因为事情相当复杂,“惟有其不死而不媿者,是以有虽死而犹媿者”,复杂的形势使得人们的选择也变得复杂起来,单纯以传统的死节与否来判断一个人,就会有评价不当之处,由此他提出要注意他们的“心之所欲”[11](P369)。陈确还撰写《死节论》,对“死节”进行了理性反思。在他看来,真正的死节,理应是“不可过,亦不可不及”,是一种“中和之谓和”的精神境界[11](P152~154)。
明清之际,由于思想家们对气节、忠孝问题进行了辨析和反思,其所包含的内容也悄然发生了变化。无论是死或不死,只要践行圣贤之道,他们所担当的都是民族大义,都是人间的浩然正气。
三、“圣君”与“民贼”:从尊君到批判专制独裁
明清之际,思想领域出现一股批判专制集权的思潮,李贽、黄宗羲、唐甄、顾炎武、王夫之、傅山、吕留良等人都在自己的著述中对对专制集权的弊端及危害进行了研究,并对之进行了严厉批判,这些具有启蒙意识的思想成为后世中华民族反对独裁政治的精神来源。
明清之际对专制独裁的批判,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尊君到抑君,甚至指斥君主为“贼”;二是政治伦理关系上宣扬社会平等观念;三是从历史兴亡的角度揭示专制集权的危害,主张变革君主专制制度。
几千年中国专制社会,君主均被视为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明清之际,有识之士努力把君主还原为普通人,甚至直接斥责君主是“独夫”和“贼”,尊君观念被动摇。黄宗羲从历史发展入手,指出专制制度出现以后,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把天下当作自己的私产,胡作非为,剥夺民众利益,“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9](P2~3)。独裁君主与民众对立,专横跋扈,老百姓自然要把君主看作是寇仇和独夫,所谓“今世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9](P3)。唐甄则认为君主和一般人没有两样,“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天子虽尊,亦人也”[12](P67~69),对他们不必有什么畏惧心理。唐甄还进一步揭露了君主的本质,认为帝王是“贼”,是社会治乱的终极根源,“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12](P196),“治乱非他人所能为也,君也”[12](P66),治天下和乱天下的不是别人,正是君主。顾炎武揭露了个人专权对政治的危害,他认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政务繁复,专制君主集一切权力于一身,根本无法完成治理天下的任务,“后世有不善治者出焉,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几之广,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3](P327)。王夫之认为天下是民众之天下,不是君主一人之天下,“天下非一姓之私也”[2](P1107),提出“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13](P519),批判了传统“家天下”的尊君观。
与批判专制集权相呼应,人们还宣扬社会平等的观念。李贽从王侯与庶人的关系出发,说了一番富有哲理的话:“侯王不知致一之道与庶人同等,故不免以贵自高。高者必蹶,下其基也,贵者必蹶,贱其本也。何也?致一之理,庶人非下,侯王非高。在庶人可言贵,在侯王可言贱,特未知之耳。”[15](P17)在李贽看来,王侯之所以“高贵”,是因为有庶人这一社会基础,没有庶人做基础,也就无所谓王侯,庶人才是社会秩序的核心,如此而言,庶人也是高贵的。李贽的话已经蕴含了社会平等的思想因素。与此同时,何心隐也有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视为平等的思想倾向,他说:“人必君,则人也;君必位,则君也;臣民亦君也;君者,均也;君者,群也。”[14](卷2《论中》)和何心隐相比,黄宗羲说得就更加明白,“夫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9](P5),在他看来,君臣关系应当是平等的同事关系。顾炎武则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论述君民平等:“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代耕而赋之禄,故班禄之意,君、卿、大夫、士与庶人在官一也,而非无事之食。故知天子一位之义,则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知禄以代耕之义,则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3](P258)在他看来,君王与其他各级官僚在爵位上虽有差异,但实际上是平等的;帝王没有时间从事农耕,以处理政务作“代耕”,和各级官僚一样靠拿俸禄以生存,一句话,君主、侯王和庶人的地位是持平的,君主不能“肆民上以自尊”和“厚取民以自奉”。这样的言论在等级森严的专制社会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明清之际一批有识之士还将专制集权与王朝盛衰、历史兴亡结合起来,从专制政体本身的弊端来认识王朝的兴亡。如王夫之认为宋之亡于蒙古、明之亡于满清,就在于专制帝王将天下之权收归一己,导致汉民族不能自固其族类。专制帝王把天下看作自己的私产,导致地方政府没有任何实权,加之上上下下互相掣肘,造成“形隔势碍,推委以积其坏”[13](P509),一旦外族入侵,自然土崩瓦解。唐甄也认为,君主集权必然导致王朝治乱完全取决于帝王本身的素质,“治天下者惟君,乱天下者惟君”[12](P66),君主权力的至高无上使人们无法将昏君暗主赶下皇位,只能听其将国家引向灭亡。黄宗羲在总结明亡原因时,深入明代专制制度的深层,认真剖析了明朝的官制、兵制、赋税制和科举制的弊病,指出其对明朝覆亡的影响。
明清之际的有识之士从专制集权分析历史的治乱兴亡,必然地引出了人们改革君主制的设想,于是人们提出“众治”、“分治”的思想,并希望以此来限制君权。黄宗羲认为变革帝王集权的关键是“分治”和“置相”,提高宰相地位,以“相权”来限制“君权”[9](P8~10),并通过学校议政,监督君主言行。顾炎武更是提倡“众治”、反对“独治”的重要人物,他明确反对君主独裁,认为“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3](P222),要求分权,削弱君主的绝对权力。
四、义与利:从“重义轻利”到“义利统一”
义利问题,是道德规范和物质欲望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争论不休、延续两千多年的重要议题。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重义轻利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孔子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6](P39)把义与利当作划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董仲舒则把重义轻利价值观推向极端,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命题[17](P2524)。在此基础上,二程提出“圣人则更不论利害,唯看义当为与不当为”[18](P176),完全以道德来确定人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在中国历史上,重义轻利、存义去利、以义制利的价值观,成为具有主宰性的思想,人们对道德修养的完善超过了对物质利益的追求。
可是,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在明清时期发生了变化,市民阶层的出现,士大夫商人化倾向的凸显,功利论再度兴盛,出现了肯定私利、义利统一的新价值观,与传统的重义轻利的价值观有着极大的不同,明显表现出功利主义特征。
其一,从自然人性论角度出发,指出个人利益的合理性。晚明,自然人性论流行,“人皆有私”、“趋利避害”等这些“吾人秉赋之自然”的言论出现,合乎逻辑地导出了一种旨在肯定现实的人的物质利益追求的新义利观。李贽宣称“私”是人类的天性,“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后治田必力;居家者,私积仓之获而后治家必力;为学者,私进取之获而后举业之治也必力”[19](P626),李贽以直面现实人性的实事求是的理论勇气,揭示了人皆有私心这一为历代圣贤所否认的事实,提出正如耕田者把收获物作为私有才肯尽力劳作一样,一己物质利益之私乃是一切生产活动和其他活动的基本动力。李贽还说:“趋利避害,人之同心,是谓天成,是谓众巧。”[20](P38)认为追求物质利益是人生命活动的本能,是全部道德的基础。李贽还揭示出圣贤之人同样有“势利之心”的事实,指出:“谓圣人不欲富贵,未之有也。”“圣人亦人耳,既不能高飞远举,弃人间世,则自不能不衣不食,绝粒衣草而自逃荒野也。故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15](P358)。圣人亦追求物质利益的事实证明了“人皆有私”这一客观真理的普遍性。从此出发,李贽对董仲舒的“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的非功利主义的义利观进行了批判,认为董仲舒其实并非不讲功利,董仲舒所提出的“灾异谴告”本身就是“趋利避害”的最有力地证明,所谓“正谊”、“明道”,其实都是为了“计功”、“谋利”,亦只有现实的社会功利才是检验“谊”是否“正”,“道”是否“明”的客观标准,“夫欲正谊,是利之也。若不谋利,不正可矣。吾道苟明,则吾之功毕矣。若不计功,道又何时而可明也?今曰圣学无所为,既无所为矣,又何以为圣为乎”[19](P626)。李贽的义利观,以现实的人性和天下人无不追逐私人利益的事实来对抗虚伪的道学说教,明确肯定私人利益,并且初步意识到这种私人利益对于经济发展的动力作用。
清初思想家继承晚明思想传统,继续从自然人性论的角度论述追求私利的合理性。唐甄根据人的自然本性,指出天地间凡有生命的东西,毕生都在追求利益,“万物之生,毕生皆利,没而后已,莫能穷之者”[12](P53)。在他看来,人类的一切活动无一不是为了追求实利,利是人们活动的动力,是生存的根本,上至帝王,下到百姓,都不能不言利。只有满足人们基本的物质利益需求,社会才能“治化”,“衣食足而知廉耻,廉耻生而尚礼义,而治化大行矣”[12](P202)。无视人们基本的物质需求,道德层面的礼义教化就不可能推行。陈确也以自然人性论为基础提出“私”是人类活动的源泉。君子、圣贤都有其私,有私而后知爱其身,而后能齐家、治国、平天下,他说:“君子欲以齐、治、平之道私诸其身,而必不能以不德之身而齐之治之平之也。”圣贤之人所作的惊天之举,“皆从自私一念,而能推而致之以造乎其极者也”[11](P257~258)。可以看出,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在义利问题上超越了传统的道德至上主义,指出追逐个人利益是人类的本性,肯定了为利的合理性,为进一步深入探讨义利关系打下了基础。
其二,从义利统一的角度为传统义利观注入了新内容。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不仅肯定人们“为利”的合理性,而且进一步提出了义利统一的思想,否定了义利对立的传统观念。晚明思想家在义利观上有着诸多义利统一的言论,黄绾在《明道编》中提出“利不可轻”、“义利并重”的理论;吴廷翰在《吉斋漫录》中提出“义利原是一物,更无分别”的看法;焦竑提出“即功利而条理之乃义”的命题,批判了“猥以仁义功利歧为二途”的观念[21](P272);陈第则提出了“义即在利之中,道理即在货财之中”的思想。这些思想都强调义利的统一,它们与当时“工商皆本”的经济思想相呼应,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义利统一的观念被清初士人继承下来,傅山认为“义者,宜也,宜利不宜害。兴利之事,须实有功,不得徒以志为有利于人也”[22](卷35《墨子·大取篇释》)。在他看来,“义”就是“利”,“利”就是“义”,二者并不矛盾,“义”不能空谈,必须能给民众以实际的利益,“兴利”、“事功”乃是最大的“义”。颜元同样把“义”和“利”看成是统一的,鲜明地提出了“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的义利观。在他看来,重义轻利和重利轻义都是不可取的,“盖正谊便谋利,明道便计功,是欲速,是助长;全不谋利计功,是空寂,是腐儒”[23](P670~674)。急功近利式的“正谊便谋利,明道便计功”与“全不谋利计功”都是不可取的,正确的做法就是取合义之利、弃不义之利,“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23](P163)。由此可见,人们注意到民众的物质利益需求,把“小人喻于利”看成是普遍存在于广大民众间的自发人性,满足百姓对“利”的要求就是最大的“义”。总之,重义轻利、重道德轻事功的义利观在思想家们的重新诠释下悄然发生着变化,自此,重视人性,义利统一的义利观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可。
其三,把“利”提高到富民、救民的高度来认识,对急功近利、见利忘义者进行了批判。明清之际的义利观有着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这种功利主义的义利观极为看重社会效果,不再把义利看作是纯粹的道德修养和内圣功夫,而是把“义利”看成是外王事功,看成是富民、救民的手段。王夫之对追求“公利”极为赞扬,他认为大禹治水是为天下百姓求利,其“忘身求利”的行为令人尊敬[24](P43~70)。王安石变法也是为了追求“公利”,“期以利国而居功”,并未“怀私而陷主于淫惑”[25](P205),虽问题较多,但目的是利天下。对于有功于天下,有利于民众的“利”,王夫之认为这是“仁者”的行为,应该肯定,“功于天下,利于民物,亦仁者之所有事”[26](P6)。王夫之赞赏利于天下的“公利”,但对于那些追求私利、见利忘义、因利害义的人,无论是庶民、帝王还是士人,王夫之都表示了极端的鄙夷。他认为君主和臣民都不能唯利是图,如果人人都争一己之私利,必然导致上下离心,君民相仇,“君惟纵欲,则忘其民,民惟趋利,则忘其君。欲不可遏,私利之情不自禁,于是乎君忘其民而草芥之,民忘其君而寇仇之”[2](P977),最终导致天下大乱。一味追求私利必然放弃国家之义和民族大义。可见,王夫之倡导符合民众利益的“公利”,反对一己之私的“私利”。颜元更是把义利问题放在富国强兵、民安物阜的高度来认识,他指出,无论是尧舜的“正德、利用、厚生”三事还是周公的“六德、六行、六艺”三物,其中既有“义”又有“利”,但不管怎样,这些“义”都必须“见之事”、“征诸物”[27](卷下),也就是要落到实处,能够为天下国家所利用。那种只空谈道德,对匡世救民之术一无所知的人,很难成为真正的圣贤。
参考文献
[1]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10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2]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M].长沙:岳麓书社,1994.
[4]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2版.
[5]全祖望,朱铸禹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6]朱之瑜.朱舜水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1991.
[7]李颙.二曲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6.
[8]王记录.黄宗羲的历史哲学[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3,(2).
[9]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1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10]黄宗羲,全祖望.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1]陈确.陈确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2]唐甄.潜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增订第2版.
[13]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2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2.
[14]何心隐.何心隐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5]李贽.李贽文集(第7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6]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7]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8]程颢,程颐.二程集(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9]李贽.李贽文集(第3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0]李贽.李贽文集(第1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1]焦竑.澹园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2]傅山.霜红龛集[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23]颜元.颜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4]王夫之.诗广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4.
[25]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1册)[M].北京:岳麓书社,1992.
[26]王夫之.周易外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7]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A].颜元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7.
[责任编辑:杨全顺]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077(2016)01-0014-07
[作者简介]王记录(1964-),男,河南范县人,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历史文献学和清代学术史研究。
[收稿日期]2015-12-02
——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宋代士大夫群体意识研究》简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