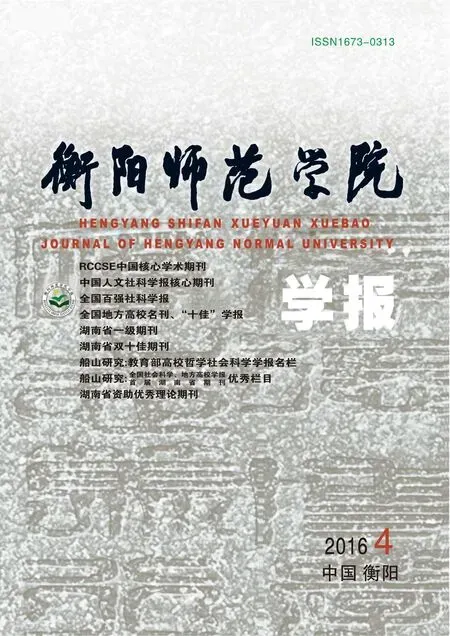(清)杨西明《灾赈全书》所见之荒政思想探析
陈文联,任丽娟
(中南大学 历史文化研究所, 湖南 长沙 410083)
(清)杨西明《灾赈全书》所见之荒政思想探析
陈文联,任丽娟
(中南大学 历史文化研究所, 湖南 长沙410083)
杨西明所著《灾赈全书》是清朝前期一部非常有影响力的荒政著作。其所载救荒措施涉及诸多方面,从灾前防范到灾后救济、从储粮备荒到发展生产,无不体现其积极的备荒救灾思想与现实社会的统一。杨西明荒政思想的形成既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又有复杂的个人因素。关注民生是其荒政思想的主线;具体务实是其荒政思想的原则;明责纠责、因时与地是其荒政思想的基本内涵。《灾赈全书》所体现的荒政思想在丰富清朝荒政理论体系之余,也为后世的备荒救灾活动提供了巨大的现实借鉴价值。
清朝 ;杨西明 ;《灾赈全书》 ;荒政思想
中国有关灾荒的历史记载十分悠久,大自然在造就灾荒的同时也为救灾提供了相应条件,荒政便应时而生。所谓荒政,即政府在灾荒之年为稳定社会、维持统治、保证社会再生产正常进行而施行救济的法令、制度和举措。荒政思想则是古人在与灾害长期斗争的实践中对救灾经验的总结和升华,是指导救荒活动的重要理论武器,因此长期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近年来,荒政思想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充、视角日渐拓展、方法亦日趋多样,对于个别人物荒政思想的研究屡见不鲜、成果颇丰。然而,迄今为止,学界有关杨西明《灾赈全书》的研究仍缺乏系统的考察和深入的分析。有基于此,本文主要对杨西明荒政思想作一浅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杨西明与《灾赈全书》
杨西明,清朝嘉庆、道光年间人,相关史籍上对其生平经历未有介述。他在《灾赈全书初稿自序》中对本人生平也未有提及,只说“余于嘉庆二十二年,蒙本邑宣明府招至幕中,赞襄金谷。”[1](463)可知其于清嘉庆朝丁丑年(1817年)入幕为仕。又据《初稿自序》篇末提及本书“语石生序于奉化官廨”[1](464),可知他为当时宁波府人士,即今浙江省奉化市人。
杨西明一生潜心著述,采古今救荒善策,取政府文件和官员奏折中可行的救荒措施进行类次排纂,编成《灾赈全书》四卷,于道光三年刊行。他在《初稿自序》中对其著书的辛劳和坚持有所表述:“余不敏,日沉闷于新陈例案,旁及故纸堆中,既足以援引,且以备登答也。嗣后随见随录,有加无己,分门别类。”[1](463)夏明方在《救荒活民:清末民初以前中国荒政书考论》中提到:“道咸年间刊行的《灾赈全书》以及《续编》,也是撰者杨西明将其嘉庆二十二年以来入幕期间‘随见随录’的‘新陈例案’,‘分门别类’,纂辑而成,并在其‘诸相知’的催促下,‘刊刻行世’。”[2](33)正因如此,杨西明《灾赈全书》所体现的荒政思想具有一定的独特性、继承性和开创性。
作为中国古代荒政发展的鼎盛时期,有清一代在近三百年的历史中不仅形成了非常完备的荒政制度,而且出现了多部与此相关的著作。这些荒政著作是研究清朝灾民生活和抗灾救荒工作的宝贵资源,在这些著作中,杨西明所著《灾赈全书》更是占有重要地位。作为清朝士大夫集团中的一员,其荒政思想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整个士大夫阶层关于荒政的思考,代表了清朝前期士大夫集团的整体荒政认知水平,独特性中又蕴含着普遍性。因此,对《灾赈全书》中荒政思想的研究也能较好地凸显它在荒政史上的启迪价值和重要地位。
二、《灾赈全书》所见之荒政思想
(一)高效细致的务实思想
自明末以来,伴随着商品经济发展,中国封建社会渐趋没落。一些有识之士日益趋向痛斥宋元理学的空疏无用,提倡留心时务以“经世致用”。杨西明在长期从政的经历中也深刻地认识到救济灾民的重要性,认识到若不有效施行荒政,不仅影响国家赋税收入,还可能危及统治阶级生存。因此,《凡例》中即指出“余浅见寡闻,无从根查,宁遗漏以待异日增补,不敢以似是而非之成案,援以为证。”[3](465)《灾赈全书》各卷内容也皆以国计民生为根本来论述赈荒济困之策。一旦发生灾伤,蠲免之诏屡颁、赈济之法频施,高效结合多种手段来治饬灾荒。此外,还明确提出办理灾赈,应以从实为准,即“经费不敷,先定实数,后再准通融,断不可听书办匀灾之说,转使灾户遗漏。果无遗漏,虽通融亦无贻害矣!”[4](530)这种细致的务实思想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治灾救荒的迅时性。为了能及时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统筹以免延误救荒时机,杨西明的荒政思想中对救荒的迅时性有很高的要求。譬如,报灾方面,书中多处提及“速报”、“飞题”和对报灾迟误官员计日处分的规定,诸如“夏灾限六月终旬,秋灾限九月终旬”[5](470)的说法屡次出现。具体上,他要求督抚在地方遇有灾伤时必须“先将被灾情形日期飞章题报”。[5](470)并明确规定对逾限延迟的官员“按月日分别议处,上司属员一律处分,藏匿者严加议处。”[5](470)除了要及时上报、不能隐瞒不报或者讳报之外,他还提出了不能敷衍上报再无后文,必须对受灾情况按限勘明续报,“题后续报灾伤,一例速奏”[5](470)。对于续灾上报,也有时间限制。卷一中即有许多关于从报灾情形之日算起,由州县府院查核灾情并续报的规定。除报灾要迅时之外,杨西明在《灾赈全书》中还提到,在遇饥荒时应“先发仓廪赈贷,然后具奏请旨宽恤”[5](467),再处理后续事宜。对违反国家报灾时限的官员要施以严惩,对官员报灾后“不令赶种,留待勘报分数”,[5](473)以致耽误农时的做法也要严加议处,而且是“上司属员一体严加议处”[5](473)。这些无不体现杨西明对报灾救灾工作迅时性的高度重视。
2.治灾救荒的层次性。杨西明还强调官员要依灾荒的大小、灾民的受灾程度和赈济规模进行周密、细致勘分,并以此给予不同层次的赈济标准。《凡例》中指出“国家喜庆,有恩诏豁免者,是恩蠲,非灾蠲也,不可误认,今止载灾蠲。”[3](465)明确表明蠲免的性质和范围。在灾荒大小的界定上,《灾赈全书》卷三中有记载:“成灾五分以至十分,此指收成之分数也。假如被水被旱田亩收成[止]正有一分,则为成灾九分;有二分,则为成灾八分;无收成者,则为成灾十分。收成自五分四分三分二分一分以至无收,均为成灾。”[4](529)而其对大小不同的灾荒的赈济也是不同的,如果各省地方被灾不及五分,则“有奉旨及督抚题请缓征者,于次年麦熟后,只令催征旧欠;其本年钱粮准于九月后催征。若深冬方得雨雪及积水退者,缓至次年秋收催征。”[5](468)“如被灾八分九分十分者,将该年缓征钱粮俱分作三年带征,被灾五分六分七分者,分作二年带征,以緎民力。”[5](468)对水旱之灾的赈济规定则更为细致:“凡水旱成灾,地方官将灾户原纳地丁正赋作为十分,按灾请蠲。被灾十分者,蠲正赋十分之七;被灾九分者,蠲正赋十分之六;被灾八分者,蠲正赋十分之四;被灾七分者,蠲正赋十分之二;被灾五六分者,蠲正赋十分之一。”[5](474)对于乏食贫民也有极贫和次贫之分,先是不论成灾分数同等正赈一月,然后“于四十五日限内按查明承载分数,分晰极贫次贫,具体加赈。”[5](483)以分别给予不同赈济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杨西明的荒政思想中既有层次,也有一体性。无论是对乏食贫民“不论成灾分数,均先行正赈一个月”[5](483),还是对贫生饥军“各随坐落地方与赈”[5](483);无论是对江南各卫饥军“准其一体与赈”[5](483),还是对住居灾地营兵“除本身及家口在三口以内者不准入赈外,其多余家口,仍准入赈”[5](483);无论是对闲散贫民“同力田灾民一体给赈”[5](483),还是对闻赈归来者“一体入册赈恤。”[5](483)这些规定和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公平,稳定了社会秩序。
3.治灾救荒的具体性。突出表现为要求审户具体切实,根据各户实际受灾程度,把有限的救灾物资发挥最大的救灾作用。官员在受灾地区除依限勘报外,还要“将应赈户口迅速开赈,另详请题。若灾户数少,易于查察者,即于勘报限内带查并报。”[5](470)对于仓库和积聚的财物也应具体到责任人身上,“主守之人安置不如法,晾晒不以时,致有损坏者,计所损坏之物价坐赃论,着落均赔还官。”[6](505)蠲免之年时,各州县应切实把蠲免欠款落实,不仅要查清应征应免数目,提前开单并送交藩司核定,还要“发回刊刻,填给各业户收执,仍照单开各款,大张告示晓谕。”[5](478)“其监临主守官吏若将侵欺借贷那移之数,乘其水火盗贼,虚捏文案及扣换交单籍册申报瞒官希图悻免本罪者,并计赃以监守自盗论。同僚知而不举者与同罪,不知者不坐。”[6](505)以严令杜绝监守自盗的现象。
《周官·大司徒》中记载荒政有十二,其中第二条举措为“薄征”。薄征包含了议蠲、议缓之意。杨西明的荒政思想中也包含了通过“减负”来救荒的思想。譬如,对一些当年无法完纳应征漕粮和改折漕价的重灾地区,要“酌量被灾轻重,或全行缓征,或缓一半,或分作两年三年带征。”[5](480)非荒之年向社仓借领谷石,每石都要收取谷米一斗作为利息还仓,而荒欠之年则有“小歉借动者,免取其息”[6](498)的规定。这些都体现了杨西明希望通过减少或推迟灾民向政府交纳赋税的数量和时间来减轻灾民负担,以达救荒之目的。
(二)因时与地的变通思想
早在清朝初年,魏禧就把“因时制宜”视作救荒奇策,并提出“因时制事,世人不能行者而独行之,则谓之奇耳。”[7]到了嘉道时期,长江水患骤然加剧、东南各省灾害频发、各种特大灾害屡见不鲜。而“江南为财赋之区”[8],战略地位举足轻重,此地的兴衰在某种意义上与清代国家机器能否正常运转有着直接关联。因此,杨西明十分注重灾荒的治理,主张借鉴古人成法之精髓,因时因势而变通,并积极鼓励民间赈济。
杨西明在《灾赈全书》中多次提到清朝救荒要因时与地而宜,并不拘泥于成法条文:“凡漕粮遇灾,其应征米石,如本地米有不足,准其籼米代抵,或以粟米暂行改兑。”[5](469)在平粜仓谷上,以存七粜三为率,但还存在不同地域间的细致分别:“其浙省仁和、钱塘、海宁、海盐、平湖、镇海、象山、定海、永嘉、瑞安十州县暨嘉松宁绍两分司,准存半粜半;乌程、归安、德清、淳安,准存六粜四。”[6](500)又规定“如遇水歉价昂,准其逾额平粜。若岁稔价平,亦不必拘定存七粜三之例。”[6](500)可见在救济灾民时各项措施皆因时与地灵活相衬,尽最大可能保全受灾百姓的生命和利益,这种变通的荒政思想不仅是古代救荒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辩证思想的重要体现,也使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成为杨西明救荒活动中所遵循的重要准则,贯穿了他整个救荒活动的始终。
通过实施荒政缓解社会矛盾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有清一代,报灾、勘灾、赈济等各项救荒程序和救灾备荒举措也已相对完备,这为嘉道时期国家荒政的有效实施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然而,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吏治腐败分外严重、财政问题日益突出,形似严格周密的救荒体制往往成为一纸空文,这为民间赈济的兴起提供了历史的契机,使之成为国家赈济的有效补充并得以日益发挥作用。这也是杨西明劝富济贫、因时与地、灵活高效的荒政思想的现实基础。《灾赈全书》有记载:“州县买补仓谷,遇本地有谷之家情愿出售于官者,准其议定价值,见谷交银,官为挽运。”[6](501)体现了官府对于民间赈济的扶持。而对于民间赈济抚恤,地方官要“先行劝谕,多方开导”[6](504),担负起相应的职责,使这些积粟富足之户“笃念桑梓,出其有余,以平市价,以惠乡党。”[6](504)以恤贫安富、“息事宁人”。事实上,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嘉庆诸皇帝都十分重视民间相互救助,极力主张贫富相维,间里相济。这种倡导民间互救、自救的思想也是杨西明救荒思想的一大特征。譬如,青黄不接、米价陡涨之时,地方官要“谆切劝谕盖藏充裕之家,令其酌留食用外,陆续粜卖,以济民食”[6](501)。除劝谕外,对一些过分积米、闭籴妨民者,甚至可以“酌量情形,勒令出粜。”[6](501)而对于一些乐于行善、愿意减价平粜救济贫民的殷实富户,由州县官“核其所粜若干、所减若干,酌其多寡,量为嘉奖,或赍花红,或给匾额,行善者多,或统作一碑志,以为乡党劝。”[6](502)“数在千石以上者,亦应如该左副都御史范所奏,酌加旌奖。”[6](504)可见,迫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杨西明在众多荒政措施中都包含着鼓励民间赈济、重视劝富济贫的救荒思想,这也是传统荒政思想向近代荒政思想转型的萌芽表现。
(三)明责纠责的任贤思想
杨西明在《灾赈全书》通篇还表现了重视地方官吏在救荒中作用的任贤思想,这与当时社会发展的背景有密切关系。在清代,荒政制度已十分完备,荒政思想也有了长足发展。杨西明作为清朝士大夫集团中的一员,其救荒思想注定被政府的荒政制度所左右。他较早地认识到,吏治事关荒政实效,尤其是地方官吏,作为救荒举措的具体执行者,他们在救荒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卷一规定了在江海河湖居民受水灾时地方官有职责“一面通报各该管上司,一面赴被灾处所验看明确,照例酌量赈济,不得濡迟时日。”[5](468)“沿河州县报潦,令地方官会同河员确勘。如有查勘不实及隐瞒民灾等弊,将地方官、河员一并题参,照例分别议处。”[5](469)不仅明确地方官职责,也强调河员的职责。对于那些救灾不力的官吏,他强调要进行严惩,譬如平粜借谷时“地方州县官不实力稽查,致书役包买渔利勒掯出入者,降一级调用。如州县官已觉察而故为容隐者,将该州县革职。”[6](523)事实上,清朝历代统治者都把能否妥善救济灾民看做治国安邦的大计,从康雍到乾嘉,无不高度重视地方官员在救荒中的职责,乾隆就多次强调“赈恤一事,乃地方大吏第一要务。”[9]
为了保证地方官切实行使职责、保证荒政措施的执行实效,明确法律就显得至关重要。杨西明在《灾赈全书》中多处提及明确法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譬如,对报灾时限和官员奉蠲就有明文规定:“州县卫所官奉蠲钱粮,或先期征存,不行流抵,或既奉蠲免,不为扣除,或故行出示迟延,指称别有征款及虽为扣除而不及蠲额者,均以侵欺论罪,失察各上司俱分别查议。”[5](469)对贫民借贷也有明确法律规定:“凡遇地方荒歉,借给贫民米石谷麦,或开垦田土,借给牛具籽种,以及一切吏役兵丁人等办公银两,原系题明咨部,行令出借。倘遇人亡产绝,确查出结,题请豁免。如有捏饰侵渔以及未经报明,私行动借者即行题参,按律治罪。”[5](469)使得荒政措施有律可依。
明令条文是和严明惩罚相辅相成的。为了消除官吏中饱私囊、玩忽职守的弊端,杨西明非常推崇明代林希元的做法,即以赏罚约束官员行为,“求贤于赏罚之中”。他在《灾赈全书》中多次提及,对于水旱霜雹及蝗灾,“一应灾伤应减免之田粮,有司官吏应准告而不即受理申报上司亲行检踏,及本管上司不与委官覆踏者,各杖八十。若初覆检踏,有司承委官吏不行亲诣田所,及虽诣田所不为用心从实检踏,止凭里长甲首朦胧供报,中间以熟作荒,以荒作熟,增减分数,通同作弊,瞒官害民者,各杖一百,罢职役不叙。”[5](467)体现了其荒政思想中严明惩罚和保民的一面。在赈济灾饥民以及蠲免钱粮时,如果州县官侵蚀肥己,“致民不沾实惠”,则“革职拿问,照侵盗钱粮例治罪。督抚布政使道府等官不行稽察者,俱革职。”[5](468)体现了对各州县官、督抚布政使道府等官的纠责思想。同时,也明确规定了官员权限,对于官吏滋扰民生者严惩不贷:“开垦荒地,任从民便。倘地方官稍涉抑勒,以少报多,或以多报少,并以熟报垦,及不分荒熟,一例升科飞洒,捏升钱粮者,从重处分。又或未曾欺隐,抑民首报荒田,托名清厘田粮,无故查丈,致滋扰累者,均予严究。”[6](520)官员为官不用心、做事草率懈怠导致疏漏不实者也要纠责:“委员内如有查灾不据实结报,办赈不实心挨查,草率从事仍前怠忽者,该督抚查明题参,照地方查办灾赈不实一体处分。”[6](523)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员,都把政务的得失和自然灾害联系在一起,因此官员在奉蠲和平粜中未能尽责也要负连带责任就不难理解。当然,对于官员失职的惩处也有所区别,主要分参请拿问、议处、降级、革职等,譬如“州县将成灾报作不成灾者,具题参革职,永不叙用。如不实心确勘,少报分数者,革职。”[6](522)可见,在备荒救灾过程中强调对救荒者进行严格监督,是杨西明荒政思想的又一大特色。
(四)关注民生的民本思想
历朝历代往往把赈救灾荒作为君主和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责,强调“民”的地位和重要性,以保证政治清明和社会稳定。杨西明所著《灾赈全书》不仅全篇贯穿这种民本思想,多处体现其关注民生、稳定农业发展、保护生态的荒政思想,更在卷三将“抚恤难番事宜”[4](545-550)专列为一目,辑录了浙江巡抚与户部于乾隆二十一年商定的“抚恤难番章程”,着重体现了其重民、保民、裕民的荒政思想。
杨西明《灾赈全书》全篇贯穿的这种重民、保民、裕民的荒政思想有诸多表现,最突出之处则在赈济灾民、以苏民困上。在卷一开篇《总略》中即有说到,凡遇岁饥应“先发仓禀赈贷,然后具奏请旨宽恤。”[5](467)体现其赈民为先的荒政思想。在借贷方面,“凡社仓谷石,不遇荒歉借领者,每石收息谷一斗还仓;小歉借动者,免取其息。”[6](498)“因灾出借籽种口粮,凡夏灾借给者,本年秋成后启征;秋灾借给者,次年麦熟后启征。均免加息,扣限一年催完。限满不完,将经征官议处,遇灾仍照例停缓,均于仓粮奏销案内造报。”[6](498)平时即与民为便,保障贫民生活,灾时更免取其息,体现其赈济灾民、保障民生的荒政思想。在卷一《赈恤》正条细则中更提及:“浙江水冲民房,楼房每间二两,瓦平房每间一两,草房每间五钱,草披每间五钱五分。淹毙,大口埋葬二两,小口一两。”[5](484)“浙江省被水田亩,沙淤石压者,每亩给修复钱二钱;水冲田禾,每亩给籽粒银一钱,令其及早垦复,不致国赋缺征。”[5](484)可见,杨西明不仅将重民、保民、裕民的思想贯彻到方方面面,而且突出了有地域性的、因地制宜的救荒理念。
除保障民生外,杨西明的民本思想还体现在宽恤百姓上。作为清朝士大夫集团中的一员,杨西明深刻地认识到与灾荒相伴的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和病疫肆虐,所以在灾荒发生之后最重要的是安定民生、发展生产和知民所苦。为了维持百姓的基本生活,他采取了如施衣、保幼的措施,对于死者也会施棺、设立义冢,鼓励捐输、据实宽恤百姓、减免百姓负担。譬如,卷二《借给贫民》中提及“各省偏灾地方,节年出借未完籽种口粮牛具等项,查明实在力不能完者,取具册结,送部保题豁免。”[6](498)由于灾民四处流徙,不仅影响国家经济发展,还可能危及政权统治的稳定,因此,安辑流民就显得十分重要。对于灾荒后的流民,杨西明倡导救济、安辑:“凡被灾最重地方,饥民外出求食,各督抚善为安辑,俟本地灾祲平复,然后送回。”[6](514)
由于饥荒之年粮价十分昂贵,农民常常食不果腹,把农事看作首务就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历朝的定制。早在春秋时期,管仲就提出:“一农不耕,民有为之饥者;一女不织,民有为之寒者。”[10]清代章谦存也曾指出:“天下之本在农,农民困则天下困。”[11](461)而荒政问题更是与农业息息相关。只有平时发展农业,生产出足够的物质资料,才能在灾荒来临之际有备无患,保证国泰民安,即“重农田而顾根本”[8]。因此,杨西明非常重视农业,尤其重视灾后政府能否创造条件帮助灾民恢复农业生产,他在《灾赈全书》卷二中不吝用大量篇幅记载垦荒的相关条例,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开展灾后重建,体现其灾荒之年对农业生产给予严格保护的重农思想。
清朝的士大夫往往通过科举进入统治阶层,对民间疾苦有一定了解。杨西明在《初稿自序》中曾提及“明府勤于政治,精明强干,知遇既深,报称益难。二十三四两年,连岁旱灾,蠲缓并办。明府以实心行实事,凡事必根求底理,且各邑以明府之贤明,修札下问者无虚日。”[1](463)可见,其入幕为仕后是真心想一展抱负,为民“以实心行实事”。因此,《灾赈全书》也体现出他对救荒有更清楚的认识。譬如,主张裕民政策、省上厚下:“凡遇歉收之岁,贫士与贫民一体赈恤。”[5](468)体现了他在救荒中对于贫士、贫民一视同仁,平等赈恤的思想;又规定“贫生赈粮,由该学教官散给;灾民赈粮,州县亲自散给。如州县不能兼顾,督抚委员协同办理。”[5](483)体现了其灾贫同赈、保障民生的思想。但《初稿自序》也表现出他实质上维护的是地主阶级的利益,致使其民本思想中有偏向保富的一面。这两种思想看似矛盾,事实上并非如此。省上厚下和保富矛盾的焦点不是在备荒的目的,而是在不同的备荒方式上。《灾赈全书》卷二中也有提及:“地方不可一日无积贮,无富民是无积贮也。贫与富皆赤子,弭其衅乃以调其平也。”[6](503)佐证了其“民本思想”的本质是为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
杨西明《灾赈全书》中也充分体现其与灾荒相抗争、与生态相平衡的思想。卷二中提及:“濒临江海湖河处所沙涨地亩,如有阻遏水道为堤工之害者,毋许任意开垦,妄报生科。如有民人冒请认种,以致酿成水患,即将该民人家产查抄,严行治罪,并将代为详题之地方官等一并从众治罪。”[6](521)可见,在保障民生、鼓励农民垦荒及强调地方官员的监督职责和连带责任的同时,杨西明也强调保护生态,避免人祸,突出其荒政思想中关注生态良性发展的一面。
(五)天命主义的禳弭思想
孟昭华先生在《中国灾荒史记》[12]中提出,中国古代救灾思想可分为天命主义的禳弭论、消极的救济论和积极的预防论。对于杨西明《灾赈全书》来说,其荒政思想主要是重民务实的,但也存在天命主义的禳弭思想。一方面,其大量篇幅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也不排斥救荒避灾的禳弭思想,表明了杨西明怀疑天命、注重人为但又无法战胜自然、不得不依赖神灵的复杂思想。该著在卷三《钱塘县祈祷事宜》[4](540-542)中,以一定篇幅介绍了“祈雨文”、“祈晴文”、“求雨文”和“谢资胜寺龙神表”、“谢资胜寺观音表”等一些反映天命主义救荒思想的文章。譬如,卷三“求雨文”说到:“某等谨昭告于山川之神云:惟神镇艮坎之位,阐岳渎之灵,德主宣而宣昭万类,性惟润而润泽群生。是以旸雨偶愆,必伸虔祷,灵威所被,用锡休征。”[4](541)体现其在免除灾害中寄希望于神灵庇佑的禳弭思想。再如,“谢资胜寺龙神表”中写道:“恭惟龙神,首列四灵,游于八级。深仁广被,庙重海疆;伟烈尤昭,寺开资胜。昨以省垣祈雨,恭迎神驾临坛。望气占云,万姓于焉共仰;清尘洒道,诸司莫敢不从。”[4](541)可见其对神灵的尊崇和顺从。“谢资胜寺观音表”也有提及:“昨以省垣望泽,恭迎法驾临坛。鸾骈初启于灵山,已浓云之周匝;凤辇甫巡于近郭,遂甘雨之滂沱。”[4](542)“获丰穰之岁,咸沾平等恩波;救艺兆之生,益信无边法力”[4](542)希望通过对天或神灵的祷告、祈拜、祭祀等,祈求早日度过饥荒或来年风调雨顺。这种天命主义的禳灾思想在杨西明的救荒思想中有一定的影响。
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开始用阴阳五行解释自然灾害。汉朝时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更是提出“天人感应”下的“灾异谴告说”。此后,天命主义的禳灾思想就在人们的意识领域里占据了主导地位。“清圣祖仁皇帝在位五十六年约有五十年祈雨,每遇旱荒, 他都在宫中设坛祈祷, 长跪三日, 减善节用, 尔后再步诣天坛虔祷。”[13](531)可见直至清代,这种救荒思想仍然占据重要地位。乾隆时期陈宏谋曾作《伐蛟说》,通篇充斥了神秘和诡异的天命思想;陆世仪作《除蝗记》也体现了大量尊奉神灵、请求恩泽的禳弭思想。所以,杨西明在《灾赈全书》中表现的天命主义禳弭思想,是在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大背景下主流荒政思想的一个分支。这种救荒思想虽然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多样的表现形式和久远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不可能从实质上认识并解决救荒弊端。值得庆幸的是,《灾赈全书》通篇所体现的荒政思想中,这种天命主义思想只占较小比重,更多是体现了一种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重民务实的思想。可见,杨西明荒政思想虽未能脱出时代和阶级的窠臼。
三、余 论
杨西明的荒政思想是在主观与客观、历史与现实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严峻的现实使他具有较强的灾情意识,重视对自然灾害的预防和治理,因此在其备荒思想中,十分强调通过人的主观努力来达到防灾减灾的目的。《自序》中即有提及:“故廷臣修辑条例,载在编册,至精至当,历厉如绘,宁可千万日不用而有所遵循,不可一日不备也。”[1](463)体现其积极防患的思想。从其荒政措施中也可以看出,杨西明是相当务实的,他采取的措施积极有效,作法也足够扎实细致。但是,我们也应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如杨西明的荒政思想及备荒救灾措施多是就灾论灾,缺乏对事件根源的综合思考,而且过分高估官员的执行力,把明责纠责看成救荒的最大法宝,这些不得不说是一种缺陷。
[1] [清]杨西明.灾赈全书(初稿自序)[M]//李文海,夏明方.中国荒政全书(第二辑第三卷).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3.
[2]夏明方.救荒活民:清末民初以前中国荒政书考论[J].清史研究,2010(2).
[3][清]杨西明.灾赈全书(凡例)[M]//李文海,夏明方.中国荒政全书(第二辑第三卷).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3.
[4][清]杨西明.灾赈全书(卷三)[M]//李文海,夏明方.中国荒政全书(第二辑第三卷).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3.
[5][清]杨西明.灾赈全书(卷一)[M]//李文海,夏明方.中国荒政全书(第二辑第三卷).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3.
[6][清]杨西明.灾赈全书(卷二)[M]//李文海,夏明方.中国荒政全书(第二辑第三卷).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3.
[7][清]邵之棠.皇朝经世文统编[M].卷41内政部十五·救荒策.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
[8][清]沈葆桢.沈文肃公政书[M].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
[9]宫中全宗朱批奏折(内政类).乾隆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许容奏朱批[Z].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0]诸子集成(第五册) [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
[11]李文海,夏明方.中国荒政全书(第二辑第四卷)[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3.
[12]孟昭华.中国灾荒史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3][清]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
(Qing Dynasty) YANG Xi-ming’s Relieving Famine Policy of “ZAIZHENQUANSHU”
CHEN Wen-lian, REN Li-juan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3, China)
Yang Xi-ming’s relief book “ZAI ZHEN QUAN SHU” consists of four volumes, It is a very influential famine relief work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It involved the famine relief countermeasures and many other aspects, from the pre disaster prevention to the disaster relief, from store up grain against famine to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on, all embodied the positive famine relief thought and social reality of the social unity. As a member of the feudal literati in Qing Daoguang years, Yang Xi-ming has servered Jiangnan region for decades, the formation of his famine relief thought has both profound social roots and complex personal factors. Concern about people’s livelihood is the main line of his famine relief thought, concrete and pragmatic is the principle of his famine relief thought and correct clear responsibility, time and place is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his famine relief thought. The famine relief thought embodied in “ZAI ZHEN QUAN SHU” not only enriche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famine relief in Qing Dynasty, but also provided great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future famine relief activities.
Qing Dynasty;Yang Xi-ming;relieving famine policy
2016-04-04
陈文联(1967—),男,湖南衡阳人,博士,教授,从事晚清思想史研究。
K249
A
1673-0313(2016)04-011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