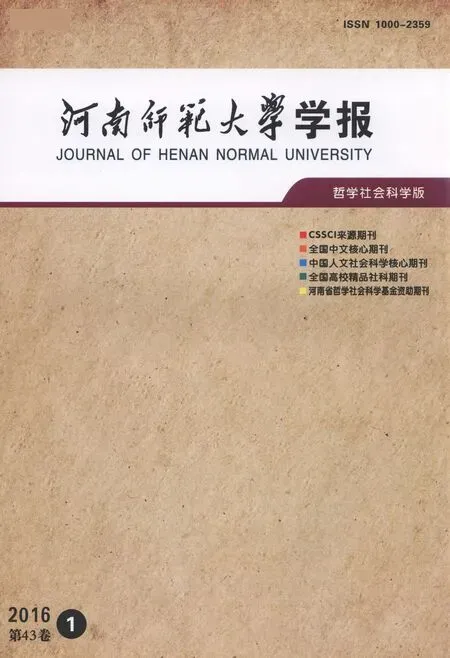戴名世以古文论为时文论的批评特色
陈 水 云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戴名世以古文论为时文论的批评特色
陈 水 云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戴名世被称为桐城四祖之首,对于桐城派文论有导夫先路的意义。虽然对八股文本身评价不高,但他却以教习八股文传名于世,因此,对于时文问题有自己独到的看法。首先,他提出由时文而学问的观念;其次阐述了道法辞相合、清气神为一的思想;第三提出八股文写作,要做到文成而法立,追求自然之美,独得于心,不入窠臼,自成一家。他的这些观念都鲜明地体现了以古文论为时文论的批评特色,在清初八股文批评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戴名世;八股文;文学批评;桐城派
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一字褐夫,别号南山,安徽桐城人,是康熙时期的时文名家:“褐夫少以时文发名远近,凡所作,贾人随购而刊之,故天下皆称褐夫之时文。”(方苞《南山集偶钞序》)戴名世自二十岁始方从事时文写作,为了养家糊口,承其父业,以课徒为生。尽管他以制义知名于时,但在科场却是屡经坎坷,直到康熙三十四年(1704)才中举,四年后以一甲第二名成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这时已是五十七岁的老人。三十余年的时文教学与科场经历,锻炼了戴名世的写作能力和鉴赏水平,使他对时文的写作及其审美追求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看法和见解,并对后起桐城派理论之形成及发展产生深刻之影响。
一、由举业而学问
在戴名世的时代,时文已是腐烂至极,人们对八股文的批评聚讼之声不断。在清初已有顾炎武“举业之害有甚于焚书”之论,戴名世也有“今夫讲章时文其为祸更烈于秦火”之言,但问题的关键还是科举制度造成士风的空疏不学。他说:“时文兴而先王之法亡。世之从事于举业者,冥冥茫茫,不以通经学古为务,其于古今之因革损益,与夫历代治乱废兴之故,无所用心于其间。则虽其文辞烂然,而识不足以知天下之变,才不足以应天下之用,是举业有累于先王之法也。”[1]卷四《汪武曹稿序》:100
他认为当世举业之徒,为求科途之便捷,“相习为速化之术”[1]卷五《送刘继庄还洞庭序》:136,平时只读烂熟之时文。对于《四书》《五经》无所用心,在科场应试时或是模仿或是钞袭,一旦得隽则弃置不顾。这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行为,“譬如叩门之石然,门开而石即弃去”[1]卷四《刘光禄墨卷序》:125,“收鱼兔之利而遂置筌蹄不顾”[1]卷四《宋嵩南制义序》:113。时文既然被作为一种获取利禄的工具,其结果是先王圣人之道不明,背离了当政者选才取士之初衷。所谓“自先王之道不明,而世有讲章时文之学,盖讲章时文之毒天下也”[1]卷五《赠刘言洁序》:137。这样的做法,何异于秦始皇之焚书坑儒,即让天下之人废书不读。“岂天之欲丧斯文灭六经,而假手于俗儒,以补秦火之遗漏,不然则鄙夫小生其罪不减于始皇、李斯,而独居穷经之名,取富贵之资,圣人之道几何而不息也!”[1]卷三《自订周易文稿序》:160在他看来,时文写作之目的,本来是为了发明圣人之道的,并非全为举业而事之。“君子者,沉潜于义理,反复于训诂,非为举业而然,引伸触类,剖析毫芒,于以见之于举业之文,实亦有与宋儒之书相发明者”[1]卷四《己卯科乡试墨卷序》:95。经义之功用在明天地万物之理,是为了体察“古今之因革损益与夫历代治乱废兴之故”。如果儒生只是求其文辞之烂然,这样的举业文章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因为它偏离了为文意在明理的目的。
在这里,戴名世提出了“通经学古”的要求,认为这才是举业之正途,时文之祈向,学问之根本。通经学古的主要途径,就是学习儒家经典,特别是《四书》《五经》。“《四书》、《五经》,明道之书也”[1]卷四《丁丑房书序》88。它是古之圣人用来讲明古今因革及历代治乱废兴的,但自汉以来对它的理解与阐释皆有其弊,直到宋代诸儒出才使圣人之道“大明”:
周之衰至于今,儒学既摒焉,圣人之道扫地无余。独幸有其书尚存,而学者大抵皆浅陋,不能申明圣人之意,自汉之训诂笺疏已失其旨,而学宫所立《五经》家皆无当于大道之要。盖道莫著于宋,宋之时不能用之,至有明而显。嗟夫!其言虽显于明矣,而其道或未之能行也。天下之士非科举之文无由进,而科举之文非宋氏诸儒之说辄斥不收。夫非宋儒之说不收,其意岂不盛哉,而学者第假其说以为进取之阶,问其何以学,曰以科举故也。则即其始学之日而固已叛于宋氏诸儒之道矣。然当世学者习其书,犹能为其言,兢兢不敢失坠。至于正德、嘉靖以来,诸儒纷纷而起,良知家言最行于天下,浸淫蔓延,而士皆以叛攻宋氏为贤,于是横议之祸渐流为门户,天下亦自此多故矣。[1]卷五《送许亦士序》:132
他非常认同明代以经义取士的政策,但不满于科举之文对于朱氏之学的偏离,特别是晚明王学对于儒家经典的歪曲。因此他一生极力于对朱氏之学的恢复,并在晚年编成《朱子四书大全》一书。“古人罢黜百家,独尊孔氏;今之尊朱氏,即所以尊孔氏也。……诸儒之说,其庞杂割裂而疵谬者,使学者眩瞀莫辨而误其所从,汰而去之,固其宜也。……学者但明于朱子一家之言,而诸儒之说是非雅正,自了然于胸中,而不为其所乱”[1]卷三《朱子四书大全序》:76。但是,自举业时文起,人于先王之教弃而不务,“而研精覃思以从事于场屋之文”[1]卷四《狄向涛稿序》:87,圣人之道因之衰息也。因此说,“《四书》、《五经》之蟊贼,莫过于时文”[1]卷二《四书诗义合刻序》:35。对于从事于举业时文者而言,必须以通经学古为务,“洗脱凡近而讲明义理之所以然”,“而后文章之事,父子兄弟脉脉相授而不至于失坠”[1]卷四《课业初编序》:128,这样才会达到“学以明道”、“道以持世”的目标[1]卷三《困学集自序》:77。他记载自己闻先辈论制义之言曰:“制义之为道无所用书,然非尽读天下之书,无所由措思也,无所用事,然非尽更天下之事,无由措手也。”[1]卷二《野香亭诗序》:36博古通今而后为文,就不会为一时科场得失所左右。在他看来,“学莫大于辨道术之邪正,明先王大经大法,述往事,思来者,用以正人心而维持名教也”。作者如果进入这一境界,那么就会独立于波靡之中,其心不为外在之物所诱,富贵贫贱亦不足以易其节。“苟其得志也,持是而往,恢恢乎有余也;苟其不得志也,亦若将终身焉。此则真所谓功名者也!此则真所谓读书之有成者也”[1]卷三《蔡瞻岷文集序》:79。相反,即使有人侥幸获致,但对先王大经大法不甚明了,也难说是读书之有成。从大之礼乐制度、农桑学校、明刑讲武所不知,到古文辞之茫如,其所为举业之文,虽一时能得当于场屋,却是臭败而不可近。“虽其富贵利达之侥幸而获,而固已为有志君子之所屑矣!”[1]卷四《己卯科乡试墨卷序》:94
在戴名世看来,国家以八股取士,意在使读书人专注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如果人之学之,自少而壮而老,终身钻研于其中,吟哦讽诵,揣摩习熟,那么就会见理也明,择言也精,其心思才力,亦中以纵横驰骋于世。从这个角度看,“文章之事,学问中之小者;制举之文,又文章中之微者”[1]卷一《答张氏二生书》:21。但是,求道还需借助于古文,而对于古文之法不甚明了,所作必然无法臻于时文之佳境。他说:“不从事于古文,则制举之文必不能工也;从事于古文,而不能学问以期于闻道,则古文亦不能工也。”[1]卷一《答张氏二生书》:21因此,写作时文当有良好的古文根基,他自谓少时先是学为儒家经典,接着泛览周、秦、汉以来诸家之史,“间尝作为古文以发抒其意”,最后是因为家贫无以养亲,不得已而开门授徒,始从事于制义。由时文而古文而道,亦即由举业而古文辞,再由古文辞而上之,至于礼乐制度、农桑学校、明刑讲武之属,终于圣人之大经大法,这才是从事举业者必须经过的一条通衢大道。他认为“文章之道”与“圣人之道”要求不同,“圣人之道”经宋儒的发明已大明于天下,“学者终其身守宋儒之说足矣”,“至于文章之道,未有不纵横百家而能成一家之文者”[1]卷一《与何屺瞻书》:19。他讲到自己作时文,即是:“根柢于先儒理学之书”,“取裁于六经诸史以及诸子百家之言”,而形成“一家之文”,故所为文“意度各殊,波澜不一,不可一定阡陌畦径求也”[1]卷四《意园制义自序》:123。这是自明代以来人们已经达成的一致共识,也是今之从事举业者所当遵守的。在时文昌盛的明代中后期,人之所以为时文者,不徒于时文求工而已也。“自《六经》之文,以至历代史乘、诸子百家之书,无不有以心知其意”[2]卷四《谢玉临稿序》:209。
二、时文为古文辞之一体
但当时的情况是,人们将古文与时文歧之为二,重时文,轻古文。对于时文,“天下之人,童而习之,至于白首”;而对于古文,“以为非功令之所在,而终其身而莫之为”,“使之为古文,宜其惊愕惶惑而不能执笔也”[1]卷四《小学论选序》:91。甚至连《左》、《国》、庄、屈、秦汉、唐宋诸大家之文“举天下而莫之知也”。在戴名世看来,古文与时文并不矛盾,如明代著名的唐宋派作家归有光,“要亦为科举之业者,而未尝累其为古文”[2]卷二《归熙甫稿序》:53,其实时文之法乃从古文辞而来,时文实为古文辞之一体。他说:
余平日读书从事文章之际,窃以为制举之文,亦古文辞之一体也。世之人废古文辞不观,而别有所以为制举之文,曰时文之法度则然,此制举之文所以衰也。今夫文之为道,虽其辞章格制各有不同,而其旨非有二也。……夫制举之文,所以求得举也,然而得失之故,初不系于此。其得之者,未必其文之皆工也;其不得者,亦未必其文之果不工也。而特君子之所以为之者,必不肯卤莽灭裂以从事,而得失之数不以介于心。是故其制举之文即古文辞,其旨莫之有二也。[1]卷四《李进潮稿序》:105
这里,他特地强调时文之工拙,与科场之得失并无必然联系,时文与古文只是体制上稍有差异而已。本来,古文宗旨在“明圣人之道”,“穷造化之微”,“极人情之变态”[1]卷一《与刘大山书》:11。时文也应如此,由古文而上之,至于圣人之大经大法。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多以时文为猎取功名之目标所在,因此,时文之风气必然随时而变,特别是考官的趣味。“制义者,与时为推移也,故曰时文。时之所趋,遂成风气,而士子之奉以为楷模者胥会于一。然而势有所止,情有所厌,思有所穷,运有所转,于是乎数十年而变,或数年而变,或变而盛,或变而衰,往往相为倚伏”[1]卷四《宋嵩南制义序》:113。决定时文文风变化的是世风,世风通过科举取士体现出来,科举却使得载道之文变成了敲门砖,从这个角度看,是科举造成了“文风败坏”、“文妖迭出”。比如以论与制义相较,“时文者,时之所尚,而上之所以取于下,下之所以为得失者,则今之经义是也。至于论者,则群以为古文之体,而非上之所以取于下,下之所以为得失者,则遂终其身而莫之为。”对时文,人们自幼习之,至于白首而不辍;对于论之一体,以为其非功令所在,故亦无所用心,终其身而莫之为,其原因盖在区古文与时文而二之,惟以科举功令作为衡文之唯一标准。“今夫经义之与论,虽皆古文之派别,而其体制亦各有不同者。”对于制义,国为是代圣人贤人之语气而为之摹拟,其语脉之承接于题词之上下文义,皆有所避忌,在文法上也有严密的要求。“一毫发之有差,则遂至于猖狂凌犯,断筋绝膑,而其去题也远矣”[1]卷四《小学论选序》:91。对于论来说,因其可以出之己意,反复辨难,穷尽事理,以求无余蕴,于题之上下文义也不必有所避忌,只须斟酌损益,而不必使轻重宾主或至倒乱于其间,其用力之处自不如经义。
因为重在功令,本来在文法上与古文相通的时文,渐渐与圣人之道相背而驰。它既不通于理,也不适于用,“两者之相悬隔,若黑白冰炭之不相及也”。他说:
自科举取士而有所谓时文之说,于是乎古文乃亡。其所谓时文者,以其体而言之,则各有一时之所尚者,而非谓其文之必不可以古之法为之也。今夫文章之体至不一也,而大约以古文之法为之者,是即古文也。故吾尝以谓时文者,古文之一体也。而今世俗之言曰:“以古文为时文,此过高之论也。”其亦大惑也。且夫世俗之言既举古文时文区划而分别之,则其法必自有所为时文之法,然而其所为时文之法者陋矣,谬悠而不通于理,腐烂而不适于用,此竖儒老生之所创,而三尺之童子皆优为之。至于古文之法,则根柢乎圣人之六经,而取材于左、庄、马、班诸书。两者之相悬隔,若黑白冰炭之不相及也。今世俗取时文之法与古文并立而界限之,曰:“吾所为时文,其法具在也,而无用于古之法为。”是其意殆以圣人之六经及左、庄、马、班诸书,不若今之竖儒老生与三尺童子也。毋乃叛圣侮经而与于无忌惮之甚者乎。故曰,自科举取士而有所谓时文之说,于是乎古文乃亡,非亡于时文也,亡于时文之法也。[1]卷四《甲戌房书序》:90
既然古文之法为时文所遮蔽,科举功令造成了古文的消亡,何以救之?戴名世提出的策略是:“救之以古文之法”。在他看来,古文之法莫备于韩(愈)、柳(宗元)二家之所论,韩之言曰:“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3]柳子之言曰:“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4]这就是人们通常理解的古文之法,如果写作时文能取乎此,则时文莫非古文也。因为科举功令把古文之法消解了,这使人们对古文之法的理解存在多种分歧:或“学古而失”,或“背古而驰”。何谓“学古而失”?就是从事于格调字句之间,跬步不敢有失,摹拟仿佛,饰为声音笑貌,而以近于某家之文相矜许,这样只会带来“古之学废矣”的恶果。学古失去自己,自是为文失败之处。那么,“背古而驰”又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其失亦然,因为它捐弃古文之法,偏离了自《史》、《汉》而唐宋八大家以来所形成的为文之道,率而相习为骈偶之风。“排偶骈丽之盛行,其节促以乱,其音淫以靡,学者相沿而不知怪,遂俨然以此为古文之体,而左、《国》、庄、屈、秦、汉、唐、宋诸大家之文,举天下而莫之知,而古之学又废矣。”如何救之?戴名世认为,当明体、平心、养气,“捐其近名之心,去其欲速之见”,这样才会自然得之,“其去古也不远矣”[1]卷一《再与王静斋先生书》:21。
对于以古文为时文,戴名世的理解是,当以时文行古文之法。“夫举业之文号曰时文,其体不列于古文之中,而要其所发明者圣人之道,则亦不可不以古文之法为之者”[1]卷四《汪武曹稿序》:100。古文之法来自经典,作时文自当行以古文之法。他曾有感于当时文运波靡,“乃集学徒,告以文章源流,而极论俗下文字之非是”[1]卷四《意园制义自序》:123。故特别称誉友人汪份力挽世俗颓风,“以先儒之旨,前辈之法,为之正告天下,天下之从事于举业者,乃恍然悔悟其向者之非,而思改其所为”,武曹所自为文,亦自横绝一世,是以古文为时文者。“顾自时文兴而古文亦亡,顷者余与武曹执以古文为时文之说,正告天下,而真能以古文为时文者,武曹而外,余未之多见也”[1]卷四《汪武曹稿序》:100。在谈到读归有光时文时,他联想到当世时文之弊,深有感慨地说:“使震川生今之时,见今之失,其为太息痛恨,尝何如者哉?呜呼!人以为古文自古人,时文自时人,而岂知不能古文者,即不能时文者乎?”[2]卷二《归熙甫稿序》:53如何纠正时文之弊,他发表的意见是:“余向与诒孙言,欲天下之平,必自废举业之文始,因劝之从事于性命与用世之书。”[1]卷四《吴七云制义序》:108也就是从儒家经典与经史百家之书入手,只有博览群书才会使其文臻于至佳之境。“吾之书固已读而吾之文固已工矣。夫是故一心注其思,而万虑屏其杂,直以置其身于埃壒之表,用其想于空旷之间,游其神于文字之外,如是而后能不为世人之言。不为世人之言,斯无以取世人之好,故文章者莫贵于独知”[1]卷一《与刘言洁书》:5。但后之人务为速化之术,目不睹古人之书,剽窃乎世俗之习,以之逢迎当世,世喜其雷同近己,遂从而称之,而要岂得之文哉?他称自己即是从古文而时文的:“自初有知识即治古文,奉子长、退之为宗师,暇从事于制举之文,于诸家独好归太仆、唐中丞。”[1]卷一《答张氏二生书》:21
三、“道、法、辞”与“精、气、神”
在阐述了时文与古文关系的基础上,戴名世进一步从文本内在构成的角度,谈到时文是由“道、法、辞”组成的,行文当做到道、法、辞三者合一。他说:
在昔选文行世之远者,莫盛于东乡艾氏,余尝侧闻其绪言曰:“立言之要,贵合乎道与法。而制举业者,文章之属也,非独兼夫道与法而已,又将兼有辞焉。”是故道也,法也,辞也,三者有一之不备焉而不可谓之文也。[1]卷四《己卯行书小题序》:109
这里所说东乡艾氏是指晚明著名八股名家艾南英,也就是说他对道、法、辞关系的论述受到艾南英的直接影响。关于文与道的关系,向为历代论文者所重视,艾南英在《陈大士合并稿序》《四家合作摘谬序》中亦针对时文作了重点论述,较之艾南英而言,戴名世更为清晰地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内涵与关系,比如“道”与“法”、“理”与“文”、“法”与“辞”等。
戴名世所谓“道”,首先是指先王之大经大法,亦即由朱熹所阐扬的孔孟之道。“今夫道具载于四子之书,幽远闲深,无所不具,乃自汉、唐诸儒相继训诂笺疏,率无当于道之要,至宋而道始大明”[1]卷四《己卯行书小题序》:109。但戴名世对于“道”的理解,也不全然出自儒家之道统,它还指天地万物之“理”。他曾引用荀子、文中子二家之说,表达了他的这一观点:文即是理,理即是文,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无文也。“今夫天地万物莫不有理,文也者,为发明天地万物之理而作者也。理之不明,是已失其所以为文之意矣,而何文之有乎?”这是从文的角度看的,再从人的角度看也是这样:“君子之言,正其名,当其辞,以务白其志义者也。”人的“志”与“义”也是“理”,这“理”与“文”相关联,“文”又是“志”与“义”的外在表现。“吾见近世之士,本无所为志义之存也,举笔为文,于理曾未之有当,正如荀子之所谓‘芴然而粗,啧然而不类,誻誻然而沸’者耳,而可以谓之文乎?”[1]卷三《杨千木稿序》:67戴氏所谓“道”较之一般人之论述更为宽泛,主要是从文章内容方面谈的,既指儒家的圣人之道,也有天地万物之理。
“法”与“辞”,实为“文”的两个层面,“法”指的是文章的内在结构(章法),“辞”指的是文章的外在表达(语言)。先说“法”,在上文之后,戴名世进一步解释说:
且夫道一而已,而法则有二焉:有行文之法,有御题之法。御题之法者,相其题之轻重缓急,审其题之脉络腠理,布置谨严,而不使一毫发之有失,此法之有定者也。至于向背往来,起伏呼应,顿挫跌宕,非有意而为之,所云文成而法立者,此行文之法也,法之无定者也。[1]卷四《己卯行书小题序》:109
这里讲到时文有二法:行文之法,御题之法。所谓“御题之法”,就是围绕文题而展开的八股文法,比如破题、承题、起讲、入题、分股、收结等程式要求,所谓“扼题之要”、“尽题词之趣”、“极题之变”是也[1]卷四《丁丑房书序》:93,像李元春《四书文法摘要》、高塘《论文集钞》、路德《仁在堂论文各法》都有此类论述。所谓“行文之法”,涉及到文章内在层面的“向背往来、起伏呼应、顿挫跌宕”等,这类文法是从文章产生以来渐以形成的,是古文之法在时文中的具体表现。它是在文本生成之后而确立的,并非有先在的格式或要求,所以说它是法之无定者。对于“御题之法”,戴名世论述不多,对于“行文之法”则有较多强调。他说:“余又以为文章者,无一定之格也,执一格以言文,而文不足言矣。”[1]卷四《浙江试牍序》:127他反对拘于一格的做法,认为这样会造成溺于世俗腐烂雷同之习,失去作者的个性。“今夫时文之弊,在于拘牵常格,雷同相从,习为判圣侮经之言,而时莫悟其非。”[2]卷二《归熙甫稿序》:53他认为“行文之法”犹如人之体态,不能预先设定,是文成而法立。“夫文章之事,千变万化,眉山苏氏之所谓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其驰骋排荡,离合变灭,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既成,视之,则章法井然,血脉贯通,回环一气,不得指某处为首,某处为项,某处为腹,某处为腰,某处为股也。而方其作之之时,亦未尝预立一格,曰此为首,此为项,此为腹,此为腰,此为股。天之生人也,妙合而凝,形生神发,而必预立一格以为人,曰:如是以为首,如是以为项,如是以为腰腹,如是以为股肱手足也,而人之生者少矣。故曰:文章不可以格言也,以格言文而文章于是乎始衰。”[1]卷四《小学论选序》:91
很显然,“法”有定与不定之分,前者是文章的骨架,后者才是文章的生命;前者更多体现为时文的外观,后者则是古文之法在时文中的表现。因为,人们对时文文法有不同理解,在时文写作中便形成了“凌驾”与“铺叙”两派。他说:“铺叙者,循题位置,自首及尾,不敢有一言之倒置,以为此成化、弘治诸家之法也。凌驾者,相题之要而提挈之,参伍错综,千变万化而不离其宗,以为此史、汉、欧、曾之法也。于是言铺叙者则绌凌驾,言凌驾者则绌铺叙,两者互相诋訾而莫之有定。”[1]卷四《丁丑房书序》:93所谓“铺叙”就是依八股文程式写作,所谓“凌驾”,就是围绕主题,反复盘旋,力求变化,不拘一格,然变化却不离其宗(主题)。戴名世主张在掌握了“铺叙”之法后,应该以追求“凌驾”为目标所在。一般说来,铺叙之法便于不学无文之人,不过循题位置,寻讨声口,兢兢不敢失尺寸,舍史、汉而取法于成化、弘治,于理道曾不能有毫发之发皇;而凌驾之法则要求更高,必扼题之要,尽题之趣,极题之变,洞悉乎题之理,而无用之卮辞,不切之陈言,无所得入乎其间,这才是真正的“以题还题”。
再说“辞”,戴名世认为它有古今之分:“古之辞,左、国、庄、屈、马、班以及唐宋大家之为之者也;今之辞,则诸生学究怀利禄之心胸之为之者也。其为是非美恶,固已不待辨而知矣。”古之辞就是古文辞,今之辞就是时文之辞,他认为古之辞清真驯雅,精纯正大,今之辞多是以“相与扬眉瞬目以求得当于场屋”的利禄之心为之,出言吐词,非鄙则倍。“且其所为鄙倍者,又非尽出所自造,而雷同剿袭,大抵老生腐儒之唾馀,雄唱雌和,自相夸耀”[1]卷四《己卯科乡试墨卷序》:95。对于辞,不但要求“雅”,而且要求“洁”。所谓“洁”,就是言简意赅,旨远辞微。这一点则得之史家之文法。“易曰:‘其旨远,其辞文’,以太史公之雄杰,覆冒百家,而柳子厚蔽之以一言,曰‘洁’。然则修辞之道,莫贵于洁矣。洁者,即予之所谓旨远而辞文者也。”[2]卷八《浙江教条》:478
较之艾南英强调文与道,戴名世更重视道与法的关系,认为文者所以载乎道也,而行文又不能以无法,“今兹之得之者,何其于道之一无所发明而适形其乖以舛也”?他谈到自己编选《九科墨卷》,其主要标准就是要体现“道”与“法”:“余之选之者,选其与道与法合者,即不尽合,而犹有所依据,而不致畔而去之远,且或背于道而犹有法之可观,与法之不合而道犹不至于大失者,皆余选之所不遗也。”[2]卷八《九科墨卷序》:503但在道与法合的前提下,还要重视“辞之修也”,亦如孔子所云“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夫言之行世而垂远者,则又不可以无文。君子冥心孤诣,其于古人之载籍,沉浸浓郁,得其精华而去其糟粕。举笔为文,洒洒自远,虽历年之多而常薪不敝,此所谓择言而精者也。”[1]卷四《己卯科乡试墨卷序》:95道、法、辞三者合一,才是文之最高境界。
在辨明道、法、辞三者关系后,戴名世又提出了精、气、神三者合一的观点。他说:
盖余昔尝读道家之书矣,凡养生之徒从事神仙之术,减虑绝欲,吐纳以为生,咀嚼以为养。盖其说有三,曰精,曰气,曰神。此三者鍊之,凝之,而浑于一,于是外形骸,凌云气,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飘飘乎御风而行,遗世而举远,其言云尔。余尝欲学其术而不知所从,乃窃以其术用之于文章。呜呼!其无以加于此矣。[1]卷一《答伍张两生书》:4
很显然,他的观点是受道家思想启发而提出来的,对于“精”、“气”、“神”的理解亦须从道家论述说起。道家从天人合一和天人相通的观念出发,指出天有三宝“日、月、星”。人亦有三宝“精、气、神”。“精者,滋身者也;气者,运于身者也;神者,主宰一身者也”。“人身精实则气充,气充则神旺。精虚则气竭,气竭则神逝”[5]。戴名世认为道家所谓神仙之说并不可信,但其养生之术却可以用来讨论文章,也就是说他把一篇文章视作为一个生命整体。对于文章来说,所谓“精”,指的是文辞之凝炼:“雅而清”。“太史公纂《五帝本纪》,‘择其言尤雅者’,此精之说也。蔡邕曰‘炼余心兮浸太清’,夫唯雅且清则精。精则糟粕、煨烬、尘垢、渣滓,与凡邪伪剽贼,皆刊削而靡存,夫如是之谓精也”[1]卷一《答伍张两生书》:4。何谓“气”?就是文章的气势。他用了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而有物焉,阴驱而潜率之,出入于浩渺之区,跌宕于杳霭之际,动如风雨,静如山岳,无穷于天地,不竭如江河,是物也,杰然有以充塞乎两间,而盖冒乎万有。呜呼,此为气之大过人者,岂非然哉!”[1]卷一《答伍张两生书》:4所谓“神”,就是文章的神韵,实为一个生命的外在表征,它寄之于文章却又不见其形迹。在他看来,通常所说的“文”是“语言文字”,“行墨蹊径”,“非所以文也”。“文之为文必有出乎语言文字之外,而居乎行墨蹊径之先”。好比九方皋之识马,人见之为牝而黄,他视之则是牡而骊,盖其识马非以形而以神也。“夫非有声色臭味足以娱悦人之耳目口鼻,而其致悠然以深,油然以感,寻之无端而出之无迹者,吾不得而言之也,夫唯不可得而言,此无所以为神也”[1]卷一《答伍张两生书》:4。他还以人之魂魄为例,指出有形的“行墨字句”为“魄”,无形的出乎语言之外的“魂”才是“神”。“今夫文之为道,行墨字句,其魄也;而所谓魂也者,来之不觉,视之而无迹者也。……呜呼,文章死生之际,在于有魂无魂之间。而执魂之一言以观世俗之文,则洋洋大篇,足以哗世而取宠,皆僵而腐而已,而岂可以谓之文乎?”[1]卷二《程偕柳诗序》:28文章的生命在其是否有“魂”,那么哗众取宠的洋洋大篇,尽管也有语言文字,行墨字句,却只是毫无生命意义的僵尸腐肉而已。
四、“自然之文”与“自成一家”
文章从构成看有“道”、“法”、“辞”,从体征看有“精”、“气”、“神”,从外在表现看则有“自然之文”与“雕饰之文”之分。戴名世在35岁那年所作的《送萧端木序》中说:
盖余平居为文,不好雕饰,第以为率其自然而行其所无事,文如是,止矣![1]卷五《送萧端木序》:134
这里讲到的“自然”与“雕饰”,也就是刘勰所说的“为情造文”与“为文而文”,戴名世强调作文应以性情为本经史为根柢。他说:“夫文章者,出于性灵之所为,此心此理,天下之所同也,而何以应试之士,自十百而千万,操笔为文,卒不得所为性灵焉?”[2]卷九《浙江试牍删本序》:534如果以性灵为之,创作时自然是为情所驱使,而非以习见所蒙蔽。他曾有文描述自己进入创作的状态是:“当夫含毫渺然意象之间,辄似为一境,以为追其所见。其或为海波汹涌,风雨骤至,瀑泻岩壑而湍激石也;其或为山重水复,幽境相通,明月青松,清冷欲绝也;其或为远山数点,云气空濛,春风淡荡,夷然翛然,远出于尘外也;其或为江天万里,目尽飞鸿,不可涯涘;其或为神龙猛虎,攫孥飞腾,而不可捕捉也;其或为鸣珂正笏,被服雍容;又或为含睇宜笑,绝世而独立也。凡此者,要使行墨之间,仿佛得之。”[1]卷四《意园制义自序》:123这就是率其自然,就是水到渠成,就是苏轼所说的“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在戴名世看来,为文之法,虽然变化不同,而为文之本旨非有他也,第在率其自然而行其所无事。“即至篇终语止,而混茫相接,不得其端”[1]卷一《与刘言洁书》:5。这一原则是自左、庄、马、班以来便已达成的,并且诸家之旨未之有异也,只是今之为时文者遗弃了这一原则。他不禁感慨道:“何独于制举之文而弃之?”[1]卷四《李进潮稿序》:105
当然,这样的自然之文,对于作者来说,有比较高的要求。只有学养深厚、人格高尚的正人君子才能进入这一境界。“君子之文,淡焉泊焉,略其町畦,去其铅华,无所有乃其所以无所不有者也”。他还以自己经历为比,说明只有历经千难万险才能走进这一境域。“仆尝入乎深林丛薄之中,荆榛罥吾之足,土石封吾之目,虽咫尺莫能尽矣,余且惴之焉惧跬步之或有失也。及登览乎高山之巅,举目千里,云烟在下,苍然,芒然,与天无穷。顷者游于渤海之滨,见夫天水浑沦,波涛汹涌,惝恍四顾,不复人间。呜呼,此文之自然者也”。他把这种自然之文的审美特征概括为:“质”与“平”。“质”就是朴素自然,“平”就是巧夺天工,亦即:随物赋形,不事雕饰。“莫质乎素,而本然之洁,纤尘不染,而采色无不受焉。莫平于水,而一川泓然,渊涵渟蓄,及夫风起水涌,鱼龙出没,观者眩骇。是故于文求文者非文也,于奇求奇者非奇也”。做文不是从文中求文,也不是从奇处求奇,而是顺乎性情,自然天成而已。从这个角度讲,“质者,天下之至文者也;平者,天下之至奇者也”[1]卷一《与刘言洁书》:5。
但是,在当时,整个科场之文充斥着趋时之作,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表现:“雷同”。“曩者文章之风气,亦尝萎?卑弱而不振矣。儒先之精义不明,古文之规矩尽裂,上之人所以取于下,下之人所以献上者,皆雷同相从而已”[1]卷一《再上韩慕庐大宗伯书》:9。这看似只是文章风气,其实也关乎士风,是士风的不正造成了文风的败坏。“士风之敝也,侥幸苟且之术……即其于文字一道,随时俯仰,雷同相从,恬不为耻,所谓黄茅白苇,弥望皆是。挟其区区雷同之技,欲于数十百千人之中求得当于场屋,不得则怨且怒,此其人品心术可知矣”[2]卷九《考卷选序》:630。他在多处撰文描述今之才士的媚俗之态,或是“习剽窃之文,工侧媚之貌”,或是“奔走形势之途,周旋仆隶之际,以低首柔声乞哀于公卿之门”。何以致此?戴名世分析了他们这样做的心理是:“雷同也而喜其合时,便佞也而喜其适己,狼戾阴贼也而以为用。”[1]卷五《送蒋玉度还毗陵序》:135在他看来,考官对文风的转变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如果司教者之不得人,因循怠废,溺于世俗腐烂雷同之习,则士无以发其曚,开其聩,愈益汩没败坏,“而文章之事遂至于举一郡一邑而失其传”[1]卷四《课业初编序》:127。这说明是司教者的因循怠废,造成了世俗的雷同之习,士子在科试时只取速成,写出来的文章自然是雷同腐烂。“自世俗趋于雷同,士之所作皆若出于一手然者,主司于此,虽欲操衡量定其短长轻重,而已困于锱铢毫发之间,故其录者未必果胜于弗录者”[1]卷二《四家诗义合刻序》:35。而在时文走向全盛的明代隆庆、万历时期,却不是这样的。“当是时,人人自为机杼,不相剿袭,其品格之高下,辞章之雅郑,波澜之大小,皆一一自呈露于行墨之间”[1]卷四《闽闱墨卷序》:126。在戴名世看来,其时之典范就是归有光,“震川之时文一以古文之法为之者也”[2]卷二《归熙甫稿序》:53,正如上文所说,归氏之文,有自然之美,为天下至文。
与反雷同相对,他标榜“独得”,要求不从俗,“自成一家”。他说:“百工技艺之为其事,必有所用力焉而自得于心。”他特别赞赏顾和达,“当是时天下文章陋矣”,却能掉臂独行,不从流俗,不趋时好,全力为之,利其器,精其技,“所谓有所用力焉而自得于心”[2]卷十《顾希才稿序》:681。他认为“士之读书而为文章”,不肯雷同诡随,以趋时俗之所好,这是江南地区文风的重要传统。“居常被服古人,闇然自晦,不求人知,盖犹有先民遗风焉”[1]卷三《梅文常稿序》:71。他自己也是这一传统的维护者,不为时好所动,因此遭到人们的嘲弄。“始余居乡年少,冥心独往,好为妙远不测之文,一时无知者,而乡人颇用是为姗笑”[1]卷三《方灵皋稿序》:53。但他始终不为时趋所动,以求自得之心,而为一家之言。“窃尝有志,欲上下古今,贯穿驰骋,以成一家之言,顾不知天之所以与我者何如,妄欲追踪古人”[1]卷三《初集原序》:59。对自己的“一家之言”,“妙远不测之文”,他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远山缥缈,秋水一川,寒花古木之间,空濛寥廓,独往焉而无与徒也。”[1]卷二《成周卜诗序》:40但是,这样的“一家之言”,却与世俗时趋格格不入。世俗之文不过是记诵熟烂之辞,互相钞袭,恬不知耻,但在当时却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苟有异己者之出于其间,辄相与诽笑诟厉,不壅蔽遏抑之不已。”[1]卷一《与白蓝生书》:17尽管如此,他不改初衷,一如既往,对于友人时文的批评亦如是。比如他论方舟、方苞,赞扬他们为文皆原本于左、史、欧、曾,“其所造之境诣则各不相同也”[1]卷三《方百川稿序》:51。另一位友人赵傅舟,他的文章亦有不尽谐于世俗者。“余尝称其文殆如古人,所云欲语羞雷同者,而骖期亦久困公车”[1]卷四《赵傅舟制义序》:120。还有郑允石的制义,“能自出机杼,不蹈科臼,卓然自成一家之言”[1]卷四《郑允石制义序》:110。特别是高明水、高念祖父子,在晚明文运波靡之时,以清真刻露之文拄其间,“真意独出,不染时解”。这样的文章是天下至文,因为它有自己的独得之见,不趋时俗。他不禁发出这样的慨叹:“余得高氏父子之遗文,益知文章之真伪所由别!”[1]卷三《高工部两世遗稿序》:73至文标准就是一个字:“真”。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对戴名世的时文理论有了大致的认知,并注意他是以古文观念来总结时文理论的,有一种将古文论与时文论相打通的倾向。但必须说明的是,我们过去把戴名世对于时文问题的论述,当作他的古文理论来讨论,却是不妥的。尽管他确实有以古文为时文的提法,并力主以时文行古文之法,但他的论述重心毕竟还是放在时文上面,基于这样的认识,这篇论文的目的是力图还原戴名世文学思想的历史原貌,即“以古文论为时文论”。
[1]戴名世.戴名世集[M].王树民,编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2]戴廷杰.戴名世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2004.
[3]韩愈.韩昌黎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59.
[4]柳宗元.柳河东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358.
[5]徐文弼.寿世传真:卷3[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19.
10.16366/j.cnki.1000-2359.2016.01.031
2015-07-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BZW067)
I206.49
A
1000-2359(2016)01-0159-07
陈水云(1964-),湖北武穴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文学与文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