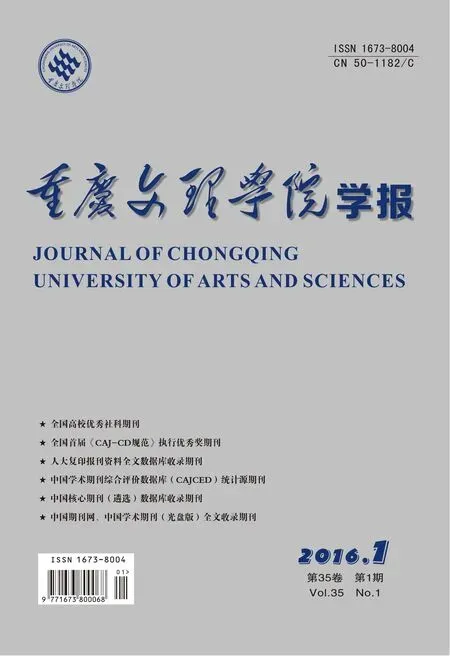关于“非遗”保护三个基本问题的话语分析
范生彪,何荣誉(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恩施445000)
关于“非遗”保护三个基本问题的话语分析
范生彪,何荣誉
(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恩施445000)
【摘要】话语研究不仅关心人们如何言说,而且更为重视分析决定言说方式的深层动因。“非遗”保护既是一个社会各阶层权力角逐的场域,又是一个可通过不断协商达成共识的平台。人们对于“非遗”保护的认识人言言殊的根本原因在于参与“非遗”保护的社会各阶层各自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非遗”保护工作正是在争论中逐渐确立了自身的工作目标、指导原则、实施方案,体现了极强的话语建构性。“非遗”作为一种传统生活方式的隐形载体,活态传承性是其精髓与灵魂;“非遗”保护必须以人为本,只有让“非遗”与现实的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发生联系和耦合,“非遗”保护才可能取得实效。
【关键词】“非遗”保护的价值与目的;“非遗”保护的原则与措施;“非遗”保护的主体与权益
“非遗”保护这一具有重大历史影响的理论话语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半个世纪以来在探索保护文化多样性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而提出的。2003年,该组织在巴黎召开的第32届会议上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下文简称《公约》),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它具体可分为五部分:一是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二是表演艺术;三是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四是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五是传统手工艺。《公约》还明确了非遗保护的意义,认为是“文化多样性的熔炉和可持续发展的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密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进行交流和了解的要素,它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目前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人类社会普遍的意愿和共同关心的事项。
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观念的界定是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的理论阐发为基础的。中国政府作为国际教科文组织的缔约国,也于2005年底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该通知结合国情厘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在语言哲学的“现象学—解释学”视域下,话语不仅是一种社会实践行为,同时还是社会主体权利角逐的场域,因而具有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重属性和涵义。为深入地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很有必要厘清“非遗”保护的价值与目的、原则与措施、主体与权益这三个基本问题。
一、“非遗”保护的价值与目的之论争
《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从宏观的角度强调了“非遗”保护对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意义:“我国文化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各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全人类文明的瑰宝。保护文化遗产,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是联结民族情感纽带、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的重要文化基础,也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前提。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由于“非遗”保护的价值和目的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因果关系,对于“非遗”保护不同的价值认知决定了不同的非遗保护的目标设定。为了推进非遗保护工作,首先需要深化对“非遗”保护的价值和目的的认识,目前学界对于“非遗”保护的价值和目的有两种主要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非遗”的本质不过是一种文化精神,其物质外壳无非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首先,随着时代的进步,新文化的创生和旧文化的湮灭是最正常不过的。因为文化源于社会生活,而生活每天都在改变。当一种文化存在的社会现实基础消失之后,文化的消亡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而“非遗”之所以有价值,只是因为在物质产品极为丰富的现代消费社会中,商品的市场核心竞争力取决于商品的符号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一种可以赋予商业品牌以深厚的文化底蕴,提升其符号价值,从而带来超额商业利润的稀缺资源。因此“非遗”中只有那些能够转化为当下的文化资源,具有现实或潜在经济开发价值的部分才是值得保护和传承的,“非遗”的其余部分属于丧失了生命力的非活态的文化遗存,尽可任其自生自灭。理由很简单,开发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用,任何投入都需要产出。取之于民的“非遗”保护工作不应该采用博物馆陈列室式的静态保护策略,而应采用创造性、分馏式的文化精神内核的萃取与从无到有滚雪球式的文化符号生产相结合的选择性保护策略,能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这样看来,“非遗”保护的商业化乃至产业化运作是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其次,“非遗”保护工作政府投入的政绩追求和民间资本的逐利行为与文化传承的美好初衷之间的博弈并非零和。资本的本质属性是要不断地实现自我增值,而多数情况下,成功运作的“非遗”保护工作的确既能为地方政府创造良好的政绩,又能为介入“非遗”保护的商业资本赚取高额利润,同时“非遗”保护工作自身还因得到了商业资本的反哺会逐渐获得自我造血功能而实现可持续发展。因为靠打“非遗”保护文化牌的成功企业只有通过源源不断地把资金投入“非遗”保护之中,通过借船出海的方式在扩大“非遗”的社会影响力的同时扩大自己商业品牌的知名度,才能实现提升商业品牌价值和利润的终极目标。2001年联合国通过的《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其实也是赞同这种思路的。其中第9条指出:“文化政策应当在确保思想和作品自由交流的情况下,利用那些有能力在地方和世界一级发挥其作用的文化产业,创造有利于生产和传播文化物品和文化服务的条件。”
另一种观点认为,“非遗”作为一笔具有巨大科学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的人类社会的精神财富和无形资产,能够真实地、完整地还原和复制出来本身就是最大的成功。所以“非遗”保护需要有超越现实功利考量的眼界和长远的眼光,通过经常的、长期的、政策性的大投入,采取无差别的整体保护措施,致力于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和本真性的保护。这样说的理由很简单:首先,“非遗”作为一种已经或即将逝去的社会生活方式,具有保存人类生活方式多样性的核心价值,能为未来人类社会的文化创新提供具有本真性的材料和保存最具原创性的灵感,维护全人类文化生态的安全;其次,“非遗”能够起到维系特定族群的文化价值认同与实现文化身份延续的作用,因为“非遗”是居住在特定时代和地域的人们创造出的与其社会生产水平相适应的特殊生活方式,是人类生存智慧的历史结晶,现实地促成了特定国家、族群或社区的特定社会文化空间意义的自我生产,具有普遍的人类学研究价值。正因为文化的演进是通过吐故纳新的扬弃实现的,文化创新的不竭动力来源于生长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现实文化土壤,所以“非遗”保护就是保护文化多样性的一条有效途径,任何对“非遗”的开发和复制都是毁灭“非遗”真实性的造假行为,都与“非遗”保护的初衷南辕北辙,是不能容忍的行为。孙家正在《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总序中曾经谈到:“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各国传统文化不同程度的损毁和加速消失,这会像许多物种灭绝影响自然生态环境一样影响文化生态的平衡,而且还将束缚人类思想的创造性,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及社会的全面进步。”[1]另外,2002年《伊斯坦布尔宣言》也把导致“非遗”传承的困境归结为:“主要因冲突,不宽容,极端重商主义,无控的城市化或乡村的衰败等原因,无形文化遗产面临消亡或边缘化的危险。”
在笔者看来,“非遗”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系统,除具有人类学研究的科学价值、文化寻根的历史价值、审美日常生活化的艺术价值之外,还应具有现实地介入和改造当下社会生活的实践功能。事实上两派观点各有其片面和深刻之处,在“非遗”保护实践过程中,这种观点实际上是相辅相成、可以调和互补的。
二、“非遗”的保护原则与措施的论争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签署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非遗”保护做了明确的界定:“‘保护’指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各种措施,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2005年制定的《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阐明了我国“非遗”保护的原则是“坚持保护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坚持依法和科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措施是“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统筹规划、分类指导、突出重点、分步实施。”对于“非遗”保护的大前提和基本原则学界都不存在分歧,分歧主要在于如何合理利用和传承发展。
主流的“非遗”保护主张倾向于采取维持“非遗”原貌的静态保护措施。这种观念认为,根据“非遗”保护的本真性和完整性原则,“非遗”保护应该反对任何形式的商业开发。“非遗”保护过程中即便是抢救性的“非遗”保护,也需遵循本真性原则和文化时空统一的整体性原则,坚持修旧如旧,尽量减少“非遗”在情景再现和景观复制过程中的修饰与创新,确保“非遗”的本真性与历史性。放眼世界,欧洲发达的农业文化观光旅游是这种“非遗”保护行为结出的硕果。从“非遗”保护的制度设计层面考量,法国、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值得借鉴。曹新民教授在《非遗保护模式研究》一文中指出:法国自1793年以来通过一系列完备的立法实现了物质文化遗产的全方位保护,大量完好的具有悠久历史的物质文化遗存,间接实现了“非遗”的系统保护。日本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制定了3部保护文化遗产的法律,1950制定的《文化财保护法》首开用法律明确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先例。1954年修订的《文化财保护法》明确规定了无形文化遗产保持人的认定制度,新增了无形民俗资料记录保存制度。1996年第4次修订的《文化财保护法》又增订了文化遗产登录制度,完善了政府主导的文化遗产登记制度这一针对“非遗”的法律保护措施。韩国“非遗”保护的制度创新在于推出了重点扶持传承人的制度,整合了政府、团体组织、社会公众的力量,国家通过制订一系列制度、奖励办法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韩国于1962年制定了《文化财保护法》,把握住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特点,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延绵传承有了保障,建立了最具特色和效用的金字塔式的文化传承人制度[2]。据此看来,无论是政府以政绩为导向的“非遗”申报保护“大跃进”式的文化扩容,还是民间“非遗”保护商业运作的文化拼贴都是对“非遗”的致命伤害。“非遗”保护应该是由政府主导、财政投入、专家操盘的基础性国家公益文化建设事业。“非遗”保护工作应以法律的常态保护为主,适当结合政府的行政保护,从而把法律保护的长效机制与政府保护极强的行动力有机地结合起来。
带有新历史主义色彩的“非遗”保护主张倾向于“非遗”保护应致力于遗貌取神的动态开发传承。因为“非遗”保护的目的是古为今用,服务于现实的精神文化生产。“非遗”的精髓是一种活态的文化精神,应该因地制宜,因时而变。正如历史的讲述形成历史知识谱系一样,“非遗”保护理念的形成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话语建构过程。“非遗”的活态传承在滚雪球般的层累过程中,由于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互文性引用和创造性转换,必然会导致其文化源流的多源性和文化内涵的异质性,这样想要对“非遗”进行文化溯源和本真性考察简直就是一个荒谬且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非遗”保护只能以开放的心态,用具有文化创意的方式物化和张扬“非遗”所包含的文化精神,实现活态传承和振兴的目标。只有采用这种富有创造性的“非遗”保护策略才能真正起到沟通古今,促进社会族群和社区的文明和谐,提升文化创新能力的作用,实现“非遗”保护的初衷。创造性的“非遗”保护工作目前国内外也有许多经典案例。德国近些年就打造了以格林兄弟的童话故事为核心的全程600多公里的大型体验式景观文化旅游项目——“格林大道”。这个誉满全球的文化景观旅游项目成功的秘诀就在于实现了“非遗”保护与当代社会生活高雅的精神文化消费需要的适时对接。又如日本冈山市以民间传说“桃太郎”的故事为文化内核,综合雕塑、电影、网络、游戏等文化传媒手段,让“非遗”以极具文化亲和力的方式走进现代人的生活世界,成就了冈山市旅游名城的奇迹[3]。再如我国湖北建始的清江画廊——武陵钟离山的民族文化风情旅游景区的横空出世也正是得益于“非遗”文化资源的深度发掘与创造性的景观再现。正如新历史主义主张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样,一切“非遗”的保护其终极目的也是服务于现实生活的文化意义的生产。杰姆逊2012年在北大作了一场关于《奇异性美学》的演讲,其中的一些观点对理解以上具有新历史主义倾向的“非遗”保护主张很有帮助。杰姆逊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后现代时代,由于土地的商品化和残余的封建制以及农民阶层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工业农业、农业商业以及农场工人。对于这些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大超市消费者来说,其生存体验感是一种空间对时间的征服:一切文化经验简化为——当下和身体。新的此刻已成为后现代的标志,一切都停留在此刻和身体里。在这新的无处不在的空间和短暂此刻的辩证法里,历史、历史性以及对历史的感觉都成为失败者。过去已经不存在,未来却无法憧憬。因为迟缓的乡村时间和令人眼花缭乱的都市及工业化节奏共存的情况已经让位于同一性和标准化。金融资本和现代信息技术让空间的距离正不断地翻译为时间实际存在的共时性,也就是说空间正在消除时间。后现代生存状态下人们生活的现实的历史性在存在层面和集体精神层面的意义丧失殆尽,我们对未来失去思考和想象的能力,而我们的过去要么化为尘埃,要么只在好莱坞电影里那些戴着假发的演员身上瞥见一二。人们集体行动能力的消失,只缘我们日益变得冷漠、玩世不恭、麻木和压抑。我们的文化艺术消费对象不再是纯粹的视觉和材料艺术,而是其中的观念。能进入人们欣赏视野的东西不是由于其具有恒久的价值和普遍性意义,而是由于其转眼即逝的易变性、无法归类的奇异性和无法参透的观念性[4]。创造性的“非遗”保护策略是对这种空间征服时间的令人窒息的后现代文化的迎合与反抗,因此它的勃兴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笔者认为“非遗”作为一种精神性存在,既具有自己内在的特征,又具有一定的话语建构性。“非遗”保护需兼顾以上两种主张,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换言之,“非遗”保护既要坚持本真性原则,追求情景还原要契合历史的真实的形似,讲究“非遗”保护、传承的原汁原味;更应追求对杂芜的历史文化现象进行提纯,以求得“非遗”文化保护和传承的离形得似的神似;还需要通过适当的话语建构,创造性地阐释和解读“非遗”的文化内涵和意义,引领时代的发展方向。
三、“非遗”保护的主体与权益的争议
“非遗”保护作为一种需要巨额投资和可能产生巨大经济收益的文化事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需要明确“非遗”保护的主体是谁,界定保护者相应的权利与责任。
主流的“非遗”保护观点倾向于认同“非遗”保护的主体是政府。各级政府应该担起所辖区域“非遗”保护的全部责任,并享有完整独立的管理权,但是各种级别的“非遗”保护所产生的利益应属于相应级别的“非遗”属地的全体民众。因为政府是国之公器,各级政府投资“非遗”保护使用的是纳税人的钱,所以权力和收益属于人民。“非遗”保护是一种涉及国家文化安全的公益事业,其投入根本无需考虑是否具有盈利性。如果让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其中并取得主导地位,就可能偏离“非遗”保护的初衷,唯利是图。持论者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早已在制度设计层面明确地肯定了政府在“非遗”保护中的主体地位。《公约》第13条的其他保护措施条款规定,为了确保其领土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保护、弘扬和展示,各缔约国应努力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制定一项总的政策,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并将这种遗产的保护纳入规划工作;第二,制定或建立一个或数个主管保护其领土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机构;第三,鼓励开展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技术和艺术研究以及保护方法研究;第四,采取适当的法律、技术、行政和财政措施,以便促进培训和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机构的形成,通过为这种遗产提供活动和表现的场所和空间,促进这种遗产的承传;第五,确保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享用,同时对享用这种遗产的特殊方面的习俗做法予以尊重;第六,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机构并创造条件促进对它的利用。
另一种非主流的“非遗”保护思路强调,“非遗”保护活态传承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保护的终极主体不应是政府,而应是认可这种文化价值的族群、部落、社区或者个人。政府不能也不应该成为“非遗”保护的主体,政府在“非遗”保护工作中扮演的角色只能是助手和服务员。政府的主要责任应该偏重于搭建好“非遗”保护的平台,做好诸如“非遗”保护的调查、规划、规范和指导等基础性工作,推动“非遗”的文化传播,让更多的公民濡染和接受“非遗”文化提供的多样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非遗”保护是一项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价值和意义的系统工程,只有举全社会之力才能办好,因此需要多元的保护投资主体。任何“非遗”保护的投资主体要依法办事,遵循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平等享有从“非遗”保护投入中受益的权利。多元的“非遗”保护投资主体的唯一义务是依法投资和规范运作。
新思维者同样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找到了根据。《公约》第14条明确规定了各缔约国应竭力采取种种必要的手段加强“非遗”的教育、宣传和能力培养,以便达到以下三个目标。第一,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会中得到确认、尊重和弘扬。这主要通过以下四种途径完成:一是向公众,尤其是向青年进行宣传和传播计划;二是有关群体具体的教育和培训计划;三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和科研方面的能力培养活动;四是非正规的知识传播手段。第二,不断向公众宣传对这种遗产造成的威胁以及根据本公约所开展的活动。第三,促进保护表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需的自然场所和纪念地点的教育。《公约》第15条的群体、团体和个人的参与条款还规定:缔约国在开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时,应努力确保创造、保养和传承这种遗产的群体、团体,有时是个人的最大限度的参与,并吸收他们积极地参与有关的管理。
“非遗”保护在笔者看来需要由政府主导,多元保护主体参与,参与主体应该平等享有依法根据投入多少和贡献大小获得相应回报的权力。因为“非遗”保护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政府才具备这种巨大的社会动员和组织管理能力,才能源源不断地为“非遗”保护组织提供人力、财力、物力等全方位的支持,所以“非遗”保护工作必须由政府主导。但是现代政府的职能定位在于为社会公共事业搭建服务平台和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宏观管理,因此要求政府包办作为社会公共事业和事务的“非遗”保护工作是不现实的,“非遗”保护需要动用全社会的力量,让更多的保护主体参与到“非遗”保护之中。由于“非遗”保护工作运作得好也可成为一个具有很高经济回报率的事业,因此多元的保护主体需要履行遵守“非遗”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义务,同时根据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分享相应的“非遗”保护的红利。需要强调的是,“非遗”作为一种可以再生、创造和丰富的精神性存在,其价值实际上是一种体现某种文化内涵的符号价值。因此“非遗”保护不能采用垄断使用权和受益权的专利保护方式,相反还需要宣传推广,让更多的人群接纳、欣赏、自觉践行。同时,“非遗”作为相应文化属地的一种公共的社会精神财富和文化资源,不应被任何“非遗”保护主体所垄断。“非遗”保护主体专有的只能是那些属于自己独创的衍生性的次级“非遗”财富。“非遗”保护的终极目的是促进有普遍价值和独特底蕴的地域历史文化的活态传承,为未来人类社会的文化创新提供多样化的文化基因和资源,守护人类的精神家园,因此必须以人为本,以精神价值为先导,以文化的活态传承为目标。综上所述,“非遗”概念的形成是话语实践的产物,“非遗”保护既是一个社会各阶层权力角逐的场域,又是一个可以通过不断的协商达成共识的平台。梳理分析“非遗”保护争论的主要问题,我们不难发现“非遗”保护本身具有话语建构性。正因为“非遗”作为一种传统生活方式的隐形载体,活态传承性是其精髓与灵魂,所以“非遗”保护必须以人为本。
参考文献:
[1]孙家正.《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总序[C]//王文章.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2]曹新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研究[J].法商研究, 2009(2):75-84.
[3]林继富.非物质文化遗产基因保护探讨——以清江流域土家族始祖信仰为例[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43-47.
[4]杰姆逊.奇异性美学[J].蒋晖,译.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1):9-17.
责任编辑:黄贤忠
The Discourse Analysis of Three Essentialities in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AN Shengbiao, HE Rongyu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Hube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Enshi Hubei 445000, China)
Abstract:Besides manner of speaking, the study of discourse pays more attentions to the deep motivation of the speaking way.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not only a field of social strata power play, but also a platform where consensus can be reached through constant consultation. Every stratum of society has its special interests express, which leads to the different views on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as a strong discourse construction, and it established its own work objectives, guiding principles, implementation plant through continual consultation. As a non - contact carrier of the traditional lifestyle, the core idea of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flexible transmission. The essence of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to put people first. Only to let the heritage and the reality of people’s daily life contact and coupling, that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an be developed continuously.
Key words:value and purpos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body and rights
作者简介:范生彪(1972—),男,湖北利川人,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何荣誉(1984—),男,湖北监利人,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5-09-08
中图分类号:F59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04(2016)01-00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