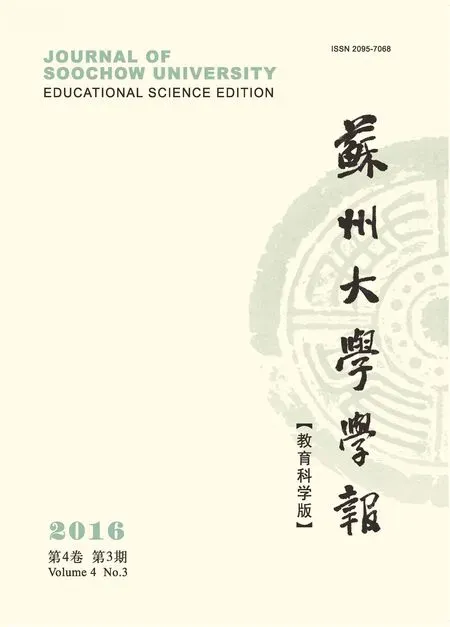多学科视域下的高校内部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
齐 明 明
(成都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051)
多学科视域下的高校内部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
齐 明 明
(成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成都610051)
高校内部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是对权力正常运行的支持与保障,对权力偏离轨道的防范与纠正。从多学科的研究视角出发,可以更为深刻地认识高校权力属性和权力内在制约原理,为高校内部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模式的构建提供理论支持。伦理学对人类本性的研究,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对权力特质的研究,为高校内部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供了逻辑论证基础。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从本学科研究视域出发,所提出的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的一般制约模式,为高校内部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机制的构建提供了实践借鉴意义。
高校内部权力运行;多学科视域;制约模式
高校内部权力制约与监督既具有权力制约与监督的普遍性,又受高校组织属性的限制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一方面,高校内部权力结构具有权力的共同属性,如工具性、强制性、排他性、扩张性、侵犯性、腐蚀性等,当权力的负面特性与高校权力主体作为人的不完善性相结合时,高校权力腐败现象频繁发生;另一方面,高校以党委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为核心的多元权力结构,使得高校内部权力运行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挑战。
一、高校内部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的必要性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权力一方面具有积极的正效应,同时又具有消极的负效应。从消极方面来看,“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1]342。公共权力具有普遍的被非公共运用的倾向,即使是在探求真理、传授知识的高校也无法回避权力腐败问题,这是由权力潜在的负面特性和人性的不完善所决定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对权力特性的研究和伦理学对人类本性的研究构成了为权力制约与监督必要性及可行性的理论基础。正是人与权力二者之间的互动催生了各种腐败问题,而对权力制约与监督的必要性也要以对二者的深刻认识为根本出发点。
(一)权力的工具性与私人主体属性相结合滋生权力腐败
权力具有工具性,它可以调动社会资源为一定的目的服务,权力的背后代表的或公开或隐蔽的利益。社会资源的分配一方面涉及组织需求和组织利益,另一方面又与权力行使者的个人利益相联系。当组织利益和个人利益诉求不一致时,很可能引发利益冲突。由于组织自身不能运用组织的权力,组织权力的运行和使用需要一定的私人载体,权力的私人主体属性需要有具体的个人来承担,因此权力运行过程必然受到掌权者个人意志的影响和作用。当掌权者将个人的意志和愿望掺杂到权力运行过程中,并为追求个人私利而背离组织的利益甚至危害组织利益的时候,权力就变成了其进行资本交换和谋取私利的工具。“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致使权力腐败的发生。权力的工具性是权力腐败的前提,权力行使的私人主体属性为权力腐败留下了可操作的空间。
(二)权力的有偿转让致使“权力寻租”现象发生
权力的工具性致使权力具有潜在的可交易性,这种可交易性主要表现为权力的“有偿转让”,也就是经济学中的“权力寻租行为”。当政府因不当干预和管制经济时,就有可能导致公共权力进入市场流通领域,一旦权力进入市场,极易破坏公平竞争、自主发展的市场经济,带来经济发展的“差价”。布坎南把各种生产要素的供求差价及优惠条件,称为“租金”。租金的存在,为寻租活动创造了机会。租金越高,寻租刺激越大,引起的权力腐败现象越严重。寻租活动的本质是寻租权力或权力寻租活动,也就是说“寻租者以钱寻租,腐败者以权分利”。具体表现为社会活动参与者为寻求租金,通过各种或明或暗的“寻租活动”行贿掌权者,掌权者借助手中的公共权力进行权与权、权与物、权与色的交易。
政府对经济生活的过度干预和官员的自裁量权太大是造成寻租活动普遍化的重要原因。在高校领域主要表现为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掌控着高校各项事务的发展,如对院系资源配置、科研项目申报和审批、职称评审等学术事务的干预过大、力量过强,使得高校各项事务特别是学术事务发展中寻租的空间很大,导致高校寻租现象的出现和活跃。那些掌握高校权力的党政机关、行政机关管理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直接进行以权谋私的活动,实现“创租”和“抽租”,以谋取更多更大的社会资本、金钱物质利益。纵观近来年频发的高校贪腐案件,绝大多数犯罪行为都与犯罪主体所承担的管理职务密切相关,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科研经费管理、招生录取等环节更是贪腐高发区,成为三大‘腐败病灶’”[2]。此外,在高校学术生态已遭破坏的情况下,普通教职员工为追求自身利益,不惜通过非法手段如贿赂、拉关系、走后门等进行“权学交易”。高校的权力寻租活动使高校发展陷入恶性循环阶段,严重影响了高校各项事务的发展。
(三)权力的扩张性导致权利主体的权力膨胀
权力一方面具有规范性和指导性,社会运行需要权力发挥维持秩序和缓和冲突的功能,但另一方面权力还具有强制性和扩张性等特质。强制性是权力的天然属性,“命令—服从”是权力的一般运行轨迹。在权力关系中,权利主体(掌权者)和权力客体(受权者)的关系是单向度的,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权利主体占据支配性的地位,权力客体处于受支配的被动地位。权力关系中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地位的不平等性,决定了权力具有自我扩张的本能,由此权力的扩张性是伴随着权力的强制性而出现的。权力的扩张性导致权力的异化,在空间结构上表现为破坏权力正常运行的边界和范围;在时间结构上表现为排除异己以扩张自己的权力,权力的排他性极易导致专制和独断的产生。权力的强制性和扩张性一旦与掌权者的私人欲望相结合,便会致使权力在没有任何约束的情况下具有无限扩张的倾向,导致越权、强权与特权的出现。学术权力弱化,党政权力过分集中是我国高校权力配置中存在的严重弊病,党政集权势必形成绝对的权力,从而造成权力难以监督、无法制约的局面,这也是我国高校权力腐败多发于党政系统的深刻原因。阿克顿也指出:“现代世界的法则,即权力趋于无限扩张,并超越任何国际国内的约束现象,直到遇上更神圣的原则,更强大的力量的阻挠,才会停止下来。”[1]231权力的强制性和扩张性,从根本上需要为权力行使设置边界,防止权力的滥用和异化。
(四)人性的弱点与权力的腐蚀性需要他律的限制
权力具有极强的诱惑性和腐蚀性,为保证组织权力的公共性和权力运行过程中不越轨、不异化,防止权力腐败和权力寻租活动的发生,客观上要求权力主体自身拥有高尚的道德和强大的自律。但权力的腐蚀性对任何人都是均等的,单纯依靠道德难以起到有效的约束作用。从伦理学中人性恶的假定来说,人生来就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者,人具有贪婪的本性,争权夺利是人的自然倾向。人性的不完善,使得人一旦掌握权力,而对这种权力又不加以制约时,人往往就会表现出对这一权力滥用的天然倾向。“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移的一条经验。”[3]154经济学中“经济人”的假定认为,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每个个体都会优先追求自身利益的满足。这一假定适用于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为抑制权力滥用的天然倾向,就必须要对权力的运行进行限制和约束。此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不但意味着对权力滥用者的惩处,同时也意味着对权力的正常运行设定边界线,以防好人犯错。通过来自外部的他律机制,对人性进行适时的警戒、引导、纠错和矫正,以规范权力的正常运行。
二、高校内部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的可行性
虽然人性具有不完善性和权力具有消极属性,但这并不是说权力无法遏制。从权力自身来说,权力在具有工具性、强制性、扩张性、诱惑性和腐蚀性的同时,自身也含有让渡性、可控性和有限性。权力运行过程中可以通过法律制度约束、程序控制和权力制衡等多种方式对其进行制约和约束。
(一)权力的让渡性使权力制约与监督成为可能
人民主权思想认为国家权力来源于人们,社会契约理论认为任何权力都是人民权利让渡而来。人民是国家的权力主体和国家权力的最终拥有者。我国宪法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让所有人亲自参加公共事务是不可能的,人们不便直接行使民主权利,而自愿让渡部分权利而形成公共权力,并通过间接方式实现民主权利。权力的让渡和间接行使,实现了权力所有者与权力行使者的分离,并在权力所有者与权力使用者之间产生了“委托责任关系”。
代议制在我国主要表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在高校组织中主要表现为各种委员会和代表大会,如党委会、校务委员会、校长办公会、教职工代表大会、学术委员会、各院系的教授委员会、院务委员会等。高校内外部利益相关者作为高校内部权力的主人,把自己的各项权力委托给高校各组织机构以及各级委员会和代表大会来行使,各组织机构、委员会和代表大会作为权力的受托者有责任和义务向高校各利益相关者负责。权力让渡中权力的主体并没有发生变更,权力主体并不会因权力的委托和让渡而导致权力的丧失。高校各利益相关者依然是权力最终的主人,他们掌握着权力的所有权和监督权,这也是他们能够行使权力制约与监督的权力基础。
(二)权力运行的有限性是权力制约与监督的基础
权力运行的有限性表现为“任何权力关系中都包含着某种最低限度的自愿服从”[4]362。权力必须在权力主体和权力客体共同肯定的范围内进行,没有服从就无所谓权力。一旦权力行使权限超过了权利客体的承受程度,就会导致权力客体对权力主体的抗拒、不服从,甚至引发冲突,在冲突状态中权力就无法运行。掌权者为维护自身权力,必须顾及受权者的承受范围,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权力的无限扩张。权力运行的有限性还表现为权力运行的边界范围是可控的。不同的权力主体分享不同的权力,通过有效的分权制衡,使得权力制约成为可能。在高校领域主要表现为党委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为核心的多元权力结构,他们分属于不同的权力主体,在应然状态下这些不同权力的行使界限是明晰的。权力行使空间范围的有限性和可控性,使得对不同权力行使内容和范围的划分成为可能。
(三)权力运行的可控性保证了权力制约和监督的有效性
权力运行的可控性表现为权力运行要以一定的合法性为基础。这种合法性包括实体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首先,实体合法要求权力行使主体合法、行为主体的职权合法、权利主体的权力行为和行为依据合法。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严格依照法定方式和程序行使权力,保证权力行使的正当性和正义性。高校的权力行使不仅应遵循国家宪法、法律的要求,还要遵循高校内部制定的章程、规章制度、管理办法等制度条款。其次,程序合法中的程序是有效防控、减少权力行使过程中的权力异化和权力腐败现象的重要保障。程序的重要性表现为:明确规定权力主体的权力界限和权力运作的条件、范围及运作方式,设定权力运行过程中各个环节的操作性规则,增强权力运行的规范化和透明化,减少权力运行的随意性和偶然性。再次,权责对等也是对权力的一种约束。组织成员将权力委托给掌权者,与此同时也要求掌权者对权力运用的行为和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权力与责任是一体两面,与权力相对应的是一定的职责,权责对等本身就是对权力主体授权后的一种约束。
三、多学科视域下的权力制约模式
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不同的学科领域,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分别提出了“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法律制约权力,以民主制约权力”的制约模式。不同的制约模式间互为补充、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权力制约体系。下面基于不同学科视角分别探究各制约模式的内涵特征及制约原理,为高校内部权力制约与监督模式的建构提供理论支持。
(一)政治学视野下的权力制约权力模式
政治学主要关注权力间的关系,深入权力运行内部,对不同权力体系或同一权力体系内部不同权力间的制约关系进行了研究,具体提出“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制约模式。
1.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理论基础
以权力制约权力是指把公共权力分解为若干不同的权力结构,并配置给不同权力主体,各权力主体间既相互独立又彼此牵制,形成一种均衡态势,表现为一种刚性力量受到另一种刚性力量的制约。以权力制约权力,实质上是公共权力的结构配置问题,它的核心要素在于分权与制衡,具体表现在“分”与“制”两个方面。
首先是分权,“分权”的理论逻辑就是科学合理地配置公共权力,将公共权力分割成不同方面和不同的层次,并授予不同的权力主体分别行使,以减弱权力过分集中的破坏力,从而构成一个合理的权力结构。权力的有效制约是建立在真正的权力分立基础之上的,先有不同类型的权力结构,才能出现一种权力对另一种权力的制约,分权是权力相互制约的前提和基础。分权虽然达到了弱化权力的目的,但还未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为达到权力间的制约关系,分权后各权力间必须形成对各自的相互牵制。其次是分权后不同权力间的制衡关系,“制”主要表现为不同权力间的限制和约束关系。权力制约权力包括两种情形:一种是高级权力对低级权力的监督,另一种是平行权力层级之间的相互监督与制约。不同权力结构间只有形成一种制约与被制约或相互制约的关系才能有效实现权力的制衡,制衡是权力相互制约的关键和保障。
2.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实现路径
权力分立是权力制约的前提和基础,我国高校内部的党委权力、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及其各权力主体间的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本应适当分离与相对独立,为分权制约创造前提条件,但我国高校内部权力配置中存在的一元化权力结构问题,严重限制了以权力制约权力这一模式效用的发挥。首先是“作为党内监督机构的纪检部门,因为在党委的领导之下,无法对党委形成有效的监督”[5]。其次,在行政管理系统中,校长与其他行政负责人是上下级单线的权力机构,校长及校行政系统作为行政权力主体,又要对政治权力主体负责。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的交织和混合运作,又增加了权力监督与制约的复杂性。学术权力由于力量疲软,不仅无法实现对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的有效制约,在强大的行政化管制下,更是受到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的长期压制。再次,我国大学内部呈现“倒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基层权力式微,严重影响了来自基层教职员工的民主监督机制作用的发挥。我国高校内部的党委权力、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三种权力现处于权力边界模糊、权力关系紊乱、权力结构不均衡的阶段,由于权力尚未实现真正分立,使得我国高校内部尚未形成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
“尽管我国大学的权力结构是一元化的,但客观上存在多元的权力和权力主体”。[6]其中政党组织机构和党务工作人员、行政组织系统和行政工作人员、大学教师集体和个人分别享有党委权力、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我国高校以权力制约权力模式建构的核心,在于打破行政化管理体制下一元化权力控制问题。首先,改革大学内部的权力结构,调整大学权力关系,构建多元权力主体共享大学治理权力的管理模式,实现党委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的适当分离;明确各权力主体的权力边界、职责权限、责任义务、行使程序,避免权力运作的混杂不清。第二,在纵向权力配置上,构建校、院、系三级管理体制,在不同权力层次间适当分权,实现治理权力重心的下移,改变权力过于集中顶层的局面,对校、院、系不同层级的职责权限明确定位,合理配置校、院、系三级治理权力。其次,在分权后的制衡上,针对高校的学术组织特性和学术运行要求,要特别注重培育高校学术权力,树立学术权力主体的权威地位,让那些本应由学术权力主体决策和评议的学术事务归还学术权力主体,学术权力主体全面享有决策、评定、审议等职权。通过分权制衡实现权力分解、职能分置、机构分设、人员分离,达到各权力主体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同时又相互牵制的效果,避免权力的僭越和滥用。
(二)法学视野下的法律制约权力模式
在法治社会,法治是权力控制的最根本方式和手段。法学主要从法律与权力的关系视角,提出以法律化的规则和程序制约权力,即“以法律制约权力”的制约模式。
1.以法律制约权力的理论基础
以法律制约权力具体指权力的设置、授予、运行、监督等都由宪法和法律来规范和调整,以实现权力的法律化和制度化。以法律制约权力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在静态的权力设置和授予上,法律要明确规定权力行使的主体,并对权力行使主体的权力进行明确授予;二是在动态的权力运行中,法律要明确权力运行的方式、方法和程序。通过法律的手段,防止权力运行过程中的越轨和异化。用法律对权力进行全方面的制约,以实现“在事前的权力授予上,做到授予有据;在事中的权力行使上,做到行使有规;在事后的权力监督上,做到监督有效”[7]27。
法律对权力的制约作用建立在法律至上的原则之上。在法律和权力的关系上,法高于权,法律支配权力,法律为约束和限制权力而产生。法律在本质上就是对权力行使的一种限制,“法律对于权力来讲是一种稳定器,而对于失控的权力来讲则是一种抑制器”[8]317。法律至上意味着一切权力都要经由法定方式授予,一切权力都要在法律规定或允许的范围内作为,一切权力行为主体都要对其权力行使后果负责。以法律制约权力确立了权力运行的制度安排、理性规则、程序标准和公正秩序。法律所具有的理性、稳定性和强制性,为权力运行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和有效的秩序保障,法律所具有的惩罚机制和震慑力量,有效保障了权力的正常运行。
2.以法律制约权力的实现路径
为发挥法律的控制作用,保证权力始终沿着法定轨道正常运行,客观上要求制定权力运行规则。首先,明确权力行为主体行使权力的法律依据。通过法律的形式对权力运行的标准、程序、职权等问题加以明确规定,一切权力都必须符合法律的授权,越权无效。其次,明晰权力运行的边界。严格按照法定的权力边界和职权范围运作权力,实现权力运行的法律化和制度化。再次,设定权力运行程序。程序是法律的生命形式,程序不仅是实现实体法的基本保障,也是控制权力运行的有效手段。
高校人治的色彩、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各项规章制度的执行效力低等原因致使法律制约权力在高校实践层面效果不佳。为规范高校权力运行,客观上要求制定权力运行规则并遵照执行。首先,明确高校内部各项权力行使的法律依据。国家层面要加大立法并根据高校实际修订完善各项法律法规;高校内部要科学编制大学章程、各委员会章程、各项议事规则、各项工作制度和各项规定并切实发挥其制度约束效力。其次,明晰高校各项权力运行的边界。通过法律的形式对高校内部权力运行的标准、程序、职权等问题加以明确规定。再次,设定高校内部各项权力运行的程序,增强权力运行过程的可控性。
(三)社会学视野下的民主制约权力模式
社会学从公民个人和社会团体的视角出发,提出“以民主制约权力”模式。民主制约的实质在于以权利制约权力。
1.以民主制约权力的理论基础
以民主制约权力模式认为民主具有限制和约束权力的功能,这种功能的发挥主要表现为公民享有的一些权利能够制约那些被委托出去的权力。这一模式具有消极制约和积极制约两重含义。消极制约指的是权力抑制型,公民所享有的法定权利起到屏障与保护的作用,为保障个人的自由权力,公共权力的行使不能逾越法定的界限而侵入公民的权利领域。当“权利”的领域成为“权力”的边界时,公民权利对公共权力的滥用发挥阻碍与制约作用。积极制约指的是权力行使型,公民虽不直接掌握权力,却拥有法律赋予的权利,如选举权、检举权、言论自由权、参与权、结社权、知情权、监督权、行政诉讼权等,当掌权者权力行使不当时,公民可以利用这些法定权利做出积极的反抗,或对权力行使过程实施监督,以规范掌权者的权力行为。
代议制学说、人民主权论和多元主义民主是以民主制约权力这一制约范式的重要的理论基础。根据人民主权原则和代议制学说,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人民的授权。代议制下的民主制约主要体现在权力来源于权利、受托于权利,因此权力必须以权利为界限、由权利来制约。个人在公共权力面前是渺小和独立的,但个人可以作为组织或利益集团中的一员来参与社会治理。多元主义民主认为,社会中存在多种社会组织和利益集团,这些多元参与者主体共同分享着有限的且相对自主的专有权,其中没有任何一个决策主体能够行使终极垄断权,不同主体的权力是受到限制与约束的,这种多中心的权力分配和制衡格局,对国家权力形成强有力的制约。
2.以民主制约权力的实现路径
高校治理中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从根本上来源于人民授权,为发挥基层民主的制约作用,从根本上需要保障并发挥具有积极制约作用的公民权利。这些公民权利主要表现在:(1)教职员工通过行使选举权和罢免权,直接发挥权利对权力的制约作用。教职员工享有选举权,他们可以选举那些他们认为合格的人代表其行使权力,也可以运用自己的罢免权力剥夺那些滥用权力之人的公共权力。(2)教职员工可以在法定范围内,行使言论自由权,发挥舆论监督作用,以对权力滥用行为构成舆论压力。(3)高校教职员工通过行使知情权和参与权,可以增强高校权力的透明化运作,对权力运行中的暗箱操作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4)高校教职员工可以通过结成团体以增强权利制约的效果。他们可以通过借助集体的力量来保障和维护其合法权益。(5)高校教职员工可以对权力滥用行为直接行使举报、检举、控告权等,通过申诉、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等方式获得自身的救济权利。
(四)公共管理学视野下的有限权力运行模式
公共管理的基本目的是,运用公共权力,实现社会公共意志,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管理学从权力的公共性出发,具体关注公共权力的有限运行问题。
1.公共管理视野下的有限权力运行问题
公共管理是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公共管理视野中的权力,是代表了公共机构和替代社会公共意志行使的公共力量,公共性和服务性是公共权力运行的核心。“公共权力的特征是其公共性。它是社会公共领域中由公众所赋予和认同的,能给公众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集体性权力。”[9]现代社会由于公共事务涉及内容和对象的复杂性和多样化,以及管理技术要求的专业化和技术化,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亲自参加公共事务管理是不可能的,社会成员只能委托部分人代为其履行公共管理的职责。作为公共管理最大提供者的政府正是这样的代理者,政府通过履行代理人职责,执行公共意愿,满足公民即委托人的利益并为他们服务。政府与公民间的关系实质上是权力所有者与权力使用者之间的“委托—责任关系”。“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的提出体现了我国公共服务领域政府角色和职能的全面变革。
2.公共管理视野下的有限权力运行模式
各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委托是高校内部治理中公共权力的直接来源。高校内外部利益相关者作为权力的主人,把自己的各项权力委托给高校各组织机构、各级委员会和代表大会来行使,如学校党委会、校长办公会、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及各院系的教授委员会、院务委员会等,这些代理组织与高校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权力委托”关系,代理组织作为权力的受托者有责任和义务向高校各利益相关者负责,并代为行使高校各项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责。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首先要树立“有限行政”和“服务”的观念,打破行政权力一揽独大的局面。使那些本应由学术权力主体决策和评议的学术事务交由学术权力和学术委员会治理,以改变学术依附行政的局面,行政组织主要发挥咨询、服务的职能。其次,学院作为教学、科研和行政组织的基本运作单位,学院要承担一定的学术管理及行政管理职责,学院作为学术组织的特性决定了其必须要享有充分的学术权力,在学术事务的管理和决策中有一定的自主地位。学校要积极构建以二级学院为主体的管理模式,如基层学科的建设、专业设置、课程改革、实验室建设、科研事务管理等管理权限要下放到学院,实现学院的实体化运作。再次,民主监督的核心在于教职员工的参与,教职员工要积极参与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高校事务管理,积极发挥各级委员会和代表大会的作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四、多学科研究成果对高校内部权力制约模式构建的启示
多学科视域下的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研究,从多个视角阐述了权力制约与监督的必要性、可行性与制约模式。不同的权力制约模式之间并不是彼此对立和相互隔绝的,并且也没有严格的学科划分,他们互为依存,相互补益,共同构成了多元化的权力制约模式。多学科视域的研究成果对我国高校内部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模式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构建多元化的权力制约模式,形成权力制约与监督的合力
不同学科视域下的制约模式有其不同的理论基础、价值预设和适用条件要求,每一种权力制约模式都有其具体的适用范围和作用条件。
首先,从控权机制来看,以权力制约权力是从权力自身视角来探究如何控权的机制,它是对权力运行的“内部控制”;以民主制约权力是从权力主体(权力归属主体和权力行使主体)的视角来考察由谁来制约的问题,它是对权力运行的“外部控制”;以法律制约权力是从控权方式和手段的视角,来考察如何制约权力的问题。它是以民主制约和以权力制约两种模式的具体实现路径,是对权力的“硬控制”。
其次,从控权主旨来看,分权制约的必要前提是民主,因为分权机制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才能正常运作;民主制约模式的本质是,国家权力和公民个人权力以及集体权力之间的平衡问题;法律制约的本质是为防止公共权力滥用,保障公民个人权利不受权力的非法侵害。
再次,从各自的适用局限来看,每一种权力制约模式都有其适用范围和作用条件。权力制约模式是发轫于西方的制约模式,我国社会主义政体的性质就决定了不能完全照搬。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刚性特征导致其弹性不足,这种制约机制仅局限于权力运行内部的制约,而忽视了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制约力量;以民主制约权力的根本前提,在于国家权力是否能够保障公民权力和集体权利的合理分配与行使,权利在一定程度上也要受到国家权力的牵制;以法律制约权力在于立法主体是否能够坚持人民主权的原则,以及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能否发挥其权威性和威慑力。只有构建多元化的权力制约模式,才能发挥不同制约模式的优势,形成权力制约与监督的合力,保障权力的规范运行。
(二)立足高校的组织属性,构建“三位一体”的权力体系
高校内部权力结构的复杂性和权利主体的多元性,构成了高校内部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的组织基础,多元权力主体的多样化利益诉求使得高校内部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的构建显得更为复杂;高校内部党委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三者力量的不均衡性和各自职责权限的模糊性增加了权力制约与监督的困难性;高校内部存在大量“双肩挑”的兼职人员,这些人员所代表的权力主体身份的复杂性和多重性影响了权力制约与监督模式构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高校权力制约与监督模式的构建,必须立足权力制约与监督的一般共性,同时针对高校内部权力运行的特殊性,有针对性地分析和设计。
构建多元利益主体共享高校治理权力的权力格局。在党委体系、行政体系、学术体系三者的基础上,构建以“党委领导、校长治校、教授治学”三位一体的权力体系,并通过法律和制度约束的方式明确三种权力的行使范围、职责权限和运行程序,形成三种权力之间彼此牵制的制衡格局。
首先,从党委权力来看,我国高校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外部权力制约上,高校党委是在高校党的代表大会选举的基础上,由上级党委任命的,因此它要对高校的党员代表大会和上级党委负责,接受党员代表大会的监督与上级党委的领导。在内部权力制约上,高校内部各级党组织作为下级组织“要向上级组织请示和报告工作”,党委权力制约表现为自上而下权力线中的忠诚与附庸的关系。发挥党委权力的宏观指导作用,从宏观管理的角度保证党的方针政策在高校的落实。
其次,从行政权力来看,行政权力是来源于职位的法定权力,我国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中的校长负责制是一种“首长制”,校长作为学校的法定代表人,是学校行政管理工作的最高负责人,全面负责本校的教学、科学研究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在首长制内部,校长与其他行政负责人是上下级关系,后者接受校长的统一领导,对校长负责,这种首长制内部也是单线的权力结构,因此对首长制的权力制约,主要来自外部的权力制约,这种外部权力制约主要指校长及校行政系统作为行政权力主体,要对政治权力主体负责。作为决策领导层的行政权力,要把握学校的办学方向,负责学校的整体规划,协调、监督与评估全局性工作。学校各职能部门行使参谋协调、服务保障、检查评估等职责权限。
再次,从学术权力来看,学术权力是以专业知识为基础的软性权力,大学是一个以学科和专业为基础的“底部沉重”的学术组织,大学组织的学术性本质决定了学术权力的行使是建立在以院系为核心的基层学术组织之上的自下而上的权力运行系统。院系作为大学独立的学科专业建制组织,本应享有对学术事务的管理和决策权,但在行政化管理模式下,我国高校行政权力的重心集中在学校顶部,这种以行政权力为核心的校级集权模式侵占了院系的学术管理权限。我国大学内部权力结构呈现出上端行政权力膨胀,基层学术权力式微,形成“倒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这种处于边缘化和弱势地位的学术权力,不仅无法实现对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制约,更是受到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压制。针对高校的学术组织特性和学术运行要求,要特别注重培育高校学术权力,树立学术管理主体的权威地位。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理论设计的精密最终需要实践领域中的推行和坚守。
[1]阿克顿.自由与权力[M].侯健,范亚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法制晚报.高校职务犯罪特点呈“三高”[EB/OL].(2010-04-02)[2016-01-15]. http://www.fawan.com/Article/ fzfk/fzzt/2010/04/02/10020066083.html.
[3]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4]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M].阎克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5]刘献君,张晓冬,刘皓.权力运行—高校权力运行制约机制:模式、评价与建议[J].中国高教研究,2013,(6).
[6]别敦荣,冯昭昭.论大学权力结构改革—关于“去行政化”的思考[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1,(6).
[7]申国勇.行政权力的法律制约研究[D].南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05.
[8]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9]黄健荣,余敏江.论公共管理与宪政[J].江苏社会科学,2004,(2).
[责任编辑:罗雯瑶]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Power Restriction and Supervision i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Qi Ming-ming
( College of Marxism,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engdu, Sichuan610051, China )
The purpose of power restriction and supervision is to protect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power, and to prevent and correct power abuse.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can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ower restriction mechanism i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in China and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internal power restriction and supervision mode construction. From perspectives of ethics in the study of human nature, economics, politics and law research on power characteristics, the study provides a logical argument based on these disciplines. Politics, law, sociology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each provide a separate restriction model that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power of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restriction and supervision mode
齐明明(1987—),女,河南长垣人,博士,成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高等教育政策、高校发展规划执行研究。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校内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4JZD05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G647
A
2095-7068(2016)03-0015-08
2016-0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