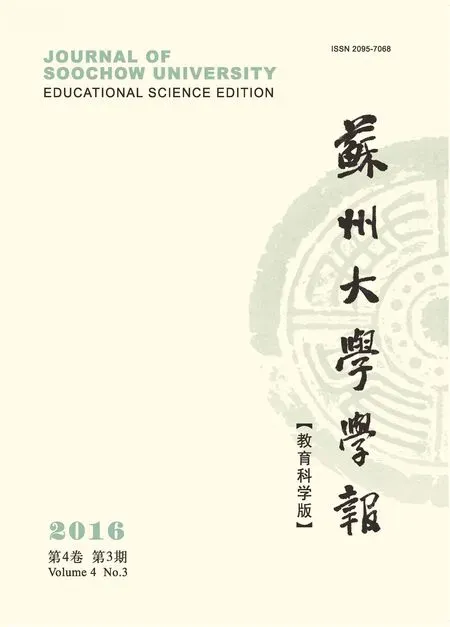我国高校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模式研究
汤 俊 雅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我国高校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模式研究
汤 俊 雅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福建厦门361005)
我国高校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模式指向高校内部权力运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核心是权力过于集中而导致的腐败问题。针对高校内部权力腐败的问题,人们在实践中已经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法,总的来看可以归纳为权力制约与监督、法律制约与监督以及权利制约与监督三种模式。但是,这些模式在实践中暴露出各种问题,集中表现为权力制约与监督模式失效、法律制约与监督模式不完善、权利制约与监督模式形式化以及文化制约与监督模式缺失。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完善我国高校权力制约与监督的三条路径:理顺权力角色之间的关系,建立完善规范的制度体系,营造浓厚的学术文化氛围。
大学内部权力;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运行
我国高校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模式指向高校内部权力运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核心是权力过于集中而导致的腐败问题。针对高校内部权力腐败的问题,人们在实践中已经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法,集中体现在现有的相关规章制度中,从这些规章制度中可以总结出现有的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的模式。然而,近年来我国高校权力腐败案件频频在媒体曝光,引发政府相关部门以及社会舆论的极大关注,这充分说明我国高校目前已有的内部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模式存在一定程度的薄弱环节和漏洞。因此,我国目前高校的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模式有哪些?这些模式在实际运行中存在哪些问题?如何在结合高校目前的实际以及长远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基础上解决模式存在的问题?这些应当是在我们面对高校愈演愈烈的权力腐败时不得不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一、我国高校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模式
从实证主义的角度来看,对模式这种抽象客体进行研究,其研究对象不得不从抽象的模式还原为具体的经验性质料。这些质料主要包括目前已有的各种成文的规章制度,如《高等学校章程制订暂行办法》《高等教育法》《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等,从这些法律法规的具体内容中可以总结出目前我国高校内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模式。
(一)权力制约与监督模式
此种模式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基础是分权,核心是权力结构。通过构建不同权力主体相对分立的权力结构,实现权力之间的制衡。在实践中这种结构通常表现为两种形式:不同权力主体的分立和同一权力主体内部的分立。
一方面,我国高校内部存在着党委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民主权力四种不同的权力主体[1],四种权力构成高校内部权力的分权结构,权力之间相互制约协调。《高等学校章程制订暂行办法》是教育部颁布的指导我国各高校章程制订的纲领性文件,不仅明确了党委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区分了两种权力的职权范围,还规定了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等组织的设立规则以及职责范围,明确了学术权力和民主权力的组织基础。
另一方面,在同一权力主体内部也有规章制度明确了分权的结构。《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在党委权力的内部确立了民主集中的原则,其基础也是分权。党委的各委员之间是平等关系,书记与委员之间也不是上下级关系,决策必须要集体商议,不能个人拍板。不仅如此,校长办公室、学术委员会等其他权力组织内部也有相关的民主议事规则。
因此,从已有的规章制度中可以看出我国高校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模式。不同权力主体的分立制衡避免了权力集中于某一个利益群体,而权力主体内部的民主议事程序则通过权力的分散避免了权力集中于某一个人。
(二)法律法规制约与监督模式
如果说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模式重点在权力主体的分立以及权力职责的确定等结构问题上,那么以法律法规制约权力的重点就转向对权力行使过程的规范与约束上。法律法规制约权力模式主要通过三种机制发挥作用:规范机制、程序机制与责任机制。
1.规范机制
规范机制是指通过制定实体性的法律法规,为权力划定边界,在权力主体行使权力之前明确权力行使的范围。这种实体性法律法规在国家层面主要体现为宪法,在高校内部则主要体现为章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作为规范教育事业的基本法明确规定了高校应制定章程。《高等学校章程制订暂行办法》进一步明确了高等学校章程的起草、审议、修订及核准、备案等事项。自2012年起我国各高校都要依据《高等教育法》和《高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基础上制定本校的章程,并送交教育部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核准,这对于我国高校规范办学自主权和依法办学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高校章程的制定从权力运行的起点上为高校内部权力划定了边界,明确了各权力主体的职权范围,防止了权力的肆意扩张。
2.程序机制
实体法的规范机制尽管给权力划定了边界,但是这个边界始终是静态的,如何能够确保静态的权力边界在动态的权力运行过程中不发生扭曲,这就需要程序来对权力的行使进行控制。程序的实质是去人格化,程序里涉及的个体被角色化、符号化,个体所携带的人际关系、情绪感情、社会地位、财富名望等因素被排除在外,程序只需要针对事情本身,从而确保权力在行使过程中不受权力主体人格因素的干扰而出现偏差甚至扭曲。程序在法律中的重要性已成为西方法学界的共识,“程序是法律的中心”[2]73,正因为程序对权力的运行过程起到了关键性的控制作用,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小了权力的肆意性,因此,“程序的完备程度可以视为法制现代化的一个根本性指标”[3]18。
我国相关的规章制度从程序的层面规定了高校组织的工作方式、工作程序、人员构成及任免等。如《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校长办公会议事规则》《学术委员会工作制度》《教职工代表大会实施细则》等。此外,高校的章程最能集中体现程序机制的存在。《高等学校章程制订暂行办法》较为详细地规定了章程应有的程序机制,包括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等权力组织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
3.责任机制
法律法规对权力的制约如果缺少责任追究的机制,那么即使前面两种机制都具备,法律法规也不会对权力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制约。当行使权力者发现滥用权力承担的风险比获得的收益要小得多时,那么就算再完备的制度约束也将无济于事。
经济活动领域是权力腐败的高发区,虽然高校不是营利性机构,但是高校的基建、后勤、采购等活动都属于经济活动,存在着大量的资金流动,是权力介入的密集区域。我国大学的内部支配钱财物等资源的权力集中在党政领导干部手中,因此,针对高校党政领导干部在经济活动领域的权力行使,政府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其滥用权力的后果进行了规定。2012年教育部颁布了《教育系统内部审计工作规定》,要求大学、独立设置的学院和规模较大的高等专科学校应当设置独立的,与本部门、本单位财务机构相同级别的内部审计机构,对本单位涉及经济责任等十一项事项进行审计。此外,各高校的章程中也都将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制列入其中,从制度上对领导干部的权力行使后果进行责任约束。
(三)权利制约与监督模式
一个社群中每个成员都有其个人权利,但是相较于强大的公共权力而言,个人的力量实在是沧海一粟,无力抵抗公权的入侵,但是,如果拥有相似权利诉求的个人集合起来形成集体,就可以成为制约公权的强大力量。权利对权力的制约,其逻辑起点是“保护弱者”,制约的方式是通过结社组成社团,表达权利主体的权利诉求。
在高校里,普通教师和学生是最主要的权利主体,他们分别通过组成教职工代表大会和学生代表大会的集体组织形式来表达他们的权利诉求,从而起到制约权力的效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通过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依法保障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教育部还依据教育法、教师法、工会法等法律,制定颁布了《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规定了教职工代表大会主要享有的审议建议权、审议通过权、审议决定权、评议监督权。[4]
此外,近年来学生群体作为高校内部重要利益群体日益受到重视,有不少高校在章程中将学生代表大会和研究生代表大会作为学生参与学校民主管理的正式组织形式纳入学校的管理体制和组织体系中,对组织的成员、职能进行了相应的规定,给予了必要的重视。
二、我国高校权力制约与监督模式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从已有的制度文本中总结出来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模式只是形式性的,模式是否能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真正起到制约权力的效果才是实质性的问题。近年来频频曝光的高校腐败案件已经向这些模式制约权力的效果提出了质疑,不仅媒体通过深度报道广泛关注这个问题,学者也就此问题纷纷撰文分析。在这些信息的基础上,可以总结出三种模式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权力制约与监督模式失效
权力制约与监督模式的失效意味着我国高校目前的权力结构只具有形式上的合理性,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党政权力过于集中且缺乏实质性的监督。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党政权力内部难以形成有效的分权制约;外部缺乏对党政权力的有效监督。
分权制约的有效性取决于不同权力主体之间的边界清晰,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对等性。首先,我国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看,这种权力结构体现出党委和校长之间既有相互制约又有相互协调,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党委和行政两大权力主体往往边界模糊。[5]有学者通过实证调研发现,在多数学校,党委会、校长办公会的成员基本上是一致的,仅仅是主持人不一样,如某地方高校8位校级领导就是8位党委常委。[4]因此,理论上党委与行政的辩证统一、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关系在实际运行中就容易变成两者之间关系模糊不清的问题。这就使得高校内部的权力运行过程中决策、执行、监督很难分开,出现“议行合一”的现象,导致分权制约的效果难以实现。例如,2015年11月24日教育部党组对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陈文申、校长苏志武等8名党员领导干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进行通报,按照程序分别给予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教育部同时处理一所高校的8名领导干部,即使是在目前反腐高压期间也极为罕见,但是这里隐藏的高校内部权力结构问题却并不鲜见。一所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同时遭到违纪处理,这本身就说明党委和行政两大权力主体之间缺乏有效的相互制约监督机制。自2014年1月至2015年11月,仅从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的信息来看,至少已有108名高校领导干部因违纪违法被查处,其中多数都是既担任校级行政领导,同时又是校级党委常委。这种行政权力角色与党委权力角色在监督制约机制中角色模糊的状况,容易造成两种结果:要么如同中国传媒大学案例中校长和书记同时违纪腐败;要么就是校长或书记某一方腐败,另一方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监督和制约,只能洁身自好或者明哲保身。因此,近来频频曝光的高校领导腐败案件集中凸显了我国高校内部党政权力难以形成有效的相互制约和监督机制的严重问题。
其次,党政权力过于集中,缺乏对党政权力的有效监督。我国多数高校内部的权力结构都表现为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权力则集中于党委书记。因此,导致实际决策中往往变成党委书记的一言堂。另一种情况则是校长拥有最终决策的权力,校长办公会议往往成为校长的“一言堂”。作为监督党委的外部职能机构是校内的纪检组织,但是长期以来,校内纪检机构的监督形式化一直饱受媒体和学者的诟病。根据《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高校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双重领导下工作。高校内部的纪检组织其实是隶属于校党委的,这就导致纪检组织难以对党委形成有效的监督。校内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和学生代表大会作为民主权力也可以对党政权力进行监督,但是这些组织都要在党政的领导下工作,实际上也无法发挥监督党政权力的功能。
(二)法律法规制约与监督模式不完善
法律法规制约权力模式的有效性取决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三个要素,分别从权力的起始、权力的运行和权力的结果三个方面保障对权力过程的全程制约与监督。然而,在实际中,由于存在法律法规的缺位和非程序化运行的问题,法律法规制约权力的模式非常不完善,导致法律法规体系漏洞百出,无法遏制权力的肆意行使。
首先是法律法规的缺位问题非常严重,导致权力的运行没有既定的法律法规与程序规范为依据。一项2011—2012年对全国64所高校与权力运行制约相关的规章制度建设完备情况的调查研究显示,高校八项规章制度的建制完备情况不容乐观[4],许多高校对权力运行起重要制约作用的规章制度如大学章程以及自由裁量权实施办法尚未制订。并且,由于我国高校的章程制定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意志行为[6],教育部在2012年才出台规定要求各高校制定章程,在这之前大多数高校没有章程,而章程作为高校上位制度的缺位也使得其他下位的规章制度因缺乏合法性基础而缺位,导致权力几乎是在真空中运行,基本上不受制度的规约。
其次是法律法规的非程序化运行,导致法律法规不能被有效落实。我国高校校领导权力过大,对权力违反程序的惩罚力度太小,导致权力可以无视程序,程序本身也成了形式化的东西。法律法规非程序化运行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已有的规章制度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低效甚至无效,党政领导可以无视规章制度滥用权力。例如2015年受到法院处理的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处处长2000多万巨额贪污案件备受关注。人大作为教育部直属重点高校,已经制定了详细的大学章程,规定了权力运行的程序,但是仍然出现巨额贪腐案件,这说明章程等规章制度对权力的约束和震慑作用太小,党政领导依然可以依惯例非程序化地行使权力。
(三)权利制约与监督模式形式化
权利制约与监督模式主要是依靠校内两大群体—教职工和学生,通过两种组织教职工代表大会和学生代表大会,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来发挥功能。然而,由于实际中存在的政务不公开、权力运行透明度低以及权利组织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方式不合理、权利主体参与表达意见的通道不畅通等问题,教职工代表大会和学生代表大会两大权利组织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功能趋于形式化。
由于传统的惯性,我国高校内部重大校务的决策都是局限于校领导的圈子里,其他人很难知情,高层权力的运作是一个黑箱,外人无法窥其一斑。由于知情权得不到保障,教职工代表大会和学生代表大会的监督职能也就只能流于形式。《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明确规定高校教职工代表大会在校党委的领导下工作,这种权力关系下教职工代表大会很难实施对校领导的有效监督。此外,该规定中虽然规定了教代会的八项职权,但是其中只有一条“按照有关工作规定和安排评议学校领导干部”是直接针对校领导的,并且评议的程序和保障机制也并未具体说明。八项职权中并无选举校领导的职权,高校的校领导既然不由教代会选举产生,就不用对教代会负责,教代会对校领导的监督作用也就有名无实了。因此,在教代会的实际运行中,其主要职能还是针对教职工的福利问题以及聘任、考核、奖惩事项进行讨论,在校领导权力运行的监督方面并无实质性的职权,其监督功能只能流于形式。
目前《教育法》与《高等教育法》等法律都没有明确的关于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条款,只有《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提到“鼓励学生对学校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支持学生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但对于参与管理的范围、方式、条件等都未涉及。此外,近年来不少高校都将学生代表大会制度列入学校章程,但是章程中关于学生代表大会的职权规定中,对校领导权力进行监督的表达较为微弱。因此,鉴于合法性依据不足,加之知情权得不到保障,学生通过参与高校的民主管理来制约权力并不会取得实质性的效果。
(四)文化制约与监督模式的缺失
文化制约权力模式发挥功能的实质是通过培育某种倾向性的文化氛围,使得权力行使者从思想、信念、精神和价值观上认同这种倾向性的文化价值内核,以滥用权力、权力腐败和权力寻租为耻,以用权力服务于公共利益、寻求公共利益最大化为荣,从而自觉抵制滥用权力和权力腐败寻租的不良意识,自然地达到制约的目的。这样来看的话,目前我国高校在文化制约与监督模式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
首先,我国高校内部的文化态势是权力文化盛行,学术文化式微,这几乎是便利权力滥用,滋生权力腐败的最佳文化土壤。作为学术组织,高校内部应当遵循学术的逻辑,崇尚学术价值,以学术为核心,建构内部组织体系和运行规范,为实现学术使命、履行学术责任营造良好的学术文化。但是,我国高校内部不但移植了外部党政组织的建制,建立了体系完备、规模庞大、分工明细的党政职能机构,而且沿袭了外部党政组织的领导与管理制度[7]116-121,高校的党政领导几乎垄断了高校的主要权力,包括管理学术事务的权力,形成一种居高临下、牢不可破、等级性鲜明的权力文化。这种权力文化导致行政权力价值主导高校办学,高校的学术价值不彰,师生员工价值扭曲或异化,学术被边缘化,学术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学术文化极度式微。在这样的文化态势下,行政权力不是为了学术的存在而存在,其目的不是服务于学术的发展,而是为了其自身的目的,学术的价值只有贴上权力的标签才能显示其意义。应该说,就高校的文化制约机制而言,只有学术文化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权力腐败的文化土壤,在学术文化中,行政权力的行使是为学术的价值和学术事业的发展服务的,而不是为权力行使者个人谋取私利。但是,在目前我国这种权力文化盛行、学术文化式微的文化态势下,学术文化是被权力文化完全压制的,根本谈不上制约权力的作用。
其次,我国高校缺失文化的制约与监督模式。频发的高校职务腐败案件清楚地说明我国高校缺失制约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的文化土壤,整个高校的文化氛围倾向于“为权力滥用和腐败开绿灯”。目前我国高校内部影响校内师生员工思想、价值观和行为的文化主要有两种:权力文化和功利文化。前者的文化倾向性表现为追求个人权力的最大化,后者的文化倾向性表现为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在这种文化氛围里,个人行为的最终目的指向权力和利益,其他的一切都可以是用来达成最终目的的工具。由于权力和利益通常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这两种文化相互结合成一种异常牢固的权力—功利文化雾霾,将高校全体师生员工笼罩其中。在这种文化氛围下,高校的人员热衷于追逐行政官职的级别,掌握权力的行政官员热衷于通过自己的权力使自己的私利最大化,而教学和做研究只是用来换取官职和利益的物品,并且在高校师生员工的思想观念里,这么做是合情合理的,将学术作为换取官职和利益的工具这种做法是得到广泛认同的。因此,目前我国高校的这种权力—功利文化的文化倾向性是认同甚至鼓励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的,在这种文化氛围下制约权力的文化基本上没有生存的空间。
最后,目前我国高校对于文化制约权力的理解还停留在行政机关文化的层面上,没有从高校组织特殊性的层面来理解文化制约。从已有的有关高校文化制约权力的文献论述以及教育部发布的关于惩治和预防高校腐败的相关政策文件来看,对文化制约权力机制的理解集中在通过营造道德文化和服务文化,使行政管理人员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和服务意识,从而制约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这其实是仿效高校外部行政机关对待行政官员行使公共权力时运用的“廉政文化”,“廉政文化”只针对权力行使者本身,主要是政府行政机关的领导人。套用在高校就是集中对高校领导干部进行“廉政文化”的教育,提高高校领导干部权力行使的道德水平和服务意识,从而达到文化制约的效果。这也说明我国高校较为鲜明的政府行政机构附属的组织性质,高校在许多机制和制度的运行方面也都和政府行政机关类似。应该说,通过“廉政文化”对高校领导的权力进行制约不是没有效果,但是这种文化制约机制更多地依赖教育、训诫、谈心、榜样示范等教育性方式,并且范围只限于高校党政干部和领导,因此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文化”制约,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制约应当是高校党政干部和领导的权力在一种全校师生员工共同认同的文化氛围中得到有效的制约,在这种文化中高校领导自觉转变权力行使的思维、意识和行为,而不是通过教育性手段实现转变。
三、完善我国高校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模式的路径
通过对我国高校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模式进行描述和分析,总体上可以发现我国高校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模式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形式化问题,因而在制约与监督权力方面趋于低效甚至失效。三种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模式出现的问题首先是权力结构的问题,最根本的是不同权力角色之间的关系问题,其次是解释并规定这些关系的制度问题,最后是营造大学学术氛围的文化问题。因此,要解决我国高校现有的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模式存在的问题,健全并完善我国高校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模式,应当从这三个方面着手。
(一)理顺权力角色之间的关系
高校内部主要的权力角色可依群体分为政治(党委)权力角色、行政(校长)权力角色、学术(教师)权力角色、民主(教职工和学生)权力角色。目前来看我国高校的权力角色关系存在着两大问题:一是权力关系的等级性太强,党政权力角色对学术权力和民主权力角色多是上对下的命令和强制;二是权力角色之间错位严重,党委权力角色和行政权力角色的界限模糊不清,党政权力角色常常扮演学术权力角色和民主权力角色。针对这些问题,在实践过程中,应该重点依据治理的理念和实践经验,在坚持党的正确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的前提下,构建具有一定开放性和多元化的权力结构和相互协调、互动畅通、共同参与、共同分享的权力角色关系。
1.构建权力结构科学合理、权力主体权责范围明确、各权力主体相互协调的权力制约模式
党委代表的政治权力和校长代表的行政权力之间应当着重在权力运行中根据各校的具体情况,明确两者的权力边界,防止权力的交叉。明确规定党委会决策的事项,处理好党政之间的关系,克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委包揽一切的现象。[8]我国高校较为普遍的行政过度干预学术现象也是权力划分不合理的表现,应当明确学术权力对于学术事务的决策权、审议权和监督权,彻底改变学术委员会等学术组织仅仅只是执行行政决议的现状,规定行政权力不得任意介入学术事务领域的决策。[9]此外,要明确教代会和学代会在哪些关切教职工以及学生切身利益的事务上拥有讨论决定权、审议权和监督权。通过对权力的合理划分,明确各自权力的边界,理顺各种权力之间的关系,才能发挥权力制约与监督模式的最大效果。
2.有序推进校务公开,健全师生参与校务决策与监督的合法渠道
校务公开、权力运行透明是前提和基础,权力运行不透明,基层群众与校领导之间信息不对称,那么权利制约权力就如同水月镜花。应在校务公开、权力运行透明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如何在坚持党委领导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教代会和学代会等基层权利组织对党政领导的监督职能。要正确认识基层权利组织的监督职能,教代会和学代会等基层权利组织的主要功能是参政议政,而非执政代政,对学校党政领导的工作是监督制约,而非干预作对,是帮助党政领导做好管理工作,而非和党政对立,相互掣肘,制造摩擦。因此,党委和行政要充分尊重教代会和学代会的意见,积极支持教代会和学代会的工作,正确发挥领导作用,引导其充分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关系学校改革、建设发展的重大决策,要经过教代会审议,在充分听取意见后再做出决策。[10]关系教职工和学生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要经过教代会和学代会讨论通过,并认真按照通过的决议执行。学校行政要定期向教代会报告工作,公开校务,自觉接受民主监督和民主评议。[11]
(二)建立完善规范的制度体系
以法律法规为主的制度体系跳出了权力主体的限制,主要是作为工具和手段对权力运行过程进行制约,但是由于我国权力腐败问题的特殊性,应特别注重高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对校领导行使权力的制约。传统上我国高校的规章制度多是向下的约束,因此,应当在现有的规章制度体系中增补权力制约的内容。探索健全大学章程、规范权力运行程序、使权力运行规范透明的法律法规制约模式。
首先是健全章程,这是构建科学法律法规制约模式的前提,章程要将经过合理划分后的权力结构体现出来,使得各权力主体都能在明确的范围内行使权力,使得权力主体只能在章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从而便于民主监督。
其次是规范权力的运行程序,必须对权力运行过程的各个环节予以明确,明晰行权者行使权力的方式和步骤,使得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能够在程序上体现出来,并且程序应当公开。从解决高校权力腐败问题的实际来看,重点是要制定并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教育部已于2011年4月发出《关于进一步推进直属高校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意见》的通知,对重大决策事项、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大额度资金使用事项的主要范围,做出了明确规定。同时,明确了“三重一大”决策的基本程序和保障机制。此外,也不能忽视细节。“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细节也是底线,任何一次大的职务腐败案例都不是偶然的、一次性的行为,都是积少成多、从违纪到腐败的长期过程,因此,对待行政干部的违纪问题也要放到和腐败问题同等高度来重视,以求防微杜渐。
最后是在人财物资源流动频繁的活动领域,按照现代市场经济中关于经济活动运行的程序和规范,在人员聘任与晋升、招生、采购、基建招标、校办产业、财务管理等方面加强程序的规范与建设。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对2005—2012年高校与科研院所职务犯罪的统计显示,职务犯罪集中在财务部、餐饮部、装备处、教材科等资源集中的部室。这些部门往往存在着巨额的资金流动,这些活动都属于商业性质的交易活动,因而必须严格遵守现代市场经济中关于经济活动运行的基本程序和规范,使得权力在这些领域中的运行能够公开和透明,压缩暗箱操作和权力寻租的生存空间。
(三)营造浓厚的学术文化氛围
高校不同于政府机构、企业等科层式社会组织,它有其自身的组织特性,因此营造高校的文化制约权力模式不能简单地套用应用于政府行政机关的“廉政文化”制约模式。高校本质上是一种学术组织,高校的组织结构主要表现为基于各门学科的院系组织的松散结合,学术活动是高校最基础也是最根本的功能性活动,高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本质上是高校组织的学术性功能,学术价值是高校所有师生员工都认同的根本价值,学术使命是高校最终的组织使命。因此,适合于高校的文化制约模式应是一种以“学术文化”为根基的文化制约模式,学术文化应是高校所有师生员工包括领导干部都认同的文化,“以追求真理为目的、促进学术利益的最大化”应是高校学术文化的文化倾向性,在学术文化的氛围下,高校干部和领导的权力行使都是共同指向服务于学术的目的,而不是谋取个人的私利。
我国高校权力集中、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的问题,其根本可以归结为高校学术文化不彰、“官本位”文化盛行的文化根子问题。我国高校内部虽然存在着多元文化的形式,但是多元文化之间的地位是不对等的,突出的表现是“官本位”的行政文化过于强势,消解并同化其他文化。[12]我国高校内部盛行的是一种“官本位”的权力文化,这种文化并不是学术组织内在生发的,而是高校外部政府机关权力文化的延伸。在这种文化中,高校行政人员、教师和学生的行为方式、思维习惯、信念体系和精神状态都会慢慢朝向热衷追逐权力、官职、金钱以及利益发展,忽视了对于学术、知识和真理的追求。事实上,在高校这样的学术组织中,越是学术水平高、学术素养好的人越是集中精力在学术事业的发展和学术质量的提升上,他的信念、价值、精神、思维和行为都是指向学术的,自然就没有太多的精力和热情去谋求学术以外的东西。如果高校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人,那么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学术文化”,学术发展是全校人员集体追求的最高目标,这样,权力文化的生存空间就会逐渐被压缩最后消散。
权力结构以及制度建设可以视为是应对当前我国高校权力腐败问题严重的必要策略,但是,高校的权力制约与监督的目的不能止步于此,高校的权力制约模式建设应当成为为高校学术使命服务、促进高校学术事业发展的必要途径。从长远来看,无论是针对目前严重的高校权力腐败问题,还是中长期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提高大学学术水平、繁荣学术活动、营造学术文化的意义是最为重大的。要想根除或者最大限度地解决我国高校严重的职务腐败问题,最好的途径就是通过良好的学术文化逐渐净化权力文化的生存环境,促使大学的组织性质从目前的政府行政机构附属转变为自主自治的学术组织,使全校师生员工的工作、精力和信念都集中到学术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上来。
[1]别敦荣.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与大学权力结构改革[J].高校教育管理,2011,(11).
[2]诺内特,塞尔茨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M].张志铭,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3]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4]刘献君,张晓东,刘皓.高校权力运行制约机制:模式、评价与建议[J].中国高教研究,2013,(6).
[5]别敦荣.我国大学章程应当或能够解决问题的理性透视[J].中国高教研究,2014,(3).
[6]别敦荣.制定大学章程的策略探析[J].现代大学教育,2014,(2).
[7]别敦荣.中美大学学术管理[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
[8]张德祥.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与内部运行机制的调适[J].高等教育研究,1998,(5).
[9]别敦荣.关于高校学术委员会建设的思考[J].大学教育科学,2015,(3).
[10]张德祥.关于高校决策模式改革与教学科研组织创新问题的几点思考[J].大连大学学报,2002,(10).
[11]刘献君.论大学内部权力的制约机制[J].高等教育研究,2012,(3).
[12]别敦荣.治理之于我国大学管理的意义[J].江苏高教,2007,(6).
[责任编辑:罗雯瑶]
A Study of the Mode of Restriction and Supervision over the Internal Power of Chinese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TANG Jun-ya
(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
The mode of power restriction and supervision in Chinese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point to a series of problems with the internal power operation whose core is corruptions caused by power overcentralization. Internal power restriction and supervision as the solution include the power model, the law model and the right model. However, these models have problems such as the failure of power model, the incompleteness of the law model, the non-essentiality of the right model, and the absence of the culture model. Targeting these problems we pose three pieces of advice: straightening out power roles, establishing a full-functioning law system and cultivating rich academic culture.
internal power of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power restriction and supervision; power operation
汤俊雅(1987—),男,湖北安陆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校内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4JZD05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G647
A
2095-7068(2016)03-0023-08
2016-0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