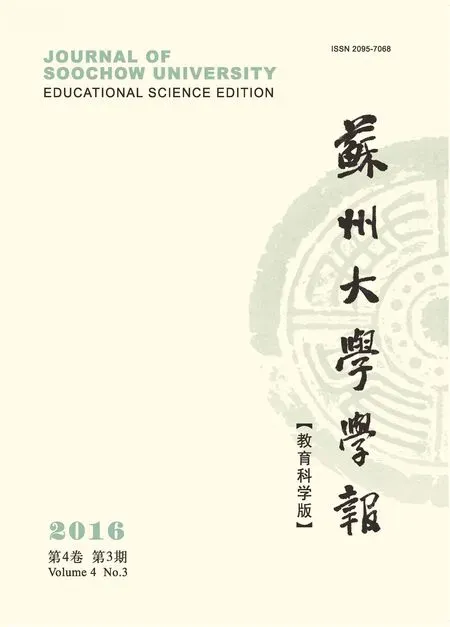论我国高等学校内部权力的构成、来源与性质
唐 汉 琦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 学术关注:高校内部权力及其制约与监督研究
论我国高等学校内部权力的构成、来源与性质
唐 汉 琦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福建厦门361005)
特约主持人:别敦荣
主持人话语:我曾经对高校权力问题进行过专门研究,原想写这个按语会很简单。但到了下笔的时候,却感到似乎无从下笔。仔细一想,这也正常,因为高校权力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真的要很清楚明晰地予以解释和说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也正说明了高校权力问题非常有研究的必要。尽管理论界关于高校权力的研究不少,但大多比较抽象,对我国高校的针对性不足。另一方面,我国高校权力运行一向保持了高度集中统一,且人治色彩浓厚。在高校权力结构中,尽管不乏监督权力及其责任部门,但却形同虚设,功能薄弱。近年来,在反腐败斗争中,高校腐败案件频发,一时之间,一贯清水衙门的高校领导似乎也成为了高腐职业,高校领导干部成为了高腐人群。究其原因,高校领导的素质不能说没有影响,但可能更为关键的是,高校权力制度存在严重漏洞难辞其咎。因此,研究高校权力及其运行机制与结构问题,从理论上廓清高校权力的性质、来源、结构、运行要求,包括监督与制约的机制,不仅对于认识高校权力制度的本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完善高校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体系、防范或杜绝权力运行的中的腐败现象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2014年,大连理工大学原党委书记张德祥教授承担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校内部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体系研究”,我应邀负责项目第一子课题“高校内部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的理论基础”的研究任务。这个子课题的研究内容主要是对高校内部权力进行理论解释,对高校内部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的基本问题进行理论剖析。我组织团队成员开展了研究,经过多轮研讨和反复修改,完成了一批中期研究成果。这里呈献给读者的四篇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对高校内部权力及其运行制约与监督进行理论阐发。
现代高等学校是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关涉多方利益,利益关系是权力关系的基础,多元利益决定了权力的多元化。从我国高等学校的内部利益相关者构成来看,主要包括党委会及党员群体、以校长为首的管理人员、教职工群体以及学生群体等,由此也就形成了与不同利益相关者相对应的多元权力,主要包括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学生权力以及民主参与权力等。作为后发外生型高等教育国家,我国高校内部权力的发展来源和合法性依据既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大学组织的权力发展规律,又强烈地体现了我国对高校内部权力运行与制约的人为设计。此外,高校内部权力的多元化,还体现在权力产生、分配以及运行等环节的不同特征,从而呈现出内生性与外铄性、等级性与平等性、强制性与协商性等不同属性的差异。
高校内部权力;构成;来源;性质
现代高等学校关涉多方利益,利益关系是权力关系的基础,多元利益关系促使高等学校成为一个多元权力博弈的教育与学术机构。那么,高等学校内部究竟包含哪些权力类型,这些权力来源于哪里,具有什么属性特征,这是我们探究高校内部权力运行与制约复杂关系的逻辑起点。
一、我国高等学校内部权力的多元构成
现代高等学校是一个复杂的利益相关者组织,其教育性、学术性以及公益性的多元利益关系特征决定了其内部权力的构成是多元多样的。关于“权力”一词,在西方,该词最早源于拉丁语“potestas”,在英文中演变为“power”,意为“力量、能力等”。在中文中,“权”最早是指一种衡量重量的器具,后来引申为两种含义:一是指衡量审度,如孟子说“权,然后知轻重”;二是指制约别人的能力。在现代东西方语境中,“权力”依然没有一个共识的定义,一般而言,权力是指影响或支配他人行为的一种合法的正当的力量或能力。就高等学校而言,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学家伯顿·克拉克认为高校内部存在着10种权力,即个人统治(教授统治)、集团统治(教授统治)、行会权力、专业权力、魅力权威、董事会权力(院校权力)、官僚权力(院校权力)、政府权力、政治权力以及学术寡头权力等[1]124,并将这些从高等教育系统最上层(国家)到最底层(系或讲座)的决策机构和群体所享有的权力统称为“学术权力”[1]185。克拉克用“学术权力”这一概念统称高等教育系统中的所有权力类型,虽然突出了高等教育的学术性,却忽视了高等教育的公共性,且容易造成高校内部多元权力的混乱,忽略了不同于“学术权力”的其他权力类型的特殊性。国内部分学者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划分的模糊性,并积极研究高校内部权力划分的多样性。别敦荣较早提出高校内部权力包含两类权力的观点,一类是教师权力,包括教师个人和教师集体非行政性的学术权力;另一类是行政性权力。[2]张德祥进一步指出,高校内部权力主要由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两部分组成,前者是学术人员所拥有和控制的权力,后者指高校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拥有的权力,主要表现为校长的权力、处长的权力、科长的权力。[3]20-22此后,高校内部权力主要由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构成的观点逐渐为我国高等教育界广泛认可。当然,也有学者反对,认为从行政法的角度看,“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争是一个在逻辑上不存在,在现实中缺乏依据的“假问题”,“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本就是同一种权力——大学自治权力或大学办学自主权,因此,高校内部权力实际上只是在教师组群、学生组群、管理人员及其他辅助人员等不同组群之间进行分配的一种自治权或自主权而已。[4]将高校内部权力统归于大学自治权或大学办学自主权,显然与克拉克所统称的“学术权力”一样,只不过是高校内部各种不同权力的一种统称罢了,此外,办学自主权在不同组群之间的分配实际上也就说明了不同群体拥有的权力具有差异性。因此,高校内部权力除了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以外,还存在其他方面的权力,从权力行使主体的角度来说,还包括如一般教师、教辅人员和学生的权力等。[5]总之,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日益认识到高校内部权力是多元多样的。
尽管高校内部权力是多元的,但究竟包含哪些权力类型却尚未形成共识,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观察角度就提出不同的高校内部多元权力类型。如以权力主体和内容为标准,将我国高校内部权力划分为党委、校长以及教师分别掌握的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等三种权力类型。[6]8也有从高校的主要活动群体的角度指出,高校内部权力系统由教师、学生和管理人员的学术权力、学生权力和行政权力共同构成,并强调我国高校学生权力长期遭受遮蔽,呼吁重新予以保障。[7]还有则从我国现行法律明示或默示的角度指出,我国高校是一个包含政治领导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以及民主管理权力等四种基本权力的权力结构体系,其中政治领导权力和行政权力居于强势地位,学术权力和民主管理权力则处于相对的弱势处境。[8]此外,还有从高校的组织结构出发,认为我国高校主要存在四个系统,即党组织系统、行政系统、学术系统、社群系统。党组织系统由高校党委会及其职能部门构成,对高校进行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坚持政治原则,把握政治方向,对学校重大问题行使最终决策权等;行政系统由校长和其领导的副校长、校长助理等组成的校长办公会议,以及各行政职能部门、各院院长等构成,执行党委决策和学术系统的学术决议等;学术系统由教授、副教授等教师组成的学术委员会、教授会、学位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等构成的学术组织系统,参与或自主决定学术事务;社群系统主要指其他教职员工、学生等组成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等,他们有限参与或监督评价其他系统的工作。与这四个系统相对应的高校内部权力就是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民主权力等。[9]总的来说,这些高校内部权力类型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高校内部权力构成的复杂性,但它们的共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即都将高校看作是一个由多元主体及其多元利益、多元关系、多元活动构成的利益相关者组织,高校内部的多元权力某种程度上源自于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差异。由于制度、法规、传统的差异,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高等学校的利益相关者构成也会略有差别,就我国而言,高校内部的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学校党委会及党员群体、以校长为首的行政管理人员、教职员工群体、学生群体等,由此也就形成了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不同权力类型,相应地有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学生权力。此外,在高校的共同治理中,多元主体不只是分权分工的,同时也强调共同参与,强调民主监督,因而,在高校内部权力中还包含一种民主参与权力类型。从现代高等教育的角度来说,作为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高校的多元权力源自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但是,从历史发展和当代实践的角度来说,高校内部权力的来源和依据又具有深刻的历史内涵和鲜明的国别特色。
二、我国高等学校内部权力的来源与依据
高校内部权力是由多种多样的权力类型构成的,但这些权力并不是从大学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的,而是随着大学组织的发展,以及外部社会环境的变化,在不断发展的多元利益关系互动中形成的。因此,高校内部权力具有不同的发展来源和合法性依据,对我国高校内部权力而言,亦是如此,只不过发展来源和合法性依据更多地体现在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的体制特点、发展目标、政策法规以及文化传统中。
(一)政治权力
大学的组织发展史表明,大学内部首先由教师与学生构成权力关系,逐渐形成了学术权力、学生权力,并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科层制的形成,行政权力也开始产生。然而,自中世纪以来,大学开始受到外部教会势力与世俗政权的双重影响,并因其不断发展的知识创新能力,或沦为教会的“婢女”,或成为国家的“知识之翼”。因此,恰如布鲁贝克所说,“高等教育越卷入社会的事务中就越有必要用政治的观点来看待它”[10]32,因为“当高等学府卷入日常生活的时候,必然会遇到如何确定目标和如何行使权力来实现这些目标的争论,而这些争论自然具有政治性”[10]15。高等学校中的政治权力日益凸显,是高等教育政治属性的必然体现,是高等学校所有者基于国家或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而对高等教育所形成的影响力。当前世界各国对高校均施以不同程度的政治控制,就具体的组织形式而言,从直接到间接,主要有党委会、学监、董事会以及调查委员会等几种形式。[11]就我国而言,党委会是高校政治权力的主要行使机构,其权力主要来源于高校党委会的上级党组织的授权,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高校政治权力更确切的是指党委权力。这种高校内部权力不仅存在于党组织之中,还是我国高等教育立法的核心内容。我国《高等教育法》非常明确地规定:“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12]这一高校政治权力的组织形式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多次改革与完善,已经成为我国一种成熟稳定的高校领导体制。不过,由于这一领导体制融合了政治权力与行政权力,而党委与校长之间的权力界限并不清晰,党委权力常常像行使行政权力一样做出各种校务决策,以至于有学者指出,我国高校的“政治权力不过是一种行政化的权力,在大学发挥作用的方式及其所作用的对象与行政权力并无二致,只不过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更大的行政权力罢了”[13]。近年来,加强和完善党委领导一直是我国高校领导体制改革的重要主题。2011年7月,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制定章程暂行办法》,要求以章程“规范学校党委集体领导的议事规则、决策程序,明确支持校长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的制度规范”[14]。2014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对党委与校长实现党政分工、协调运行提出了一系列的实施意见,要求党委统一领导学校的路线方针与教育方针、基本管理制度、人才干部、思想政治与德育、基层党组织建设等工作,支持校长主持学校行政工作,健全党委和行政议事决策制度,使党委议事决策和校长行政办公有章可循,完善协调运行机制,使党委与校长有效沟通与协调等。[15]党中央的实施意见以及高等学校陆续制定的章程进一步确立了我国高校政治权力的合法依据。
(二)行政权力
行政权力一般指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力,行政权力是依据国家宪法及相关法律,以强制性手段执行国家意志,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能力,但也常常用来指一般社会组织的行政机构和人员为了实现组织目标,依照组织的规章制度对组织自身进行管理的能力。现代大学拥有完善的行政机构体系和专业的行政人员,因此,行政权力也是高等学校中的重要权力类型之一。不过,行政权力的形成与高校的组织规模以及外部社会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一般而言,当一个组织的规模发展到需要进行劳动分工,并由于各项分工中的能力高低而产生等级时,科层制就产生了,而行政权力即来源于科层制。当学者行会或中世纪大学发展到现代大学的规模,因学科分化而产生了院与系,教学安排、学生管理、财务运作、后勤服务、对外联系等需要专门人员来负责时,大学开始形成科层制:理性的规章制度、劳动效益分工、职务等级分权、行政管理档案制度、专业训练、职业化取向等。因此,高校行政权力主要源于其自身组织的科层制发展。不过,现代大学均须接受政府的监督与控制,在由政府直接控制的现代大学中,行政权力由政府授予,对上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类似于政府科层组织的一个层级。就我国公立高校而言,其行政机构具备政府科层组织下一层级的某些特征,不同类型的大学拥有不同的行政级别,如副部级、正厅级、副厅级等等。因此,我国高校内部行政权力一方面是源于现代大学的组织规模发展对办学效率的要求,另一方面则是源于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授权,以便于控制高等学校贯彻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我国高校行政权力来源于政府授权,其中,《高等教育法》是授权依据的主要法规:“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管理由国务院确定的主要为全国培养人才的高等学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高等教育事业,管理主要为地方培养人才和国务院授权管理的高等学校”。[12]同时,国家和地方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有权任免高校主要行政负责人——校长、副校长等。所以,由于我国高校身处中央政府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下属科层组织地位,其行政权力更多的是源于上级政府的授权。不过,值得指出的是,由于高等学校是教育与学术组织机构,高校行政权力的行使与其他政府组织机构有所不同,它更强调遵循高等教育的办学规律,因此,政府不能任意下放或收回对高校的授权,而这也就形成了我国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概念。在我国高等教育法中规定的若干办学自主权中,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行政权力。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自主行政权力也进一步在高等学校章程中得以彰显。
(三)学术权力
众所周知,现代大学源于中世纪大学,而中世纪大学在早期是一个学者行会,在这个“学者共同体”中,教师因其掌握的专门知识或高深学问,广泛地控制着大学中的学术活动。这种基于知识的权力通常被概括为“知识即权力”,意思就是说,在任何领域,决定权应该为有知识的人共享,知识最多的人有最大的发言权,没有知识的人无发言权。[16]174随着专门知识不断丰富和分化,学科成为不同专门知识的主要载体,而教师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内依然保持着这种权力。伯顿·克拉克对欧美各国高等教育系统的权力构成进行考察后,即把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及教师拥有的学术权力称为“扎根于学科的权力”。因此,从中世纪大学的发展演变可知,学术权力主要源于教师的专门知识和高深学问,而且它们日益学科化。此外,教师在这种发展知识的学术活动中达成了一项共识——学术自由,学者可以自由地探究知识,追求真理。这项共识也成为高校内外部对于学术权力的共同理解,保障学术自由即是保护学术权力,国家与社会主要通过法规和制度予以保障,如德国宪法对于学术自由的保护,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对于学术自由的制度化推动。就我国高校而言,一方面大致遵循着“知识即权力”的基本规律,教师始终是学术权力最广泛的掌管者;另一方面则通过法规保障学术自由承认学术权力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如《高等教育法》规定:“国家依法保障高等学校中的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12]2014 年1月,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也规定:“高等学校应当依法设立学术委员会……并以学术委员会作为校内最高学术机构,统筹行使学术事务的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等职权”,“遵循学术规律,尊重学术自由、学术平等,鼓励学术创新……”[17]关于高校教师个人的学术权力,则涵盖在教师权利之中,这在我国《教师法》中有具体规定,教师享有“进行教育教学活动”,“从事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参加专业的学术团体”,“指导学生的学习和发展,评定学生的品行和学业成绩”等一系列权力。总的来说,我国高校同样遵循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学术权力主要来源于教师的专门知识和高深学问,遵循“知识即权力”的学术规律,国家高等教育法规对高校组织和教师个人的学术权力予以保障。
(四)学生权力
从大学的起源来说,学生权力几乎与学术权力一同诞生,不过,学生并不拥有像教师那样的学术权力,他们的权力更像是一种权利,即一方面是一种接受高等教育应有的正当权利,如他们的受教育权和他们提供学费、时间、精力等投入而应获得的“收益”;另一方面则是学生在大学事务中发挥的作用,如参与大学教育教学以及校务管理等。因此,在最早的“母型大学”中,除了闻名遐迩的教师型大学——巴黎大学外,还有一所学生型大学——博洛尼亚大学,体现了学生在中世纪大学中的不同权利与地位。在博洛尼亚大学,学生像巴黎大学的教师一样掌管了学校的一切权力,学生自治组织管理校务,招聘和解聘教师,甚至有权决定教师开设什么课程。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学生多数是成年人,且其中部分学生担任重要的社会职务,具有显赫的社会地位和殷厚的经济财富;其二,大多数教师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学生学费,学生可以借此控制教师。[18]50-51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大学在激烈的生源市场竞争环境下形成了“学生消费者至上”的理念,尊重学生通过学费获取知识的消费者权益,而这极大地改变了美国大学的学生生源结构、招生方式、教育内容、教学方式以及学生参与校务管理的制度与规则等。克拉克·克尔曾经评述指出:“这种从注重学术的价值到注重学生消费者的转变是美国高等教育历史上两次最重大的方向上的转变之一”。[19]280因此,现代大学中,学生的受教育者身份和“消费者”权益仍然是学生权力的重要来源依据。此外,学生在学术自由传统中享有学习自由,也是学生权力的来源之一。随着社会的进步,学生权力的来源已被法律化和制度化,体现在世界各国相关法律和大学章程中。就我国而言,在20世纪90年代即制定了《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规范了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权利与义务。2005年,该《规定》重新修订,高校管理权力与学生权利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定的转变,“依法治校”的原则得以体现,学生的实体和程序权利进一步明确,高校的管理权力受到严格的程序规范,“高校权力本位”开始向“学生权利本位”转变。[20]2011年,教育部下发《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其中要求各大学制定章程应当体现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保障学生的正当权益。目前,各大学制定的章程中大都专门列有学生权利条款。因此,现代大学的学生权力主要源于学生的受教育者身份及其“消费者”权益,并由国家法律与大学章程予以制度化保障。
(五)民主参与权力
现代社会中,无论是公立高校还是民办高校,它们都具有公益性,这是其本质属性之一。从利益相关者理论来看,高校没有特定的所有者,它的所有者即它所在国家的人民或社会。因此,高校是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由内而外,教师、学生、管理人员、职员、校友、企业、社团、社区、政府等都是高校的利益相关者,他们均有参与高校事务管理的权力。但是,民主参与权力并不像高校内部其他权力一样具有历史传统和制度保障,它更多是源自于现代政治文明的一种理念——民主,民主的要义之一即是所有人平等地共享权力。显然,现代高等教育系统的权力结构均基于民主理念之上建立,因而,利益相关者拥有分享高校内部权力的正当性。一般来说,高校内部的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学生权力的运行必须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公开透明。只有在权力主体完全公开其权力行使的程序、过程与结果,毫无隐瞒地呈现权力运行的一切信息,其他人员才能分享和监督这些权力,而这也正是高校的民主参与权力的合法性来源。现代大学制度提倡“共同治理”,其实质就是在合法分权基础上公开行使权力,提高权力运行过程的透明性,从而使得大学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均有机会通过知悉、评议、建议甚至一定程序取而代之等方式共同分享权力。就我国而言,自1985年国务院出台《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来,关于建立健全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加强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改革理念就成为高校民主管理的指导方针,此后,《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高校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具有民主参与高校管理的合法权力。不过,由于没有完整的有效参与的程序制度,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等民主参与组织的职能履行有限;更由于我国高校内部权力运行不甚公开与透明,没有完善的监督问责机制,若非权力机构成员,对高校权力的运行过程几乎毫不知情,更别谈民主参与管理。高等学校章程的制定是落实非权力机构成员民主参与校务管理的重要依据,但民主参与权力的彰显仍然有赖于高校切实落实《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和《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建立有效的大学内外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监督问责机制。
三、我国高等学校内部权力的属性与差异
从整个社会系统来说,高等教育管理权力是维系社会秩序及其发展的社会权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与其他社会权力相同的一般属性,如强制性、等级性和功利性等。[21]高校内部权力是高等教育管理权力的一部分,同样具有其他社会权力的一般属性,事实上,它们在权力的产生、分配、运行等环节呈现出不同的属性特征,体现出高校内部权力的多元差异。
(一)高等学校内部权力的内生性与外铄性
从权力产生的角度来看,高校内部权力具有内生性和外铄性之分,即高校内部权力主要是通过内生和外铄两种方式形成的。所谓内生性,即是指部分高校内部权力产生于高校承担着某些内在的、永恒的人类追求,如探索真理,传承文化,培育青年等不同于其他社会组织的本质功能;而外铄性,则是指部分高校内部权力产生于与社会和国家的契约关系,如创新知识与技术、培养统治者接班人、教化社会等。因此,高校内部权力一部分产生于自身的内在功能,一部分产生于外部组织的契约授予。显然,从大学的组织发展历程和本质功能来看,在高校内部权力中,学术权力与学生权力源于大学组织的发展与传承知识的内在需要,因而具有内生性;而行政权力、政治权力以及民主参与权力则主要是外部社会与国家的某种契约性要求与赋予,因而具有外铄性。从学理上说,行政权力可以认为是源于大学组织自身发展规模扩大、学术事务与行政事务日渐分离、组织管理效率需要提高等因素。因此,有学者指出,大学的行政权力是由原本浑然一体的学者权力分化让渡形成的,大学行政权力是大学内生的一种权力。[22]这一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行政权力更多的时候受到政治权力的支配,而且,政治权力往往依托行政权力的科层结构进入高校的内部权力结构。就现代大学的形成而言,也正是由于国家的政治权力介入,才推动了中世纪大学的世俗化,由宗教“婢女”转变为人类社会的“知识之翼”。因此,高校的行政权力更多的是与政治权力结合,由国家外铄形成。民主参与权力与其他四种权力类型的产生属性皆有不同,一方面,民主参与是大学从学者行会起就形成的古老传统,内生于“一人一票”的行会民主;另一方面,民主参与更多的时候是一种监督问责权力,因而需要制定有效的参与机制,否则,民主参与只会徒具形式。因此,民主参与权力更像是一种内生与外铄共同作用的权力类型。在我国高等学校中,党委权力、行政权力具有强烈的外铄性,皆来自于党组织和政府授权,甚至民主参与权力也需要党组织和政府出台政策法规予以保障,学术权力与学生权力虽然具有内生性,但往往被视为一种可管制的自主权而受到党政权力的干预。
(二)高等学校内部权力的等级性与平等性
从权力分配的角度看,高校内部权力具有等级性与平等性之别。高校行政权力与政治权力总是依赖科层结构运行,而科层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等级分权。因此,高校行政权力和政治权力在分配过程中,按照科层结构的组织机制,将权力逐步分配给校、院、系各级行政机构,并形成了各级机构遵循逐级对上负责的权力等级原则。由此,高校行政权力与政治权力具有等级性,其权力运行路径是自上而下的。而学术权力、学生权力以及民主参与权力则不同,学术权力源于学者探索知识与真理的自主活动,学者之间虽有知识水平的高低,却没有权力大小之分。在最常见的学术权力机构——诸如教授会、评议会、学术委员会等组织中,学者之间通常遵循“一人一票”的学术权力行使原则。学生权力源于学生受教育者身份,每一位学生都享有平等接受高等教育、参与校务管理的权利。因而,学生权力并不具有等级性,而是与学术权力一样,具有普遍的平等性,所有学生都平等地享有此权力。民主参与权力更是现代社会民主进步的表现,现代大学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关涉高校内外部利益相关者,高校各个层次的利益相关者均平等地享有民主参与高校管理的权力。因此,学术权力、学生权力以及民主参与权力具有平等性,它们的权力运行路径是平行的。在我国高等学校中,党委权力与行政权力具有鲜明的等级性,无论是高校党委书记、各学院党支书记还是校长、副校长、各处科负责人以及各学院院长都具有行政级别,整个高校党政体系与政府部门行政体系几乎是一致的。学术权力、学生权力以及民主参与权力是平等的,学者与学者之间即使存在学术水平高低之分,但不是权力大小之别,学生之间更是一体平等,几无差别。
(三)高等学校内部权力的强制性与协商性
从权力运行的角度看,高校内部权力还具有强制性与协商性的差异。从上文可知,高校政治权力与行政权力由国家与社会外铄形成,按照科层结构的等级制度自上而下运行,而且依照规章制度严格行使权力,如在具体的高校权力运行过程中,校一级的党政机构有权要求院系一级的党政机构执行上级做出的决议,也就是上级机构有权通过强制命令的方式要求下级执行自己的方针政策。因此,高校政治权力与行政权力具有强制性,这种强制性可以有效地保障高校外部社会与国家的意志贯彻于高校管理之中。但是,高校作为一个以教育性和学术性为本质属性的学术机构,过多的强制性权力只会损害高校的“学术自由”。高校的学术权力、学生权力以及民主参与权力等由于其分配的平等性,在运行时更多地通过对话、协商等方式实现。具体来说,教师群体、学生群体以及一般普通民众主要通过民主协商的形式行使学术权力、学生权力以及民主参与权力。因此,这些权力的运行具有协商性的特征。在我国高等学校内部权力运行中,党政权力的强制性表现得非常突出,甚至长期存在着干涉学术权力、学生权力以及民主参与权力的现象,譬如高校管理过度“行政化”。造成“行政化”过度的原因,一方面源自高校内部权力集中于政府和高校党政负责人,他们掌握着高校事务所有的甚至包括学术事务的决策权;另一方面,由于政府高等教育行政管理政策变化快,高校管理必须高效率地与之相适应,党政权力因其强制性而具有极高的运行效率,从而日益“越俎代庖”,使“行政化”充斥于高校管理之中。我国高校管理改革的主要方向是消解过度“行政化”,促进学术权力、学生权力以及民主参与权力的彰显。为此,近几年来,尤其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以来,推动“高等学校章程建设行动计划”,全国高校纷纷制定大学章程,依据教育部出台的《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建立完善本校学术委员会,拟定学术委员会章程,为保障学术权力等协商性权力提供了有效的可行的法规依据。
总而言之,高等学校作为一个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多元利益决定了高校内部权力的多元多样,而这些权力类型又产生于大学组织发展的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发展来源和合法性依据,并在产生、分配与运行等环节具有不同属性的差异,因而,高校内部权力在运行与制约过程中难免会产生深刻的矛盾冲突,成为高等学校管理永恒的难题。
[1]约翰·范德格拉夫.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M].王承绪,张继平,徐辉,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2]别敦荣.我国高等学校管理权力结构及其改革[J].辽宁高等教育研究,1998,(5).
[3]张德祥.高等学校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4]周光礼.问题重估与理论重构—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二元对立质疑[J].现代大学教育,2004,(4).
[5]谢安邦,阎光才.高校的权力结构与权力结构的调整[J].高等教育研究,1998,(2).
[6]毕宪顺.决策·执行·监督—高等学校内部权力制约与协调机制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
[7]张维红.大学三种权力的历史、现状与反思[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
[8]秦惠民.我国大学内部治理中的权力制衡与协调—对我国大学权力现象的解析[J].中国高教研究,2009,(8).
[9]刘献君.论大学内部权力的制约机制[J].高等教育研究,2012,(3).
[10]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郑继伟,张伟平,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11]杨克瑞,祁型雨.高等学校的政治权力及其监督[J].复旦教育论坛,2007,(5).
[12]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EB/OL].[2016-08-18]. 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 moe_619/200407/1311.html.
[13]别敦荣,冯昭昭.论大学权力结构改革——关于“去行政化”的思考[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1,(6).
[14]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EB/OL].(2012-01-09)[2016-08-18]. http://www.gov.cn/flfg/2012-01/09/ content_2040230.htm.
[15]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EB/OL]. (2014-10-15)[2016-08-18]. http://www.gov.cn/xinwen/2014-10/15/content_2765833.htm.
[16]伯顿·R.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王承绪,徐辉,殷企平,等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
[17]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EB/OL].[2016-08-18]. 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 s7964/201402/xxgk_163994.html.
[18]贺国庆,王保星,朱文富,等.外国高等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19]黄福涛.外国高等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
[20]罗爽.从高等学校权力为本到学生权利为本——对公立高等学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分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
[21]别敦荣.论高等教育管理权力[J].高等教育研究,2001,(2).
[22]李从浩.中国大学行政权力的合法性限度[J].高等教育研究,2012,(5).
[责任编辑:罗雯瑶]
On the Composition, Origin and Nature of the Internal Power i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in China
TANG Han-qi
( Institute for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
The modern institution of higher learning is a typical stakeholder organization involving multiple parties. The interest relationship is the foundation of power relations, and the multiple interests determine the diversity of pow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keholder organization, the institution of higher learning includes the CPC committee and CPC members, president of the university, staff and students, etc. So, the university includes the political power, administrative power, academic power, the students' power and the power of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From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the university, the internal power produced at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has different historical origins and legitimacy basis. They show different attributes because of the diversity of the internal power and its differences in the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operation. Generally speaking, the university's internal powers are endogenous and exogenous, hierarchical and equal, mandatory and negotiable.
the internal power of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composition; origin; nature
唐汉琦(1986—),男,湖南绥宁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理论与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校内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4JZD05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G647
A
2095-7068(2016)03-0001-08
2016-0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