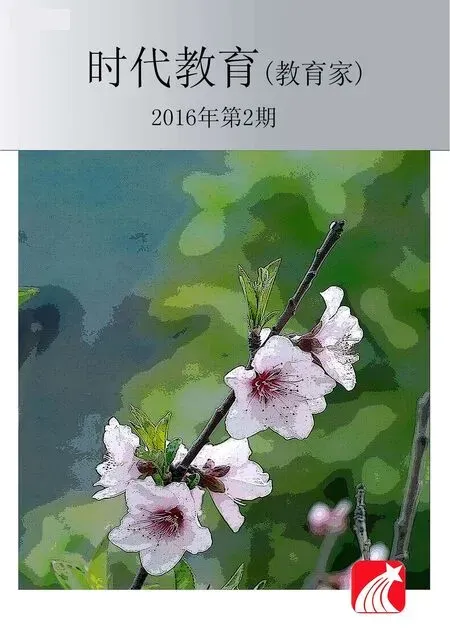蒙学之争
——“《弟子规》的传播是一场骗局”?
本刊记者_张艺芳 四川成都报道
蒙学之争
——“《弟子规》的传播是一场骗局”?
本刊记者_张艺芳 四川成都报道
编者按:
《弟子规》,是清人根据圣贤之学的再创作,创作者李毓秀为当时秀才,卒于雍正年间。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因此,“弟子”二字含义不仅针对儿童,成年人同样适用。《儒林外史》,成书于乾隆年间,比《弟子规》稍晚,作者吴敬梓出身望族,但反对科举制,憎恶士子们热衷功名利禄。有人荐举他入京廷试,但他 “坚以疾笃辞”,从此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至晚年,饥寒交迫。其中 “范进中举”最为人熟知。《儒林外史》,可说是刻画了当时 “弟子普遍无规”的社会现象,因而《弟子规》的流传,有其相应的社会历史渊源。
2015年11月,黄晓丹在首届“儿童传统文化教育论坛”上发表演讲:《“弟子规》在最初的使用环境是祠堂、茶馆、书馆,使用对象是干完农活的成年人,适用范围是社会下层。”且《弟子规》毫无童趣,只教以规范。不久,《新京报》发文《弟子规的传播是一场骗局》。
本刊以此为契机,试图探讨一下《弟子规》的当世之用应当如何展现,是否需脱离 “蒙学”的范畴,抑或是无辜被成人见解妖魔化的经典类文本?
记者采访了从事儿童传统文化的教育者,也搜集了一些历史学者的研究,供读者兼听。
《教育家》:《弟子规》是否适合如今的儿童?
吴梅(允元小学馆创办人):
黄晓丹那篇文章我浏览过,当看到一些事实错误的时候,就没细看下去了。至于它是不是专给底层人民做规范用的,黄晓丹有她的考证,我没有研究,不好评论。好吧,就算我们认可这个结论,那么,是不是给底层人民做规范用的,就不适合孩子?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问。
文化断丧百年后,不要说今天的孩子,就说今天的成人,我们真的自信自己的基本修养高过传统中国的基层百姓吗?如果谦卑一点,我们可以扪心自问:在《弟子规》面前,我们是高于它还是低于它?
《弟子规》是可以读的。不仅可以读,而且要付诸行,或者更准确地说,首先要付诸行,而且首先还不是为师者要求孩子付诸行,是为师者要求自己付诸行。
当然,在我自己的教学中,没有设置《弟子规》的课程。这并不是我鄙薄它,而是因为,作为一个周末读经的小学馆,我没有足够的时间给到它,在有限的时间辖制下,我有更重要的功课要给到孩子,那就是真正的“经典”。
《弟子规》是蒙书,不是经典。
我做的是读经教育,不是国学教育。什么是经?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传统中国人那里,是很清楚的,是不会有第二个回答的,只是到了现代人这里,因为不学无术,它才成了一个问题。经,很清楚,在传统中国那里,就是四书五经,扩而言之,说十三经亦可。之后,儒释道三家融合,经典的范围得到扩展。到了近现代,诸文明继续合流,中华文明又迎来新的可能性:中西会通。这种情况下,经典得到了又一次扩充和丰富,将西方文化的重要经典也包括进来。读经教育,就是在这样广阔的胸怀和这样具包容性的教育哲学下所展开的一种教育。我们要读的经,包括“老庄”,包括“佛经”,包括《圣经选》,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
回到《弟子规》。“孝弟三百千千”,即《孝经》《弟子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它们是“蒙书”,不是经典。
我们允元小学馆从一开始就立志做读经教育,但目前我们也开设了一个童蒙班,只是教的不是《弟子规》,是《千字文》和一些古诗词。这是应一些朋友的请求开的,他们的孩子想到我这里来读书,又觉得读四书五经孩子会不会受不了啊,请求从童蒙读起。我们做了一个实验,同时开了一个《论语》班,一个“童蒙班”,现在,一个学期结束了,实践结果确如王财贵先生所说:高度的涵盖低度的,低度的涵盖不了高度的。
一个读了《弟子规》的孩子,读不了《论语》,而一个读了《论语》的孩子,去读《弟子规》却很容易,只不过他已经不需要读《弟子规》了。这里有两方面意义可以展开说。从智力角度说,《弟子规》和《三字经》是简单的韵文(三字反复),对于孩子的记忆能力和脑容量要求很小,《论语》是散文,散文并非没有节奏,只是节奏很复杂(这种区别,就相当于一首交响乐和一首钢琴小品的区别)。一个孩子如果把较复杂节奏的散文读背刻在大脑里,他大脑的发展程度显然和一个读三字节奏的孩子大脑是不同的。事实就是,一个背下了《论语》的孩子,玩儿着就地把《弟子规》搞定了。
再从修养的角度说。大经和蒙学读物,一个是义理,一个是对义理的应用,明了义理,开用是相对容易的,但有了用不懂后面的义理,却有可能在用的过程中出问题,比如,僵化,比如,对身心造成束缚。《弟子规》定了很多明确的规矩,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挺好,让人知道如何措手足,但,仅仅这样,不够。我们有一个公益性的“青年读经班”,上节课正好读到《论语·子路第十三》,其中有一句“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硁硁然,就是像小石头那样坚确,不懂机变。真正的君子应该怎么样呢?孟子说了,“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懂了义理,再去规范行为,处事更可以灵活机变。
当然,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更多是处于“使由之”,而不是“使知之”的阶段,所以《弟子规》是不错的。只是,我们是不是要把它放一个这么高的地位上去看待?我们需不需要花那么大力气去学?这个可以讨论,可以实践。
《教育家》:如果儿童有学习传统文化的打算,其间的次第又是怎样的?
吴梅:在允元小学馆的学习规划中,第一学期,是诵读《论语》。第二学期,诵读《大学》《中庸》的时候,我会给他们再加一些《诗经》润一下。
儒家讲本末,现在有很多人是在“末”上下功夫,去读一些词。有位家长被读幼儿园的女儿问及“寒蝉凄切”中,“什么是凄切?”家长无言以对。
我要把国学教育和读经教育分开,国学教育是所有的国粹就要拿过来。读经教育是要抓住根本的经,给人的心性、智力打下基础,有责任感在那里。光芒的发出是你要有那个根本,稍微触发,就放出来。但是你没有这些根本的时候,你只拿那些末梢的东西去刺激他,很可能孩子会走偏。
我的次第,就是从最根本做起。就像一个家庭主妇,要做一桌菜,首先,要先有白开水、大米和阳光,然后才有维生素。现在多数国学教育做的就是拼盘,讲究怎么样把一个菜摆得好看,这是求其次而又其次的事情。如果做出的菜,不堪下嘴,对人的营养毫无用处,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
《教育家》:在目前的教育界,让孩子自由去生长的理念很盛行,“儿童本位”是筛选教材和实施教学的唯一标准,你认同吗?
吴梅:儿童本位,或许是大人本位,家长觉得什么适合、不适合孩子,然后去教育孩子。孩子喜欢重复,小时候听一个故事,百听不厌。我儿子小的时候,你问他,“这个音乐,喜欢吗?”他回答,“我没听过”。孩子对于熟悉的东西,才会谈喜不喜欢。
记者后记:
关于“五四”,其中最有名的一个论断是上世纪80年代李泽厚提出来的——“救亡压倒启蒙”,意思是说,“五四”这件事半途而废了,原因是当时民族主义高涨,为救国,需强调国家之重要性,个人的权利被忽视了。
同样是李泽厚先生,十多年以后,又提出一个主张,叫作“告别革命”。这个“告别革命”纳入当时的保守主义话语,就兴起了另外一股对“新文化运动”的否定,说“新文化运动”的问题是太激进。如果太激进的问题值得反思,这就不是启蒙被压倒的问题,而是“启蒙”的定义本身是否合适都成问题。而时移世易,我们如今要问的是——“启蒙”与“蒙学”只是针对幼儿吗?
所以就回到了对《弟子规》的争论本身,幼儿成人可同为“弟子”,一本《弟子规》,成人之用与幼儿之用,必有不同,承载如此多的“成人见解”是否合适?要知道,成人,生理上来说只是“长大的幼童”;而心理上,如今很多成人也难以摆脱幼童的心理状态,所以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