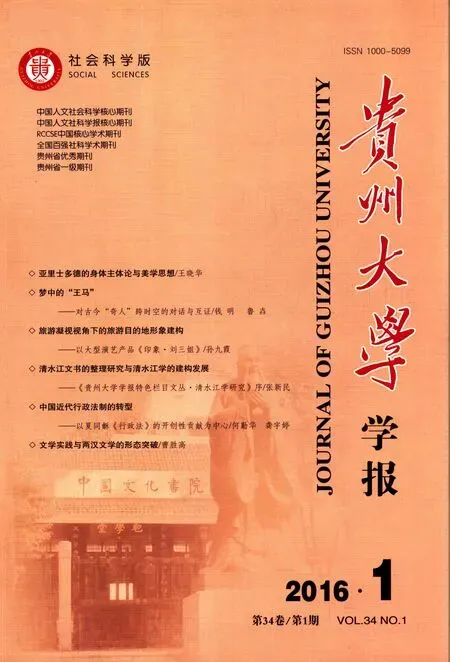亚里士多德的身体主体论与美学思想
王晓华
(深圳大学 文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亚里士多德的身体主体论与美学思想
王晓华
(深圳大学 文学院,广东深圳518060)
摘要: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把身体界定为具有感受—行动能力的主体,并因此提出了重视身体的美学观点。这套话语内蕴着一种研究范式,深刻地影响了此后西方美学的建构——从托马斯·阿奎那到舒斯特曼,有关身体积极意义的言说延续至今,被不断纳入到美学(感性学)话语中。不过,亚里士多德的身体主体性理论未超越二元论,不乏自我矛盾之处,因此,其对后世的影响也具有明晰的双重性。只有超越亚里士多德身体主体论的暧昧品格,美学才能踏上回家的路。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身体;主体论;美学;二重性
在1992年出版的专著《实用主义美学》中,美国学者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写道,西方主流美学理论忽略了“身体的主体角色”(the body’s subject-role)。[1]274这种说法可能令某些熟悉西方美学的人感到诧异:依据广为人知的概念谱系,主体性不是专属于精神(灵魂或心)吗?身体又焉能进入主体的行列?要消除此类困惑,我们就必须敞开西方美学史中一个久被遮蔽的线索:早在古希腊时期,大哲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就曾强调身体具有主体性,并据此提出了重视感性活动的美学研究范式。对于研究美学的人来说,它可能意义重大:如果美学是鲍姆嘉腾(Alexander Baumgarten)所说的感性学,那么,它必然牵连出相应的“身体话语”(the discourse of body)——没有身体,何来感性和感性学?进而言之,如果身体是一种主动性的存在,那么,它是否会参与审美活动?倘若会,又在多大程度参与?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将重构亚里士多德的身体主体性概念,敞开内蕴于其中的美学研究范式,探寻它对后来者的影响。
一、感性活动的特性与身体主体性概念的提出
在提出美学概念时,鲍姆嘉腾曾经给出了这样的定义:“美学作为自由艺术的理论、低级认识论、美的思维的艺术和与理性思维类似的思维的艺术是感性认识的科学。”[2]13由此可见,美学(Aesthetics)这个词的原初意思就是感性学。于是,有关美学的思辨必须回到一个根本问题:感性认识如何可能?
从逻辑上讲,感性认识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存在能感—可感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是如何建立的?它是否可以超离身体?
当笔者面对一颗树时,后者与身体的关系会明晰地显现出来:它距离笔者3米远,比笔者高2米;被微风浮动的枝干映入眼帘,耳朵听见叶片沙沙的响声,鼻子嗅到汁液的芳香;走上前去,双手会感受到它的硬度,躯干能体验到树身的坚实。在此过程中,笔者的身体性(embodiment)也显现为不可忽略的存在:倘若人没有身体,假如身体不与其他事物打交道,这一系列感性认识就无从谈起。那么,感性认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身体相关?


原初身体是主体。主体性的身体可以直接与外物打交道。承担外部运动是身体实现主体性的基本方式。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运动有两种:“(1)自身能运动的,例如身体的部分,或者船身的铆钉;(2)自身不能运动,永远是附随着运动的,例如白和学问,因为它们变换了空间是由于它们所属的主体变换了空间。”[8]101那么,身体所能承担的运动是什么呢?在解释主体性这个概念时,亚里士多德曾说:“一个人不能被称作行走或运动,而说他是行走或运动的。”[9]271作为外部运动的一种,行走的承担者是身体:“正是通过双腿的特定运动,人才以自己的方式行走……”[7]138当身体行走时,它所涵括的灵魂也随之“变换空间”。[8]245虽然这不意味着身体比灵魂优越,但至少证明它具有运动能力。除了行走之外,身体还能以更复杂的方式参与空间运动。譬如,织布或造屋。与自然物不同,布匹和房屋产生于人类的劳作。虽然身体的活动“应于灵魂”,但它不可能全无主动性,否则,身心之间就不存在联合关系。在织布或造屋时,人类身体是行为的承担者,显现为外部运动的原因:“没有实体就既没有属性也没有运动,故而万物都有相同的原因。进而言之,这些原因或许是灵魂和肉体,或者说,是理智、欲望、肉体。”[9]365
那么,身体为何具有石头和树所缺乏的主动性?亚里士多德的答案是:“凡具有灵魂而不是固定(能移动)的躯体,绝都不能没有感觉。”[6]170有了感觉,人才可能在触及事物之际捉摸它们,恰当地调整自己的行动,因此,拥有诸种感觉乃是获致“优良生活”的必备前提。[6]170-171在阐释与身体相关的主体—客体关系时,亚里士多德着力最多的是感觉问题,曾于《动物诸短篇》中设专章论述之。[6]191根据他的推理,诸感觉中最重要的是触觉:“所有的身体都是能触摸的,即,通过触摸而感觉,动物的存活需要其身体有能力触摸。其他感觉,如嗅觉、视觉、听觉,其感应需要经过其他事物,但均以接触为前提。没有触觉,它将无法回避某物并获得他物。倘若如此,动物必将无法存活。”[7]218能触摸的身体能够可以分辨硬与软、冷与热、湿与干,绝非纯然被动的容器。[7]202由于触摸的对象繁复多样,相应的触觉必然“具有中和的性质”。[7]220故而,动物的身体构造不可能是简单的。没有分化的身体构造,就没有相应的感觉机能。器官越复杂,则机能越多,生物就越高级。譬如,手的结构高度分化(由开叉的手指结合而成,手指的关节“构制得适于把握和加压之用”),搭配合理(如五指的短长搭配十分得当),功能多样(抓、握、夹、捏等)。[10]202-203正因为如此,它是使用工具的工具,可以同时拥有许多工具的功能:“这样,手既是枪,又是剑,又是任何其他随心所欲的武器或工具;因为他具备了把持所有这些事物的能力,自身就可能是这些事物了。”[10]202有了灵活的手,人就可以“织布或造屋”,实现自己的主体性。由此可见,高度分化的结构乃是身体主体性的具体依托:(1)感觉一定依赖感觉的器官:视觉之于眼睛、听觉之于耳朵、味觉之于舌头、嗅觉之于鼻子、触觉之于手,均是如此[7]171-183;(2)离开了手和喉咙,人就无法抓取和说话,完成外部运动。[7]179
有所感觉地与外物打交道,乃是身体主体性的体现。如果说审美是一种感性活动,那么,主体性的身体必然参与其中:其一,它与外物打交道,触及并改造之;其二,在触及外物的同时感受之,摄入其基本特性,使人可以对他者进行恰当的认识、评估、鉴赏。正是由于能感受的身体(aesthetic body),才有aetheta(感受)和感性学(aesthetics)。通过此类天才性的洞察,亚里士多德已经敞开了审美与身体主体性的原初关系。
二、身体的主体性及其在审美过程中的作用
从表面上看,亚里士多德并未提出完整的审美学说,但将其零珠散玉般的论述串联起来,我们就会确证:(1)他眼中的审美首先是一种感性活动;(2)主体性的身体在审美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3)审美的结果原初地具有合身体性。
在《诗学》中,他曾提到:“尽管我们在生活中讨厌看到某些实物,比如最讨人厌的动物形体和实体,但当我们观看此类物体的极其逼真的艺术再现时,却会产生一种快感。”[11]47此处,“快感”显然指的是审美愉悦。可兹佐证的是,亚里士多德撰写《政治学》时也说:“在仿照的形象面前感到痛苦或快乐与亲临其境面对真实事物的感受几乎相同,好比一个人面对某人的雕像时倘若仅仅因其优美造型而不因别的缘故而生欣喜,他在亲睹雕像所仿照的原型时必定会同样感到欣喜。”[12]276观看(目睹)实物或仿照的形象会产生快感。这种愉悦与对象实用性无关,源于康德所说的“不带任何利害”的审美鉴赏。[13]显然,如此说话的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两个彼此相关的命题:其一,审美首先是感性活动;其二,引发审美愉悦的是事物的形象而非事物的实用功能。
如果审美是一种感性活动,那么,它必然依赖拥有感觉器官的身体。当身体与其他实在者打交道时,后者就会变成“可感觉物”(sense-object)。这不是一个静态过程,相反,它意味着改造和被改造:“具有感觉机能的事物,潜在地与实际可感觉事物相类似;起初,在潜在与其实现的变化过程中,作用于被作用两者不相类似,末后,作用者同化了受作用者,受作用者和作用者的品质相类似了。”[6]104对于作用—受作用的具体机制,亚里士多德并未专设章节阐释,但仍然提供了可兹利用的线索:“受供养者施其作用(消化)于食物,食物不能反其道而行事,有如木匠施工于木材,这样的功力是不能倒施的;在这过程中,木匠也有所变化,但这仅仅是一点子变化,木材到了他手,一个原来闲着的木匠转化为现刻在忙碌着的一个木匠,从一个不着力的状态转入了着力的状态。”[6]98摄入食物,制作家具,均为主动的活动。主动者改变被动者,被动者接受主动者赋予它的形式和意义。不过,改变并不意味着率性而为:要改变某物,就必须摄入其属性。摄入首先是一种感性活动。对木材进行加工时,木匠打量、触摸、把玩它。这是原初的感性活动。如果说审美隶属于感性活动,那么,它必然与身体具有本质性的关联:“无论是活的动物,还是任何由部分组成的整体,若要显得美,就必须符合以下两个条件,即不仅各部分的排列要适当,而且要有一定的、不是得之于偶然的体积,因为美取决于体积和顺序。”[11]74排列恰当与否和体积大小,皆相对于行动—感觉着的身体而言:其一,行动的意欲不同,有关“恰当”的定义也有别;其二,身体本身的物理学—生理学参数决定了人对于“体积”的感觉。对于第二点,亚里士多德的言说尤其明晰:“因此,动物的个体太小了不美(在极短暂的观看瞬间,该物的形象会变得模糊不清),太大了也不美(观看者不能一览而尽,故而看不到它的整体和全貌——假如观看一个长一千里的动物便会出现这种情况)。”[11]74由于看不清和不能总览全貌,事物才会显得“太小”和“太大”。 在不借助工具的情况下判断大小,人(灵魂)只能以身体的物理存在为基本尺度。如果人身长一千公里,那么,一千公里的事物就不会显得太大。同理,对于只有微生物大小的身体而言,细菌亦是合适的观看客体。正因为人只有数尺之躯,“一指长或者半里长的船干脆就不成其为船了。”[14]显然,亚里士多德不自觉地设定了一个尺度:人类身体。正是以后者衡量万物,它们才有合适与否的问题,“例如一指长或半公里长的船干脆不称其为船了”。[12]237“一指长”的船无法载人,“半公里长的船”难以用人力驱动(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因而满足不了具身性主体的需要。恰如梅洛-庞蒂所言:“习惯于一顶帽子、一辆汽车或一根手杖,就是置身于其中,或者相反,使之分享身体本身的体积度。”[15]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大与小都以人类身体为尺度。此时,“人是万物的尺度”具体化为“身体是万物的尺度”。只有适合身体尺度者,方为合适,才谈得上美。相对于身体,万物具有大小、秩序、确定性。换言之,秩序、对称、确定性皆为具身性概念:正是相对于这个劳作或静观的身体,周围事物才会成形为一个属人的体系,才会凸显出其相对于身体而言的大小、多寡、湿干、冷热、轻重和有序性。借助从属于这个体系中的某些工具,身体可以超越自己的生理学局限:“倘竟有一延伸不断的长管从视觉所在处直通于事物,在远处的事物将可看得清楚了,这样,所有从那事物来的活动将全不分散;若说这是不可能的,那么这管总是延伸得越长,那远处的事物就可看得愈精审。”[10]614循此理路,我们也可以说,如果配备显微镜,“太小”的事物就会变得正常。事实上,望远镜和显微镜都是“我们身体的延伸”[16],它们的功能恰恰说明了感性活动(当然也意味着审美行为)的具身性(embodied)。
那么,审美的具身性是否意味着它从属于实际活动?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是:“善永远居于行动中,美则可以存在于不运动的东西中。”[9]400从逻辑上讲,观照“不运动的东西”意味着美善之别:如果说善只能通过运动来实现的话,那么,审美则可以体现为对“不运动”之物的观照。当然,“不运动”是相对的:在亚里士多德的体系中,除了完成使命后的第一推动者外,万物皆动。显然,仅仅相对于观察者来说,某物处于相对静止状态。在审美活动中,这意味着机缘:面对静止之物,人会暂时放弃功利性态度,更从容地打量它,将它的形象尽收眼底。譬如,当忙碌的木匠静了下来,仔细端详产品的具体形态,便会欣欣然陶醉于其秩序、对称、确定性。[9]270此时,他已经升格为审美主体,所注重的则是对象的形式因素。显然,审美至少意味着身体劳作的暂时中断:(1)当且仅当忙碌的个体闲下来时,他/她才会静观自己的作品乃至整个世界:(2)只有功利性诉求暂时退到意识的边缘,万物的形式才会凸显出来,人才会沉浸于审美快乐之中。正是出于上述考虑,亚里士多德才认为审美与演练数学接近。数学是形式化的演绎,审美体验着眼于事物的形式化因素。恰如数学操作,审美活动也可以升格为独立的演绎,进阶到艺术创造层面:在编制史诗、悲剧、喜剧、音乐的过程中,艺术家均可以自由地摹仿“行动中的人”。[11]38行动由身体承担,故而这种模仿不是对身外之物漫无边际的再现,而是对具身性活动及相应世界体系的演绎。身外之物的摹本即使单独出现,也要被还原到具身性的活动体系中,否则,其意义便无从谈起。譬如,原型的可怕之处源于它对具身性体系的威胁和侵扰,而摹本则丧失了这种实在功能,因此,人可以在观看它们时获得审美快感。毫无疑问,相关的实在体系依然存在,却又暂时处于退隐状态。于是,人似乎可以放心地流连于纯粹的审美情境,面对艺术作品中的形象。这种超越性中蕴含着“遗忘的诗学”:似乎我们不是具身性存在,灵魂可以独自静观摹本。为了阻止遗忘的发生,亚里士多德强调了摹本和原型的关系:“倘若观赏者从未见过作品的原型,他就不会从座位摹仿品的形象中获得快感——在此种情况下,能够引发快感的便是作品的艺术处理、色彩或诸如此类的原因。”[11]38见过原型意味着曾经建立过实在的感觉—被感觉关系。后者同样是具身性活动:具身性主体摄入外物的映像,建构出对应的心理印象。当人面对艺术品时,心理印象和原型的关系即使未被意识到,也仍然在起作用。此刻,“所凭的似乎是灵魂内在的影像或思想”,“实际上却是视觉在线所察见的”。[6]158离开了感觉提供的映像,人就不能学习和思想,当然也谈不上欣赏和创作艺术品了。故而,“在组织情节并将它付诸言词时,诗人应尽可能地把要描写的情景想成就在眼前,犹如身临其境,极其清晰地‘看到’要描绘的现象……”[11]125只有通过恰当的编制,作品才能刺激受众的想象力和情感,使后者体验到审美愉悦。
从身体主体性理念出发,亚里士多德建构出了一种重视感性的研究范式。它涉及实践、日常生活、艺术鉴赏和创作,成形为相对完整的具身性美学(Embodied aesthetics)体系。在他这里,古希腊身体美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
三、亚里士多德身体主体性理论的含混品格及其影响的二重性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亚里士多德虽然承认身体的主体性,但他并未将身体当作独立的主体,更没有确认“感性学”对身体的完全归属关系。相反,在他眼中,灵魂才是第一主体,其地位远远高于身体。相对于灵魂,身体不过是辅佐者和配角。
写作《灵魂论》时,亚里士多德曾说:“灵魂是有生命物体之因与原(第一原理)。‘因’与‘原’居于多种命意。而灵魂就通有一切生物诸原因中的三因:灵魂为生物动变所由缘起(动因),又为其动变所趋向的终端(目的),又为一切生物的‘本体’。”[6]95换言之,生物之灵魂具有营养、欲望、感觉、思想、运动的机能。[6]95可是,如果灵魂是感觉的主体,那么,下面的问题就会显现出来:其一,“寓于内”的灵魂如何感觉外物?其二,怎样估价身体在感觉中的作用?对此,他并未给出明确答案。事实上,他对身体的定位不无矛盾之处:既强调身体具有感觉能力,又把感觉定义为灵魂的机能。于是,潜在的悖论被忽略了。至少在感性认识层面,亚里士多德未能建构出自洽的理论体系,其身体话语具有无法遮掩的暧昧品格。当后者成为可兹利用的遗产时,这种暧昧品格也延续下去:既承认身体的主体性,又把主要的功能分配给灵魂。对于继承者来说,如何分配主体性就变成一个面对的问题。于是,身心之争在所难免,美学必须向重构者开放。意味深长的是,后世的大多数美学家都沿袭了亚里士多德的二元论体系。这等于说,他们也继承了亚里士多德身体思想的张力,同样会被卷入身心之争中。
以托马斯·阿奎那(Saint Thomas Aquina)为例,这点清晰可见。身为经院哲学家,他自觉地以亚里士多德为师,试图将基督教教义与古希腊神学结合起来。[17]在《神学大全》一书中,他将人定义为肉身和精神的联合体:“下面,让我们思考肉身性生物(corporeal creatures)和精神性生物(spiritual creatures)之别:首先,在《圣经》中,纯粹的精神性生物叫做天使;其次,完全肉身性的生物;第三,肉身和精神性的组合物,这就是人。”[18]480在组合中,身体依旧承担外部感觉:“以这种方式,灵魂与身体联合着,因为他不完善,在理智实体所在的种种仅仅是可能的存在,并不在本性中就拥有完善的知识,而要通过身体感觉才从可感物那里获得之,此乃我们以后将要详加阐释的观点。”[18]492没有身体,就没有感觉,便无法参与审美活动,因此,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联合中的一方,它又不可能是纯粹的被动者:“身体由潜能和行为所构成,故而它同时是主动的和被动的。”[18]1058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可以与灵魂相提并论:灵魂乃“此间所有生命的第一原理”,给“事物以生气”;相比之下,肉身“虽然同是生命的一个原理”(如“心脏是动物生命的一个原理”),但却注定只能占据次要的位置。[18]683如果说灵魂是形式,那么,身体就是质料。在与身体结合之后,灵魂既是推动者,又是目的。它具备身体所不具备的“灵性智识能力”:“理解不可能是身体的行动,也不是任何肉体性力量,因为身体总是被局限于此时此刻。”[18]481于是,亚里士多德式的难题又显现无遗:倘若认识被归结为灵魂的功能,如何估价身体在感觉过程中的作用?它仅仅是个通道或接收器吗?如果是,又有什么理由谈论它的主动性?面对这些挑战性的问题,托马斯·阿奎那试图建立一个调和性的体系,但上述难题并未被消解,相反,内蕴于亚里士多德身体话语中的悖论被延续下来。
与托马斯·阿奎那相比,笛卡尔(Rene Descartes)无疑是另一个关键人物。对于后来者来说,他的《第一哲学沉思录》可谓深邃的现代性宣言。在这本巨著中,这位大哲试图严格区分身心,以便彻底克服上述悖谬,但却再次提出了相互矛盾的命题:其一,“人的肉体就其有别于其他物体这一点而言,它不过是由一些肢体和一些偶性组成的;而人的灵魂就不是这样,它是一种单纯的实体,绝不是由什么偶性组合起来”;其二,“人的灵魂实在有别于肉体,然而又和肉体紧密结合得就像一个东西似的。”[19]11-13如果身体与灵魂完全有别,二者又如何能够联结?吊诡的是,他随后又强调:“自然也用病、饿、渴等感觉告诉我,我不仅住在我的肉体里,就像一个舵手住在他的船上一样,而且除此之外,我和它非常紧密地连结在一起,融合、掺混得像一个整体一样地同它结合在一起。”[19]85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明显的矛盾?事实上,笛卡尔也面临典型的亚里士多德困境:倘若灵魂住在肉体中,它又焉能抵达外界?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不得不再次肯定身体的作用,断言它与灵魂拥有“共同感官”,宣称它的感受会转化为灵魂的感受。[19]90-91于是,身体的不可或缺性再次顽强地展示出来:它至少具有感受能力。如此说话的笛卡尔又回到了亚里士多德。当他论述感觉时,我们似乎听到了《灵魂论》的回响:“当我觉得脚上疼的时候,物理学告诉我,这个感觉是通过分布在脚上的神经传来的,这些神经就像绳子一样从脚上一直通到大脑里,当他们在脚上被抻动的时候,同时也抻动了大脑里面这些神经的起点和终点这些地方,并且在那里刺激起来为了使精神感觉疼而制定的某一种运动,就好像疼是在脚上似的。”[19]91神经体系承担着相应的感觉功能,拥有它的身体并非纯然被动的存在。相反,它可以如自动机般运作:“如果我把身体看作由骨骼、神经、筋肉、血气、血液和皮肤组成的一架机器”,那么,“即使里面没有精神,也并不妨碍它跟现在完全一样的方式来运作”。[19]88-89在他看来,身体是神造的机器,结构“安排得十分巧妙”,“做出的动作十分惊人”,可以按照其内在结构来演绎动作。[20]在使用身体机器这个意象时,笛卡尔已经部分地承认身体的主体性。遗憾的是,他依旧断定“我们不能说精神是身体的一种样式(a mode of body)”,仍然维系着亚里士多德流传下来的二元论理路。[21]通过笛卡尔的选择,我们可以再次领受到亚里士多德影响的双重性:其一,在感觉层面承认身体的主体性;其二,假定存在高于身体的主体并因此将身体置于次要的层级。
最终,这种二重性深刻地影响了美学的体系性建构。1750年,当鲍姆嘉腾正式提出美学(Aesthetica)概念时,“身体学”和“心灵学”之间的冲突再次凸显出来:一方面,他提出“美学作为艺术的理论、低级认识论、美的思维的艺术和与理性思维类似的艺术是感性认识的科学”[2]13;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心灵是这个过程的主宰者。[2]25按照前一个线索,身体必然凸显出来:没有身体,哪有“感官的感受”,又谈何感性(aesthetic)和感性学(Aesthetics)?同时,后一种说法又使“身体学”为“心灵学”所压抑:如果心灵是审美的主体,那么,身体至多只能是辅佐者。显然,这类矛盾牵连出亚里士多德式的二元论框架,再次涉及历史悠久的身心之争。从鲍姆嘉腾曾多次提到亚里士多德来看,他显然受到了后者的影响。到了他这里,亚里士多德思想的二重性直接转化为美学体系的内在张力。
事实上,现代西方美学至今仍未超越二元论的研究图式。以倡导身体美学的舒斯特曼为例,这个事实依然清晰可见:恰如亚里士多德,他重视“活生生的、敏锐的、动态的、具有感知能力的身体”,强调其所扮演的“主体角色”。[22]同时,他又不反对“有关心—身(mind-body)关系的心理学与本体论理论”。[1]266-277如果设定了心身二元关系,那么,身体就不可能是整全的主体。从他所给出的身体美学定义中,我们不难发现定位的模糊性:“对一个人的身体——作为感觉—审美场所和创造性的自我塑形——经验和作用的批判性和改善性的研究。”[1]267在这句话中,有关身体主体性的言说又牵连出对它的客体定位:能进行“创造性的自我塑形”,显然说明身体可以扮演主体性角色;可是,“作为感觉—审美场所”,它似乎又被更高的主体所征用和掌控。那么,这个更高的主体是谁?只能是他此前所说的“心”(mind)。它栖居于身体之中,却又代表人的“自我”:“一个统一的自我,不是同一的自我;但是,也不能是栖息在同一个肉体机器中的不可比较的‘准自我’的混杂集合。”[23]330相对于它,“活生生的、敏锐的、动态的、具有感知能力的身体”不过是执行者:“由于行为只有通过身体来实行,我们的意志力量——像我们想要去行动那样去行动的能力——依赖于身体的功效。”[23]356显然,如此说话的他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了亚里士多德的相关论述,又复活了一种古老的研究范式。恰如他所不断引用的亚里士多德,舒斯特曼同样试图在二元论的框架内彰显身体的意义。这使得他的身体美学也具有挥之不去的暧昧品格。
从托马斯·阿奎那到舒斯特曼,一个二元论的美学研究范式延续至今。从谱系学的角度看,它的主导逻辑源自亚里士多德。由于这种传承关系,亚里士多德身体主体性思想的双面性形成了贯穿性的影响。随着西方身体美学的东渐,这个传统也开始内化到汉语文化中。正因为如此,对它的重构和反思也与汉语美学的发展息息相关。
四、结语
亚里士多德既创立了身体主体性理念,又未走出二元论的疆域。从根本上说,身体主体性理念与二元论并不相容:其一,如果身体是生活实践的主体,那么,灵魂或心就是个无用的假设;其二,假设存在灵魂或心,必然会将思想等“高级”机能与身体割裂开来,因而无法建构统一的身体主体论。事实上,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思想与大脑乃至整个身体的关系日趋明朗,超越二元论的机缘已经成熟。沿着这条线索前进,我们就可以推动美学研究走上回家的路:既继承亚里士多德的身体主体性思想,又克服其暧昧品格,彻底敞开感性学对身体—主体的归属关系。对于汉语美学的建构者来说,这或许意味着超越后殖民语境的机缘。
参考文献:
[1]Richard Shusterman. Pragmatist Aesthetics: living Beauty,Rethinking Art[M].New York & London: Ro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0.
[2]〔德〕鲍姆嘉腾.美学[M].简明,王晓旭,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
[3]Dorothea Frede,Burkhard Reis edited.Body and Soul in Ancient Philosophy[M].Berlin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2009:1.
[4]Jonathan Barnes. Early Greek Philosophy[M]. London: Penguin Books,2001.
[5]〔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二卷[M]. 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80-81.
[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灵魂论及其他[M]. 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7]Aristotle. De Anima[M].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1986.
[8]〔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物理学[M]. 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9]Aristotle.The Metaphysics[M].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1998.
[10]〔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动物四篇[M]. 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1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M]. 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1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 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3]〔德]康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8.
[14]Aristotle.Politics[M]. New York: Barnes & Noble Classics,2005:178.
[15]〔法〕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90.
[16]Terry Eagleton. After Theory[M]. London: Penguin Books,2003:156.
[17]Berys Gaut,Dominic Lope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Aesthetics[M].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0:26-33.
[18]Thomas Aquinas.Basic Writings of Saint Thomas Aquinas(Volume One-Ⅱ)[M].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1997.
[19]〔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录[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20]〔法〕笛卡尔.谈谈方法[M]. 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44.
[21]Descartes. Key Philosophical Writings[M]. Hertfordshire: 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1997:339.
[22]〔美〕理查德·舒斯特曼.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M]. 程相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
[23]〔美〕理查德·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M]. 彭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责任编辑钟昭会)
中图分类号:B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6)01-0001-08
作者简介:王晓华(1962—),男,辽宁黑山人,教授。研究方向:美学、文艺学、文化理论。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西方美学中的主体观和身体意象”(12FZW052)。
收稿日期:2015-12-09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shb.2016.0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