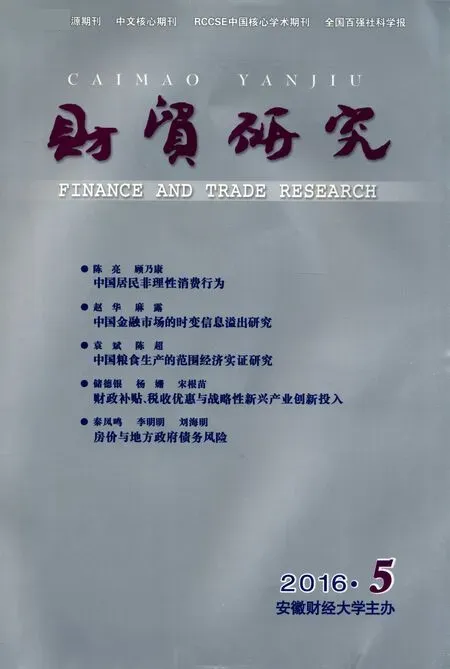中国省级消费风险分担:测度、影响因素与福利效应
洪 勇
(九江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西 九江 332005)
中国省级消费风险分担:测度、影响因素与福利效应
洪勇
(九江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西 九江 332005)
基于1978—201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消费增长与产出增长关系视角出发,测度中国省级消费风险分担水平,并进一步研究其影响因素和福利效应。结果显示:虽然中国省级消费风险分担水平相对偏低,但在研究的样本期内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资本市场整合、信贷市场发展、人均受教育水平、财政转移支付对消费风险分担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其中,资本市场整合的作用力度最大;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增长、服务业发展则会阻碍消费风险的分担。1978—2013年间,中国已实现的福利收益呈逐年上升之势,而潜在的福利收益则呈下降趋势。
消费风险分担;资本市场整合;福利收益
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的快速增长,人均GDP从1978年的381元上升到2013年的41908元,30多年增长了近110倍,这是人类历史上主要经济体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高速增长。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得居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居民的消费增长却严重滞后于经济增长,消费的缓慢增长阻碍了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偏低、增长缓慢已引起政策制定者和学者的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也较为丰硕,但现有文献却忽略了风险因素对消费的重要作用。现实中,在面临产出或收入冲击所造成的不确定性时,居民通常会降低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加以应对,同时,产出或收入的波动如果传导至消费,也会减少居民从消费中所获得的福利。为了规避或降低消费风险,提高消费的福利水平,消费者通常会进行消费风险的分担。消费风险分担是指消费者在面临特定风险时(通常是指外生的产出或收入冲击),通过各种渠道(主要是资本市场和信贷市场)规避或化解该风险,降低消费的波动程度,提高消费的平滑性,从而提升消费的福利水平。鉴于消费风险分担的重要作用,相关研究正逐渐兴起,通过文献梳理和归纳,我们发现,已有研究主要围绕风险分担的水平、影响因素及其福利收益三个方面展开。
学者通常用消费与产出或收入的关系来衡量消费风险分担水平。Asdrubali et al.(1996)研究了美国1963—1990年间的风险分担水平,结果发现,美国的收入冲击有75%得到平滑,其中资本市场贡献了39%,借贷市场贡献了23%,财政体系贡献了13%。Sorensen et al.(1998)发现,不管是欧盟国家还是OECD国家,国家间的消费风险分担水平并不高,这与Crucini(1999)的研究结论保持一致,后者认为一国内部的风险分担水平比国家间要高。Kim et al. (2003)的研究发现,东亚国家的消费风险分担和消费平滑水平均低于欧盟国家和OECD国家。郑海青(2008)、俞颖(2011)对东亚国家间消费风险分担的研究结果也表明,东亚地区的消费风险分担水平还很低,并且没有表现出随时间不断增强的趋势。Kose et al.(2009)对不同国家群体的研究结果显示,发达国家之间的风险分担水平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
现有对消费风险分担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金融市场一体化。Sorensen et al. (2007)对OECD国家的研究表明,国际金融一体化能有效促进风险分担水平的提高;Prasad et al. (2009)也发现,金融一体化对消费风险分担具有促进作用。二是信贷市场。Asdrubali et al. (1996)认为,借助信贷市场这一渠道,消费者可以显著提高风险分担水平;俞颖(2011)、何青等(2014)的研究也表明,信贷市场发展能促进消费风险的分担。三是交易成本。Obstfeld et al. (2001)发现,较高的国际商品和资产交易成本会弱化市场主体进行跨国消费风险分担的动机;Fitzgerald(2012)认为,地区间的市场摩擦和壁垒会增加产出和收入跨地区分配交换的成本,进而削弱风险分担机制的作用,降低风险分担水平。四是不可贸易品。Ho et al. (2015)发现,不可贸易品的存在阻碍了贸易的发展,从而抑制了产出和收入在地区间的分配交换,这会导致风险分担水平的下降。
消费风险分担能在消费水平不变的条件下提升消费者的福利,因而引起了学者的关注。Lucas(1987,2003)认为,美国从消费风险分担中所能获得的潜在福利并不高,这可能与美国现有较高的风险分担水平有关(由于潜在福利水平是指从现有风险分担水平提升至完全风险分担水平时所能获得的福利收益,故现有风险分担水平越高,提升至完全风险分担水平所能获得的潜在福利就越少);Cole et al.(1991)基于产出不确定性的一般均衡模型,从理论上探讨了国际消费风险分担收益,认为即使实现了消费风险的完全分担,从中获得的收益也很小;Mendoza(1995)、Tesar et al.(1995)的研究发现,消费风险分担的收益较小,其大小与Cole et al.(1991)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Rangvid et al.(2014)基于16个国家1875—2012年的研究结果也显示,从消费风险分担获得的潜在福利并不大;Wincoop(1994,1999)则发现,一些OECD国家从消费风险分担中所获得的福利较多,远高于Cole et al.(1991)所认为的水平;郑海青(2008)基于东亚13个经济体的研究结果也表明,东亚各经济体风险分担的福利收益是比较高的。
相比于研究国际消费风险分担的大量文献,探讨中国国内消费风险分担的文献较少,笔者只发现Tochkov(2007)、Xu(2008)、Du et al.(2010,2011)、何青等(2014)曾研究过中国消费风险分担问题,但这几篇文献只涉及消费风险分担的测度和影响因素分析,并没有对福利效应展开研究。基于此,本文不仅要测度中国消费风险分担水平,分析其影响因素,还要探究其福利效应;同时,前述研究福利效应的文献仅分析了潜在的福利,并没有探讨已实现的福利,而这正是本文贡献之所在*潜在的福利是指风险分担由目前水平提升至完全风险分担水平时,将来能够实现的福利收益;已现实的福利是指在现有风险分担水平下已经实现了的福利收益。。
二、中国省级消费风险分担测度
(一)测度方法
如果存在消费风险分担机制,意味着消费者在面临特定的产出或收入冲击时,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规避该风险,降低消费的波动程度,提高消费的平滑性。完全消费风险分担是指一个地区的消费增长与该地区的产出或收入增长完全无关,也就是说,即使存在特定的产出或收入冲击,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加以化解,使其无法传导至消费。当完全不存在消费风险分担时,特定的外生冲击会完全传导至消费,一个地区的消费增长与该地区的产出或收入增长就会密切相关。由此可知,消费风险分担水平可以用消费增长与产出或收入增长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来衡量。实践中通常有两种方法测度风险分担水平:一是相关性分析,即计算消费增长与产出或收入增长之间的相关系数;二是回归分析,即以消费增长为因变量,以产出或收入增长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用得到的估计系数来衡量风险分担水平。本文将采用回归分析来度量中国省级消费风险分担水平,具体地,使用如下回归方程进行估计:
dcit=α+βdyit+εit
(1)
其中:dcit为省区i在t年的人均消费增长,即dcit=cit-ci,t-1,cit表示省区i在t年的人均最终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两部分);dyit为省区i在t年的人均产出增长,即dyit=yit-yi,t-1,yit表示省区i在t年的人均GDP;εit为随机干扰项。式(1)中的β能反映出消费风险分担水平的高低,其取值在0~1之间,越接近于1,表明消费增长与产出增长之间关系越密切,风险分担水平越低;反之,越接近于0,表明风险分担水平越高。本文用1-β来衡量消费风险分担水平,其值越大,表明消费风险分担水平越高;反之则越低。人均最终消费和人均GDP数据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折算为按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实际变量,最终消费和GDP数据均来源于相应年份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区的统计年鉴。此外,在估计前,本文预先对变量进行对数处理,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异方差和偏态性问题(Wooldridge,2003)。
(二)测度结果及分析
基于式(1),本文使用中国29个省区1978—2013年的相关数据*本文研究样本包括除港澳台、西藏和重庆以外的29个省区。西藏由于数据缺失,没有包含在研究样本中;重庆是1997年才设立的直辖市,1996年以前的数据无法得到,故将1997年以后的数据合并到四川省。,以1991、2001年为时间节点分别对全时段和三个子时段中国省级消费风险分担水平进行测度,此外,将29个省区划分为东、中、西部三大地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黑龙江、吉林、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进行风险分担情况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1978—2013年中国省级消费风险分担情况
注:括号里的数值表示估计的标准差;***、**、*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下同。
从全国情况看:1978—2013年的消费风险分担水平为0.4546,而美国各州在1963—1990年间平均的消费风险分担水平在0.6~0.7之间(Asdrubali et al. ,1996),可见,中国的风险分担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有明显差距;从时间趋势上看,全国的风险分担水平上升趋势明显,从1978—1991年的0.4131上升到1992—2001年的0.5901,再提高到2002—2013年的0.6501。从三大地区情况看:1978—2013年东部地区风险分担水平最高(0.5218)、中部次之(0.4655)、西部最低(0.3752);与全国情况相似,三大地区的风险分担水平也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进一步观察风险分担的时间趋势可以发现,全国和三大地区在1992—2001年间的上升趋势最明显。本文认为,这与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确立了市场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使得分担消费风险的渠道所受的束缚逐渐减少,从而有效提高了风险分担水平。
三、消费风险分担影响因素分析
(一)模型、变量与数据
消费风险分担主要是通过资本市场和信贷市场两条渠道发挥作用,资本市场和信贷市场可以将不同地区的产出以资本性的方式进行分配交换,使某地区特定的产出冲击不至于完全传导至消费,因而能平滑该地区消费,降低该地区消费与产出的相关程度。例如,大的自然灾害(地震、台风等)会对当地经济造成巨大破坏,形成特定的产出冲击,如果当地居民通过资本市场和信贷市场持有非灾害地区的资产,就可以通过资产收益,或者出售所持有的资产来对冲收入的下降以保持消费的平稳。本文除重点关注资本市场和信贷市场这两个核心变量外,还加入了一些对消费风险分担有重要影响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包括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水平、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受教育水平、财政转移支付。在实证分析消费风险分担的影响因素时,本文借鉴Kose et al.(2009)的如下方法,即在式(1)的基础上,引入上述影响因素与人均产出增长(dyit)的交叉项。
(2)
其中:dcit、dyit的含义与式(1)相同。CIit表示省区i在t年的资本市场发展水平,用资本市场整合水平表示,其数据使用F-H模型估计得到,即通过投资-储蓄关系来刻画资本市场整合水平,具体方法参见徐冬林等(2009)、王维国等(2014),在此不赘述。Creditit表示省区i在t年的信贷市场发展水平,用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表示。Financeit表示省区i在t年的财政支出水平,用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表示。Serviceit表示省区i在t年的服务业发展水平,用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表示。Eduit表示省区i在t年的人均受教育水平,用人均受教育年限表示,其计算借鉴陈钊等(2004)的方法,即将每一种受教育水平折算成一定的受教育年限,然后将其与该受教育水平的人数相乘,加总后再除以相应的总人口,就可以得到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数据,由于1986年以前各省受教育水平的人口结构数据无法获取,故只能得到该变量1987—2013年的数据。Transferit表示省区i在t年的财政转移支付水平,用各省中央补助收入与上解中央支出之和占GDP的比重表示,1989年以前各省中央补助收入与上解中央支出的数据无法获取,故只能得到该变量1990—2013年的数据。
对于面板数据而言,通常应考虑无法直接观测的且会对因变量造成影响的个体效应和时期效应,否则会导致有偏和非一致估计,但就式(2)而言,只要考虑时期效应(αt)而不需考虑个体效应,其原因在于,dcit、dyit为表示人均消费增长和产出增长的一阶差分项,非时变的个体效应会因一阶差分的存在而被消除,故不需考虑个体效应。时期效应可分为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如果αt与解释变量相关,就应采用固定效应(FE,Fixed Effects)模型进行估计;反之,则应采用随机效应(RE,Random Effects)模型进行估计。实践中,通常用Hausman检验来对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进行取舍。此外,式(1)中,笔者用1-β来衡量消费风险分担水平,故在式(2)引入交叉项后,可用下式表示风险分担水平:
1-β0-β1CIit-β2Creditit-β3Financeit-β4Serviceit-β5Eduit-β6Transferit
由上式可知:如果式(2)中交叉项的估计系数为负,则表明该因素对风险分担水平具有促进作用;反之,则表明该因素会阻碍风险分担水平的提高。
(二)估计结果及分析
表2报告了中国省级消费风险分担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结果,其中,第(1)列给出了只含有核心变量资本市场和信贷市场而不含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其他各列在此基础上依次加入控制变量进行估计。
由表2第(1)列的估计结果可知,人均产出增长与资本市场整合(CIit)交叉项、与信贷市场(Creditit)交叉项的系数均为负,且都是高度显著的,表明资本市场整合程度提高、信贷市场发展都能有效促进消费风险的分担。此外,资本市场交叉项的系数绝对值远大于信贷市场,这表明资本市场整合对消费风险分担的作用更大。第(2)—(5)列分别加入了财政支出水平(Financeit)、服务业发展水平(Serviceit)、人均受教育水平(Eduit)、财政转移支付水平(Transferit)与人均产出增长的交叉项,从各列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到,加入各控制变量后,资本市场、信贷市场交叉项的系数依然高度显著为负,说明资本市场、信贷市场确实是促进消费风险分担的重要渠道。此外,在所有能促进消费风险分担的因素中,资本市场整合交叉项的系数绝对值最大,表明其对消费风险分担的促进作用最大。第(2)列中财政支出水平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财政支出水平的提高会降低风险分担水平,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对本地经济的干预程度越深,越有可能阻碍风险分担水平的提高,其原因可能是,微观主体与宏观主体的目标函数存在差异,居民的经济行为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原则,而地方政府通常则是以促进本地经济增长和就业为目标,与地方政府相比,居民更注重通过消费风险的分担来提高个人福利,因此地方政府对本地经济干预越多,越有可能降低风险分担水平。第(3)列中服务业发展水平交叉项的系数为正,且高度显著,表明服务业中大量存在的非贸易品会对消费风险分担产生阻碍作用,这与Ho et al.(2015)的研究结论一致。第(4)列中人均受教育水平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提高风险分担水平,这可能是因为个人素质随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后,主观上更能深刻认识到消费风险分担有利于提高个人福利,因而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分担消费风险。第(5)列中财政转移支付水平交叉项的系数为负,且高度显著,表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转移支付能提高风险分担水平,这是因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地区特定的产出冲击,故而有助于提高风险分担水平。第(6)列将所有控制变量都引入模型,结果发现,核心变量和各控制变量系数的符号都保持不变,但各变量的显著性有所下降,特别是财政支出水平交叉项和财政转移支付水平交叉项系数变得不再显著,这很可能与解释变量间存在的多重共线性有关。

表2 中国消费风险分担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注: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的确定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得出,下同;第(4)列中人均受教育水平变量只有1987—2013年的数据,故其观测次数为783,第(5)、(6)列中财政转移支付水平变量只有1990—2013年的数据,故其观测次数为696,下同。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提高研究结果可靠性,本文对风险分担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进行以下稳健性检验:
首先,由于人均消费增长(dcit)和人均产出增长(dyit)存在着双向影响关系,即在产出影响消费的同时,消费也对产出有影响,因此,在用式(2)进行估计时,必须要考虑这种双向影响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内生性问题会造成模型的估计偏误,为此,就需要为人均产出增长寻找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选择合适的工具变量通常比较困难,但在面板数据条件下却存在很好的选择,即用该变量的滞后项来作为工具变量。人均产出增长的滞后项通常与当期的人均产出增长高度相关,但当期的人均消费增长却无法对前期的人均产出增长产生影响,从而很适合作为工具变量。具体地,本文采用滞后1期的人均产出增长作为工具变量。结果如表3第(1)和第(2)列所示。在只含有核心解释变量资本市场和信贷市场的第(1)列中,这两个变量交叉项的系数依然高度显著为负;第(2)列引入全部控制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和各控制变量交叉项系数的符号与表2第(6)列保持一致,且各变量交叉项系数的显著性也无明显变化,引入工具变量后,模型的稳健性良好。
其次,在分析消费风险分担影响因素的类似文献中,部分使用人均居民消费增长作为因变量(何青 等,2014;赵国庆 等, 2010),而不是人均最终消费增长,故本文也尝试用人均居民消费增长作为因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3的第(3)和第(4)列所示。可以看到,不管是只含有核心解释变量的交叉项,还是包含核心解释变量和全部控制变量的交叉项,各变量系数的符号都没有发生改变,其显著性也只有少许变化,表明模型并没有因为因变量的改变而发生太大变化,模型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表3 中国消费风险分担影响因素稳健性分析
最后,对于核心解释变量信贷市场发展水平而言,本文之前用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表示,但信贷市场中不仅有贷款,也有存款,有文献用金融机构年末存款余额占GDP的比重来反映信贷市场发展水平(何青 等, 2014),因此,本文也用存款占比替代贷款占比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引入模型中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3的第(5)和第(6)列所示。对于只含有核心解释变量的第(5)列而言,资本市场和信贷市场的交叉项系数依然为负,且高度显著;引入全部控制变量后,第(6)列中各变量系数的符号依然不变,除人均受教育水平交叉项的估计系数变得不显著外,其他变量的显著性水平都变化不大。因此,更换信贷市场发展水平这一核心解释变量后,模型依然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从风险分担影响因素及其稳健性分析结果来看:资本市场整合、信贷市场发展、人均受教育水平、财政转移支付对消费风险分担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其中,资本市场整合的作用力度最大;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增长、服务业发展则会阻碍消费风险的分担。
四、消费风险分担福利效应分析
消费风险分担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规避特定的产出冲击风险,降低消费的波动性,使消费变得更加平滑,因而能提高消费者的效用,增进其福利。本部分拟分析中国省级消费风险分担的福利效应,具体探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在目前的风险分担水平下,已实现的福利收益;二是如果风险分担由目前的水平提升至完全风险分担水平时,能够实现的福利收益,即潜在的福利收益。
(一)福利收益分析方法
在计算消费风险分担福利收益时,现有文献通常使用如下的常数相对风险厌恶(CRRA)效应函数:
(3)
其中:Ut为t年从消费中所获得的效用;Ct为t年的消费;θ为相对风险厌恶系数,其值通常取为3(Wincoop,1999)。潜在的福利收益等于完全风险分担条件下福利水平与现有风险分担条件下福利水平之差。完全风险分担条件下与现有风险分担条件下福利水平的计算可借鉴Rangvid et al.(2014) 的思想,他们是在计算16个国家消费风险分担福利收益时提出该思想的,本文对其进行简单修正,以适应一国内部不同地区的情形。该思想可以简述为:如果实现了完全风险分担,则意味着省区特定的产出冲击风险会被完全消除,但完全风险分担也无法消除系统性的产出冲击风险,各省区依然存在的系统性风险使得各省区的消费波动与全国的消费波动完全一致,因此,完全风险分担条件下的福利水平应该是将全国的消费水平带入式(3)计算得到的福利水平,具体地,以各省区GDP为权数,先计算全国加权平均的消费水平,然后带入式(3)计算福利水平。现有风险分担条件下的福利水平则是先利用式(3)计算各省区在现有消费水平下的福利水平,然后以GDP为权数,计算各省区福利水平的加权平均数得到。
对于已实现的福利收益,现有文献很少涉及,原因在于已实现的福利收益是用现有风险分担条件下的福利水平减去完全无风险分担条件下的福利水平,由于完全无风险分担条件下的消费水平无法获得,故难以计算已实现的福利水平。在此,本文将采用一个简单而巧妙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完全无风险分担表明任何特定的产出冲击都完全无法消除,这意味着产出的波动会完全传导至消费,再假定消费者会将当期收入全部用于当期消费,当期储蓄为零,因此,可以用产出水平来代替完全无风险分担条件下的消费水平,将其带入式(3)计算完全无风险分担条件下的福利水平,然后以GDP为权数,计算各省区福利水平的加权平均数,此加权平均数即为完全无风险分担条件下的福利水平。
(二)福利收益计算及分析
根据前述方法,笔者对中国1978—2013年已实现的福利收益和潜在的福利收益进行逐年计算,结果如图1所示。从中可见,已实现的福利收益呈逐年上升之势(2003年略有下降),从1978年的0.50%提高到2013年的1.02%,由于已实现的福利收益随着消费风险分担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因此,这与表1所表现出的消费风险分担水平的上升趋势是相符的。与已实现的福利收益呈上升趋势相反,潜在的福利收益则呈下降趋势(1989年稍有提高),从1978年的1.19%下降到2013年的0.58%,这也不难理解,随着消费风险分担水平的提高,其与完全消费风险分担水平的差距会缩小,故从已有消费风险分担水平提升至完全消费风险分担水平所能获得的潜在福利收益就缩小。1978—2013年间,平均的潜在福利收益为0.86%,这表明如果实现了完全的消费风险分担,在消费水平不变的条件下,通过完全的消费平滑,消费者的福利会增加0.86%;反过来也可以说,消费者愿意在现有消费水平上减少0.86%的消费,以实现完全的消费风险分担,此时,其福利水平依然保持不变。

图1 消费风险分担的福利效应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中国29个省区1978—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从消费增长与收入增长关系的视角出发,测度了中国省级消费风险分担水平,并进一步探讨其影响因素和福利效应。研究结论如下:(1)虽然中国省级消费风险分担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明显偏低,但在研究的样本期内其上升趋势明显;分地区看,东部地区的风险分担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2)资本市场整合、信贷市场发展、人均受教育水平、财政转移支付对消费风险分担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其中,资本市场整合的作用力度最大;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增长、服务业发展则会阻碍消费风险的分担。(3)1978—2013年期间,已实现的福利收益呈逐年上升之势,而将现有消费风险分担水平提升至完全消费风险分担水平的潜在福利收益则呈现出下降趋势。
在消费水平不变的条件下,随着消费风险分担水平的提高,消费者的福利也会相应增加。为了增加中国居民的消费福利,应尽快提高相对较低的消费风险分担水平。基于本文研究结论,笔者认为应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由于资本市场整合水平的提高对消费风险分担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需要加快推进资本市场整合进程。为此,各级地方政府应该高瞻远瞩,摒弃“本地思维”,逐渐减少直至最终废除已实施的各项地方保护主义政策和措施,消除人为造成的市场分割,逐步提高资本市场整合水平。第二,金融监管部门应该从促进信贷市场发展的角度出发,赋予金融市场主体更大权力以提高其创新活力,并制定相应制度,保护和鼓励金融创新行为,从而进一步丰富金融市场的投融资渠道和方式,促进信贷市场的繁荣与发展。第三,各级政府在加大教育投入的同时,还应鼓励和动员社会力量投身到教育事业中来,以此提高国民素质,增强国民分担消费风险的主观能动性,进而提高消费风险分担水平。第四,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充分发挥财政转移支付的“收入减震器”功能,从而提高消费风险分担水平,平滑消费。第五,各级地方政府应尽量缩减不必要的地方财政支出,只要是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地方政府就不要加以干预,并且要尽可能按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来安排财政资金支出。
陈钊,陆铭,金煜. 2004. 中国人力资本和教育发展的区域差异:对于面板数据的估算[J]. 世界经济(12):25-31.
何青,杜巨澜,薛畅. 2014. 中国消费风险分担偏低之谜[J]. 经济研究(S1):4-17.
王维国,薛景. 2014. Feldstein-Horioka之谜在中国省际间的再检验:截面相关下的变结构面板协整分析[J]. 上海经济研究(3):59-66.
徐冬林,陈永伟. 2009. 区域资本流动:基于投资与储蓄关系的检验[J]. 中国工业经济(3):40-48.
俞颖. 2011. 东亚金融一体化与消费风险分担的实证研究[J]. 亚太经济(1):47-51.
赵国庆,张中元. 2010. 金融发展与中国跨省消费风险分担[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2):19-26.
郑海青. 2008. 东亚消费风险分担的度量及潜在福利分析[J]. 财经研究(9):91-100.
ASDRUBALI P, SORENSEN B E, YASHA O. 1996. Channels of interstate risk sharing: United States 1963-1990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1(4):1081-1110.
COLE H L, OBSTFELD M. 1991. Commodity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risk sharing: How much do financial markets matter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8(1):3-24.
CRUCINI M. 1999. On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dimensions of risk sharing [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1(1):73-84.
DU J L, HE Q, RUI O M. 2010. Does financial deepening promote risk sharing in China [J]. Journal of the Asian Pacific Economy, 15(4):369-387.
DU J L, HE Q, RUI O M. 2011. Channels of interprovincial risk sharing in China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9(3):383-405.
FITZGERALD D. 2012. Trade costs, asset market frictions, and risk sharing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2(6):2700-2733.
HO C Y, HO W Y A, LI D. 2015. Intranational risk sharing and its determinant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51(3):89-113.
KIM S, KIM S H, WANG Y. 2003. Financial integration and consumption risk sharing in East Asia [R]. KIEP Working Paper 03-13.
KOSE M A, PRASAD E S, TERROES M E. 2009. Does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promote risk sharing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9(2):258-270.
LUCAS R E. 1987. Models of business cycles [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UCAS R E. 2003. Macroeconomic prioritie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3(1):1-14.
MENDOZA E G. 1995. The terms of trade, the real exchange rate and economic fluctuations [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36(1):101-137.
OBSTFELD M, ROGOFF K. 2001. Global implications of self-Orientated national monetary rules [R]. CEPR Discussion Paper,No.2856.
PRASAD E S, ROGOFF K, WEI S J, et al. 2009. Effects of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R]. IMF Occasional Paper 220,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RANGVID J, SANTA-CLARA P, SCHMELING M. 2014. Capital market integration and consumption risk sharing over the long run [R]. CEPR Working Paper.
SORENSEN B E, YASHA O. 1998. International risk sharing and european monetary unification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45(2):211-238.
SORENSEN B E, YASHA O, WU Y T, et al. 2007. Home bias and international risk sharing: Twin puzzles separated at birth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6(4):587-605.
TESAR L L, WERNER I M .1995. Home bias and high turnover [J]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14(4):467-492.
TOCHKOV K. 2007. Interregional transfer and the smoothing of provincial expenditure in China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18(1):54-65.
WINCOOP E V. 1994. Welfare gains from international risk sharing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34(2):175-200.
WINCOOP E V. 1999. How big are potential welfare gains from international risk sharing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47(1):109-135.
WOOLDRIDGE J M. 2003. Introductory econometrics: A modern approach [M]. South-Western:Thomson Learning.
XU X P. 2008. Consumption risk-sharing in China [J]. Economica, 75(298):326-341.
(责任编辑彭江)
Provincial Consumption Risk Sharing in China:Measurement, Influence Factors and Welfare Effect
HONG Yong
(School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 Jiujiang University, Jiujiang 332005)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1978 to 2013, this paper measures provincial consumption risk sharing in China and studies its influence factors and welfare effect from the view of relationships of consumption growth and output growth. The results show that although the level of consumption risk sharing is low, it shows a clear upward trend in the sample period. Capital market integration, credit market development, per capita level of education and financial transfer payment can promote the sharing level of consumption risk, among these factors, capital market integr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However, loc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and service industry development will impede the sharing level of consumption risk. The realized welfare is on a upward trend, but the potential welfare shows a downward trend from 1978 to 2013.
consumption risk sharing; capital market integration; welfare benefits
2015-11-24
洪勇(1975--),男,湖北武汉人,经济学博士,九江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企业规模分布视域下的中部地区城市规模分布与产业圈层耦合机制研究”(13BJY04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中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的代价测度:生态效率的视角”(15YJC790042)。
F063.2
A
1001-6260(2016)05-00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