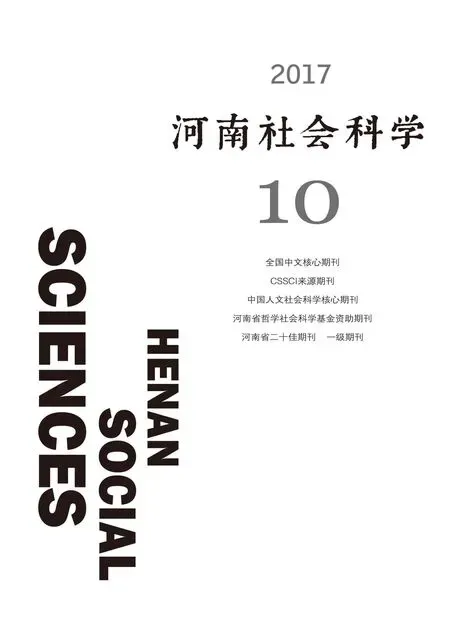当代艺术应在审美批判中寻求构建途径与社会责任
赫 云,李倍雷
(东南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当代艺术应在审美批判中寻求构建途径与社会责任
赫 云1,李倍雷2
(东南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当代艺术”作为当下艺术的一种形态,理所当然地进入我们当下的文化和社会现实中,触及我们的生活层面。当我们的现实社会和生活被当代艺术家以“当代艺术”的形态呈示在我们面前时,又让我们始料不及,似乎远离了我们的社会与生活。特别是有一些混同于“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表现形态的当代艺术作品,超越了我们对社会道德与生活的常态理解,甚至碰触着社会道德的极限;“当代艺术”中还有一些以“非艺术”的形式挑战了艺术自身的界限,超过了我们视觉的、生理的与精神的承载极限,致使艺术自身也遭遇到解构的危机。这种艺术现象必然引起我们思考。或许当代艺术自我建构的文化基础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油画家杨飞云说:“国外的现当代艺术有些陷入无路可走的境地,比较盲目,但更重要的是缺少真情实感,而且拒绝或者说忽视与人群的交流,大多在自说自话地、在挖空心思地花样翻新,但花样有些类似泡沫,完了就完了,留不下什么东西。中国有一批人在跟着国外潮流走。国外有了一种行为,中国跟着也模仿一个,意思不是特别大。”①这是作为一个坚持架上绘画的艺术家的担忧。因而,我们认为当代艺术不是西方现代艺术与后现代艺术路径上的艺术形态,中国当代艺术必须以本土文化为基础并本质地区别于西方现代与后现代艺术,使我国当代艺术的主题在当代语境下的批判中寻求建构的途径与凸显其社会功能的价值和意义。
一、对“前当代”艺术的形态与观念层面的反思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基本上把西方的现代艺术与后现代艺术上演了一遍。许多理论家认为“85’美术新潮”在挪用和模仿的文化层面的确有点像一场“艺术运动”。艺术批评家殷双喜认为:“85时期只是一种狂热,缺少扎实的艺术语言,只给人留下了运动,没有给人留下作品。我们今天提起85’只是感觉一种宏观的气势,所出现的优秀的艺术家及作品却很少。”②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艺术好的作品的确不多,当然也有个别的“现代艺术”出现有那么一点“现代”的气息,比如浙江美术学院的“85新空间”展览的张培力的手套《X?》系列、耿建翌《第二状态》等作品,徐冰、谷文达等的作品也不凡不俗,企图在传统的文化结构符号中寻找到现代性的意义和价值。表层看有一定的现代艺术的语言也触及了一些现代文化的现象。王广义的“政治波普”艺术系列,显然是对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1928—1987)的波普语言的挪用与移植,艺术语言上没有独立性,仅仅换了母题,主题的表达依然属于移植。模仿、挪用与移植的确是“85’美术新潮”现代艺术的一个普遍的问题,在艺术语言和艺术形式上几乎没有多大的贡献,可以说“85’美术新潮”企图表达中国特殊语境中的文化现代性并不成功。“85’美术新潮”这种貌似具有精英式的对文化捍卫的艺术姿态,本质上是对西方现代艺术的模仿与初级学习,当时艺术理论界习惯称之为“现代艺术”。实际上事隔三十多年的今天,当我们回溯时,发现它的内质是希望通过一种“精英”的方式或激进的文化态度来接纳西方的现代艺术,而它的表现语言是想通过内部改造来寻求一种被认为新的形式,但是这种新的形式却并不具备真正的创新意义,模仿、挪用与移植的方式决定了“85”时期的“现代艺术”母题与主题无法创新。正是这个原因,当今的许多批评家仍然认为“85’美术新潮”在艺术的创新方面和艺术主题方面没有多少建树。也因此,我们认同“85’美术新潮”只是一场艺术运动。这场运动是没有统一风格的,表现的也是一次乌托邦式的现代艺术的运动,不具备现代性的文化意义。毕竟8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85’美术新潮”的“现代艺术”缺乏现代大工业机器生产和物质基础以及缺少现代文化基础的支撑。如果说“星星美展”的反思性是主调,那么“85’美术新潮”就希望是精英式的姿态。因为“85’美术新潮”与当时整个中国精英文化运动确有点呼应关系;如果说“85’美术新潮”有成功的话——就“运动”广度而言,是因为它切合了当时中国的现代思想解放运动的精英文化内在的需要。但也正是因为现代思想解放运动,当时的艺术界误把“85’美术新潮”当作了“现代”艺术。我们都记得20世纪80年代,劳申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1925—2008)来中国表现他的拼贴、波普和行为的艺术方式,实际上他的作品几乎属于后现代艺术的方式,但当时我们都误读为现代艺术。这个误读上的认知混淆了“现代”与“后现代”的观念。因此,我们认为把“85’美术新潮”当作“现代艺术”是认知上的错位。这种错位直接影响到我们正确判断当代艺术与本土语境的内在需求,从而影响到我们对“当代艺术”在我国的出现与发展的认识。
事实上错位的认识还是延续下来了,把“错位的认知”演绎成为“认知的错位”。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1989年2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89’现代艺术大展”在观念上的确可以看作是“现代性”的,但在方式上与呈现的作品却是“后现代”的。这种现象还不同于西方20世纪60—70年代的混杂时期的艺术形态。西方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之间是现代主义开始转向后现代艺术的时期,因而我们说这个时期是“混杂时期”,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形态也是现代艺术与后现代艺术混杂的形态。“89’现代艺术大展”的艺术家们的认知的错位是把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所有艺术形态都当作“现代艺术”,这就是说把很多属于后现代艺术的形态与观念看成现代艺术的形态与观念。对“认识的错位”这个现象,尽管如今的艺术理论家多数已经有了共识,但在20世纪80年代对于同年代的现代艺术现象没有做出应有的及时的正确反思,导致我们很长时间还在炒西方后现代艺术的“剩饭”。20世纪80年代末的现代艺术家在意识上仍然是要创造一个“精英”式的神话,并用西方的现代性来矫正和判断自己的认识和坐标。同时把“星星美展”单纯的批判意识转换为艺术的、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批判意识,这种观念和意识的延伸到“85’美术新潮”的现代性,却使用了后现代的形式去表达,到“89’现代艺术大展”用了后现代的“反艺术”的形式。这与当时中国努力构建一个新的艺术文化时代的内在要求十分矛盾。所以,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艺术在今天看来不太成功。西方的现代性是建立在颠覆19世纪以前的西方传统艺术与文化基础上的,而中国的现代性“颠覆”的对象是模糊的,当然也不是建立在颠覆西方传统的基础上的。如果与西方现代主义的颠覆对象相一致,那只能是西方的现代性翻版,不符合中国的现代性的要求。如果说被颠覆的对象是模糊性的或不确定的,那么中国艺术的“现代性”就有乌托邦的色彩。反映在“89’现代艺术大展”中的很多作品的确有乌托邦的幻想,因为它们没有“颠覆”的体系或谱系的对象。简单地说,颠覆的对象不明确,仅仅是假设了一个颠覆的对象。即虚设了一个类似西方19世纪前的传统文化,模仿、挪用和移植西方的“现代艺术”形式。同时,“89’现代艺术”几乎也没有留下什么经典的艺术作品。即或是“枪击电话亭”也只是作为一个新闻事件的发生,或者就是给人留下了肤浅的模仿印象。
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现代艺术而言,当意识到“现代性”出现了错位的时候,中国当代艺术家们为了纠正这种“认识的错位”,开始大量使用“前卫艺术”或“先锋艺术”这样的词语。习惯上使用“前卫”的多一些。“前卫”概念最早由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1909—1994)提出,他在1939年发表的题为《前卫与庸俗》的论文中说:“正是在绝对的探索中,前卫艺术才发展为‘抽象’或‘非具象’艺术——艺术亦然。前卫诗人或艺术家努力尝试模仿上帝,以创造某种完全自足的东西,就像自然本身就是自足的,就像一片风景——而不是一幅风景画——在美学上是完全自足的一样。”③格林伯格所“发现”的“平面”与“抽象”这两个关键词,是他找到“现代艺术”理论的根本性出路的概念词语。毫无疑问,格林伯格的现代艺术理论建立在“平面”和“抽象”概念上,为西方第一幅现代主义作品《亚威农少女》(毕加索,1907年)以及后来的现代艺术提供了理论支撑。中国使用“前卫”艺术及其概念已发生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这时的“前卫”是与“装置艺术”“观念艺术”“行为艺术”“媒体综合艺术”等相对称的。但是在文化体系和哲学层面的判断上和艺术表现形式的形态上多数是“后现代”的。这一点对中国的当代艺术家来说,是一个没有克服的认知上的错位。认为“后现代”在“现代”之后,就比“现代”先进,理所当然就是比现代艺术要“前卫”。基于这种“社会进化论”认识,观念上和艺术上的失效是必然的。而且,“前卫”的方式越玩越邪乎,“离奇”“怪异”无创新性倒也罢了,消解艺术和文化也可以“理解”,毕竟西方艺术家早就“示范”过了,但对于挑战中国的社会道德底线的“行为艺术”,显然有点过了头,也不是本土的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的内在需求。“后现代”是一个在传统中寻求语言和任意挪用各种风格的碎片化、拼贴化、无逻辑性的艺术形态,也企图在消解二元对立和精英文化中消解艺术本身。后现代艺术挑战传统艺术及其观念,对宏大叙事进行消解,它“关心”政治但又不想“干预”意识形态;在消费市场里,把“我消费故我在”作为后期资本主义市场的运营模式用来控制艺术市场,把艺术视为商品作为资本的一部分来控制非西方国家艺术。这是后现代的一个基本立场。
上述认知方面错位的结果是,在模仿、移植和挪用西方现代与后现代艺术的方式中,不是以批评和反思的姿态来建构中国的当代艺术与文化形态,把“破而不立”乔装成为“不破不立”的姿态。这使得曾经热心鼓励中国当代艺术的理论家感到非常为难,也感到难堪。这一点与在海外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和参加国际性的双年展的中国当代艺术家相比,国内的一些挑战艺术与道德的现代艺术家,无论在文化战略上还是在艺术形态上,以及对本土传统艺术文化的认同方面都远远不及。“但不容中国艺术界和有志之士忽略的是,这些海外中国新艺术活动大多数是由西方策划人在西方艺术机构的支持下按照西方人的眼光做给西方人看的。”④也因此,为了共同推进中国当代艺术的正常发展,活跃在85时期以来的理论家,诸如栗宪庭、高名潞、刘淳、段炼等都在为中国当代艺术寻找前景而深刻地反思,重新梳理和判断现代艺术与后当代艺术观念与意识,在梳理和判断中寻找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中国当代艺术,而不是用西方的现代艺术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当代艺术。提出了从中国出发的理念,如“中国牌”“中国春卷”等概念,建立中国自己的当代艺术。因此,我们认为,现代性必须转变为本土语境内在需要的当代性,才是中国“现代”艺术的出路。
二、当代艺术应当转变为社会内在的需要
1989年以后知识精英社会意识逐渐被商品化的社会意识所取代,这一事实不可否认地也说明了中国的当代艺术与商业结合。当今走红的当代艺术家被国外的商业集团包装之后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这是西方策划人的策略,不断地“俘虏”中国一些当代艺术家的智慧。使“中国现代艺术已经自觉和不自觉地掉入了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语境中,同时失去了对自身历史文脉和当下的特殊的关注热情”⑤。王岳川从当今在国外走红的当代艺术现象中分析了它的另一种身份意识。他说:“现代性的悖论出现了——从真诚地反对现代性丑恶到假笑式的自我欺瞒。这样的‘集体假笑’造成的人的精神灾害波及了被媒体炒红的艺术家。如方力钧最初出现时,画了一些政治高压下的痴呆的大光头,百无聊赖地打着哈欠挤眉弄眼地嘻笑,表情怪异地傻瞪着前方。这种情绪表达对上世纪90年代中国状况有某种程度的挑战或回应。然而,其后傻样‘光头泼皮’在美术国际化中被西方话语操纵者所独赏——咧嘴傻笑者的内心世界表征为一张东方集体愚昧的证书,成为中国现代艺术政治策略的标志性形式,被中外不断误读和想象的玩世现实的绘画中理解为‘中国人形象’,并在近20年类型化绘画中成功地转变为西方辨认中国的意识形态符码。”⑥王岳川指出的这种现象基本是可信的,也是深刻的。我们的当代艺术家的确是在用我们过去的某些伤痛在迎合西方人的意识形态,并非完全是为了满足西方人的猎奇心态。因为,在西方的话语权中“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才被认为是前卫的艺术,对中国现代艺术家所做的装置艺术、行为艺术、波普艺术并不看好也不认为是前卫艺术。西方人的话语总是把中国的现代艺术纳入他们的政治话语中或是意识形态中作为“艺术”的选择标准,然而这种西方意识形态话语并没有引起我们的艺术理论家重视或者说警觉,仅仅从艺术本体审视或审美的视角来回应西方的话语,如高名潞所说:“我们需要找到另一种解读中国艺术的现代性和前卫性的叙事模式和修辞方式。而这种新的方式本身就已经包含了某种不同于西方的新的美学经验、新的艺术创作方法论和艺术阐释方法论。只有通过建树这样一种新的话语标准,非西方的前卫和现代才能宣称它的平等存在价值。”⑦仅仅是这样表层的理论意识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当代艺术需要在中国在当代文化发展过程中,应该找准中国当下社会、文化的内在需求和目标,应该在提升国际文化形象和国家形象方面努力建设中国当代艺术,以我们自身的本土语境为视角、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脉在比较当代世界文化与艺术的变量中,寻求当代艺术的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探索、试验和建设中国的当代艺术。“‘从中国出发’的标题暗示了艺术家应立足于中国现实的土壤来记录今日中国的巨大变迁和结构转型;从自身的文化根性出发来演绎当代中国的故事,从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出发来思考当代国际文化的交流、竞争、互渗和互融,以期传达年轻的中国艺术家在世纪之交对中国与世界的认识。”⑧中国的艺术当代性,不必按照西方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框架或范式来架构,也没有必要。西方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中有一个最大的失缺就是彻底破坏性地颠覆传统和把二元对立绝对化,把构建或创新建立在破坏性的颠覆和二元对立绝对化的基础上。我们要建立一个完整的中国本土化的当代艺术创新模式和当代艺术理论话语体系,让“传统”与“当下”相遇,让“当下”与“传统”相遇,使中国的当代艺术家把中国传统艺术和文化的资源转化在当下的艺术创作中,将中国人文精神作当代阐释,即当代艺术与传统文化相遇,让传统艺术与文化具有当代价值与意义,进而转向社会内在需求的艺术形态,使中国的当代艺术关注中国自己的文化、社会与意识,关注当下人们的生存环境。尽管审美不是当代艺术的全部内容,但当代艺术依然要承担社会与民众的审美需要的责任,满足当下人们和社会对当代文化的精神诉求,满足人们和社会对中国当代艺术形式创新的心理需求。
三、当代艺术的审美批判精神与责任
中国当代艺术之所以能够体现文化现象、经验、精神和情感的当代性,主要在于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艺术创造活动和当代艺术形成的精神文化、审美情感具有“当代意识”。这些当代意识是依据世界语境中的当代社会提供的文化现象和后物质消费现象而生发的,并显示出对后文化境遇的审美批判精神。这种审美批判精神,使中国当代艺术具有“批判的形式”。
中国当代艺术的审美批评精神,是从审美文化领域的视角,以一个更高层的文化姿态对当代社会提供的文化现象、文化经验、当代精神和当代情感,发掘与阐释当代艺术的审美性。中国当代艺术的审美批评精神,以探讨当代艺术与当下人们在后消费时代的精神活动与主体创造活动之间必然关联为逻辑起点,力图获得在世界文化境遇中对产生于不同艺术形态的文化区域间的相互沟通、相互阐释和对话的机遇,进而蕴聚中国当代艺术的深刻内质和文化意蕴、批判精神和审美文化体系于一体的独立担当,并参与到世界艺术文化语境中去构建本土的艺术文化使其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当代艺术的审美批判精神,在世界语境中阐释当代人类共同的审美文化与精神意蕴,使中国当代艺术真正成为世界语境中不同形态文化区域的、人类共同享有的文化资源。征用中国特有的文化符号,表达本土文化蕴含的艺术形态,使中国当代艺术在建构当代中国的人文精神与艺术品位的基础上,强调中国当代艺术的审美文化的开放效应和突出中国当代艺术对回归到文化批判的高度和层面中发生重要的意义,而不是个人隐私的宣泄。中国当代艺术的审美批判精神,是使中国当代艺术占据世界重要地位的根本基础和保证。如果中国当代艺术缺少这种批判精神,将失去上述的全部话语和任务,也将失去全部的生命与活力。
中国当代艺术的审美批判精神具有中国传统的“士志于道”的文脉精神,是精英文化的批判精神和审美文化态度,与西方后现代语境下的“媚俗”“平面”“粗鄙”“轻浮”“调侃”“嬉戏”相区别。我们看到成熟的中国当代艺术都是极其严肃地提出中国自己的文化问题和社会问题,或者是对社会文化的历史回应。因此,中国当代艺术无论是批判还是阐释,都体现了自己的文化品位和审美文化态度。中国当代艺术的审美批评精神、重新建构中国的审美文化与艺术品位,逐步遏制了西方后现代消解深度和历史大叙述后所引发的“媚俗”“粗鄙”“调侃”“嬉戏”“平面”等方式在艺术与审美文化中的滥延,也使当代艺术的审美批判精神成为当代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关注当代人类共同的生存境况和向世界文化的多向度的审美文化结构方面发展。中国当代艺术所显现的审美批判精神,站在了关注人类自身的文化高度,思考人与社会、自我与他者、人与自然之间的互为关系与共同命运,这些特征都显示中国当代艺术在当今社会功能的价值与意义。
中国当代艺术的社会功能的实现,任重而道远。中国当代艺术在世界文化语境中,以审美批判的姿态参与世界话语系统的对话机制。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当代艺术成为与世界文化精神和人类心灵的一种对话方式、交流方式和沟通方式。中国当代艺术的审美批判精神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灵魂,也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出发点,从而构成了中国当代艺术迈向更高境界的一步。因此,中国当代艺术以审美批判精神确立自己的面貌,参与世界艺术文化的建构,并以开放的姿态体悟和感受世界文化,把审美批判精神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基本模式,使之真正成为人类精神和世界文化结构中的一个重要范式。当然,中国当代艺术要想完成这些任务,还有很多困难和问题需要认真对待和解决。譬如,如何将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置入当代世界语境中重新阐释,使其在当代文化语境中具有再生成当代文化资源的可能,并使其具有文化意识的当代性;在艺术形态中,如何将表达语言图式的能指结构进行新的整合,使其具有国际性的语言图式的通约性,或者使其本身成为国际性的语言图式,参与到世界文化语境中去,真正把带有效仿他者性质的语言范式内化成自己的表达图式,最终践行中国当代艺术的社会功能。这都是中国当代艺术所面临的而且应该解决的问题。
四、结语
中国当代艺术亟待解决的是建立自己的艺术话语现代系统,立足点只能是自己的传统文化根脉,其他的文化无法取代也不可能取代自己的文化系统。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提出“传统与当代相遇”“当代与传统相遇”的主张。其重要意义在于我们强调的是将传统置于当代语境中寻求价值与意义,显示传统在当代的“语境身份”。这一身份也昭示了传统的当代意义与价值。“传统与当代相遇”“当代与传统相遇”就是有序化地相互穿越,要摆脱把传统作为自缚的窠臼就要不拘泥于传统的形式层面,要穿越在传统文化精神中,超越其表层形式的元素,使传统文化精神与当代文化语境相遇,显示当代艺术的文化责任。所以,中国当代艺术要咬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中国的社会现状、政治、经济体制等实际上都是国际大舞台的一部分,在当代文化演变与发展的进程中,中国当代艺术在传承自己的传统文化中需要具有当代性。也就是说,中国当代艺术要使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在当下具有当代的价值与意义,这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任务。同时,中国当代艺术的社会功能就是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关系。所以,中国当代艺术要提出具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符合文化发展逻辑的人文精神与人文关怀的文化问题,关注人类与社会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社会责任。
注释:
①殷双喜:《画坛偶像》,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页。
②刘淳:《中国前卫艺术》,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01页。
③[美]格林伯格:《前卫与庸俗》,沈语冰编著:《经典文献导读书系·美术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1页。
④⑧张朝阳:《当叛逆沦为时尚》,湖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98、200页。
⑤⑦高名潞:《另类方法另类现代》,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版,第28、29页。
⑥王岳川:《当代艺术炒作的后殖民话语》(上),《美术报》2007年5月18日。
编辑 王秀芳
Research on the Realistic Func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The former proposes that new poetry is a modern art that uses modern Chinese and modern poetry to express modern emotions and modern life,which,In the 20th century,was a special style that promoted the proces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In the 21th century,it is supposed to contribute greatly to the realization of Chinese dream.The practical functions and practicability of new poetry should be given great importance.Its educational function should be considered major and its therapeutic function important.Poetry writing is both“personal writing”and“social writing”.There is both a sense of life and a sense of mission.It is concerned about both survival of the citize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The spiritual reconstruction of today’s new poetry is exactly to build such a modern spirit.The function of today’s new poetry is to highlight these functions.The latter proposes that the situation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is quite complicated.Instead of being the western modern and postmodern art form,it is an art form based o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The“contemporary nature”of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determines its social function and responsibility.It is supposed to endow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art with modern value and meaning.It represents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among people,nature and society.Therefore,it is supposed to raise questions with its own values according to humanistic spirit and concern.It is the current responsibility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to focus on human and society.Although one paper focuses on“literature”and the other on“art”,both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immediacy”,“ Chineseness”and“tradition”.This is the best strategy for realizing the realistic func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the Func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Chinese Dream;Cross-boundary Discussion;Realistic Function;Immediacy;Chineseness
2017-07-03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重点课题“中国传统艺术母题与主题学体系研究”(16AA00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242017S10037)阶段性成果
1.赫云,女,艺术学博士,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艺术学理论研究;2.李倍雷,男,艺术学博士,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艺术理论系主任,博士生导师,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合作导师,主要从事艺术学理论研究与油画创作。
——评《全球视野下的当代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