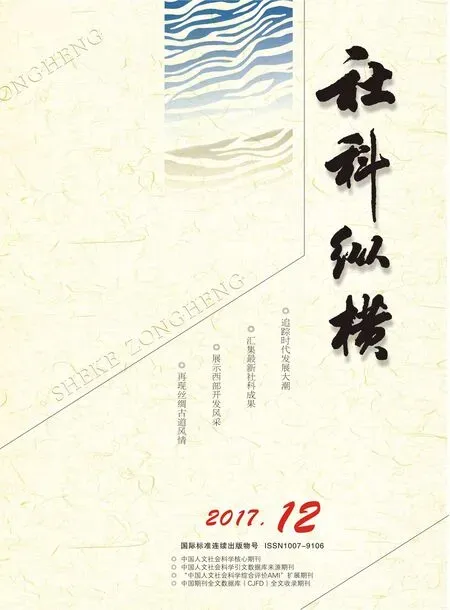论加缪的文化身份与伦理选择
陈 娟 陈丽娟
(1.大连外国语大学 辽宁 大连 116044;2.南京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92)
·文学与语言学·
论加缪的文化身份与伦理选择
陈 娟1,2陈丽娟1
(1.大连外国语大学 辽宁 大连 116044;2.南京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92)
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并存斗争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加缪文化身份的多重性和复杂性。多元混杂的文化身份不仅使加缪文字书写中呈现出一种“殖民情结”,而且在面对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问题时,文化身份的复杂性让加缪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迫使他不得不做出艰难的伦理选择。谴责一切暴力行为是作家伦理选择的出发点。从文学创作到“介入活动”,加缪都在向世人传达一种真挚而朴素的人道主义。
加缪 文化身份 “殖民情结” 伦理选择
一、引言
作为法国文学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尔贝·加缪(1913-1960)凭借其文学创作、哲学思想和“介入活动”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20世纪50年代,加缪开始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迄今为止,国内学术界从作家作品译介、哲学思想解读、文学作品分析、戏剧作品上演等方面对加缪及其作品进行了多角度、不同层次的研究,批评视角和研究方法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但是,对加缪文化身份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有些学者受到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他们借鉴萨义德在《文学与帝国主义书》中对加缪的论述[1](P240-264)认为加缪的作品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也有学者认为加缪的书写是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批判。这种看似矛盾的研究成果从侧面反映出加缪文化身份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文化身份对加缪的文学创作和“介入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有关此问题的研究一直没有受到学术界足够的重视。本文将以文化身份为出发点,揭示这种特殊的文化身份对加缪文学创作和伦理选择的影响。
二、永远的“流放者”
加缪生来就不具备纯粹的身份归属:1913年出生于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父亲是法国移民的后代,母亲则是西班牙裔。终其一生,加缪都在“法兰西”和“阿尔及利亚”之间徘徊和选择。“身份不是由血统来决定的,而是社会和文化共同作用的产物……文化身份的形成和认同在很大程度上被具体的历史进程,特定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语境所制约。”[2](P27-28)加缪所处的正是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同时存在并斗争的社会,一方面法国推行种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试图“同化”阿拉伯人,维持其在阿尔及利亚的军事统治;另一方面,殖民地人民日益觉醒,开始奋起反抗,为自己的尊严和独立而战。宏观的历史背景让加缪的文化身份呈现出多重、复杂的特点。
生在阿尔及利亚,长在阿尔及利亚的加缪视其为故乡,把她当成自己的祖国:“关于阿尔及利亚,……至少我可以说她是我真正的祖国,在世界的任何地方,我都会以朋友的身份认出阿尔及利亚的儿子、我的兄弟。是的,在阿尔及利亚城市中,我钟爱的一切与住在那里的人密不可分。”[3](P596)这里提到的“阿尔及利亚的儿子”和“兄弟”不是指别人,指的是在阿尔及利亚定居的欧洲移民。加缪的祖辈就是最初来到北非的法国移民。但是,在阿尔及利亚,欧洲移民始终都处于流放者的位置。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欧洲移民实际上是从欧洲流放到阿尔及利亚的拓荒者,他们离开了自己原来的家园,在阿尔及利亚也只有短短一百多年的历史,他们是这片土地的外来户,没有任何根基。“正如所有出生于此的男人们,一个又一个地出生在没有根基、没有信仰中试图学会生活。”[4](P563)欧洲移民是从19世纪30年代才进入阿尔及利亚的。在他们到来之前,阿拉伯土著早已扎根此处。加缪穷其一生所追寻的,就是欧洲移民在阿尔及利亚的根,证实欧洲移民在阿尔及利亚的合理合法居住权,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其次,从空间上看,阿尔及利亚和法国地处两个大洲,中间隔着一个地中海,气候完全不同,严酷的沙漠、炙热的阳光、强劲的海风这些都是移民们需要去接受和适应的,而这些也是加缪作品中最重要的素材。最后,欧洲移民和阿拉伯人在教育上也有着不同待遇。移民的后代从小在学校里接受的是法兰西文化,学的是法语。他们根本就不懂当地的语言,也不了解当地的文化。即使加缪再热爱阿尔及利亚,也改变不了他“流放者”的身份,他不可能被称为 “阿尔及利亚人”,总会在前面加一个定语:“法国籍阿尔及利亚人”。
在学校里,课本上的“法兰西”正是加缪需要铭记效忠的祖国,但是显而易见,这个“祖国”在“别处”,如此遥远、如此模糊。由于不断在报纸上发表反殖民文章,加缪受到了当时殖民当局的压迫,不得不离开阿尔及利亚前往法国。等他到了法国以后,真正接触和了解自己的祖国时,也没有找到“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感觉,相反,对他来说,真正的“流放”生活开始了。他曾写信给一个朋友:“在阿尔及尔以外的地方我完全无法生活,完全不能。……在别的地方我永远会有流放的感觉。”[5](P57)来到巴黎以后,他写下这样一段话:“在这阴暗的房间里,在一个顷刻间变得陌生的城市的喧嚣声中突然醒来,这意味着什么?一切都与己无关,没有亲人,没有地方可以愈合这个伤口。我在这里做什么?……我不是这里的人,也不是别处的。”[6](P61-62)
这种既不属于这里(阿尔及利亚)也不属于那里(法国)的感觉,才是加缪最真实的感受。“流放作家”才是他真正的文化身份。这种“无根”的状态成为加缪文学创作的动力和源泉。他试图从写作中去寻找归属感和生命的意义。
三、书写中的“殖民情结”
虽然加缪出生贫寒,是白人阶级中的下层人民,但他还是属于殖民阶层,他的文字中也流露出一种“殖民情结”。加缪的“殖民情结”首先表现在作品的素材上。加缪大部分小说的故事背景都是阿尔及利亚,散文《反与正》、《夏天集》、《婚礼集》中更是充满了对这种地中海生活方式热情洋溢的赞颂。在他的第一部散文集《反与正》(1937)再版序言中,加缪写道:“每个艺术家都在心灵深处保留着一种独一无二的源泉,在有生之年滋养着他的言行。当这源泉干涸的时候,作品也就萎缩,甚至破绽百出。……就我来说,我知道自己创作的源泉就在《反与正》之中,在我久久居留过的贫困和光明的天地里。”[7](P4)这里的“贫困和光明的天地”指的就是阿尔及利亚,那里的阳光、大海和母亲就是他文学创的灵感来源与永恒主题。从文字中,可以读出加缪对阿尔及利亚的依恋和热爱之情。正是出于这种真挚的情感,他不愿意失去承认法国移民合法身份的阿尔及利亚。
“殖民情结”的第二个表现是对“他者”的建构。“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每一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8](P426)加缪作品中的“他者”就是阿拉伯人。美国文学批评家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以《局外人》和《鼠疫》等为例,指出了加缪小说中“阿拉伯人”无名无姓、无身份的现象,并评论道:“加缪的长短篇小说非常精确地提炼了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的传统、习语和话语战略。……它们代表了法国殖民主义作品。”[1](P262)的确,加缪小说中阿拉伯人形象是模糊的,基本上他们“既不说话,又无表情”[4](P356)。这种“失语”现象被很多学者解读为话语权利的丧失。甚至有阿尔及利亚作家据此将加缪和种族主义联系起来。[9](P893-906)小说中阿拉伯人这个“他者”的形象是加缪小说中的客观存在,但是不能因此就简单地将加缪划入“殖民主义”作家的行列。在阿尔及利亚欧洲移民眼中,阿拉伯人就是“他者”。在建构“他者”的同时,欧洲移民试图建立和确立自己的身份。加缪小说中阿拉伯人没有身份、没有话语权利也可以解读为当时阿拉伯人生存现状的真实反映。加缪只是用一种冷静、客观的笔触在讲述一个个虚构的故事。在《局外人》中,加缪借主人公默尔索之口,描述了欧洲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巨大差异:“因为铁栏杆之间隔着一大段距离,探监者与囚徒都不得不提高嗓音对话。”[4](P43)所以白人都是站着互相高声说话,而“大部分阿拉伯囚徒与他们的家人,都面对面地蹲着。这些人都不大叫大嚷。”[4](P43)两种阶层,两种行为方式,两种语言,泾渭分明,跃然纸上,这是对当时殖民社会的一种无情地揭露,而不应该将这种书写解读为种族主义。
加缪作品中“殖民情结”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对法国殖民统治现状的主题考察。生活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加缪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看到了帝国主义存在的危机。他曾经作为记者,旗帜鲜明地揭露殖民主义的罪恶。1939年3月到6月期间,他深入卡利比亚山区进行采访,以《苦难的卡利比》为题在《阿尔及尔共和报》发表了11篇系列报道,揭露了当地居民的困苦生活和殖民当局的虚伪政策。他在文章中强调,如果要真正实行民族同化、让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都成为法国人的话,首先就不应该将他们与法国人区分对待。加缪亲眼见证了阿尔及利亚土著人民的困苦生活,也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消除这种不平等,他为阿尔及利亚土著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仗义执言、争取平等权利和利益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对如何解决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困境,如何帮助他们脱离苦难,加缪还是寄希望于殖民政府能有所改变,“但愿一项明智而民主的政策的执行能够减少一些这种苦难。”[10](P323)在加缪看来,“从来就不存在阿尔及利亚民族。犹太人、土耳其人、希腊人、意大利人、柏柏尔人都有同样的权利要求领导这个虚拟的民族。现在,阿拉伯人自己并不能代表整个阿尔及利亚。……严格意义上来说,阿尔及利亚的法兰西人也是本地土著。”[3](P388-389)加缪否认了“阿尔及利亚民族”的存在,不承认八百万阿拉伯居民对阿尔及利亚的绝对主权,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因为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虽然实现了阿拉伯人的意愿,但却给阿籍法国人从他们那个天然的祖国给驱赶出去。……如果这一类型的阿尔及利亚果真组成,并且反对或疏远法兰西的话,无论是出于自发的力量,还是纯出于自卫的力量,还是两种力量都不是,那对我都是一个巨大的不幸”[10](P292)。站在加缪的立场,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战争对他和他的家人来说不啻于噩梦和灾难。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之父斯图亚特·霍尔说过,“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藏身于许多其他的、更加肤浅或人为地强加的‘自我’之中,共享一种历史和祖先的人们也共享这种‘自我’。”[11](P200)对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来说,这种“自我”只能在阿尔及利亚找到,一旦阿尔及利亚独立,阿籍法国人被驱逐出阿尔及利亚,他们无疑就丧失了这种“自我”,丧失了身份。
加缪“法籍阿尔及利亚人”的身份以及当时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并存的社会历史背景导致其书写中呈现出这种“殖民情结”。但是,不能以此为根据定义他是一个殖民作家或是一个反殖民作家。他坚决反对殖民主义对人的压迫,同时也反对在阿尔及利亚彻底抹掉殖民主义的痕迹,建议成立一个“同法国联系起来”的阿尔及利亚。
四、艰难的伦理选择
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战争爆发后,多重复杂的文化身份给加缪带来的冲突和矛盾激化到了顶点。“在文化碰撞的过程中,权力常发挥作用,其中一个文化有着更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基础时尤其如此。无论侵略、殖民还是其他派生的交往形式,只要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存在着冲突和不对称,文化身份的问题就会出现。身份要成为问题,需要有个动荡和危机时期,既有的方式受到威胁。……正如科伯纳·麦尔塞所说,‘只有面临危机,身份才成为问题。那时一向认为固定不变、连贯稳定的东西被怀疑和不确定的经历取代’。”[12](P194)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就是这里所说的危机。
阿拉伯人和欧洲殖民者之间的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进一步恶化。二战结束后,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者发动起义,争取阿尔及利亚的永久独立。虽然法国殖民政府用武力镇压了民族运动,阿尔及利亚暂时恢复了表面上的平静,但是仇恨的种子已然埋下。法国国内的新闻媒体并没有给这一件事件应有的关注,而作为战后法国新闻喉舌的《战斗报》的主编,加缪当时先后发表了六篇文章来报道阿尔及利亚的危机。“流放状态”给加缪提供了切身观察了解两种文化的机会,他清楚地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战争和解放已经激起了阿拉伯人民的政治期望,他们希望有自己的宪法和议会,获得政治上的独立。加缪正确地预见了帝国主义的式微。他强烈地谴责暴力伤害无辜平民的行为。但他还是希望法国能继续拥有对阿尔及利亚的统治权,他呼吁法国能实践共和主义的承诺,给阿尔及利亚人民真正的公民权益,他依然天真地相信一个完全民主平等的法属阿尔及利亚是有可能实现的。
1954年,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正式开始,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矛盾已经不可能缓和。加缪此时仍然选择发表文章呼吁双方立即停战、和平协商。1956年他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前往阿尔及尔发表演讲,呼吁休战:“在这片土地上,聚居着一百万法兰西人,……还有数百万穆斯林……;还有许多宗教团体,……所有这些人都应该共同生活在一起,生活在这个各条大路和各种民族的交汇处,这是历史的安排。”[10](P366)他希望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和阿拉伯人能够求同存异,享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共同生活。但是没有任何效果。他在《快报》上发表了最后一篇谈论阿尔及利亚问题的社论,其中提出建立“一种类似瑞士联邦那样可以使各个民族共同生活的联合体制”[10](P381),但是很显然,他低估了阶级矛盾激化的程度与阿拉伯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决心,而且,这种“联邦制”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在各团体之间自然资源分配极其不均的阿尔及利亚根本无法实行[13](P209)。这篇文章没有引起任何共鸣,阿尔及利亚的局势日趋紧张。此后,加缪对阿尔及利亚解放战争缄口不谈,保持公开沉默。他的沉默使他成为世人攻讦的对象,阿拉伯人对他怀着沉重的敌意,认为他是“叛徒”。左翼指责他无视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右翼攻击他作为一个“法国人”却在捍卫法国利益方面毫无作为。正如他所说:“我同阿尔及利亚有着源远流长的联系,而且毫无疑问,这种联系还将永远继续下去,这种联系使我完全无法对它有一个客观的认识。”[10](P249)
“伦理两难由两个道德命题构成,如果选择者各自对它们做出道德判断,每一个选择都是正确的,并且每一种选择都符合普遍道德原则。但是,一旦选择者在二者之间做出一项选择,就会导致另一项违背伦理。”[14](P262)加缪就陷入了这样的一种伦理困境,他的复杂身份让他无法任选其一。一方面对阿尔及利亚的深厚感情让他能够理解和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但是他不能接受杀戮平民的罪恶行径,更何况他的母亲和亲人都有可能被杀害;另一方面,无论从情感上还是理智上,他无法像萨特他们那样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因为一旦独立,包括他的家人在内所有定居阿尔及利亚的白人就成了外国人或是没有身份的暂住者。处于伦理困境中的加缪认为阿尔及利亚战争是一场悲剧,他只能选择“沉默”。但是保持沉默的加缪并没有停止对社会事务的介入。他写了一百多份上诉书替那些被捕的阿拉伯囚犯辩护,要求释放他们。他也希望各方面的干预能促成两方和解。
1957年加缪赴瑞典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期间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举行的座谈会上,一位阿尔及利亚人质问他为什么没有为阿尔及利亚的正义事业出力。加缪是这样回答的:“……我从来都谴责恐怖主义。我也要谴责那种在阿尔及利亚大街上不问对象盲目进行的恐怖袭击,也许某一天它们会伤及我的母亲及家人。我相信正义,但在捍卫正义之前,我首先要保卫我的母亲。”[5](P724)这便是加缪的伦理选择。在“正义”和“母亲”之间,他选择了“母亲”。他拒绝接受任何披着暴力罪行外衣的“正义”,反对“以正义的名义,原谅那些与真正的正义相背离的东西”[10](P287)。在他看来,不管是法国政府对阿尔及利亚人民阵线实施的武力镇压,还是阿拉伯人对白人平民百姓的屠杀,都是与正义相背离的。他坦承:“这种立场是不会使任何人满意的,我事先就知道了,双方都不会对它表示欢迎。”[10](P283)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义无反顾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样的勇气源于对人道主义的坚持。
五、结语
在加缪生命的最后几年,得不到世人理解和支持的他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小说《第一个人》的创作中。在这部他生前并没有完成的小说里,加缪借主人公雅克进行了一次“精神返乡”[15](P155)。通过雅克的“寻父”之旅来在追寻自己完整的身份。可以说,加缪的一生都在写作和公共事务参与中探索和构建自己的身份,证明法籍阿尔及利亚人身份的合理合法性。与阿尔及利亚和法兰西这两个地域既近又远,既熟悉又陌生的关系使加缪成为一个永远的“流放者”。文化身份的复杂性和所处时代的特殊背景让他的写作中呈现出一种“殖民情结”。这种情结并不意味着应该给加缪打上殖民主义或反殖民主义的烙印。“杂糅的文化身份总是使加缪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境地,他既生活在‘欧洲的边缘’也生活在非洲的边缘。”[16](P90)但也正是这种“边缘人”的身份让他能游离两种文化之外,看到非边缘人无法看到的文化景观,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价值观。曾深陷伦理困境的加缪一直坚守着自己作为“艺术家”的职责和使命,正如他在接受诺贝尔奖时说的那样:“他虽然是众矢之的,但却十分执著;他虽然有时有失偏颇,但却主持正义。他敢于在众人面前不卑不亢地拿出自己的作品,他虽然经常在痛苦和美之间徘徊,但最终却能从中走出,在破坏中以顽强的精神从事新的建设。”[10](P428)虽然饱受争议,虽然背负着时代和阶级赋予的桎梏,加缪一直坚持不懈地反抗社会的不公,弘扬人的尊严,保持着对真理和爱的信仰,是一个真挚而固执的人道主义者。
[1][美]爱德华·萨义德.李琨译.文化与帝国主义[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2]黄晖,周慧.流散叙事与身份追寻——奈保尔研究[M].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3]Camus,Albert.Oeuvres complètes III[M].Paris:Gallimard,2010.
[4][法]阿尔贝·加缪.柳鸣九等译.加缪全集(小说卷)[M].上海译文出版,2011.
[5][法]奥利维耶·托德.黄晞耘等译.加缪传[M].商务印书馆,2010.
[6][法]罗歇·格勒尼埃.顾嘉琛译.阳光与阴影[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7][法]阿尔贝·加缪.丁世中等译.加缪全集(散文卷 I)[M].上海译文出版,2011.
[8][美]爱德华·萨义德.王宇根译.东方学[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9]Mathieu-Job,M.Comment les écrivains algériens francophones lisent-ils Camus[J].Revue d'histoire littéraire de la France,2013(113).
[10][法]阿尔贝·加缪.杨荣甲等译.加缪全集(散文卷 II)[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11]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00.
[12][英]乔治·拉伦.戴从容译.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194.
[13]Pierré-Caps,S.Albert Camus [J].le fédéralisme et l’Algérie Civitas Europa,2014(32).
[14]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15]郭艳娟.寻找自己的亚当[J].齐鲁学刊,2004(3).
[16]刘成富.加缪:徘徊在基督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的人[J].外语研究,2016(3).
(责任编辑:潘维永)
I106
A
1007-9106(2017)12-0127-05
* 本文为2017年辽宁省高等学校基本科研项目(编号:2017JYT2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美学思想研究”(编号:16BWW071)的阶段性成果。
陈娟(1983—),女,南京大学在读博士,大连外国语大学法语系讲师,研究方向为法国文学;陈丽娟(1979—),女,大连外国语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法国文学与文化。
——晚近西方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编纂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