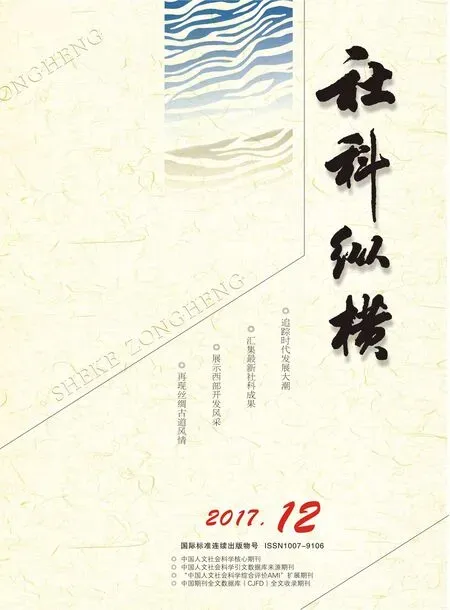救世与利己的价值尴尬
——探析严歌苓新移民小说中的美国形象
朱耀龙
(邵阳学院 湖南 邵阳 422000)
救世与利己的价值尴尬
——探析严歌苓新移民小说中的美国形象
朱耀龙
(邵阳学院 湖南 邵阳 422000)
严歌苓的新移民小说是当代华文文学中的一朵奇葩,她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不同于其他作家笔下的美国形象。她以一个文化两栖人的视角细致地剖析了美国文化的两个特征:以拯救世界为价值的理念和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的尴尬,深刻地揭示了美国文化中个人主义价值的巨大影响,以及对新移民所产生的巨大心理震撼。
严歌苓 救世主 逐利化 数字化
一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关于美国形象的描写充满了戏剧性的变化:从二战时的民主自由与和平的卫士到新政权笔下的万恶的资本主义的恶魔,再到改革开放后的黄金国度等等,都充满了中国人对美国形象与其文化的探索和想象。这里面既有当时特定的政治思维的叙述,也有东方文化和民族立场的虚拟,当然其中也有理性客观的描述,只是在当时特定的时代中,却显得那么的渺茫微弱。而在这些对美国异域的想象和叙述中,有两组人物的叙述特别引人注目,这就是20世纪的50、60年代台湾留美学生和80年代的大陆新移民。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真正的亲身经历者,将自己在异国他乡的生活遭际真实地展示在自己的作品中,而其中的意味确实耐人寻味的:都是同样的民族,都展示出了完全不同的美国面貌。
细细品味,两者叙述的是角度是不同的。
台湾留学生们是站在民族文化的立场上对美国文化持批判的态度的。他们认为美国文化是冰冷的机械的物质文明,一切都是以利益为目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冷漠孤寂的,而且美国对这些后来的亚裔充满了歧视。他们难以融入到美国真正的社会文化中去,认为美国文化是一种没有精神追求的文化,而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充满了眷恋。这里面最有代表性的是白先勇和於梨华。她们的作品中充满了对美国社会的失望、不满和愤怒。如白先勇的《芝加哥之死》的吴汉魂和《谪仙记》的李彤,以及於梨华《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的牟天磊等形象,集中地反映了留学生的苦闷、寂寞与迷惘,作者的自身经历是小说情节的重要来源。如牟天磊,在众人眼里已是功成名就,但他付出的代价却是旁人所不能理解的。为了挣扎着求得生存,他干着各种粗重的工作,还要忍受老板的随意侮辱和美国人的种族歧视,失去了初恋的情人,也无法与在美国寻得的情人最终在一起,在情感上受尽痛楚。而人生和情感的失落还不是他面对的仅有的问题,在激烈的文化冲突之下,他的理想不仅在重理轻文的现实中沦落,而且也无法真正与美国社会相融合。无可避免流浪情结,让他感到“我是一个岛,岛上都是沙,每颗沙都是寂寞”[1]。这种“无根的一代”心理是由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导致的。所以在台湾留学生文学中,美国的形象总体是负面的,他们对美国社会是批判的。
但在大陆新移民文学中,美国形象是复杂的。他们对美国是既爱又恨,爱恨交加的。如果说台湾留学生文学主要基于传统文化来批判美国社会的话,那么大陆新移民文学主要是基于当代大陆的民众生存叙述美国的经历遭遇的。他们既有着种种不堪的过往,在大陆所经历的不幸和悲惨,所以他们对美国制度文化中的人性化是爱慕的,也是从心眼里认可的。而且刚刚从贫穷落后的国家来到美国,对美国的富有也是从内心里仰慕的。而且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家,这种异质的文化是我们国内无法想象的。这就是许多中国人千方百计的要持有美国绿卡的原因。但是另一方面,毕竟是不同的文化,其冲突是不可避免,尤其是美国人骨子里对中国人的偏见处处可见。对于一个在美国飘零的中国人来说,其种族的印记标签,以及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意识,对于异质文化的反抗无疑在内心引发激烈的波澜。但是,他们毕竟是要在这块土地上永久的生活的,所以他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融入到这个社会中去,认可他们的规则,认可他们的文化,按美国的文化思维生活。如严歌苓的《也是亚当也是夏娃》的中国女博士伊娃,《栗色头发》中的我,《无出路咖啡馆》中的女留学生,《海那边》的王老板等。所以,大陆新移民文学中的叙述视角是双重的,既有人性的也有文化的,既有肯定也有否定,但总体是肯定的正面形象,而不同于台湾留学生文学作品中的否定的负面形象。
二
而严歌苓小说是大陆新移民文学中最独树一帜的,近年来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她的小说,通过一系列美国人物形象的描写,展示非常明晰的美国国家的整体形象,透视出美国文化的一些本质的共性。
一是救世主的形象。在严歌苓的小说中,美国人的优越浸透在骨子里,尤其是面对来自东方的中国人。非常有意思的是,在严歌苓的小说中,为了将这种优越明显的展示出来,特别采用了男性/女性的身份标签来叙述故事。救与被救、看与被看来淋漓尽致地展示美国的强者地位。如《扶桑》中的克里斯与扶桑的关系,如《栗色头发》中的美国男子与中国的女留学生,《也是亚当也是夏娃》中的美国男同性恋者与中国的女博士,《无出路咖啡馆》中的美国外交官与中国女留学生,这些女性都有着共同的特性:生活无着落,贫困孤独,时时处在生活的贫穷的煎熬中。
而在当时所有的美国人眼中,中国都是贫穷、野蛮落后的代名词。
“听说中国人没有足够的粮食和肉,全国在一夜之间就打死七百三十五万零三条狗,然后全把他们吃了!”
“你笑起来牙齿真美。不过听说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不刷牙。”
“在他开车的一路,在他兴致勃勃地谈起他将怎样帮我摆脱中国人不整洁、不礼貌、不文明的居住环境时。”[2]
在美的中国留学生,居住在脏乱的房子里,开着会移动的垃圾箱的车,所有的家具都是从大街上捡来的。
正是中国留学生的贫穷,恰好印证了美国人心目中的野蛮落后贫穷的中国形象,以致凸显她们的优越感。这一种优越感有着美国人的傲慢。如在《栗色头发》中,“我”违心的夸奖一个残废的美国姑娘画得很出色,她自信地笑笑,说:“中国人长得都这样。”
正是基于对中国这样的认识,美国人展现出了自己高尚的救世主的面孔。克里斯在面对着生活如同猪一样受人奴役的妓女扶桑时,心中悠然而生出一股解放和拯救世界的骑侠的梦想:“克里斯感到自己顶天立地,不是神话,而是现实中的忠勇骑侠。而两条始终微微叉开站立的腿铁一般坚硬地立于马蹬,居高临下的看着被他深爱的女奴:你自由了。”而具有这样思想的人不只克里斯一个,而是整个美国社会。“克里斯从演讲人的手势和词汇中感到了正派的力量,他们正在做的是解放奴隶,解放所有的被他们的同胞贩卖到此地的中国奴隶。他认识到靠自己个人的力量是不够解放包括扶桑在内的几千中国女奴,必须投身到这样的人群中来。他想像自己随着人群冲上那幢小楼,一手执火一手执剑,然后他会对扶桑宣布:你自由了。”[3]
《栗色头发》中的美国小伙,面对来自大陆、语言不通、飘零无依的“我”时,给予热情的帮助,并保护我不受画廊老板的欺诈。
而在《无出路咖啡馆》里,小说中的美国人大多以救世主自居。年轻帅气的小伙理查福慈,身为FBI特工,在对“我”这个中国大陆来的穷留学生不断调查审问的同时,一再强调他对第三世界的满腔爱心,并以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言说。他收养了韩国女童阳光灿烂,每天要与烦人的尿布和幼儿园打交道,不但牺牲了大把休闲时间,偶尔还要耽误工作。他与“我”的幼时好友阿书交往,想与阿书结婚,以实现他对第三世界人们拯救的愿望。房东牧师夫妇见“我”经济困窘,为“我”多次举办教友募捐会。年迈的牧师太太犹如一只护着小鸡的母鸡,为30岁的“我”追回电话公司的电话费,并对调查审问“我”的约翰进行义正言辞的指责。当听说系里还有“我”这样的贫困生时,系主任所表现出极度愤慨[4]。这些美国人来自各行各业,有外交部官员、FBI特工、牧师、教授、还有年轻漂亮的白领劳拉、年老的贵妇米莉等,他们以世界优等公民自居,对来自贫穷的第三世界的我们表示关心与善意。在他们看来,我们是被置放于篮子中的孩子,顺水漂流到了此岸,拯救我们也就成为他们神圣的职责。这反映了这些美国人把他者置于弱势地位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历史根源,按萨义德的观点,是前殖民时期西方对东方殖民的优越感,而就中国社会现实来说,80、90年代中国经济在文革后刚刚复苏,还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强国美国,美国人把中国人当成被拯救者,就是这种现实的反映。
哪怕有时在友好地帮助他人时,美国式的救世主般的优越感是非常明显的。他们甚至以自己为解救他人而做出的牺牲而心里感觉自己的伟大。《无出路咖啡馆》中的安德烈为女友的窘迫生活而感到心痛,为爱情而放弃自己美好的外交生涯。而另一个特工喋喋不休的叙说自己的韩国养女时所流露出的心态,还有《栗色头发》中的美国男工程师的蛮横。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介入对方的生活,自以为是在帮助他人,自以为对方应该对她们感激涕零。但事实的结果,由于他们的这种解救者与苦难者之间的不平等心理与现实处境,他们自以为令人感动的非常伟大的举动,却并没有使被拯救者出现他们心目中应该出现的顺从感恩的姿态。结果恰恰相反,他们这种以救世主自居的面孔,让被解救者远离了他们,安德烈尽管作了巨大的牺牲与付出,但最终没有留住自己的女朋友,扶桑也没有与克里斯结合,而特工理查的养女一点也不感激他,反而越来越桀骜不驯。这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的。因为他们的言行不仅仅伤害了一个人的心灵,而是伤害了一个民族甚至一个种族的尊严,而这种伤害是任何拯救或牺牲或付出难以补救与挽回的。这是严歌苓笔下的喜欢标签化他国人民的美国人所根本没有想到或他们根本不屑想到的。
二是利己的理性化。很有意思的是,美国清教徒充满了对沉沦苦难世界的拯救意识,这本是利他的。可以看出当时立国的清教徒们的伟大理想。但美国文化又是典型的个人主义加之为核心的文化,尤其是美国是一个商业化高度发达的国度,是一个典型的利己主义的民族。大家看看他对二战后日本态度的转变,就能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所以在美国的文化里面充满了这样救世与利己的价值尴尬。
所谓理性化是指面对生活时很少有情绪化的冲动选择,一切都展现出以自我为中心的逐利性的倾向,不让情绪来干扰自己的选择。归根结底,这是美国浓郁的商业社会中契约意识在日常生活中行为的展现。美国的这种契约意识最核心的内核就是对自我利益的保护。它是以个体利益的取向为标准的,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情为核心的价值思维取向。在严歌苓的新移民小说中,它有两条不容他人违背的原则:规则化的契约意识和精准的数字化意识。而初到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往往还是遵循着故土的传统文化的行事逻辑,却往往在美国这个西方文化的国度中,遭遇到了一系列文化的冲击,感受到了巨大的心灵震撼。
规则化的契约意识。在美国文化中,对个体利益的保护是其最为核心的行事原则和思想。这一切都归因于最初从英国来到美国的清教徒立国的思想。为了避免出现民众个体利益像欧洲一样遭受王权任意侵犯,做出了种种对个体权益的保护措施,形成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政府之间的契约精神,认真履行成文的、不成文的各种契约,信守承诺,勇担责任,对别人、对社会有一种永恒的负责态度,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如在《也是亚当也是夏娃》中,怀孕的伊娃,一位已经离婚的中国女博士为一位美国男同性恋者怀孕生孩子,因为经常吃标准的营养餐而乏味,偷偷地吃了一包方便面。
“伊娃,为这个孩子,我和你都已经牺牲了不少东西。已经要成功了,别前功尽失,好吗?味精在美国连成人都不吃的,怎么能让胎儿吃呢?”[5]不要以为亚当是在关心伊娃,而是担心自己的女儿受到伤害。因为这个女孩是属于他个人的,而伊娃只不过是个出租自己子宫的母体,所以如果因吃方便面而伤害了胎儿,那就是侵犯了他的利益!美国文化中的这种自利性是非常浓厚的。
所以美国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对个体利益的伤害和损失,他们有着一系列的规则意识,即规则化的思维,它渗透在美国人日常行为习惯中。这些文化特性往往让初到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原有的处事规则受到挑战甚至坍塌瓦解。如在《栗色头发》中的中国女留学生“我”与娄贝尔夫人的交往,让我们看到中美文化的碰撞与冲突。“我”为了学好美国英语,又是帮两位粉刷工人粉刷墙壁,又是请他们喝果汁,以为这样既很好地训练了自己的英语口语,又帮助了这两位辛苦的粉刷工人,这是一种双赢。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中国传统美德的体现。但娄贝尔说,我花钱是请他们粉刷墙壁,而不是给“我”补习英语,补习英语是你的事情,不应该占用她雇请工人粉刷的时间,而且你粉刷墙壁不专业,刷得不好,影响了质量。
“她耐心地接着讲解:‘就是说:他们拿了我的钱,在这段时间里,应该全心全意、集中精力为我工作,而你占用了我付了钱的时间,使他们为你工作。这显然是不对的。’
我口吃道:‘我一直在帮着他们油漆啊,我并没有要求你付我工钱!……’
‘怪不得我昨天觉得漆的质量很差,现在我才明白原因!’
她脸沉下来,告诫我不可再犯这样的错误。然后拿着我熨好的衬衫,迈着典雅的步子,一路轻轻放着小屁,回她房间去了。我一动也动不得,说不上气和委屈,却出来一种严重的挫败感。我使劲克服着挫败感,她连声喊我我都没意识到。”[2]
在这里,“我”为什么会有严重的挫败感,是因为“我”还秉承着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情为核心的情理思维,认为自己在帮助他人,又有利于自己的语言学习,是一个双赢的行为。然而这样一个在中国人看来的双赢的行为,在娄贝尔夫人等美国人看来,正违背了他们的契约规则:专业化的精细操作,你替他们给我粉刷墙壁,你有他们的专业水准吗?墙壁没有达到应有的工艺水准,这不是影响到我房屋的美观吗?这不是损害了我的利益吗?而且在娄贝尔夫人看来,他们给我粉刷墙壁,我给了他们粉刷墙壁的费用。这就够了,至于他们天热口渴,那是他们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是不能另外付费的。而对于“我”这个想学好美国英语的中国人,来找粉刷工人学英语,完全是捣乱,让工人们不能很好的粉刷墙壁!而且,你学英语,是应该自己付费的,为什么要占用我的粉刷墙壁的费用和时间?娄贝尔夫人的自利思维逻辑的强大到“我”“说不上气和委屈”“严重的挫败感”。为什么,美国文化中的自利原则,也可以说是一种契约意识。而在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助人为乐的美德,却恰恰违背了美国文化中的契约意识。所以“我”只能感到一种无力的挫败感。而这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所难以适应的。
而这种自利性规则意识还体现在事物的归属问题上。娄贝尔夫人丢了一块蓝宝石,三番五次地隐约其词地试探,怀疑是“我”偷了。“我”不胜其烦,后来在在门外小径上的草丛里捡到,以为从此可以彻底摆脱嫌疑。“我从来没这样焦灼和喜悦地期盼娄贝尔夫人回来。我几乎将她堵在门口,就将那颗蓝宝石捧给了她。”但结果,“她客气地说了声‘谢谢’,然后说:‘我明天把它带到首饰店去鉴定一下。不过你有把握它的确在门外草地上?’刹那间,我又回到对这种语言最初的浑沌状态。我不懂它,也觉得幸而不懂它。它是一种永远使我感到遥远而陌生的语言。”
在这里的“我”处处还是按着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行事,满以为可以得到对方的理解和赞赏,但在娄贝尔夫人的美国文化面前碰壁而沮丧。像这种文化差异所引发的冲突以及产生的心理落差,在严歌苓的新移民小说中随处可见。如《方月饼》中的“我”在异国他乡过中国的传统中秋节,当“我”热切地向外国舍友玛雅介绍中国嫦娥奔月、玉兔捣药的传说时,玛雅却产生了误解,那种东方的诗意美在她的解释下荡然无存。在分享完“我”买来的月饼之后,她还让我一起分担买花的费用,异国的月亮瞬间失去了温暖的情感抚慰,感觉好像一枚苦涩的“阿司匹林大药片”[2]。美国是一个以个人主义价值为核心高度发展繁荣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样重商主义的国度中,利益是这个国家运转的中心和动力,责任义务划分得非常明晰。这种超出中国人以情为核心“以和为贵”生活方式的理性原则,对于刚到美国的严歌苓来说,显然是不能很快接受的。
数字化精准式的做事原则。如果说契约化的规则是为了防止自己利益遭受侵害的话,那么数字化精准式的做事原则是保障自己的事情顺利有效地进行,以达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最优化。《也是亚当,也是夏娃》中,同性恋男子亚当为了家族的利益,不得不生育一个后代。为了这个目的,他戒除了身上所有的不良习惯:“他在三年前戒了大麻,两年半前戒了烟,紧接着戒了咖啡因、酒,把每天锻炼一小时改为一个半小时。他喝纯度最高的水,严密控制食物里的盐分和脂肪,很少吃甜食,一步一步地为这次怀孕准备一具最理想的父体。”[5]
选择在他看来最理想的母体: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国女博士“我”。因为“生育器官最成熟、心智也最成熟”,而且“现实、自律、忍耐”。还有“比起白种女人,我们少许多麻烦,不会事后上法庭、闹财产、争夺孩子监护权”,也“少有吸毒、酗酒、吃抑郁症药片”,以“确保他的孩子不会从基因中得到任何形式的乖戾”。还因为“我的身高、体重、五官排列,都正合他心里的刻度。太出众的东西是危险的,适度的平庸是一个人心智健康、终生快乐的最好保障。他要他的孩子终生快乐,这比富有、才华、相貌标致重要得多”[5]。
采用最科学合理的孕妇营养方式和婴儿养育方式:“各种以最科学、最理性的配方配制的养料。每天,餐桌上出现了三支小杯,排成一列,里面盛着五颜六色的各种维生素片剂、胶囊,亚当要我以它们来做三餐。牛奶是按刻度饮进,大叶片的绿色菜蔬也按斤两消耗。”[5]
但唯一的缺陷是他在养育的过程缺乏人类最需要的关爱和情感。在这一切最好的方式当中,一切都是在冷冰冰的理性下精准的进行,原以为会得到一个最理想的baby,但最后却是一个畸形的婴儿。亚当的生活都是按理性原则操作的:用维生素的药片制定自己的营养食表,牛奶按刻度饮用,大叶片的绿色菜蔬也按斤两消耗,甚至包括对未来生命的设定也可以通过借腹生子来完成。但是亚当生命规划最致命的一点就是没有生活乐趣与感性冲动,一切都好像在完成应尽的义务,这样的理性变异者正是美国这个高速运转社会的现实产物。作者对这些变异者充满了焦虑,并试图找出其行为背后社会文化的深层原因。
三
严歌苓对美国形象的塑造,以其亲身的经历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省为参照,深刻的揭示了美国文化的本质特征:它既有美国最初立国的清教徒的对世界的救济理想,也有这后来以民主和自由斗士自居的全球救世主的自傲和优越感,这恐怕是严歌苓笔下救世主形象的来源。但这种形象由于不顾其他民族的尊严和情感,甚至有时是伤害和践踏其他民族的尊严和情感,所以他并没有得到他所希望得到的感恩戴德。从这一方面来讲,严歌苓是坚持了自己的民族立场和情感的。但另一方面,严歌苓置身在美国浓郁的商业文化的社会里,对美国文化中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自利的行事思维和方式,是深有感触,也是有抵触和批判的。这是一种不同于中国农耕文明以情为核心的工商文明,对于在中国文化中浸润长大的留学生来说自然是难适应的。难能可贵的是,严歌苓虽然从情感上接受不了这样的处事方式,但客观上展示了美国社会中自由个性的发展,虽然这种发展不一定是人们所接受的,但严歌苓总体上是认可的。正因为有了这种个人主义的思维方式,所以在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反省时,才能深刻的解释中国文化日常行为和思想方式中许多不人道的阴暗面。也正因为如此,严歌苓笔下的美国形象是复杂而又充满了价值理念的尴尬。
[1]於梨华.又见棕榈,又见棕榈[M].江苏文艺出版社,1965.
[2]严歌苓.严歌苓文集·少女小渔[M].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
[3]严歌苓.严歌苓文集·扶桑[M].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
[4]严歌苓.无出路咖啡馆[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5]严歌苓.也是亚当,也是夏娃[M].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丁芳琴)
I207.42
A
1007-9106(2017)12-0136-05
* 本文为2012年湖南省教育厅一般课题“论严歌苓新移民小说中的美国形象”(编号:12C0878)。
朱耀龙(1973—),邵阳学院中文系讲师,文艺学硕士,研究方向为文艺鉴赏与文艺理论批评、文学理论教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