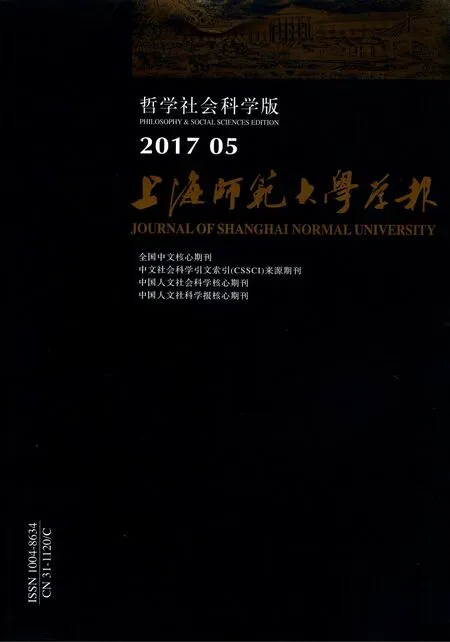论刘勰“研术”说的本体论与方法论意义
张利群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论刘勰“研术”说的本体论与方法论意义
张利群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刘勰《文心雕龙·总术》提出“研术”说,通过“原道”的文学本体方法论、“圆照”的文学鉴赏方法论、“见异”的文学批评方法论构成其方法论体系,在道、法、术的宏观方法与微观方法结合中体现出其历史和辩证的方法论,从思维方式、创作方法、艺术技巧和鉴赏批评方法的多维综合视角建构了“文心”与“雕龙”的方法论体系。
研术;原道;圆照;见异;方法论
前言
刘勰《文心雕龙》文论批评体系中,方法论是重要的构成内容。因为世界观与方法论是有着紧密联系的,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体现世界观。因而刘勰的方法论通过世界观,即文艺观、文论观,渗透于《文心雕龙》全书中。其本体论(总论)中含有文艺本体方法论;创作论中含有创作方法论;文体论中含有文体方法论;赏评论中含有赏评方法论;等等;尤其是在《总术》篇中专题讨论方法论问题。所谓“术”,指方法及其技巧、技法。刘勰在《书记》中,从文体角度解释“术”时指出:“术者,路也。算历极数,见路乃明。”说明“术”作为方法,具有工具、手段、途径、方向的含义。故而“总术”立意并不仅仅在于阐述具体的方法,而且在于对方法进行理论层面的总体讨论从而构成方法论,从方法的定位、功用、意义等方面构成对方法的实践运用的指导和规范。这无论是对创作还是赏评而言,也无论是对文学本体还是文体而言,都具有方法论的普遍意义和作用。故而陆侃如、牟世金认为“这里的‘术’概括了刘勰所论各种创作原理方法和技巧”。[1](P522)
刘勰在《总术》中提出“研术”的命题,围绕“研术”这一主旨构成其“总术”理论体系。在《总术》中,刘勰还提出“晓术”“执术”“术有恒数”“文体多术”“有术有门”等,在其他篇章中也大量涉及对“术”的讨论,例如,在《神思》中提出“驭文之首术”“秉心养术”“心总要术”等,故而“术”在刘勰文论批评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刘勰提出“研术”说,其现实针对性是十分明确的。首先,这是针对一些文学研究的偏颇而言的:“昔陆代《文赋》,号为曲尽;然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故知九变之贯匪穷,知言之选难备矣。”这说明陆机《文赋》虽讨论文学很详细,但流于琐碎,没有抓住要点。其原因一是批评所研究的文学千变万化,批评难以穷尽这些变化;二是陆机缺乏正确的研究方法,从而批评不得要领。其次,针对文坛不重方法的弊端进行批评,“凡精虑造文,各竞新丽;多欲练辞,莫肯研术”。不重“研术”导致的结果为:“落落之玉,或乱乎石;碌碌之石,时似乎玉。精者要约,匮者亦鲜。博者该赡,芜者亦繁。辨者昭晰,浅者亦露。奥者复隐,诡者亦典。或义华而声悴,或理拙而文泽。”没有“研术”自然会导致创作和批评中出现失误,因而文学“研术”是十分重要从而会影响创作和批评成败的大问题。再次,刘勰认定“研术”与文学规律有密切关系。“知夫调钟未易,张琴实难。伶人告和,不必尽窕槬桍之中;动用挥扇,何必穷初终之韵?魏文比篇章于音乐,盖有征矣。夫不截盘根,无山验其器;不剖文奥,无以辨通才。才之能通,必资晓术。”这说明“研术”是针对不谙文学规律、不懂方法的人而提出来的。
当然,刘勰主张“研术”的用心不仅仅在于此,“研术”还牵涉作文和文章之“大体”:“文场笔苑,有术有门。务先大体,鉴必穷源。”所谓“大体”指作文和文章的基本规律与根本规则,延伸为文学体制和文章体制。正如王运熙指出的:“可见这术不是局部性的锤炼字句(所谓‘练辞’),而是就整篇文章的体制而言,也就是所谓‘大体’。”[2](P130)故而刘勰“研术”不仅是针对文坛时弊的批评而言,更重要的是针对作文“务先大体”而言,“研术”是为了把握作文的规律以及方法和途径。
那么,“研术”的重要性何在呢?“术”的功用和意义何在呢?刘勰提出“执术驭篇”的命题,也就是说通过掌握方法来进行写作和把握文学创作的规律。他指出:“是以执术驭篇,似善弈之穷数;弃术任心,如博塞之邀遇。故博塞之文,借巧傥来;虽前驱有功,而后援难继。少既无以相接,多亦不知所删;乃多少之并惑,何妍蚩之能制乎?若夫善奕之文,则术有恒数,按部整伍,以待情会;同时顺机,动不失正。数逢其极,机入其巧,则义味腾跃而生,辞气丛杂而至。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断章之功,于斯盛矣。夫骥足虽骏,纆牵忌长;以万分一累,且废千里。”刘勰以下围棋做比喻,说明讲究下棋方法才会有棋艺;否则不讲方法而追求撞彩,以投机取巧去碰运气,自然就不会有棋艺,偶尔的碰彩所赢也不能阻止此后必输的命运。因此作文与下棋道理一样,讲究方法技艺才会赢得成功。黄侃指出:“是知术之于文,等于规矩之于工师,节奏之于朦瞍,岂有不先晓解而可率尔操觚者哉?”[3](P208~209)
以此而论,“执术”关涉“驭篇”的大问题。首先,“执术”从表层看,似乎是一个方法技艺的问题,但深入分析,就不难发现作文之“术”实则反映出作文的规律,方法技艺必须依循规律而设定,也就是“截盘根”“剖文奥”的作文规律,顺应规律也就能“执术”。其次,“执术”还能“通才”,“才之能通,必资晓术”,要使文才妙用无碍,就必须通晓写作方法技艺。这也就说明“执术”与作者的创作才华有关,是作者洞悉文奥的才华智慧的表现方式。再次,“执术”才能抓住机遇和顺应机遇。“术有恒数”说明方法技艺与作家作文的基本素质和能力密切相关,故而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持久性;而机遇则是不稳定、不持久的,甚至还会有巧合、碰巧的情况,因而只是一种机会而已。如果“莫肯研术”,一味碰运气,是难以成功的;只有“执术”“研术”,从而才能“因时顺机”,抓住机遇或创造机遇。最后,作文“执术”才能“乘一总万,举要治繁”,方法实质上是引导或导向目的、目标的途径,有方法可以让人少走弯路,或者说能走“捷径”,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掌握了方法,就能举一反三,抓住要点,纲举目张。可见,刘勰对“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是十分明确的,从而对“术”的功用和意义的认识也是十分明确的。张少康指出:“然而,仅仅懂得文术之重要,显然还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懂得驾驶文术的要害所在。对于文术,历来的文人并不是完全废弃不讲,而都是重视它,讲究它的。问题是在于仅仅注重某些具体的写作技巧,往往还只是抓住了枝叶,而没有把握根本。刘勰讲究文术之比别人高明之处在于:他强调了必须在统观全局的指导思想之下,来具体考虑写作技巧,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具体技巧达到各得其所的积极效果。”④[4](P197~198)因而刘勰在“赞曰”中总结说“文场笔苑,有术有门”,明确指出有“术”就有“门”,“术”是进入文场笔苑的门路。继而针对创作方法的多种多样,他认为要把握四条原则:一是“务先大体”,也就是说“研术”宜从总体把握;二是“鉴必穷源”,也就是说“研术”宜认清写作规律;三是“乘一总万”,也就是说根据基本方法来掌握各种技巧;四是“举要治繁”,也就是说抓住要点来驾驭其他。这四条“研术”和“执术”的原则说明刘勰是从方法论角度来讨论“术”的,同时也是从写作规律、写作艺术原理的角度来讨论“术”的;他不仅仅局限于“术”的技巧技术层面,而是在规律、原理亦即“道”“法”层面来讨论“术”,从而构成方法论意义上的道、法、术结构和构成系统。诚如刘勰所说的“思无定契,理有恒存”,方法是有规律、有理数的。写作文思虽千变万化而无定数,但方法之“理”则是有定数的,故而“术”与道、法密切相关。尽管“术”也有多种多样的方法形式,但“术”之理是相通的,“术”之理与道理、法理一样,有其自身的路数和规律。故而,进一步讨论“术”之理就必须从刘勰的方法论入手,深入讨论道、法、术的关系及其支撑“术”的深层次内涵之理。
一、“原道”:文学本体方法论
早在刘勰之前的先秦庄子就在“庖丁解牛”寓言中阐明了道与技的关系。当文惠君见庖丁解牛是如此快捷完美而惊叹曰:“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答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5]也就是说,庖丁解牛之法靠的是“道”而非“技”,依靠的是对对象、活动规律的把握而非技巧、技法的运用,由此而得出“道进乎技”的结论。当然,从辩证法角度看,“道”与“技”的关系其实应是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或层面,“道”是规律和本体的呈现,故而亦是“技”的规律和本体,只有循“道”之“技”或“技”之“道”才是最佳方法;“技”应是“道”的外在表现形式,或者说是获“道”之“技”,入“道”之法。因而“道”从方法论角度而言可谓大技、至技、绝技,而非雕虫小技,“道”与“技”的辩证统一,必须寻求由“道”入“技”、因“道”而“技”的途径。就此亦可知,“道”是方法本体和规律,显然更高于、更进于方法技巧之“技”。这不仅是因为“道”具有形而上的宏观指导意义,“技”则具有形而下的微观操作运用意义,此乃所谓“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的缘故,而且还因为,庄子之“道”为自然之道,具有规律、本体、规则的意义。如果将刘勰讨论的“术”对应于庄子讨论的“技”的话,就可明白刘勰的用心也像庄子那样必须揭示出“术”之理,也就是“术”后面的“道”“理”的规律和本体。因而在刘勰著作总论中首先是《原道》,不仅是“原”文学之道,而且也是“原”方法之“道”、“术”之“道”,从而在作为方法的“术”中揭示其“道”的层面。也就是说,对“术”也必须“原道”,必须探寻“术”的规律和本体。从方法论角度而言,“原道”除了具有探讨方法之“道”来获“道”之义外,“原”作为方法使用的动词具有溯源、原则、还原之义,作为名词具有本原、本体、本质之义,因而这是一种探讨本质、本体、本原的方法。刘勰不仅提出“原道”,而且还提出“原道心以敷章”“原始以表未”等命题,因而“原”作为方法论可以从四方面展开其内涵和意义:
其一,“原道”的探讨文学本质的方法论。《原道》的目的在《序志》中讲得很清楚,即“本乎道”,是为了说明文学本质、本体、本原的根本性问题,故而刘勰“原道”的目的是使“文”能归本归宗,能“原”文之道。要使文道能“原”,首先必须将文放在宇宙天地、自然万物中定位,亦即将文道放在天道、地道中定位。故而刘勰先提出天才、地才、人才的“三才”说,将人放在天、地、人中定位;后列出天文、地文、人文的“三文”说,从而将人文放在天文、地文中定位;此后再由天道、地道引出人道,将人道放在天道、地道中定位;最后得出文之道乃“自然之道”的结论。这个“自然之道”就是指规律,顺应自然之道也就是顺应规律、顺应自然,遵循自然而然、无迹可求之法。引申而论,“原道”所“原”文之道,其实就是以自然为本体、本质、本原之道,回归自然之道,返璞归真之道,拨乱反正之道,追根溯源之道。同时,刘勰还指出“原道心以敷章”,所谓“道心”,指道的精神。刘勰以人之“心”来比喻道,其用心正如《文心雕龙》用“文心”一样,是指称源自于心的精神。因而,“道心”一方面含有遵循自然、遵循规律之义;另一方面也含有“人文”所强调的人的精神、人之“心”的作用的意义。故而,刘勰认定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因此,“原道”的实质是“原人”,“原人”的实质是“原心”,只有“原心”才会有“文心”。这正如易中天指出的:“刘勰的‘自然’境界亦然:‘率志’即‘从心所欲’(自由、合目的),‘合契’即‘不逾矩’(必然、合规律)。它们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唯其如此,刘勰尽管大讲‘术’‘法’‘数’‘则’,强调审美形式的规范化程式化,都与‘自然’观念毫不冲突。”[6](P155)由此可见,文原于道,也原于心,是道与心的统一,也是自然之道与人文之心的统一,故而“道心”既可作道之心解,亦可作道与心解。那么,文学的本质、本原、本体是顺道之心,是合心之道,是体现道的精神和实质的人文结果。
其二,“原始以表末”的溯源方法。刘勰在《序志》中指出文体辨析的“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四法。这里所用“原始”是做动词用,指探原、溯源之义。因而“原”的方法是寻找源头、初始、根源、原因的方法。这既是一种史源式的探溯源流的历史之法,又是一种辩证逻辑式的探讨前因后果关系的揭示本质、本原的方法。文学何以要“原始”,首先是因为文学的本质、本体、本原有一个发生、起源的问题。也就是追寻文学的源头、根源在哪里,只有找到文学之源,才能发展文学之流。其次是因为文体要“囿别区分”的辨体,没有文体发生起源之源头,就难以把握文体的发展变化,也就难以区分辨别不同文体的差别。再次,“原始”是为了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文坛时弊所形成的“谬体”“讹体”“变体”必须通过“原始”而“表末”,清源才能正本,反正才能拨乱。最后,“原始”是为了探讨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从前因后果的逻辑联系中找到理据和根源,因而刘勰在运用“原始”法时,并不仅仅局限于对文体源流的评论,而且广泛运用于作家、作品、文学史的评论中,使其在运用中不仅是一种历史的方法,而且也是一种逻辑的方法,通过“原始”应用将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有机统一在一起。
其三,“原”是“师乎圣,体乎经”的确立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的方法。《原道》所提出的“原”的方法对《征圣》《宗经》的方法论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也就是说文学不仅要“原道”,而且还要原圣、原经。虽然刘勰是用“征”“宗”来说明圣、经之“原”,但其内在逻辑性及其事理是殊途同归的。因为无论是圣人也好,还是经书也好,在刘勰看来都应是文学之根、文学之本。“道”“圣”“经”的关系在《原道》中已说明清楚,“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故而“圣”“经”与“道”一样,对于文学而言都有本质、本体、本原的决定作用。由此“征圣”是从作者角度“原”至“圣”,“宗经”是从作品角度“原”至“经”,将圣人视为作者的源头,将经书视为作品的源头。故而刘勰提出:“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六义”既可谓“宗经”的具体标准和原则,又可谓是对作品完整把握的方法。尽管这不乏刘勰思想中的正统、正宗因素,但对于纠正当时文坛时弊,规范和保障文学活动的开展,确立文学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是起了积极作用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原”的方法和“征”“宗”的方法结合在一起,强调征验实证方法,强调师法传统的作用,从方法论角度而言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的,这对如何确立文学观,确立文学理论批评的指导思想,确立文学评价的价值取向和标准,尤其是确立核心价值体系,是有方法论意义的。
其四,“原”的方法在“通变”“因革”文学史理论中的方法论意义。刘勰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理论主要表现在“通变”“因革”方法论中,无论是刘勰对作家作品的评论也好,还是他对各种不同的文体的评论也好,都是将之放置在文学史、文体史中来辨析评价的,也就是说,都会有一个史源式的追根溯源的研究,从而准确地为其定位和评价。在《通变》和《时序》中,刘勰还专门讨论了“通变”“因革”的理论,其核心就是文学的传承与革新的辩证关系。这些文学史理论讨论的初衷无疑是当时的文坛发展现状所致,也就是说面对当时文坛的发展和变异状况,一方面必须从理论上说明其发展变革的根据和原因,这就要“原始”,以说明“变则其久,通则不乏”的道理;另一方面必须通过“原”来辨析创新发展和故作标新立异的文坛时弊的区别,不仅在于“原始以表末”,而且在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故而出于这两方面的创作态势和动机,以“原”的方法来总结文学史理论,必然提出“通变”“因革”的结论。因而“原”的方法对于文学史研究而言,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且辩证合理的方法。因为不“原”就难以知晓“通”和“因”,也就是说不了解背景和源流;不“原”也就难以知晓“革”和“变”,也就是说不了解其发展变化的根据和原因。从这一角度而言,“原”的方法对文学史理论和文学史观的确立起了重要作用,当然,也对文学评论和文学史评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至此,道与术的关系已昭然。刘勰在《总术》中指出“举要治繁”,说明“要”与“繁”的关系,从而也就说明了道与术的关系。“举要”也就是抓住根本、本体、源头,因而要“原道”;“治繁”也就是纲举目张,以道统术,以道总术。正如周振甫指出的:“刘勰最后提出掌握创作方法,要‘举要治繁’。不仅要抓住根本,就是对于各种细微末节也不能放过。像驾驭时的绳子长一点,虽是细节,‘且废千里’。这正说明他的创作理论讨论到根本问题像神思、体性、风骨等,也不放过像造句用字等小节了。”[7](P475)故而从方法论角度的“原道”也是为了“总术”,是为了阐明道与术的关系。
二、“圆照”:文学鉴赏方法论
对文学鉴赏和批评方法,刘勰有《知音》专论,同时他又以《才略》《程器》的作家作品论和《通变》《时序》的文学史论,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对“知音”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整体的认识,构成其赏评理论体系。从创作方法和写作方法而言,刘勰在《熔裁》中提出“三准”说:“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余于终,则撮辞以举要。”也就是由情、事、辞元素所构成的创作标准和要求,同时也展现了创作过程及其创作方法。由此,《知音》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鉴赏途径逆创作途径而回溯。刘勰在《知音》中提出的“圆照”说,可谓赏评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刘勰指出:“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并且他还在《总术》中提出“圆鉴”的概念以与“圆照”相映成趣。这虽则是立意于平时积累而后才有创作冲动和灵感勃发的理论观点,但其中引出的“圆照”说则与《知音》中所有赏评理论密切相关,是其理论内核和关键。何谓“圆照”?作为一个合成词,是“圆”的“照”之义。所谓“照”指观照,即观赏、审视、评鉴之义;所谓“圆”指圆通、周延、全面之义。“圆照”意指全面、整体、公正的赏评。赏评提倡“圆”,不只是一个方法问题,而且是一个态度、原则、立场问题。刘勰深受儒家思想文化影响,同时也更深受中国传统“圆”文化和“圆”意识影响。“圆”显然与和谐、中庸、中和、中正等思想有关,从而在思想意识及其方法论上影响刘勰。同时,刘勰倡导“圆照”也直接与他所处的当时文坛现实有关,也就是刘勰是针对当时文坛时弊有感而发。他在《知音》中一开篇就感叹地提出“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的问题,其原因是赏评者往往存在“贱同而思古”“文人相轻”“崇己抑人”“信伪迷真”等弊端;而文学作品“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从而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丧”,“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显而易见,这些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矛盾和问题,不仅会形成“知音”难的困惑,而且会形成误读、误解的偏颇和失误。故而刘勰针对“人莫圆该”的问题才题出“圆照”之说。从方法论意义上理解“圆照”,对批评方法和鉴赏方法而言具有四方面作用和表现方式:
其一,“圆照”是一种全面、完整、多角度、多层次的整体赏评方法。刘勰针对“各执一隅之解”“东向而望,不见西墙”的片面主观的视角提出“圆照”,其正面主张无疑是要求一种多维度的整体赏评方法。他在《序志》中论及其创作用心时,也指出“各照隅隙,鲜观衢路”的文论批评的片面性所形成的弊端:“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巧,《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干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论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因而刘勰创作《文心雕龙》的用心之一就在于能弥补“近代文论”的片面性所造成的偏颇,在其创作中力图全面、完整、多角度、多层面的整体把握,由浅入深、由表入里、由此及彼、由一到多地进行批评,从而无论是在其文论体系的构建中也好,对作家作品的评论中也好,还是在对各种体裁的史论结合的文体批评中也好,都能以多维的眼光、博大的胸怀、执正驭奇的立场和全面、综合的方法来确定评价体系和标准,去获得超越“近代文论”偏颇的整体评价效果。除以“圆”纠偏外,刘勰还以“圆”定“术”。为此,刘勰的鉴赏论“圆照”具体表现为“六观”方法:“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这“六观”之术可谓周全、完满,体现了“圆照”的精神。韩湖初认为:“‘六观’正是‘披文以入情’,即从形式入手分析作品内容的‘观文’方法,故‘六观’应是方法之义。”[8](P148)也就是说,“圆照”应具体表现为“六观”之法,故而才会有《杂文》“事圆而音泽”、《体性》“思转自圆”、《风骨》“骨采未圆”、《比兴》“触物圆鉴”之论。
其二,“圆照”是一种中和、中庸、中正的朴素辩证法。刘勰所接受并以之为指导思想的儒家、道家文化,其实质都含有朴素辩证法思想或因素。老庄主张虚实相生、有无相应、美丑相对,其“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的命题不乏辩证法色彩;儒家主张的“中庸之道”“中和之美”“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也不乏辩证法因素。因而刘勰在《序志》中明确指出“擘肌分理,唯劣折衷”,亦即主张通过具体细致的分析,力求找到不偏不倚、恰当适中的正确主张,故而“折衷”法是充分体现了“圆照”精神的。从“折衷”这一角度来看“圆照”,其含义并非在原则和立场上和稀泥、调和矛盾、混淆是非的圆滑主义或滑头主义,而是一种寻求合理、合适、合度的辩证方法和方法论,因而“折衷”方法导向具有和谐、和平、中和、中正的含义。刘勰在其批评实践中对作家作品的评论,都能执历史观和辩证观结合的方法来一分为二地看问题。诸如,在《正纬》中不仅指出纬书异于经书的荒谬之处,而且提出其有益于文学创作之处;在《辨骚》中也辩证提出屈原《离骚》的宗经有四、离经有四的变异之处。暂且不论其结论准确与否,仅就其辩证折衷的方法而言,“圆照”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种辩证方法还影响到其思维方式,在刘勰的理论思辨中,“圆照”在处理一些理论范畴、命题、理论要素间关系时亦执辩证态度和方法。在《文心雕龙》中,艺术辩证法和理论辩证法的闪光时时可见,“通变”“因革”“情采”“风骨”“体性”以及对文质关系、情景关系、虚实关系、心物关系等的论述中都不乏艺术辩证法和理论辩证法色彩。因此,“圆照”通过“折衷”导向和谐、协调、中和,也是吻合“自然之道”和“为文之用心”的。
其三,“圆照”是一种“执正驭奇”的“正名”方法。刘勰秉承儒家孔子的“正名”思想,在其批评理论和实践中无处不见“正名”的踪迹,如“正纬”、正体、正声、正言、正位,等等。这虽不乏正宗、正统思想的因素,但也不乏倡导积极上进的健康正确的导向因素。“正名”就其方法和方法论角度而言,“执正驭奇”就不仅仅是牵涉方法论的价值取向和思想立场的问题了,而且也牵涉正确方法的选择和运用问题。也就是说,赏评不仅要讲究方法,而且要讲究方法的选择和运用。如果没有选择正确恰当的方法,不仅会走弯路,而且会走错路。因为方法的问题实质就是途径的问题,途径对否也就决定了目的、目标能否实现。因此,刘勰主张“执正驭奇”的方法和方法论,实则是主张正确、公正、合理的方法,主张对正确方法的选择和运用。同时,刘勰还注意一方面用辩证法来对待“执正”,对一些偏离正宗、正统的“异体”“变体”采取了折衷的态度和肯定其发展变化的态度;另一方面则强调方法在运用时的灵活机动性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针对性,以保证在“执正”而不失正的同时,能“与时俱进”地发展变化,这就使“执正”也落实于“圆照”方法中了。
其四,“圆照”是一种“知音”式交流沟通方法。所谓“知”是知己知彼,知根知底,知心知情,因而是一种彼此间相亲相近的交流沟通方式,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相知方式。“圆”从形式和形状看,具有周延、循环、交通、圆满之含义,因而也象征了赏评中主客体之间相互交流、沟通契合的“知音”状态和相知方式。刘勰将“知音”视为赏评活动中的最佳状态和最佳方式就是因为“知”。一方面是因知己知彼、相亲相近的主客体关系,才能交流沟通;另一方面也是因主体性充分发挥,甚至能融情于景、借景抒情的对象化观照、移情观照,共鸣观照的主客体交融、主体间性状态。因此,“知音”作为一种方法来看的话,其实就是一种以交流对话的方式进入赏评活动,从而达到沟通契合目的的“深思鉴奥”赏评方法。
综上所述,“圆照”“圆鉴”“圆该”不仅是方法,而且也是方法论,更是思维方法和理论方法,因而对创作鉴赏批评和理论构建都具有方法论意义。王先霈从中感悟而提出“圆形批评论”,说明现代文论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的结果。
三、“见异”:文学批评方法论
刘勰在《通变》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夫论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胡大雷认为:“这里指出了创作的两大目标,即追求‘有常之体’与‘通变无方’,这里也指出了批评的两大任务,一是对‘有常之体’的考察,‘必资于故实’的‘名理相因’的‘有常之体’,批评时通过‘宗经’与对照文体规范即可解决问题;二是对‘变文’的‘无方之数’的考察,这是‘异’,如‘文辞气力’之类,每个作家、每篇作品都是相‘异’之处,这所谓‘异品’一定要通过‘酌于新声’来解决,这就是‘见异’的过程。”[9](P120)
刘勰在《知音》中提出“见异”观:“见异,唯知音耳。”故而,“见异”与“知音”密切相关,相互作用,只有“知音”者才能“见异”,而能“见异”者才能谓之“知音”。所谓“异”是与同相对而言的差异、特异、奇异,一是指两者比较而有所区别和差异;二是指具有不同于其他的个别性、个性、独特性从而形成的特性和特征;三是指区别于常态的非常态、超常态、变态现象,甚至会出现怪异、奇异的变异现象或异端现象。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的正统、正宗一贯有排除异己、排斥异端邪说的“非异”观念,这显然不利于创新发展和追求个性、独特性,因而对标新立异总会存在着众说纷纭的正反分歧和争执。刘勰标榜正统、正宗,这是不言而喻的,从《原道》《征圣》《宗经》《正纬》等篇章中均可见一斑。然而刘勰力倡个性、独创性、独特性也是有目共睹的,这在《辨骚》《通变》《时序》《体性》《神思》诸篇章中显而易见。因此,刘勰在《知音》中提出鉴赏批评必须“见异”的观点,是不足为奇的。严格而论,“见异”并不仅仅是指一种批评方法或思维方式,而且是指批评的价值取向和批评原则,是指批评者的独特视野和独特发现。这显然既联系于作家作品的创作独特性和个性,而且也联系于批评家的批评独特性和特征。从这个角度看,刘勰不仅建立了“见异”理论,而且实践了“见异”批评,他的《文心雕龙》就充分体现了其独特的用心和创意,其理论批评的独特性和个性的“见异”是显而易见的。从批评方法论角度看“见异”,其表现方式和意义体现在三方面:
其一,“见异”的批评方法是源自创作的“异采”而设置的。批评“见异”是因为创作“见独”。文学创作是作家的一种独创性写作活动,作品凝集了作家的个性、个别性、独特性,因而文学才具有其特性和特征,这在《体性》《神思》《物色》等创作理论中早已阐发。在《知音》中,刘勰提出“见异”是缘于“昔屈平有言:文质疏内,众不知余之异采”。屈原之说见于《楚辞·九章·怀沙》,意称其文外表与内涵不注意修饰而表面上会显得朴实无华,但世人则不明白其中蕴藏着与众不同的独特才华。故而刘勰接此言说而论:“见异,唯知音耳。”也就是说针对这种“异采”之文的批评,只有“知音”才能“见异”,而要“知音”就必须使批评具备“见异”的眼光和素质,使批评家与作家的独创性在“见异”上成为“知音”,在“见异”上获得共识和交流沟通。这说明,批评“见异”是因为批评对象的文学作品是创作“见异”的产物,是“异采”纷呈的批评对象,只有通过批评“见异”才能真正有效地发掘作品的内涵和价值。因此,从批评“见异”缘于创作“异采”的角度看,批评只有发现作品的“异采”才能“见异”;批评只有依循作品的“异采”才能“见异”。由此可以说,批评“见异”是对创作“异采”的继续和发展,它实质上是批评家创作“见异”的表现形式,是批评家的创作方法、创作原则、创作价值取向的个性、独创性体现,也是批评的特性和特征的体现。
其二,“见异”是针对谬见、成见、雷同之见的批评时弊而提出的创见主张和方法。针对批评时弊,刘勰提出对“贱同而思古”“文人相轻”“崇己抑人”“信伪迷真”“执一隅之解”的批评。这些现象的弊端会形成批评谬见、成见以及雷同之见的结果,这不仅会造成对文学作品的误读、误解,甚至是歪曲和损害,而且也会造成批评制度、秩序的混乱无序,对批评造成伤害。这些批评存在的谬见、成见、雷同之见的弊端,从思想立场角度而言是不难知其价值取向、思想观念的偏颇的,其思维方式、认知方式的偏颇也是明显的,从而导致在批评态度上的固执性、独断专横性和私心成见。从方法论角度而言,囿于成见的批评方法无疑是一种带有片面性、绝对性、肤浅性的方法,既缺乏整体、全面、综合的辩证视角,又缺乏公正、公平、准确的正确视角,当然就更不用说缺乏“见异”的独特视角了。因而刘勰提出“见异”批评方法,一方面是对谬见、成见的批评和校正;另一方面则是对那种人云亦云、从众趋同的雷同之见的批评和校正。“见异”批评不仅提出了要求公平、公正、准确的批评原则,而且也提出了要求创新、有个性和独创性的批评原则。
其三,“见异”是依循辩证法的批评方法。刘勰针对自己的批评实践在《序志》中指出:“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由此可见,刘勰对同与异的看法也力求辩证折衷,合情合理,并不是一味地绝对反对“同”而追求“异”。他认为在评论作家作品中会与过去的评论有同的一面,但绝非雷同,而是情理、事理、物理之“势”必然会在交流沟通中认同;而会与过去的评论有差异的一面,也绝非刻意标新之异,而是循其道理规律则无法赞同旧说。因而,无论同或异,不能以古今之说而论,而应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才能得出不偏不倚的正确结论。由此可见,批评“见异”也是具有辩证法因素和意义的。其实,辩证法思想贯穿于刘勰批评理论体系,使之呈现出艺术辩证法色彩。同时,“见异”方法在其文体观、文学史观中通过辩证法也得到充分体现。例如,《通变》中提出“通”与“变”、“因”与“革”的辩证关系,无论是就“变”与“革”也好,还是就“通变”“因革”也好,都能充分体现“见异”的精神,体现出创新、发展、变化的精神。
其四,“见异”是一种独辟蹊径的方法。刘勰的“见异”不仅是在众说纷纭中鹤立鸡群、不流于俗的独见;而且是在颇有争议,甚至为正统、正宗、主流所排斥的“异端”的辩护中的自持独见。他一方面要从“执正驭奇”的立场出发,对“异体”“变体”及其“异端”提出批评,并要求一种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正体”;另一方面,他又从辩证折衷的方法论角度,对“异体”“变体”及其“异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一分为二的辩证考量,对它们积极可取的一面进行充分肯定,从而体现出他力排众议、独辟蹊径的“见异”之独见。如在《辨骚》中他针对屈原《离骚》的各种颇有争议的不同意见,提出“将核其论,必征言焉”的征验、核实、考证的主张,从事实出发,从作品实际出发,从“变乎骚”的立意和基本思路出发,肯定其优点和特点,批评其不足和缺陷,在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思想和方法论引导下,对屈原及其《离骚》做出公正、公平、准确的评价。其宗旨并不仅仅是平衡和折衷对屈原的宗经还是离经的不同争议,而且更是超越两种截然对立、矛盾的观点所做出的极富创造性的独见:“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锱毫。”这样的评价无疑是对屈原及其《离骚》的充分肯定,甚至奠定了中国文学的“风骚”传统和《离骚》在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刘勰对屈原及其《离骚》的独见,无疑一方面来自他的综合、整体、全面的批评方法;另一方面来自他的“见异”方法,即对“变乎骚”的“变异”的强调。冯春田认为:“刘勰辨析屈赋等,即在于剖析一个‘文变’的典型。这个典型是由‘取经意’和‘自铸伟辞’而成为影响几代辞人的‘艳逸’之文:‘取’便有‘宗经’,即继承(经典)的一面,‘自铸’便有新变的一面,并且是在‘取’这一基础上的新变。”[10](P145)因此,自刘勰之后,对屈原及其《离骚》的争议以及各种偏见才由此平息,同时也才由此开辟了富有“见异”色彩的批评独见的新天地。
由此可见,“见异”不只是批评方法,而且也是批评目的;不仅是批评视角,而且也是批评原则。没有“见异”就没有独创性和个性。正因为刘勰有“见异”的思想和方法,才会有其理论的创新、批评的创新、理论批评的“见异”,也才会有其文学的创新和文学的发展。
小结
综上所述,刘勰的“研术”通过“原道”“圆照”“见异”及“三准”“六观”“六义”“四法”构成了一个完整、系统、整体的方法论体系,包括其创作、欣赏、批评的总体方法和具体方法,也包括由道、法、术所构成的宏观与微观的不同层面的方法,更包括由方法而涉及的思想、立场、态度、价值取向以及评价原则、评价标准的完整的评价体系。因而“总术”的立意是通过“研术”对方法论进行讨论,将思维方式、创作方法、艺术技巧技法统一为一体,从而达到对文学规律把握和运用的目的。“总术”从方法论角度说,一方面是对“文心”的“心术”做进一步阐发;另一方面也是对“雕龙”的“文术”做进一步表达。正如吴林伯指出的:“那么‘总术’即篇中的‘执术’,主张作者‘联辞结采’,一定要掌握‘文术’,决不允许‘弃术任心’。彦和非常重视文学语言的艺术美,他看到‘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以‘雕龙’名书,认定作者作文要像工匠雕刻龙的纹采似的。’”[11](P526)这不仅要看到“总术”对“雕龙”的意义,而且也应该进而推至其对“文心”的意义,如此才能深入理解通过“研术”而获得的“原道”“圆照”“见异”的方法论意义。
[1] 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5.
[2] 王运熙.文心雕龙探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4] 张少康.文心雕龙新探[M].济南:齐鲁书社,1987.
[5] 庄子·养生主[M].诸子集成·三[Z].上海:上海书店,1986.
[6] 易中天.《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7] 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8] 韩湖初.《文心雕龙美学思想体系初探[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3.
[9] 胡大雷.《文心雕龙》批评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0] 冯春田.文心雕龙阐释[M].济南:齐鲁出社,2000.
[11] 吴林伯.《文心雕龙》疏义[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斐 然)
SignificanceofOntologyandMethodologyofLiuXie’s“YanShu”Theory
ZHANG Liqu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LiuXie’sTheLiteraryMindandCarvingofDragon.GeneralTechniqueproposes “Yan Shu” theory, and constructs his methodology system based on literary ontology of “Yuan Dao”, literary appreciation of “Yuan Zhao” and literary criticism of “Jian Yi”. The combination of macro and micro methods of “Dao, Fa, Shu” displays their historical and dialectical methodology. The methodology system of “LiteraryMind” and “CarvingofDragon” is constructed from the multi-perspective of modes of thinking, creative methods, artistic skills and appreciative criticism.
Yan Shu, Yuan Dao, Yuan Zhao, Jian Yi, methodology system
I206.2
A
1004-8634(2017)05-0099-(09)
10.13852/J.CNKI.JSHNU.2017.05.012
2017-03-09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东亚《诗品》《文心雕龙》文献研究集成”(14ZDB068)的阶段性成果
张利群,湖北罗田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与批评、古代文论等研究。
——“原道”传统与刘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