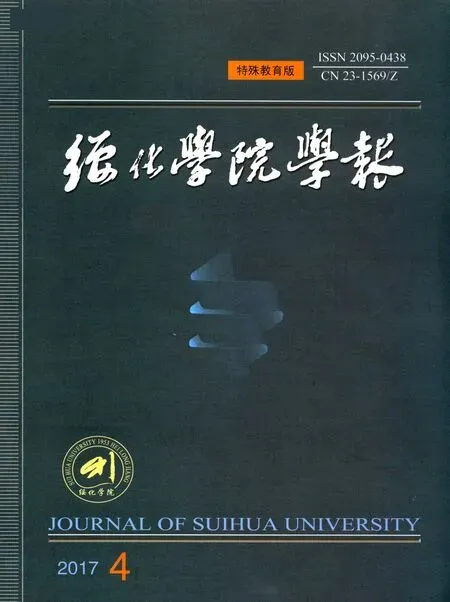中国手语隐喻概念投射路径与翻译处理
傅敏
(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 浙江杭州 310023)
中国手语隐喻概念投射路径与翻译处理
傅敏
(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 浙江杭州 310023)
隐喻是人类思维的一种认知和概念方式。中国手语在词汇层面的隐喻概念投射路径主要有本体型概念隐喻、方位型概念隐喻和通感型概念隐喻。隐喻也是手语扩展词义的重要方式之一。隐喻认知机制在揭示手语翻译思维及把握翻译的实质上能显示其独特的认知功能。手语翻译,不仅仅是语码的转换,也是手语译员积极的思维认知活动。对于一些疑难或新生词汇的翻译处理,可以采取隐喻手段,运用对等策略和转化策略进行翻译。
手语;隐喻;认知;翻译
一、引言
隐喻是人类思维的一种认知和概念方式。Lakoff认为,隐喻是以一个独立的域来概念化另一个域,即域之间的一种映现(mapping)[1]。隐喻也是一种语言使用现象,每一种语言都由隐喻手段构成了大量的委婉语、隐语、谚语等。因此,隐喻是人们认识世界的重要工具,具有提供看待事物的新视角和创造新的意义两大认知作用。人们通过隐喻来创造新概念和新词,建立新理论,认识新事物。聋人同样用隐喻手段创造了大量的手语词汇。翻译也是人类的一种认知行为,不论是在词源学还是在翻译技巧或翻译理论的层面,隐喻与翻译都有着不解的渊源[2]。认知语言学的隐喻理论为翻译的探讨也带来了全方位的变化。本研究将考察隐喻在中国手语中的体现和应用,并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揭示中国手语的隐喻认知心理机制和隐喻概念主要的投射路径。同时探讨手语翻译中的隐喻系统,以及如何拓展隐喻翻译空间,根据实际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为创造性隐喻翻译提供多样化的认知路径。
二、手语中隐喻的语言学功能
相对于外部世界的纷繁复杂和人们内心世界的丰富多彩,无论何种语言的词汇都是极其贫乏的。隐喻是人们对抽象范畴进行概念化的认知工具,是连接已知和未知的桥梁,主要功能是语言意义的产出、传送和创造。因此,隐喻可以丰富词汇,扩展词义,保持语言系统的活力,增强语言的表现力。同样,手语中的隐喻也极大地丰富了手语词汇,并能够言简意赅地表达复杂思想和抽象概念。
(一)填补手语词汇空缺。《中国手语》全书共计词目5586个[3],相对于浩瀚的汉语词汇,仍显得十分匮乏。聋人自然手语现有的词汇中没有合适的词来表达某些概念,尤其是抽象概念,因此存在着严重的“语言贫困”现象。聋人往往通过借用现成的词语来表达,这就形成了手语中大量的隐喻性词汇。在创造新词和各种术语的过程中,聋人通常使用隐喻,用熟悉的事物来表达新的事物,寻找彼此间的相似性,形象化地反映新事物的本质和特征。例如,“坎坷”:双手平伸,掌心向下,交替上下移动,表示路不平。这样,聋人使用隐喻化的语言表达手段,用易于理解的形式将抽象概念表达出来,还能将某些复杂的无法言明的事物特性表达出来。
(二)增加手语表达的形象性和精确性。隐喻能增强手语的生动性和形象性,对于一些抽象概念,尤其是人的内心情感状态,用隐喻化的方法可以将抽象的情感直观形象地表达出来。例如,“怀疑”:一手伸拇指、食指在胸口处轮流弯曲拇指与小指。这是用“在心里考虑好不好”来隐喻这一情感状态。有时,手语中已有的一些词汇用来表达某些现象或概念时缺乏精确性,聋人也往往用隐喻构词方式来弥补这种缺憾。例如,“寂寞”:一手拇指、食指捏住鼻子,表示不通气,心情很闷,以此来隐喻“寂寞”的心理感受。聋人借用了某一更为熟悉或直接的经验领域里的感觉来更精确的表达另一种经验领域里的感觉。
三、中国手语词汇的隐喻概念主要投射路径
(一)本体型概念隐喻。本体型概念隐喻是将抽象的概念用具体有形的实体来理解。根据目标域的概念特征,我们发现,手语中的本体型概念隐喻大部分是实体隐喻。
实体隐喻是指抽象概念的表达通过可以感知的实体来喻指。实体隐喻广泛存在于各种语言中,很多具体词在隐喻用法中都可能产生新的抽象意义。容器隐喻是实体隐喻最典型的代表。每个人本身就是一个容器,人体的头脑和心脏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容器,思想、情感等可以放进去也可以跑出去。在中国手语中,通过头和心构建的隐喻词汇不胜枚举。比如:“幻想”:双手伸拇、小指,从两侧太阳穴交替向上移动。这是以人在脑子里做梦比喻幻想。又如“舒服”:一手五指张开,贴于胸部,顺时针转一圈。这是以心的轻松惬意来比喻舒畅的感觉。再如:“揪心”:一手五指张开,指尖朝内,置于心脏部,然后握拳。这是以心的收紧来比喻揪心的感觉。
(二)方位型概念隐喻。
1.空间隐喻。空间隐喻是运用如上下、前后、内外、远近等空间方位概念来理解另一概念体系。以具体的方位概念来隐喻一些抽象概念是人类思维的共性。由于空间领域受到非语言认知的强有力支持,加之空间本身就是手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此,手语较之有声语言更具备空间隐喻的条件。聋人往往用空间域的意象图式结构映射到非空间域上,以此来表达情绪、状态、社会地位等抽象概念。蓝纯(1999)通过汉语语料库分析空间概念“上、下”的隐喻义拓展路径和方向,发现“上”常喻指好的事物,“下”常喻指不好的事物,主要用于构建状态、社会等级、时间等目标域[4]。手语中的空间隐喻也主要体现在“上”和“下”两个方位所表达的隐喻意义上。比如“优秀”:大拇指在胸前向上高举;“坏”:小指向下甩动。“进步”:右手从左手手腕顺着手臂向上方的肩部移动;“退步”:右手从左手的肩部顺着手臂向下方的手腕部位移动。手语在表达积极情绪时,手势运动方向为上,消极情绪手势运动方向为下。如“畅快”:双手伸拇食指边转边向上运动,表示心情如行云流水般舒畅。“失望”:一手五指张开置于胸前,边向下移动边撮合五指。另外,手语在表达事物的理想状态时,手势运动为上,不理想状态时,手势运动为下。如“胜利”:双手拇食指捏合,然后同时弹开向上移动;“失败”:一手先伸拇食指,然后改为拇指向下栽倒在另一手掌心。这是用空间上的高度来暗示自己的心理感受。
2.时间隐喻。时间作为人类生活的基本因素,从本质上讲是隐喻性的,因为抽象的时间观念往往要通过空间概念来说明。从语言学上看,借助空间隐喻来建构一个时间系统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时间隐喻表征具有跨文化普遍性,无论哪种语言,时间词大多都源于视觉性的空间概念词素,手语也不例外。在人类语言里, 时间沿着线形从过去向未来运动,各种语言中较多地运用“前——后”的轴向来表达时间的线行,如“一月前”“十年后”等。但汉语中“上——下”纵向时间表达丰富且成系统,谈论事件、星期、月、学期等的顺序均用竖轴时间隐喻,过去的时间在“高处”,未来的时间在“低处”。如“上半年、下半年;上旬、下旬”等。徐丹认为,汉人观察世界、感受世界与许多语言不同,用“上——下”表达时间流逝的方法也许与太阳的升落有关[5]。聋人受汉民族文化的影响,手语中较多地用“过去在上,未来在下”的隐喻来表达时间。比如:聋人在表达“上午、下午”就用空间的高度来隐喻其时间差。“上午”:一手伸食指、中指在右侧下颚边往上点动几下;“下午”:一手伸食指、中指在左侧下颚边往下点动几下。聋人在表达以前、昨天等时间概念时手势也都指向后面的高处,表达“以后、未来”的手势都指向低处。人们的语言习惯和感觉运动经验直接影响着时间隐喻图式的建构。尽管聋人在阅读方向和书面语的书写方向上与健听人一样从左到右,但由于听觉缺陷,聋人获得空间经验的主要途径是手语和视觉经验,加之手语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因此,聋人较少用左右方向的隐喻来表达时间[6]。另外,聋人的视觉经验也导致他们难以形成过去在前,未来在后的时间隐喻表达。
(三)通感型概念隐喻。通感型概念隐喻是指某一感觉中枢产生的感觉概念去隐喻另一感觉中枢产生的感觉。因为对某一感官的刺激也会引起其他的感官产生反应,因此,以通感隐喻扩展词义是语言的普遍规律。手语中聋人也会借助表达某一感觉的词汇来表达另一感官产生的感觉。比如“生气”:五指撮合放于胸口,然后向上放开,同时脸上露出生气的表情。这是以“火在燃烧”的感觉来隐喻生气的感受。“冤枉”:双手拇食指张开成大圆形,指尖相对,由侧上方扣向头顶,表示扣帽子。这是以被别人乱扣帽子的感觉来隐喻冤枉的心理。
四、认知语言学视角下手语翻译的创造性
认知语言学为重新认识语言和翻译的创造性提供了可能。Lakoff&Johnson提出:“思维大部分是无意识性的”“抽象概念大体上是隐喻性的”[7]。Dirven&Verspoor指出:语言是认知系统的一部分,其中的一般认知能力受到语言的影响[8]。不管从事何种语言活动,人们都会利用已有的认知资源,调整信息组合,触发认知建构活动,进行创造性的映射和转换。隐喻集中体现了创造性思维所涉及的想象力。隐喻与翻译紧密联系,同其他翻译一样,手语翻译的一个定义性特征是换位情境,翻译不是意义从一种语码到另一种语码的传递过程,而是需要在新的语境中重新概念化的过程。手语翻译的创造过程是调动各种认知资源创造新的意义的认知建构和重构过程。
(一)手语翻译中的隐喻系统。Lakoff认为,概念隐喻在一个文化中具有系统性[9]。隐喻作为发生在概念层面的跨域映射,并非孤立存在,它们彼此呼应,共同构建起一个呈层级形态分布的隐喻概念网络系统。首先,同一个概念隐喻与其衍生出的具体语言隐喻间具有内部的系统连贯性,亦即一个概念隐喻内部存在一个连贯的系统。如“灵机”“智慧”等,这些手语的隐喻表达均为概念隐喻“聪明”(思维是发散的)在语言层面上的扩展。隐喻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两个认知域是凭借经验基础才得以维系,脱离了经验基础,隐喻就无法进行表征。因此,隐喻作为人类一种基本的认知手段同样植根于涉身体验。比如,“厌恶”“恶心”“令人作呕”,均可以打“呕吐”的手势,即一手掌心向上,置于嘴边,模仿接住呕吐物状,同时面露痛苦表情。这几个隐喻图式的共性是,它们的源域“呕吐”,相对于情感来说是低级的生理意识,是以想象中的身体体验为基础的,而目标域则是作为高级意识状态的情感。因此,它们构成了情感隐喻的另一个映射系统,即内部体验映射系统。
(二)手语翻译过程中疑难和新生词汇的隐喻翻译策略。美国的语言学家提出手语是一种真正的语言,既可表达具体概念,也可表达抽象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聋人参与社会生活的程度加深,这就需要挖掘手语的表达潜力,不断丰富和充实手语的词汇。而隐喻就可大大提高手语表达抽象概念、新生词汇的表现力。构成人类认知基础的隐喻图式不仅仅是身体赋予的,也是文化世界中身体经验的产物。各种概念隐喻的构筑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文化知识[10]。语言翻译时,会使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化相互影响和融合。Casagrande 认为,翻译语言事实上是在翻译文化[11],翻译的难点在于文化的差异。因此,在翻译一些新生词汇和专业性很强的词语时,翻译员要根据聋人文化特点和聋人的需求及文化水平差异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
1.对等策略。西方语言学翻译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奈达提出了“动态对等”的翻译标准。他认为翻译要用最贴切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信息[12]。手语翻译的对等策略就是指在手语与汉语隐喻中源域向目标域对等映射的策略。由于聋人和听人的认知理解存在较大的相似性,因此,一些手语词汇可以通过隐喻概念对等映射方式来进行隐喻翻译。有些书面语词汇,聋人平时的日常交流中极少用到,《中国手语》中也没有收录。在课堂教学翻译时,这样的词汇可以依据汉语的意思,结合聋人手语形象化的特征来表达。比如:“瓶颈”的意思是比喻易生阻碍的部分,就像瓶子的颈部一样是一个关口。因此,“瓶颈”手语可以这样打:食指与拇指捏成半圆,并置于颈部。这是用人体的颈部来隐喻事情的关口,这种翻译处理,聋人较易领悟该词汇的内涵。还有些新生词汇,比如“房奴”, 一个闪现着智慧光芒,也透着辛酸的新词汇2006年开始在坊间流传。“房奴”意思为房屋的奴隶。翻译时可以这样打:一手搭成房子屋顶的形状,置于另一手Y手势上面。 这是以房子压在人身上来隐喻房奴让人感到奴役般的压抑。成语“不翼而飞”翻译时可这样打:双手掌心相对,同时伸出拇指、食指和小指,然后向前上方转半圈。这是用了双手“鬼”+“飞”的手势,来隐喻物品像鬼一样不见了[13]。由此可见,手语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认知活动。
2.转化策略。由于不同语言的思维和认知差异以及文化差异,有些词汇不能用对等策略的隐喻表达,就可以运用转化策略,改变源域中的隐喻形象,从而达到意义对等。现代中国首屈一指的语言学家赵元任认为,人类语言所表达的事物和语言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关系,完全是任意的[14]。手语翻译时,手语和汉语文字不一定要一一对应,尤其是一些新生词汇或者成语都可以根据聋人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和符合视觉特征的语言表达习惯来翻译,这是合乎现代语言学的理论的。比如:成语“格格不入”,打法是:双手横伸,掌心向内,五指张开对立,交替上下移动”。这是用双手五指的不搭调来隐喻事物的彼此不协调,不相容。再如:“微博”,聋人的打法是:一手拇食指捏合,置于眼睛的上下框处,其余三指向上微屈,这是以新浪微博的图标“一只大眼睛”来表示“微博”这个新生事物。再如:“孤苦伶仃”,聋人的打法是:一手食指置于胸前,然后向外移动,最后左手伸拇食指,右手五指抓住左手拇指在胸前转一圈,表示自己一个人独自游走[13]。这是以具体形象的动作来隐喻孤苦伶仃的抽象感觉。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手语隐喻翻译要考虑聋人文化因素,保持聋人文化色彩才能使聋人有更高的认同度和接受度。
五、结语
隐喻作为一种认知方式极大地丰富了手语词汇。聋人利用隐喻手段来表达很多抽象概念,是语义扩展取之不尽的源泉。手语翻译,不仅仅是语码的转换,也是手语译员积极的思维认知活动。作为一种思维机制,隐喻虽然具有普遍性,但是汉语和手语在隐喻认知心理机制和概念投射的取向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翻译本身隐藏着语言符号深沉机制的沉淀,其过程需要采取一定的隐喻角度。隐喻认知机制在研究探索手语翻译思维方面有积极的作用。在国内,对于隐喻认知本身的研究尚需进一步深入,而隐喻在应用语言学领域实质性的阐释研究尤其缺乏。隐喻认知机制在把握手语翻译的实质及揭示手语翻译思维上定能显示其独特的认知功能。这需要研究者深入探索手语隐喻机制,进一步细致考察手语翻译特性,从而积极地推动手语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的不断发展完善。
[1]Lakoff,G.Women,Fireand Dangerous Things[M].Chicago: 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7:34.
[2]谭业升,葛锦荣.隐喻翻译的认知限定条件:兼论翻译的认知空间[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3):59-63.
[3]中国聋人协会.中国手语(修订本)[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4.
[4]蓝纯.从认知角度看汉语的空间隐喻[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9(4):7-15.
[5]徐丹.从认知角度看汉语的两对空间词[J].中国语文,2008(6):504-509.
[6]王文斌.英语词汇语义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01.
[7]Lakoff,G.&M.Johnson.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M].New York:BasicBooks.1999:148.
[8]Dirven,Rene&Verspoor,Marjolijn.(esd.)[M].Cognitive Exploration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Amsterdam:John Benjamins.1998:1.
[9]Lakoff,G.&M.Johnson.MetaphorsWe Liveby[M].Chicago UniversityPress.2003:1-6.
[10]谭业升.认知翻译学探索:创造性翻译的认知路径与认知制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131.
[11]Casagrande,JosephB.Theendsoftranslation[J].InternationalJournalofAmericanLinguistics,1954(20):335-340.
[12]NIDA E A.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on[M].Shang hai:ShanghaiForeign LanguageEducationPress,1993:2.
[13]吴玲.中国聋人手语500例[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15:72,191.
[14]钱歌川.翻译的基本知识[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3:6.
[责任编辑 刘金荣]
G762
A
2095-0438(2017)04-0028-04
2017-02-26
傅敏(1977-),女,浙江金华人,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手语语言学、手语翻译教学。
2015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5NDJC295YB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