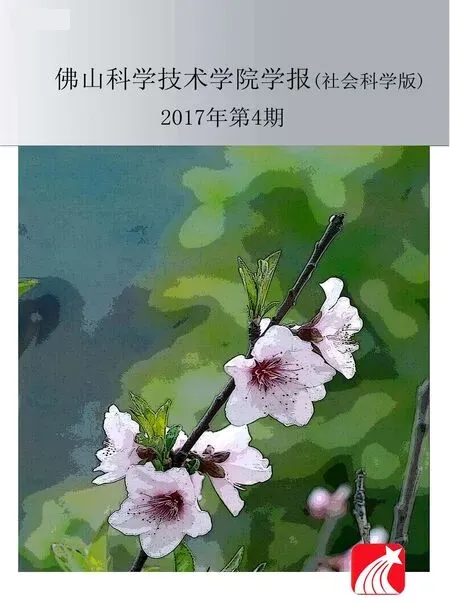自然还是修养:康有为人性论新解
张 恒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济南250100)
自然还是修养:康有为人性论新解
张 恒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济南250100)
人性论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问题。身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康有为,借助先秦诸子、宋明理学以及佛学、近代西学的思想资源,对明中叶以降的气质人性论思潮展开批评和改造,明确提出了以“天欲人理”为表征的人性学说。就“天欲”来说,生之谓性、气质一元、性无善恶、人性平等;就“人理”来说,人需要勉强学问、变化气质,以至积善为圣。康有为从天欲出发,最终是要抵达人理。由此他的人性论既不同于传统儒家德性论,也不能简单定义为自然人性论,他主张的实际是一种修养论,这种修养论极具现代性意义。
康有为;人性论;气质;修养;天欲人理;现代性
19世纪后期,身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开始了从器物变革向制度变革的探索,作为这一探索的领导人物,康有为的主张和行动已毋庸赘言。需要指出的是,康有为著名的政治实践背后,有其独特的哲学和伦理思想作支撑,而其哲学与伦理思想的核心便是人性论。
总的来说,康有为的人性学说承接了明中叶以后的气质人性论传统,不同的是,康有为又调和并借鉴吸收了告子、孟子、荀子、董仲舒、宋明理学家乃至佛学、近代西学的相关概念、观念。如果说明清之际的气质人性论仍纠结于如何调整、修正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康有为则颠覆性地喊出了“天欲而人理”的主张。
即天言欲(天欲)和即人言理(人理)基本反映了康有为人性论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天欲”主要是对人性本质的言说,他主张人的欲望是天赋之性,天赋之性无善无恶、人人平等;而“人理”则是对人性养成的工夫之言说,他主张理(善)是道德实践的结果,人应该通过勉强学问实现气质的变化,进而积善成圣。由此,康有为既肯定欲望,又主张修养。从这个意义上说,近几十年来关于康有为的研究中视其人性论为单纯“自然人性论”的观点略嫌简单化,他从欲望出发,最终走向的是修养。
一、“欲者天也”:本质论
康有为的人性学说,就其本质来说,涵盖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两个方面。事实判断方面,康有为较为认可告子、董仲舒一系“生之谓性”的观点,即视人性为天赋,且“全是气质”;价值判断方面,康有为从事实判断出发,提出了“性无善恶”“人性平等”等主张。由此,康有为基本完成了其对人性本质的理论建构。
(一)生之谓性
在《长兴学记》开篇,康有为说:“夫性者,受天命之自然,至顺者也。不独人有之,禽兽有之,草木亦有之,附子性热,大黄性凉是也。若名之曰人,性必不远,故孔子曰:性相近也。”[1]341在这里,康有为提出了“性”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他认为,世间万物皆有其“性”,“性”是“天命”在万物身上自自然然的流行;不同类别的事物所禀受之“性”不同,同一类别的事物所禀受之“性”相近,比如同样是人,人性的差别不会太大。
紧接着,康有为回溯两千年前的人性论争,进一步阐明他对人性内涵的看法。康有为说:“孟子性善之说,有为而言。荀子性恶之说,有激而发。告子生之谓性,自是确论,与孔子说合,但发之未透。使告子书存,当有可观。王充、荀悦、韩愈即发挥其说。”[1]341在其他地方,康有为还曾说:“凡论性之说,皆告子是而孟非,可以孔子为折中。告子之说为孔门相传之说,天生人为性。”[2]186“董子言生之谓性,是铁板注脚。”[2]184
可见,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早期的人性论争,康有为相对认可告子、董仲舒一系“生之谓性”“天生人为性”的观点,即主张人性是人与生俱来的天赋。
需要注意的是,“生之谓性”其实是先秦时期普遍的论性原则。“生之谓性”本身是对“性”的事实判断,意在阐明“性”的来源问题——性是天赋;孟子“性善之说”与荀子“性恶之说”实际上是事实判断之后的价值判断,即意在阐明“性怎么样”的问题——性是善的还是恶的,而其背后隐含的事实判断仍然是“生之谓性”,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就性是天赋这一点上,思孟与荀子并无差别……”[3]同理,就性是天赋这一点上,孟荀与告子也无差别,差别在于天赋的内容及其价值判断。
由此,康有为从批评孟荀人性论的角度来论“生之谓性”,其实隐含着两层意思:其一,他主张性是天赋;其二,天赋之性不含善恶之价值判断。对于第二层意思,后文将予以详述。
(二)气质一元
康有为关于人性的事实判断的另一部分是“性的内容”。在这一点上,康有为否定了自张载开始、为程朱学派所普遍认可的“分性为二”的做法,他说:“程子、张子、朱子分性为二,有气质,有义理,研辨较精。仍分为二者,盖附会孟子。”[1]341
“气质”一词源出张载,他认为性分“气质之性”和“天地之性”:“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固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人之刚柔、缓急、有才与不才,气之偏也。天本参合不偏,养其气,反之本而不偏,尽性而天矣。”[4]15这就是说,气质之性以“形”(气之聚)为载体,气有偏,因此气质之性也有优劣,然而天地之性不会偏,其较气质之性更为根本。嗣后程朱学派以理言性,对于张载的二分之性作了进一步诠释:“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5]2688天地之性是纯之又纯的天理,气质之性则理气驳杂,经常被人欲所遮蔽,因此程朱学派主张“存天理灭人欲”。陆王学派虽以心言性言理,主张“心即理也”[6]16“气即是性”[6]168,认为心、性、理、气是一回事,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欲观与程朱学派是一脉相承的。
明清之际的学者鉴于心学之弊,淡化了“心”“理”等超越性概念,专就“气”上言性,如公认的最早发生转向的学者罗钦顺就曾提出:“盖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千条万绪,纷纭胶葛,而卒不可乱,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7]4在宋明理学那里至高无上的“理”不再具有超越性和主宰性,而成了依附于气的存在。
康有为承接明清之际的“气本论”传统,他说:“实则性全是气质,所谓义理,自气质出,不得强分也。”[1]341又说:“凡物皆始于气,既有气,然后有理。生人生物者,气也。所以能生人生物者,理也。人日在气中而不知,犹鱼日在水中而不知也。朱子以为理在气之前,其说非。”[2]133这就比较明确地主张了“气质”作为人性本体的一元论。至于气质的具体内涵,康有为说:“人之生也,惟有爱恶而已。”[1]100又说:“人之始生,便具爱恶二质。”[1]148气质之性就是爱恶二质,也就是人人生而就有的各种本能欲望。
气先理后、以欲为性的主张使康有为进一步做出了如下纲领性的表达:“夫有人形而后有智,有智而后有理。理者,人之所立。贾谊谓立君臣、尊上下,此非天之所为,乃人之所设。故理者,人理也。若耳目百体,血气心知,天所先与。婴儿无知,已有欲焉,无与人事也。故欲者,天也。程子谓‘天理是体认出’,此不知道之言也,盖天欲而人理也。”[1]111在此,康有为将王夫之等人暧昧的意思彻底言清,即“欲者天也”“理者人立”,“天欲而人理”精炼地概括了其基本的人性主张。
(三)性无善恶
上文已说明康有为人性论的事实判断部分——性是天赋且全是气质。对于价值判断部分,康有为又是如何论述的呢?
回顾中西哲学史,对于人性的价值判断首先是人性的善恶问题。关于人性善恶的观点主要有性善论、性恶论、性非善非恶论、性既善既恶论、性善恶相混论等五种,“从逻辑上来说,人性的善恶问题也可能有这五种观点,再找不出别的观点了”[8]73。这些观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相互论争、各领风骚。按照这一分类方法,康有为的人性论主要倾向于性非善非恶论。
首先,康有为认为性、善异质。
康有为说:“‘性’字,‘善’字,要分开讲。”[2]203又说:“‘性是天生,善是人为’……。其善伪也,伪字从人,为声,非诈伪之伪,谓善是人为之也。”[2]184
在这里,康有为借鉴荀子的说法,对“性”和“善”作了区分,他认为性与善存在着异质性。其中,性是天赋,是与生俱来的,具有先天性,实际上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天欲”;善则与人类后天的道德实践有关,是人依据外在的道德准则所作出的调整或改变,它并不具有先天性,也就是上文所说的“人理”。
其次,康有为认为性无善恶。
在区分“性”“善”的基础上,康有为顺理成章地提出,“性”中并不天然地包含善恶之价值判断。他说:“性者,生之质也,未有善恶。”[2]166又说:“性只有质,无善恶。”[2]188亦曾直接说:“性无善恶……”[2]186
为了证明这一点,康有为引用了《中庸》关于“性”的经典诠释作为证据,即《中庸》首章所提出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三句话。康有为认为,子思在其中蕴含了“人性非善”的潜台词:“若子思既有性善之说,则必无‘修道之谓教’语……”[2]169也就是说,如若性善,何需教化?既然子思提出“修道之谓教”,提出需要教化,那就说明在子思看来人性至少不是“善”的,至于是不是恶的又当别论——实际上,按照康有为的逻辑也不可能是恶的,如若性恶,教化又有何用?据此,康有为认为“此性字乃是人之质也,方为确诂”[2]169。
除了儒家的解释进路,康有为还用佛家思想解释了《中庸》首章上述论性之语。康有为提出:“‘天命之谓性’,洁净法身也。‘率性之谓道’,圆满报身也。‘修道之谓教’,百千万亿化身也。”[2]169在佛教中,法身是一切事物的法性之体,洁净法身没有烦恼垢染,如同涅槃,康有为用洁净法身作比天赋之性,实际上也是在强调人性的不着善恶,自自然然。
(四)人性平等
康有为人性论中价值判断的另一维度与人性等级有关。
康有为说:“孔子曰:性相近也。夫相近,则平等之谓,故有性无学,人人相等,同是食味、别声、被色,无所谓小人,无所谓大人也。有性无学,则人与禽兽相等,同是视听运动,无人禽之别也。”[1]341
此处,康有为将孔子“人性相近”的表述转换为“人性平等”,即如果单就人性作为天赋、气质的角度来说,其表现无非是食味、别声、被色等视听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人人相等,就是人禽之间也没有差别。人与禽、人与人的差别在于后天的学习以及智慧的获得,用康有为的话说,“人禽之异,智也”[2]188。
“人人相等”甚至“人禽相等”的人性学说在当时遭到了叶德辉、朱一新等人的激烈批评,如叶德辉曾尖锐地指斥康有为释“相近”为“平等”是无父无君,与周、孔为仇敌,在他眼里,康有为简直成了离经叛道、与儒家思想水火不容的“异教徒”。
事实上,中国传统哲学中并非没有“人性平等”的思想资源。如孟子提出,人人皆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四个善端,“圣人与我同类”(《孟子·告子上》),“尧、舜与人同耳”(《孟子·离娄下》);荀子也曾提出,“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但是,孟荀从形上层面对“人性平等”的确认却未能贯彻到形下层面,孟子最终还是区分了“小人”和“大人”,荀子则指向了“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荀子·富国》)的礼制建构。
嗣后自汉至唐,更多的是人性不平等的言说。董仲舒将人性区分为三等:“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春秋繁露·实性》)王充进一步把这三品之性对应于善、恶、善恶相混:“馀固以孟轲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孙卿言人性恶者,中人以下者也。扬雄言人性善恶混者,中人也。”(《论衡·本性》)至韩愈,人性等级论发展为复杂而精致的“性情三品说”,其中性、情均分上中下三品,性三品划分的依据(所以为性者)有仁、礼、信、义、智五个方面,情三品划分的依据(所以为情者)有喜、怒、哀、惧、爱、恶、欲七个方面,各品性、情的差异源于五个、七个方面不同的排列组合。
至宋代,宋儒精致区分了天地之性(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义理之性虽纯粹至善,气质之性却有善有恶。因此,平等在形下层面仍难实现。
康有为承接明清之际的人性论思潮,这一思潮倒转了理学家的言说方式,认为气在理先,理依于气。气质之性的平等首先展示为人欲的平等与合理,而人欲的展开就是日用伦常,由此也确立了日用伦常上的各种平等,这就使得平等的观念从形上贯彻到形下。比如,康有为说:“孔子最重报施,礼无不管,故《记》言‘凡非吊丧,非见国君,无不答拜’者,此平等之义也。”[2]134把待人接物上的一视同仁视为平等,这意味着平等不再是一种抽象的言说,它已经成为一种现实诉求。
二、“理者人立”:工夫论
康有为既拒绝对人性作善恶之道德判断,同时又追求社会运行的秩序,如此他就不得不找到处理现实生活中善恶的办法。他找到的办法就是上文提及的“由人立理”。由此,康有为建构了人性养成的工夫论,即通过勉强学问,实现气质变化,最终使天赋之性走向人为之善乃至圣人之善。
(一)目标:积善为圣
如前文所述,在人性本质问题上,康有为并不认同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他一再强调性、善异质,性无善恶。但是,这并不代表康有为否认善恶的存在,在他看来,善恶只是没有先天地蕴含于人性之中,而是需要人通过后天的道德实践来获得或完成。换言之,善恶并非“性”而是“习”。康有为所说的“其善伪也”“善是人为”以及“入至人界,始有善。不入人界,无善恶”[2]188等表述都是在阐明这层意思。当然,善的标准是后天的、外在的,其制定权在于“圣人”,即康有为所说“性无善恶,善恶,圣人所主也。”[2]186
如此,康有为就在“性”与“善”之间建立起了某种关系,即经过后天的人为努力,天赋之性有可能通向后天之善,对此,可用“性→善”这种方式来表达这一路向。
在此基础上,康有为又提出“圣人之善”这一更高级别的“善”:“孟子下质于禽兽之所为,故曰性已善。吾上质于圣人之所为善,故谓性未善。善过性,圣人过善。”[9]427孟子将人为之善下比于禽兽天赋之性,得出的自然是“人性善”的结论,而康有为将普通人之善上比于圣人之善,得出的结论便是普通人之善仍有欠缺,仍有待提升。如此一来,“性→善”路向可以进一步扩展为“性→善→圣人之善”,即从“性”到“善”再到“圣人之善”是善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过程。
在这里,有一个隐藏的问题凸显出来,即天赋之性如何能够导向后天之善?
有些地方,康有为从“出于性”的角度对此作了解释。他说:“天生民以物则善性,人人可为善也。”[9]426又说:“若夫人之贵于万物,其秉彝之性,独能好懿德。”[9]426上文曾指出,康有为认为气质之性无非就是爱恶二质,而“好懿德”恰恰就是人的自然本性,而且是人别于万物、贵于万物的一个核心标志。“懿德”具体指什么呢?康有为说:“仁义礼智即懿德也。”[9]426而仁义礼智正是孟子“性善论”意义上的善。由此,康有为所说的“人性好懿德”完全可以转换一种说法——人性好善。当然,“好善”并不能等同于“善”,但是“好善”之天性显然是后天之“善”的依据,正因为“好善”所以才会学习并改变。
在另一些地方,康有为又从“出于智”的角度进行分析。如上文所指出,康有为曾说“人禽之异,智也”,亦曾说“有人形而后有智,有智而后有理”“天欲而人理”,人理也就是后天的道德准则,就是善,就是仁。
总的来说,无论是说善出于性,还是说善出于智,康有为的解释都指向了善的人为性和后天性,这与其人性本质论并不矛盾。正如康有为所说:“王阳明、罗念庵,谓‘满街皆是圣人’,以为人性本善,此非也,谓之觉人可也。”[2]204在康有为这里,言善是为了启发、鼓励大众做出符合道德准则的言行举止,从而保证社会运行的秩序。
(二)方法:勉强学问
天赋之性人人相等并不意味着后天善的程度的相等,如何实现善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呢?康有为认为最主要的途径是学习,是“勉强学问”。
其实中国哲学史上重视学习的学者不在少数,孔子以降,最早、最典型的要数荀子,荀子基于“性恶论”倡导学习,这从《荀子》一书以《劝学》为首篇即可见一斑。尽管康有为并不赞同荀子的“性恶论”,但他极为赞同荀子“通过学习由恶至善”的致思路径,他认为由无善无恶之性到后天之善同样需要学习。康有为说:“孟子言性善,扩充不须学问。荀子言性恶,专教人变化气质,勉强学问。论说多勉强学问工夫,天下惟中人多,可知荀学可重。”[2]182
勉强学问是人禽之别、人人之别的根本所在。如康有为说:“孔子曰:性相近也。夫相近,则平等之谓,故有性无学,人人相等,同是食味、别声、被色,无所谓小人,无所谓大人也。有性无学,则人与禽兽相等,同是视听运动,无人禽之别也。”[1]341而学习这件事情只有人才能完成,他说:“学也者,由人为之,勉强至逆者也。不独土石不能,草木不能,禽兽之灵者亦不能也……顺而率性者愚,逆而强学者智,故学者惟人能之,所以戴天履地,而独贵于万物也。”[1]341学习的方式和程度决定了人与人后天的差异,他说:“同是物也,人能学则贵,异于万物矣;同是人也,能学则异于常人矣;同是学人也,博学则胜于陋学矣;同是博学,通于宙合,则胜于一方矣;通于百业,则胜于一隅矣;通天人之故,极阴阳之变,则胜于寻常蹈故拘文牵义者矣。故人所以异于人者,在勉强学问而已。”[1]341
勉强学问学的是“仁”。在康有为看来,善的最高标准就是仁,“圣人至仁……故学者学为仁而已。若不行仁,则不为人,且不得为知爱同类之鸟兽,可不耸哉!”[1]342
勉强学问的过程是“节欲”“节情”的过程。康有为说:“凡言乎学者,逆人情而后起也。人性之自然,食色也,是无待于学也;人情之自然,喜、怒、哀、乐无节也,是不待学也。学所以节食、色、喜、怒、哀、乐也。圣人调停于中,顺人之情,而亦节人之性焉。”[1]102而之所以要“节欲”“节情”,是因为如果不如此会导致欲、情的失调进而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康有为说:“夫勉强学问,务在逆乎常纬。顺人之常,有耳、目、身体,则有声、色、起居之欲,非逆不能制也;顺人之常,有心思识想,则有私利隘近之患,非逆不能扩也。人之常俗,自贵相贱,人之常境,自善相高,造作论说,制成事业……党类立矣……积习深矣。”[1]341可见,康有为的最终指向在于秩序。
勉强学问的具体做法是读书著书与讲学交友相结合。康有为对顾炎武“今日只当著书,不当讲学”的说法提出了极为激烈的批评,认为“国朝读书之博,风俗之坏,亭林为功之首,亦罪之魁也”[1]342。在康有为看来,从孔子到陆九渊都倡讲学,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才能相互砥砺提高,而明清之际只重著书,“猎奇炫博,于人心世道,绝无所关”[1]342。因此,康有为主张追随孔子讲学的传统,关心节气与政事。
反对空谈天理,积极介入现实,这正是康有为“天欲而人理”哲学主张的现实反映。无怪乎钱穆要如此高度评价康有为:“严正地出来提倡一种新的读书风气的人,则此一百年内,不得不首先要轮到康有为。”[10]114
(三)实质:变化气质
要想实现“积善为圣”的目标,仅靠“勉强学问”还不够,还需要进一步“变化气质”。
如前文所述,“气质”源出张载,而讲求“变化气质”的学者主要在程朱学派,比如朱熹认为气质之性理气驳杂、私欲遮蔽,因而需要依据天地之性(义理之性)对其进行调整和改造。他提出的变化气质的方法主要是格物致知,也就是体贴天理、涤荡私欲。
康有为也主张变化气质,他说:“人莫不有杂质,如大黄性凉而兼补。物质尚尔,况人耶!既落气质之中,则不能纯。”[2]248又说:“昔朱子论谢上蔡,陆子静谓:无欲之上,尚隔气质一层。吕东莱少时气质极粗,及读《论语》,至‘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于是痛自变改。故朱子曰:学如伯恭,始得谓之变化气质。”[1]344应当承认,康有为“变化气质”之话语实出于宋儒,出发点也与宋儒极其相似,即都认为气质之性不够纯粹。
不过,二者语境却有根本不同。康有为说:“学既成矣,及其发用,犹有气质之偏,亟当磨砻浸润,底于纯和。”[1]344言外之意,变化气质是在勉强学问基础之上的道德实践。也就是说,康有为仍然坚持“天欲”没有善恶之别,只是一旦进入人界,进入社会关系之中,“天欲”就需要按照人界、社会的道德标准予以节制、调整、改造,这项工作首先应该付诸学习,但是仅靠学习又是不够的,因为学习解决的主要是知识层面(知)的问题,知识还需要进一步转化为自主之行动(行),只有付诸行动,才能真正地变化气质,成善成圣,实现“人理”。
尽管用了宋儒的话语,但康有为并不愿承认这观念来自宋儒,他认为“变化气质”观念的源头在荀子,“宋儒言变化气质,已不能出荀子范围”[2]181,“荀子言性恶,专教人变化气质”。可见,康有为“变化气质”之话语装的是荀子化性起伪的“旧酒”,而不是宋儒的“新酒”,他与宋儒的哲学立论有着根本上的区别。
“变化气质”如何开展呢?康有为提出,《皋陶》之“九德”、《洪范》之“三德”、《大学》正心修身之传、《中庸》“发而皆中节谓之和”都是“变化气质”的好教材。总而言之,康有为认为“变化气质”就是“心戒其有所,身戒其有所”,即不能有所固执,应该接受并内化作为道德标准的人为之善。
三、超越与意义
康有为视人性为气质,认为欲望源自天赋,无善无恶,人人平等。从这个角度说,近几十年来的康有为研究将其人性论视为自然人性论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仅仅看到这些还不够,康有为的人性学说不仅是明清之际“气质人性论”思潮的末流,他还从先秦诸子、宋明儒学乃至佛学、近代西学中汲取了诸多灵感,实现了对“气质人性论”的批评和超越。
(一)批判、调和与超越
首先,就人性本质论层面说,康有为对“理-气”关系问题的论述更加彻底和直接,某种程度上摆脱了明清之际“气质人性论”思潮中普遍存在的欲说还休、暧昧不清的状态。
在明中叶以前,在儒家人性论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德性论,从孟子到宋明理学家多数秉持的是这一传统,尤其是张载及程朱学派将这一传统发挥到了极致,他们将人性一分为二,其中天地之性(义理之性)是纯而又纯的天理,气质之性则理气驳杂、理欲相混,天理无善无恶,人欲则有善有恶,因此天理、人欲不能并立,故朱熹一再力倡“明天理,灭人欲”。
明中叶以后的“气质人性论”开始了对宋明理学的反动,但是在这一思潮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多数学者仍难摆脱“天理-人欲”思维模式的束缚。如罗钦顺说:“一性而两名,且以气质与天命对言,语终未莹。”[7]7王夫之、戴震等人的观点,固然已以气为本,已在确认人欲的合理性,但同时仍然承认天理对于人欲的规定性,重点在于理欲合一。有学者指出,他们“没有从根本上突破传统道德天人合德的价值观……强调的仍然是德性原则”[11]。
康有为与前人不同的地方在于其在人性本质论层面上,彻底抛弃了德性原则,他以一个人的成长史来作论证,说新出生的婴儿无知无识、不懂善恶,但显然是有欲望的,这不是由人所决定的,而是由天所决定的,康有为明确称其为“天欲”,而这是此前的“气质人性论”学者想说但没有说出来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康有为的确是名副其实的自然人性论主张者。
其次,康有为又不仅仅主张自然人性论,他还重视后天之善。不过,康有为所论之善与天无关,而是人类在社会关系中经验形成的道德准则,这体现出康有为人性工夫论方面的超越。
按照康有为的观点,道德准则——如贾谊所主张的“立君臣尊上下”——与天无关,完全是“人之所设”,因此道德准则所蕴含之理也就不是什么天理,而是“人理”。由此,理并不神秘,它是人出生以后在社会生活中、在道德实践中逐渐认识并把握的。
这种将“理”彻底形下化的做法,天然蕴含着让人积极入世的要求。因此,康有为提出,在寻求人理的道路上,也就是实现“性→善→至善”的过程中,不仅要勉强学问,还要变化气质。其中“勉强学问”是为了防止人性为外物所引夺而出现“异化”,“变化气质”则是为了防止人们在“勉强学问”的过程中陷入纯粹知识的海洋不能自拔。前者是对清代考据之学实事求是追求知识的治学态度的肯定,后者则是对其只“追求知识”而不肯“言心言性”的治学态度的一种纠偏,唯有“勉强学问”和“变化气质”并举,才能在后天不断提升“善”的层次。
总而言之,康有为以“天欲人理”为表征的人性学说,从本质论到工夫论,既调和了告子、孟子、荀子、董仲舒,又借鉴了佛学、近代西学的观念,[12]115-116“天欲”与“人理”并行不悖,人的欲望追求和社会的道德准则相互塑造,在时间中发展和变化,这种人性思想蕴含了诸多现代性因素。
(二)现代性意义
2006年,李泽厚在香港《明报月刊》发表《漫说康有为》一文,指出:“作为政治家的康有为,特别是戊戌维新那一段时期,他是非常拙劣的、愚蠢的……但作为思想家的康有为,他却仍应有崇高地位。回顾百年以来,观念原创性之强、之早,思想构造之系统完整,对当时影响之巨大,以及开整个时代风气等各个方面,康都远非严复、梁启超或其他任何人所可比拟……至今具有意义。”[13]393-394李泽厚对康有为的评价是极高的,而康有为的思想至今仍具有的意义,首先体现于其哲学思想尤其是人性论所展现的现代性因素。
当前中国身处其中的“现代化”过程,从哲学角度来说也就是走向“现代性”,而“现代性”最核心的标志即是“个体性”。这是因为,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从根本上说“并不基于宗族或家族那样的集体,甚至也不基于现代核心家庭这样的集体,当然也不基于‘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这样的集体,而是基于个体(individual)”[14],“个体”才是现代社会真正的主体。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至少自阳明心学开始就已经出现了“内生现代性”的萌芽,王阳明将程朱学派所主张的外在于人心的客观之“天理”收摄进入“心”之中——心即理,强调每个人都能感知“天理”,个体性因此成为普遍性的根基。嗣后明清之际,王夫之、戴震等人直接视人欲为性,重新确认了人欲的合理性,个体性问题进一步显化。而康有为则比上述学者都要激进和彻底,他“天欲而人理”命题的提出把人欲上升到了天欲的高度,道德则被“贬抑”到了人间。
这一致思进路,一方面使欲望所带来的个体之差异具有了完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很显然,每个人的欲望是不同的,欲望的不同导致差异,尽管这种差异并不具有价值判断上的区别——进而带来了权利意识,康有为说:“以天之公理言之,人各有自主独立之权,当为平等,不当有奴。”[15]40对此,有学者指出,“权利观念的引入是现代个体观念在中国确立的重要标志……从儒家观念发展史的角度来说,康有为把‘自主之权’理解为‘天之公理’革新了儒学的基本政治观念,使传统的儒学有了现代性色彩”[16]75。
另一方面,“理”的形下化、经验性使康有为对“群己关系”这一老问题做出了新的回应。康有为说:“人非人能为,天所生也。性者,生之质也,禀于天气以为神明,非传于父母以为体魄者……循人人公共禀受之性,则可公共互行。”[9]369而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期间,康有为更加强化了其对于现代社会“群己关系”的理解,并直接使用了更具现代性的语汇——立公民。他说:“公民哉!人人与之同忧,而君可免忧;人人与之同患,而国可免患。公民哉!人人与之同权,而君权益尊;人人与之同利,而君利益大……故明夷子曰:‘今中国变法,宜先立公民哉!’”[15]268强调“公共互行”“先立公民”,这都为现代公民社会的构建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思路。
结语
人性论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中居于主干地位[17]2,深入考察、分析康有为的人性思想有助于把握其哲学、伦理学及政治变革思想的精髓,进而更好地挖掘其现代性意义。
回顾过去几十年的康有为人性论研究,多数将其定义为“自然人性论”,就其人性本质论——性是天赋且全是气质,性无善无恶且人人相等——而言,这种定义有一定道理。然而,就康有为的人性工夫论——勉强学问、变化气质、积善为圣——而言,单纯的“自然人性论”定义又失之偏颇。康有为从“天欲”出发,走向的却是“人理”,他不仅重视欲望,也重视后天的教化。少数研究已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亦有学者将康有为人性论视为自然人性论与道德人性论的统一。本文认为,这样的理解较单纯的自然人性论定义已全面得多,但仍有失准确。
儒家传统人性论主要是德性论,这种“德性”不同于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virtue,前者是具有道德内涵的天性,而后者则需要通过教育、习惯等途径才能获得,实际上是一种修养。[18]康有为从“天欲”走向“人理”的人性学说,更多属于修养论,尤其是其中的道德修养论。
从某种意义上说,康有为式的道德修养论比传统儒家德性论更注重人性在社会中的展开,更注重道德实践的主体,更注重个体性。从中国哲学发展史的角度看,这既是中国内生现代性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能够与外部现代性接榫的根本所在。
[1]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一集[M].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二集[M].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颜炳罡.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与荀子的情性哲学[J].中国哲学史,2009(1).
[4]张载.张子全书[M].林乐昌,编校.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
[5]朱熹.朱子全书:第23册[M].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6]王阳明.传习录[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2.
[7]罗钦顺.困知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0.
[8]邓晓芒.康德哲学讲演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9]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五集[M].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0]钱穆.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M]//学籥.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
[11]张怀承.天欲与人理:近代人性论对传统人性论的批判与改造[J].求索,1998(6).
[12]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M].汪荣祖,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13]李泽厚.漫说康有为[M]//杂著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14]黄玉顺.论儒学的现代性[J].社会科学研究,2016(6).
[15]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七集[M].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6]蒋孝军.“群”与“独”:个体性问题——康有为政治儒学研究[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5.
[17]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18]沈顺福.修养与德性——兼论修养伦理学[J].人文杂志,2009(5).
(责任编辑:梁念琼liangnq123@163.com)
Natural or Cultivated?A New Study on Kang Youwei’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ZHANGHeng
(Advanced Institute ofConfucian Studies,ShandongUniversity,Jinan 250100,China)
The theory of human nature is the cor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With the help of the thought resources that came from Pre-Qin philosophy,Neo-Confucianism,Buddhism and modern western knowledge,Kang Youwei criticized and transformed the temperament theory of human nature which originated from the middle of Ming Dynasty.Kang Youwei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human nature which was characterized by “natural desire and human truth”.In terms of natural desire,human nature is congenital,temperamental,equal and no good or evil.In terms of human truth,people should learn and change their temperament in order to be good,even prime good.As a result,Kang Youwei’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is neither natural nor virtuous,but cultivated.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modern times.
Kang Youwei;theory of human nature;temperament;cultivation;modernity
B258
A
1008-018X(2017)04-0026-08
2017-04-28
张恒(1985-),男,山东邹平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哲学、比较哲学、比较伦理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