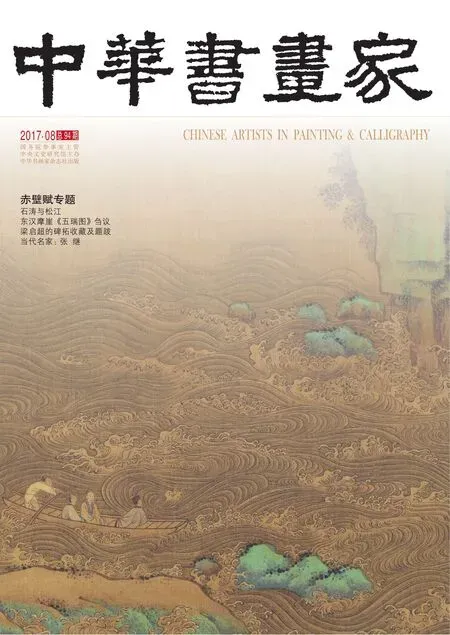石涛与松江
□ 陶喻之
石涛与松江
□ 陶喻之
一、由相传石涛法名“超济”说起
石涛名号众多,相传有“超济”法名。明复《石涛原济禅师行实考》(一)“家世之研究·名号”曰:“他的法名,最初称为‘超济’。依佛门命名的规矩,法名通常是两个字组成的,上一字,表示宗派辈份,下一字由剃度恩师视其因缘际遇而选定之。多半寓以励勉告诫之意,也有用为祝福祈禧之辞的。石大师名字中的‘超’字,是根据临济宗龙池传祖演派诀:‘方广正圆通,行超明实际’一联而来的。这个字代表的是第三十六代。‘济’字乃是专用的,所以,一般人称之为济禅师。他自己署名,也常单书一个济字。……至于‘石涛超济’应如何解,典出何书,则未确知。……后来,康熙年间,石大师叩九峰善果本月禅师得其法。依例纳入善果法系,改换法名,称作‘元济’,也可书作‘原济’。盖善果月公为木陈道忞的法子,而木陈道忞则为龙池传祖的二世传人,因法缘特盛,座下徒侣众多,乃就龙池演派诀道字下另起一诀:‘道本元成佛祖先,明如杲日丽中天’云云。‘元’字仍为第三十六代。”(三)“道缘之研究·初发心”曰:“石大师在湘山寺中,可能住了一年零两个月。该寺于明末清初,有‘行’字辈的禅师数人,相继住持。‘行’字辈,是临济宗龙池派下第三十五代,石大师是‘超’字辈,显然是他们的徒弟,但哪位是石大师的‘剃度恩师’,现尚无法查考。”①
萧燕翼《石涛书画全集·绪论》“一、关于石涛”也提及石涛“法名初为超济,后改元济(或原济),号石涛,又有别号甚多”,“又,石涛的法名,初为超济,后改为元济,又称原济。”②另外,李万才著《石涛》也指出“据考证,石涛出家以后法名很多,有超济、元济或原济”③。
由此看来,石涛最初法名“超济”是获得学术界的公认的了。现在问题是,清初隶属松江府的今上海市区一大丛林、相传三国赤乌十年(247)吴主孙权创建的千年古刹龙华寺牡丹园内,有清顺治年间(1644-1661)龙华寺住持韬明行宗禅师的弟子超济和尚于康熙六年(1667)替行宗所立石塔,此“超济”究竟是否就是“石涛”呢?还是另有其人?颇令人顿起疑窦。
案,康熙初年,临济宗高僧旅庵本月(?—1676)驻锡上海松江泗洲塔院,石涛慕名曾自湖北、江西和浙江一路专程赶赴松江盘桓逗留了一段日子,蒙旅庵授经传道,而这与上述龙华寺超济禅师履历可谓时地俱符,相去不远。又,龙华寺住持韬明行宗禅师亦与旅庵、石涛一样,系出自临济同宗,按上述临济宗龙池传祖演派诀“行超”的先后辈份关系排比,“行宗”跟“超济”显然符合这一命名规矩;而石涛法名由“超济”到“元济”之变易,似乎也当在此时此际,即康熙初年的松江时期;且石涛早年如行脚僧人,走南闯北,行踪不定,是人所共知的。那么,他是否有同时或稍后到同郡(华亭松江)的上海龙华寺参禅进修的可能呢?此“超济”与“石涛”究竟是怎么样的关系呢?这是本文首先想解决的问题。
二、关于松江府上海龙华寺的“超济”和尚
今上海龙华寺牡丹园内有六角形九层石塔一座,塔高260厘米,其间第五层为六角形石柱,每面宽25厘米,高70厘米,有关超济和尚替行宗禅师镌刻塔铭即位于此层:“本山开法第一代临济三十二世韬明宗禅师之塔(面南),大清康熙岁次丁未嗣法人超济等建立(面北)。”④
又,清张宸辑、上海图书馆藏康熙十二年(1673)共读楼钞本《龙华志》卷二“建设”之“舍利宝塔”亦载:“韬明禅师塔院,康熙丁未嗣法超济禅师等建。”
案,康熙丁未系康熙六年(1667),按今人编纂石涛谱牒编年,本年石涛似已离开松江去皖南宣城,其于画史上有名的《十六阿罗应真图卷》正作于此时此际,而其间题款:“丁未年天童忞之孙善果月之子石涛济”和钤押白文印“善果月之子天童忞之孙原济之章”⑤,是他表明自己身份以及师承关系最直接、可靠的确证。
按理,释家师承,何门所出,规矩和表述相当严格,一如今人理解的“不二法门”。石涛自己在《生平行》长诗中讲“五湖鸥近翩情亲,三泖峰高映灵鹫。中有至人证道要,帝庭来归领岩窦”云云,也分明在说他在松江的师傅是从帝庭南归的善果月。不过,如前所述石涛自幼出家,后一路寻访名师,仿佛不拘一格,跟多方僧侣均相往还,并未一门心思认定一师,至少在20岁以前是这样的。这本也怪不得他的,因为当时石涛毕竟还是一个在人生道路上寻觅探索的青年僧侣,或者说尚未完全出道。所以,奔走各地、拜师问道、广结善缘是不难想象的。
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石涛除了在松江拜善果月为师以外,是否还就近参拜了上海龙华寺的同宗禅师韬明行宗和尚,以致康熙五年(1666)行宗死后,他于次年以受业人名义按“行超”辈份署名“超济”替行宗树碑立传了?就此问题的考辨,在有关石涛本身的史料当中,似乎是没有找寻答案的空间余地了,好在有关清初释教史传暨龙华古刹志乘资料尚属完备,足以为我们提供不少确切的查考依据。

[清]石涛 十六阿罗应真图卷 25×311cm 纸本水墨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中“超济”名录有二:一为清尼,自与石涛无干;另一传见《五灯全书》卷第九十八补,字牧翁,系嗣出古卓浚法禅师门下,住持江苏吴江遯村报恩寺,料亦与石涛无关。再检《五灯全书》卷第七十一上海龙华寺住持行宗(1611-1666)禅师小传载:行宗字韬明,浙江盐官人,本姓董,自幼出家,初见天童密云圆悟(1566-1642)禅师,数遭痛棒。再参金粟费隐通容(1593-1661)禅师,遂为入室真子,当年即住持嘉定(今属上海)罗汉寺。不久,“云间(松江)缁素扳主沪上龙华古刹,未几而蜂房大厦,郁郁金碧可观。”案,石涛的太师爷亦天童密云圆悟禅师。那么,此行宗禅师的弟子“超济”是否就是“石涛”本人了呢?检《五灯全书》卷第九十一“临济宗南岳下三十六世随录”韬明宗嗣之超济传略曰:“上洋龙华大壑济禅师,盐官朱氏子,弱龄颖异,业儒嗜佛,十九脱白,往参金粟容(即费隐通容)。才入门,容便当头一棒曰:‘不可忘却这一棒。’师当下领旨。逾年复谒龙华宗(即行宗),巾瓶随侍,及掌记室,殚力辅弼二十年,锯解不开,彻法源底,晋职西堂,以偈嘱之,遂命继席龙华。”另据康熙《龙华志》卷五“法语”所载与此相合,“国朝康熙丙午(1666)十一月二十六日沛堂济禅师入院至佛殿……”
综上记述,可知龙华寺韬明行宗禅师之法子大壑超济虽亦俗姓朱氏,跟石涛同姓;并且他跟石涛嗣出同一太师爷密云圆悟和尚,同属龙池传祖幻有正传禅师的四世传人和临济宗南岳下三十六世。另外,他在上海龙华寺时与石涛到松江泗洲塔院修行时间前后相去不足三年,东西相距不出百里之遥,但他与石涛其实并不是一个人已端倪可察了。事实上,由《五灯全书》目录所列辈份,大致也可见一斑,南岳下第三十三世是天童密云圆悟禅师,而圆悟法嗣较多,计有十四高僧,其中认可的嗣法弟子十二人,包括余杭径山寺费隐通容禅师(即龙华寺超济的入门祖师)和天童山翁木陈道忞(1596-1674)禅师(即石涛祖师),他们均属南岳下第三十四世,而石涛师父善果旅庵本月禅师系南岳下第三十五世。至于出自旅庵本月门下的石涛(金陵一枝石涛)⑥和石涛自幼随行由广西北来的喝涛和尚(宣州广教喝涛亮)⑦,则同属南岳下第三十六世。

[清]石涛 山水花卉册(12开之七) 25×17.6cm 纸本水墨 广东省博物馆藏

[清]石涛 山水人物卷 27.7×313.5cm 纸本水墨 故宫博物院藏
三、石涛法名“超济”献疑
由“超济”法名辨析证实大壑超济并非石涛,而石涛是否有“超济”法名不免同样令人怀疑,这是本文其次要辨析的问题。
众所周知,关于石涛传略,同为康熙间人李驎的《大涤子传》和陈鼎的《瞎尊者传》仅及石涛“名元济,字石涛,号苦瓜和尚,又自号曰瞎尊者”,“大涤子者,原济其名,字石涛”,两传均无道及石涛又名“超济”者。另外根据石涛大量信实可据的书法绘画作品中自署款识和印记,也以“元济”或“原济”为法名。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石涛款署、钤印为“清湘石涛”“济山僧石涛”“石涛济”“膏盲子济”“臣僧元济”“湘源石涛济道人”“石道人济”“湘源济山僧石涛”“清湘石涛济山僧”“清湘石道人济”“清湘老人原济”“清湘大涤子济”“清湘瞎尊者元济”等,根本没有署名或钤押“超济”法名的签款与印章。
又,临济宗龙池传祖的圣地在常州、宜兴一带龙池山(参看光绪《宜兴荆谿县新志》卷一疆土·山),石涛的太师爷密云圆悟禅师就是在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到常州龙池山落发,后住持龙池山禹门禅院的。案,临济宗龙池传派系所传弟子大多活动在江南地区,即便石涛的祖师、广东潮阳人木陈道忞似乎也并无剃度弟子去岭南布教。倘若按照童年或少儿石涛在广西湘山寺即以龙池传祖演派诀“行超”辈份为序有了“超济”法名,那么,替他取名的法师究竟是湘山寺僧还是龙池山僧?他跟龙池传派系究竟有什么关系?法名或俗名是什么?究竟是“行”字辈还是跟龙池传祖演派诀“行超”排行无关的其他人呢?

[清]石涛 山水图 46×67cm 纸本设色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值得提醒的是,应石涛生前委托而写的李驎《大涤子传》,谓石涛是“生始二(一说“四”)岁,为宫中仆臣负出,逃至武昌,剃发为僧。年十岁,即好聚古书,然不知读。……又学画山水人物及花卉翎毛。楚人往往称之。既而从武昌道荆门,过洞庭,径长沙,至衡阳而反”。这跟清张庚(1681-1756)《国朝画徵续录》关于“明亡隐入全州湘山浮图为僧”,和石涛友人、清初亦曾从事反清活动而后为僧的“岭南三家”之一广东屈大均(1630-1696)诗“师本全州清净禅,湘山湘水别多年”⑧等说法似乎不无出入。但据今广东省博物馆藏目前所知石涛最早有纪年作品—《山水花卉册》之七《水仙》页间石涛款书“丁酉(顺治十四年,1657)二月写于武昌之鹤楼”;约成书于清初康熙年间佚名《十百斋书画录》辛卷著录石涛《黄鹤楼卷》款作“时壬寅(康熙元年,1662)秋深,李泉石山人、胡二传道士、赵还清招予登鹤楼感赋,清湘小乘客复为此者,可见乐事,但诗不足传耳”分析,石涛20岁左右确曾在湖湘、武昌一带“居久之”⑨。另据同一《山水花卉册》之一款作“小乘客石涛济写于岳阳夜艇”;之八款作“石涛画于开先寺之龙坛石上”;之十款作“九日五柳斋中写石涛济”各十二字;以及故宫博物院藏石涛《山水人物卷》首段“石户农”款书“甲辰客庐山之开先寺写于白龙石上”十五字综合推考,石涛于顺治十四年至康熙三年(甲辰,1664)期间一直活动于岳阳、武昌和庐山的湘北洞庭湖到江西鄱阳湖的长江沿线,当时他的名号为“石涛”“石涛济”或“小乘客石涛”,钤印亦为白文“原济”“老涛”,朱文“石涛”。如果上述作品和印鉴确凿无疑的话,证明青年老成的石涛并无“超济”名号。
悬想石涛即便是在湘山寺出家,当时应当也不过是一个少不更事的懵懂小沙弥,似乎还算不上、达不到修行很深的、佛门高僧入室弟子、传法弟子而正式命名的程度;纵使有了僧号,大抵也只不过是一个身处佛门为资区分彼此入山先后、长幼的临时符号而已,绝非正式的法名。根据陈垣《清初济宗世系表》,密云圆悟诸嫡传弟子中,费隐通容和石奇通云等的再传弟子是“行”字辈,如韬明行宗、隐元行琦、孤云行鉴、独冠行敬和法幢行织、道严行恂等,而木陈道忞的再传弟子却是“本”字辈,如石涛的师父旅庵本月及天岳本昼、山晓本皙、犀照本彻、蛤庵本圜等。至于“超”字辈虽属自圆悟以降第四代,但据世系表可知并不出自木陈、旅庵一系。综上所述,石涛法名“超济”,无论廿岁之前的少儿时期还是廿岁左右的青年时代,都显得扑朔迷离、波谲云诡,有不少值得再探讨、再证实的成份,因为“石涛超济”的师承关系远不如当时松江府的上海龙华寺僧“大壑超济”等师生关系来的明朗透彻。
四、关于石涛得道的上海松江府华亭县泗洲塔院
石涛的“超济”法名看来得存疑待考了,而他跟几乎同时松江府的上海龙华寺暨其僧“超济”禅师,更没有什么特殊关系可言。不过,石涛曾特地赶赴上海松江的泗洲塔院追随从北京善果寺南下的旅庵本月禅师修炼,则是千真万确的不争事实;甚至他的正式法名“元济”应该也始于松江证道之后。就此,明复《石涛原济禅师行实考》(五)“道缘之研究·立雪”也有专门论述。但他根据石涛《生平行》诗中“五湖鸥近翩情亲,三泖峰高映灵鹫。中有至人证道要,帝庭来归领岩窦。三战神机上法堂,几遭毒手归鞭骤”等诗句,言之凿凿地认定旅庵和石涛“他们师徒间这场‘法战’是在三泖湖中、灵鹫峰下进行的。三泖在今江苏省松江县,灵鹫即湖中九峰山,其侧有古寺,名曰正觉,一般也称作九峰寺,或简称为九峰”;并说“泗洲塔院……因滨临泗泾得名,为九峰诸祖灵塔所在之地,乃正觉寺的一部分,故也可称为九峰”云云,料部分出自对文献记载的望文生义,并非结合实地踏勘考察的结论。兹先照录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松江陆树声(1509-1605)撰《重修昆山泗洲塔院记碑》以窥塔院历史地理。
小昆山之创塔院,自宋乾道元年僧心古始。……父老云,昆山故号马鞍,吾郡西北二十三里,一峰郁然,绾结泖口,晋陆机、云兄弟读书其中,是为真昆山,陆之祖征北将军祎墓在焉。……余八十五矣,常杖山椒,相与徘徊藤花松影之下,顾视石气沉秀,诸僧次第驯谨,雅有规绳,信兹山重兴之会也。大较干将、横云诸山,寺枕山麓,山不能兼泖,泖塔浮水中,水不能兼山,独小昆山两收之,而又二陆先生之灵实依于此,非濂上人曷能成是胜乎?于是余施田数亩,以少续先世遗志。而士大夫之属游于山中者,各捐若干亩,皆不可以无记。
又,清乾隆《娄县志》卷十“祠祀”载:
泗洲塔院,在昆山之巅,宋乾道元年释心古建,明弘治四年建观音殿,嘉靖二十年建真武殿,二十六年又建西方殿,隆庆元年建三圣阁,万历中建藏经阁。本朝顺治五年,郡人范宏议以山势宜北而殿独南向,于形家不利。僧溯本源遂鸠工易置法像,不动一时皆旋,观者谓有神助。
清《江南通志》卷四十五所记略同。
案,松江九峰(自西南东北走向依次为小昆山、横云山、机山、天马山、辰山、佘山、薛山、厍公山、凤凰山)三泖(长泖、大泖、圆泖),古来被视为松江风光旖旎旅游胜地,三泖水域面积也远大于今日湖区。不过,据上记述,可知泗洲塔院近泖(下泖或圆泖)但并非如澄照塔院(泖塔)独处泖湖岛心。明复关于泗洲塔院在泖湖的说法,殆来自梅清(1623-1697)康熙十四年(1675)托回松江探望师父、泗洲塔院住持旅庵本月的石涛带诗问候中有“渺渺泖湖寺,经年闭竹关”句⑩。而小昆山可能有灵鹫峰,一如明末夏完淳《题昆山水殿》诗云:“鹫岭岧峣谷水阴,昆冈迢递快登临。始知灵运寻山志,犹是昙摩泛海心。古寺松声清磬远,寒潭鹰影碧云深。青丝天棘风流在,如见当年祇树林。”但一说灵鹫系指小昆山附近横云山下灵鹫庵,其上有石壁横亘数十丈。结合石涛“三泖峰高映灵鹫”句分析,也可能指泗洲塔院所在地的圆泖边上小昆山北峰跟横云山灵鹫庵上石壁遥相映照。
鉴于往昔三泖水域面积远大于现在,故主张小昆山位于三泖湖中或不为过,但认为泗洲塔院之“泗洲”冠名因濒临泗泾塘(河浜)而来,则绝非事实。泗洲塔院的确又名九峰寺,盖因其位于云间九峰之最南端而名列九峰之末的小昆山北峰。但塔院名称由来,盖因寺院傍慈雨塔而建,而宝塔相传系唐龙朔初年(661年前后)西域僧伽来江南宣化时建。僧伽晚年定居泗洲,号泗洲和尚,故慈雨塔又名泗洲塔,泗洲塔院因此得名;又因为塔院位于小昆山巅,故亦名昆山塔院。而泗泾塘系远在小昆山东北三五十里开外的河塘,跟泗洲塔院命名浑然无关。一如松江小昆山不能跟江苏昆山玉峰山(即昆山,亦称“马鞍山”)相提并论同理可证。
清初泗洲塔院的住持,即石涛的师父旅庵本月和尚,是康熙初年自北京城西南善果寺隐退,旋受上海松江府九峰寺(即泗州塔院)溯本禅师之请来山住持的。就此本末原委,与旅庵本月有过数面之缘的时人叶梦珠辑、康熙三十二年(1693)成稿《阅世编》卷九“释道”较之《五灯全书》更有详尽记载:
九峰旅庵和尚者,浙之秀水人,姓孙氏。初生,白光满室。襁褓中,有高僧见之,摩其顶曰:他日当为人天师。年二十一,辞家,就本郡敬畏庵,从日明轮法师薙发。二十三,遍叩诸方,曾于玉林大觉禅师备记室。玉林法名秀天隐法嗣两稔,渡钱塘参宏觉老人于越之大能仁寺。宏觉禅师即木陈法名忞密云法嗣,二十九,以悟彻得法。顺治十六年己亥(1659),世祖章皇帝遣使宣宏觉老人入都问道,师同徵入。天子嘉之,降礼如法门故事。命驻锡椒园中,延访日至;宫内大臣賫帑金设伊蒲精供,特敕旅公开法堂于京师之善果寺,驾时临幸,赐赉有加,自诸王大臣而下,莫不北面同参。至洒宸翰以赐,有“天上无双月,人间只一僧”句,以旅公法名本月也。方外之契,可称一时极盛。迨世祖上宾宏觉老人及旅公,深鼎湖之痛,先后请归故山,今上慰留半载后得请。岁在戊申(康熙七年,1668),松之缙绅先生循舆情所慕,争通尺素,从九峰禅寺溯本长老之请以请于师,而师乃惠然莅止。缙绅中周釜山先生护持尤力,余与釜山父子俱雅慕旅公,未获参叩。癸丑(康熙十二年,1673)暮春,旅公来访玠右先生于笋里,余得追陪杖履,一见如旧识。挥麈而谈,移时不倦,遂作诗文倡酬而别。甲寅(康熙十三年,1674)之冬,复偕鹰垂兄弟访师山中,作信宿谈。九峰禅寺,地当山后,旧故面南,溯本承其先师之志,向欲改创面北而力未能办。顺治七年庚寅(1650)冬,忽有一工来山,自言能任其事。询其所费,惟须数十人力,足令自转。众咸异之,刻期聚观,观者即为助力。工取木干及巨絙数根,遍缚壁上,众属干上,齐声起肩,殿随而转,一壁不移,寸瓦不动,并殿中塑像、供座,皆用此法转而北向,宛若天然。其人不索酬而去,一时惊传以为神。溯本住锡几二十年而退居于横云山之麓,迎旅公升座。宏开方丈,大振宗风,则知天将令国师建此道场,故先有异人来转此殿。法会因缘,良非偶然也。余在甲寅之春,即闻其事,以为太异,犹未敢轻信。迨冬十月到山,亲在殿中与大众谈之略悉。丙辰(康熙十五年,1676)春,复同蓉左叔翁及碧涵兄弟,访师山中,适会溯本邀过横云,静室谈转殿事更详,至冬而旅公示寂。今法嗣中勗元迪继之,玉林天隐法嗣;宏觉,密云法嗣;天隐与密云,皆幻有法嗣也。
康熙八年(1669),旅庵本月见师父道忞自京南返在宁波天童寺建“奎焕阁”,必研读了一番道忞的《宝奎说》而心领神会。为使“圣敬隆崇,奎章焕发”,遂也在泗洲塔院建起“奎章阁”,用来供奉顺治十七年(1660)十月初三、初四日清世祖在北京故宫正北景山便殿特赐他的“乐天知命”和“一池荷叶衣无尽,数亩松花食有余”、“天上无双月,人间只一僧”等宸翰,以及御赐的古铜佛像一尊。所以,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康熙南巡到松江,御赐泗洲塔院“奎光烛泖”匾额,或与旅庵本月创建“奎章阁”有关。
泗洲塔院的明末清初故物,抵今几已荡然无存,湮没殆尽,如慈雨塔毁于清嘉庆年间,庙舍尽为20世纪40年代初日伪期间拆除。今唯一幸存树龄达450年古银杏当属塔院旧物。想必康熙初年石涛初次到泗洲塔院参拜旅庵本月禅师;康熙十四年(1675)石涛于祖师木陈道忞圆寂(康熙十三年)后再次去泗洲塔院探望旅庵本月师父;次年(康熙十五年,1676)十月十四日旅庵本月圆寂于泗洲塔院,作为其高足的石涛依僧林习俗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赴松江替师父追福、起塔(骨塔)、整理处置物什,守塔小昆山二陆读书台左,每日青灯红鱼,虔修忏摩,历康熙十六年至十七年冬月始返回宣城期间,均当见过上述御赐宸翰、法器等物。而小昆山上遗存至今的古银杏,显然是石涛当年与松江泗洲塔院朝夕相处、因缘际会的唯一存世见证物了。

[清]石涛 余杭看山图 30.5×134.2cm 纸本设色 上海博物馆藏

[清]石涛 山水花卉册(12开之一) 25×17.6cm纸本水墨 广东省博物馆藏
五、石涛到松江的时间
石涛到松江确有其事,这有其《生平行》长诗为凭,但可能时间较短,因而清人撰写的石涛小传多忽略不计。如李驎《大涤子传》说他“又从武昌之越中,由越中之宣城”,就没有谈及松江之行。那么,石涛究竟是什么时候到的松江呢?

[清]石涛 山水花卉册(12开之二) 25×17.6cm纸本水墨 广东省博物馆藏
萧燕翼《石涛书画全集·绪论》认为“康熙元年(1662)石涛又拜松江昆山泗洲塔院住持旅庵本月为师”,李万才《石涛》年表基本因袭傅抱石《石涛上人年谱》,亦将石涛到松江拜旅庵为师的时间系在康熙元年。又,孙世昌《石涛艺术世界》也认为“旅庵本月于康熙元年(1662)返回松江,住持昆山泗洲塔院。石涛与喝涛拜旅庵本月为师,大约在旅庵本月返回松江驻锡泗洲塔院时”,明复《石涛原济禅师行实考》(五)“道缘之研究·立雪”载:“石大师在《生平行》中,自谓得法于九峰。应该在壬寅年(康熙元年,1662)呢,或是丁未年(1667)呢?现今传世有他丁未年在宣城所绘的《十六阿罗应真图卷》一种,其上署款已作‘木陈忞之孙,善果月之子,石涛原济’。当时他是由何处到宣城,不得而知。然依其《生平行》所叙,他于得法之后,先赴浙江,在杭州、天台遨游很久之后,才到宣城的。故而推知他应该在丁未年以前,业已得法。那么就是说,他得法的时间是壬寅年,月师第一次住九峰时。当时他正寄居南京天隆寺中(见傅谱),去九峰仅三五日的行程,真可谓‘近水楼台’,方便至极。”张长虹《六十年来中国大陆石涛研究综述》“二、身世行迹及交游问题”则概括“几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就石涛到松江的时间较上述各说提前了一年。石涛“17岁左右赴越中,1663年在松江拜旅庵本月为师,学习禅学;1666年赴宣城,住锡敬亭广教寺”。

[清]石涛 山水花卉册(12开之三) 25×17.6cm纸本水墨 广东省博物馆藏

[清]石涛 山水花卉册(12开之十二) 25×17.6cm 纸本水墨 广东省博物馆藏
据上记述,石涛到松江的时间表似乎可以确认在康熙元年或二年了。但据前及《十百斋书画录》著录石涛《黄鹤楼卷》款作“壬寅(康熙元年,1662)秋深,李泉石山人、胡二传道士、赵还清招予登鹤楼感赋”,和《石涛书画全集·下卷》著录故宫博物院藏石涛《山水人物卷》首段“石户农”款书“甲辰客庐山之开先寺写于白龙石上”推考,如果这两件作品经鉴定真无疑的话,那么显然表明康熙甲辰(康熙三年,1664)石涛根本没有到达松江还尚在江西庐山。而此说如若成立,则石涛于康熙元年二月在天龙古院作《人物山水》及款题“壬寅春仲造天龙古院作此,以拟古人精华,识者赏之。大涤子石涛济山僧”作品疑伪。由此上溯顺治十八年(1661)石涛于“谷雨前一日,过天龙古院作山水轴”乃至顺治十四年(1657)春石涛“至杭州六通院,叩谒曹洞门下的愿庵净伊禅师。伊师俗名丁元公,能文善画,尤工佛像。他不但热情地接待了石涛,还为之画了一幅肖像,‘无发僧服,道貌岸然’”云云,恐怕亦都靠不住。不说相关作品疑伪,至少这些作品跟相关年份无关,因为这些年份的石涛根本不在上述地点,而远在湖湘鄂赣等地。更何况石涛之别署“大涤子”号,当始于康熙三十五(1696)到三十六(1697)年之间,其时石涛已年届五十五六岁。所以,举凡上述康熙元年款作“大涤子石涛济山僧”和日本山本悌一郎《宋元明清书画名贤详传》著录款题“癸亥(1683)三月游天台山……戏图是幅,并著大涤子于其间。不亦快事耶”等作品并属可疑,与之对应年份踪迹自然亦不可靠可知。
既然石涛康熙元年到三年不可能到松江,那么他该是哪一年有松江之行呢?汪世清《石涛的〈余杭看山图〉》认为石涛曾有浙西余杭大涤山之行,根据其生平行迹考察,“只能在他东下‘从武昌之越中,由越中之宣城’的途中,时间在康熙甲辰(1664)和丙午(康熙五年,1666)之间,年约24岁。因为在他以后定居宣城、南京和扬州的三个时期,都没有再次到过浙西。”由此判断石涛松江之行当在从余杭去宣城期间。因为他“初至宣城约在五年丙午”,具体去松江的年份,笔者比较倾向于康熙乙已到丙午之间,即康熙四年(1665)到五年的约两年左右时间。因为据上文考证,石涛康熙三年深秋尚远在江西长江沿线的庐山九江一带,他松江之行前还有越中之行,即余杭看山,湖上小住。按他同年晚秋已到杭州稍作停留,寻师访友推考,他松江之行暂设定在次年到后年约两年当中自觉合乎情理。因为石涛早年的各地行踪,或多或少有与之相关的画迹、款识或著录作品可资考证,惟独康熙四、五年几乎没有为后世留下片纸只字。证诸仅见于其《生平行》长诗提及的松江证道之严峻乃至近乎封闭式的严酷培训,也许就不难理解其潜心师从本月进修禅学而心无旁骛的执著投入之一斑了。另外,前已论及,石涛康熙五年(1666)去皖南宣城已获得学术界共认,虽然就其师父旅庵本月也于当年冬月启程去宣城尚有不同看法,但倘以石涛修行证道两年毕追随侍奉师父去宣城弘法,似于道理上持之有据,恰如其分而无可非议。
设定石涛康熙四、五年在松江的另一个原因,是该年松江发生了一桩出乎意料之外的突发事件。当年清廷宣布明宗室改易姓名隐匿者皆复旧回籍,仿佛统治者针对前朝宗藩嫡嗣实行了较为亲和的怀柔、开放政策,原本制定的敌视举措及因此造成的紧张空气貌似相对宽松、缓和了些许。讵料到了次年(1666),明河南安昌王后裔改换姓名,隐匿于华亭城北郊龙珠(树)庵为僧,却被松江官府侦知,遂办“谋逆”大狱。一时间被抓遭凌迟处死者有27人,斩首者计七八十人,株连更达五六百人之众,松江府上空顿时再度笼罩起大肆杀戮隐瞒身份的明朝宗亲成员的血腥气氛。
针对就发生在自己周遭这引蛇出洞、敲山镇虎般血淋淋的事实,对于同属明宗室后裔并且同样置身佛堂百衲加身潜心修道的石涛而言,自然不会事不关己,毫无觉察。相反,首当其冲、感同身受、不寒而栗,仿佛惊弓之鸟而惶惶不可终日。面临随时可能被逮、被杀而危机四伏的时势,同年,怀着忐忑不安心情的石涛悄然身随为清廷宠遇优渥的旅庵本月禅师作脱身之计,即刻启程,束装就道离开了松江这片是非之地。而当时与其说是他陪本月去宣城,倒不如说是本月保驾护送他与喝涛去皖南寺院暂避风声。
另外,仅隔一年(康熙六年,1667),惊魂甫定、心有余悸而立足未稳的石涛,赶紧在新绘制的象征与世无争宗教题材画《十六阿罗应真图卷》上,款署起“丁未年天童忞之孙善果月之子石涛济”字样,并钤盖了新刻的白文“善果月之子天童忞之孙原济之章”,借重自己两位极受清廷礼遇,尤其受顺治皇帝抬举而有“国师”和“红顶僧人”头衔的后台老师予以自我标榜,以此向世人表明他的师承关系,恐怕也跟上述时代背景有关。事实上,在宗派谱系上,石涛虽属木陈道忞之孙辈,但木陈道忞似乎并未如旅庵本月般向他正式传道,他跟石涛是否正式见过面也从无文献明确记载。所以,照此情况分析,石涛当年将木陈道忞抬将出来以示自己不菲身价,无非是在向统治当局出示他处世云游的“护身符”和“通行证”,同时表达自己的政治倾向和激流勇退之态度,即他是属于深受清廷崇敬的道忞、本月一系的入室弟子,藉此使自己苟全性命于乱世,以免遭致不必要的杀身之祸。
总之,剖析了石涛到达松江前后的行迹和时代背景以及他用印、款署的变化,足见他康熙四年到松江,约两年左右即告离开去宣城,是有其“不可告人”的原因的。换言之,新印鉴和款署的问世绝非跟此前松江突发事件的时局一无瓜葛。否则,上述表态何以出现在紧接松江事变之后,难道这仅仅是偶然的不谋巧合吗?其实,石涛在《锺玉先生枉顾诗》中就道出了幼年家难逋逃,险为株连追杀经历,同时似乎又吐露了松江有惊无险的感受。“板荡无全宇,沧桑无安澜。嗟余生不辰,龆龀遭险难。巢破卵亦损,兄弟宁忠完?百死偶未绝,披缁出尘寰。”最后两句“百死偶未绝,披缁出尘寰”,恐怕就是他旁敲侧击,感慨当初松江时局波动而风云变幻的咏叹调。
六、赘言

[清]石涛 山水花卉册(12开之十一) 25×17.6cm 纸本水墨 广东省博物馆藏
就石涛生平史迹及其书画艺术的研究,清代已不乏学人梳理。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许多书画界前辈就此更有不少新的挖掘,取得了一批学术成果。不过,就石涛研究,不论生平履历的爬梳,还是书画艺术的钩沉,相当程度上尚偏重于其青年以后的踪迹、作品,而就其20岁前后行踪、创作的探索,似乎还处于眉目不清阶段,以致有学者在《六十年来中国大陆石涛研究综述》“有待深入研究的几个问题”章节中指出:“石涛的前期经历,尤其是定居宣城之前的少年及青年时期的行踪尚不够清楚。由于石涛的画风形成与其生活经历密切相关,所以这一段的经历不明,画风来源与发展的问题也就难以确定。”事实上,清代方鼎锐在作《清湘老人题记》的序言时即已指出:“老人(指石涛)既以画名天下,独其生平,惝恍支离,莫能窥测,故一涉笔,往往多不解。”据此也反映石涛其人居无定所,尤其早年行踪飘忽,难以把握之一斑。
如上所述,石涛中青年以前的活动,值得深入发掘的地方委实不少,而20岁前后他旅居上海松江两年左右的启蒙证道经历,事关其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艺术观的形成和价值取向的确立,就其个人评价和作品的分析,也具有窥斑知豹、见微知著、举足轻重的研究作用;石涛此后大半身的人生走向和艺术生涯,也无不与松江两年进修息息相关。但就此阶段石涛的师从、交游、参禅、修炼等相关信息的提炼,除了其本身《生平诗》高度概括、浓缩介绍之外,其余文献史料多语焉不详。本文抛砖引玉,旨在引起大家对这一话题的兴趣。
(作者单位:上海博物馆)
责任编辑:陈春晓
注释:
①明复《石涛原济禅师行实考》(一)“家世之研究·名号”录临济宗龙池传祖演派诀后半诀作:行超明“实”际。见《艺坛》第79期,台北艺坛社,1974年,第4页。
②萧燕翼《石涛书画全集·绪论》录临济宗龙池传祖演派诀后半诀作:行超明“空”际。见《石涛书画全集》上卷,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年9月,第3页。
③李万才《石涛》第二章《石涛家史及生平经历》,第一节《明皇族子孙,南昌王的后裔》,吉林美术出版社,1996年5月,第8页。
④参看柴志光、潘明权主编《上海佛教碑刻文献集》(清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第181页;《上海文物博物馆志》第一编文物古迹、第六章建筑、第二节寺庙建筑一、佛教1、龙华寺将“超济”讹为“起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6月,第171页。
⑤上海博物馆藏石涛康熙戊辰(1688)《释海仑罗汉图卷》题跋上亦有其白文“善果月之子天童忞之孙原济之章”,参看《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上,文物出版社,1987年12月,第216页。
⑥⑦[清]超永《五灯全书》卷第九十四补遗,第323页。
⑧《石公种松歌》。
⑨[清]李驎《虬峰文集》卷十六《大涤子传》。
⑩[清]梅清《天延阁后集》卷二,《因石涛师诣九峰复寄旅庵大师》诗,自注年款:“乙卯”。
——松江二中(集团)初级中学校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