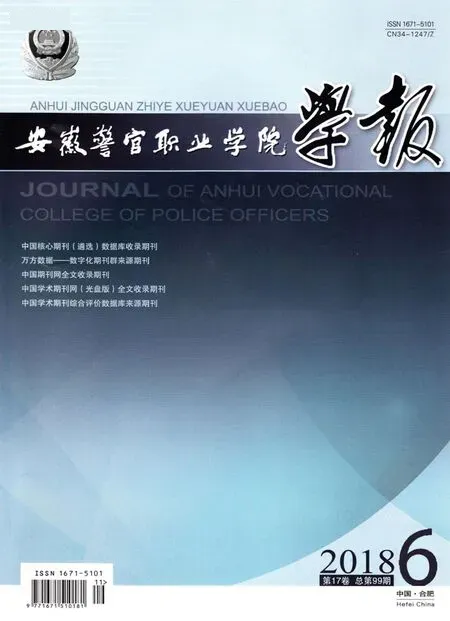共犯关系脱离新论
——以脱离前行为产生作为义务为切入点
吴学龙
(云南大学 法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一、研究现状
处于共同犯罪关系中的行为人,虽细观之下仍有不同,其或者如共同正犯一般同心协力分工合作,又或者如教唆犯和帮助犯一般怂恿挑拨助人下石,但是可以一并讨论的是随着正犯行为的展开,假若部分行为人因反悔等原因中途退出,未继续参与后续犯罪行为,但其他行为人则继续完成了犯罪,那么那些中途退出的行为人应当在什么范围内承担罪责呢?这就是共犯关系的脱离问题。关于这一点迄今在我国学界与实务界的讨论与思辨仍然不足,而且多限于对日本等域外学说的借鉴评析。而日本学界内部对此一问题也产生了激烈的讨论,争论的焦点在于共犯脱离的认定标准上,对此先后产生了四种不同的学说。具体而言:(1)“意思联络欠缺说”认为,脱离者如果在主观上欠缺了同其他参与者间的“意思联络”,就不能再评价为整体行为,其为脱离所付出的真挚努力就须单独评价,因此可作为中止未遂处理;[1](2)“障碍未遂准用说”认为,在脱离者脱离之后,仍然产生了既遂结果的话,就没有适用中止未遂的余地。认定脱离的依据不是在于“意思联络”的欠缺,而是在于脱离者为从共犯关系中脱离出来付出真挚努力,切断了与其他参与者之间的相互利用、补充的共同关系,即使未能最终防止结果发生,但也要承担障碍未遂的责任;[2](3)“因果关系切断说”从共犯的处罚根据(惹起说)出发,认为认定共犯脱离的根据在于切断了自己的行为和最终的法益侵害结果之间的因果性,因此不应对最终既遂结果承担责任;[3](4)“共犯关系消解说”认为,在共犯脱离的认定上,关键在于是否基于脱离者的行为而建立了新的共犯关系,新的关系的建立便意味着旧的共犯关系的消解,原行为对最终结果的影响力就不存在了。[4]可以说以上观点各有利弊,但在有关共犯的处罚根据的因果共犯论占据通说地位后,与其更具有整合性的“因果关系切断说”自然便成为了解释共犯关系脱离的有力学说。因为从因果共犯论的角度出发,行为人仅就与自己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事实承担共犯罪责,那么在共犯关系脱离的场合,脱离者既然通过切断与最终法益侵害结果间的因果关系而从共犯关系中脱离出去,自然就无需再为该法益侵害结果承担罪责。不过也不是只要采取了“因果关系切断说”,共犯脱离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该学说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没有划定一个明确的因果关系切断界限。即究竟在怎样的条件下可以说脱离者与其他行为人之间的行为或所造成的结果间的因果关系切断了,该学说对此并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尤其是在面对这样的批评——从事后的角度来说要切断一旦给予的因果性影响是极其困难的——之时,该学说则反而极大限制了共犯关系脱离的成立范围。[5]
基于上述考虑,本着“因果关系切断说”的立场不变,主张即便没有在事实上完全切断因果关系,但如果从规范的角度对 “因果关系切断”予以软化处理,使得其在法律评价上可以称之为是切断了因果关系,进而实现共犯关系的脱离的“规范的因果关系切断说”逐渐成为多数说。[6]例如针对日本判例,甲、乙深夜一起饮酒,两人出于对在同一酒吧的丙的态度的愤怒而将其拖至乙的房间内,后用竹刀、木刀击打之,暴行持续了将近一个多小时后,甲说“已经可以住手了吧,我回去了”,然后离开,过后不久,乙则因再次被丙激怒而击打丙,最终致其死亡。①东京高判1988年7月13日《高刑集》第42卷第2号第259页。对此,前田雅英教授认为如果脱离者在脱离过程中 “做出了努力,进行了充分劝说,在心理上打消了共犯一方的攻击意思,且收拾起木刀等除去了物理上的因果性,那么可以认定脱离。即通过规范评价,判断因果性是否减弱到了不必对结果(包含未遂的结果在内)进行归责的程度”。[7]可以说该观点从心理因果性与物理因果性切断两个方面切入进行具体认定,符合一般“因果关系切断说”的认定路径,但是究其采用的规范评价的依据却转而变成了 “处罚必要性”问题,对此则仍有以下疑问:首先,是否在规范层面没有处罚必要性(处罚程度低)就可以说是没有了因果关系呢?很显然这个推论并不成立,处罚必要性的降低并不能得出没有因果关系的结论,既然坚持“因果关系切断说”自然要以因果关系切断为前提,而不是正好相反。其次,即使承认以上这一思路是正确的,那么所谓的“处罚必要性”又应该如何进行具体认定呢?对此持“规范因果关系切断说”的大多数学者都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而且这些学者所持的“规范评价”依据也各不相同,在具体案例中观点各异,很难有统一的评判标准。②例如井田良教授采取“相当因果关系说”,即是否将自己的影响降低到相当低的程度;岛田聪一郎教授则采是否可以评价为“另外的犯罪事实”作为评价依据;盐见淳教授将中止措施本身是否具有作为脱离的“适格性”作为评价依据。参见王昭武:《共谋射程理论与共犯关系脱离的认定——兼与刘艳红教授商榷》,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第59-60页。正如国内学者王昭武教授所言“从什么视角、以什么标准来‘规范地’判断才是问题所在”,而这些都有待进一步明确。[8]可以说,从因果关系切断的立场来解决共犯关系脱离问题能否维持,本来就是一个有待继续深究的问题,即需要对其具体内容进一步进行挖掘和深化。但是由此发展出来的“规范说”似乎又转而进入了另外一条不同的胡同中,而且还是条“死胡同”。因此,本着这样的问题意识,本文试图在原有的理论基础上,整合现有的理论资源,尝试从“先前行为产生作为义务”的视角来对共犯脱离问题做些探讨。
二、现有学说的启示
(一)问题之所在
有关共犯关系的脱离问题,有力观点是基于因果共犯论的立场通过判别是否切断了与其他共犯人所继续造成的法益侵害结果间的因果关系这一标准予以解决。但是正如上文所说,该观点面临切断标准过于严格的问题。按这一观点展开,要完全切断与其他共犯人之行为间的因果关系,在进入实行行为阶段,几乎只剩阻止其他共犯人继续实行犯罪行为这一唯一方法,方能切断脱离者脱离前行为所施加于其他共犯人上的因果性影响。可是正如大谷实教授所言 “事实上共犯的脱离本就属于只有犯罪结果发生之时才成为须要探讨的问题”,[9]即要解决在产生最终结果的情况下,能否将该结果归属于脱离者的问题。而如若要求阻止其他人继续实行之行为进而防止结果发生这一条件,那么当条件成立时,该问题显然已经不再是共犯脱离的问题,转而变成犯罪停止形态领域的问题了。于是我们不难发现,坚持因果关系切断的认定路径将会走向一个十分矛盾的境地,即要求事实上切断因果关系反而否定了共犯脱离理论本身。这不得不让人产生疑问,“因果关系切断说”在关于共犯脱离的认定问题上究竟能否发挥作用?
(二)“先前行为产生作为义务”的解决方案
实际上以上问题学界已有解决思路,即立足于规范评价的立场,对于因果关系的切断予以软化处理,这一点上文也有介绍过。但是正如上文所述,这种方式让有关共犯脱离的问题愈发复杂化,认定标准也趋于模糊,并不能有效处理所有共犯脱离情形。对此笔者认为,合理的处理方式仍然是沿着“因果关系切断说”的路径,对于脱离者“先前行为”的与最终既遂结果间的因果性切断采“防止结果发生”的认定方式,但是对“防止结果发生”这一条件进行适当扩张,即在脱离者完成了脱离行为后,必须具体考察于当时之情境下,脱离者是否仍有阻止其他行为人继续实行犯罪行为并最终防止结果发生的作为义务。对此山口厚教授也认为“对于企图实施犯罪,且已经开始实施犯罪的人来说,在各个不同的时点、阶段,都要求其解消此前所引起的指向犯罪之实现的效果或者作用,以避免结果之发生”。[10]也就是说,在这一过程中,脱离者实际上基于自己的先前行为(从开始实施犯罪起),便一直被科以了“防止结果发生”的作为义务。即使在其自己完成了脱离行为后,仍然有考察其是否仍存有作为义务的余地,如若存在这一作为义务,则脱离者必须履行这一作为义务,否则将对其他共犯人所造成之结果承担不作为的刑事责任。如若不存在这一作为义务,则脱离者在完成了自己的脱离行为后便从共犯关系中脱离出去,对于其他共犯人所造成之结果则无需承担责任。以上,围绕“因果关系切断说”展开的关于共犯脱离的讨论,在引入先前行为产生作为义务理论后,实际上是想要通过该理论具体考察脱离者在完成脱离行为后是否对于所有脱离情形仍有必要实行“防止结果发生”这一极为苛刻的认定条件,以此对于该条件进行适当“扩张”,排除一些不必要予以“防止结果发生”义务的情形,进而将这些脱离情形在即使产生最终结果的情况下,也认定为共犯脱离。通过这样的处理方式,一方面可以维持现有共犯脱离理论的逻辑自洽性,避免因为过于严格的共犯脱离认定条件,而使得该理论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另一方面,从整个刑法理论体系的广度来考量,如果脱离者在完成脱离行为后,通过不作为的作为义务理论考察后,没有避免结果发生的作为义务,那么我们还能有什么更强的理由要求脱离者去防止最终的结果发生呢?在这样的前提下,认定构成共犯脱离,在理论体系上更具有整合性。
据此,有关共犯脱离的认定问题,有必要借助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理论来判断具体案件中脱离者是否有“避免结果发生”的作为义务。因此,问题的核心便转移到了判断脱离者“是否具有作为义务”这一方向上来。而这一问题首先需要解决的便是脱离者的作为义务来源,即作为义务的发生根据问题。关于作为义务来源,学界一直争议不断,我国刑法学界一般从形式上对作为义务来源进行界定,即包括其他法律规定、职务行为、法律行为以及先前行为的“形式四分说”。[11]而在这里与共犯脱离情形相契合的是“先前行为”领域的问题,因为在脱离者实现脱离之后,实际上整个犯罪进程便被分隔成了“脱离前行为(先前行为)”及“脱离后行为”两个板块。在这一情形下,几乎所有共犯脱离问题都满足“先前行为是否产生作为义务”这一认定模式,即可通过借助“先前行为理论”来判断具体案件中共犯人是否有“避免结果发生”的作为义务。于是乎现在的关键问题便限定在先前行为的认定上来,因为究竟怎样的先前行为才能产生相应作为义务,仍然是一个有待明确的问题。对此国内有学者做出过相应表述,认为先前行为是“制造了法益侵害的紧迫危险”的行为,在此情境下具有保证人地位。[12]日本学界有学者则认为,“如果行为人给与了结果发生的危险以重大的原因,则会成为给作为义务奠定基础的因素”,此时应当承担作为义务。[13]但是,以上观点还是显得过于抽象,无益于对于具体案件的准确判断,对此仍需对先前行为理论进行深入挖掘以寻找合理答案。
三、先前行为产生作为义务的理论展开
(一)基本概述
回望整个不作为犯领域对作为义务来源的研究历程,其经历了从形式化向实质化的漫长变迁。[14]而形式化的义务来源路径现在已被一般性地拒绝,尤其是在先前行为领域,借助形式的法义务说已经无法对其作为义务来源根据做出明确说明。[15]现今占据主流学说地位的乃是实质的法义务说,该说试图在先前行为产生作为义务的依据上进行实质化限定。而沿着这条实质化的路径,则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实质限定方法,一是基于法益侵害说的立场,从先前行为所制造的危险与最终造成的构成要件结果间的关联性角度来限定其作为义务的产生范围;二是基于规范违反说的立场,从先前行为与最终造成的构成要件结果间的规范关联来限定其作为义务的范围。前者强调行为对于结果事实的支配性,后者强调行为本身的义务违反性。[16]因此,在这两种不同的立场下,关于先前行为是否限于“违法行为”产生争议。在法益侵害说的立场下,只要先前行为具有产生构成要件结果的危险性,就肯定作为义务,也就是说合法行为也可能产生作为义务。例如在正当防卫的情况下,由于防卫人的防卫行为支配性地产生了构成要件结果,对于该结果防卫人具有作为义务。而在规范违反说的立场下,先前行为必须是违反义务的违法行为才能产生作为义务。因此,在正当防卫这一适法行为下,并不产生作为义务。很明显,以上关于先前行为范围的限定中,采规范违反说立场的认定范围要窄于法益侵害说。对此,有观点认为,诸如“支配”“紧迫”等这样的事实性的判断,实际上是混淆了“作为义务的判断”与“因果关系认定”两个不同的范畴,因为“义务并不是根据事实产生于任何经验的存在,而是产生于规范的分配”。[17]笔者赞同这一观点,“裸的危险”并不能产生作为义务,仅仅根据事实性的“支配”是不能当然推出作为义务的,它还需要一个“规范的分配”作为前提依据。在该依据下,先前行为的实行者产生了“去支配”的义务,如若因为没有支配事实的发展而产生了构成要件结果,对此结果将承担不作为的责任。至于什么是“规范的分配”这一问题,无疑核心在于解决“规范”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即“规范论”的问题,在此不予以过多展开,其更多的是价值层面(主要是法秩序)的考量。①对此有Rudolphi的“中心人物理论”、Jokbos的“阻止领域理论”、Herzberg的“防卫责任理论”等。参见陈文涛:《先前行为产生作为义务的根据及限定》,载《刑法论丛》,2017年第4卷,第446-447页。
(二)基于客观归责的转用
通过以上相关学说的概述,可以发现围绕“规范违反说”所建立的限定先前行为范围的方案,一般的违法行为、过失犯罪行为、故意犯罪行为均可以被纳入这一限定方案的范围之内,因为他们都符合“一个被法秩序否定的行为造成了刑法所保护法益之危险”这一认定依据。这一点可以通过客观归责的方法予以进一步认定,对此陈文涛博士将其归纳为以下几个条件:(1)先前行为突破了法所允许的范围;(2)先前行为制造的危险与行为基准的规范目的关联;(3)危险非属于他人的答责范围。[18]通过以上三个条件的限定,笔者认为这可借鉴至共犯脱离的情形中进行相同的考察。将其放在共犯脱离的情形下,对于符合以上条件的先前行为类型,自然可以通过该方案予以相同之限定,从而对基于“因果关系切断说”共犯脱离的构成要件进行适当“扩张”,使得原先不满足脱离条件者,也能够因不存在作为义务,而从共犯关系中脱离出去。因此,如果要符合这一构想,脱离前行为自然也要满足以上设定。但又因为在共犯脱离情形下,脱离前行为基本都是基于与其他参与者间的共谋而实行的一部分行为,特别是进入着手的实行行为阶段后,脱离前行为基本上都是突破了法所允许范围的行为,所以对于以上条件之(1)即无认定的必要。因此,像为了让侵害人A放手继续拽B的头发,被告人C与D、E、F等众人对A实施了反击行为,A放手后往后退的过程中,C、D仍然对A保持攻击状态并最终导致A摔倒在地造成重伤结果,B在一旁并未参与后续的追击行为但也没有制止这样的案例就没有必要放在共犯脱离的情形下予以讨论。②[日]最决平成6年(1994年)12月6日刑集48卷8号509页。因为这完全不符合条件(1)的限定,本案中B的前行为属于正当防卫行为,是法秩序所允许的行为,其并不因此产生阻止其他人的追击行为的义务。对此山口厚教授便认为该情形“不应放在在以存在作为义务为前提的‘共犯关系的解消’这一框架内解决,而是应以不以存在作为义务为前提的‘是否成立新的共谋’为必要”。[19]至此,可以肯定的是脱离者脱离前行为创设了法所不允许的风险时,自要肯定作为义务,因此满足这一条件的基本上就可以肯定脱离者负有避免结果发生的作为义务。但是,根据以上限定条件,其仍需接受接下来两个条件的考察,在全部满足后才能完全肯定其作为义务。
1.风险关联的考察
风险关联的考察,即考察脱离前行为制造的危险与行为基准的规范目的关联性,对此主要考虑的是刑法上的一般预防效果,即只有通过禁止法所不允许的行为来保护法益才是有意义的。[20]因此,在先前行为所制造的危险所违反的规范的保护目的之外的结果,是不受刑法保护的,也就不能归责于行为人。放在共犯脱离的情形下,需要考虑的便是脱离前行为所违反的规范的保护目的是否包含最终所发生之结果。如果不包含在这一规范保护目的下,即要否定避免该结果的产生作为义务。例如,甲乙两人共谋深夜时分入室盗窃丙家,甲在一楼盗窃,盗窃到一半时心生悔意独自离去,只有乙独自一人在二楼卧室完成了盗窃,但无意中惊醒了丙,乙遂匆忙离去,丙为了追回自己的财物独自追逐乙至室外,却因意外跌落楼梯,造成重伤。此情形下实际上产生了两个结果,一个是由乙独自一人完成的对丙的财物所有权的侵害结果以及丙自己身体损害结果,那么对于半路退出的甲需要对哪一结果的避免负有作为义务呢?很明显根据风险的目的关联判断,甲只需对丙的财物所有权的侵害负有作为义务,而丙自身身体损害结果,因为在甲脱离的前行为制造的危险所违反的规范(盗窃罪)的规范保护目的之外,因而对此无作为义务。
2.他人的自我答责之情形
考察他人(被害人或者第三人)的自我答责之情形,目的在于排除那些由于被害人自己(自我危害行为)或者第三人(介入第三人故意行为)的原由而阻断了先前行为风险实现的情形于先前行为作为义务的认定范围之外。因为在这样的情形下,先前行为所创设的风险实际上被他人所接管或者由他人另外创设的风险所阻断,在这样的情形下,先前行为不产生作为义务。[21]因此,在共犯脱离的情形下,如若最终结果的产生系由被害人自我的危害行为或者第三人的故意行为所造成的,脱离者脱离前行为不产生作为义务。但这里先前行为不产生作为义务,是对于被害人的自我危害行为以及在共犯行为人之外介入的第三人的故意行为不产生作为义务,而对于其他共犯行为人继续实行行为产生之结果是否产生作为义务则存有疑问。对此,有观点认为在存在教唆犯、帮助犯的场合,由于“正犯对犯罪法益侵害的事实处于答责的地位”,即满足了 “第三人故意地接管了危险”,因此仅实施了教唆、帮助行为的共犯人对正犯所创设的法益侵害危险并不具有救助的作为义务。这放在共犯脱离的场合下,在共同犯罪中脱离后,脱离者先前的教唆、帮助行为由于并不产生对于正犯创设之风险的作为义务,因此教唆犯、帮助犯的脱离仅仅只需从事实上进行考察,切断了物理、心理因果性即可。[22]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因为在限制正犯的概念下,教唆犯、帮助犯并未亲自实施构成要件行为,其可罚性与直接实施构成要件行为的正犯相比是虚弱的,得从离构成要件较近的正犯那里传导而来。[23]因此,在先前行为产生作为义务的问题上,共犯(狭义的共犯)与正犯之间有必要区别对待,以同两者在规范和事实上的构造相匹配。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在教唆、帮助的场合,如若否定了脱离者对最终侵害结果的作为义务,是否意味着其随时随刻都可以脱离?答案是否定的,在教唆、帮助的场合,脱离者虽然没有对最终结果产生的阻止义务,但是却有“解消此前引起的指向犯罪之实现的效果或作用”的义务(对受侵害法益间接的救助义务)。不切断因为教唆、帮助行为所加功于最终结果上的影响,同样要对最终结果的产生承担不作为责任 (不作为的教唆、帮助犯)。至于所谓“解消此前引起的指向犯罪之实现的效果或作用”如何解释这一问题,仍需予以明确。例如,在教唆的场合,施加于正犯的效果主要是心理性的内容,即使得正犯产生了犯罪的决意,那么,要切断这一效果,对于脱离的教唆犯而言,需要做的唯一途径想必就是使得正犯回心转意。[24]然而使得正犯回心转意本身就有阻止结果发生(间接的)这一层含义,但这并不是共犯脱离下需要考虑的问题,因为既然正犯已经回心转意,那么接下来他自己单独再创设之风险自然已经不属于之前的共犯关系中,其已经是一个新的单独的犯罪行为。
四、共犯脱离的具体认定
(一)问题的提出
沿着上文的认定思路,事实上,在共犯脱离之下,存在两种不同的脱离情形,一是共犯人主动从共犯关系中脱离;二是共犯人因为其他行为人基于新的共谋实施新的犯罪而被动脱离。对于前者,因脱离前行为创设的法益侵害风险产生了阻止犯罪结果发生的作为义务(教唆犯、帮助犯除外),要从共犯关系中脱离出去,就必须积极履行这一作为义务。而对于后者,因其他行为人基于新的共谋而实行了新的犯罪,因此脱离者先前行为产生的法益侵害风险被其他行为人新的犯罪行为所阻断,被脱离者对由此产生的法益侵害风险不存在作为义务,因此对这一结果不承担责任,从而实现了从共犯关系中的脱离。于是乎问题变成了如何去具体界定其他共犯人之行为是否基于新的共谋而实施的新的犯罪行为?如案例:韩某与张某甲、孙某共谋抢劫杀害被害人张某乙,为此孙某将张某乙租处的位置指认给了另外两名共犯韩某和张某甲,此外他还多次带领韩某和张某甲二人前往被害人住处蹲守,但都因张某乙未在家,抢劫未果。后当韩某、张某甲再次前往被害人住处实施抢劫时,孙某因故未去。而被害人则在回住处的途中被韩某、张某甲控制住,在成功取走被害人财物过后,被害人被挟持至一废矿井旁,韩某在车上强奸了她,随后两人将其用胶带缠住头部抛入矿井内,被害人最终受害身亡。①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中国刑事审判指导案例》(01卷刑法总则),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94-98页。该案中韩某等人在孙某不在的情况下实施了犯罪行为,这是否满足“基于新的共谋的新的犯罪”呢?对此该指导案例持的是“因果关系切断说”的思路,如认为“孙磊(孙某)在多次参与蹲守未遇张某后,虽然未再继续参与作案,但显然没有消除其物理帮助和心理帮助的影响。”可事实上韩某当时认为是“孙某通过其他非法途径获得了钱财,不想再抢劫张某乙了”,也就是说在韩某的心理层面已经“抛弃了”孙某,客观上孙某施加于后来再次的抢劫行为上的心理性效果已经擦除,事实上孙某已经被排除在了犯罪之外。但裁判理由依然要求孙某必须“采取措施防止共同犯罪结果的发生”,对这一点指导案例没有给出明确理由。对此,首先必须给出认定韩某等人是否是“基于新的共谋的新的犯罪”认定方法,其次才可以从先前行为的作为义务的视角下予以分析。
(二)对共谋的射程理论的借鉴
对于“基于新的共谋的新的犯罪”的认定,关键在于对“基于新的共谋”作如何理解。所谓“新的共谋”是区别于之前“旧的共谋”的,即可以理解为在原初旧的共谋的内容之外,形成了新的共谋内容。也就是说,新的实行行为超出了原初共谋的射程之外,创设了新的法益侵害风险。这一点,正好与共谋的射程理论相契合。因为所谓“共谋的射程”问题,即是指在共同犯罪中,发生了不在当初共谋的射程范围内之行为,而对于该行为引起之结果是否仍归于当初共谋射程范围内予以评价的问题。[25]对于不能归于原初共谋射程范围内予以评价的行为,对其所创设的法益侵害风险自然也不能归于原初行为(先前行为)下予以评价,因此被脱离者对后行为产生之法益侵害风险不具有作为义务。
因此,判断是否“基于新的共谋的新的犯罪”的问题被转化为认定“共谋的射程范围”这一问题。确定了共谋的射程范围后,在该范围之外的行为,自然便是“基于新的共谋的新的犯罪”。对此,需要具体考察共谋的射程范围的认定标准。而学界关于共谋射程范围的认定主要采取主客观两个维度进行认定:(1)在客观的维度考察基于当初共谋之内容是否付诸实行,实行行为的样态、状况是否保持同一性、连续性,即要保证整个共犯行为的进程不因时点、地点等客观条件的不同而发生很大改变;(2)在主观的维度考察的是基于原初共谋产生的犯意、犯罪动机以及目的是否发生很大改变,即要保持主观上仍是以共同的意思完成犯罪。[26]如若通过以上两个维度判断认定其他共犯人之行为处于共谋的射程之外,则当以肯定其行为乃为与原初行为不同的新的犯罪行为,即可评价为是“基于新的共谋的新的犯罪”。对此我们可以回到案例中,通过共谋的射程理论予以检验,以此来为该案例的判决结果寻找一合理的理论依据。
1.客观维度的检验
在客观上孙某虽然事实上被排除在了犯罪之外,但显然孙某完整地参与了共谋这一事实,且具有一定影响力。如他“提出将张某作为抢劫对象,参与购买作案工具,提议杀死张某”,无疑表明其在共谋阶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直接影响到了后来犯罪的走向。其次,原初的共谋内容引起最终结果的行为在接下来韩某等人继续实行犯罪的行为那里也得到了延续,比如被害人仍然是张某乙(被害人同一),实施的仍然是抢劫杀人行为(侵害的法益、行为样态同一),而且作案地点与原初共谋的计划一致,时间上也相隔不长(1个月左右),这表明与原初的共谋内容间具有同一性、关联性。再者,孙某本身虽然并没有直接参与引起结果行为 (抢劫杀人),但从前期参与预谋的内容来看,其在预谋阶段所创设的那种“支持、鼓励犯罪”的效果仍然存在于最终引起结果时韩某等人身上,其对引起最终结果的行为本身的参与程度不能轻易抹去。因此,综合以上各个方面的考察来看,后行为在客观上并没有超出原初共谋的射程范围。
2.主观维度的检验
对于该案,虽然客观上最终结果只是由于部分共犯的行为引起,但是孙某在此前并没有采取相应措施,如报警或者将此情况通知被害人等防止结果发生的措施,不过是任由事态继续发展,因此可以说韩某等人之后的抢劫杀人行为仍然是基于原初的犯意而实施,犯意具有同一性、持续性。其次,韩某等人原初预谋抢劫,目的乃在于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而最终引起结果之行为也是为的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因此两者间的动机、目的具有共同性。相反,对于韩某最后单独的强奸行为,则不具有这种共同性,即便原初共谋的内容中包含暴力行为,而韩某也基于这种暴力的压制(捆绑)而实现了自己的强奸行为,但仍应该以目的的不同而否定强奸行为处于原初的共谋射程范围之外。因此,孙某对此并无作为义务,无需承担责任。但对于在一旁的张某乙,对于韩某自己的强奸行为是否承担责任呢?对此需要从实现过限的角度予以解决,假如张某乙对此存在认识而在一旁负责望风,想必便具有成立强奸罪的帮助犯的可能了。再者,韩某等人后来实行的引起最终结果的行为(抢劫杀人)完全在孙某的可预测范围之内,综合以上各个方面后行为在主观上并没有超出原初共谋的射程范围。
(三)共同正犯的“正犯性”问题
以上,在经过主客观两个维度的考察过后,综合判定韩某等人实施的引起最终结果的行为并没有超出原初共谋的射程范围,因此孙某原初基于共谋行为所创设的法益侵害风险并没有被韩某等人的行为所阻断,因此他具有“防止共同犯罪结果的发生”的作为义务。但在共同犯罪的体系内,此处仍需要考虑的是对于孙某而言,由于在事实上其并没有亲自实施最终引起结果的行为,是否因此便可否定了其在共同犯罪中的正犯性?如若否定了孙某的正犯身份,那么其对最终引起结果的(抢劫杀人)行为便仅有成立帮助犯的余地。而按照上文的观点,帮助犯对于实行犯(正犯)所创设的风险是没有作为义务的,因此孙某并没有避免最终犯罪结果产生的义务。对此,该指导案例也持了相似的观点,在“裁判理由”部分,将孙某定性为帮助犯,以区别于实行犯、教唆犯。显然该案例将帮助犯仅仅定义为在事实层面为实行犯提供帮助的行为,但按其对于共同实行犯的定义“各共犯人之间按照分工,相互利用,相互配合,共同完成犯罪”而言,似乎孙某的行为也完全符合这一定义。因为其在原初共谋犯罪之时,即使没有一起参与实行犯罪,但也完全符合“出谋划策”这一共同实行犯的分工类型(任务分担型)。虽然该指导案例并没有引用实行共同正犯的概念,但在本质上该概念和共同实行犯并无二致。而关于共同正犯的成立,国内有学者认为需“客观上有共同实施行为的事实(行为的分担),主观上有共同的行为意思(意思的联络)”,[27]而所谓共同实施行为的事实是指分担了导致结果发生的重要行为,即并不要求行为人正真分担了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国外有学者基本持这一立场,如佐伯仁志教授便认为“行为人只参与了共谋,其他什么也没有做时,如果能够承认对共谋形成发挥主导型作用、对共谋的维持发挥了重要作用(附加因子),就能肯定共同正犯”,而这种类型便包括了以出谋划策代替出力的行为方式。[28]笔者赞同以上关于共同正犯的认定方案,将其放至该案例中进行检验,孙某虽然在事实上并没有参与最终这一决定性的构成要件行为(因故未去),但从孙某参与对于整个犯罪行动的共谋(共谋的射程之内),主观上具备了共同实行的意思联络 (如多次伙同韩某前去被害人住处蹲守),而且客观上其原先的共谋参与对之后共谋内容的维持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文有提到),结合以上两点无疑可以肯定其在共同犯罪中的正犯性。既然肯定了孙某的正犯身份,自然也就肯定了其对最终引起的法益侵害危险的作为义务。
四、结论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部分共犯行为人从共同犯罪中脱离的情形并不少见,但一般都被划入到了是否成立共犯中止的问题范围之内,共犯关系脱离之理论就鲜有出场的机会。而在理论内部,以因果共犯论为共犯处罚依据所构建的“因果关系切断说”一直是认定共犯脱离的有力学说。但是该学说存在着认定标准过于严格的弊端,本着解决这一弊端的目的出发,本文借助先前行为作为义务之理论,尝试从作为义务的方向上处理共犯脱离的边界问题。在这一方向上,客观归责理论的作用在于明确认定先前行为是否有作为义务。共犯脱离者的先前行为如若对其他共犯人的后行为创设的侵害结果具有作为义务,而脱离者又没有履行这一作为义务,那么他将对于其他共犯人造成的法益侵害结果承担不作为的法律责任。而关于“共谋的射程”理论的应用,则在于为先前行为产生作为义务中的第三人自我答责类型的具体认定构建明确的认定方法,如若其他共犯人的后行为处于原初共谋的射程之外,则脱离者的先前行为对此后行为造成的法益侵害结果不具有作为义务。通过以上方案,有关共犯脱离的认定问题在先前行为作为义务理论的借用下,经过客观归责理论的一步步筛选,排除了那些事实上存在因果关系,但是不存在避免法益侵害结果的作为义务情形。对于这些情形应认定从共犯关系中脱离出去,理应给予较继续实行完成犯罪行为的其他共犯人相对较低的法律评价。但究竟应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如未遂、中止或其他形式的法律评价,本文并没有展开。毕竟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尝试,上文的观点还是有些过于激进。对于法律责任的问题,还需进一步讨论,这也是笔者此后仍需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