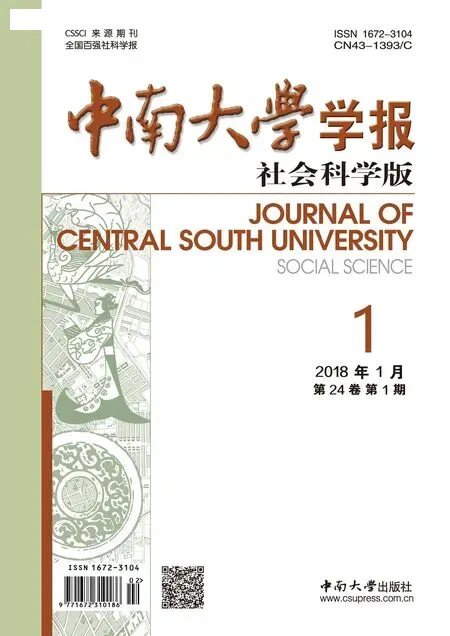全真道与马致远神仙道化剧的情节建构
王亚伟
全真道与马致远神仙道化剧的情节建构
王亚伟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300071)
马致远的神仙道化剧与全真道渊源颇深,其情节建构基于全真道的思想主张,其中的精妙之处尚未被真正认识。这些剧作的结构、线索、矛盾设计分别来源于全真道宣扬的“真行”“断酒色财气”“妻儿冤亲”思想。在此基础上,马致远根据杂剧剧情发展和作家主体抒情的需要,对这些道教修仙理论作了很多艺术化的处理,创造出了一种适合神仙道化题材的杂剧创作模式,并能于窠臼中出变化,赋予剧作很强的艺术表现力。揭示这些剧作在情节建构方面的特点,是认识马致远神仙道化剧的关键所在,有助于我们深入把握其中的艺术价值,进而充分理解马致远的艺术成就。
神仙道化剧;马致远;全真道;情节建构
马致远有“万花丛里马神仙”[1](167)之誉,其神仙道化剧在元杂剧中别具一格,是同类剧作中的典范,颇受后世瞩目。不过,长久以来研究者对这些剧作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思想主题方面,关于其艺术形式的探讨则尚显不足。即使有一些,也多着眼于曲词。至于剧情,论者往往粗陈大概,缺乏深入论析。如王季思说:“关目安排上的公式化倾向已较为明显地在马致远的戏曲里出现,特别是他的几个神仙道化剧。”[2]佘大平则认为,马致远神仙道化剧中“有不少关目情节安排得十分别致的好戏”[3]。他们虽然指出了这些杂剧在情节设计上的一些特点,但并没有对此进行深入探讨。
马致远神仙道化剧与全真道渊源很深,从情节建构方面考察这些剧作对全真道的吸收和发挥,有助于我们深入把握马致远以杂剧艺术处理全真道思想和故事的独特方式,充分认识其中的艺术价值。邓绍基说:“(神仙道化剧)的内容大抵是或敷演道祖、真人悟道飞升的故事,或描述真人度脱凡夫俗子和精怪鬼魅的传说。不管故事的具体内容和表现的角度有多么纷繁的变化,这些作品大都是以对仙道境界的肯定和对人世红尘的否定,构成它们内容上的总特点。”[4](46-47)在诸家对神仙道化剧的定义中,邓氏的界定最为贴切。基于此,本文讨论的作品主要有《岳阳楼》《黄粱梦》和《任风子》,共计3种。
一、依据“真行”思想架构的“度脱”模式
任何剧作都需要有与剧情相适应的结构来支撑并展开叙事。清代戏剧家李渔论剧将结构置于首位:“至于结构二字,则在引商刻羽之先,拈韵抽毫之始。如造物之赋形,当其精血初凝,胞胎未就,先为制定全形,使点血而具五官百骸之势。倘先无成局,而由顶及踵,逐段滋生,则人之一身,当有无数断续之痕,而血气为之中阻矣”[5](4)。这虽是针对当时剧坛重音律、轻结构的风气而发,但就叙事层面而言,结构之于戏剧确实至关重要,决定着剧情发展的总体方向。
马致远神仙道化剧在结构上的程式化特征十分明显,形成了适应于神仙道化题材的结构模式。对其结构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两大特点:① 均以神仙度化他人成仙为基本结构模式。如《岳阳楼》敷演吕洞宾度脱郭马儿,《黄粱梦》表现钟离权度脱吕洞宾,《任风子》讲述马丹阳度脱任风子。② 不同剧作可以通过剧中的人物关系连缀起来,形成了两条度脱链。为了方便叙述,这里以“→”来表示人物之间的度脱关系。《岳阳楼》:钟离权→吕洞宾→郭马儿;《黄粱梦》:东华真人(王玄甫)→钟离权→吕洞宾;《任风子》:王重阳→马丹阳→任风子。此外,马致远还有一部题为《王祖师三度马丹阳》的神仙道化剧,仅存剧目。《任风子》第一折马丹阳上场自报家门云:“贫道祖居宁海莱阳人也。俗姓马,名从义,乃伏波将军马援之后。钱财过万倍之余,田宅有半州之盛。家传秘行,世积阴功。初蒙祖师点化,不得正道,把我魂魄摄归阴府,受鞭笞之苦。忽见祖师来救,化作天尊,令贫道似梦非梦,方觉死生之可惧也。因此遂弃其金珠,抛其眷属,身挂一瓢,顶分三髻。按天地人三才之道,正一髻受东华帝君指救,去其四罪,是人我是非;右一髻受纯阳真人指教,去其四罪,是富贵名利;左一髻受王祖师指教,去其四罪,是酒色财气。方成大道,正授白云洞主,丹阳抱一无为普化真人。”[6](38)这极有可能就是《王祖师三度马丹阳》的大致剧情,即敷演王重阳度化马丹阳的故事。综合以上人物关系,可构成两条度脱链:“王玄甫→钟离权→吕洞宾→郭马儿”和“王重阳→马丹阳→任风子”。可见这些作品主要表现度与被度,其基本结构可称为“度脱”模式。
马致远神仙道化剧的“度脱”结构设计是以全真道宣扬的“真行”修仙理论为根据的。全真道自丘处机遇见成吉思汗,逐渐发展至鼎盛局面,道观和信众遍布北方大地。在蒙古灭金的战争中,全真道积极结纳北方文人,一度成为文人的庇护所。马致远出生于1250年前后,此时全真道正处于鼎盛期。而他生长的大都更是全真道的发展中心,自幼必定耳濡目染。在他青少年时期,全真道先后经历了几次释道论辩的失败,政治上一再受挫,其发展也逐渐转衰。尽管如此,全真道在北方仍是实力最强的道派,在文人间的影响依旧很大。从马致远的神仙道化剧中可以看出,他对全真道故事和学说谙熟于心。剧中的主要人物大多是全真道祖师或道士,除了全真道四祖刘海蟾外,初祖王玄甫、二祖钟离权、三祖吕洞宾、五祖王重阳均有涉及。《任风子》中的神仙马丹阳就是马钰,乃王重阳的七大弟子之一。可见这些作品表现的是全真道故事,而非佛教或道教其他派别。
深入这些剧作的“度脱”结构,不难发现剧中神仙积极主动地度化他人,与全真道宣扬的“真行”思想具有相似性。全真道倡导“三教一家”,“在继承钟吕内丹说基础上吸收大乘佛教普度众生及儒家济世的思想”[7](195),将源于佛教的“度脱”思想纳入自身的理论体系,提出了“真行”,并将其视为修仙的重要内容。其创始人王重阳说:“若要真行者,须是修仁蕴德,济贫拔苦,见人患难,常行拯救之心,或化诱善人,入道修行。所行之事,先人后己,与万物无私,乃真行也。”[8](335)可见,“真行”大致包括济危救困和度人入道两个方面,整体上强调通过入世实践来提升道德修养,达到与万物无私的神仙境界。而度化之事在全真道历史中确有其事,如《重阳分梨十化集》专门记录了王重阳度化马钰夫妇的故事和诗词,王重阳“每十日索一梨,分送于夫妇,自两块至五十五块。每五日又赐芋、栗各六枚。及重重入梦,以天堂地狱十犯大戒罪警动之。每分送则作诗词,或歌颂,隐其微旨”[9](383)。这样的故事颇有传奇色彩,但王重阳诱化马钰入道确有其事。考察全真道道士诗文集,其中有大量劝人入道的诗词,也是这一思想的体现。马致远神仙道化剧中的神仙与全真道关系密切,他们积极度脱他人的行为,是“化诱善人,入道修行”的具体表现,其指导思想显然来源于全真道的“真行”修仙理论。
马致远在杂剧创作中借鉴“真行”思想,并非生搬硬套,而是经过了精妙的艺术加工。将剧中的“度脱”模式和全真道的“真行”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两点不同:① 实践的主体不同。全真道“真行”的实践主体是修道者。修道者通过修习全真道的修仙理论,追求得道成仙。而剧中的实践主体却是得道者(神仙)。也就是说,“真行”在剧中的表现不再是成仙的必经阶段,而成为剧作家塑造神仙形象的一种方式。② 方式和目的不同。全真道的“真行”是修道者通过助人或度人来实现自己的成仙理想,剧中表现的却是得道者利用种种手段诱惑、威逼他人出家修道,最终使其位列仙班。可见通过对全真道“真行”思想的发挥,剧中的神仙反而成了“真行”的实践者,在道化活动中表现出了强烈的主动性。他们苦口婆心地劝道,甚至不惜破坏被度者安定的世俗生活,诱导其抛妻杀子,逼迫其出家修道。同“真行”主张的“化诱”相比,这种纠缠般的点化、威胁式的度脱显得十分极端,与“修仁蕴德,济贫拔苦,见人患难,常行拯救之心”严重背离。但是经过艺术处理,剧中塑造出了对改变他人命运具有高度热情和强烈愿望的神仙形象,完全颠覆了人们对道教神仙潇洒飘逸的刻板印象。
支撑这种神仙形象的正是剧中创造的“度脱”结构模式,也是一种新的成仙模式。考察元代以前的仙话,凡人成仙的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自我修炼成仙,二是寻仙得道,三是遇仙点化。前两种强调的是修道者的主动性,第三种则侧重偶然性。这在《列仙传》《神仙传》等神仙传记中有集中体现。如《神仙传》中记载古强追随李阿修仙的故事:“有古强者,疑阿是异人,常亲事之。”[10](87)刘政为了学道,“勤寻异闻,不远千里,苟有胜己,虽奴客必师之”[10](130)。与剧作密切相关的全真道故事也是如此,如“甘河遇仙”讲的就是王重阳得道的故事:“(王重阳)于甘河镇醉中啗肉,有两衣氈者继至屠肆中。其二人形质一同,真人惊异,从至僻处虔祷作礼。其二仙徐而言曰:此子可教矣。遂授以口诀。”[11](114)这些成仙模式对求仙者的设定往往是十分主动的,神仙则冷静处之,相对被动。而剧中恰好相反,被度者起初几乎没有求仙热情,神仙度化他人的愿望却极其强烈。相较而言,“度脱”模式中的神仙与被度者对比鲜明,矛盾激烈,因而更具艺术表现力。
二、围绕“断酒色财气”安排情节线索
从内容上来讲,神仙道化剧至少应该包括两点:其一,道化活动的主体必须是道教人物;其二,表现的应是道教人物以道法度脱他人的故事。二者缺一可。马致远神仙道化剧中,神仙度化他人所采用的道法有两种:一是神仙法术;二是以“断酒色财气”为核心的修仙理论。神仙法术是激化戏剧矛盾和丰富戏剧艺术表现的重要手段,而“断酒色财气”则是设计剧情发展线索的重要参照。
“断酒色财气”即戒除嗜酒、好色、贪财、逞气四事,也是全真道的基本主张。全真道追求的心性炼养是以宗教禁欲为基础的,“断酒色财气”正是其禁欲思想的体现,也是修道者必须严格遵守的戒行。王重阳说:“凡人修道,先须依此一十二个字,断酒色财气、攀缘爱念、忧愁思虑。”[12](372)马钰说:“酒为乱性之浆,肉是断命之物,直须不吃为上。酒肉犯之犹可恕,若犯于色,则罪不容诛矣。何故?盖色者,甚于狼虎,败人美行,损人善事,亡精灭神,至于殒躯,故为道人之大孽也。”[13](403)马钰明确指出酒、色等不良嗜好对人的危害很大,其中尤以犯色戒之罪孽最为深重。因为酒、色、财、气有损修仁蕴德,不利于性命双修,所以全真道视其为修道成仙的障碍。相比全真道那些令人费解的内丹修炼理论,“断酒色财气”的优势在于直指人性,十分具体,阐释的空间也很大,容易在不同阶层得到推广。往浅了说,“酒色财气”是普遍存在于个体身上的不良习惯;往深了说,“断酒色财气”又能与全真道的修仙理论很好地融为一体。杂剧在古代的受众趋于多元化,有王公贵族,有文人雅士,也有平民百姓,将宗教思想引入杂剧艺术首先必须要考虑受众能否接受的问题。而“断酒色财气”不像有的宗教理论那样晦涩、空洞,很容易落实到剧情上,也容易被观众和读者接受。
马致远神仙道化剧围绕“断酒色财气”设计剧情发展线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酒、色、财、气各作一事,被度者经过神仙度化,一一断除,最后得道成仙。如《黄粱梦》第一折钟离权说:“这人俗缘不断。吕岩也,你既然要睡,我教你大睡一会,去六道轮回中走一遭。待醒来时,早已过了十八年光景,见了些酒色财气,人我是非,那其间方可成道。”[6](191)剧情设置先以吕岩统兵出征前饮酒吐血表现“断酒”,又以发现妻子偷情表现“断色”,再以因受贿事发而被罪表现“断财”,最后以家庭破裂、迭配牢城遇祸表现“断气”。四事断除,吕岩终于入道成仙。另一种是杂糅酒、色、财、气,着重表现其中某些部分。《岳阳楼》和《任风子》即属此类。如《岳阳楼》也宣扬“断酒色财气”,吕洞宾唱:“俺那里白云自在飞,仙鹤出入随。……这壁银河织女机,那壁洞中玉女扉,怎发付你那酒色财气。”[6](180)自楔子至第四折的剧情围绕“断色”和“断气”展开,将其杂糅于郭马儿与吕洞宾的纠葛之中,以“杀妻”和“寻仇”进行具体表现。可见这些剧作对全真道“断酒色财气”的处理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并非套用一个模式。
在不影响剧情发展的情况下,马致远也会跳出“断酒色财气”的思想窠臼,积极打破宗教思维的限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剧中设计的“神仙醉酒”情节。剧中主要表现被度者“断酒色财气”而成仙,但是作为度人的神仙却是一副醉酒形象,完全不符合剧中宣扬的修仙思想。如《岳阳楼》表现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第一醉”和“第二醉”分别在剧作的前两折,“第三醉”是全剧的叙事重心,以楔子、第三折和第四折来着重表现。剧中的神仙吕洞宾宣扬“断酒”,自己却醉酒,这正是剧作家马致远对全真道“断酒色财气”思想的突破。考察《岳阳楼》本事,剧中的“三醉”是马致远改编的结果。据宋人范致明《岳阳风土记》载:“岳阳楼上有吕先生留题云:朝游北越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入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14](8)元代赵道一修撰的《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吕岩”条载:“尝题岳阳楼诗云:朝游北岳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入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15](515)而剧中吕洞宾宝剑上有诗云:“朝游北海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醉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6](177)通过对比可发现两处不同:① “北海”与“北越”“北岳”不同。其实,“北海”在宋代文献中比较常见,如阮阅《诗话总龟》增修卷之四十四、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十,以及《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二十七所载均为“北海”。马致远沿用“北海”,并不难理解。② “三醉”与“三入”不同。宋代文献引用此诗均为“三入”,并没有“三醉”的记载。在元代道教文献中,同样也作“三入”。可见,将“三入”改为“三醉”应是马致远有意为之。
经过改编,“醉酒”与“断酒”构成了神仙形象塑造上的一组矛盾,其中渗透着作家的主体情志和生命体验。马致远在剧中将神仙之醉和俗人之醉区分得十分清楚,他推崇的是神仙之醉。《岳阳楼》中的神仙吕洞宾唱道:“想那等尘俗辈,恰便似粪土墙。王弘探客在篱边望,李白扪月在江心丧,刘伶荷锄在坟头葬。我则待朗吟飞过洞庭湖,须不曾摇鞭误入平康巷。”[6](160)在神仙眼中,王、李、刘等人乃“尘俗辈”“粪土墙”,他们醉酒各有缘由,或嗜酒如命,或避乱远祸,或借酒消愁,这正是剧中神仙所唾弃的。与之不同,剧中的神仙之醉象征着超脱世俗的人生境界。如《黄粱梦》中钟离权唱:“常则是醉醺醺,高谈阔论,来往的尽是天上人。”[6](189)《岳阳楼》中吕洞宾唱:“你看承我做酒布袋,请看这药葫芦;不是村夫,还有三卷天书。”[6](183)神仙之醉不是烂醉如泥,恰恰是高度的清醒,是彻悟宇宙真理的体现。
其实,这也是马致远个人精神状态的反映,蕴含着作家的主体情志。酒在马致远的生命中是一种特殊的存在,醉酒不仅体现了他内心的挣扎,也是他获得精神超脱的方式。在他现存的115首小令中,直接写到“酒”“醉”“饮酒”的有34首。如[双调•庆东原]《叹世》云:“拔山力,举鼎威,喑呜叱咤千人废。阴陵道北,乌江岸西,休了衣锦东归。不如醉还醒,醒而醉”,“三顾茅庐问,高才天下知,笑当时诸葛成何计。出师未回,长星坠地,蜀国空悲。不如醉还醒,醒而醉”。[16](66)这组感叹历史人物悲剧命运的小令共有六首,均以“不如醉还醒,醒而醉”结尾。醉醒之间,正是作者于人生苦痛中体会到的超脱境界。又如[双调·清江引]《野兴》(其四)云:“天之美禄谁不喜,偏则说刘伶醉。毕卓缚翁边,李白沉江底。则不如寻个稳便处闲坐地。”[16](70)从“则不如寻个稳便处闲坐地”不难体会到作者超越功利、超然物外的生命境界。所以说,剧中设计的神仙醉酒情节,不仅突破了宗教仪轨的束缚,而且丰富了戏剧矛盾,提升了剧作的思想性。
三、发挥“妻儿冤亲”思想激化戏剧矛盾
马致远现存三部神仙道化剧中均有“杀亲”情节,并将“杀亲”视为被度者证道的必经阶段。这样的情节设置违背人性,悖逆伦常,在宗教和文学中极为鲜见,马致远却以之为激化戏剧矛盾的重要手段。现将剧作中的“杀亲”情节作一简要介绍:
《岳阳楼》中的“杀亲”主要体现在“杀妻”上。此剧用很大篇幅来表现“杀妻”,自楔子至第四折均与之相关,是剧作矛盾的总爆发。如“[仙吕·赏花时]……(正末云)郭马儿,我与你这一口剑,要些回答的礼物。(郭云)可要什么回奉的礼物?(正末唱)要一颗血沥沥妇人头。”[6](175)剧中的正末即神仙吕洞宾。经过一番索妻报仇的斗争,郭马儿最终得度。《黄粱梦》中“杀亲”主要体现在“杀子”上。剧中设置“杀子”情节主要是为了使被度者吕岩(即吕洞宾)断除“酒色财气”中的“气”。第四折中吕岩的孩子被人摔死:“[叨叨令]……(做丢男俫在涧科)(洞宾云)可怜见!(正末唱)这厮死尸骸也济得狼虫饿。(拖女俫科)(洞宾云)留下这个小的者!(正末唱)至如将小妮子抬举的成人大,也则是害爹娘不争气的赔钱货。不摔杀要怎么也波哥,不摔杀要怎么也波哥?觑着你泼残生,我手里难逃脱。”[6](209)以上两剧中的“杀亲”尚为神仙借法术幻境所为,而《任风子》中任屠的儿子却是被其亲手摔杀的:“[四煞]……(旦云)任屠,你看这孩儿。(正末唱)将来魔合罗孩儿,(做摔科)知他谁是谁。(旦哭云)任屠,你怎么把孩儿摔杀了!(正末唱)我见他揾不住腮边泪,休想他水泡般性命,顾不的你花朵似容仪。”[6](54)面对这样的场景,神仙马丹阳不仅没有劝阻,反而说:“此人省悟了。菜园中摔死了幼子,休弃了娇妻,功行将至。再教他见妻子恶姻缘,然后引度他归于正道,未为迟也。”[6](55)经历了“杀亲”,被度者无一例外地得度成仙。
考察全真道的修仙理论,并没有“杀亲证道”之说。相反,全真道极力反对杀生。王重阳对修道者有明确要求:“第一先须持戒,清净忍辱,慈悲实 善”[17](394),“大凡学道,不得杀盗、饮酒、食肉、破戒犯愿”[12](372)。杀生尚被禁止,“杀亲”这种严重悖逆人伦的行为当然不会被允许。所以说,在全真道修仙理论中,“杀亲”与“证道”是相互矛盾的。
全真道虽未提出“杀亲”,但其宣扬的“妻儿冤亲”却是剧中“杀亲”情节的思想基础。全真道采取道士出家修行的制度,对世俗家庭生活持反对态度。在全真道文献中有很多关于“妻儿冤亲”的说法,如全真道尊崇的吕洞宾有诗云:“妻子冤亲还了了,死生途路得休休”[18](261),“养得儿形似我形,我身枯悴子光精。生生世世常如此,争似留神养自身”[18](263),“一世人身万劫修,何须苦苦为家愁。到头付与儿孙计,着甚来由作马牛”[18](261)。吕洞宾将妻子儿女置于个人的对立面,劝人抛妻舍子,选择出家修行,炼养身心。这种思想后来被全真道全部接受,在全真道道士诗文集中普遍存在。如王重阳说:“家人便是烧身火,干了泥团却变尘”[8](287),“儿非儿,女非女,妻室恩情安可取。总是冤家敌面仇,争如勿结前头苦”[8](323)。王重阳将夫妻关系、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定性为“冤家敌面仇”,劝人勿种夫妻儿孙之苦因,以免最终得受苦果,引火烧身。刘处玄《上平西》云:“恋恩亲,恩生害,死难逃。气不来、身卧荒郊。改头换面,轮回贩骨几千遭。世华非坚如石火,火宅囚牢。……他年蜕壳朝贤圣,名列仙曹。”[19](579)更加明确地借佛教三世轮回和因果报应之说来解释家庭内部关系,将家庭视为火宅和修道成仙的巨大障碍。马钰《渔家傲·自觉》云:“梦见娇妻称是母,又逢爱妾还称女。因为前生心不悟。心不悟,改头换面为夫妇。”[20](494)由于“心不悟”,不能斩断家庭因缘,所以又堕轮回,再受家庭带来的苦。因为“心不悟”,所以身陷火宅,不能成道。
马致远本人受全真道“妻儿冤亲”思想的影响很深。其散曲[南吕·四块玉]《叹世》云:“子孝顺,妻贤惠。使碎心机为他谁,到头来难免无常日。争名利,夺富贵,都是痴”,“带月行,披星走。孤馆寒食故乡秋,妻儿胖了咱消瘦。枕上忧,马上愁,死后休”,“风内灯,石中火。从结灵胎便南柯,福田休种儿孙祸。结三生清净缘,住一区安乐窝,倒大来闲快活”。[16](59−60)作品中表现出了对婚姻家庭的厌倦和排斥,甚至予以彻底否定,与全真道的主张十分一致。虽然我们无法确定这是作者的一时激愤之辞,还是他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但由此可见马致远的确受到了全真道“妻儿冤亲”思想的影响。在剧中,他将妻儿、家庭视为出家修道的障碍,将“杀亲”作为被度者省悟的标志,显然吸收了自己熟悉的全真道修仙理论。
马致远神仙道化剧对“妻儿冤亲”思想的处理同样是在吸收的基础上作了改造,并使其适应了剧情发展的需要。这些作品并没有单纯地表现“妻儿冤亲”,而是将其极端化,发挥为“杀亲”情节,并与“断酒色财气”相结合,融于剧情之中,成为激化戏剧矛盾的重要手段。在剧中,“杀亲”的执行者多为被度者。他们原本都是平凡之人,对世俗生活有着很深的眷恋。《黄粱梦》中的吕岩热衷于功名利禄,《岳阳楼》中的郭马儿和贺腊梅一心想生育儿女,《任风子》中的任屠经营的屠宰生意也十分兴旺。对于他们而言,家庭并不像火宅,妻儿也不是冤家。但在神仙看来,这些被度者有“神仙之分”,有得道成仙的可能性。只有使他们真正意识到“酒色财气”有百害而无一益,才能助其位列仙班。而世俗家庭正是他们的火宅囚牢,妻子儿女更是他们修道的最大障碍。因此,神仙必须通过道化活动使被度者彻底放弃家庭。于是,在“仙”与“俗”的对立中激发出了一系列矛盾。当剧情发展至“杀亲”,全剧达到了高潮,被度者的家庭遭到彻底破坏,神仙终于铲除了被度者成仙的最大障碍,所有矛盾至此也得到了最终解决。以《任风子》为例,第一折写马钰为了度脱甘河镇屠户任风子,将一方之地都化的不食荤腥,严重影响了任屠的生意,剧作的矛盾由此而起。第二折中矛盾进一步发展,任屠毫无出家修道之意,决心杀死马钰,不料却困于马钰设下的法术幻境之中。在生死面前,任屠只好求饶,选择出家。至此,之前积累的矛盾貌似已经解决。但是第三折又引出了任屠妻子,将妻儿家庭这一修道的最大障碍摆在了任屠面前,剧作的高潮出现。虽然妻子苦苦哀求,但是任屠还是决意出家。于是,他以休妻杀子来表达自己与世俗生活的彻底决裂和选择修道的决心。出家的最大障碍被消灭后,所有的矛盾也就得到了解决。第四折则写任屠经过一番心性修炼,真正认识到了“妻子恶姻缘”,终于得道成仙。由此可见,“杀亲”是神仙道化活动中相当关键的一个环节,具有激化戏剧矛盾的重要作用。
综上可知,全真道对马致远神仙道化剧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神仙道化剧在题材选择上相对狭窄,剧作主题十分鲜明,神仙道化活动的结果也毫无悬念,因而比较容易流于枯燥乏味的宗教说教,或者过度依赖于法术表演。马致远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从来不生搬硬套全真道教义和故事,而是根据剧情发展和主体抒情的需要,对其进行适合杂剧艺术体式和神仙道化题材的艺术处理。从元代杂剧艺术本身来看,马致远神仙道化剧的艺术贡献在于创造了一种适应于神仙道化题材的创作模式,而且能于窠臼中出变化,综合多种素材,灵活处理剧情,极大提升了这类剧作的艺术表现力,使其成为元代剧坛上一颗独特而又璀璨的明珠。
[1] 中国戏曲研究院.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二)[M].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9.
[2] 王季思. 元人杂剧的本色派和文采派[J]. 学术研究, 1964(3): 73−90.
[3] 佘大平. 马致远杂剧的艺术特色[J]. 江汉大学学报, 1993(4): 77−81.
[4] 邓绍基. 元代文学史[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5] 李渔. 闲情偶寄[M]. 单锦珩校点.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
[6] 王季思. 全元戏曲:第2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
[7] 卿希泰. 中国道教思想史: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8] 王重阳. 重阳全真集[C]//张继禹. 中华道藏:第26册.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4.
[9] 王重阳. 重阳分梨十化集[C]//张继禹. 中华道藏:第26册.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4.
[10] 葛洪.神仙传校释[M]. 胡守为校释.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11] 李道谦. 甘水仙源录[C]//张继禹. 中华道藏:第47册.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4.
[12] 王重阳. 重阳教化集[C]//张继禹. 中华道藏:第26册.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4.
[13] 王颐中集. 丹阳真人语录[C]//张继禹. 中华道藏:第26册.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4.
[14] 范致明. 岳阳风土记(据古今逸史刊本影印)[M]. 台北: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6.
[15] 赵道一.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C]//张继禹. 中华道藏:第47册.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4.
[16] 瞿钧编注. 东篱乐府全集[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0.
[17] 王重阳. 重阳真人金关玉锁诀[C]//张继禹. 中华道藏:第26册.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4.
[18] 吕洞宾. 纯阳真人浑成集[C]//张继禹. 中华道藏:第26册.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4.
[19] 刘处玄. 仙乐集[C]//张继禹. 中华道藏:第26册.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4.
[20] 马钰. 渐悟集[C]//张继禹. 中华道藏:第26册.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4.
Quanzhen School and the plot constructionof Ma Zhiyuan’s immortal drama
WANG Yawei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 Zhiyuan’s immortal Taoist drama and Taoism. These dramatic plot constructions ar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Quanzhen School, whose subtleties, however, have not yet been truly recognized. The structure, clues and contradiction of these drama are derived from the thought of “Zhen Xing”, “Quiting alcohol, sex, money and anger” and that “family members are enemies”. According to the plot development and the lyric needs of writers, Ma Zhiyuan made some artistic treatment of these Taoist theories. Finally, he created a kind of drama creation model suitable for immortal theme, and constantly broke through the old plot, giving the drama a strong artistic expression. Reveal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plays in the plot construction is the key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mmortal and immortal drama.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reveal the features of plot construction in these plays, and also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Ma Zhiyuan’s immortal drama. It helps us grasp the artistic value of these dramas, and then fully understand Ma Zhiyuan’s artistic achievements.
immortal drama; Ma Zhiyuan; Quanzhen School; plot construction
[编辑: 胡兴华]
2017−09−18;
2017−12−29
王亚伟(1989—),男,山西运城人,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元代文学,宗教与文学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18.01.024
I237.1
A
1672-3104(2018)01−018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