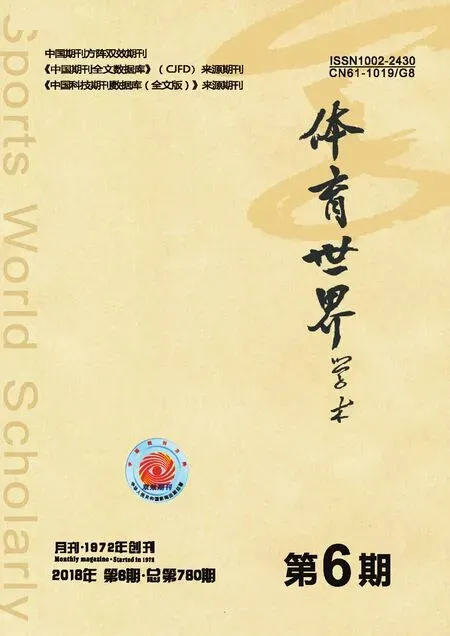娱乐与启蒙:普通大众和知识精英对全国运动会的不同反应
——以20世纪30年代全国运动会为考察中心
陈明辉 黄传昶 孙于婷
1928年底,以蒋介石集团为主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基本统一全国。但是,这种“大一统”只是表象,中国依然是派系林立,军阀割据,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始终未能建立。在这种背景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在党国草创之初即20世纪30年代,通过各种途径建立中央权威、塑造国家认同。全国运动会(以下简称“全运会”)这一颇具影响力的全国性大型体育活动也被纳入国民党政府的控制之下,并以之作为塑造政治权威,展示政党、国族观念及教化、规训民众的重要工具。当然,这只是国民党政府一厢情愿的想法,社会对此是否认同、在多大程度上认同则有待考察。因此,本文从普通大众和知识精英的视角重新审视20世纪30年代的三次全运会,即1930第四届全运会、1933年第五届全运会和1935年第六届全运会,展示全运会的多元面相。
1.“凑凑热闹,看看玩玩”:普通大众的娱乐心态
与近代博览会所具有娱乐功能一样,对普通大众而言,全运会最重要的功能是近代都市休闲、娱乐的新舞台和新空间。
运动会这种新式的观赏性景观进入中国之初,就因其竞技性、充满动感和悬念,迎合了百姓“看热闹”的娱乐心态。20世纪30年代所举办的三届全运会分别以杭州、南京和上海三大都市为依托,大有全民“嘉年华”之势。1930年在杭州举办的第四届全运会,观者如潮:“大会开幕以来,看客之多,真是空前未有!……就连虬江静土庵中的东海和尚……看得哈哈大笑,喜逐颜开。和尚是一尘不染,四大皆空,今竟能引动和尚,当不怪别人的狂热。”
第五届、第六届全运会均定于双十节举办,各界放假一天。因此,这两届全运会更是热闹非凡。以第六届全运会为例,开幕式“完全免费,任人参观”,场面极为热闹。“各界民众暨各学校团体到场参观者,共不下三十万众人,会场内外,行人如织、万头攒动,诚属空前之盛举。”据《申报》统计,第六届全运会期间,参观观众超过10万人以上的天数,就有5天。
民众对全运会“狂热”之情,最直观的写照就是因争相赶往全运会会场而导致公开汽车站拥挤的场景:“八时起,公共汽车、火车无不客满,拥挤不堪,气力较小者有候至数小时尚无上车者,其热闹可知。”面对蜂拥赶往运动场的观众,“南京……并没有一只汽车停留着,街头的野鸡汽车,虽然增高了五倍价格,而也是座上客常满奔驰着,马车和人力车也是每一只都有人占据着,而街道的两旁还涌流着人的巨潮。”数以万计的观众,挤公交车而不得的焦躁乘客,繁忙的出租车,伺机而动的“野鸡”汽车,运动场外拥挤的交通状况,正是民众对全运会“狂热”的侧面写真。
“大会参观人士,因慕名各地选手之技术而来者,固属多数,但为凑凑热闹,看看玩玩而来的,亦属不少。一些冬烘先生和乡下老太太,向来不知体育运动为何物,对于田径、球类虽不生好感,也并不反对”,只是“凑凑热闹,看看玩玩。”
而全运会中的赏玩因素,也足以满足普通百姓的“热闹”、“玩玩”的需求。除了竞争激烈的体育赛事外,全运会中也安排了国术、飞机等表演项目,以增加观赏性。第六届全运会时,明星影片公司经全运游艺会的邀请,在市中心区体育场举行“破天荒之明星歌咏夜”,这在中国“尚属创见”。可见,全运会已经自觉地将现代都市娱乐元素吸纳其中。对大众而言,全运会吸引他们的也正是此种新鲜、热闹的娱乐元素。
视全运会为重要娱乐盛会的,不仅仅是普通大众!随着新兴传媒力量的兴起,各种报纸、杂志、影视公司也积极参与到消费全运会的行列。经过现代传媒的包装,全运会作为重要的媒体事件,成为公众消费的重要对象。第五届全运会期间,全国各大媒体纷纷到场报道:“上海之申报、时事新报、天津益世报、北平之世界日报、南京之民生报……荒凉土原,一跃为舆论中心。”除各大报纸外,一些影视公司也将新奇、热闹的全运会作为吸引大众的重要的素材。上海明星影片公司、联华影业公司及南京东方影片公司三家就曾参与第五届全运会影片的拍摄,并以此为素材制作有声电影。
综上可见,普通大众争相参观全运会的目的,并非基于对体育之于国族存亡意义的深刻理解,也未打算去运动场接受精英所预想的道德教化,而是怀着“看热闹”的心态走进运动场,感受全运会的新奇、热闹。
2. “从运动场上培养国民的政治道德”:知识分子对全运会的期望
面对多数普通大众视全运会为娱乐的状况,知识精英甚是忧虑。时人撰文言,全运会“关于国计民生,有何贡献裨益?……煌煌开幕典礼,结果一场儿戏,谁复关心此日,正是国庆双十。”在文章作者看来,全运会虽然热闹非凡,但却不能引起人们对民族、国家福祉的关注,终不过是场“儿戏”。类似的担心同样出现在第六届全运会中——“上海空前的本届全运会开幕了,我们的老爷少爷们大可以换点新鲜刺激受受。不过,但愿在兴高采烈躬逢盛举之余,放眼四顾,看看四伏的当前危机。”两位论者的论调基本相同,都认为全运会新奇、热闹的娱乐氛围,与现实中国族危亡的形势格格不入。
与普通大众视全运会为大众娱乐迥异的是,知识精英更多地将全运会与国家命运相关联,视之为宣扬身体改造、教化民众及塑造民族精神的场所。
第五届全运会开幕当日,罗家伦在《中央日报》撰文强调,“在运动场上训练国民的政治道德”,即“第一要能恪守规律,在大众监视下,做公开的竞争。第二失败了要能坦白承认失败,不可怨天尤人,甚至以不正当手段谋报复”。与罗家伦以全运会“培养国民的政治道德”的期望相似,王世杰在第六届全运会欢迎辞中也着重强调国民精神的培养:“一、严守正当竞争的信念。二、充分表现团体合作的能力”。王正廷对第六届全运会的四点展望——“有恒心”、“体育运动之精神”、“发扬国光”、“强健国民”,亦是注重全运会的教化功能,而只字不提全运会的娱乐功能。以“坚韧”、“团结”、“竞进”等作为全运会冀望的表述屡见于当时的报刊。可见,知识精英对全运会的期望,更多围绕“道德”、“精神”、“国家”等层面展开,较少强调全运会的娱乐面相。
因此,普通大众只看热闹的娱乐心态令知识精英大失所望:“我们观众的体育知识太肤浅……他们去参观运动会,好像上海人去看赛狗跑马似的,根本不懂体育的意义,也没有特别的爱癖与嗜好,只把运动会当游戏消遣的场所。”
并且,全运会中若“未改良戏院”般混乱的秩序也与知识精英视运动场为文明、进步的理想大相径庭:“观众台上小贩太多,小贩到看台售货,既碍视野,又多呼声,几使人有入不改良的戏院之感慨” 。第四届全运会更是纠纷叠出:“大会办事员闹,新闻记者亦闹,即居公正人地位之裁判员亦闹;运动员大打出手,观众亦大打出手,为此庄严之大会留下不少污点”,有些观众更“因争坐而动武……血流满面。”这些问题之所以纳入精英的视野,背后其实都蕴含着某种价值评判——运动场为进步、文明空间,全运会为重要启蒙工具的预设。
也有论者从普及体育、国族兴亡的角度关注全运会。通过全运会这种公开仪式推动整个社会对体育的认知、普及,进而实现保国保种的夙愿,也是当时知识精英大力提倡全运会的另一缘由。知识精英希望以全运会达成“提倡体育普遍化”之目的,“深望此次全运会,能予国民以优良印象,增进人民爱好体育之兴趣,使全国人民均以运动为唯一娱乐,以达到强种救国之目的。”值得注意的是,此文虽注意到全运会的娱乐面相,但却并未以普通民众的思维来看待娱乐,而是采取比较功能的态度从国族存亡的高度来定义娱乐的价值。
与此逻辑相同,戴季陶在第六届全运会祝辞中重申了娱乐与国族之间的关联,“运动大会之目的,在于强种保国,而其道实在身心并重,术德双修,使从事运动与参观运动者,皆得自然之乐,生油然之兴,则其事乃可大可久,其益能实能多。”
可见,对于知识精英而言,全运会其实是重申民众身体之于国族意义,通过普及体育进而规训、改造民众身体以应对民族危机的重要宣传舞台,而全运会中潜在的娱乐因素也往往被功能性地理解为“强国保种”的工具。
3. 结语
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全运会,知识精英更多的是以启蒙者的姿态,本着国族存亡的现实关怀,将全运会视为塑造民众身体、培养现代公民乃至实现“强国保种”的重要工具;而下层民众对全运会的热情,并不尽然围绕知识精英的预期,更多关注的却是全运会中的新鲜、热闹的娱乐元素。可见,知识精英与普通大众对于全运会存在截然不同的解读。其实,作为民国时期重要的“视觉综合体”,全运会作为一个在开放空间并进行公开展示的文化性文本,存在着从各个立场和视角对其进行多维解读和评价的可能性,无论是主办全运会的政府还是掌握话语权的知识精英都无法垄断全运会自身展示与观众观赏的多样性,更无法左右普通大众对全运会的娱乐心态。由此,20世纪30年代的全运会在知识精英与普通大众的不同立场的中呈现出启蒙与娱乐的多元面相,超越了体育与政治的范畴,成为审视精英和大众、启蒙和娱乐、体育论述与和体育实践的一个重要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