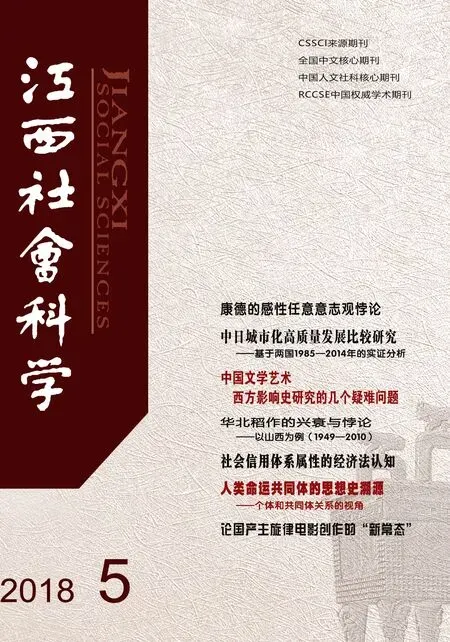中国文学艺术西方影响史研究的几个疑难问题
西方对中国的关注,一开始是将视点主要朝向物质产品,如丝绸、茶叶及工艺美术品等,后来才扩展到思想文化等非物质性成果。就文学艺术而言,其物质形态——作品,也早就流入欧洲,远远早于有关艺术的观念和思想。但是,对西方艺术创造真正发生影响是17世纪中下叶以来的事,即从西方艺术史上声势浩大的“中国风”(Chinoiserie)开始的。之后,这个影响从未停止过。中国人最早关注这段史实的应该是丰子恺,他在1930年曾以笔名婴行发表了一篇《中国美术在现代艺术上的胜利》的文章,这个“胜利”指的是中国绘画对印象派的影响。可惜,这篇文章在当时以及之后没有引起很大的重视。长期以来,中国学界和创作界对中华文学艺术对西方有持续性影响这一史实了解不多。直到新千年以来,情况明显发生变化,相关文章在国内不断出现。可是,有不少问题有待进一步梳理和澄清。
一、影响话语的内涵指向及其多元性
新千年以来,中国学界开始明显出现中国艺术对西方创作界发生影响的话语。就年代来看,指向从近代的“中国风”一直延伸至现代;就艺术门类来看,从园林建筑、文学等向绘画、工艺美术、音乐、设计等领域延伸。这表明:中国文学艺术对西方创作界发生持续影响这段历史史实开始渐渐为国内学界知晓。但是,这个影响的多元性,即影响程度和方式上的多元性却大多被忽略,以致如此这般的影响话语似乎成了中国人单纯赖以筑起文化自信的口号。因此,要使这样的话语真正站住脚,还有待深入这段史实的实际情形中。
中国艺术对西方创作界发生影响的第一个驿站应该是17世纪出现、18世纪盛行的“中国风”。对此,国内外谁都不会否认。涉及领域首当其冲的是园林建筑和工艺美术。当时欧洲出现了建造中国式园林和日常工艺美术(漆器、挂毯、陶瓷、室内装潢等)运用中国元素的时尚,遍及欧洲几乎所有主要国家,如德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匈牙利、俄国等。那时建造的中国式园林以及具有中国风格的建筑物不少至今尚存,工艺美术品如今则大多进入博物馆或私人收藏。其次,这股中国时尚在当时绘画领域也明显出现,当时绘画作品中时常不是出现了中国器物(如青花瓷)就是融入中国画法(如华托、布歇等)。再次,当时文学和音乐中也有不少案例可以看到这股中国时尚的影子。
这股具有如此广度的“中国风”在影响方式和内涵上的多样性迄今却很少有人提及。园林建筑领域出现的所谓“中国式园林”“中国式建筑”等,那只是“中国式”而已,较之于中国本土的建筑还是有些许甚至明显差别的,也就是说,其中多多少少融入了欧洲样式。工艺美术中虽然乍一看直接运用了中国图案,但其构图方式、着色等方面还是出现了变异。绘画方面的“中国风”甚至出现三种方式:其一,中华要素的直接移入,大多是画作中直接出现一些中国器物,比如陶瓷。但画法全然是西洋的;其二,中国画法的直接承袭,比如华托和布歇等,用中国画风去画以及用中国服饰去装饰西洋人物;其三,用西洋画法展现中国题材(风景、人物等),比如亚历山大等。文学领域的情形主要是借中国题材去表达自身的文学理想,比如借《赵氏孤儿》表达当时的启蒙思想(伏尔泰《中国孤儿》等),借中国题材去表达浪漫主义文学理想(柯尔律治的《忽必烈汗》等)。音乐领域的情形则体现为三种:第一,以西方歌剧形式表现中国,如西方表现中国公主图兰朵的最初尝试源自该时期,从意大利剧作家葛奇的《图兰朵》到德国席勒的诗剧《图兰朵》,已经开始用中国元素进行表现,如实物、礼仪等;第二,对中国音乐的最早记谱开始出现,如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中的《柳叶锦》等;第三,早期浪漫主义作曲家创作中对中国曲调和旋律的运用,如韦伯的《中国序曲》(1806)等。不同艺术门类,也包括同一艺术门类内部出现众多接受中国影响的不同情形和方式。
现代时期的接受同样如此。西方艺术自19世纪中叶开始的现代主义转型中也受到中国文学艺术的影响,这一话语明显没有近代“中国风”那样广为人传。这绝不是影响程度或广度不如从前,而是影响方式发生变化,开始一步一步从显向隐或从直接向间接转化。由于影响变得不那么外显,不那么直接,所以论说影响的话语也变得困难。事实上,该时期有案可稽(艺术家自述和创作史料)的影响在广度和深度上丝毫不逊于近代的“中国风”。从绘画、设计,到文学戏剧,再到音乐。该时期西方现代主义绘画的几乎每个流派都不同程度受到过中国绘画方式的启发和影响,现代设计就是在此过程中诞生和发展出来的,这一点在西方普遍为人知晓,中国却不然。在文学领域,美国意象派(庞德、艾略特、洛厄尔等)受到中国古诗影响同样在国内外业内几乎谁都知道。此外还有一些风格特异的作家如圣琼·佩斯、亨利·米肖等都自觉在创作上接受来自中国的影响。至于卡夫卡、博尔赫斯等作品中出现的中国题材更是广为人知。在戏剧领域,除了众所周知的布莱希特外,法国阿尔托的“残忍戏剧”理论、德国导演莱因哈特戏剧革新实践、俄国戏剧家梅耶荷德的戏剧教育和实践以及美国奥尼尔的《马可百万》和谢克纳的环境戏剧等都直接有来自中华的影响在。至于音乐领域的影响主要以两种方式出现:其一,对中国音乐调性的接受。著名的有克莱斯勒的小提琴作品《中国花鼓》和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当然还有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里的《中国舞曲》、巴托克舞剧《神奇的满大人》和凯特尔比的《中国寺庙庭园》等;其二,主要是德、奥音乐家将中国古诗引进西方音乐,最著名的是马勒的《大地之歌》,还有威伯恩的《四首歌曲》、勋伯格的《无伴奏合唱歌曲》和《混声合唱作品27号》以及施特劳斯的《五首东方歌曲》等。此外还有德彪西、布索尼、鲁塞尔、拉威尔、法里雅等一大批作曲家都程度不等地受到过中华文化的影响,尤其是齐尔品对中国音乐的热爱更是广为人知。如此广度的影响在影响方式上呈现出很大程度的多样性,这个多样不仅见诸不同流派间,而且还见诸同一流派不同艺术家之间。无疑,有关影响话语必须深入诸多不同方式中。
到了“二战”后的现当代,西方艺术创作虽然进入所谓的后现代,中华文学艺术的影响却没有中断,战后西方的美术、文学、音乐、平面设计,甚至摄影领域,依然可以找到不少自觉接受中华艺术影响的案例,此间只是影响方式和内涵又发生变化而已,由原来对中华艺术外在语汇的关注开始渐渐转向内在精神。此时,视点大多落在中国艺术所传递的精神性上。美术方面抽象表现主义中几乎每一位重要代表,从波洛克开始,都程度不等地受到中华艺术精神尤其是书法的影响,托比、马瑟韦尔、阿德·莱因哈特、弗朗兹·克兰、罗思科和德·库宁等都是如此。此外,20世纪50年代席卷整个西方的禅画潮更是集聚了一大批深受中华艺术影响的画家,如:法国的克莱因、米肖,美国的约翰·凯奇,西班牙的塔皮埃斯,德国的比希尔、鲍麦斯特,等等。还有,由禅画演化出的德国无体画派(das Informell)中也有相当一批画家自觉接受来自中国的影响。另有一些独立画家像汉斯·哈同、昆特·约克等同样有受中华影响的痕迹。
文学方面的影响首推英美文学界的“垮掉派”诗人,从最早的雷克斯罗斯,到著名的史奈德、金斯伯格,还有凯鲁亚克;其次就是有超现实主义特点的深层意象派诗人,像罗伯特·布莱、詹姆斯·赖特和路易斯·辛普森等。这些诗人在接受禅宗以及中国古诗的过程中虽部分具有鲜明的为我所用色彩,却将所接收的中华文学推向英美主流文化。音乐方面著名案例是约翰·凯奇和彼德·利伯森,他们与此前现代时期有所不同,不再直接沿用中国艺术的一些要素(调性、曲目等),而是直接从中国音乐的思想源头汲取养料,比如易经、禅宗和藏传佛教思想等。这不是简单用西方音乐既存手段和方式来表现和诠释东方思想,而是在做新音乐,接受这些思想的同时也在实践着新的音乐方式。至于战后西方的平面设计更是大量运用来自中国的图案要素,几乎到了日常生活随处可见的情形。摄影方面的影响主要见诸英国当代风景摄影家Michael Kenna的作品,尤其是其中展现出的中国水墨墨韵。
中国艺术对西方创作界自近代开始如此绵延不断的影响,是一段有案可稽的史实,这段史实如今正越来越浮出水面。但是,众多的影响史实中,影响方式及其内涵却呈现出很不相同的情形。如果忽略这些不同,单纯仅凭一些单一资料,艺术家自述或作品样式之类去言说影响问题,就会使该问题成为一个没有实际内容的口号式话语。简言之,有关中国艺术对西方艺术创造的影响话语必须深入程度界面,必须揭示众多的影响方式和存在形态。
二、影响话语的合法性建构问题
西方自近代以来如此众多而且具有持续性的案例,在西方艺术史叙事中却几乎没有地盘。近代艺术史部分讲到17-18世纪时大多连“中国风”提都不提,其他一些关注“中国风”的文献又大多将此定性成对异国情调(exoticism,exotism)的好奇[1](P186),因而成为当时艺术创作的一个边缘现象。对于现代以来的情形,更是在西方的艺术史叙事中很少触及。这绝不是对如上所述那些艺术大家的不重视,而是对他们接受的来自中华的影响不关注,这些大家只是被置于西方艺术发展的脉络关联中去考察。对于如上所述那些接受中国影响的事实当然没有人去否定,此间否定的只是这一接受对艺术家们的创作行为和艺术语汇发生了主导性影响。就现代以来那些西方艺术家们推出的最终艺术语汇而言,确实与中华艺术少有直接关联,或者说很难看出或听出有什么中国味。但是,因此不去关注这些艺术家本人所申明的受到了中国艺术的影响或创作中临摹过或钻研过中国艺术的事实,这明显忽略了影响问题上的创造性改造和发挥的问题。西方艺术史叙事对中华影响这一现象的集体沉默,应该不是源于史料不足或证据不充分,而是欧洲中心主义思想在作祟,准确些说是受意识形态影响的“贬中”情绪在作怪,因为他们对西方艺术受到过东方影响这样的话题却并没有那样沉默。“东方”一词固然也将中国包含在内,但明显淡化了中国。相反,对于日本的影响却不断提及,不仅没有用“东方”一词去淡化,而且还专门创制了“日本主义”(Japonismus)一词来加以强调。
西方主流文化长期以来这股“贬中”潮流使得艺术史上的中国影响问题严重被忽略和遮蔽,这使得与之对立但没有那么进入主流文化中去的“褒中”潮流在这个问题上也不敢轻易断言。比如,对于“中国风”如此明显的中国影响,西方汉学家们,包括那些专门研究东亚艺术史的学者们也还是将之阐述成单纯对异国情调的好奇,而看不到其对西方艺术发展(告别文艺复兴传统转向艺术创作新风——洛可可和巴洛克)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在强大的欧洲中心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贬中”潮流下,谁突出这样的作用,往往就会被忽略而弃在一边。比如,法国当代汉学家施瓦布(Raymond Schwab)在其《东方文艺复兴》一书中就中华艺术对西方的影响所说的“第二次文艺复兴:东方文艺复兴”其实早在1841年就由奎内特(Edgar Quinet)提出[2](P11-12)。那是西方创作界刚经历了“中国风”正走向现代转型的时代,而且创作界不断推出的现代新风正自觉借助东亚艺术的影响。但是,奎内特的观点显然没有引起重视,直到约150年后的当代,这样的观点才重又出现。这个关注当然得益于后殖民主义时代当代西方学界出现的东方主义潮流。
具体就中国文学艺术对西方的影响这个话题而言,东方主义学者们固然力举其对西方艺术创作发展的推动作用。但是,在欧洲中心主义长期盛行的西方,不做深入艺术史发展内里的实证研究,而单凭一些作品现象就去断言这个影响深入到西方艺术发展主脉中,还是难以让人信服,尤其难以说服那些有欧洲中心主义情结的人。对于17-18世纪的中国风,包括现当代的一些情形,即便那些欧洲中心主义论者也没有否认有影响在,他们只是否认这个影响已深入西方艺术发展的主脉中,所以才将之断言为西方艺术史的边缘现象,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东方主义论者由于没有具体深入的实证研究做支撑,他们的断言不仅无法获得广泛认同,而且还会被说成是对历史的误解或夸大,尤其大多东方主义论者具有东方身份背景这一点,更难以让人信服那些没有具体论证做支撑的断言。而问题的另一端,即否认其主导作用的一端却有着强大的艺术史学科传统,这个传统已经梳理出一条清晰的西方艺术发展史主脉。有关中国文学艺术对西方的影响史研究如果不切入这个已经被西方学界建构出的主脉,所述事实便难免被看成是西方艺术发展的一些边缘现象。由此,相关影响话语的合法性将被限定在偶发现象上,纵使有大量材料证明有影响在,也不免被说成是偶然或单个现象。这样,艺术史上出现的那些众多案例就难以获得重视。
这里,影响话语的合法性建构就在于深入细致的影响程度分析。这个程度分析首先是具体揭示中华影响在特定艺术家或流派那里所起到的作用;其次还要深入西方艺术发展的前后脉络中具体指出这一影响对于那个时代艺术创作的作用。比如,迄今国内外对17-18世纪“中国风”的研究就大多流于对这个影响存在的展示或论证,少有将之与当时西方艺术创作主流进行比照,进而切入对当时艺术创作主导形态的影响。孤立来看,“中国风”与当时艺术创作新风如洛可可、巴洛克以及早期浪漫主义似乎没有什么直接关联,但是,将这些新风置入其赖以出现的前后关联来看,不难看出“中国风”对这些新风的出现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具体而言,这些新风是告别此前由文艺复兴开创的新古典主义传统的产物。就这个“告别”而言,“中国风”便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因为中国艺术让当时欧洲艺术家看到一个完全不同于希腊传统(文艺复兴)的新方式:来自于对象给定的和谐、比例等可以经由人的安排而破掉(破除自希腊以来对客观给定之秩序的信奉),作品中的形象最终是由人安排出来的。这样,艺术方式中就可以有更多主体心性方面的内涵。于是,严肃、拘谨的古典主义被抛弃,出现了洛可可艺术中的轻松和细腻以及巴洛克艺术中的反规则(古典主义看重的规则)。19世纪中叶开始的西方艺术创造转向现代主义过程中,包括“二战”后的后现代转向中,中华艺术都起到特定的助推作用。有关中国艺术对西方艺术创造之影响话语的合法性构建就要深入这个影响程度的分析中,首先是对相关艺术家或流派的影响程度分析,其次是对时代艺术潮流递变的影响程度分析。这样的影响程度分析进一步由内和外两方面组成。
“内”主要见诸作品整体效果分析。对于西方艺术作品中直接出现中国元素或创作方式的情形,不能仅停留于指出这些元素,更要考察这些元素或方式在作品整体效果中的份额和地位,是直接参与到作品的总体表达中还是借中国艺术方式表达着西方的主题;对于将中国艺术方式进行创造性改造的作品,就要具体分析和还原出这个改造的中间环节,以建构出与中国艺术的内隐关联。影响程度分析的“外”主要见诸发展史地位分析,主要考察所接受的中国影响与时代艺术主导形态及其发展之间的关系,由此来回答单个艺术家或流派所接受的中国影响是偶发的边缘现象还是进入西方主导艺术形态中这个问题。所以,中国艺术对西方艺术创造之影响话语的合法性建构决不单纯是史料证据方面的问题,更是影响程度分析和定位方面的问题。
三、影响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由于中国艺术对西方艺术创造的影响呈现出极其多元和众多异质的情形,这个影响史研究有一系列特有的方法论问题有待关注。
首先,影响话语的确定问题。西方近代以来艺术创造中出现的中国艺术元素呈现出多层面性,不少情况是在借用中国题材或符号来表达西方的主题,比如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及其一系列改编本以及柯尔律治《忽必烈汗》等,前者在借元杂剧《赵氏孤儿》的题材表达当时法国盛行的启蒙思想;后者在借中国题材表达刚刚萌生的早期浪漫主义文学理想。这其实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对西方的影响,而是中华思想文化或中国文学精神对西方艺术创造的影响。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影响应该是进入艺术方式或作品方式中去的,比如中国戏曲艺术对布莱希特间离化或陌生化戏剧方式的启发。当然,我们可以谈中国艺术体现出的思想性对西方艺术创作的影响,作品表达的精神性是可以有跨文化影响发生的。但是,如此话语还是要深入艺术方式层面,因为作品中的精神性传达是以艺术方式(感性方式)实现的,没有对这个层面的嵌入,影响话语就会流于空泛。
其次,影响方式的多样性问题。影响话语的确定就是要深入实际发生的具体方式中去展开阐述。总体而言,要区分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种方式。直接影响指西方艺术家创造出的作品直接沿用中华艺术方式或中华艺术元素,主要是近代西方出现的情形。这种影响方式本身又具体呈现出两种情形:其一,对中华艺术器物、造型或符号的直接运用;其二,对中华艺术方式(画法、制作方法等)的直接运用。两者在影响的发生方式和效果上有着明显差别,而且,同样的方式在不同艺术门类中的效果也不尽相同。对于直接影响决不能下一个有影响存在的简单判断了事,而是要深入指出什么意义以及何种程度的影响。迄今研究有不少成果就是凭借一目了然的中国艺术元素在西方作品中的存在而断定影响的存在,并止于这样的断定,而没有深入挖掘出这些元素在西方作品的整体效果中所起到的作用,更没有再返回中国艺术本身剖析出这些西行的要素本身以及西行之后新生出的表达。
间接影响即西方艺术创造者对中华艺术的作品语汇进行了创造性改造,因而创造出的作品中看不出与中华艺术的直接关联。这种情形主要出现在现代与后现代。对此,迄今研究往往仅凭一些文字资料(艺术家自述)去断言有影响存在,很少深入作品语汇层面进行分析。因此,改造在哪里,转化在哪里就成了无以得知的。没有对创造性转化各个环节的揭示,有关影响话语就严重与作品脱节,比如有关中国书法对美国抽象表现主义影响的问题不少人在说,但由于没有相应的作品分析和具体的语汇指向,这个话语不免空洞无物。进一步看,由于间接影响所关注和接受的中国艺术往往不是某一艺术门类或某一作品的全部,而是其特定的方面,仅凭艺术家本人大多笼统的自述而不结合作品分析,就很难将这些特定方面揭示出来,进而也就无法深入这个影响的实情。总体而言,直接影响不仅外在、感性,而且机械、易把握;间接影响除了内在、精神化外,而且具有显著的创造性,因此较难建构起影响话语。要克服这个难点,唯有深入中西艺术各自特有的方式中,尤其是要指出西方作品语汇形态中没有中华的影响会是怎样?有了这个影响又会怎样?这样的研究还内聚着中华艺术创新的思路引领。
再次,关于中华艺术影响西方问题上的中国、日本之纠缠。凡是深入了解下该论题材料就会发现:有关中国艺术对西方影响的问题时常会与日本纠缠在一起。除了近代明确出现了西方艺术史上的“中国风”外,现代和后现代都会出现中国与日本纠缠在一起的情形,主要是因为现代以来中国开始渐渐落后于日本,大量日本艺术产品开始进入西方,导致许多艺术家是通过接触日本艺术品去言说东方艺术的。加上该时期“贬中”情绪和势力在西方抬头,导致不少西方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刻意对中国与日本做出区分,比如在印象派那里就指出,那不是中国艺术,而是日本浮世绘对之产生了影响。而中国学者大多淡化这个区分,主张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主义中占主导的是中国,以此表明即便西方艺术家直接接触的是日本艺术,同样可以据此言说中华艺术的影响。这固然于理说得过去,但还不具有充分说服力。问题关键在于,接受了什么?事实是,西方艺术家大多不关心或不明白中国艺术与日本艺术之间的区别,不时出现说的是日本,指的却是中国的情形。进一步看,大多数情况下西方艺术家在接受日本艺术影响时,接受的并不是日本艺术特有的东西,而是其与中华艺术共有的东西,比如日本水墨与中国水墨在画法上就有许多共享层面,而西方艺术家接受的往往是这些共性,即具有相似性的东西。因此单纯根据作品产地去断言这个影响来自日本而不是中国,未免简单粗糙,而且会有“贬中”色彩。当然,也有一些少数案例确实是接受日本艺术中特有东西的,如梵高“开花的梅树”“千住大桥之雨”等,但那也只是极少数而已。绝大多数情形是:不管西方艺术家们直接接触的是中国艺术还是日本艺术,他们接受的基本是两者共有的东西,而这恰恰来自中国。所以,有关对西方影响的问题决不能单纯看西方艺术家接触的东方艺术品是来自中国还是日本,而是要看他们接受的东西是什么。比如印象派艺术家直接关注的东方作品固然以浮世绘为主,但他们从中接受的并不是其固有的东西,而是其与中国艺术共有的东西,也就是说:“印象派与浮世绘的交界面,同样可以为中华美术所共享,浮世绘中对印象派发生影响的两个界面都存在于中华美术之中,即空间处理上的非三维透视和色彩处理上的无光源化。”[3]据此,决不能说印象派与中国艺术无关。因此有关中国艺术对西方的影响话语必须深入具体实情中,不为西方艺术家笼统的言说所惑,更不为具有“贬中”倾向的学者言论所左右。
四、影响的评估问题
如上所述的影响程度分析其实已经涉及到评估问题,即对中华文学艺术影响西方文学艺术创造之话语的量化定性。这固然是问题的关键,但是,有关误读或误解的话语却往往会扰乱该问题的解决,尤其在国内。国内学者凡涉及中国艺术对西方影响问题,往往会出现这是对中国艺术的误读或曲解的言论,以致有关影响话语的根基受到动摇,影响史研究本身内蕴的跨文化新知的可能受到遏制。这样的言论无异于说,所谓影响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艺术。其实,这里有个不易察觉的学理混乱。现代阐释学以及相关的众多跨文化交际理论早已澄清,所谓影响从不会是全方位的跟风,而总是从对方选取某点或某些方面来作为自身进一步发展的启发和促动。否则,那就不是影响,而是照搬、跟风。如果就西方艺术家只是从中华艺术中选取某一或某些点加以发挥或改造而指责其对中国艺术有误解,这不仅与影响问题研究的题旨不合,而且还彰显出对中国艺术的狭隘理解,看不到其历史长河中的递变,包括跨文化递变。影响研究不是也不可能去评估对中国艺术是否有误解,而是要揭示中国艺术在哪些方面受到关注并对西方艺术创造的发展起到怎样的推进作用。由于文化差异或跨文化的缘故,这些方面不可能与我们对中国艺术的自我理解完全一致,差异或误解是不可避免而且正常的。影响问题研究的题旨不是去评判是否有误解,而是去评判哪些方面受到关注并引发怎样的新发展,进而披露跨文化影响所催发的新发展空间。
就中国文学艺术对西方的影响而言,评估问题当然聚焦在对西方文学艺术创造的发展起到了什么作用问题上。迄今,国外相关研究对此基本集体沉默,所谓的研究也就是根据作品分析指出有影响在,话语基本到此为止,充其量就单个非主流艺术家指出该影响推进了其艺术语汇的出现。而那些大多有亚洲身份背景的东方主义论者却似乎只是凭着一股热情在演说西方艺术中的“东方文艺复兴”问题,而没有具体深入的实证研究作为支撑,以致很大程度失落了话语的可信度和广泛接受。实际上,在近代以来中国艺术对西方持续不断的影响中潜伏着很多实情没有揭示出来,尤其是这个影响对西方主流艺术创造的发展起到的推进作用。
具体而言,西方文艺创造中的希腊传统与中华传统应该没有多大关联,只有对峙、相异。但是,以后的发展则不然,恰是在中华这个异体文化的刺激和影响下,西方文艺创造在文艺复兴高举希腊大旗不到约二百年后,开始出现了告别这个新古典主义寻求艺术创造新风的倾向。恰在此时,与希腊传统完全相异的中华艺术引起关注,指明了不同于希腊传统的另一种创造的可能,那就是作品不以客观给定的和谐、原则为中心,而是将此和谐、对象关系看成是经由人心安排出来的,是与人有关的。这表面看是客观的对象关联,其实是经由人心安排的。对17—18世纪建筑艺术中出现的“中国风”产生巨大影响的英国政治家和文艺批评家坦普尔爵士(Sir.William Temple)在其1685年写成的《论伊壁鸠鲁的花园或关于造园的艺术》就持此说。他写道:“对欧洲人而言,花园之美主要来自建筑物和植物安排的比例,对称与规整……但中国人却鄙视这样的方式,他们会说,即便一个能数数到一百的小男孩,也能够以他自己喜欢的长度和宽度来安排林荫道上排成直线的树木。”[4](P131-132)对象的秩序由心来安置而不是听命于给定的规则,这是中华艺术在17-18世纪西方受关注的核心要点所在。恰是在这个异体文化的影响下,欧洲艺术转向了洛可可和巴洛克风,开始告别自文艺复兴开始的古典主义艺术创造的那些以单纯客观关系为依循的法则。单纯将洛可可或巴洛克时期的艺术品与中国艺术比对,固然很难看出有一致和关联的地方,但是,该艺术风格所依循的美学路径却离不开中国艺术的促动,即告别古典主义传统,开创艺术创作新风。当时,应该是中国艺术对这个“告别”和“开创”起到了推动作用,尤其是洛可可风。不仅大量史料告诉我们,不少洛可可艺术家主动接受来自中国艺术的影响,而且洛可可艺术总体展现的那种轻松和细腻,主要不是与此前古典主义(希腊传统)的严肃、拘谨,而是与中国艺术的美学路径相关,那就是面对给定对象时的放松和对情感流变的细腻。这应该就是17—18世纪西方艺术中的“中国风”所引发的效果:推进了西方艺术告别古典主义文艺复兴传统,转向洛可可、巴洛克等艺术新风。
这也可以进一步说明:为什么近代西方掀起“中国风”,而不是“埃及风”“印度风”之类,虽然当时西方艺术界同样可以接触到这些国家的艺术品。那当然是中国艺术的特质使然。就当时受关注的园林建筑而言,恰是中国园林中避免几何形直线,多用曲线以及借景等原则开启了西方园林建筑告别古典主义传统的思路:多用曲线以及发明落地窗以达到借景的效果。就同样受到关注的美术(绘画和工艺美术)而言,中国艺术中的装饰风格,平面效果就格外受到重视,恰是这一点形成与欧洲古典主义传统的明显反差。因此,17-18世纪的“中国风”应该不是西方艺术史上的一个边缘现象,而是推进了西方艺术告别自文艺复兴开始的古典主义转向近代艺术创作新风。
同样的作用在19世纪中叶开始的西方艺术创造新一轮转型中,还是存在,也就是推进了西方艺术创造转向现代性或现代主义。在19世纪中叶至“二战”爆发近百年时间内,西方文艺史上可以找到许多接受东方(中国)艺术影响的案例,从美术到音乐,从文学到戏剧等等。这些案例同样不应该是西方现代艺术诞生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些边缘现象,而是对之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总体而言,该时期看向东方、看向中国艺术的西方艺术家大多聚焦于心对艺术形式创造的决定作用,这比近代时又向前进了一步。近代时作品中的形还是对象性的,只是与文艺复兴时期不同成了由心安排出的对象之形而已。现代主义中,这个形是否对象性的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由心而来,以致心在形式创造中起到决定作用。这一点在西方此前的艺术创造中是找不到任何对应的,而在中国艺术中则可以。事实上,现代主义时期的西方艺术家看向中国艺术时,大多将视点朝向中国艺术中主观情性表达的一面。恰是这一点推动着西方现代艺术不断沿此方向前行。从一开始的平面化、变形,经由陌生化、象征等语汇,最终走向形式创造中完全摆脱对象性给定,转向主体心灵创造或心的感知,即走向抽象。“二战”后西方艺术出现的所谓后现代转向中同样有中国艺术的踪迹,那些大量出现的自觉接受中国影响的案例就是例证。这时,关注点又从主体心灵中心抽离出来,开始关注中国艺术位于主客之间不以任何一端为中心的造型原则,因此西方后现代艺术呈现出消解中心、走向多元的特征。具体到作品语汇上就是转向抽象,以行为或流变为主导。所以,后现代时期西方艺术家凡看向东方、看向中国的,大多聚焦于中华艺术所传达的禅、易等精神性内涵。
毋庸讳言,不同时期西方艺术家对中华文学艺术关注的方面有着明显变迁,这主要表明的还不是对中国文学艺术的曲解,甚至歪曲,而是西方文学艺术发展不同时期的文化诉求。正是这个变化了的文化诉求使得他们从中华艺术中截取出了不同方面加以发挥。从影响研究角度看,不管他们截取的是哪些方面,对西方艺术创造不断向前发展起到的推进作用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当然,这段影响史也体现了西方对中华艺术的体认经历了一个不断由浅入深的过程。近代时不仅对中华艺术具体语汇有很高的关注,而且看到的只是对象性的安排这一面,即如何再现对象的形。他们所受到的启发是:艺术再现中对象间的某些客观关系可以有所改变;到了现代,这种改变进一步推进到可以不顾对象的客观给定之形。因而,视点由对象之形转向主观,看到了主观之心对创造起到的巨大作用,甚至可以完全不顾对象而只是由心来造型;最后,在后现代时期才看清,即便决定形式创造的主观之心最终也还是受制于自然,所以抛弃了现代时期的单纯以主观之心为中心。但是,由此并没有退回到现代时期之前的以客观世界为中心,而是转向消解任何中心,让没有中心依循的过程,行为本身来引发造型。西方近现代对中华艺术这个不同接受角度的变化和深化,一方面展现了中华艺术的诸多面向,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了西方艺术自身发展的美学轨迹。影响史研究的意义最终应该落在以他人为镜像进行自我审视上。
[1]Eleanor von Erdberg.die Anfaenge der ostasiatischen Kunstgeschichte in Deutschland.Kategorien und Methoden der deutschen Kunstgeschichte 1900—1930.Von Lorenz Dittmann.Stuttgart,1985.
[2]Raymond Schwab.The Oriental Renaissance:Europe's Rediscovery of India and the East(1680-1880).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
[3]王才勇.印象派与中华美术无关吗?[J].上海文化,2017,(12).
[4]William Temple.Upon the Garden of Epicurus or of Gardening in the Year of 1685.Miscellanea,the Second Part,in Four Essays.London,16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