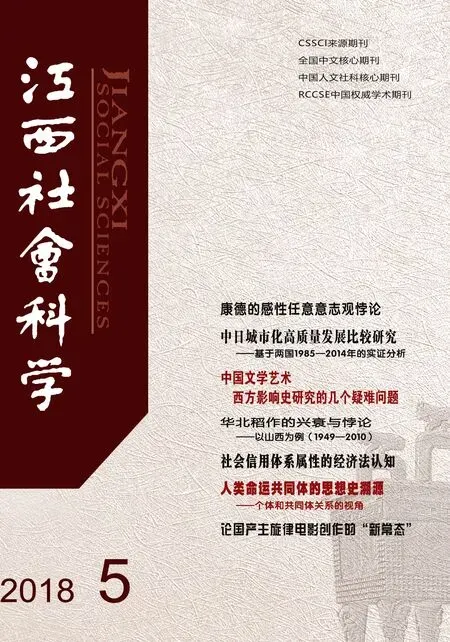麦金太尔的美德转向及其对解决当代道德困境的启示
当代西方的伦理是沿着两条研究路径而各自发出自己的声音,一条是由美国当代最著名的伦理学家罗尔斯为代表的“规范伦理”,另一条则是在随后出现的另一位美国伦理学家麦金太尔提出的“美德伦理”(a morality of virtue)。在《追寻美德》中,麦金太尔提出“美德伦理”与“法则伦理”(a moralityoflaw),并断言“拥有正义美德的人,不仅懂得如何应用法则,而且还超越法则。”[1](P27)西方学界普遍认为,用“美德伦理”替代“规范伦理”,是通过批判西方主流道德伦理和重构亚里士多德道德伦理的新路径,由此,产生了一场关于“什么样合理的道德才是正确选择”的争论。
麦金太尔的美德伦理考察现实社会生活内容的两个方面:一是社会语境中的科层组织生活;二是受西方启蒙文化中的理性主义影响的个人情感主义及其导致的困境。他指出,我们只能选择两种社会生活模式,第一种是由个人的自由主义指向的权利选择,第二种是社群主义的目的选择。同时,他又指出,社群主义占主导地位时有很可能会限制个人的自由和任意选择。因此,在社会生活中,社群主义与个人主义既是对手又是伙伴。但麦金太尔通过对历史、文化传统的道德考察,将美德转向社群主义的道德伦理,即亚里士多德的共同体的“善的目的”,并重新倡导个体生存的集体的和社群的意义,试图把“美德”作为整个社会生活价值体系的核心。当前,在我国道德教育还有待进一步升华的背景下,麦金太尔跃过“规范伦理”而至“美德伦理”的理论,虽然让人感到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残酷,但还是为我国当代经济建设转型之时的社会伦理建设提供了有益可鉴的思考与启示。
一、对道德的历史考察与正名
当代日常道德话语的特殊性质是如何形成的?麦金太尔首先从“道德”演化的历史视角,从叙事的传统上对“道德”的根源与演化进行分析和考察,接着指出道德是一种有目的的实践过程,最后为道德正名:道德既不是理性,也不是激情,而是一种“可能所是”。
(一)对“道德”词源演变的历史考察
麦金太尔指出“道德”(moral)一词源自拉丁文“moralis”,意思是“属于品格的”(pertaining to character),是指向一个人在日常生活叙事中的某种品格。[2]英语中“moral”的早期用法就是译自拉丁文,作名词用,表达的不是形而上的理念或宗教信仰,也不是规范自我权利的规则,而是实践训诫,即一种指导人在日常生活叙事中的言行规范。随后,“moral”逐渐由实践的行为规范变为美德。到16、17世纪,“moral”开始具有现代意义,主要与一种社会日常行为的规定有关。17、18世纪,“moral”由谓词“实践”变成“morality”(道德),成为既不属于神学和法律,也与审美无关的行为规则,而是人们在生活的叙事实践中普遍接受的一种道德原则。[1](P49)
麦金太尔通过对“道德”的词源演化的历史考察,指出历史上的道德概念本身就具有规范性。他考察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之前的道德历史,发现在荷马、亚里士多德、简·奥斯汀、富兰克林等人的著作及《新约全书》中,道德皆指向一种品质,但不同时代对人担当的社会角色的责任和义务规定的品质也不同:在荷马史诗里,道德是一种英雄般的卓越品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道德是个人善的品质;在简·奥斯丁那里,道德是人取得人生与生活平衡的品质;富兰克林则认为道德是人实现幸福所应具备的品质;《新约》认为道德是有利于人获得从尘世通往天国所应持有的品质。[1](P185)虽时代语境不一,“品质”作为一种道德概念具有自身的规范性。
麦金太尔并不赞同道德是一种普遍原则,他认为,道德是一种个人的“品质”属性,但必须是内化于心的实践,是一个动态的逐渐认识并提升的运动过程。古希腊英雄追求的勇敢、坚毅、卓越、诚实、正直等品质,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社会土壤中的历练与修为中获得和养成的。道德、法律的规则是社会出于维持自身的秩序和有效运转而制定的言行规则,人出于某种外在需求而不得不遵守这些规则,但遵守并不能使人由衷地获得这种品格。再说,有些普遍的规则未必就是合理的。如在有些国家,堕胎、安乐死是合法行为,而在有些国家则是非法行为。允许与不允许,仅仅是法律的硬性规定,未必就一定是合理的。
麦金太尔批判当代以洛克为先驱的情感主义强调的自由权利中的规则道德,称其中弥漫着自相矛盾的气息:一是在概念上具有不可公度性;二是通常以一种非个人的模式出现。这两点在文化的表层话语中倾向于道德多元论。我们都知道,多元论夹杂着不同观点。麦金太尔认为,当代情感主义的道德判断无非是偏好、态度和情感的表达,而表达态度和情感的道德判断既无真也无假,道德判断中的意见一致并不是由任何合理的方法来保证的。他认为,使用道德判断,不仅要表达自己的情感与态度,还要对他人造成一种良好的影响与促进。
而在现代社会,情感主义者认为,个人皆是独立的个体,与社会保持距离,社会只是实现自身利益和达到自身目的的场所,因为在他们看来,自由和权益是一种品质。麦金太尔指出,情感主义的社会观只是把社会当作满足自己私欲的竞技场。而古希腊时期的普遍观点是,人是社会这个大宇宙中的小宇宙,小宇宙与大宇宙之间是从属关系,个人是处于社会群体中的一员,个人光辉只有置于社会群体之中才能彰显自身的价值。个人品格的习得,是在与社会的群体关系实践中产生与养成的。即便在中世纪,由教会引领的诸如救赎、忏悔、宽恕等美德,无一不是指引人不断去恶从善,最终达到一个神圣的目标。因为按照中世纪的理解,人是带着原罪来到尘世的,人生就是一趟不断赎罪、忏悔、施善而最终通向幸福天国的旅程。美德正是帮助人去克服人生旅程中的迷惑、艰难、困苦等各种恶的阻碍,最终到达至善(幸福的天国)的目的。人若离开朝向至善目的的艰难前行、探索的实践过程,仅有宗教的道德规定,也不能获得这些品格。宗教的道德只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规定,它存在那里,却并不与人产生关联。人若没有一个内在内化于心的动态的接受—理解—消化—吸收—表现的过程,不可能获得美德。
从某种意义上说,麦金太尔的美德“是一种后天习得的品质,拥有和践行这种品质往往使人能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缺少这种品质则会妨碍人获得这样的利益”[1](P191)。在麦金太尔看来,所谓传统也正是由这样的品质所维系。传统不是别的,而是一个历史上承前启后,具体体现在人们对内在利益的不断实践而构成的社会性的论证过程。
(二)道德是一种有目的的实践过程
在《追寻美德》中,麦金太尔从文化的角度考察道德,他以克尔凯郭尔的《非此即彼》中表达的观点,进一步阐释道德的两种含义:广义的道德是一种“权威”;狭义的道德是一种“目的”。[1](P60)克尔凯郭尔将道德的普遍义与特殊义对立起来,使“怀疑的自我与基督教的自我”“审美的和伦理的道德生活”陷入“非此即彼”的道德相对主义。麦金太尔质疑这种将道德的诸原则独立于人的态度、爱好、情感,而所谓的道德原则之所以具有权威性,是人把它视作具有权威性的指导和约束。例如,人若出于健康或某种宗教的理由而自愿选择过禁欲、素食的生活,那么,“禁欲”“素食”的规定对此人来说便具有一种权威性,这种权威性显然来自人的目的,道德原则不能保证人的目的,就丧失其权威性。也就是说,对个人的目的是善的选择,就是具有权威性的原则,且这个选择是与人的爱好、情感及态度紧密相连,但只因外在理由而采纳的东西则不具有权威性。“体现在各种可普遍化的道德原则中的诚信、坦白和仁慈,若只是以一种极为简单的方式被理解。那么,伦理的人一旦作出最初的选择,也就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解释问题。”[1](P53)例如,“要求你必须仁慈地待人”与“你从内心里感觉到必须仁慈待人”,两者有本质的区别。
在麦金太尔看来,怀疑的自我与基督教的自我,审美的和伦理的生活,并不是截然二分的内在矛盾,两者具有一个动态的认识。我的怀疑,只有在出于一种“我要达成何种人生目的”为前提的追问时才有意义。人正是在对此人生目的追问、探寻与实践过程中不断修正自己的道德行为,个人的道德才与宗教的道德达成统一。
(三)道德是一种“可能所是”
康德认为,合理的道德规则必然对所有理性的存在者都有同样的约束力,而理性的存在者遵循这些规则的偶然(任意)能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履行这些规则的意志。[2]在康德看来,实践理性排斥任何经验的判断与实践,而只诉诸主观判断,道德理性的本质就在于制定普遍的原则。此原则能够为每一个理性的行为者所遵守。[1](P56)麦金太尔对康德的超感性道德原则提出了质疑:若道德的需求不是出于人自身需要的欲望,不是出于一种宗教信仰,而只是出于一种合乎某种规则的意志驱使,则不可能保证人达成幸福的目的。与康德持不同见地的休谟则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开明地从长远观点出发来追求自身欲望,那么我们便会看到,保守的道德规则大多是可以通过诉诸欲望和激情的基础来成功证明的规则”[1](P71),“道德必须基于激情和欲望在人类生活中的位置来予以理解、说明和辩护”[1](P28)。在休谟看来,道德的基础绝不是理性,而是激情。康德将人性特征看作理性规则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狄德罗和休谟却认为,相应的人性特征是激情,他们重视“同情”“仁慈”“怜悯”等,并认为这些道德意识或道德情操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伦理规范。
麦金太尔既不赞成康德的理性道德,也不支持狄德罗和休谟的激情道德,而是肯定以激情道德(欲望)为前提的理性的合道德性。麦金太尔肯定人的欲望,将欲望看作人在社会中追寻一种美德创造与实践活动的基础。但他也指出,欲望也有善恶之分。有些欲望是合理的,有些欲望则应予以禁止、扼杀和再教育。如“对简素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的欲望是具有道德合理性,是美善的,而“对奢华生活和物欲的追求”的欲望则不具有美德合理性,是应予以再教育。人皆潜在地具有大量的欲望,有些彼此冲突、互不相容,所以,对欲望需要作出合理而正确的抉择。朝什么方向引导我们的欲望,如何安置我们体内各种各样的冲动、需求、情绪和目的等等,都是要在认识中作选择,而选择的动机正是源于人最终所要达成的美德之目的。亚里士多德的道德主张着眼于的欲望,他认为“生命”(也是生物学上的生命)或现实既在解决矛盾,又在产生新的矛盾,在道德现象上,善与恶的矛盾,也是现实的变化与规律。
关于选择的目的,麦金太尔用亚里士多德的三重目的论——“偶然所是的人”“可能所是的人”与“伦理学的训诫”,加以阐明。“偶然所是的人”指的是自我尚未认识到自身目的的状态,只有经过伦理学的训诫并按照这些训诫去行动,自我才能认识并实现自身的目的,从而成为“可能所是的人”。理性道德和激情道德,任意一方皆不可能使人成为“可能所是的人”。
因此,伦理学正是促使人们明白自身的状态从而不断向善的学问,能敦促人朝“可能所是的人”转变。伦理学敦促美德而禁绝恶行的训诫,教导人如何认识自身的潜能,又如何将潜能变为行动,从而实现人的真实本性并达到真正的人的目的。由此不难看出,麦金太尔反对人对自身外在利益,即外在欲望的自由追逐,而是提倡“有效追求”,如对物质的追求仅是满足自身生存的需要,而不是对物质追求过度的欲望膨胀。在麦金太尔看来,人只有在对卓越品质的追逐中,才能最大限度地达成“可能所是的人”,而对外在欲望的自由追逐,则只能成为“偶然所是的人”。但外在利益,如名誉、财富等等,不仅可以体现人们实践的卓越,而且也是可以共享的善。例如,作家创作作品获奖而声名鹊起、科学家研发产品而广为人知,这便是一种内在善的外在表现,是内在善与外在善的统一。因为作家只有在长期艰苦的创作中,科学家只有在长期执着的实验与研究中,才能表现出其卓越并获得到荣誉和快乐。作家或科学家正是从内在善出发,达成外在善,再从外在善回到内在善的卓越追求,让内外善达到统一,也即从“可能所是”出发,但正是通过“偶然所是”来彰显自身的能力与价值,从而坚定自己的“可能所是”。
因此,麦金太尔认为,传统的道德体系本质上存在着一种由未被开化的人性升华为具有美德的人性。人应该做什么,指的就是在客观现实的语境之下通过什么样的行为才能实现人的真正目的。而伦理学的意义,就在于阐释人之为人应该追求的价值目标,并以伦理戒规规整人的行为。
二、麦金太尔美德考察的转向:重构善的美德伦理
从洛克开始,西方哲学逐渐强调权利优先于善,而传统社群主义则认为“善优先于权利”。这就涉及个人与社会,权利与价值的区别。情感主义重视个人的权利的事实,而传统社群主义则重视个人价值最大化的实现。个人的价值是通过社会的作用才得以最大化。麦金太尔对此持反对态度,他主张权利与价值合一。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里,人与人有关的美德都包含价值之意。例如,公民、哲学家、士兵等,这些角色皆规定了其应承担的责任或应当履行的义务。而且,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人是什么”与“人应当是什么”,是同一个问题,人的自然本质就是追求善,在善的实践中体现美德。所以,麦金太尔将美德考察转向尼采与亚里士多德、托洛茨基与圣·本尼迪克特。因为规则在现代道德观念中占主导地位,而尼采拒斥和摈弃现代的各种规范伦理,无论功利主义还是康德式的,提出“重估一切价值”“必须创造有关善的东西的新清单”等。[1](P63)尼采对现代道德的批判始终是在自由个人主义与亚里士多德传统之间展开,在推崇超人式权力意志的同时又陷入道德唯我论。
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美德乃是有目的的选择之目的的正确性的原因”[1](P187)。善是人类本性所趋的目的,人的每一种活动、每一种探究、每一种实践都旨在某种善。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善便是美德,美德也便是善。而在麦金太尔看来,并不是所有的“善”都可称为美德,善有三个层面:内化于实践的善、个人生活的善和共同体的善。[1](P189)个人生活的善和共同体的善皆必须由内在的内化于实践的善来完成。人因社会角色不同,参与的社会实践以及体现的社会功能也不一样。但不管如何不一样,人在履行其各自的社会角色时皆能获得相应的善。他用“内在善”与“外在善”来进一步阐明。“内在善”是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潜能(如下棋的快乐)只能在相关的实践(下棋)中获得,而“外在善”是出于功利效应(如对地位、财富、名誉的追逐)也能在其他活动中得到。内在善(内在利益)不仅对行为者本人是善的,而且是利他的。而外在善,对行为者本人来说相对要“恶”,是利己的。因为行为者是出于利益的考虑而为之,一个人对财富、地位、名誉的追逐必定会产生竞争,而竞争必然就会有输和赢的较量。
麦金太尔高扬“内在善”,将“内在善”称为一种卓越的品质,并用“卓越善”(goods of excellence)与“有效善”(goods of effectiveness)来区分“内在善”与“外在善”。[4](P220)在这里,“卓越”便是一种美德品质。内在的善体现了人在某种实践活动中的性情和行为的卓越,而这种卓越对所有人是有益的。有效的善是指财富、权力、声名等等。麦金太尔站在亚里士多德的立场,高扬内在善,贬低外在善,显然有失偏颇,因为实践是人们履行社会角色的行为,这些行为有可能是相互冲突的,而且不同行为之间的冲突必然引起善的冲突。如外在善,对金钱的合理追逐可以为人的幸福生活提供一定的保障,对名誉的合理追求可以为人的存在获得能力的认可及价值的实现,等等。为解决此冲突,他从“内在于实践的善”过渡到“个人生活的善”。而追求个人生活的善不是重点,重点是为达到目的而努力的过程。在这种追求的过程中,人遇到的各种痛苦、迷茫、危险、诱惑、挫折、坎坷等使人更加领悟到追求的最终目的,使人获得善的知识和自我知识。[5]
麦金太尔并不是反对外在善,而是强调对善的目的的追求过程比结果更重要。也就是说,在追求善的过程中,一定是要合乎道德德性与理智德性的行为。那么,我们如何展开对善的追求?善的目的为何?在不同的时代,处于不同的境况,每个人的目的(个人生活的善)是不同的,这样就推导出社群主义的善。任何一个人都必然生存于某种社群之中,从属于这个社群中的一员。作为个人存在的人需要“个人认同”(人格的统一);作为社群成员存在的人需要“社群认同”(价值实现)。社群可以小到家庭、宗族、友谊、小群体、单位,大到国家、民族。所以,在麦金太尔看来,最高的善的目的,即个人与社群的统一。人的最终目的不是追逐金钱,名誉、权利等等,而是自我价值在社会群体中得以最大化的实现,也即通过利他的行为,提升自身的价值。
三、对解决当代道德困境的启示
伴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而来的大量外来文化,使整个社会照搬西方的市场竞争机制,却忽视与市场自由竞争机制相伴相随的文化因素的制约,导致市场秩序既缺失规范道德,又无视传统美德。[6]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这个比喻,不是要市场去道德化,而恰恰是强调人的道德情操以及市场和社会的自由道德价值。另外,为了促进社会经济的飞速增长,“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思想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消费主义取代新教伦理成为支持当代消费社会发展及经济增长的信仰支撑。人就是消费者这一符号的产物[7](P5),对超越物质性的宗教、内在善、卓越品质等“善的目的”嗤之以鼻。在消费观念的主导下,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就体现在消费的质与量。所以,无尽的欲望、焦虑、困惑、虚无等成为时代特征,并因此造成自私、自利、冷漠、虚假等道德混乱的社会局面。[8](P118)
中国当前的道德滑坡,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统文化的失落,二是西方文化的入侵。从传统文化而言,不断扩张的城市化进程,使人脱离传统生活的土壤,陷入一种无根之感。经济、科技的巨大冲击,使人的生活、思想观念呈碎片化状态,人与历史、人与传统、人与社会断裂。人们急于摆脱贫穷,追求个性、追求欲望,因此,也急于摆脱传统文化与思想的桎梏,用物质及用消费数量与质量来衡量成功。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文化的引入更是加速了传统文化的断裂,好像凡是传统的就是落后的,都要批评和变革;凡是西方最新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都是值得效仿与追逐。
所以,从个人道德的消极方面来说,对“外在利益”的追逐已是时代特征,人在时代的裹挟下皆是“偶然所是的人”。另外,从个人自由的积极方面来说,新经济的时代背景下,某些传统的道德特质已适应不了当代人的道德需求,不断贬值,而新的美德,如创新、进取、独立、自主等不断升值。新的时代,经济发展的趋前与道德伦理思想发展的滞后致使传统的伦理观已无法再满足人的目的需要。然而,人的美德需要仍然存在,所以,我们必须探索新的能满足当代人需求的新伦理观,在此社会背景下,麦金太尔的美德转向便有了很强的现实启示意义。
从社会层面来说,要将过去的传统美德、过去的精神资源为现代所用,构建一种现代社会的伦理框架。因为传统就是因践行一种善的品质而维系,并承接过去、面向未来。作为社会,相较于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先要建立一个有规矩(法律、制度、有利于提升社会文明并促进社会进步的传统习俗)和长远价值追求(有利于子孙后代良性发展)的社会。社会要引导个人正确认识自身、树立信仰,正确地履行人生的职责与义务。作为社会中的个人,要学会换位思考、将心比心,从而具有一颗追求内在善的“利他”之心。
从个人层面来说,个人与自身、家庭、职场、他人、社会,建立一种既合乎道德伦理又合乎规范伦理的新的时代背景下的伦理观,才能促进人的身心发展,既有利于人的善的目的,又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没有人的自我意识的认识是不可能做得到的。人在各种与自我相连的关系里,只能沦为一种功利性、实用性的工具。自我意识是对自我的反思以及自我忏悔的精神,只有具有了这种精神,人才能在各种关系中具备善的品质。不能只是一味地指责道德混乱、批判道德,在批判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如何构建新的美德伦理。
按麦金太尔对道德的历史考察,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和个人的价值取向(善的目的的选择);二是在这些价值取向上取得的实践成就。第一个方面是根本。倘若价值取向出现问题,那就谈不上成就。因此,要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准必须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哪一种价值取向是善的价值取向(善的目的);哪一种是恶的价值取向。对于可取的价值取向,社会要营造积极气氛,追求一种共同的善。对于不可取的价值取向,则应该寻求转化,使之朝向善的价值取向。不管是对善的目的的追寻,还是由恶(各种各样的欲望)转化为善的选择,道德的实践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因为在过程的实践中,善的目标会不断地重新确定。
四、结 语
“我应该成为何种人”“何种生活目的才是值得追求的”,是每个时代都在深思并努力解决的问题。当前时代,由于传统社群的瓦解,取而代之的是由职场和陌生人组成的公共空间,自我的社群角色变成职场角色和公共交际角色,由于自由主义权利的泛滥,社群与自我不再是传统的从属的关系,而是现出对抗与分离、操纵与被操纵的紧张关系。“社会世界无非是各有一套自己的态度与偏好的个人意志的交汇处、一个满足其个人欲望的竞技场。”[1](P31)失去了传统社群角色的自我,在当前的社群中只关注个人的利益得失,对社会利益和他人利益毫不关心。一旦个人利益的实现遇到他人、社会之间的关系便会呈现出对立的状态。在这样一种以利益为目的的价值观里,他人、社会永远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自我更容易迷失自身,陷入更大的虚无、困惑与矛盾。而由法律、法规等维系起来的规范道德,虽然能维系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但在其冰冷、理性的背后,却不乏麻木而冷漠的灵魂。麦金太尔的美德转向为我们解决当前的道德困境提供了重要启示。当代美德既需要亚里士多德式的传统美德,又需要构建新的与时俱进的规范伦理,既需要理性主义的规范道德,又需要超越规范,上升至美德道德。可以说,当代美德是一种在传统与现代、理性与情感之间的“调和”,美德不在最终要达成的结果,而在不断追寻美德的实践过程。
[1](美)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追寻美德:伦理理论研究[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2]邓晓芒.康德自由概念的三个层次[J].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3](德)弗里德里希·尼采.论道德的谱系[M].谢地坤,宋祖良,程志民,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3.
[4]Alasdair Maclntyre.After Virtue(second edition).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84.
[5]姚大志.麦金太尔善观念的批判[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
[6]梁健惠.论我国社会转型期道德与经济的协同发展[J].湖湘论坛,2016,(4).
[7](美)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M].毕聿,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8]包亚明.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