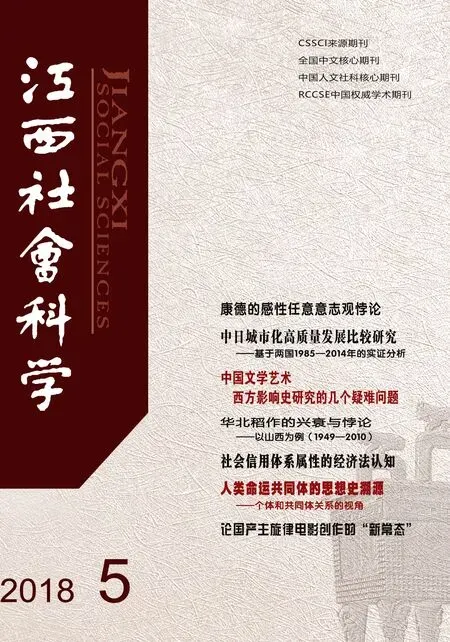自由与道德的目的:康德历史哲学诠释
何兆武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康德也懂历史吗?》。乍一看,只是觉得题目很炫酷,细考究,觉得颇有深意。的确,历史对康德而言是一个陌生的领域,这一点康德自己也不否认。但他认为,历史的研究有两条路向,一条是从经验到规律的路向,另一条是从规律到经验的路向,它们分别体现了普通历史学家与历史哲学家不同的致思取向。在康德看来,阐释、罗列历史事实是普通历史学家之所为,而在哲学家眼里,辨析历史事实背后的观点和理念、统一性和目的、意义和价值,才是自己需要做的工作。建基于后一种理念,康德寻找到的先验规律便是历史是自然与自由的统一,并且是目的论基础上的统一。
一、自然与自由
历史是人的历史,人作为现象界的一分子,一切行动必须符合自然律,作为本体界的一分子,又需符合自由律。符合自然律,亦即不违背“天意”,符合自由律,亦即不完全限制自由。
关于历史中自然与自由的关系,康德在1784年的 《关于一种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的理念》一书的第一段讲的非常明晰:“历史仍然可以使人希望:当它宏观地考察人的意志之自由的活动时,它能够揭示这种自由的一种合规则的进程。”[1](P24)这句话有三个关键词:“希望”“自由”“规则”,历史是按照“规则”(天意、自然)行事的,并因人的意志“自由”造成其合规则(规律)。由是,历史既不是绝对的必然性,也不是绝对的偶然性,它体现了“天意”和“自由”的张力,这种张力给人以面向未来的“希望”。面向未来的给人以勇气和希望的历史,必然具有“预告性”或“预言性”。如何实现其“预告性”或“预言性”,传统的做法是从经验总结推知规律,即在知识论的意义上预言未来之可能。但要在知识论意义上预言未来之可能,则必须在全部原因基础上推出必然的结果,而要想穷尽事件之全部前因,在知识论意义上是困难的或者说是不可能的。康德认为,由经验所得出的综合不具备绝对的必然性,只有先天性的综合判断才能克服经验的偶然性,从而具备绝对的必然性,才能打破天意颠扑不破的地位,留给自由以适当空间。
这个理解体现了康德独特的历史观,即人类历史是在自然与自由的张力下发展起来的,包含自然和自由这两个重要方面。历史具有时间属性,所以它必定与因果性、必然性相连,即便是人类的自由意志,也是人类的原始禀赋(自然)发展的产物,且是其按一定规律发展起来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自然法则影响了自由法则;同时,人类的自由法则又会作用于自然法则,使历史呈现二元性或二维性,并倾向与自然法则保持一致,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法则又关联着自然法则。
具体而言,康德在澄明“天意”和“自由”、“自然”和“自由”概念时给自由留下余地:
从它那机械的进程之中显然可以表明,合目的性就是通过人类的不和乃至违反人类的意志而使和谐一致得以实现;因此之故,正有如我们还不认识它那作用法则的原因的强制性而言,我们就称之为命运;然而考虑到它在世界进程之中的合目的性,则作为一种更高级的、以人类客观的终极目的为方向并且预见就决定了这一世界进程的原因的生成智慧而言,我们就称之为天意。[2](P28)
“自然”常常被康德称之为“命运”“天意”,但使用“自然”概念“凸显合目的性”,而“命运”则强调我们因不认识“作用法则”受到的“强制”,“天意”影射决定历史进程的深层智慧。康德在著作中讲到用“大自然”更好,因为较之于好像与上帝的意志相连的“天意”(康德之所以提到“天意”,虽有他自己的想法,但总有似无实有地关联起上帝的意味),这是一个“谦逊”而“不狂妄”的用法;用“命运”(康德没说,但可逻辑地推出)又容易导向宿命主义和悲观主义倾向。
虽然把“自然”(“天意”“命运”)放到研究历史的首要出发点和历史的主体,是康德非常明确的态度:“一种造物的所有自然禀赋都注定有朝一日完全合乎目的地展开。”[1](P25)但是,康德区分自然、命运、天意的态度表明,他想为自由留下一定空间。他深刻地觉察到,如若没有自然之必然性,而只有盖然性,那将是可怕的。但只有必然性的历史更可怕,所以历史不仅是自然,而且还要实施“隐秘计划”,这一隐秘计划就是自由的计划。
人类脱离自然状态实现自由,才能得到发展,而这种发展是以人类自身的努力为前提的。自然与自由在历史领域中的张力根源于历史的主体是“人”的矛盾性。历史哲学就是要解释,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如何服从自然的必然性过程中创造并推动历史。由是,康德在提到“历史”作为“自然”的“隐秘计划的实施”时,还用了“在宏观上”“可以把……视为”两个词,他是想通过这种非独断论的论述表明自己对“自然”和“自由”在历史中的张力态度:历史无自然则空,历史无自由则盲。因为自然不能统观历史,否则人就是自然的奴隶;自由也不能统观历史,否则历史就是偶然与杂乱无章的交集。但可以确定的是,没有自由法则,历史一定不能称其为历史。
二、自然史与道德史
为了进一步阐明历史是自然的历史还是自由的历史,康德引入《纯粹理性批判》中的两个著名观点,考量人类心灵的机能活动或者事件,从而得出“自然的历史从善开始,因为它是上帝的作品;自由的历史从恶开始,因为它是人的作品”[1](P118)。
康德主要从经验和智性两个方面来考察人类历史发展。从经验的角度看,人类历史开始于恶,人类刚刚开始使用理性时,人的理性总是那么弱小,在它与人的动物本能发生冲突时常常伴随罪恶,人常常是无知并且不自觉地陷入道德方面的堕落状态。如果人只关注或只看到人类的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或是人世间发生的一切恶的事件,就会对人的自由乃至人性产生怀疑,因为人是在运用自由时犯错的。依据这种观点,人的自由度越大,犯下的罪行越大,除非对人类的活动进行限制。从此种观点,常常会得出三种历史观:第一种认为人类会趋向于更坏的境地,最终走向灭亡(康德称之为恐怖主义的人类史观),第二种认为人类的行为是不断趋于善和向善的(康德称之为幸福主义的人类史观),第三种认为人类历史像西西弗斯所推的巨石一样,一旦达到山顶,巨石就会滚下。
之所以形成关于人类历史的这些争论,实际上也是因为它们从经验现象的角度看待历史,就容易得出类似卢梭和基督教的结论。卢梭指出,一切出乎造物主之手的,都是好的;一经人手,就变坏了。基督教也蕴含着人一旦运用自由就会犯错的观念,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一旦拥有自由,就偷吃禁果,这就是原罪。按照康德的观点,这些都是运用经验的观点容易得出的结论,但这恰恰对历史、对自由的误读。
在康德那里,以超越的智性观点看,人类的意志按照自由法则使得人类由坏向好、由野蛮无知进展到高度文明,并达到道德,“这样一来就(由于普遍性)证明了人类在整体上的一种品性,并同时(由于无私性)证明了人类至少在禀赋中的一种道德品性,这种道德品性不仅使人期望向着更善的进步,而且就人类的能力目前所能及而言,其本身就是一种进步”[3](P82)。以智性的观点考量的历史就是道德史,历史中的人就是兼具道德禀赋的人,即具有自由意志的人。因为“善恶”出自人的自由,并非出自自然,因此是道德问题,而不是必然问题,也不是知识问题,因为必然与道德、事实与价值它们分属不同的领域,而且严格说来,道德善恶与人的感性欲望不是一回事。
依据超越的智性理论,康德指出:
人们要求有一部人的历史,确切地说不是一部关于过去时代的历史,而是一部关于未来时代的历史,因而是一部预言的历史……如果要问:人类(总的来说)是否在不断地向着更善进步,那么,这里所讨论的也不是人的自然史 (例如将来是否会产生新的人种),而是道德史。[3](P76)
为什么道德史是预言史呢?因为道德的问题不是“是”而是“应当”的问题,换言之,不是“实然的问题”而是“应然的问题”,所以,道德不是曾经做过什么,而是应当怎么做、应该有怎样的道德担当的问题。
预言的历史是对未出现、未在场的事件进行阐释,预言的历史不能穷尽所有可能的原因,所以预言的历史必然是先天可能的,而且其可能性不在人之外的世界、人以外的自然,而只存在于作为预言历史的主体人身上,即从人的先验主体性中开出整个历史。雅斯贝尔斯认为,康德的历史哲学要求历史学者能够在他们趋向理念的态度指引下去研究历史事件。
康德运用超越智性的观点,以“预言的历史”的视野分析法国大革命这一时髦的历史问题,得出了不同于旁人的结论。他没有把法国大革命作为一个经验的事件来分析,既没有分析法国大革命的利弊得失,也没有阐述法国大革命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对人类进步带来的不可比拟的成绩,而是作为一个理性的旁观者把法国大革命上升为道德事件,认为应从超越智性的角度看法国大革命的内在道德倾向。从观众同情的角度看,那些没有亲自投入法国革命的人普遍地表现出对革命者的同情,这种同情甚至建立在冒犯党派性的风险之上。从革命者的热情看,革命者对于革命更是表现出理性的热情。从这两个方面看,这一事件体现了人类全体禀赋上的道德性,它不仅说明人类有希望,而且也说明人类具有不断改善的希望和可能,人类有向善的灵明。基于此,历史是道德史,并且是可预言和预见的。
三、社会性与非社会性
正如基督教的观点“自由造成了恶”表述的,人性中有恶的成分,而且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巨大的恶(天灾人祸)把人类辛苦建设起来的成果毁灭,不能回避的理论问题就是,既然自由既可向善又可择恶,那么,恶到底在历史的发展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康德的基本观点是,历史发展中的确存在着物欲横流与理性向善的张力、罪恶与进步的张力,而且人类历史恰恰是在这种张力中进展的。
康德提出了“非社会的社会性”。他认为社会的和谐统一,并不一定是像卢梭等哲学家设想的那样,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一致(社会性),也有可能在于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斗争和竞争(非社会性)。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与竞争是“从野蛮到文明的真正第一步”,即便是魔鬼的非社会性,也能成就天使的社会性,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它还是必需的。
历史不能仅仅分裂为对立的两类:好与坏、善与恶。事实上,这两类事物相互关联,并没有明显的界限甚至不可或缺。这两类关系体现为,在某种状况下是好、善,在另一种状况下可能是坏、恶,反之亦然,但无论好坏、善恶都有助于大自然意图的实现,善恶之交替促动了人的发展。康德在《人类历史起源臆测》中清晰地分析了人类理性发展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人的饮食欲望扩大的阶段。人的饮食欲望最初与其对象是直接的关系,随着理性的发展,人借助想象力创造出超越本能的欲望。当人出于好奇为树上的果子吸引,并不顾本能排斥,品尝这个果子时,人就迈出了有历史意义的一步,开始与自然决裂,但这时人类对自己运用理性的状况还一无所知。第二阶段是人与人之间的吸引关系(爱情关系)超越了感官欲望而代之以理想的吸引力,艺术与道德产生。到第三阶段,人类不止满足于生活在当下,还会思考未来,并因未来之不可预测而产生恐惧、焦虑情绪而无法自拔。第四阶段,人类意识到自己是大自然的真正目的,是大自然的宠儿,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意识到自己与动物的区别,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进而断绝了和纯自然状态的关联,开始依据自己的理性而非本能行事,这是社会状态的开端。
一方面,人具有社会化的倾向,这种倾向使人进入社会,获得安全感,使人认为自己的自然禀赋能够通过社会得以发展;另一方面,人又具有单独化的倾向,因为理性的人想要运用自己的理性和意志,自由地控制、支配一切。这样两种撕裂的倾向使得人的活动常常受阻,但正是这种观念阻力把人的全部潜能唤醒,使其努力“克服”自己的“恶”,并使得人不断地由“野蛮”进化到“文明”,“人类全部才智”不断发展,逐渐形成“趣味”,并通过“不断的启蒙”开启新的思维样式,从而把“病态地被迫组成了社会的一致性”,转化为“道德的整体”。
在康德那里,善是一种禀赋,恶是一种倾向,正因为善是作为禀赋而存在,所以人有希望,因为恶是倾向性的,所以善恶会相斗,但善最终占上风,于是历史是由恶向善的进展。
“非社会的社会性”使人不盲从于追求绝对安逸和睦,但此种非社会的社会性又不能过强,因为当其强烈到使人灭亡的地步时,历史就不复存在,所以它应该以这种对抗性终将成为人类合法秩序的原因为限,亦即它使人们意识到,要建立合法的秩序、形成公民宪法,从而使人在适当的环境中使自己的自然禀赋得到充分而全面的发展。
由是,人作为自由者就意味着即便是对于作为大自然的作品的对象也需要道德的拷问,自由比自然有了更为现实的、更深入人心的意义。以自由—道德的视角观测善恶,就会发现,自由是善与恶的根源,这意味着不仅善出自自由,而且恶也可能与自由相关。虽然恶出自自由而非自然,但规定自由的道德律却是善,恶也只有在与善在这一层次的关联中成立,即它只能构成对善的挑战、反抗与否定,但绝不能抹杀善,因为一旦抹杀了善,就抹杀了道德法则,就抹杀了自由,进而就抹杀了恶自身存在的可能性。人在绵延的时间中展开的活动构成历史,历史是趋善的,所以是我们可以预言的。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历史不是自然史,只能是道德史,它不可能是恶的无限累积以至更恶,也不是善的无限累积以至无限美好,亦不是循环往复如。历史体现为善的进步、趋善和向善,它体现为在与恶作斗争中善的不断开显和展开,体现为人的理性—自由—道德这一内在秉性的不断外化和凸显。虽然这一过程绝不会是顺利的,但依据康德的观点,我们也应在理性上确信这一未来。
四、历史与目的
作为道德史的历史必然包含着人的目的,这是康德的逻辑推断。虽然康德的历史目的论一直饱受诟病,并常常被作为不合时宜的“神学残余”,但目的论在康德的历史哲学中起到桥梁和贯通的作用,它直接导向自由。
严格说来,历史目的论应该称之为历史的合目的性,它指的是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寻求到一种具有调节意义的终极目的,并以此目的来把握人类历史,从而使历史具有意义。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已有对目的的阐释,自然概念本身是遵循因果律的,但人基于判断力可以发现其合目的性。正是依凭判断力特别是反省的判断力,人的实践的合目的性可类比于 “自然的合目的性”。他把此理论运用到历史中,提出了从自然目的论到道德目的论到历史最终目的的理论,这也是一条从应当到目的再到历史的理路。在康德看来,人类历史就是自由的人不断趋善的过程,就是善及目的的理念在时间中的实现历程。
康德提出,如果只用机械的原则解释自然,必然把人当成机器,于是人只有决定性,而不具备生成性,不可能兼容自由能力,“一种造物的所有自然禀赋都注定有朝一日完全地并且合乎目的地展开”[1](P25),所以需要提出一种目的论原则,以解释有机物尤其是人的活动。这种目的论不仅仅是关注事物之间的目的与手段的外在目的论,而且是必须引入实践性和方向性的内在目的性,即不管事物因何而在,其自身的各个部分都互为目的和手段。内在目的较之于外在目的,具有优越性,因为有机物是一种自组织之生物,可以自成目的。基于内在的目的论,康德把自然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亦即自然也是合目的的体系。把内在目的论引入历史哲学中,有深刻的考虑:一个原因是,康德并不相信理性是万能的,所以需要历史目的论来保证历史的进展;另一个原因是,康德的总体主义情结阴魂不散,相信历史必然有其意义。
内在目的或是合目的性原则并非客观存在的规律,它不能对事物的存在发展起构建作用,只能为人们理解和认识自然提供指引,所以即便把它看成规律,那也只能是主观调节性的规律。在这个意义上,目的论不能替代自然因果性,合目的性不是自然领域的概念,也不是自由之概念,而是一个联通自然与自由并使自然与自由的过渡得以可能的先验概念。合目的性与目的性也是康德与赫尔德的最大差别。赫尔德认为,通过类比,我们能够发现自然界、人类历史包含目的。康德主张,自然目的论只是好像存在,但人类无法证实。反思判断力在面对历史、自然时只能看作符合某种目的,所以历史过程是合目的的过程。
康德提出,人的理性和智慧对历史发展带来的可圈可点的东西的确存在,但人毕竟是有限的,所以目的论的引入非常重要,否则历史就会无目的、无意义,充满偶然性,而且令人绝望。人不是上帝,也不是无理性的动物。对上帝而言,一切都是可能的或现实的,所以不需要目的,而无理性的动物仅仅依靠本能,又不可能提出目的。人是地球上独一无二地拥有理性且具有自主选择能力的生物,只有人有资格作为“自然的主人”而存在,只有人才能作为“目的王国”的成员。在《人类历史起源臆测》中,康德深刻地指出,当人看到羊并且说,自然赋予羊的皮,不是为了羊,而是为了人,学会把皮从羊身上剥下来当成衣服穿时,他就觉解了他就是自然的目的。
依据自然目的论,人之所有禀赋都是合目的的发展,在此过程中,科学、艺术等获得了发展,人类文化进步、教养水平提高,人由自然状态逐渐向社会状态过渡,这一过程也是激发人的理性进一步发展的方式。大自然的“隐秘计划”由于这样一个合目的性而逐渐实现。
但是,人的自然禀赋的发展不是自然而然、和谐无碍的发展,人既要“社会化”,又想“非社会化”,既要合作,又要占有。那么,人类如何进展,才符合大自然的最终目的呢?当然是向真正道德而非虚假道德的发展,而且是实现道德自由的状态,并且达到至善。康德和卢梭的不同就在于,卢梭既不完全相信人能完全社会化,又不相信人完全属于自然,而康德能提出“非社会的社会化”,是因为他相信目的论。尽管历史充满了不幸,但历史也能实现从坏到好的进步,因为历史是有目的的,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也逐步迈向真正的道德。
道德是目的或者说道德自由是目的,就是说道德人自己给自己规定目的,并且它不受其他目的的规定,但对其又不能作具体的规定,否则就会导致只看目的而不看手段,因为只有手段正义才能保证目的正义。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的进程就是有道德的理性人的目的性的展现。但是,历史常常表现为,由于人性中的不可移易的向恶,导致社会生活中的冲突和矛盾频发,使很多人包括有些精英学者们都认为历史是倒退的,体现为与科技的进步相伴随的,是道德的沦丧。康德抱着积极的乐观主义的态度,认为人类历史尽管充满了罪恶,充斥了愚蠢,包含欲望,但它在朝着改善前进,人类历史由自然状态走向自由状态,体现为道德史。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方向和目的是至善,它体现了自然与道德、自然目的与道德目的的和解。它作为一个调节性理念出现,具有指导意义,但它意义重大,它展示了人的自由与尊严。
康德这里提出的至善已然不同于第二批判中实现德性与幸福统一的至善。第二批判中的至善是彼岸的、不可能实现的,它表征的更多只是康德的无奈和向往,但这里的至善却可以作为人类的一种希冀,它就在此岸,尽管人类不能实现,却可以无限接近它。约威尔清楚地阐释了这一点:
在前两大批判中,康德更倾向于把至善理解为分裂的且在我们之外的世界……但是,从第三批判起,康德的至善概念发生了变化。至善自身变成了创造的最终目的……尽管至善离我们异常遥远,但却真实可靠,它实现于道德意志和经验实在的实践中。至善不再把世界分裂为两个,而是包含了理想和现实的同一个世界。一言以蔽之,它变成了历史的目的。[4](P72)
既然至善有现实维度,那么人们就可以有促进至善的努力,一方面,发展自身的理性禀赋;另一方面,推己及人,即运用发展起来的理性创造新世界,形成“各民族的联盟”“国家共同体”,达到“完美的公民结合状态”,实现世界“永久和平”。这样,在第二批判中作为德性和幸福的统一的超验的至善就来到了“世俗”的人类世界。
之所以能顺利实现这种转换,是因为康德关注的不再是个体的人及其幸福与德性,而是处于社会中的群体的人,个体的人是有死的,有限的,它无法实现灵魂不朽,所以必然无法实现作为幸福和德性的统一的至善,而群体的人或者人类是能够实现“灵魂”之延续,人类通过代际传递,能够实现从野蛮到文明,从自然到自由的发展,而人类历史则能够实现从自然史到道德史的变动,从而越来越趋近于终极目的至善的。此时,作为一个前提存在的上帝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因为重要的不是上帝怎样,亦不是上帝对我怎样,而是我怎样。即便考虑到上帝,那么这种考虑也只能体现为上帝赋予我们的道德以神圣性,并且使我们的生活方式更道德。
[1](德)伊曼努尔·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M].李秋零,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德)伊曼努尔·康德.永久和平论[M].邓晓芒,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3](德)伊曼努尔·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7卷)[M].李秋零,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4]Yirmiahu Yovel.Kant and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