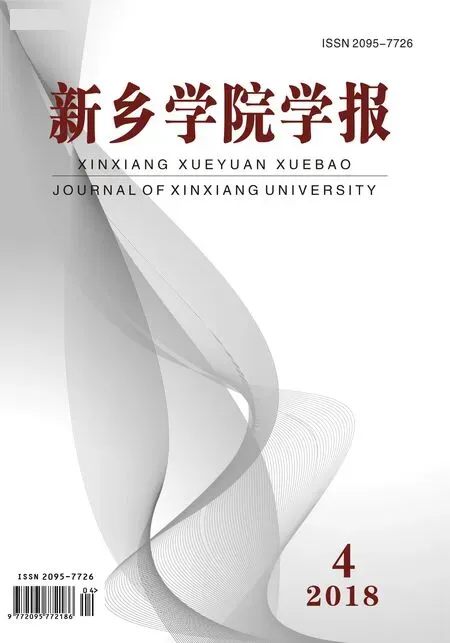走在“学古”与“创新”的平衡木上
——试析黄庭坚“宋诗”地位确立的源流
陈娜娜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基础部,河南 郑州451100)
黄庭坚对后世的影响,最大的方面无疑是在文学上。作为开宗立派的一代诗人,黄庭坚虽师法杜甫、陶渊明,但却摆脱了两位诗人的坎坷命运,在当世就得到认可,被公认为宋诗风格的典型代表。自然,这也使得发生在他身后的诗风的演变、诗学的论争每每表现为对他诗学观的贬抑、离合。可以说,他对中国诗歌的影响一直维持到近代,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历史进程相终结。笔者从三个方面来寻求黄庭坚宋诗地位确立的源流,并全新审视黄庭坚的诗学观及其对中国诗歌的影响。
一、黄庭坚诗学体系的建构
黄庭坚的诗被视为具有独特风貌的宋诗的代表,在宋诗的理想范式方面,具有他人无法比拟的典型性,反映了北宋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现象和宋人独特的文化心理。可以说,黄庭坚诗学体系的建构,是宋代特定历史时期的现象。
(一)宋代特定的社会背景
北宋时期,社会始终处于动荡不安的状况,重文轻武的国策使北宋处于积贫积弱与内忧外患的状态,北宋士人再也没有了唐人那种追求建功立业的气魄。而频繁剧烈的党争迫使诗人避祸以保其身,在背离现实的处境与惶惑迷惘的心境中努力寻找自我的地位与价值,其作品更多地反映了个人生活的狭小范围和心灵世界的内省体验。黄庭坚也不例外,他所能做的只是抛却政治一端的纠葛,倾毕生精力致力于诗歌创作和理论探索,着意于学习陶渊明、杜甫、白居易及韩愈等人的创作,心态渐趋于内敛而非外张,喜深微澄静而非壮阔飞动。黄庭坚的诗多能反映北宋的社会文化背景,观照北宋士人的文化心态,故而吸引了一批文人墨客的追随,在北宋诗坛独树一帜。
(二)北宋的学术文化氛围
北宋统治者重文轻武,大力倡导释道,对隐居山林的僧道恩宠有加,主张三教合流。道家那种自然无为、存神养气的生活态度和释家那种心性本觉、随缘自适的禅悦情趣,对士人的心理和思想均影响极深,反映在作品里就是“理学”思想的渗透,使宋诗独具理性意识和思辨色彩。事实上,理学恰恰适应着北宋士人当时转向心性的心态,也促使士人们注重个性才情的发挥和群体道德的自觉等主体人格的建构,进而形成宋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精神特质,养成一种清静平和的文化性格和自然适意的人生情趣,并在创作上形成了一种追求平淡清远的思想倾向。黄庭坚就是这样一个在文学的诸多领域都有较深造诣的人,他倡导士人注重内在品性的修养,使刻苦读书成为一时之风。黄庭坚从“理趣入诗”的角度出发,主张“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他所说的“学问”是指各种思想和创作技巧。他很重视用典、句法、用字、声韵等方面的才学和功力,主张“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点铁成金”等观点。黄庭坚喜好用典,以此点化前人的诗意或诗句。如“百年中半夜分去,一岁无多春暂来”是点化白居易《寄元九》中的“百年夜分半,一岁春无多”。黄诗求深务奇,力求“无一字无来历”,也是建立在博学的基础之上,达到“以学问为诗”而“自铸伟词”。
对于诗歌技艺已成熟的唐诗,宋人除了易其蕴藉空灵为深刻透辟之外,还在技巧上想以人力夺天工。李东阳说:“唐人不言诗法,诗法多出于宋。”这一现实要求黄庭坚只有提出自己的创作纲领,才能领导有宋一代的新诗潮,确立其在宋代的诗学地位。
(三)黄庭坚及其成员的性情与修养
黄庭坚之所以能成为开宗立派的一代诗人,与他追求创新、兀傲脱俗的性格和博学多闻的才情是分不开的。一方面,黄庭坚出身于学者世家,他早期思想深受其父黄庶和岳父谢师厚的影响,这一点,宋人已经注意到了。《后山诗话》云:“唐人不学杜诗,惟唐彦谦与今黄亚夫庶、谢师厚初学之。鲁直,黄之子,谢之婿。”而二人学杜,主要在于学习杜诗既学古人以继承传统,又大胆创新而力求超越古人的变通态度和求变精神,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黄庭坚学杜、学韩、学陶。黄庭坚做到了学杜而不袭旧,强调师法中有变革,继承中有创新。另一方面,黄庭坚是一个以创变精神为内驱力的艺术家。他多次申述:“随人后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题乐毅后》)黄庭坚不甘“随人后计”“践前人旧行迹”,他奋力开一代新诗风,与唐诗平分秋色。自身的个性注定了他会成为那个后来居上、后浪推前浪的人。在元祐时期,黄庭坚的诗名越来越大,超过苏门的其他作家而足以与苏轼相颉颃。苏、黄的不同诗风形成了宋代诗坛双峰对峙的局面。正如刘克庄后来所说:“元祐后诗人迭起,一种则波澜富而句律疏,一种则锻炼精而性情远,要之不出苏黄二体而已。”[1]就连最初未曾谋黄庭坚之面的苏轼在 《答黄鲁直书》中也对之推崇有加,言:“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将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称扬为!然观其文以求其为人,必轻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苏轼高度评价了黄庭坚的人品和才华,也指出了其兀傲脱俗、难为世用的禀性。尽管后来党锢之争让黄庭坚仕途坎坷,经受颠沛流离的生活,可他的才华与名声还是吸引了远近的文人学子来向他求教请益,他也热心于指导青年,共同切磋讨论,创作与理论兼重,实现了开宗立派的事业。黄庭坚就是这样一个以创新精神为内驱力的兀傲脱俗诗人,他将自己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诗歌创作和理论构建上,提出了较为全面、系统、便于操作的诗学观,为宋代的诗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黄庭坚诗歌的价值观
宋初,文学领域内兴起了一场诗文革新运动,在诗坛上主要有“晚唐”和“西昆”两个派别。但无论是晚唐派还是西昆派,都未能较好地承担文学为社会政治服务的使命,故北宋诗文革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二者进行反拨。首先是高扬儒家的文学价值观,提倡诗骚感事而发、美刺比兴的传统,以诗歌反映国事民生,发挥道德教化的功能。其次是开创新的诗歌风格,变浮浅靡丽为质直古雅,使诗内蕴劲、气骨健,这就是宋诗特有的“气格”。黄庭坚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步入诗坛的。对这场诗文革新运动,他又是持什么立场与态度的呢?流行的观点认为,黄庭坚所代表的诗学倾向力图以学问和技巧来补救宋初以来诗风柔靡的缺陷,从而背弃了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走上了新的形式主义道路,成为诗文革新的逆流。这一观点现被各种文学史著作所袭用,陈陈相因,几成定论。许多学者因于教材的定论,对山谷诗心怀惶恐,避而远之。而今笔者细品其作,查其背景,方感文学史言其轻视思想内容、只重形式技巧是皮相之论,是将他的理论与创作脱离了宋诗发展演变的历史的偏颇之辞。事实上,无论是赠答、唱和的抒情诗,还是题画咏物之作,它们都承载了一种理想人格,有时竟谐谑成趣令人会心解颐。史论黄庭坚太重形式,只因黄庭坚的“道”与传统疏离,由指陈时弊、发愤鸣不平而内化为怨而不怒、重道德人格。
黄庭坚的诗学要义集中表现在 《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一文中。此文最后署曰:“元符元年八月乙巳,戎州寓舍退听堂书……年五十四。”说明此文作于他贬谪戎州时,可以被视为黄庭坚对自己诗歌观的一个总结。概括言之,这段文字阐释了三个问题:一是诗歌的本质,二是诗歌的风格,三是诗歌的功能。
(一)诗歌的本质
黄庭坚在《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认为,诗人必须加强道德修养。在黄庭坚看来,人格美是构成诗美的内核,强调了道德人格修养对文学艺术创作的决定作用。“不俗”正是黄庭坚执着追求的人格理想,也是他整个诗学观的内核。他每以是否“俗”来论人品诗。比如他批评晚唐五代诗坛点缀风月、纤巧琐碎和宋初西昆体藻丽浮糜的诗风。从表面上看,他所批评的只是其语言风格等外在形式,而实质上是对其思想内容贫乏的不满,二者融合而成的境界就是他所称的“俗”。相应地,他喜用“不俗”来赞扬艺术作品的成就和风格以及人的精神境界。他认为苏东坡就是不俗之士,在评论其诗词时云:“东坡道人在黄州时作,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2]在黄庭坚看来,诗品与人品是应该相提并论的,二者密不可分。对诗来说,所谓“不俗”,固然首先体现为作品的主题、意境、语言、风格等因素的高品位,但本质上它是高尚人品和修养的反映。
全面考察黄庭坚的诗论与创作,可以看出他是恪守儒家正统文学观的,他力图提高诗歌的思想意义,但是他的“道”已表现出与传统的疏离,尽管他也写了一些反映社会民生问题的作品,如《流民叹》《虎号南山》等,但他的创作重心已转向表现人格精神境界方面。所以用传统的价值观来衡量,他于诗歌的政教讽喻方面确有欠缺,于是人们对他有了现实主义不充分,甚至反现实主义的判词。他的抒情诗着力向内心深处透视,以刻画入微见长,如《再和答(林)为之》;描写人物之作与其抒情诗异曲同工,传神写照中展现了人物的精神风貌,如《戏赠彦深》;咏物题画及题咏书法、音乐等艺事的诗也多寄寓着他的人格境界,如《戏题小雀捕飞虫画扇》。总之,黄庭坚不同主题的诗最终都归结到了表现其人格与精神境界这一总主题上。但是也应该指出,黄庭坚的诗学与创作存在较大的局限。他关于“道”的含义较为狭窄,缺乏广泛的社会政治内涵。所以从总体上看,他的诗歌主题仅局限于表现文人的生活与雅趣,尤其是元祐以后的作品批判锋芒减弱,一部分应酬咏物之作意义贫乏,或罗列学问、枯燥说理,或作文字游戏、取笑调侃。
(二)诗歌的风格
所谓文如其人,作品的体貌决定于作家的思想品格,作品的艺术风格即艺术家人格在艺术中的外化。我国古代文论是用“气”来描述创作个性和诗风的。对黄庭坚独特的诗风,文学史上的评论有不少,最有代表性的说法是“清新奇峭”与“瘦硬”。笔者认为这两种诗风都只是黄庭坚不同阶段诗歌特征的一种表现,并不能代表黄庭坚诗歌的主导风格,其主导风格应是其人格的外化即兀傲绝俗。这从黄庭坚的代表作如《登快阁》《寄黄几复》中可以得到证实。翁方纲评《登快阁》说:“坡公之外又出此一种绝高风骨,绝大之境界,造化元气发泄透矣。”[3]方东树评《寄黄几复》说:“山谷兀傲纵横,一气涌出。”[4]此外,文学批评方法里有知人论世一说。在笔者看来,黄庭坚的人格既是天性使然又是时代所造,具体说,黄庭坚兀傲绝俗的人格和诗风,是特殊时代所铸成的。在严峻现实面前,他保持了兀傲绝俗的人格,经受住了考验,保全了节操。
黄庭坚前期诗风特征主要是清新奇峭,这是他尚“奇”诗学观指导下的自觉追求。“奇”是一种反传统、反流俗的品格,是与众不同、标新立异。一方面,黄庭坚要求继承传统,所以他教人博览前人的作品,从中揣摩文学创作的经验,学习经典作品的技法。但学古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超越古人。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在学古的基础上变古、创新,“以俗为雅”就是他翻新出奇的一个很好体现。“以俗为雅”取法于杜甫,但在黄庭坚那里得到了全新的发展与运用,他用民间俗语的质朴原始状态来调剂陈旧的文言,使粗俗的口语反显新奇之“雅”,使平庸的陈言顿显生新峭拔。黄庭坚以求奇创新的手法造成了清新奇峭的风格,表现了其兀傲绝俗的精神气质。到了元祐年间,黄庭坚处境得意,待遇优裕,生活安定,与苏轼、晁补之、李公麟等酬唱游赏颇乐。《次韵王定国扬州见寄》《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题郑防画夹五首》(之一)等,都是这类作品,它们将诙谐风趣与兀傲绝俗有机地统一,反映出黄庭坚以超然的目光审视生活的态度。而绍圣元年以后,黄庭坚先后经历了两次贬谪,特别是第一次的文字之祸,使他的诗学观发生了重大转变。《名贤诗话》云:“黄鲁直自黔南归,诗变前体。”黄庭坚在《与王观复书》中也说:“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他重建了诗学观:“皮毛剥落尽,唯有真实在。”(《次韵杨明叔见饯十首》之八),即诗歌要剥落浮华,返璞归真。在这种诗学观的指导下,黄庭坚的诗歌一改先前的清新瘦硬、诙谐成趣的风格为平淡朴拙的风格,而平淡朴拙正是陶诗的精髓,也是黄庭坚极力效仿追求的,只可惜他的诗虽有陶诗之神,但无其冲淡闲远之韵。《武昌松风阁》《池口风雨留三日》《书摩崖碑后》都比较好地体现了兀傲绝俗、平淡朴拙的风格特征。
以上我们描述了黄庭坚前、中、后三个时期的诗歌创作,可以看出黄庭坚三个时期不同的诗歌追求及明显的诗风差异。这种不变与变相辅相成、有机统一,既体现了黄庭坚迥异于唐人的创作风范,又不失自己独特的风貌。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黄庭坚对诗歌的创作,乃至一切艺术创作,都有一个根本的要求,就是在学古的基础上创新,学古与创新成了他创作论的两翼。黄庭坚是一位有着强烈崇古倾向的人物,事事以“古”为指归、楷模,但同时他又不以重复古人为满足,热切追求变古与创新,他既有继承传统的一面,又有“以故为新”的一面。他在理论与创作中,借助典故丰富、深化诗意,强调作家多读古书以拓展学问。他的这些做法给人以追求技法效果的深刻印象,从而招来了 “形式主义”的批评,尤其是他的“点铁成金”论以及惠洪转述的“夺胎换骨”说更使他蒙受了“剽窃模拟”之名。毋庸讳言,黄庭坚有偏重形式技巧的倾向,但他的本意主要是为了表现那种清高孤介、反流俗尚气节的精神境界,以体现其诗品乃至人品的不俗;通过这些技法的运用,他要造成奇硬、瘦健、朴拙、老成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与其精神境界是互为表里的。
(三)诗歌的功能
黄庭坚在《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中指出,诗可以产生移人性情的道德感化作用,也就是“闻者亦有所劝勉”。“故世相后或千岁,地相去或万里,诵其诗想见其人,所居所养,如旦暮与之期,邻里与之游也”,对诗歌的功能作了具体的表述。他从诗歌接受的角度说明了诗可以超越时空,使接受者受到诗人人格的感染,如同与之朝夕相处。
正是因为诗歌有如此重要的功能,古往今来的学者赋予诗歌强大的战斗性。有学者就诗歌的战斗性来批判黄庭坚的诗学,批判黄庭坚主张取消诗歌的战斗性。这是因为他们将“战斗性”仅仅理解为“怒邻骂座”“讪谤侵陵”的褊狭所致,殊不知“怨而不怒”也是战斗性的一种方式。我们不应该就理论而谈理论,而应该结合具体作品,看作者在创作时所进行的努力,看其诗歌所产生的作用。
三、知行合一的力行实践
难以置信,当时连一部理论专著都没有的黄庭坚,他的诗学观竟在宋代诗坛蔚然成风,并确立了与苏轼并驾齐驱的地位。我们发现,黄庭坚的成功正在于他的亲力亲为,他用实践总结出一套比较完整系统的诗歌创作理论,以此指导创作实践,使自己的诗歌理论在诗歌创作中得以强化,两者相辅相成,成为黄庭坚诗学观的最好推广。正是这样的反复讨论、操练、总结,让尽管没有成书的黄庭坚诗学理论变得较为全面、系统,便于全面操作,成为文人墨客心中的一部知行合一的学诗、论诗理论体系。所以,一种理论的建构既离不开时代文化背景,也离不开建构者本身的力行,只有这样,才能使理论与实践完美地结合起来。
四、结语
宋诗之所以能独立于唐诗之外自成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黄庭坚体”的确立,这对改变唐以来诗坛的风尚是有意义的。但其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苏轼当时就曾指出了:“读鲁直诗,如见鲁仲连、李太白,不敢复论鄙事,虽若不入用,亦不无补于世也。鲁直诗文如蝤蛑江瑶柱,格韵高绝,盘飨尽废;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5]综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黄庭坚的诗学观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尽管它存在着明显的时代局限。还有两个负面影响则是黄庭坚所始料不及的:一是使一批后学误入以书为诗的歧途而不能自拔,以致忘记了诗歌创作最主要的材料来源;二是一些后学为才力所局限,达不到运用自如、炉火纯青的地步,以致诗歌佶屈聱牙,不可卒读。从这种现象中,我们需要进行一些思考,即应该如何对待前人的经验,是学步而不逾规矩,还是从学步“悟入”诗法,进而自成一家。黄庭坚的伟大,就在于他走在“学古”与“创新”的平衡木上,确立了其作为宋诗代表的地位。
:
[1] 龙榆生.中国韵文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54.
[2] 朱祖谋.宋词三百首[M].施适,辑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56.
[3] 吴晟.黄庭坚诗歌创作论[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100.
[4] 孔凡礼,刘尚荣.黄庭坚诗词选[M].北京:中华书局,2006:104.
[5] 郭预衡.唐宋八大家文集[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7:6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