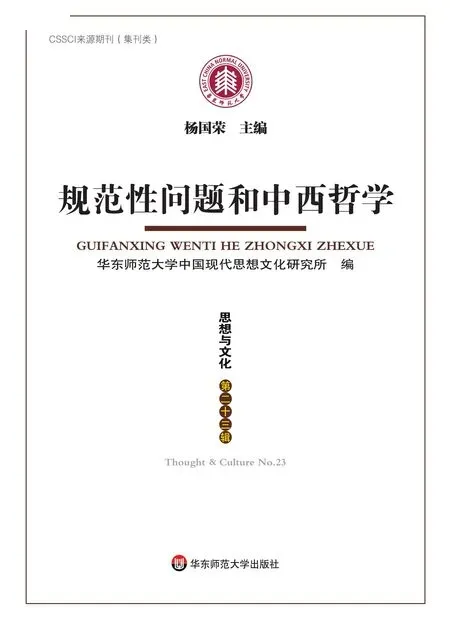萨特与波伏娃
●
1. 这把椅子留给萨特
巴黎有很多家咖啡馆,门口摆放着画有夸张图案的店标,整洁的古色古香的桌椅从店堂延伸到人行道上。黄昏时分,当塞纳河大桥与巴黎铁塔的灯光一起点亮,巴黎的一条条幽静的巷子里,手磨与碳烧咖啡的香味分外浓郁。花神、双偶、多姆等,是巴黎最负盛名的咖啡馆。
其中花神咖啡馆是巴黎文人、画家、学者最爱光顾的地方。波伏娃常去那里。每天差不多同一时间,波伏娃都会走进店里,坐在靠窗的位置。她性格沉静内敛,陷入沉思的时刻,更显得凝重与执着。她偶尔看着窗外的风景,人们惊艳于这位知性女郎的美丽侧影。
当侍者在她面前放上一盏拿铁的时候,她从手提包里取出一本书或一卷纸。有时她低首阅读,有时又埋首疾书。预先准备的一小瓶墨水放在离咖啡杯不远的地方,水笔在纸上快速移动,不多久就把一卷纸写完。除了巴黎高师的图书馆,花神咖啡馆是波伏娃最好的读写场所。细心的人们会发现,在波伏娃的身边,有一把椅子是空着的。
这把椅子专门留给萨特。与波伏娃一样,萨特也是花神咖啡馆的常客,人们常能在这里看到这一对情人的身影。果然,不久萨特就已经坐到波伏娃的身边。这一次相聚,两个人的怀里揣着同样的心事。在父母的催促下,波伏娃将要回到乡下过一段时间,分离的痛苦如天边的乌云飘浮过来,压抑在他俩的心头。他们的交往已走到一个转折点,从单纯的志趣相投,转向强烈的爱情吸引。
西蒙·德·波伏娃(1908—1986年),法国作家,女权运动领袖,萨特的亲密伴侣。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毕业。她出生于巴黎一个富裕的天主教家庭,父亲为律师。14岁对神失去信仰。19岁时,发表一项个人“独立宣言”,主张“我绝不让我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注]参考方珏: 《波伏娃存在主义的女性主义哲学思想渊源探析》,《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12期。。
波伏娃写有《第二性》,被誉为女人的“圣经”,围绕当代妇女问题,如生命自由、堕胎、卖淫和两性平等展开讨论。对于男性,“她是他所不能成为的而又渴望的一切,是他的否定和他的存在理由”。而最终,女人成为男人的附庸。波伏娃如是说。[注]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陶铁柱译,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168页。
有一个意识是独立的、自为存在的,而另一个则是依赖的,只为对方的存在而存在。前者为主体、后者为客体;前者是主人,后者是奴隶。[注]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27页。他的意识是“主要的”,而他的“对象”的意识是“非主要的”。他的“对象”是他的“他者”,陪衬着他、服从他,构成他的自信。[注]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上卷),第129页。
波伏娃阅读黑格尔的著作,久旱逢雨般地惊喜。她说: 黑格尔的这一论点非常适用于男女关系,对于男人来说,女人是“他者”,其意识是一种依附意识。女人确实没有确立过同男性价值相对等的女性价值。女人们今天所要求的是“与男人同等的权利”[注]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第3页。。历史犯下了错误: 父权社会赋予女性的仅是“服务的功能”,只要这个“功能”还在,女性就永远摆脱不了“奴隶的地位”[注]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第659页。。
波伏娃通过对旧式婚姻家庭制度的考察,得出结论:“在这里主奴的辩证关系得到了最具体的应用: 一个人在压迫的同时变成了被压迫者。”[注]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第547页。男人打算把女人固定在客体地位上,“使她永远是内在的,因为她的超越必定要失去光彩,并且必定要被另一个主要的主权自我(男性)所永远超越”[注]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第25页。。
她本着存在主义的自由精神,呼吁天下女性为应有的权利而斗争。人类进步的实质是人性的解放,妇女的解放是人性的解放,人类因妇女的解放而获真正的进步。
她的小说《名士风流》获法国最高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小说剖析知识分子的思想情况,产生重要影响。此外,波伏娃还写过多部小说如《女宾》、《人不免一死》,以及论文《存在主义理论与各民族的智慧》等。
1986年4月14日,西蒙·德·波伏娃于巴黎去世,享年78岁。波伏娃曾说过: 我的生命将在坟墓外延伸。如今,巴黎塞纳河第37座桥上镌刻着她的名字。《第二性》已有五十多种语言的译本,无数读了这本书的女性从屈辱与悲哀中站起,成为自强自立的人。
2. “像被闪电所击”
对于萨特来说,波伏娃是他一生所遇到的最重要的女人,是深藏心底最珍贵的女人。红尘滚滚,人来人往。多少事经历了走过了,也就忘却了。多少人相遇了招呼了,也就疏离了。然而有一些事却是刻骨铭心,有一些人却是终生不忘。当他和她因一个偶然的机会相遇,伫足不前,四目相望,虽无语言,却是心起波澜,涌动难抑。这样的感觉,像耳边响起霹雳、眼前划过闪电那样强烈,像热泉流过心田、轻风掠过花瓣那样温柔。
萨特说不上是一个英俊男子,因童年时代一场疾病的缘故,右眼近于失明并留下斜视的病症。这使他在阅读的时候,会把书本或任何一个纸质文本尽量靠近鼻尖,仿佛要去嗅出读物中特有的气息。一旦与人交谈,常是一个眼晴直直地盯视对方,另一个眼睛像是看着别的地方,不由自主地流露出睥睨与高冷的神情。他长得矮小,与他的亲密伴侣波伏娃一同出场的时候,波伏娃高挑美艳,而他仰着头也只比她的肩膀略高一点。这种情形有似一位女老师带着她的尚未发育的初中生。
让·保罗·萨特(1905—1980年),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人称其《存在与虚无》为存在主义的巅峰之作。他是法国人,出生于巴黎一位海军军官的家庭。他不到两岁时,父亲去世,在外祖父母家度过童年的岁月。外祖父是一位语言学教授,拥有大量的藏书,这使萨特自小获得较好的教育。随着年龄增长,他读叔本华、尼采的书,并深受影响。
1924年萨特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攻读哲学,这是世界著名的大学,人称法国思想家的摇篮。这时期波伏娃也在巴黎高师就学,可谓鸳鸯同池。1929年两人又一起参加教师资格考试,萨特第一名,波伏娃紧跟其后考了第二名。接连的巧遇,让他们互相关注,走到了一起。
萨特后来在书中写道:“她很美,我一直认为她美貌迷人,波伏娃身上不可思议的是,她既有男人的智力,又有女人的敏感。”
“萨特完全符合我15岁时渴望的梦中伴侣。因为他的存在,我的爱好变得愈加强烈,和他在一起,我们能分享一切。”波伏娃回忆当时的心情,这样说:“那个夏季,我像被闪电所击,‘一见钟情’那句成语突然有了特别罗曼蒂克的意义。”
1931年,萨特在法国北部港口城市勒阿弗尔的一所高中教哲学。1933年萨特赴德国留学,学习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由此发端。与此同时他从事文学创作。1938年长篇小说《呕吐》出版,这是一部自传性质的日记体小说,中心人物为罗康丹,存在主义成为该书的思想脉络。
1940年,萨特应征入伍,成为一名投身反希特勒、反法西斯战场的战士。然而没等他被卷入硝烟,参加过一场真正的战斗,就成为俘虏被关进了集中营。一次德军释放俘虏中的老年人、病弱者,萨特因眼部残疾获释。回到法国后,他组织了法国较早一批的抗德组织,并与法国共产党取得联系。
1933年以来,萨特开始考虑《存在与虚无》的思路与架构。入伍,走上战场,他依然在思考这本书的章节字句。从德国人的战俘营被释放出来后的1941年秋,萨特正式开始写作《存在与虚无》。这是萨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本书,1943年初成稿。这一年的夏日,《存在与虚无》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
1945年萨特与人合作创办《现代》杂志,评论时事。1954年5月,访问苏联。1955年9月至11月,萨特和女友波伏娃应邀访问中国,受到热情接待。10月1日他们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大典。这个时期,萨特还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斗争,反对法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有人要求戴高乐总统逮捕萨特。戴高乐回答: 人们并没有把伏尔泰投进监狱。1960年4月,萨特访问古巴,会见切·格瓦拉,写下《格瓦拉访问记》,说切·格瓦拉是“我们时代最完美的人”。
1963年《现代》杂志发表论萨特的自传性小说《词语》。1964年10月22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萨特,因为他“充满自由精神及探求真理的创作,已对我们的时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萨特出人意料地拒绝了这个奖项。他发表声明说:“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我都不接受,我只接受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
1968年,萨特支持法国学生“五月风暴”运动。他宣布:“大学生跟大学,只有一种关系,就是把大学砸了。要砸,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上街。”此后,萨特担任《解放报》(法国左翼最大报纸,第三大全国性日报)主编。1980年4月15日,病逝于巴黎,许多群众为他送葬,场面热烈。
3. 《存在与虚无》
萨特一生最重要的书是《存在与虚无》,这本书论证人类的自觉、自为的活动是一种伟大的“构成”,是将精神的碎片“总体化”。这个“总体化”,不是别的,乃是“人本身,亦即生物学上的个人”,“是一个整体: 在既定历史条件下他的需要、劳动和享受”[注]萨特: 《科学和辩证法》,见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编译: 《外国哲学资料》第四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55页。。
“我思故我在”(I think, therefore I am)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儿(1596—1650年)提出的哲学命题。而萨特无意中与笛卡尔发生思想的碰撞。萨特认为,意识(“我思”)是活泼的、生动的,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意识活动着,总把别的事物卷入到它的范围之内。意识施展它的自由性、无限性、主动性,被它摄取的事物无以脱身地一个个附着其上。
意识是自由的,因此人注定是自由的。自由一旦在人的心里点燃明灯,上帝便失去威力,唯物论的光辉由此普照人间。与尼采一样,萨特欢呼上帝的死去,宣称无信仰的人群才是真正的自由人。人们舍弃神意,将因意志的任意活动创造自己的未来,不受约束。
萨特的“存在”论,最终回到对“人本质”的阐述。人也是一种存在,然而在其刚诞生的时候,不具备本质。他像一块石头、一根原木那样,是“自发的存在”,而不是“自为的存在”,是非本质的存在,而不是本质的存在。人的“存在”是后天形成的,人在其一生中不断经由“自由选择”而造就其“存在”。这是本质的存在,也是真正与真实的“存在”。
“自由选择”成为人从“非本质存在”到达“本质存在”的必由之路。“自由的选择”是主体存在的标志,表现人的充分与完备的“存在”。选择的前提是“自由”,不自由的“选择”,等于不选择。
斯宾诺莎承认人类具有“自由意志”,有时人们会设想自己是一颗能“自由选择飞行路线与落点的石头”。他认为,人强调“自由意志”是因为具有“欲望”,“心灵的决定若扣掉欲望就不剩什么”。然而他笔锋一转,又说: 心灵内没有绝对值,也没有绝对的自由意志,心灵的意愿由一个因素来决定,而这个因素又由另一个因素决定。
其实,萨特也惶恐地看到,他口口声声主张的自由,并非绝对的,而是会受到道德、社会、他人的束缚与限制,因此是有权限的、有边界的与有禁忌的。他也试图与人讨论: 自由是一种权利,因此也是一种义务与责任。
不过,萨特还是想得很远。他自省: 这些是不是自找“麻烦”的思考,是不是陷入形而上学的二元论。他主张用现象的一元论表达人的认识活动,“由此消除一些使哲学感到麻烦的二元论”[注]萨特: 《存在与虚无》,见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组编: 《存在主义哲学》,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625页。。
“就裁纸刀而言,可以说是本质(指裁纸刀得已生产和规定的生产程序和本性的总合体)先于存在。”人是裁纸刀吗?如果是,那么人的本质的存在就是被“预定的”,与“人”本身没有关系。[注]萨特: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7页。
萨特立刻纠正了上述这个想法,他强调:“人首先是一种把自己推向将来的存在物,并且意识到自己想象成未来的存在。”人的本质,即真正的存在,是活生生的人的“自我选择”的结果。人自己“把自己推向”一个境地,人把自己想象成什么,他就会成为什么。他的幸福是他的“选择”,他的灭亡也是他的“选择”,一切都是自我的享受,一切都是“自作自受”。[注]萨特: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第30页。
他发出如下的咏叹: 追忆的幻影支离破碎。殉难、拯救、大厦将倾,一切已遭毁坏。“我已把圣灵从神龛中驱逐出去。”[注]黄颂杰等: 《萨特其人及其“人学”》,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68页。
斯多葛派与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主张是:“道德的目标就是把存在的方法提供给人”,“把人尊崇到本体论的最高尊严上去”。是这样吗?萨特反问。这样的“人”就不是属于自己的,而是属于先验的“道德”。这样的“人”并不具有“最高的尊严”,因为他是“他造”的人,而不是经自由选择而成的“自造”的人。[注]萨特: 《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552页。
他寻章摘句,服膺康德的说法: 人当否定既定的道德立法,而当“自己立法自己遵守”,人具有“绝对的自由意志”。[注]康德: 《实践理性批判》导言,见杨祖陶、邓晓芒编译: 《康德三大批判精粹》,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86页。
道德,是“通过自由而可能的”。倘若“道德”是一种罗网与约束,不如冲决而得自由。人生是自己的、道路是自己的、“立法”是自己的,唯如此,方可找到真实自在的“我”,“最高尊严”的“我”。
自由不应该有“边界”,一切传统与法则,一概妨碍人“自由选择”的东西,都是“上帝”和“神明”编造出来吓唬人的。“上帝如果不存在,一切事情都是可能的。”[注]黄颂杰等: 《萨特其人及其“人学”》,第170页。“人世间没有什么先天的善,人世间也没有一个地方写着‘善存在着’,‘必须诚实’,‘勿说谎’。”[注]萨特: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第18页。
行文至此笔者在想,选择是一个意念,也是一种权利。我想选择,这是选择的意念。我能选择,这是选择的权利。当人决定选择,选择才进行到一半,还有选择权的问题。有人有选择权,有人没有这个权利,或者这个权利被束缚与限制。因此要能“自由地选择”,第一步要做的是争取“选择的自由”,即自由选择的权利。
萨特写作《存在与虚无》这本书的时候,德国法西斯正在肆虐,疯狂剥夺人类的自由权利,从这个意义说,萨特的“自由选择”论具有历史的“新启蒙”意义。
不过,“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注]卢梭: 《社会契约论》,北京: 商务印书馆,何兆武译,1987年,第1页。。萨特以自由选择论为基调的“存在主义”强调意志的绝对自由而不去承认自由背后的“责任承担”。这使他的哲学常有进退失据的尴尬,而“没有为自由与责任的统一找到一个坚实的基础”[注]参考卢云昆: 《自由与责任的深层悖论——浅析萨特“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概念》,《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自由毕竟是有条件的与受框限的,这犹如舞者在悬崖上跳舞。舞者向往舞蹈的自由,因为舞者知道,自由的舞蹈方是美丽的舞蹈。美丽的程度取决于自由的程度,最自由的舞蹈方是最美丽的舞蹈。然而舞者受到悬崖的限制,不能超越悬崖的边界,超越了就会跌死,跳舞的美丽也将丧失。人在社会里生话,也如悬崖上的舞蹈,受到法制与道德的限制。限制之内,人是自由的,超越了限制就会不自由。
4. 特殊的“爱的约定”
萨特与波伏娃之间有一个特殊的“爱的约定”。在约定生效的时间里,双方有义务满足对方,同时各具自己的爱情生活。萨特绝对的自由精神从这里跨出门槛,他要冲破一切清规戒律,崇尚无拘谨的爱。萨特的爱情观与他的存在主义有关。
波伏娃问萨特: 你说过在柏林有一个恋爱事件;那个女人,你称她为月亮的女人。你喜欢她什么?不漂亮,也不那么聪明。萨特回答说: 是的,是不完美,但她有一种乡下人谈话的方式,一种奇特粗俗的谈话方式。正是这一点,才深深地吸引我呢。1956年萨特51岁时,向19岁的女学生阿莱特射出爱的箭矢,这位阿尔及利亚小姑娘,很快就成为他的情人,1965年萨特又将她收养为女儿。
他宣称自己在与一个女人相爱的同时,也与多位其他女子缠绵。这显然有悖于基督教义,因为基督宣告,一对一的婚姻才被上帝首肯,婚姻中无论男女必须向对方保持忠诚。这样的教义成为婚礼的誓言、生活的原理、道德的准则,乃至于法律的条文。然而,基督教的原理怎样呢?法律的条文又怎样呢?萨特早就脱离了宗教。他自己成为自已的“教主”,上帝管不了他。
你总是希望女人首先去爱你,而一旦女人爱上了你,你的感觉又是怎样的呢?每当波伏娃提出类似的问题,萨特总把烟斗轻轻地放在桌上,仰头张开嘴巴,就像接受牙科医生的询问。然后略为急促地回答: 对!当某个女人决定把自己交付给我的时候,她仿佛就成了我身上的一样东西。她们不得不爱我,这种爱意已经迫不及待地流露到她们脸上。我从她们的表情中得到证实,收获了这种爱意。
波伏娃又问: 就像你说过的,在同女人打交道时,你是有支配性的,对吗?萨特回答: 对的,这种支配性从我的童年就开始了。我的外祖父支配外祖母,我的继父支配我母亲。然而,萨特既是一个女性支配者,又是一个女性崇拜者。萨特回顾一生,说女人给了他许多,没有女人他不可能获得这些成就和地位。这时,萨特总把波伏娃拥入怀中,加重语气地表白: 在我所有爱过和爱着的女人中,“你是第一位的”。
人们至今还百思不解,萨特与波伏娃的爱情契约的背后,是不是还埋藏着不见天日的隐情。按照正常人的思维,爱情总是自私的,爱情的林间小路,常常埋伏着“警觉”与猜忌。波伏娃既然深爱着萨特,难道她就没有想到去“独占”自己的爱人吗?
她怎么能够做到,能容忍他在自己知晓的情况下去向别的女人求欢,而不生妒意?同样,按照正常人的思维,真正的爱情总是与“忠诚”这样的概念相伴,当爱情有另外的女人插足而“拥挤”不堪,波伏娃怎么还能继续维持这在普通人眼里已名存实亡的爱情?
人们只好作以下的猜测: 在萨特与波伏娃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真正的爱情,他们的“相爱”,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与一个女权主义者所做的社会试验。他们要以自身的“爱情传奇”,陈述陈旧的一夫一妻制度因抑杀性爱的激情与自由,理当抛弃,一个新颖的婚姻时代即将开启。
人们还在继续猜测,这场“实验”的过程中,波伏娃是心甘情愿的“同谋”,还是这场实验的策划者只有萨特一人,而波伏娃仅是无奈的参与者。因为对萨特的深情挚爱,唯恐失去萨特,波伏娃不得已在那特别的爱情约定上“签字画押”。
种种的猜测如检测色盲的杂色画板,也如色彩变幻的万花筒令人目眩。然而最后一种猜测是可能的。波伏娃毕竟是女人,她因为不能“独占”萨特而深夜哭泣,醉酒不醒。对于这场爱情“实验”,她一半是“同谋”,一半是受伤者。
5. “斗篷”笼罩下来又合拢
因为特殊的“爱的约定”,波伏娃一生中除与萨特交往,也有过另外的情人。然而她将最深的情感倾注于萨特身上。萨特生命的最后十年,在病痛中渡过。1971年萨特中风,1973年旧病复发,处于半痴呆的状态,已不认得身边的人。这时,波伏娃不弃不离,日夕陪伴在侧,悉心料理病人。
1980年4月15日晚,萨特进入弥留状态,他紧握波伏娃的手,断断续续地吐出最后的话语:“我非常爱你,我亲爱的海狸(波伏娃的小名)。”当萨特的手在波伏娃的手上轻抚的时候,无意中触摸到波伏娃手指上的一枚戒指。这枚戒指很冰凉,萨特知道,这是另一个男人给予海狸的爱情信物。
萨特逝世后波伏娃陷于深深的痛苦中,忍痛握笔撰写《永別的仪式》,回顾萨特生命中最后十年与她相处的日日夜夜。同时又出版萨特书信集《致海狸和其他人》,其中包含萨特给她的大量情书。可惜的是,“海狸”致萨特的信笺没有收录其中。
“他的死将我们分开,我的死也不会使我们重聚。就是如此。我们能在一起生活那么长时间,已经很好。”在《告别仪式》中波伏娃这样写道。她和萨特一样,是个唯物论者。他们两人在生前都有意把上帝和天堂的神话忘却了。
而当此时,死神将暖热的黑色斗篷笼罩下来,又合拢起来,要抱着她飞去的时候,她也许感悟了,也许反悔了。人不可无宗教,尤其走到人生的末路,教堂顶楼轻摇的钟声,能把生命中最后的摇篮曲吟唱。
也许宗教是一个谎言,但却是善意的谎言,给孤寂的灵魂以体贴的慰藉。也许宗教是一个梦境,但却是七彩的梦境,能让临终的人们忘记畏死的恐惧。也许宗教是一种杜撰,编造了彼岸的世界,去到美丽的彼岸,可以重遇心爱的人儿。
这时的波伏娃是否会想,毋宁要神,要天堂,要一座云霞里的伊甸园。她要神来接引,渡她去天堂。要萨特在天堂的台阶上迎她,带她去伊甸园,满园都是玫瑰的芬芳。她会不会问萨特,在这个天上的世界,你还要不要坚持人间的主张,依然不肯结婚,再与她做一世的“情人”。她在萨特逝后的第六年去世。她留下遗言,要与萨特合葬。她追随萨特一生,愿死后依然与他相伴。
成千上万的人为她送行,前面是灵柩,载在车上,缓缓驶向蒙巴纳斯墓地。她安卧其中,轻合双目,身穿红色晨衣。那一年她也是穿着红衣,穿过树林,跨过小溪,像轻风掠过带露的草地。她奔跑着要去见他。看到了,她的情郎,正在前方不远的麦田里,向着她来的方向,使劲地张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