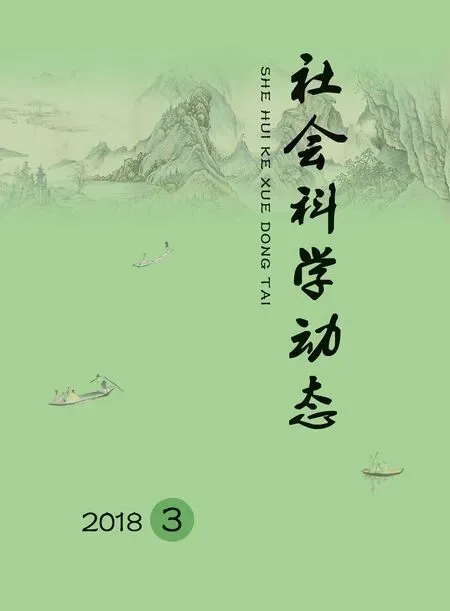文学伦理学批评术语运用问题
——邹建军教授访谈录
邹建军 熊素娟
熊素娟副教授(以下简称“熊”):文学伦理学是近些年来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有一些学者动不动就是文学伦理学,似乎任何文学都可以是伦理学研究的对象,任何文学作品都可以从伦理的角度进行研究,似乎没有了文学伦理学理论,就不能与不可研究文学了。不知您是如何认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出现及其价值的?“伦理选择”作为文学伦理学的核心术语之一,它的本义与延伸义是什么?不知您对此有什么样的认识?
邹建军教授(以下简称“邹”):首先我们要承认,文学伦理学是由中国学者自己提出来的一种文学批评理论,最近十多年以来许多人都参与其中,包括本人在内。虽然我们作了很大的努力,然而文学伦理学的批评理论至今也并不完善。“伦理选择”只是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一个术语,它的提出不是本国学者的专利,在西方早就有人在讨论这个问题。如“伦理选择”这样的术语,从理论上来说,本身没有任何研究的价值,因为任何人都可以懂得它的内涵与意义。只有在结合具体作家作品的时候,特别是在分析主人公自身的伦理困境、与他人所发生伦理冲突的时候,伦理选择才可以发生意义,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也才存在伦理选择的问题,在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研究具体的问题也才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如果我们只是抽象地在社会生活中讲“伦理选择”,在文学理论中来讲伦理选择,不会产生任何的意义。因为任何社会生活中的人们,他们如何选择伦理道德规范,是在自然而然中产生与实现的,往往并不需要所谓的“选择”,也就过渡到了下一个阶段。比如我们每个人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到高中,从高中到大学,从大学到研究生,我们经历了所谓的“伦理选择”吗?一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之中,也许会有伦理选择的发生,那是他在人生过程中发生困难的时候,在与他人与社会发生严重冲突的时候,并且这种选择每个环节都不可能离开自己的生存环境。如果存在伦理选择,那么首先在于选择者所具有的特定环境,他本人的家庭出身、家族环境、成长经历、教育程度等。在一般情况下,根本不存在选择与不选择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伦理选择这个术语不可乱用,只有在分析文学作品里的人物面对问题而不得不进行选择的时候,才可以运用来进行解释。不然的话,就会产生泛化与误解,因为它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定的学术意义。
熊:文学伦理学属于特定的文学研究,当然也就是一种学术研究,并不只是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来解读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就是文学作品,它本身并不是文献,也不能构成文献。您为什么说全面地占有相关的文献,是文学伦理学研究的基础与前提?
邹:在对中外作家作品的研究中,与研究课题相关的所有文献,客观、全面、翔实的文献是极为重要的。凡与论题相关的文献,无论是何种类,越全越好,越细越好。选择是可以的,然而首先是要全,如果有的文献你都没有看到过,那你还选择什么呢?就没有什么好选择的了。重要的东西你还不能选取,必须如实地加以照录。有的与此题相关性不大的东西,当然可以舍弃一些,但从总体上来说,你所列出的文献还是要尽量的全面、尽量的客观、尽可能地真实与可靠。所以,全面地占有文献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与前提,这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一种提醒,而是必须做到的一个标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历史虽然不是很长,然而从前的文学伦理学研究还是大量存在的。西方自古希腊时代开始,中国自先秦时代开始,就存在从伦理的角度来批评文学的实践,我们不能说他们所从事的不是文学伦理学批评,不能说他们没有进行文学伦理学的实践,只是那个时候还没有系统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所以,我认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历史情况,是必须全面地了解的,不能只是了解最近20年以来的东西。西方与东方各国的学者们相关的理论成果,如伦理学研究的成果、道德研究的成果、文学的发生基础与构成要素方面的研究成果,当代学者对于文学伦理学的相关论述,也都是必须全面而客观地了解与研究的。既然文学伦理学是文学研究的一个方面,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门类,那你就要像做其他方面的学术研究一样,不可自以为是地认为哪些是文学伦理学,而哪些不是文学伦理学。文学伦理学理论研究方面,成果最大的当然是聂珍钊教授,然而也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才有理论,在当代中国有一批人在从事这个方面的研究,包括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的研究,这也是他本人的认知。
熊:有的人在使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术语的时候,似乎总是存在混用与乱用的问题。我看过近年来中国学者特别是一些青年学者的论文,几乎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您如何认识当代文学伦理学批评实践中所产生的这种现象?
邹:现有的术语概念可以用,然而不可生硬地搬用,还是要争取在反复思考之后提出一些新的术语。要理解学界现有术语之间的关系,不可随意地选择一个术语来用,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术语,是根据自己的论文展开的需要,而不是为术语而术语。在文学伦理学的批评术语中,伦理身份是就人物而言,伦理困境是就人物的心理而言,伦理冲突是就主要人物之间的特定关系而言,伦理选择是就文学作品里的人物生存与发展的可能性而言,伦理思想是就作家和思想家而言,伦理观念是就作家本身是言,伦理意识是就作家而言,当然伦理观念与伦理思想首先是体现在他的作品中,同时也体现在除文学作品之外的一些言论中。如果我们说伦理选择就是一个过程,只是说对了一半,因为任何事情都是一个过程,伦理困境、伦理冲突也是一个过程,那就与“伦理冲突”相混淆了,这样的说法无异于无知而胡说。当然,也不可丢掉相关的东西。
熊:文学伦理学批评现在已经有了不少的术语与概念,聂珍钊教授在《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后面所附的两个目录中,就有53个之多。如此多的术语,在一篇论文中是不可能全部运用的。在对文学伦理学批评术语的使用中,是不是存在一个分级与分类的问题?对现有的文学批评术语,不知如何分类与分级才会比较合适?
邹:在文学伦理学的研究实践中,术语与概念当然是可以用的,当然也是可以不用的。术语与概念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对于具体问题的研究。对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相关术语要分级别,不可一视同仁,相互混用。在聂老所列的53个文学伦理学术语概念中,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本能”、“本性”、“冲动”、“非理性”、“非理性意志”、“激情”、“理性”、“理性意志”等等属于心理学的概念;“道德”、“道德榜样”、“道德价值”、“道德教诲”、“道德情感”、“道德批判”等,是属于哲学的概念;“伦理”、“伦理悖论”、“伦理环境”、“人性”、“人性因子”、“兽性因子”、“斯芬克斯因子”、“天性”、“伦理价值”、“伦理启蒙”等是属于伦理学的概念;“电子文本”、“科学选择”、“脑文本”、“语言”、“物质文本”、“数字文本”、“自然选择”等是属于科学的概念;“意志”、“意志力”、“自然情感”、“自然意志”、“自由意志”等是属于心理哲学的概念。上述所有的概念都是属于文学伦理学的外围概念,不是文学伦理学的本体概念。它们虽然与文学伦理学相关,然而它们指向的问题都不是文学伦理学本身的问题。
在文学伦理学的本体概念中,“文学伦理学”、“文学伦理学批评”属于最高层的概念,是关涉到学科与批评方法的理论问题。“伦理悖论”、“伦理混乱”、“伦理混沌”等是第二层概念,是针对与作家本人相关的文学现象的。“伦理结构”、“伦理结”、“伦理建构”、“伦理解构”等是第三层的概念,是针对相关的文学作品本身的,不是针对作家本人的。“伦理禁忌”、“伦理两难”、“伦理身份”、“伦理问题”、“伦理线”、“伦理语境”等术语,则是针对作品里的人物与人物之间关系的。因此,我个人认为对于文学伦理学批评实践而言,还是要对数量众多的理论术语进行分类与分层,以便让大家可以更加准确地理解、更加准确地使用它们,不然除了理论创见之外,就没有了什么真正的学术意义。更为重要的是,除了上面所列的这些术语之外,我们还可以有其他的术语,也需要在实际研究中得到更加广泛的运用。对此我们还可以再讲清楚一些。
“文学伦理学”、“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伦理”、“道德批评”等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的一级概念,主要指文学伦理学的观念和方法、范畴和类型。这一个级別的概念,一般的论文不用,因为不需要,也用不上。如果讨论文学伦理学的一些根本问题,或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问题,方可运用之并产生实质性的意义。
“伦理观念”、“伦理意识”、“伦理意义”、“伦理启示”、“伦理解构”、“伦理建构”等,属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的二级概念,主要针对作家本人的。这样的概念一般论文也用不上,因为我们现有的文学伦理学论文,一般都是分析文学文本的。按照我的理解,用于作家的一般不能用于作品,用于作品的,一般不可用于作家。在一篇学术论文中,研究作家就研究作家,研究作品就研究作品,不可混乱而无序。
“伦理结构”、“伦理线”、“伦理结”、“伦理网”、“伦理主题”等,属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三级概念,这样一些概念与术语是针对文学作品整体的,每一个概念所标示的内涵,只有通过研究者自己的阅读和判断,才有可能得出。如果我们没有阅读文学文本,就根本无法讨论这些问题,当然也无从理解这样的概念。
“伦理身份”、“伦理困境”、“伦理冲突”、“伦理选择”、“伦理指向”、“伦理理想”、“伦理景观”等,属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四级概念,主要针对作品中的具体内容以及所存在的问题的。在一般的文学伦理学论文中,都可以进行运用以说明相关的文学现象,也应当得到具体的运用。
在以上四个级别或类型的概念和术语之外,还有一些是外围概念,如“斯芬克斯因子”、“伦理教诲”等。我们暂时不想讨论这种概念及其所涉及到的问题。然而,针对作品的概念不可用于作家,针对作家的概念不可用于作品,针对文学的概念不可用于伦理,针对伦理的概念不可用于文学。当然有的概念可以借用,如科学的概念、哲学与宗教的概念、心理学的与伦理学的概念等,但每一次运用都需要进行界定,不然就会引起混乱,让读者摸不着头脑,当然首先是不能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
在实际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中,还是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有一篇论文《文学与伦理学:文学伦理学批评发展的“自由空间”》 (《外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1期),一开始就讨论“文学与伦理学的源际关系”,这就是把“伦理”和“伦理学”混用了。从历史上来看,“文学”与社会生活里的“伦理”存在关系,而“文学”与“伦理学”则没有什么关系,“文学研究”可能与“伦理学”有一些关系,这就是文学伦理学。所以,文学是文学,而伦理学则是伦理学,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想当然的,相关的概念和术语不可乱用。再比如说“伦理教诲”这个术语,本身有其特定的内涵,那就是指有的文学作品经过读者的审美阅读之后,正面人物形象会起到教育的作用,因为一些文学作品特别是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的确是存在惩恶扬善的主题思想,教育意义特别是对青少年的教育意义是很大的。然而,有的硕士与博士论文在标题上就直接叫某某作品的“伦理教诲价值”,这就是把在后来的文学传播与文学消费中产生的意义,放到文学作品里面去了,于是产生了严重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首先,文学不是为教诲而产生的,作家也不会为了教诲而去创作文学作品,文学作品的首要价值是审美价值,没有审美意义的产生就不会有真正的文学作品的存在。这是文学理论中对文学与艺术的最基本认识,经过了多少代人的努力才从“文革”中纠正过来,也正是这样的纠正才造就了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创作的繁荣。如果我们要创作之前就强调作家要教诲什么什么,我想作家就没有办法创作了;如果我们要求作家在作品中一定要具有教诲的思想,我想他无论如何也创作不出真正在文学史上有价值的作品,即使是童话与寓言等儿童文学作品,也同样是如此。所以,“伦理教诲”这个术语不可乱用,否则后果严重。
熊:最近30年以来,西方的文学理论在中国大行其道,有的人开口闭口言必称西方,似乎离开了西方的东西就不会进行文学批评与研究,甚至于不会讲话了。女权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大致也是如此,并且有的时候还相当严重。不知您如何认识西方的女权主义理论,及其近些年来在中国的实践?
邹:女权主义是西方当代文论中的重要理论之一,引起了评论家们与作家们的高度重视,西方多国出现了诸多典型的女权主义者。这种典型的西方理论传到中国之后,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高度封建化的国家,妇女的社会地位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女权主义理论一进来,中国当代学者特别是一些女性学者,似乎就找到了一种重要的理论依靠,他们认为西方哲学中的女权主义思想与观念,是我们许多中国人可以接受的,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理论,并且我们的社会现实需要这样的理论。然而到了今天,在中国知识女性的地位普遍高于男性的时候,再来讲所谓的女权主义,似乎已经过时了,因为这样的理论基本上已经没有针对性了。因此,我认为在讨论文学的时候,再从一般理论的意义上来讨论女权主义,已经是没有意义了,因为这个时候,女权主义已经成为了一种常识。如果研究的对象是奥尼尔,我们所要做的只能有根有据地揭示作品中和作家身上的女性观,而不能把自己的女权观强加在作为对象物的作家身上,因为你是你,而奥尼尔还是奥尼尔,你的女权观念和奥尼尔没有任何关联性。你的女权主义思想是从西方来的,而他作品里面所表现出来的是他对于女性人物的认识与他对于女性问题的关注。所以,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的主观思想自然而然地会起一定作用,然而只是在对作品的理解和作家的研究时,对于具体问题与现象的看法不同,而具有不同的认识。所以任何观点的提出,也得要有依据,不是说你想如何讲就可以如何讲,想当然的东西就不叫研究,而叫主观臆想。这样的人可以当哲学家,却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学者。
熊:在学术论文的写作中,参考文献自然是不可少的。文学研究以至于所有的学术研究,文献是我们研究的前提,当然文献的获取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当我们研究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时候,所涉及的文献就会比纯粹研究中国文学要广泛一些,也复杂一些,那么,分类就会成为一个问题。我们在文末列出参考文献的时候,不知如何分类才会比较科学?
邹:我认为在列出相关的“参考文献”的时候,分类不可太细,细了则可能琐碎而显得混乱。我个人认为分“中文著作”、“外文著作”、“中文论文”(下分报刊论文、硕博论文)、“外文论文”四大类,这就不会发生交叉,不会产生混乱。在这四类之下,可以按重要的程度而排,也可以按时间的后先顺序而排,也可以按时间的先后顺序而排,我们一般采取前者。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从道理上来说,时间离我们越近的材料,就越有参考价值,因为它体现了学术前沿。学术论文写作在文献方面的一些基本规则,任何时候都不会改变,并且相当管用。为什么呢?因为变了就不正确,就会对不上而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现在的学术论文特别是学位论文,规范是五花八门、各行其是,就是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东西,各个学科也不太一样。当然,语言学与文学的确不一样,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确不一样,历史文献学与民间文学的确也不一样,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也的确不一样,那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学术论文,也就要有自己的规范。
熊:当代中国的学术研究似乎存在很大的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究竟何为真正的学问?什么样的人是真正的学问家?不知您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
邹:首先要搞清楚何为学术研究?何为真正的学问?如果我们都趋炎附势、一切为他者而动、在学术研究中毫无学者之独立判断,那还做什么学问呢?今天成立新区,就去研究新区,明天撤掉了呢?这样的现象说明我们有的人之言行与当年的跟风没有什么区别。学术研究不可为他人而动,也不可为政治而动,特别是不可为政权而动。政府需要什么,你就去做什么;政府需要你如何讲,你就如何讲,这叫什么学者呢?因为从根本来说,这不是学术研究,而是实用主义的极致化,而实用主义的观念及其所体现出来的言与行不是学术,或者说与学术研究没有任何的关系。学术研究是追求真理的、求得真知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空间。也许有的人不同意这样的观点,那你可以说一下什么叫学问、什么叫“学术研究”吧?常识是不是学问?政治需不需要学问?学问之所以神圣是因为什么?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工程科学也许不一样,科学也许没有或缺少人的感情与思想的内容,而人文与社会科学则主要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与构成形态、人的生存与发展、人的思想与情感、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一些根本的问题,它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不是科学。首先不是自然科学,其次不是技术科学,再次也不是工程科学。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具有很大的区别。严格说来,人文科学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是社会科学,宗教与哲学是宗教与哲学,它们分属于不同的领域和学科门类。然而,任何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宗教哲学都是以追求真理为目标的,不可能有任何外在的目的。如果有了先入为主的外在目标,或者把学问当成了人生上台阶的工具等,都是不可以的。如果明白了这样一点,我们就可以认识到什么叫学问、什么是学者,与此相反的就不是真正的学问与学者了。说得明白一点,那些与政治、政权关系过密的东西,都不是真正的学问,也不是真正的学问家。研究政治可以成为学问家,然而多半是对于政治的批判性反思。
熊:最近一两年以来,似乎我们总是在讲“学问之道”。不知何为“道”?是不是只是指做学问的方法?“道”与“术”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一个学者是不是首先要有“道”,其后才可以有“术”?
邹:关于论文写作与学术研究,我曾讲述了“术”的部分,而没有讲“道”的部分。有的人沾沾自喜,忘乎所以,以为听一次就得“道”了。关于学问之道,有机会再讲,并且就此问题展开讨论。学术研究是学问的具体体现,即一个人的学问体现在他的学术研究实践中,如果没有从事学术研究,也许人们不会认为他是一个学者,或者是一个真正有学问的人。而既然学术研究是以人为主体而从事的学术思考与学术探索活动,那当然就存在“术”的问题,即方法的问题,同时也存在“道”的问题,即根本的观念与思想的问题。所以,我们立志一生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一定要懂得学问之“道”,同时也要知道学问之“术”,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二者往往是可以统一起来的。“道”就是根本,就是立场与观念,就是思想与主张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我们现在不少的人都把学术研究当成了“术”,也就是方法与手段,就是工具与技巧,这是有违学术之根本的。学术研究首先要讲“道”的存在,就是要坚守真实、真理与真诚,任何时候不说一句假话、不说一句违心的话、不说不符合事实的话,敢于讲真话才是学者的最重要的品格。有的学者写论文,根本就不做调查研究,为了获得一点课题费、一个奖励、一个职称,就在那里东拼西凑、胡说八道,想当然与自闭狂是我们当代中国学者最大的毛病。
熊:当代中国有的学者对于自己没有清楚的认识,有的人往往认为自己的学问是最大的、最为重要的,别人的学问都是不重要的,于是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浮躁的风气。不知您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
邹:在我们求学的过程中,首先要知道自己的不足,对自己要有明确的认识,要有一个基本的估价。自己的知识结构里缺哪一块,我们就要补哪一块,不然就会有问题。当然,在三年之内,要补别人四年才可以学到的东西,是不容易的了。学外语的要补中文的,不努力、不谦虚、不发奋,再加上如果方法不对,要成功谈何容易?从道理上来说,一个要人做学问,亡羊而补牢,未为晚也。然而问题在于有的人没有自知之明,还在那里自以为是。自己的学问如何,难道自己不知道吗?你读了几本书?写了几篇论文?提出了什么新的问题?解决了什么理论问题?发现了什么样的新材料?什么都没有,你有什么大的学问呢?在这种情况下,你还不付出劳动与努力,那就没有办法了。我一直对有的中国学者所谓的学问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的论文没有提出问题,也就不可能解决什么问题。文学伦理学研究实践也同样是如此。许多人只知道运用几个已有的概念与术语,对现有的文学作品进行解读,说明的是同样的早已被人论证过的理论问题,似乎经典作家与作品成为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的注解,并且是最为恰当的注脚。这可以成为真正的学术研究吗?自然不是,只是解读了一个作品,与利用来自于西方的文论解读中国作品是同样的失误。
熊:有的学者或初学者热衷于做文献综述,并且止于文献综述,似乎文献综述成了学术研究的唯一形态。我们期刊发表的许多论文都是这样的,没有什么真正的学术见解。您认为在学术研究中,文献综述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与价值?
邹:我一直是坚决反对那样一种观点与做法,就是做文学研究,总是要从前人的研究开始的方法。文学研究与其他专业研究是一样的,研究综述可以做,然而研究综述本身没有什么学术意义,其目的只是了解前人研究到了什么程度,已经提出了哪些主要的观点,采用了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在自己的研究中不再重复前人已有的或已经做过的东西,如此而已。只有那些半桶水学者,才特别强调做文献综述的重要意义;也只有那些门风不正的人,才带头攻击他人,说別人从小是个坏人。你和他是同村的,还是同校的?做学问是从自己的研究对象开始,而不是从前人的研究开始。所谓自己的研究对象,就是你所研究的作家、流派与思潮,文学史或文学理论。有的人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不全面地阅读、反复地思考,却用了大部分的时间来关注前人的研究成果,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我们要注重读的是本课题的对象方面的文献,即研究什么,就要以70%或80%的时间与精力来读,根据个人的经验至少要读四遍以上。研究华兹华斯,其诗、诗论、传记等,需要全部的细读,以新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去发现问题,并且在作品等文献中寻找根据,从而有可能回答所发现的所有的问题。在文学研究中,文本本身就是最重要的根据。有的人认为前人的研究成果才是最重要的根据,有的人认为相关的理论观点才是最重要的根据,有的人甚至认为相关的哲学与宗教材料是最重要的根据,其实这样的认识都是走入了学术研究误区。这就是许多人不能按时完成自己学位论文的重要原因。你读书也许不少,然而当读的没有很好地读,而不当读的却读了一大堆,所以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意义。所以,研究方法也是十分重要的。方法得当,事半功倍;方法不当,事倍功半,时间和历史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
熊:看来读什么书是相当重要的,这就有一个选择的问题。有的人就是喜欢读当代学者的论文与著作,认为与自己近一些,容易读懂。而那些经典的学术著作,特别是比较古老的哲学与美学著作,读起来自然要花更大的力气、更多的时间,然而却不得不读。关于读书上的选择,不知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邹:我们要读那些特别重要的书,不读拼凑的教材之类。勃兰兑斯、韦勒克、伊格尔顿、艾布拉姆斯之文论代表作,来自于苏联学者的《世界文学史》8卷16册、中国学者自己编撰的《中外文学交流史》17册等文学史代表作,罗素《西方哲学史》、朱光潜《西方美学史》等哲学美学代表作,尽早全读、细读、反复读。不然的话,我们的学术素养就会有问题,如果许多东西我们都不知道,对于作品里所存在问题的认识与分析,就会产生严重的困难。我们现在的图书数量巨大,特别是在当代中国,因为学术评价所产生的问题,许多本来没有什么价值的书也出版了,数量太大反而给我们造成一定的困难,不好选择。到底我们要读哪些书而不读哪些书?而一般的人也没有这样的区分能力,这就要求我们选出一些重要的著作,而放弃更多的没有价值或价值较小的著作。当代没有大师也没有大家,然而还是有一些重要的学者,他们的著作就是需要读的。在文学伦理学方面,聂珍钊的一些著作如《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王宁、刘建军、王松林和我本人的一些著作与论文,也是需要了解的。在文学地理学方面,杨义、曾大兴、梅新林和我本人的一些著作,也是需要阅读与了解的。学科不同需要读的书也就不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一个大的学科,比较文学是一个方面、世界文学是另一个方面,两者对于学生的要求有所不同。比较文学方面,乐黛云、曹顺庆、谢天振、钱林森、王宁、高旭东、王向远等人的著作,也是需要读的。在世界文学方面,还要分出西方文学与东方文学,西方文学中还要分出德国文学、法国文学、英国文学与美国文学等,各不相同,因此要读的书也就不一样。
熊:上次我听了刘慧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做得很细、很深,当然也还有一些问题,老师们也指出了一些问题。关于学位论文写作,不知您有什么样的具体要求?
邹:首先,关于论文写作,我们还可以讨论以下一些问题。其一,硕博论文的研究综述,我认为不能以视角和方法来区分,而当以前人的观点来统率你所发现的材料,即国内对什么有哪些观点,国外对什么有哪些观点?其后再进行论证。首先分期,分期之后再讲观点,再对观点进行论证。这样的逻辑结构简要而科学,也可直接说明你的选题和问题的重要价值。其二,戏剧的展开在于戏剧冲突,在作品中存在的许多都是人与人之间所发生的伦理冲突,而你把原来提纲中第三章,即伦理冲突这一部分删掉,没有经过导师的同意,认为不好写的也就不要了,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是一种错误的选择。其三,在博士论文中,一定要根据作家作品的事实,出于论述和展开自己观点的需要,提出一些新的术语,而成为本文的核心概念,并在“引论”中进行清楚地界定,在论述中进行论证与运用。那种认为学位论文中可以没有新的术语和概念的说法是错误的,那种认为只有自己才能提出概念与术语而别人不能提出概念与术语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可笑的。其四,对于任何问题的论述不可流于表面,不能只是在论文中罗列一些现象,而不探讨根本的问题。在学位论文的写作中,教科书式的写法是不可取的,因为它只讲常识,不讲问题,没有任何学术价值。学术论文要提出问题,回答和论证问题,并且得出独立的结论。论文中的每一个标题都是一种观点,其下所述的内容就是论证这个观点。要集中、深入、具体地进行论述,如果全篇都是如此,就可以成立了。其五,就刘慧的博士论文而言,全文必须回答如下问题:(1)奧尼尔戏剧中三种最重要的伦理关系是什么?为什么会如此?(2)其戏剧中人物主要的伦理困境有哪四种?为什么?(3)其戏剧中存在的三种主要伦理冲突是什么?这些伦理冲突是如何造成的?(4)其戏剧中的伦理选择有哪四种?它们是如何实现的?(5)从作品中来看,奥尼尔的伦理观念有哪些,是如何构成与表达的?是如何形成的?如能回答这样的问题,则可以进入写作阶段;如果回答不了,则只有继续思考,把主要的作品联系起来思考,直到发现了问题,可以充分地进行解释,而进行令人满意地回答为止。
熊:您是研究文学伦理学与文学地理学的专家,每一年要审阅许多学术论文,包括发表的论文和参加答辩的学位论文。对于他人的论文,您往往都有自己的评价。不知您对王亚民等人的论文有何评价?
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栏目要发表的三篇论文,都以作家作品为研究对象,并以作品为中心而提出问题来讨论,得出了真实、独到和可靠的结论。王亚民、张严峻论文从布尔加科夫的长篇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中诗人柳欣形象的内涵与特点出发,以大量材料证明其原型就是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认为作家在此形象上寄寓了对苏联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与精神道德的思考,有力地解答了这部作品长期以来争论不休中的诸多问题。汪树东、刘玉杰论文立足于对德国作家克莱斯特的小说与戏剧作品的解读,发现其创作历程经历了从启蒙理性到基督教信仰体系的u形转变,诸多文学作品与《圣经》之间构成了一种互文性,同时也表现出一种相当复杂的态度,从而在有所创造的同时也有所缺失。赵小琪、周肖肖论文以阐释学理论来观照英国玄学派诗歌的意义,从文本价值、批评价值与批评史的价值三个方面展开,体现了一种全面、客观与科学的批评观念与圆形的批评方法。这样的文学研究论文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因为它们都讨论了自己发现的问题,是对于文学文本的深入分析。而文学伦理学研究中的有些论文,没有立论的史实与文本依据,也就没有发现与研究什么真正的问题。有一篇发表在《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上的论文《文学批评的伦理转向: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开始向伦理转向,文学伦理学批评又悄然占据了学术界并作为一种明确的批评方法在学术界全面复兴”。这样的表述只是看到了一种现象,那就是从伦理的角度研究文学特别是外国文学的论文比较多,然而它们都集中发表在某一些刊物上,讨论的问题都大同而小异,基本的观点也都是一致的,其实这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而是中国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在当代中国的整体文学研究中,并不存在文学批评的“伦理转向”的问题,而只是一种批评方法的采用问题,然而过度地只是采用一种批评方法,就像一个人总是吃一种东西,会给自己的身体造成重大问题。
文学伦理学是不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当然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因为从前的学者不太注重从这个角度去研究,特别是对于外国文学作品的研究。为什么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认为文学伦理学没有什么新意呢?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学研究,文学伦理学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自孔子开始就从伦理的角度研究《诗经》,自此开始的儒家诗学其实就是“伦理的诗学”,然而,“伦理”具有特定的内涵,那就是具有血缘与亲缘关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就不可把什么都当成了伦理,把“伦理”等同于“道德”,或者把“伦理”等同于“政治”。如果这样的话,文学伦理学批评就可以包打天下了,就可以把整个国家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当成文学伦理学研究了,甚至把整个人类的文学都当成伦理的产物了。如果这样的话,那就等于取消了文学本身。如果人类没有了文学,那就等于人类的天空没有了“星星”,更不要说“月亮”和“太阳”了。
熊:您是中国最早从事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学者之一。您认为文学伦理学批评与文学伦理学研究,在中国具有什么样的美好前景?
邹:文学伦理学并不是中国学者提出来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是由中国学者提出来,并在最近十年加以修订与完善的。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方面,聂珍钊教授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王松林、罗良功、杨革新、杜娟、朱卫红、刘兮颖、刘红卫等也发表了重要的论述。我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方面,其实没有什么建树,多半从事具体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实践。我的博士论文是从文学伦理学的角度研究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的长篇小说的,《“和”的正向与反向:谭恩美长篇小说中的伦理思想研究》,2008年12月已由华中师大出版社列入聂珍钊先生主编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建设丛书”出版。后来发表过十余篇关于文学伦理学的论文,主要是具体研究作家作品中的伦理问题的,从理论上进行探讨的论文不多,提出的新术语与概念十分有限。然而,我还是时时关注中国学者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及其实践。据了解,文学伦理学批评在最近十年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且在文本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首先,以文学伦理学的理论重新认识现有的文学理论,发现了并回答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其次,以文学伦理学思想为中国所面对的问题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如强调文学教育、文学的经典阅读与文学传播的伦理环境等。其三,以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来强化文学文本研究,证明中国学者自己提出来的理论,与西方学者的理论相比具有同样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其四,以现有的文学伦理学理论为工具,重新解读了许多经典文本,得出了一些从前学者所没有的、新的认识,充分说明文学经典具有再生功能,强大的生命力是与生俱来的。正是在此四项意义上,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其实践,会对中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文学理论研究、民间文学研究发生重要的推动作用。当然,对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如果处理不当,也会产生一些问题。比如说上面我提出过的伦理术语与概念混用的问题、过分强调文学的伦理意义而忽略美学意义、生硬地认为一切文学都是伦理的产物、过分地强调文学的教诲功能而影响文学的创作等。当然,如果加以纠正与修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