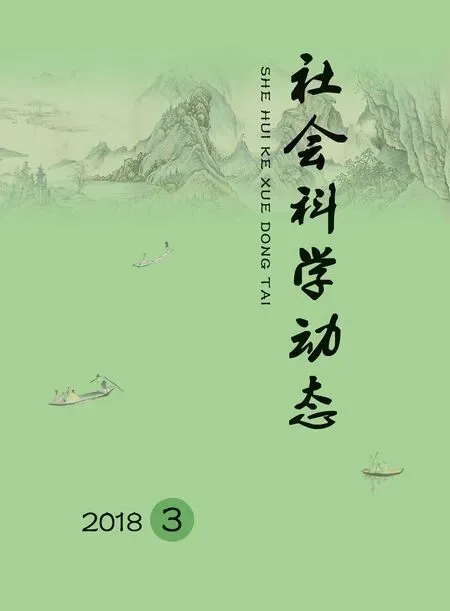论近代的息讼歌及息讼的思想根源
白中阳
息讼歌古已有之,但近代文献中记载的息讼歌数量最多且内容最为丰富。目前学界涉及息讼歌的相关研究甚为匮乏,仅林中厚的《碾伯知县徐志炳与〈息讼歌〉》①一文稍有提及,还只是配合历史人物的分析引入一篇息讼歌而已。对于息讼歌的类别和产生根源等系统性的研究成果尚未出现。笔者在此基础上梳理了相关史料,对息讼歌及息讼观念产生的根源进行了尝试性的解读,以期相关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一、息讼的经济根源
经济原因和生存问题是息讼歌创作和发挥实际效果的根本原因。近代的中国乡村充斥着贫困、疾病、战乱等影响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这些因素一直困扰着近代乡村的经济发展,尤其是贫困让近乎每个农村家庭饱尝生活的艰辛。梳理史料不难发现,近代的大量息讼歌多是围绕诉讼费用花销极大、增加家庭经济负担为主要题材而创作的,创作者紧紧抓住了农民贫困的经济现实来劝民息讼。以光绪年间宁国县县令所作息讼歌为例,歌曰:
劝我百姓莫赌气,赌起气来两不利。自古官廉吏不廉,一打官事便花钱。写呈词也是钱,堂费也是钱,十桩官事九宕延,不觉又是两三天。住客店也是钱,吃茶饭也是钱,一经投到又花钱。官坐高堂民跪地,种种情形真可怜。赢了官事财已破,输了官事难更难。难!难!难!不如忍耐且种田。”②
在这首官创息讼歌中,歌谣创作者用浓墨重彩的笔调将诉讼中存在的经济利害关系放置其中,其目的就是让民众看到诉讼带来的巨大经济负担后能知难而退,进而撤诉、罢讼。当然,这并不能说明官方对民众的深切同情,但其对民众的生活困境是有一定了解的,也正是抓住民众困窘的经济现实,才有该类息讼歌的海量出现。诸如此类以陈述经济利害关系为主题的息讼歌在史料中绝非个案,最知名的当数民国时期河南南阳内乡县的一首息讼歌,此歌源于明代,由青海乐都县令徐志炳所作,因朗朗上口便于传颂而被后人多次、多地改编。这篇息讼歌将诉讼费用的高昂和封建官吏的贪婪描绘的淋漓尽致:
听人教唆到衙前,告也要钱,诉也要钱。差人奉票又奉签,锁也要钱,开也要钱。地邻干证车马连,茶也要钱,酒也要钱。三班丁书最难言,审也要钱,和也要钱。自古官廉吏不廉,打也要钱,抄也要钱。唆人本来为腰缠,赢也要钱,输也要钱。”③
众所周知,息讼歌的主题构建和创作意图主要是为了让百姓止讼、罢讼,在这点上各地息讼歌均无不同。民国时期的息讼歌与晚清时期息讼歌的区别主要在于语言艺术上的差异。鉴于息讼歌是写给老百姓传唱的民间歌谣,因而民国初年的创作者一改前期文言化的创作笔法,剔除了晚清及前代息讼歌合辙押韵的文言格式,而采取了更通俗易懂的白话语言来创作息讼歌,且歌谣中夹杂着大量乡俗俚语,其目的就是让更多的百姓能够读懂歌谣的本意,达到止讼、罢讼的效果。同样是从经济视角出发劝民息讼,通过以下两首不同时期息讼歌的对比,从中可以发现二者语言艺术上的差异:
词讼不可兴,家业从此废;纵赢一万兵,自损三千骑。讼师摇软桩,干证索厚币;哪有善公差?亦无白书吏。官断未可知,危惧如临履;倘然失足时,辱及难遮蔽……我劝世间人,词讼勿儿戏。若非不共仇,切勿相牵系;俚言详且确,万恳牢牢记。④(上海松江地区)
劝尔永邑民,还是息讼好。忍得一时气,解得百日恼。些小不平事,只消自按倒。切莫听人唆,祸来他不保。钱要自己费,路要自己跑。罪是自己当,愁是自己讨,你若要告状,事事耽误了。头畜无人看,地里不生苗。秋来无粮食,冬来无皮袄。仔细思量起,告状有何好?⑤(陕西永寿县)
这两首息讼歌分别创作于清光绪年间和民国初年,均表露出创作者希望当地百姓能遇事忍让的美好愿望。二者在创作语言上稍显差异,前者还无法彻底脱离文言创作的形式,而后者则加入了一些白话和乡间俗语,更易于被普通民众所接受。当然,二者最大的共同点还是歌谣中一再强调的“争讼”会导致“劳民伤财”、“牢狱之灾”等不变的主题,同时也增添了官方对“争讼”的排斥态度,目的是让百姓认识到政府是不提倡、不支持诉讼的。
经济根源是息讼歌创作和推广的主要原因之一。首先,这是因为传统农业经济占主体的中国,人们多采取“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然经济的生活方式来重复每天的日常生活。较长的农业生产周期决定了传统农业社会是一个力求稳定的社会。普通百姓不愿意因诉讼而耗财、费力去打破这种稳定。其次,农耕条件下商品经济不发达,客观上限制了人际间的广泛交往,压抑着人们诸如诉讼这般“人权”式的社会性诉求。最后,对于统治者来说,只要人们交足赋税,也就懒得去管百姓间的一般纠纷,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民众的诉讼诉求。所以,这类紧抓诉讼者经济现实的息讼歌能够广泛地被民众接受并吸收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息讼的社会根源
并非所有的息讼歌都以“耗财败家”这种“一元化”的经济视角来劝民罢讼,更多的息讼歌中所夹杂着的是有关宗族荣辱、家庭和谐、邻里和睦等不变的主题。这是因为传统的中国社会是由一个个宗族构成的,宗族观念像血液一样流淌在每个中国人的身体里,这种“敬宗”“祭祖”“血缘”的传统观念传承了数千年。时至近代,纵然国门洞开,西方文明也仅仅是沐浴了沿海地区的通商口岸而已,广大中华腹地,尤其是乡村地区,传统的宗族观念依然十分浓郁,人们把对祖先的敬畏和宗族的荣辱时刻放在心间,并作为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凡是有悖于宗族礼法的事情不做,凡是有损于宗族荣耀的事情不为,早已成了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座右铭”。所以,官方创作的大量息讼歌时常紧紧围绕百姓们根深蒂固的宗族观念来行文,以宗族荣辱、家庭和睦、邻里关系和谐等这些被宗族视为永恒不变的主题来推广和扩散,以此来扩大息讼歌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如清末清水县知县高蔚霞所作息讼歌就为该类息讼歌中的典型,歌曰:
谕尔四民,各有五伦,弟恭兄友,孝顺双亲。夫妇和睦,相敬如宾,同宗叔侄,辈分当遵。凡遇小事,切勿怒嗔,家庭兴讼,玷辱先人。联婚交友,信义立身,毋争雀鼠,结仇乡邻……⑥
在宗族观念中,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扩张。不仅如此,宗法时代所提倡的以血缘为纽带的聚族而居和世代毗邻的地域关系,使得社会成员如同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之中,枝蔓相连,很少流动。再加上儒家伦理道德学说的渗透与潜移默化,形成了和睦共处、和谐无争的生活准则,以致发生纷争时人们很少诉诸法律和求助于官府,而是寄托于纲常礼教的道德感化和族长、邻里的日常调解。经过这种宗法式“漏斗”对民间纠纷的过滤,诉讼案件自然也就减少了。如民国陕西永寿县的息讼歌:
你若不告状,诸事无焦躁。乡里既和睦,宗族不吵闹。夜里得个眠,日里得个饱。钱在腰里藏,儿在怀里抱。差使我早完,刑罚不用拷。人说你是呆,我说你是宝。皇天自然佑,何用神前祷。劝尔永邑民,还是息讼好!⑦
在旧时代的乡村,与农耕经济相适应的是乡村封闭的村落社会,而村落又是由宗族组成,人们之间多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血缘、亲缘关系。所以,同宗族内部的纠纷和诉讼自然会很少,即使偶有纷争,也往往由村落或家族内部自行解决如:
有罪的谢罪,有错的认错。该让的让些,该忍的忍着。分白随保正,劝解由乡约。免在衙前伺候,免教皂隶咄喝。⑧
这里的“保正”和“乡约”就是传统乡村宗族的代言人,宗族成员和邻里之间的纠纷在诉诸于司法途径解决之前,均由他们来进行裁决。
在宗族观念里,“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是自古以来恒定不变的行为准则,即家与国的利益是相互捆绑的。宗族为维护“家国一体”的传统观念,必须秉持无讼、息讼的态度。因为在宗族看来,家庭是国家的起点和缩影,国家又是家庭的延伸和放大,国家的政权组织与民间的宗法组织是互为补充的,宗法与国法是并行不悖的,国家与家族二者是统一的关系,国犹如家,家好似国,不管是国还是家都是以安定和睦为归宿,因而争讼被视为宗族不睦的表现,是不被提倡的。加之家庭、宗族内部成员之间又有浓厚的血缘亲情,个人之间再大的纠纷和冲突,也应在家族整体利益面前退居次要地位。如果有家人一旦参与诉讼,则被宗族视为大逆不道的行为。所以这类息讼歌能够在民间广为流传并被民众吸收。
三、息讼的政治根源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国家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始终是统治者的终极追求,以无讼、息讼为法制建构的价值取向,就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因为在官方看来,诉讼所涉及的绝不仅仅是双方当事人的事情,往往还会把整个家族,乃至更多的人卷入其中。侥幸胜诉者固然得遂所愿,然而败诉者也绝不会善罢甘休,以致有的诉讼延续几代仍纠缠不清。这种“冤冤相报”的残酷现实极易造成社会关系的高度紧张和社会秩序的动荡。因此,历代统治者宁愿将民间诉讼化解在公堂之外,以求社会的和谐安定。历代政府均极力提倡息讼、罢讼。以晚清道光年间浙江分水县县令饶芝所作息讼歌为例:
嗟我分阳民,风气本敦睦。迩来十余年,积案颇尘阁。岂其吏不廉,岂其政不肃。胡为雀与鼠,纷纷穿墉屋。或恃笔与符,或唆亲与族。令之蚌鹬争,饱我囊橐欲。投应畀豺虎,毒甚等虺蝮。不于为政入,严刑为驱逐。何以安善良,何以厚风俗。作诗以告汝,终凶爻须卜。狱货府辜功,辈带讼褫服。恢恢网不漏,毋谓任诋诱。⑨
从歌谣中不难看出,作者极力反对地方百姓为琐事争讼于公堂,因为这不仅劳民伤财、怠误民生,而且还有损于当地的社会风气和百姓教化,影响当地安定的社会秩序。在歌谣中他将唆使人诉讼的讼师、讼棍比作麻雀、老鼠、豺虎、虺蝮,并劝诫当地百姓不要受他们的怂恿而浪费大量的钱财去与人争讼,唯有如此,分水县才能够“安善良”、“厚风俗”。事实上,传统的儒家观念认为诉讼是不应该被提倡的,在儒家看来,一个地方官的执政能力的高低,并不是由他曾经办过多少个案子来作为衡量标准的,而是由他所治理的区域发案频率的高低来决定的。因而,息讼宁人、息事宁人、天下太平,日益成为一个地方官员的职业追求。所以,地方长官在处理一般性民事案件时,往往采取以“调解”代“诉讼”的方式来为自己谋求政绩,而息讼歌就很好的起到了以“调节”代“诉讼”的功能。
另外,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官方认为诉讼必然耽误民间生产,影响民众生活,甚至会造成妻离子散、流离失所的惨剧。这样既会影响国家的赋税收入,亦可能影响国家政局的稳定,这是所有统治者所惧怕出现的噩梦。为避免诉讼所造成的上述不良后果的出现,政府极力提倡并奖励息讼、无讼的地方官员,且逐渐将这种社会管理方式作为其向地方施政的重要手段之一。例如:
我劝百姓莫好讼,一事认气万事定。我闻健讼必终凶,讼棍唆弄切莫听。刀笔无非谝人钱,一人牢笼脱身难。功夫浪费田园荒,转眼秋来要完粮。一家老小都不安,可怜花的冤枉钱。银钱花尽一家哭,衣裳当去何日赎。人说花钱争口气,事后想想有何济。本县在家亦是民,今乃作歌广劝人。人能让人自家好,纵有小事亦可了。大家敬听本县言,落得过个太平年。年!年!年!父兄和气子弟贤。”⑩
在这篇息讼歌里创作者极力强调的是普通民众要学会“忍让”,遇见纠纷能调节的尽量调节,能忍让的尽量忍让,因为这样既不会因官司和别人结怨,也不会给家庭及宗族制造不必要的麻烦,更能够安稳地享受自己的生活。诚然,这种官方创作的息讼歌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地方统治的需要,以此来安定地方的社会秩序,教化民间百姓,使百姓养成息讼、罢讼的恒定观念。这里所说的能够使用调解结案的案件范围,显然主要指那些能够和解的民事诉讼,或者是属于轻微刑事案件,而非刑事重案。而且官方并不否认某些官吏的贪婪和利益驱使下的不公正,他们甚至会在息讼歌中公然承认一些现实,如在某些诉讼案件中执法官员贪赃枉法、营私舞弊,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利益,造成了官与民的尖锐冲突,从而成为社会动乱的诱因。为了消减和弱化这种现实中存在的矛盾,以求社会的稳定,他们会在自己创造的息讼歌中以“自嘲”的方式明确地告知和警示民众息讼、罢讼。如清末流传于山东滨州的一首息讼歌:
款待票差托值堂,终是向情不向理。厅批候审多焦劳,九牛难回呈一纸。无端何苦告诳词,弄假都言人不知。堂上高悬照胆镜,鬼狐哪能神明欺。指东说西白说黑,瞒天造谎能几时。一经审问是非判,徒惹讪笑遭刑笞……鹬蚌相持渔翁利,凡事还须细忖量。官清纵为民作主,衙役家中不种粮。安分良民听我劝,勿因小事到公堂。”⑪
在当时的官吏们看来,太平气象远比百姓争讼的是非曲直重要。他们往往运用调解的方法对争讼者进行道德说教和劝和,使之放弃诉讼需求以息事宁人,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并为自身积攒政绩。所以,官方总体上的态度是希望百姓安居乐业,不要轻易涉讼,倡导“纳税完粮,父老有闲须教子,省钱息讼,乡民无事莫来衙”⑫这样的无讼理念。官员除在公堂上针对涉讼深入剖析、晓以大义的同时,还会在日常生活中倡建“无讼堂”、“申明亭”、“省气楼”这些借以息讼、止讼的“风雅”场所。再者,在民间的家谱中亦可发现大量的以“戒终讼”、“息讼歌”等为主题的家规或族规。另外,在乡村社会也有很多诸如“茶肆乡评”、“中人劝处”、“里老剖断”等“普法讲座式”的教化形式,甚至还会出现宗族内部合资兴建“息止庵”式的义举,这些无不表达了政府在息讼宁人上的政治谋划。
四、息讼的文化根源
中国古代的文化崇尚和谐,在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追求和谐与无讼一直是社会价值观中的主流。《论语·颜渊》中就有“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的明确记载。可见,儒家所秉持的以和为贵、厌讼恶争的处世哲学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性格深深植根于国人的血脉之中。儒家自孔子提出“无讼”的主张以来,“无讼”、“无争”的和谐社会一直是该学派和历代统治者追求的最高社会理想或价值取向,在儒家看来,这个社会是“一个没有纷争和犯罪而不需要法律或虽有法律而搁置不用的社会”。因为儒家自古以来就主张息讼、罢讼,以求社会的安定及人际关系的和谐。
墨家向来主张“兼爱”、“非攻”、“尚同”,力主构建并意图实现这种理想化的社会模式,尽管这种“乌托邦式”的社会管理方式和现实相脱节,但其中所隐含的人与人相敬相爱、和睦共处、息兵止战的传统观念中多隐藏有大量“息讼”、“止讼”的成分,尽管墨家学派并未在秦汉之后传承下去,但随着历史岁月的斗转星移,墨家学说中的“无讼”思想却早已深入人心,并渗透到普通百姓灵魂的深处并流淌在其血液之中而代代传承。所以墨家思想中隐含有“息讼”“无讼”的观念是毫无疑问的。
对于道家而言,自学派开创以来,后人便始终遵循老庄“清净”“无为”的哲学理念,秉持“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哲学真谛,统治者也虔诚的认为道家倡导的“自然”就是要求人们遇事能做到“无为”,而这种“无为”反映在诉讼上就是“使民不争”。因为在道家文化里“争”是万恶的根源,为了避免这种“恶根”带来的“恶果”,道家提倡只有通过“绝仁弃义”、“绝圣弃智”、“见素抱扑”、“绝巧弃利”、“少私寡欲”的身心修养层次的提高,才能达到自然、和谐、无争的理想境界,才能结出人性的“善果”。因而以道家的哲学视角来看,近代的息讼、止讼观念中一直隐藏有丰富的处世智慧。
而法家往往从“人性本恶”和“好利恶害”的理论出发,主张法律的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定纷止争。战国早期的法家代表人物慎到就以“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的生动比喻来说明法律对人不良行为的束缚作用。因而法家主张“以刑去刑”,极力奉行重刑主义,然而其根本目的还是为达到“无刑”,而“无刑”中隐藏的内涵也正是“无讼”。所以,由此看来法家在看待诉讼问题上也是秉持着“息讼”和“无讼”观念的。
尽管诸子百家的思想中均含有“无讼”观念,但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支配统治者作出日常司法决策来推行“息讼”、“止讼”措施的主要还是儒家学说。儒家坚持为政以德,主张以德入刑,反对一味地严刑峻法,极力强调教化对臣民的影响和作用。因而自汉代以来董仲舒就提出“德主刑辅”的施政主张,具体来说就是要借助道德教化来建构和谐的无讼世界,而法律虽以刑为主,但刑罚只是治理国家的手段而已。因而自汉代以来历代统治者均大力提倡重人伦、兴教化、明礼仪、厚风俗。因为统治者深知国家的和谐与稳定仅凭法律的制约是很难实现的,更需要凭借道德的教化才能奏效。因此在实际的执法施政中统治者积极主张息讼、止讼,久而久之在人们的心目中,诉讼日益变成为贤者所不肖、为礼制所不容的无耻行为而受到人们排斥。
此后,“德主刑辅”这一施政方针成为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传统社会起主导作用的立法准则。在这种方针指导下,统治者极为重视民众的德行,主张用教化的方法推行传统道德,其对司法道德的主要要求是:“教化为首,德刑并用,慎狱恤刑。”⑬在该观念的指导下,“息狱讼”、“求无讼”,不仅成为各级官员的首要职责,也成为他们获取声名和政绩的现实诉求。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一旦有案件诉诸于官府,各级官吏一定会想出诸多办法来息讼、止颂。
我国传统法哲学中的价值学说虽然在诸子百家中均有提及,但自董仲舒之后,儒家学说却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和正统思想,受到历代统治者们的推崇并占据国家司法施政方略的主导地位。而作为儒家法哲学最高标准的“和谐”观念便日益成为整个传统法律文化体系中的最高价值追求,近代的“无讼”思想也正是这一价值取向发展的必然结果。
无讼、息讼观念,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影响悠久的历史传统已经传承数千年。近代的息讼歌虽然仅为中国千百年来无讼观念的一个缩影,但其背后隐藏的原因深刻而复杂:传统小农经济羁绊下形成的封闭、穷困的城乡环境让人们安于现状,从而力求生活上的稳定化和常态化;传承数千年的宗族荣辱观念延至近代,成了无讼思想产生最现实的社会原因;统治阶层对国家政局稳定的终极追求为息讼歌的大量出现和息讼观念的拓展提供了合理的解释;诸子百家的文化思想中隐含的“无讼”成分,尤其是儒家治世哲学中鼓吹的“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⑭的“息讼”观念,成为历代统治者和民众所长久信奉的处世“格言”。息讼观念被沿袭和息讼歌的大量出现,正是历史“隧道”中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斗转星移的历史时空里,唯有将这些隐含的历史线索逐一梳理,才能最终拨云见日,解开尘封已久的“息讼”密码。
注释:
① 林中厚:《碾伯知县徐志炳与〈息讼歌〉》,《中国土族》2011年第3期。
②⑩ 刘萍:《辛亥革命资料选编》 (第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635、635页。
③ 南阳地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南阳地区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4页。
④ 胡祖德:《沪谚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90页。
⑤⑦ 永寿县志整理委员会:《民国永寿县志》,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第355、355页。
⑥ 通渭县志编纂委员会:《通渭县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51页。
⑧ 宋同太:《应都滍阳》,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383页。
⑨ 陈常铧:《光绪分水县志》,上海书店1993年版,第38页。
⑪⑭ 侯玉杰:《滨州百家诗歌词曲》,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05、305页。
⑫ 龚汝富:《明清讼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36页。
⑬ 夏锦文:《刑事诉讼法学教程》,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