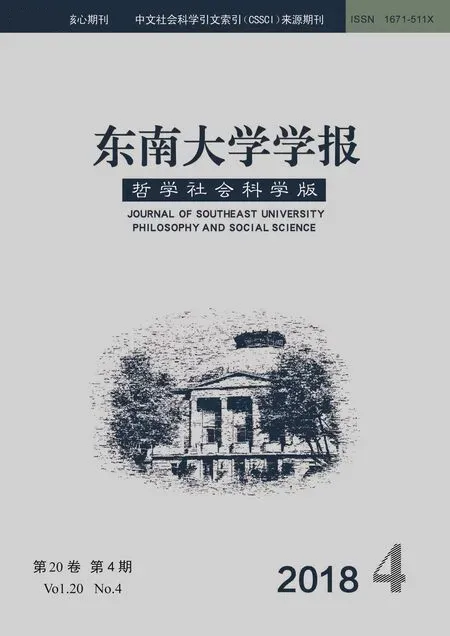中国传统艺术母题、主题与叙事理论关系研究
赫 云
(东南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6)
艺术主题通过叙事显示主题的含义与价值,也就是说任何艺术主题都具有叙事性。中国传统艺术主题在叙事结构中呈现艺术作品的主要功能,诚如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所说“成教化,助人伦”以及其他主题性的功能。当然,必须通过对作品主题叙事予以深入的分析,艺术主题的含义与文化价值才能出现。南宋李唐的《采薇图》(图1)用了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母题意象,以视觉的山水图绘形式呈现了曾被历代文人所表现过的宏大叙事的主题。“不食周粟”的母题不是偶然孤立的母题与主题表达,体现了历时性绵延发生的特殊价值以及系列性的呈现,使之具有母题与主题学体系的探究价值与意义,我们从“成教化,助人伦”的功能角度研究才有将“不食周粟”转化为一种艺术母题与主题体系的可能。如果我们把艺术母题与主题提升到母题与主题学理论层面,把叙事提升到叙事学的理论层面,探讨艺术主题学与叙事学的关系,则对与艺术母题与主题学的体系建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艺术主题在叙事结构呈现含义
艺术主题不像文学主题那样使人们容易理解其含义与价值。在文学主题中,线性情节的语言叙事结构相对“直白”,而艺术图像的“线性情节”深藏在图式的结构中。音乐主题多数需要谙熟音乐诸要素,通过对音乐旋律节奏的敏锐把握与理解才能阐释音乐主题含义;绘画主题同样需要谙熟绘画诸要素,通过对图像的辨认以及对图式结构的理解才能阐释绘画的主题含义。一方面,文字传递思想的确定性具有图像所无法企及的优势,很大程度上,文学作品表达主题的清晰度要优胜于艺术作品主题表达的清晰度。但另一方面,艺术主题阐释的空间却比由语言表述的文学主题空间大。当然阐释艺术主题不是随意的,需要以艺术的母题、意象、题材、隐喻以及原型等诸要素作为阐释的依据。因此,当面临绘画作品主题时,我们往往需要对图像中的母题或原型做必要的辨认、识别与追索,对题材、意象等进行分析,才有可能理清叙事结构并对艺术主题及其相关问题做出合理的探讨与诠释。把绘画作为图像的方式来分析与研究,大概是借用了图像学的某些方法阐释其主题含义,并显示图像学理论的价值,但是图像学把绘画作为图像引向象征意义的阐释时,却又忽视了绘画的艺术性问题。因为“图像志是美术史研究的一个分支,其研究对象是与美术作品的‘形式’相对的作品的主题与意义”[1]1。在艺术作品里艺术特殊的表现“形式”是艺术的“现象”,这个方面也有从艺术风格进行讨论的,沃尔夫林称为“艺术风格学”。同样,也有从现象学方面作讨论的,称为“艺术现象学”。日本学者伊集院令子认为“图像发生的现象学,作为胡塞尔图像理论的嬗变的结果,虽然胡塞尔自身还不能进行深入的展开,但是它已潜含着展开图像意识分析的可能性”[2]4,并在此逻辑上认为“图像主题,指的是通过图像客体而被模像的东西,也就是被想象的对象……以图像主题与图像客体间的类似性(和相合)为前提的模像性构成图像意识成立的基础,从相互渗透与直观性之间的关联出发,我们可以加深对图像意识就是把主题注入到图像中的直观意识和理解”[2]15。这是基于胡塞尔现象学的理论与脉络尤其是“必须关于现象”和“不证自明”所产生的艺术现象学理论。艺术现象学理论尽管也超越了胡塞尔的图像意识理论,但艺术现象学存在着其自身无法解决的难题,“回到事物自身”就容易把现象与本质的关系混同,更主要的是艺术现象学通过对艺术现象的探讨企图寻求艺术所拥有的哲学(现象学)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是图像学还是现象学都有自己的知识“盲点”,一个是丢弃了艺术本质,另一个是不涉及现象后面的艺术。钱锺书在说到文学时指出一个有趣的问题:“‘现象’‘本质’之二分是流行套语,常说‘透过现象,认识本质’。愚意以为‘透过’不能等于‘抛弃’,无‘现象’则‘本质’不能表示。例如‘索隐派’的文论以为文艺作品是真人真事的化妆,就是对‘现象’不够尊重。”[3]316这里说对现象不够尊重,不是指现象学所说“现象”,而是对“艺术形式”而言的。我们这里可以合理地借用图像学和现象学的方法,探讨绘画主题如何在叙事结构中呈现。

图1 南宋·李唐《采薇图》
艺术主题以“形式”这个“现象”在叙事中得以展示的。艺术形式不仅涉及艺术形象及所呈现的母题,还指涉艺术结构,如绘画的图式结构、色墨结构、音乐的旋律结构等。如果艺术主题一定要在叙事中才能得到确认,那么,叙事就需要母题、意象、题材以及结构等基本要素才完成。即艺术母题、意象、题材等在一定的图式结构中才构成叙事。换句话说,叙事是母题、意象、题材在某个逻辑展开中表述已经发生事件的独立结构,有了这个“独立结构”主题才能被清晰地揭示出来。由此看来,艺术主题与叙事是密不可分地存在于同一图式结构中的两个相关联的逻辑主体,一些没被显示的主题却会被暗示或隐喻的“空白”由观者进行补充或阐释,使“已经发生事件”的叙事趋于完整,这便是主题学、母题学所要从事的研究工作。李唐《采薇图》作品中两个人物形象是确定的,分别为伯夷、叔齐,图中石壁上著款有“河阳李唐画伯夷、叔齐”。背景“首阳山”则基本上是用山水图式暗示出来的特殊语境,因为这里的“山水”图式没有任何特质可以被认为是“首阳山”的地貌,但是可以通过观者补充完成它指涉“首阳山”这个特殊的“山水”语境,这补充的依据是提款的内容和图像中出现的挖掘工具和藤编篓,藤编篓里还有类似蕨菜叶(野薇菜)等母题元素,暗示着画中人物处在特殊的“山水”语境中,这既是《采薇图》绘画作品的图式结构与母题结构,同时也显示了《采薇图》主题的叙事结构。图画中伯夷、叔齐二人席地对坐,目光交流,似有对语,这也可以看作是《采薇图》中“情节”细化的一个母题性结构。但是这里的山水语境只有在确定了人物身份以及相关母题的出现时,“特殊语境”才可能产生明确的母题意象,否则这里的山水图式与中国传统山水画几乎没有区别,所以我们说它是暗示性的,需要观者补充或者阐释者去阐释才会有清楚的叙事逻辑结构。当然,这里还有两个母题是作为观者补充的重要细节元素,就是画中出现的类似于新石器时期水平的挖掘工具和藤编篓,它直接暗示伯夷、齐叔二人“采薇”这个情节,这个细节化的“情节”观者还可以无限补充,可以看作是绘画视觉叙事的细节化母题,也是暗示“山水”为首阳山的细节母题。一幅绘画作品的主题有着多个母题连接并存有其无限细节化的可能,这便是主题与叙事的同一基本结构。我们也可说这是绘画艺术主题以视觉方式叙事的主要特征,但这些母题、意象在图式结构中不是任何可以返回的时间动态元素,而是在结构中处于“静止”状态的,于是“静止”状态的母题、意象在结构中就有了“空白”(某种意义上与山水画的空白类似),就是说绘画作品的视觉叙事还需要观者的补充或阐释者的阐释,如同我们阐释山水画的“空白”一样,因为“在各种事物之间存在着实际上可以想象的细节的无限连续体,它们通常没有表达出来,但却‘可能’表达出来”[4]12。绘画作品中所谓的“通常没有表达出来”的是绘画艺术特性决定的,受制于绘画的“空间”因素,它们不同于“一本连环画或一部电影,都能毫不费力地转向接近长镜头并返回来”[4]12。这里就涉及我们通常说的“空间艺术”与“时间艺术”差异问题(中国长卷绘画图式另作别论)。《采薇图》需要通过对“图像”中人物(二者之间的关系)、首阳山(实际需要经验补充完成的)、藤编篓和简陋的挖掘工具等母题(实际已经成为意象),并借助“已经发生事件”的文本或传说来帮助完成叙事,从而使观者真正理解《采薇图》的主题表达。
我们说的“已经发生事件”是指在《采薇图》出现之前就有多种版本形式叙伯夷、叔齐 “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的气节之事。《史记·伯夷列传》载: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5]1688。
《史记·伯夷列传》文本中“不食周粟”是《采薇图》叙事的“原叙事”。它描述了伯夷、叔齐都是孤竹君之子。孤竹君欲立次子叔齐为国君,当其父孤竹君去世后,叔齐却要让位于兄长伯夷,伯夷认为父命不可违而逃避,叔齐也随兄逃走。后来,伯夷、叔齐听说西伯侯姬昌善养老幼而投奔周。刚到周,文王逝。武王继位,却拥兵伐纣。伯夷、叔齐认为诸侯伐君为不仁,便极力劝谏,责问“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士兵欲拿下二人,太公劝止,以为有仁义,扶他们离去。之后武王灭殷。伯夷、叔齐对周武王的行为而耻之,誓死不作周民,不吃周食。从此隐居在首阳山,采蕨菜为生,食不果腹,饿死首阳山,所做《采薇诗》表现了一种中国古代贵族高士的气节。此后中国古代诗歌中对“不食周粟”母题做了大量的描述即各种文本的叙事。
东晋陶渊明(约365—427)《夷齐》云:“二子让国,相将海隅。天人革命,绝景穷居。采薇高歌,慨想黄虞。贞风凌俗,爰感懦夫。”[6]36唐代韩愈《伯夷颂》云:“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崒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7]2741唐代白居易《续古诗十首》之一曰:“朝采山上薇,暮采山上薇。岁晏薇已尽,饥来何所为?坐饮白石水,手把青松枝。击节独长歌,其声清且悲。枥马非不肥,所苦长絷维,豢豕非不饱,所忧竟为牺。行行歌此曲,以慰常苦饥。”[8]19这些文本以诗歌的方式叙事,对伯夷、叔齐不食周朝之食,朝暮采食首阳山薇蕨,对“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的周武王感到悲愤宁愿饿死的举动,作了深刻的价值判断,对伯夷、叔齐二人宁可忍受饥苦而不变节操给予了赞颂。李唐的《采薇图》用绘画的形式通过对母题、意象的选择以及结构上的安排与诗人们做了同样内容的叙事,多种母题意象在结构上的叙事逻辑连接所显示的价值判断直接指向《采薇图》的主题。
需要注意的是《采薇图》的图式结构与母题、意象的组合与上述诗歌文本叙事结构明显不同,这是画与诗表达方式的主要区别与界限。诗歌可以按照时间的逻辑进行叙事,绘画则依据主题需要安排母题、意象逻辑结构进行叙事,如上述我们提到《采薇图》中的几个关键性的母题意象。同时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从母题、主题历时流变过程来观察,“采薇”“伯夷”“叔齐”等就是母题或意象,这些母题或意象倘若在诗歌与绘画中有差异性地出现,那么主题思想的重点就并不完全相同。《采薇图》用了更多细化视觉性的母题意象叙事,呈现的是“不食周粟”主题这个重点,不是“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的主题,也有隐喻君臣关系以及道德性的主题意义。当然,《采薇图》也有“隐逸”这个次级主题,即不为立国君而隐,也因“武王平殷”事件隐逸首阳山,借此表达隐逸主题。
二、叙事性结构以艺术主题为起点
上面我们探讨了艺术主题在叙事结构中得以呈现,同时提及母题或母题意象的概念。母题一旦与意象关联构成母题意象,它在诗歌或文学的“语法”方面便具有“修辞”意义,即“隐喻”的意义,也就是说母题意象就是隐喻。“采薇”(蕨菜)“伯夷”“叔齐”“首阳山”等母题的原型均与“让贤”后所发生的“事件”——饿死首阳山一起被赋予特殊的含义。“采薇”(蕨菜)“伯夷”“叔齐”“首阳山”这些母题只要在文本或图像中按照一定的结构组合在一起,它们立即成为母题意象,即成为文本或图像的隐喻,可能是隐喻的“隐逸”主题,也可能隐喻的是“气节”主题,这时文本或图像的母题在作者想象或预想的主题中便做好了叙事的准备,即母题意象具备了叙事性。不难理解,隐喻是叙事的基础或基本语言方式,尤其是绘画、音乐等艺术作品中的隐喻是叙事的根本方式。但是,叙事本身是在作者的主观意识或价值判断基础上进行的,或者说是以作者拟定与想象的某个主题开始的。母题意象叙事方式的结构由作者(艺术家)所想象或预想的主题而决定,艺术家在运用母题、意象时首先是依据自己对母题、意象作价值判断后,想象或预想艺术主题,再按照主题所表达的价值为坐标设定叙事的逻辑结构,使其叙事的逻辑结构符合主题内容的需要。
“隐逸”是中国传统文学诗歌的母题意象,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独特的“隐逸文化”现象。南朝梁刘孝威《奉和六月壬午应令》:“神心重丘壑,散步怀渔樵。”唐代王维《桃源行》:“平明闾巷扫花开,薄暮渔樵乘水入。”唐代杜甫《村夜》诗:“胡羯何多难,渔樵寄此生。”唐代高适《封丘县》诗:“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宋代苏轼《前赤壁赋》:“况吾与子渔樵於江渚之上,侣鱼鰕而友麋鹿。”宋代范成大《携家石湖赏拒霜》诗:“渔樵引入新花坞,儿女扶登小锦城。”明代屠隆《綵毫记·乘醉骑驴》:“乾坤傲,永不踏红尘向市朝,真唤做圣世渔樵。”明代杨慎《临江仙》:“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清代顾光旭《弓插》诗:“隔水断渔樵,横斜坏木桥。”几乎历代文人骚客都曾用过“渔樵”这个隐喻。隐逸文化已渗透到中国传统山水画领域,可以认为在中国传统山水画尤其是文人山水画中,隐逸是永恒的主题。渔父、樵夫成为中国传统山水画中具有恒定性的母题或意象隐喻,山水画中只要出现了渔父、樵夫母题,基本上就形成了隐逸这个主题。我们曾经分析过渔父、樵夫乃至渔船等都是隐喻,这些隐逸性的母题出现在山水画中便形成了山水主题倾向并决定了主题含义。“渔父”的母体原型我们曾经在《艺术主题在不同时期变迁渊源研究》《艺术变迁史中的主题学与图像学关系》中分析过,它源于《庄子·渔父》和《屈原·渔父》,后由此“渔父”成为隐逸者的隐喻[9-10]。中国传统隐逸文化萌芽于先秦,除了屈原和庄子“渔父”的原型,孔子《论语》还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同样明确地提到了“隐”。孟子亦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独善其身”就是典型的隐逸文化。
汉代是隐逸文化的发展阶段,文献中亦出现对隐逸的描述。《汉书·何武传》:“吏治行有茂异,民有隐逸,乃当召见,不可有所私问。”[11]2587《后汉书·岑彭传·子熙嗣》条云:“迁魏郡太守,招聘隐逸,与参政事,无为而化。”[12]439这里提到的实际为“招隐”,即统治者要招隐纳逸。两汉时期有不少不仕的隐逸者,魏晋南北朝是“隐逸文化”的鼎盛期。东晋葛洪《抱朴子·贵贤》:“世有隐逸之民,而无独立之主者,士可以嘉遁而无忧,君不可以无臣而致治。”[13]312有一大批隐逸者及其隐逸文化的形态,诸如文学、诗歌、绘画和音乐等几乎都涉及“隐逸”这个主题。“竹林七贤”是这一期的代表人物,隐而不仕,形成一股隐逸风气,他们也多用自己的方式表达隐逸行为与思想,服散五石,宽衣解带,放浪形骸,或操琴放歌,善琴的嵇康常用音乐表达隐逸思想。同时,社会招隐也说明了魏晋南北朝隐逸成风。左思写过《招隐诗》,其一云:“杖策招隐士。荒涂横古今。岩穴无结构。丘中有鸣琴。白雪停阴冈。丹葩曜阳林。石泉漱琼瑶。纤鳞或浮沉。”诗中描写了隐者的隐逸生活状态。其二云:“惠连非吾屈,首阳非吾仁,相与观所向,逍遥撰良辰。”诗中提到的“惠连”是指柳下惠、鲁少连,曾屈已受禄;“首阳”则指不食周粟、宁愿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诗中提到的人物、地名母题皆为隐逸母题或隐喻。东晋诗人陶渊明《饮酒》第五的诗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这篇典型的隐逸诗,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后来被放大为隐逸母题,被历代画家运用在山水画中,乃至“菊花”也成了“隐逸”的隐喻。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被历代画家作为“隐逸”主题不断地表达,“归隐”“仙境”成了隐喻和被放大的母题或主题。宋、元时期是隐逸文化鼎盛至精致的演变时期,苏舜钦《独游辋川》诗:“隐逸何曾见,孤吟对古松。”宋、元绘画中表达“隐逸”主题的作品达到一个历史高峰,《隐逸图》《归隐图》以及图像中绘有渔父、樵夫、渔船等母题元素的绘画皆属于隐逸主题的作品,山水画中的萧瑟、淡泊、简远等都属于隐逸主题的叙事结构。山水画隐逸主题演变到明清时,依然有仿照宋元的图式和母题借以表达隐逸主题,当然隐喻主题在流变过程中,逐渐呈现出与魏晋和宋元时期隐逸主题的差异。
我们上面大致对“隐逸文化”作了一个简单的梳理,目的在于用艺术中的“隐逸”主题来探讨主题与叙事结构关系。艺术作品“隐逸”主题的表达,依赖于具有隐喻特征的母题要素。但是,母题要素的叙事结构需要以主题为起点,这样才能形成明晰的隐逸主题内涵,而且艺术隐逸中主题还有微妙的区别,诸如“隐”“逸”“独钓”“归隐”“高隐”等多种主题。我们看看以宋元为主体的传统山水画。《归去来兮》(传陆探微)、《归去来辞图》(钱选) 、《溪山归隐图》(文嘉)、《归庄图》(何澄)、《归舟图》(戴进)等属于“归隐”主题;《清溪渔隐图》(李唐)、《洞庭渔隐图》(吴镇)、《花溪渔隐图》(王蒙)、《清溪渔隐图》(文伯仁)等属于“隐逸”主题;《桃园问津图卷》(文徵明)、《桃花源图》(仇英)、《桃源仙境图轴》(仇英)也属于隐逸主题,但主题源自陶渊明《桃花源记》文本。上述主题中,有的山水画题目可能是后来依据画面母题叙事结构补加的,而有的就是原题。无论哪一种情形,都显示了母题的叙事结构与主题的关联性。这个关联表明了叙事结构以主题为起点,也就是说这些以“隐逸”为主题的作品,很大程度上是“主题”决定了叙事结构和母题逻辑关系。譬如《归去来兮》主题出自于陶渊明文本《归去来兮辞并序》,无论是陆探微、钱选、文嘉、何澄还是戴进,他们的《归去来兮》图式的母题叙事结构都是以主题为起点的,即主题是母题叙事结构的逻辑起点同时也是终点。钱选的《归去来辞图》(美国大都会美术馆藏)作品主要描绘了一个归隐官员乘舟回家的场景,画面中还有岸上迎接的人物(两个儿童和一位站立院舍门前的妇女)、岸边上的院舍、柳树等母题, 隐喻“归隐者”为穿着官服辞官回家的陶渊明,这些母题叙事结构的组合是围绕“归去来兮”这个“归隐”主题的。当然这些母体叙事的结构是在隐喻的意象空间中展开对主题的呈现,而文徵明《桃渊问津图卷》(辽宁省博物馆藏)却是以时间隐喻而展开的对主题呈现叙事性的结构,因为《桃渊问津图卷》为长卷图式结构。我们曾分析过:
这种长卷图式结构提供了一个阅读的时间概念,所以它不完全属于人们通常说的“空间艺术”的图像。长卷图式结构是中国古典绘画艺术中独有的图像形式,这给叙事带来极大的方便。《桃渊问津图卷》像《韩熙载夜宴图》一样具有分段记叙不同阶段不同叙事内容的功能,同时又将不同阶段、不同叙事内容连贯成一个整体的大叙事。《桃园问津图卷》分段描述了陶渊明《桃花源记》文本的所有叙事主题,该图大致分六段:第一段为江岸到洞口处。这段场景分别描绘了弯曲的溪水以及溪水两岸成林的桃花,山洞的入口处,一位渔父手持船撸正往洞口里行走。第二段为山石树木,相当于一个镜头横扫一段山水的画面,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过渡的画面,是呈现泉林之心的山水图式。第三段为洞内的桃园景色,有桑田、荷锄的农夫以及湖塘中的捕鱼者,远山溪流与近处山石、树木合围着这片湖塘,山上还有一间茅草亭。第四段为在一条通往村庄的道路上,渔父正在向路人询问各种情况,道路上有三五成群的农夫,一条正在吠叫的狗,这应该是“问津”的主题,顺着道路再往里行走,可见近距离的村舍细节。第五段,一位农妇在院内的门槛出半身向外探望,似乎已经听说外面有人进到桃园里,在一座主要的房舍里,村中的三位长者正与渔父共餐,房舍外面有农妇带着小孩玩耍并向里窥望。这一段绘有更大的湖塘与小桥流水,远处有村落茅舍、远山树木以及瀑布。第六段以近景描绘为结束,崇山峻岭中有一条从村舍通向山后的山间小道,小路隐蔽的尽头处有瀑布自上而下地倾泻,一位长者正往村中走来。文徵明《桃渊问津图卷》是一幅典型山水形态的叙事绘画作品[10]。
我们之所以认为这幅作品是具有时间隐喻特征的母题叙事结构,在于文徵明完全是按照与陶渊明《桃花源记》文本中所描述的主题时间顺序来安排母题叙事结构的,这里的“时间”与“母题”重叠已经成为一个隐逸意象的时间概念。因此,艺术母题结构的逻辑关系是艺术叙事题材、意象、情节与事件的脉络,无论是空间隐喻还是时间隐喻,叙事脉络的起点是主题,如同“辞以意为主”,这样艺术主题的呈现才会清晰,否则主题就容易变得模糊或被误读。
三、艺术主题叙事与隐喻
南宋陈骙《文则》云:“《易》之有象,以尽其意;《诗》之有比,已达其情。文之作也,可无喻乎?……二曰隐喻:其文虽晦,意则可寻。《礼记》曰:‘诸侯不下渔色。’《国语》曰:‘没平公军无秕政’。”[14]16这里用《周易》《诗经》来说文学的比喻问题,用《礼记》《国语》中的例证说隐喻问题。隐喻不仅能在文学诗歌中作为修辞手段,《易》之象之所以能够尽意,也因隐喻功能而体现。钱锺书在《管锥篇》说:“义理之博大创辟者每生于新喻妙譬。致以譬喻为致知之具、穷理之阶。”[15]20*钱钟书.管锥篇(一)[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16:20.足见“比喻”作为修辞手段的重要意义。比喻作为修辞手段,陈骙讲了有十种之多,一般而言有“直喻”“暗喻”“类喻”“诘喻”“对喻”“博喻”“简喻”“详喻”“引喻”“虚喻”[14]16。闻一多《说鱼》说:“隐在《六经》中,相当于《易》的‘象’和《诗》的‘兴’(喻不用讲,是《诗》的‘比’),预言必须有神秘性(天机不可泄露),所以占卜家的语言中少不了象。”[16]187所言的正是“隐喻”。艺术作品中有大量的母题,很多情况下属于隐喻类型,隐喻不仅仅是修辞手段也是艺术家表达主题的思维方式,它隐藏在叙事结构中,“合而仍离,同而存异”[15]182,叙事离不开隐喻思维和手段。因此,这里我们重点探讨隐喻与艺术主题和叙事的关系。
语言文学常用“辞格”或“修辞格”来增强语言文学的表达效果,隐喻常作为修辞语言或意境的一种手段。亦如人们赞赏“说梅不用一个梅字”。“梅”字不出现,其修饰手段不外就是隐藏梅花,即隐喻。闻一多先生在《说鱼》的开篇就是探讨“隐喻”问题,意在探明“鱼”在中国文化中所具有的“隐喻”文化特征。闻一多说“喻有所谓‘隐喻’,它的目的似乎是一壁在喻,一壁在隐。”[16]186隐喻不仅仅在文学中体现为一种常用的辞格手段,在艺术作品中也有类似“辞格”或“修辞格”的隐喻手段。艺术作品中隐喻的外观相对视觉艺术而言,我们可以称为之“物格”,音乐艺术称为之“音格”,是艺术的修辞手段。如前面我们用了大量的篇幅讲到渔父、樵夫母题就是隐喻,还有常与渔父、樵夫在图像结构形成认同后的转喻母题,如渔船、茅舍、菊花等形成的母题,从艺术修辞学角度讲就是“物格”。当然,提到隐喻必然要讲到母题,讲到母题必然要论及原型再到隐喻。这是主题叙事中必然涉及的隐喻、母题、原型等基本问题。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Lvy-Bruhl Lucien)在《原始思维》中说:“为什么一张画像或肖像对原始人来说和对我们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呢?如在上面见到的那样,他们给这些画像和肖像添上神秘属性,这又作何解释呢?显然,任何画像,任何再现都是与其原型的本性、属性、生命‘互参’的。这种‘互参’不应当理解成一个部分——好比说肖像包含了原型所拥有的属性的总和或生命的一部分。原始人的思维看不见有什么困难使它不去相信这个生命和这些属性同时为原型和肖像所固有。由于原型和肖像之间的神秘结合,由于那种用互参律来表现的结合,肖像就是原型。”[17]82有关“原型”,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把它称为“原始意象”或“集体无意识”:“个人无意识的内容主要由带感情色彩的情结所组成,它们构成了心理生活中的个人和私人的一面。而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则是所说的原型。”“正如一个人的本能迫使他进入一种特定的存在模式一样,原型也迫使知觉与领悟进入某些特定的人类范型。和本能一样,原型构成了集体无意识。”[18]17“在深化研究中它们被升为‘母题’。”[19]61如果我们将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改为“集体认知”作为“原型”来理解似乎更符合隐喻的特征。钱锺书在谈到对女性容颜的比喻时认为:“引彼喻此,杏歟桃歟,而依然不失为人之脸颊,玉乎雪乎,而依然不失为人之肌肤;合而仍离,同而存异,不能取彼代此、纳此入彼。”[15]182“合而仍离,同而存异,不能取彼代此、纳此入彼”很符合文学隐喻修辞的方式与手段。艺术图像中反复出现的母题在历时性的运用中以叙事表达艺术主题,它是人们在对母题原型的共同认知基础上形成的隐喻,并以此确认叙事的艺术主题。“渔父”与“樵夫”作为艺术母题,它们的隐喻是在人们集体认知意识的“原型”中形成,并在历时性中成为具有恒定性的母题意象或隐喻。正因为“渔父”在《庄子·渔父》《屈原·渔父》中是以隐者的身份出现并与孔子和屈原对话,使“渔父”在历时性的叙事中固化为隐者这样一个隐喻。渔父这个母题出现在山水画中,不仅作为山水画的构图“修饰”,以及作为图式结构上的视觉需要来点缀的人物形象,而且也是给绘画作品带来无穷的阐释空间与解释隐喻的内容。“桃花源”作为一个宏大叙事的主题、母题和意象,其最早的原型是陶渊明《桃花源记》文本,它也是有一个“渔父”的母题,但不同于其他渔父的叙事结构,却又与“渔父”这个隐喻具有相近似的母题原型,“渔父”作为隐喻成为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集体认知,尤其是创作者(艺术家)在运用“渔父”这个母题时,在潜在的认知中都指向“隐者”这个隐喻,读者或阐释者也会在这个认知的指向中确认绘画叙事并理解艺术主题。
但是,“渔父”与其他母题组合在一起构成相关联的母题群时,其叙事结构与主题意义可能不同。“渔父”如果与山洞、溪流、桃花林、桑田、农舍等母题或意象组合,叙事结构可能与一般性的“渔父图”不同,它很可能指向的是“桃花源”这个人间仙境。台湾美术史学家石守谦在《移动的桃花源》中,将不同地域和不同时期流行的“桃花源”主题、母题作了变迁研究,他从元代至清代不同版本的“桃花源”山水画中分析了由于母题、意象等变迁或变异其叙事结构所发生的移动,发现桃花源主题出现了较大的差异性,大体形成了“人世化”和“仙境化”两类主题叙事。石守谦是这样对“桃花源”图像“人世化”叙事主题作诠释的:
有趣的是:出自赵伯驹的《桃花源图》的末尾段却对文本的结尾作了调整,既不作离去的渔人,也不作象征政治力的郡守人马的“不复得路”,而只描绘了高山流水环绕中,独行于道的刘驎之策杖身影。策杖高士在中国山水画中向来意指着对某种理想境界之追寻,辽宁叶茂台辽墓所出《深山棋会》中便有策杖高士仙人居所行去的形象,《桃花源卷》最后的高士亦有此意才是。相对于卷前已经加以“人世化”的桃园世界,以及身在其中的渔人而言,独行于山中而被密实之山体所包围的策杖高士,可说被赋予了更强烈的企求桃园之感。它的重点已非在于惋惜桃花源之永远失落,反而表达了一种呼应苏轼等人将桃花源“人世化”的诠释[20]42。

图2 元·王蒙《花溪渔隐》
这里的“渔人”(“渔父”)作为“策杖人”来处理,母题形象作了较大的改变,使母题意象发生演变,“人世化”主题与陶渊明本文《桃花源记》或带有仙境叙事的《桃花源图》主题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变迁。“它一方面进一步淡化与《桃花源记》的直接关系,另一方面也抛弃了原来仙境传说的母型,加强了‘人世化’的理解,甚至开始展现‘实地化’的现象,几乎可以说是第一模式仙境山水的相反对立。如此的发展,最佳之图绘范例应属14世纪中期的王蒙《花溪渔隐》。”[20]43这种演变的发生正是由于母题隐喻性质的变化从而使叙事结构发生变化的结果,石守谦分析《花溪渔隐》(图2)有着“人世化”和“实地化”的主题表达,其原因在于王蒙在淡化与《桃花源记》的直接关系的同时,也抛弃了原来仙境传说的母型。这就是说,《桃花源记》中呈现的母题、隐喻和叙事结构与“渔隐”主题的内容相一致、相统一,与仙境中的“仙隐”主题相反对立。我们再略分析一下王蒙《花溪渔隐》图中的母题、隐喻、叙事与主题的关系。《花溪渔隐》以轴型图式结构展现渔父划船以及溪流中的情景,在一个特定的隐喻空间中展开了叙事,在放弃陶渊明文本母题原型中一些重要元素的同时,保留了一些母题如桃花、溪流、房舍、渔父、渔船等,叙事逻辑尽在此空间中呈现,放弃了《桃花源记》文本的描述: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

图3 明·文徵明《桃渊问津图》局部

图4 明·仇英《桃源仙境图》
王蒙的《花溪渔隐》与文徵明《桃渊问津图卷》(图3)在叙事结构上完全不同。文徵明图式结构如前所述与陶渊明文本描述几乎一致,而王蒙《花溪渔隐》图式则仅保留了“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的叙事空间结构。图像中母题如上述所说为桃花、溪流、房舍、渔父、渔船和高大的山峰等,图式结构完全是独立山水画范型,并且没有“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母题与叙事结构,亦如图像两岸疑似的桃花中,偶有杂树,而非是“落英缤纷”的母题。说明王蒙确有摈弃“仙境”的意图,将陶渊明文本母题和叙事结构做了重大的调整,以符合自然山水的常态化,保留渔人(渔父)在船头摇橹的母题以及溪流、桃花等母题。还需注意的是,渔船上不是渔人(渔父)一个人,船尾也有人划桨,船篷中似端坐一人,这三个人的出现改变了陶渊明文本“渔人”独自一人进入仙境的叙事逻辑,作为渔人的隐喻性涵义回到了单纯的渔父隐逸主题上,使母题、意象的隐喻和叙事离开了陶渊明《桃花源记》的主题。文徵明《桃渊问津图卷》主题接近陶渊明《桃花源记》“仙境”主题,图像中的母题、意象的隐喻和叙事逻辑也与“仙境”主题的表达相一致。当然,空间叙事结构并不是影响主题表达的唯一结构。同样作为轴型范式的仇英《仙境图》(图4),图像中的母题、意象的隐喻和叙事结构与陶渊明《桃花源记》“仙境”主题相一致,不仅如此,仇英的《仙境图》还强化了陶渊明“仙境”的主题,将桃花源中的人物处理为仙风道骨的隐士,把陶渊明的“人间仙境”演变为“天上仙境”的主题来表达。艺术主题不同,图式结构、母题、意象的隐喻以及叙事的逻辑或结构也就不同。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艺术主题,就有什么样的母题、意象的隐喻和叙事逻辑或结构,它们之间都是统一的。这也说明为什么母题性质、意象显现和隐喻内涵直接关系到艺术主题的形成与内容的表达。“桃花源”作为陶渊明诠释的一个仙境意象或宏大主题,可能就是一个现实的虚构意象,我们也可以把“桃花源”本身看作是一个仙境母题的隐喻,这样就可以通过源于同一虚构仙境意境的母题、意象、隐喻的演变,以及图式结构的移位与叙事逻辑的变迁判定“桃花源”主题是“人世化”或“实地化”还是“仙境化”叙事主题的山水画。王蒙的《桃花源》图显然带有“实地化”,尽管山水造型有着理想的图式结构,但图中船上三人颇有“现实”质感。仇英《仙境图》本身就表明了主题的含义,图式结构、母题、隐喻、意境以及叙事逻辑都作为强化陶渊明文本“仙境化”的视觉图像。文徵明的《桃渊问津图卷》,母题、意象、隐喻、叙事结构与主题表达,则完全是遵循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叙事逻辑路径和母题的视觉化,是青绿山水“仙境”图的典型代表。如石守谦所说:“桃花源意象虽然起于虚构,在后来的发展中则出现了各种随不同需求而生的人世化的化身,它们的山水图绘方式也因之所调整。有的时候选择青绿山水那种非自然的形式来强调桃花源永远失落的感叹,有的时候选择隐居山水图的模式来寄托对平静生活的单纯期望。……桃花源不必具有固定的形象,那个传说的原有情节亦无需一再重复,山水画所表现的人及人与自然关系在此时即被转化为对桃花源意象在不同情境中的不同追求。”[20]25的确,不同时期的艺术家在表达自己(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借用已有的母题隐喻或借用已有的某个主题,可能会按照已有的母题或主题绘画作品追求一个相同的主题含义而把自身置于其中,有时可能仅仅是借喻却不必局限于原有的母题与主题,表达艺术家现实中的自身与自然关系所做的重新思考和理解,这就形成了母题、意象、隐喻与主题的转化而所呈现出的不同的图式结构、母题隐喻与叙事逻辑。
四、结语
“桃花源”本身作为母题被广泛地运用,表达画家对“仙境”的理想与追求。元、清这两个时期“桃花源”母题意象或主题表达再次成为文人画家表达的对象,其中主要原因是由于异族的统治,汉族文人士大夫“学而优则仕”的宏大抱负愿望难以实现,使文人们仕途的机会与途径受到严重的影响,于是隐逸成为他们的选择。以“桃花源”为母题意象或主题的各种绘画版本在元、清两个时期出现的相对比其他时期多,这与异族统治时期对汉族文人仕途的冲击有极大关系,作为文人画家自然把目光重新投向魏晋时期的隐逸生活与理想。明代画家出自各自的需求多少延续了这个“母题”与“意象”,只是在母题、意象、题材包括主题等方面,不同时期对“桃花源”母题意象与主题所做的理解、诠释和处理有所不同。与此相呼应的是“归隐”母题或主题,如元代钱选《归去来兮图》,同样表达了在异族统治时期文人“隐逸”的心态倾向。而且,“归隐”母题或主题大量出现,在“归”的母题隐喻方面强调“隐”的理由,同时又对“归”母题隐喻做不同的理解与诠释,“待渡”“归舟”也许就是对“归”的隐喻的不同诠释。这就是艺术母题、主题在不同时期的流变,构成了不是孤立的而是绵延的母题或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