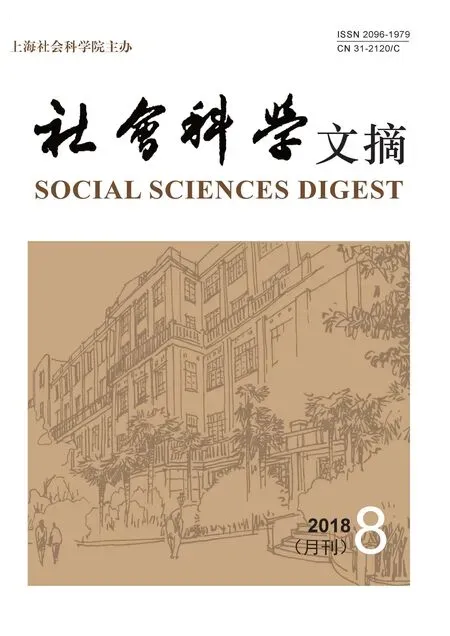以更宏大的格局推进中国古代文明研究
20世纪初兴起的疑古思潮和几乎同时开展的古史重建工作,无疑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大事,距今恰已有百年的历史。一方面,疑古思潮对破除传统的古史观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为以科学方法重新探索古代文明扫清了思想障碍;另一方面,以文献为主的历史学和以田野为主的考古学相互结合,不断取得新知,对早期的疑古工作多有匡正。正是在这百年来艰苦曲折的摸索过程中,学者们先后提出了多种建设性的学科概念,影响卓著的如王国维的“古史新证”、李济的“古史重建”、张光直的“新先秦史”、李学勤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需要指出的是,近几十年来新资料的不断涌现,各分支学科的日益壮大,都为古代文明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与此同时,传统的先秦史学科却遭遇了不小的尴尬。随着考古学、古文字学等学科的独立性日渐突出,留给传统先秦史学科的空间却被逐渐压缩。在传统的学科框架下,当越来越多的邻近学科不断闯入上古时段的研究领地并取得突破时,“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内涵更显宽泛全面,且具延展性。
学者们之所以提倡将中国早期时段的文明研究单独列出,并不单纯是为与西方的埃及学、亚述学、古典研究等相抗衡,更是源于这一时段的学科特性与秦汉以后大不相同。秦汉以后文献记载较为丰富,历史学的研究可以起到主导作用。早期时段则不同,它不能单独以文献为主建立自己的谱系,需要用大量考古学、人类学的方法进行补充,不过也不能因此就忽略文献的记载而走向完全极端的另一面。这一点是由它所处时段的特殊性决定的,即国际上所通称的“原史时期”(protohistory),正处于史前(prehistory)和历史时期(history)之间。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达成早期文明研究中历史学与考古学应当并重的共识,至于二者之间如何实现进一步的有机融合,则是我们当下面临的重大课题。在这种背景下,以已有的传统学科概念指称这一时段的研究似乎都不合用,这正是建立“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学科的意义所在。
回顾百年来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历程,可以看到前辈学者们取得的成就,也需要冷静思考目前学科发展面临的问题。笔者以为有三个方面需要特别注意。
相关学科的精细化与交叉
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牵涉的学科甚多,如果从时段来着眼,其中历史学(主要是先秦史)作为基础是不言而喻的,此外最为密切的便是考古学和古文字学,正是史料构成了三者共同聚焦研讨的部分。主要由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综合而成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自然也具有交叉学科的特征。
20世纪初,由于科学思想的传播,近代考古学由西方开始传入中国,当时中国考古学成就,以安阳殷墟的长时期、大规模发掘最为突出,各处发掘所得的甲骨、青铜器及其他考古资料,为学者尝试重建古史带来了曙光,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就诞生于这样的背景下。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考古学更是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重大发现层出不穷,考古学理论和方法越来越丰富,学科框架和谱系日益完善,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也更加广泛。时至今日,考古学取得了与中国史、世界史并列一级学科的地位,已经显示出分庭抗礼的态势,在具体的理论、思路、方法和手段上都会有所不同,随着学科发展的精细化,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学科分界将会进一步拉大。
现代意义上的古文字学与考古学联系最为密切,古文字材料大都是从地下发掘获得的,同时也都是考古材料。借助于考古学的层位学、类型学等基本方法去整理和研究带有文字的古器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文字之外的疑难问题。同时,古文字学对于考古学和古代史的研究也贡献巨大,这一点在甲骨文之于殷商史、金文之于两周史的关系中体现得最为明显。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古文字材料的大量出土,尤其是青铜器、战国秦汉简牍等资料层出不穷,古文字学科加速成长,业已从“绝学”变为“显学”。
学者已经指出,古文字学下属的分支如甲骨学、青铜器学、简帛学等已发展得相当成熟,皆可成为一门独立的专门学科。21世纪成长起来的古文字学者与前辈学者相比,最大的不同是需面对原始材料及研究成果的加速堆积,使得每人的精力只能应对古文字学下的某一分支学科。需要注意的是,在日益精细化发展的古文字学科中,释字及字形规律的总结仍是目前研究的主流,而如何将王国维等开创的古文字学与古史研究密切结合乃至合而为一的传统发扬光大,还任重道远。
如何让历史学获得更多源头活水的支撑,让考古学超越遗址遗存的物质意义,真正使二者有机融合,是研究者需要虚心思考的大问题。跳出各自学科的程式,以更宽阔的视野和更宏大的格局关注共同的研究对象,正是“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这一综合学科的优势。
信息超载的困境与史学本位的出路。
与考古学、古文字学等学科的精细化迅猛发展形成反差的是,传统先秦史学科似乎在逐渐丧失研究领地和话语权。最近一二十年,先秦史学者较多地作具体的点状研究,更大层面上的专门史乃至通史著述明显减少。一方面这固然表现出先秦史研究脱离了大而化之的空谈强谈,实证精神越来越得到弘扬;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传统先秦史学科的困境,即新材料日益堆积造成的信息超载和史学本位淡化之间的矛盾。
欧美学界颇具影响的乔·古尔迪、大卫·阿米蒂齐《历史学宣言》指出近三四十年来,西方历史学界“养成了只求时段缩短、文献精益求精的习惯”,只追求“对越来越少的东西知道的越来越多”。这种局面在中国史学界也同样呈现,研究碎片化便是最突出的弊病。与之相比,传统先秦史学科可谓同病相怜,学者们一面感叹邻近学科带来的信息超载,一面又感到深入开展史学专题研究时材料不足,其结果必然是史学研究逐渐缩小自己的范围,越来越多地让位于考古学和古文字学。
何以会造成这种矛盾?主要原因在于考古学、古文字学与历史学之间的融合不足,乃至最终造成各自都对史学本位出现了回避和退让。近年来,学者开始越来越多地对学科发展进行反思,在考古学越来越精细的现状下,考古学理论又暂无大的突破,考古学处于学科发展的瓶颈期,它必须注重观察长时段文化和社会的变化,以更开阔的视野来研究整个历史发展过程。20 世纪历史科学的发展与现代考古学的确立和壮大息息相关,考古学的终极目标同样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
与考古学界的自觉反思相比,古文字学科还表现得不太敏感。这一方面与古文字学所处的学科体系有关,古文字学目前分属于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等不同的学科门类,研究者受各自学科体系的影响,自然容易产生不同的研究风格和路线;另一方面,古文字学需要从事的初阶工作常常是材料的整理和文字的释读,这也大大强化了研究者对具体点状问题的关注,而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对高阶宏观问题的探索。有鉴于此,李学勤教授近来公开呼吁:“我们是不是能有更多的人,能够投入更多的时间,对于学科各个分支所涉及的一些关键性问题进行深入的整理和探讨?这样我们的学科就会得到更快的发展。”看来,在推动新出材料整理和研究的同时,如何对次新材料进行持久的关注、深入的探索、充分的吸收和融会的概括,是古文字学科今后提升自身格局的关键。
如果说文字和文献的碎片化研究,对于理解历史的演进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助益,不能刷新人们对重要问题的看法,大大限制了新出资料发挥应有的史学价值,那么,传统的先秦史学科又该如何应对自己的困境呢?如果最终史学产生的知识无益于对历史时段的解释和反思,其价值就相当可疑,这是从事史料整理和历史问题探索的终极关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清醒地判断早期时段的文明研究,落脚点必然在史学本位上。只有明确了这一点,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等相关学科,才能从具体材料的细密整理中超越开去,提升学科的整体格局,并最终打破信息超载的困境。
学科融合与比较研究的必要性
正是由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是以史学为本位、以史料处理为基础,那么史料来源的多样性,就决定了该领域下多学科的融合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正是必须。研究领域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古文献学、古文字学、科技史、艺术史、学术思想史等诸多方面,需要研究者具有深厚扎实的古文献基础,掌握大量的一手资料,尤其是以现代考古手段所获取的地下出土材料,而且还必须运用视角广泛的比较和理性充分的思辨,对所有这些基础资料和相关学科,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整体的把握。
要深入理解具体的史学问题,总离不开对长时段、大视野下历史脉络和背景的把握。由于对史学问题探索程度的深浅不同,作为整体知识的历史背景也呈现不同的尺度。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已经注意到不同时段以及不同区系之间对比研究的必要性。还应注意的是,在更大尺度上对中西文明进行比较,大有益于中国的古代研究。
李学勤《比较考古学随笔》指出:“较广阔的视野,会纠正孤立看待一种文化或其因素时每每出现的弊病,使我们对这种文化或文化因素取得更深入的认识。”事实上,中国考古学的前辈李济、夏鼐以及中国古史研究的前辈王国维、郭沫若等先生,无不吸收借鉴了世界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当然,比较研究不是随意的对比陈列,纳入比较对象的视野越宽,越需要研究者具有足够广博的知识储备,相应地,由此取得的认知也会越发深入透彻,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探索也将达到更高的理论层次,这需要史学界全体同仁的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