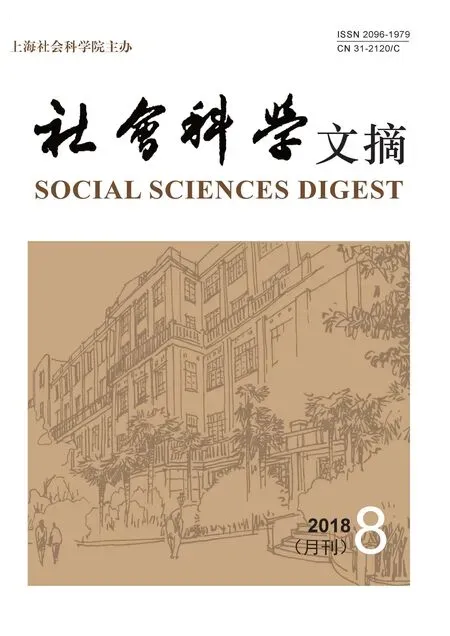论中国古代文学形式中的政治意涵
一
从历史演变角度看,确实如伊格尔顿所说,每一种文体的产生或者重大变化差不多都与重大的历史激变相关联。如汉末曹魏时期的文章体式与修辞由繁缛到简洁的变化就有着明显的政治原因。刘师培说:
建安文学,革易前型,迁蜕之由,可得而说: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一也。建武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尚通侻,侻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二也。献帝之初,诸方棋峙,乘时之士,颇慕纵横,骋词之风,肇端于此。三也。又汉之灵帝,颇好俳词,下习其风,益尚华靡,虽迄魏初,其风未革。四也。
这段话论及了两汉之间、汉魏之间重大的社会政治变革在文学形式上留下的深刻印记,揭示出文体、修辞、文风与时代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对于魏晋时期文体形成背后的政治意涵,王瑶先生曾有过深入而全面的的剖析,他认为汉末魏晋时期由于政治上选人得才的需要,社会上人物识鉴之风盛行,因之校核名实,即所谓“名检”,就在当时的学术思想中居于重要位置。在此基础上就形成了名理之辨的学术旨趣,以及“位”与“职”符、“职”与“才”符的评价标准。
二
除了重大社会政治事件之外,身份政治也是考察造成文学形式变化原因的重要视角。文学形式往往与文学主体身份具有极为密切的关联。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形式,包括文体,常常也成为主体身份的符号表征。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五言诗的兴盛与汉魏之际文人身份认同的联系中得到充分印证。有大量文献材料可以说明,正是因为东汉后期在民间渐渐出现的一批既不同于穷经皓首的传统儒生,又不同于那些被称为“辞赋之士”的文学侍从的宦游文人,五言诗这种新的文体才得到蓬勃发展的。可以说,五言诗正是文人趣味的产物。这里所谓“文人”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士大夫阶层,而是指士大夫阶层中的部分成员在东汉中后期逐渐形成的一种新的身份,其基本特征是赋予诗词歌赋这类传统文学形式表达个人情趣的新功能。在此前两汉三百多年的历史上,诗词歌赋或者是用来美刺讽喻的,或者是用来“润色鸿业”的,都是官方意识形态的附属品,缺乏真正的文学所应有的自律性、自主性。只是到了东汉中叶以后,出现了张衡、秦嘉、郦炎、蔡邕、赵壹以及“苏李诗”和“古诗十九首”的作者等一大批士人,开始在诗词歌赋中表达离愁别绪之类的个人情趣,这些人已经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他们又获得了一重新的身份,那就是“文人”。这不是司马相如、枚乘、东方朔那样专门迎合帝王趣味的“宫廷文人”,而是表达个人羁旅之情与生命情怀的民间文人。“古诗十九首”堪称这类文人之趣味的集中体现。这种以玩味、表达个人情趣为特征的文人身份与两汉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家或经学家身份迥然相异,两者之间甚至存在某种内在冲突,但又常常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张衡、蔡邕等人在政治上都有所建树,这与传统士大夫一般无二,但他们又同时是可以借助诗歌展示个人内心感受和体验的文人。
如果说四言诗作为《诗三百》的主要文体形式带有强烈的正统性、经典性,与士大夫之政治家、经学家身份相契合,那么五言诗则刚好成为那些疏离于正统观念的文人身份的话语方式。刘勰说:“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这是说四言作为诗歌的正宗,体现的是“雅润”风格,五言诗作为诗歌后起文体,特点是“清丽”。所谓“雅润”,即是雅正润泽的意思,正是对《诗经》“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内容与“温柔敦厚”的风格的概括。钟嵘说:“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烦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这段话被论者广泛引用,但通常被理解为“滋味说”之始出。对于“滋味”,一般理解为“诗味”,指艺术效果或审美感染力而言,鲜有深入究其与文人身份之关联者。这里可略作申说。盖四言,因其为《诗经》之基本体式,故汉儒视为诗歌之正宗。而汉儒以“《三百篇》当谏书”,是故亦以四言诗负载美刺讽喻之使命。由此观之,四言诗之在两周,是为贵族言说之形式;其在两汉,则为士大夫言说之形式,其内涵直接即具有政治性。因其主要功能或美或刺,所以是“文烦而意少”,此即谓,徒然花费许多言辞,所能展示的意涵却很少,根本无法表达更丰富细腻的情感体验。故刘勰说:“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意指汉代四言诗与诗经讽谏传统的密切关联。看韦孟现存的《讽谏诗》和《在邹诗》确实严守“诗三百”的“美刺”传统。其他汉代四言诗也大抵如此。
与四言诗相比,五言诗则为“众作之有滋味者”,这里的“滋味”显然是四言诗所缺乏的,那是何所指呢?明人许学夷说:“汉魏五言,为情而造文,故其体委婉而情深。”这正是对钟嵘“滋味说”极好的诠释。这就意味着,在钟嵘这里,五言诗这一诗歌体裁是与张衡、秦嘉、郦炎、蔡邕、赵壹以及“苏李诗”和“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三曹”以及“建安七子”等魏晋以来的士族文人联系在一起,是这些人创造并使用的情感表达方式。因此,五言诗与四言诗看上去仅仅是文体上的分别,属于审美范畴的事情,然而实际上却是有着深刻的政治意味。 四言诗与传统士大夫身份关系紧密,多用来表现主流意识形态;五言诗则与文人身份相契合,多表现个人情感。当然,这只是就大体而言,由于文化惯习的作用,汉魏时期也有文人用四言诗来表达个人情感的,更有士大夫用五言诗来表现美刺讽谏的。
三
各种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在解读文学时常常能够读出一般读者无论如何也读不出来的意思,有“过度阐释”之嫌,近年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诟病。那么文本形式中的政治意涵究竟是批评家“过度阐释”的结果还是文本形式原本就蕴含着的?这无疑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从中国古代文学的“叙事”和“隐喻”来看,文本形式中的政治或意识形态意涵至少有两个不同的层面。一个层面是接受者在特定语境中“读”出来的,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文本中原本就一定包含这些意蕴;另一个层面是文本形式中蕴含的,是文本与社会历史的“同构性”造成的。
我们来看第一种情况。先看“叙事”,《左传》隐公元年:“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言克;称郑伯,讥失教也。”。《春秋》中的“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乃是对一件历史事件的简洁记录。如果不联系具体历史语境,仅从字面上是看不出政治意味的。但《左传》的作者就从这一叙事中对二人的称谓以及动词的使用上看出了对郑伯和其弟段的讥刺与批评,因此这一叙事除了记录事实以外,还具有张扬一种贵族政治伦理观念的意义。这样的例子在“春秋三传”中比比皆是。所谓“春秋笔法”或“春秋书法”就是指此而言。我们再看“隐喻”,《诗经·邶风》:“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从诗的文本呈现出来的情景看,完全是一副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的恋爱图,哪里有什么政治意涵呢?然而《毛序》却说:“《静女》,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德。”这就是饱受后人,特别是现代学人质疑与嘲笑的“汉儒说诗”。在汉儒的眼中,《诗经》中那些吟咏男女情爱的作品大多为政治隐喻,不是美某公,便是刺某王。从诗人的动机看这些诗是否真的是为着“美刺”而作的呢?根据现有文献材料,这几乎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因为诸如《关雎》《汉广》《静女》这类诗歌究竟何人何时因何而作已经是难以考索的问题了,所以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的回答都是轻率的。我们只知道,汉儒如此说诗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是有其必然性的,是他们意识形态话语建构工程的一部分。在特定语境中,在今天看来那些纯粹的审美或者形式的因素都带上了明显的政治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简单地判定古人就是错的。
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情况。文本形式与社会意识形态具有某种同构性,对此只有通过具体的分析才可以看出来。中国古代诗歌的比兴手法为什么受到普遍推崇?我认为这里主要是政治因素发挥着作用。《毛诗序》有“主文而谲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之说,郑玄有君臣之间“上下相犯”“情志不通”“故作诗者以诵其美而讥其恶”之说,都是旨在说明诗歌隐晦曲折的表达方式是“君道刚严、臣道柔顺”之政治状况的产物。所以自先秦以降,历代《诗经》阐释大都是把诗三百当作政治隐喻来解读的。字面上是男女相悦之辞,如何和政治讽喻联系起来呢?这需要一个纽带,这便是“比兴”。借助于“比兴”之说,说诗者就可以大加发挥了。这是古代文学中隐喻这种修辞手法政治意涵的一种表现形式。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隐喻政治意涵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就比较隐晦了。例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这样的纯粹描写自然景物的诗句,如何具有政治意涵呢?如果我们仔细体味这两句描写寻常春景的诗句就不难发现,它从两个层面上体现出来了“自然”二字。一是其所写之景物:春天来了,池塘边的小草吐绿了,园子里的鸟鸣也变了声调。一切都自然而然,自己而然,非人力所为,乃是“悠悠天钧”的体现。二是其写法恰恰契合了其所写:都是简单朴素的大白话,没有用事用典,也没有雕琢词句,绝无“谢家池上、江淹浦畔”之弊。如此,这两句诗便是以自然之手法呈现了自然之意境,故而成为“自然”之标示。在谢灵运所处的文化语境中,“自然”至少有下列三层涵义。一是道的存在方式。《老子》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说,所谓“道法自然”可以理解为“道以自然的方式存在”或者“自然是道的存在方式”。因此自然便是道,道便是自然。体现到人世间,这种自然之道就成为一种人生理想和人格境界:安时处顺、任真自得。二是对名教伦理的超越。在两晋南朝时期,“自然”就意味着“明教”的对立面。王弼标举“名教出于自然”,可以理解为,他为了给受到普遍怀疑的儒家伦理纲常找到一个更为坚实的学理依据,从而向老庄之学中寻找思想资源。本质上是借助于道家学说来改造儒学,从而建立适合于彼时历史条件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三是表达一种现实的政治立场。王弼、郭象试图把“自然”与“明教”统合起来,体现了一种认同现实政治的立场。嵇康把二者对立起来,体现的是对司马氏统治的厌恶与拒斥的政治态度。可见在魏晋六朝的历史语境中,“自然”既有哲学的意涵,又有政治的指向,还体现出一种人生理想与人格境界。如此看来,这两句再普通不过的诗句,因为它是自然之道的表征,体现了道家的根本精神和疏离现实政治的人生旨趣,因此成为千古绝唱。
四
中国古代诗文评之评价标准的形成与社会评价系统相呼应,从而使看似纯审美意义的作品评价以隐晦的方式参与到社会意识形态的建构与维系工程之中,这同样是“形式的政治”之重要表现。在中国古代,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涵盖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也自然在文学观念上留下深深印记,于是文学的审美评价也就常常会成为等级观念的表现形式。
秦汉以后,政治上的君主官僚政体与思想上的儒家学说携手共进,相得益彰,是有着深刻的必然性的。儒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之后,其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也浸透于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的各个层面,几乎是无处不在,甚至可以说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在文学艺术的审美评价上,等级观念也同样深入其中。对诗词歌赋的形式与风格等方面的评价看上去是纯粹审美趣味的表现,不食人间烟火,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相去甚远,实际上也同样是社会等级观念的表现形式。我们不妨通过分析有代表性的现象来说明这一情况。
被称为“百代诗话之祖”的《诗品》的评价标准与六朝时期社会意识形态之间存在同构关系。这部书也就成为士族文人审美趣味的重要表征。这主要表现在下列方面:
其一,分品论诗与以品论人。士族之谓士族,最基本的条件是门第。门第有高下,士族自然也有等差。以品论人本来是汉代之“清议”的主要内容,因为这种“清议”是察举选士的重要依据,所以其人物评价的主要标准乃是品德与才能。班固《汉书》之《古今人表》把古今重要政治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等九等;魏文帝曹丕接受陈群建议以“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吏,这都为钟嵘以品论诗人提供了思想资源。自此以后,以品论人更成为一种风尚,而举凡操守、功业、才性、风度等方方面面都要分品类、别高下,这是对汉代人物品评的泛化。玄奥幽远的高层次精神活动,也成为士族文人一争高下的方式。彼时名士谈玄论道与其说为了辨明道理,弄清真相,毋宁说乃是为了争胜负、分高下。这正是士族文人独特的精神旨趣。概而言之,在魏晋六朝时期,清谈、玄学以及诗词歌赋、琴棋书画表征着多重意涵:就社会政治层面而言,它们都是士族文人精神贵族身份的确证方式,具有社会区隔的功能;就生命个体而言,它们又是士族文人自身价值自我实现的方式,具有弥补其因经学的退场而造成的精神匮乏的作用;就哲学与文学艺术发展演变而言,这又显现为一种自律性与独立性的形成,确实具有哲学思辨和审美静观的价值。社会政治伦理层面以品论人与审美层面的以品论诗有着深层的同构关系。钟嵘《诗品》看上去是纯粹的诗歌评价,但其思想底蕴却是传统的等级观念。这在《世说新语》等史籍中有大量记载。
其二,诗品的标准。钟嵘究竟以怎样的标准为诗定品级呢?如前所述,钟嵘代表了一种不同于汉代士大夫的文人趣味,其核心之点便是“吟咏情性”四个字。“吟咏情性”原是汉儒卫宏在《诗大序》里提出的说法,意指诗经作品是表达的是一种“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的民众之情感,目的是“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钟嵘在这里借用这一概念已然剥落了那种美刺讽谏的政治伦理内涵,乃是指对个体情趣与个性气质的玩味和抒写。这里的“情性”已不再是那种代表民风民俗的“集体情感”,而纯粹是文人们的个体情感了。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一部《诗品》从分品论诗的结构,到具体的评价标准都表征着士族文人的精神追求,其深层旨趣乃是这个特殊社会阶层保持其文化领导权的政治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