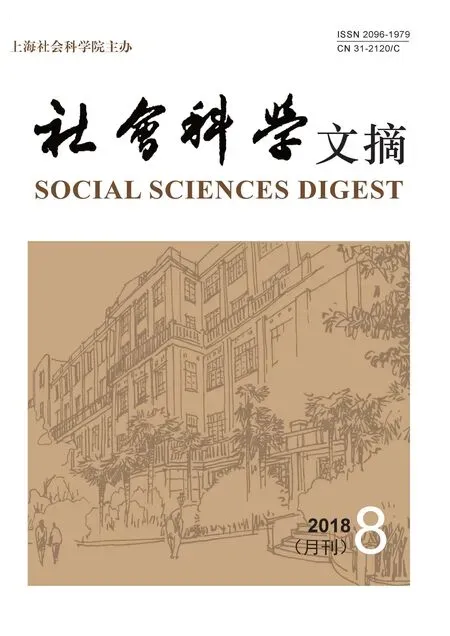论鲁迅与茅盾对文学核心价值的不同认识
鲁迅与茅盾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存在种种差异,其中一个根本性的差异是他们对文学核心价值的认识不同。这在他们的言论尤其是转向左翼文学的创作过程中有明显的表现。
一
鲁迅对文学作用的看法有过很大的变化,对文学形式的看法更是“天马行空”,但对文学核心价值的认识,却始终保持一致。他坚信,文艺是作家个性和人格的展现。文艺作品是否具有作家的个性,是否含有作家的真情实感,是文艺之所以成为文艺的基础。
五四时期,他指出“《呐喊》的来由”,是他年轻时候曾经做过的“许多梦”中“不能全忘却的一部分”,其中饱含着他 “自己的寂寞的悲哀”。“革命文学”论争时期,他又反复强调,创作“革命文学”的“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加入“左联”后,他仍然一再重申,“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
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学价值观,与他同样根深蒂固的功利主义文艺观一样,都是他衡量“文学”的基本尺度,从根本上影响着他的创作。
鲁迅晚年将主要精力放在杂文写作上,他自己的解释是因为环境的催促,认为“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瞿秋白的解释,则除了强调“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地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外,又加上了“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后来流行的文学史著作,对这个问题的解释,都是依据他们两人的观点。
这样的解释固然是很有道理的,它确能从外在社会环境的层面找出一些有说服力的依据,也符合鲁迅功利主义的文艺观。但是,如果从鲁迅创作的主观愿望和努力的内在视角,着眼于鲁迅对文学核心价值的认识和态度来看,鲁迅创作重心的转移却并非如此简单。
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
其一是鲁迅在不同的时期对美文、杂文和短篇小说三种体裁的创作有不同的侧重,但始终没有完全放弃其中任何一种体裁。早年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是《呐喊》《彷徨》《野草》和《朝花夕拾》。之后,他也并非只写“诗与政论相结合”的杂文,而是在断断续续中仍然写短篇小说《故事新编》。即使就他在20世纪30年代写的大量杂文而言,也既有继承了《坟》《热风》那样的斗争精神的“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也有延续着《野草》《朝花夕拾》那样的富含艺术精髓的美文。像《为了忘却的记念》《病后杂谈》《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我的第一个师傅》《女吊》等,其艺术水准都不在早期美文之下。
其二是鲁迅原本“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的,《呐喊》中就有取材于古代神话的《不周山》,后来事实上偏向于现代题材。对古代题材的小说创作,则几经转变。先是“决计不再写”,之后是在“不愿意想到目前”的心态下,又写了《奔月》和《眉间尺》。特别是在他生命晚期,又连续写下了《非攻》《理水》《采薇》《出关》《起死》,表现出愈来愈强烈的写作“故事新编”的冲动。
如果把这两个现象综合起来考察,则可以清楚看到,鲁迅由短篇小说、美文向杂文的转移并不彻底。而且,鲁迅创作重心的转移事实上有两个,并非一般文学史著作中所说的只有一个,即一是由短篇小说、美文向杂文的转移,二是由“现代” 题材的短篇小说向“古代”题材的短篇小说的转移。很明显,鲁迅虽由其功利主义文艺观所决定,在外界环境变得日益严峻和紧迫的时候,必然会走向匕首、投枪式的杂文,但他对小说、美文的创作却表现出相当大的留恋。这种既舍弃又有留恋、既留恋又不得不舍弃的徘徊状态,以及最终宁可向“古代”题材小说伸展也不愿回到“现代”题材的小说创作的做法,就非常清晰地表现出他对文学核心价值的独特理解和尊重。
这里,有四个层面的问题必须理清楚。
一是鲁迅的创作并非只追求功利性,也同样追求文学性。所谓“文学性”,在鲁迅的心中,既包括艺术技巧,更包括尊重文学的核心价值。当他认为自己的“真性情”与他的创作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基本一致时,他会“一发而不可收”地潜心于创作;如果不能一致,则会减少甚至暂时终止他所理解的文学创作。
二是鲁迅对小说、美文和杂文三种文学体裁所蕴含的“文学性”的理解是有区别的,他把小说和美文称之为“创作”,把杂文更多地看作是战斗的工具。1933年他出版《鲁迅自选集》时,不仅只选《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故事新编》中的作品,而且明确表示:“可以勉强称为创作的,在我至今只有这五种”。
鲁迅对小说的推崇,其实在《〈呐喊〉自序》中就有明显的表示。这篇序言一方面用大量篇幅和诗一般的语言叙述作者的身世遭遇、精神裂变和理想愿望,指出《呐喊》蕴含着他自己久久“不能全忘却”的精神和心血,一方面又反复强调他写作《呐喊》的功利性动机、目的和与此相应的情节安排。结尾时又说了这么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话:“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一件侥幸的事,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我们不能把鲁迅的这段话仅仅理解成是他一时的“谦虚”,即使从“谦虚” 的角度看,也表明他对文学创作的“诚敬”。鲁迅这种心态事实上贯穿着他创作生涯的始终,直至晚年写《〈故事新编〉序言》时,还念念不忘表达对自己的创作“从认真陷入了油滑”的不满,明确表示“油滑是创作的大敌”。
三是鲁迅创作重心的转移显得特别艰难。他清醒地认识到,像小说、美文一类的“文学创作”,更多地熔铸着作者的“真性情”。就作者来说,它形成不易,改变也很难。就文学创作来说,要恰当地将它熔铸到作品中去不容易,想彻底清除它在作品中的痕迹也非常困难。一方面,他一再表示“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所以,他或者在写作时就有“故意的隐瞒”,或者在之后出版《自选集》时,“将给读者一种‘重压之感’的作品,却特地竭力抽掉了”。另一方面,他又一再慨叹人心的隔膜,“自憾”不能透彻地“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尤其是,当他“看见了新的文学的潮流”,而又断定像他这样的作家无法写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之后,他陷入了“写新的不能,写旧的又不愿”的两难之中,只好减少甚至暂时中断小说和美文的创作。
四是鲁迅对“历史小说”的看法比较特别。他因为“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创作的《故事新编》“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形式上“也还是速写居多,不足称为‘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
如果说,他先前写作《不周山》时“从认真陷入了油滑”,主要是受其功利主义文艺观的支配,那么,当他明知“油滑是创作的大敌”,自己“决计不再写这样的小说”之后,又断断续续地接着写这样的“古代”题材小说,但又不能够“认真”去写,那就决不是仅由其功利主义文艺观所能解释得了的。其中至少还包含着他对“小说”所具有的那种难以割舍的情缘的成分,包含着他对文学创作核心价值的独特理解和尊重。因为只有不够 “诚敬”和“认真”的《故事新编》,才能最大限度地排解他的两难心态。在一定程度上既满足他文学创作的内在愿望,又可回避他的创作有可能给新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
茅盾也是文学功利主义者,但与鲁迅不同,他从来没有把作家的个性和情感看成是构成文学作品的核心因素,他念念不忘的,一是文学的社会性和时代性,二是作品的艺术技巧和艺术创新。
五四时期,他更注重文学“内容”的社会性、功利性和平民性。虽然他在讲“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时,既讲了“环境”和“时代”,也讲了“人种”和“作家的人格”,但他所说的“人种”,侧重的是“种群”而不是“种差”,他讲“作家的人格”,也并非要强调作家的个性,而是强调文学的“真”,不要“欺世盗名”。
1925年他倡导“无产阶级文学”时,虽然既注意文学的“内容”,也注意文学的“形式”,但仍然不重视作家的个性。就“内容”而言,他沿袭自己一贯的要求文学反映时代和社会的思路,希望“无产阶级作者”能够以扎实的理性分析精神而不是满足于“刺激和煽动”的态度,真实全面地反映社会生活,其核心是突出“阶级”观念,否定“个人”意识。就“形式”而言,他虽然认为“形式是技巧堆累的结果,是过去无数大天才心血的结晶”,承认“此与阶级斗争并无关系”,具有不同于“内容”的超时空性,但他的这种强调仍然不彻底。
典型的事例,是他在强调“无产阶级首先须从他的前辈学习形式的技术”时存在明显矛盾:他将文学遗产分成“健全的”和“腐烂的”两类,甚至指明应该学习哪一历史阶段的文学遗产。他说,“无产阶级如果要利用前人的成绩,极不该到近代的所谓‘新派’中间去寻找,这些变态的已经腐烂的‘艺术之花’不配作新兴阶级的精神上的滋补品的”。“无产阶级的真正的文艺的遗产,反是近代新派所詈为过时的旧派文学,例如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文学和各时代的不朽名著。为什么呢?因为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文学是资产阶级鼎盛时代的产物,是一个社会阶级的健全的心灵的产物”。
正是基于这种思维,在革命文学论争中,茅盾一方面批评一些作者“仅仅根据了一点耳食的社会科学常识或是辩证法,便自负不凡地写他们所谓富有革命情绪的‘即兴小说’”;另一方面更是猛烈地抨击一些作者或者因为注重“革命热情而忽略于文艺的本质”,或者把文艺视为“狭义的”“宣传工具”,或者自己原本就“缺乏了文艺素养”,因而使得他们的作品事实上成为“标语口号文学”。
加入“左联”后,茅盾对现实的左翼文学运动不再有那么激烈的批评,但从他正面主张的理论来看,其注重“内容”与“形式”,忽视作家个性的基本思维仍没有改变。在《〈地泉〉读后感》中,他将“一部作品在产生时必须具备”的条件简化为两个,即“社会现象全部的(非片面的)认识”和“感情地去影响读者的艺术手腕”。
茅盾不仅这么说,他的行动也证明他对作家的个性没有足够的尊重。
从茅盾的文学生涯来看,他一生中也有两次重心转移。一是由文学批评、社会批评转向文学创作;二是其创作模式由“托尔斯泰”式转向了“左拉”式。
茅盾早年热心地“鼓吹过左拉的自然主义”,但当他开始“试作小说”的时候,走的却是“经验了人生以后才来做小说”的路子。粗粗看来,这种“言行不一”的事发生在以理性和稳健著称的茅盾身上,是不可思议的。仔细分析其“言”其“行”,则可发现所谓“言行不一”其实只是表象,骨子里两者是相通的。
其一,茅盾早年所看重的是“社会运动”而不是“文学”。他自己说得很清楚:“我对于文学并不是那样的忠心不贰。那时候,我的职业使我接近文学,而我的内心的趣味和别的许多朋友——祝福这些朋友的灵魂——则引我接近社会运动。”从他早年的工作经历看,其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所占的时间和精力,呈明显的上升趋势,一度是全身心地投入。即便就其早年的著译工作而言,也有相当一部分不属于“文学”的范畴。
其二,茅盾是在大革命失败,并对自己曾全身心投入的社会政治运动产生了“极端的悲观”“幻灭”和“消沉”的情形下开始文学创作的。这给他的《蚀》三部曲带来了浓厚的个性色彩和幻灭绝望的情绪。但就茅盾的主观意愿而言,他的社会政治运动优先意识并没有变。他的创作,也并不是想成就什么文学事业,而是想为后人留下一点历史见证。他的写作原则是:“不把个人的主观混进去,并且要使《幻灭》和《动摇》中的人物对于革命的感应是合于当时的客观情形。”因此,茅盾开始文学创作时虽然走的是“托尔斯泰”的路子,但在具体创作中贯彻的却仍然是“左拉的自然主义”。
其三,在茅盾的创作生涯中,“经验了人生以后才来做小说”的模式事实上只维持了大约两年的时间,他很快就转向了“因为要做小说,才去经验人生”的路。
《蚀》三部曲的面世,在给文坛带来震惊,充分展示了茅盾的文学天才外,也给他带来了众多的批评。其中,核心的批评意见,是指责他的作品里主要人物“全是些没落的……前途只是悲观,他所表现的只是小布尔乔亚在革命失败后的幻灭情绪而已”。
起初,茅盾对这种指责是否定的,后来则小心翼翼地将书中人物的思想情绪与“小说的立场”区分开来,再后来,则是接受批评,不再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悲观消沉,而是写他们的转变和进步了。茅盾非要抑制住自己深切的个性感受,按照“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要求创作,以表明自己的不落后,就不得不为此“去经验人生”,结果是造成《虹》《路》《三人行》等作品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
茅盾此时并非没有鲁迅那种“写新的不能,写旧的又不愿”的苦恼。他与鲁迅一样,也曾一度转入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写下了《豹子头林冲》《石碣》《大泽乡》等作品。但与鲁迅不一样的是,茅盾没有长久地徘徊在这种苦恼中,他很快就进入了新的写作状态,创作出《子夜》《农村三部曲》等作品。这些作品都是“先从一个社会科学的命题开始”,再“处理人物,构造故事”。
茅盾从写《虹》时“欲为中国近十年之壮剧,留一印痕”,到完成“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子夜》,只有短短的三年多时间。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自己创作模式的大幅度转换,其奥秘就在于他不注重文学创作中作家的个性。《蚀》三部曲其实是茅盾整个创作生涯中的一个例外,是他不屑于文学创作却又抑制不住创作冲动时的一个“矛盾”的产品。当他确定以文学创作作为自己常态的生活方式时,转向“因为要做小说,才去经验人生”的路是其必然的归宿。